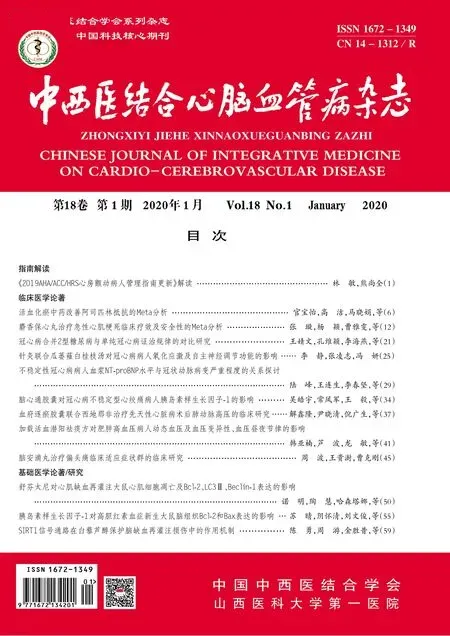脑出血急性期两型分法探讨及客观化研究进展
脑出血发病率占脑卒中的10%~30%,常见病因主要是高血压[1],此类脑出血约占各类出血的50%。脑出血的其他原因还包括微动脉瘤、动静脉畸形、脑淀粉样血管病、凝血障碍疾病等。脑出血属中医“中风病”范畴,多由素体虚弱、劳倦内伤、忧思恼怒、嗜食厚味等使人体阴阳失衡、气血逆乱而发病。对于本病的治疗,现代医学主要采用保守治疗(对症治疗)和手术治疗,脑出血手术治疗的远期疗效和保守治疗无显著性差异,中医则本着整体观念进行个体化辨证论治,但辨证治疗因缺乏统一标准,亦未体现出明显优势。因此,需探析相关实验室指标与中医辨证分型的关系,总结出中医辨证分型与其之间的规律,简化分型,制订具有可计量性、可重复性及可行性高的脑出血急性期辨证分型模式,推广能被广大中医、西医接受的可复制的中西医结合治疗脑出血急性期的理论,最大限度挽救病人生命及降低脑血管病的死亡率、致残率。参考近年发表的有关中风证候学与客观化关系的文章,从证候学、实验室指标、分子生物学等多个层面对证型与相关指标进行了梳理,以期为脑出血急性期辨证分型的客观化提供实验室参考依据,并根据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多年来对脑出血辨证分型的研究,进行了两型分法探析。
1 脑出血急性期两型分法的探析
1994 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脑病急症科研协作组《中风病辨证诊断标准(试行)》将中风病分为风证、火热证、痰证、血瘀证、气虚证、阴虚阳亢证6个基本证候要素,2006年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科专业委员在《脑梗死和脑出血中西医结合诊断标准(试行)》中将中风病分为风痰瘀阻证、痰热腑实证、痰湿蒙神证、气虚血瘀证和阴虚风动证5型。目前从临床可操作性来看,上述分型过于复杂,不利于在综合性医院推广,从实验室研究来看,众多研究表明多个证型之间没有明显的统计学差异。
郑肇良等[2]从中医辨证分型分组分析脑出血病人血液流变学变化,发现风、火、痰3证间两两比较,全血黏度(高切、中切、低切)、血浆黏度、全血还原黏度(高切、中切、低切)、红细胞比容和纤维蛋白原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2]。杜凯音等[3]研究发现,脑出血气虚血瘀组、阴虚风动组及风痰瘀血、痹阻脉络组病人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水平明显高于肝阳暴亢组、风火上扰组及痰热腑实、风痰上扰组(P<0.01),但痰热腑实、风痰上扰组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上述研究结果明确显示出辨证分型的多样化、相关标准不统一导致疗效的不可重复性,更揭示了不结合脑内病理变化的辨证分型导致的实验研究缺陷。故脑出血的简化分型有必要统一认识,统一分型,以获得客观的临床实效。
著名医家张景岳提出了八纲辨证法,认为所有疾病皆存在“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的区别。在此八纲中,阴阳又可总领其余六纲,表证、热证、实证属于阳证范畴,里证、虚证、寒证属于阴证范畴。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高利教授在长期临床实践基础上结合六型分法曾将其简化为四型,即痰热证、痰湿证、气虚证和阴虚证,经推广虽出现一些进展,但多数西医医生仍不易掌握。为使广大中西医临床医生能对分型分法达成基本共识,高利教授根据中医八纲辨证阴阳为总纲理论,结合以往对脑梗死急性期实验室基因聚类研究结果,将急性期脑出血仅分为“热证”和“非热证”两型。之所以不称为“阴类证”和“阳类证”,是因为确有不具备显著的阴、阳特点的部分临床病例。用此分型方法在北京多次进行多中心推广收到良好效果。高利教授为推行中西医结合简化分型治疗方法,牵头组织业内专家多次研究探讨形成了《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中西医结合诊疗专家共识》并发表于中国全科医学杂志[4]。王永炎院士主审的《中风脑病诊疗全书》收录了该分型方法亦可作为重要证据[5]。
2 脑出血证型与相关指标的实验研究
2.1 分子生物学 目前国内研究者对脑出血分型的生物学指标研究集中于血浆内皮素(ET)、降钙素相关基因肽(CGRP)、血清缺血修饰白蛋白(IMA)、基质金属蛋白酶-9(MMP-9)、人核苷二磷酸激酶A(NDKA)、泛素融合降解蛋白(UFDP)等方面。
血浆ET、CGRP是血管活性类物质,ET及CGRP的含量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脑组织的血液循环状况和组织损伤程度。有研究选择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住院病人80例,分析其中医证型与ET及CGRP的相关性,发现在出血性中风急性期不同证型组中血浆ET、CGRP水平均有不同程度升高,以风痰瘀阻、痰热腑实组升高最为显著,提示ET及CGRP水平对于诊断此两型中风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6]。血清IMA是人血白蛋白在缺血缺氧、酸中毒、自由基损伤等因素的影响下,氨基末端发生一系列化学性改变而形成的蛋白,它在缺血开始后数分钟内即可升高,已有IMA与急性脑血管病的相关研究发现,脑梗死及脑出血病人血清IMA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7-8]。黄经纬等[9]研究发现,脑出血不同证型中,风痰火亢证、风火上扰证、痰热腑实证IMA含量明显高于风痰瘀阻证、痰湿蒙神证,提示血清IMA可作为脑出血急性期辨证参考指标。泛素化-蛋白酶体系统(UPS)与多种神经退行性疾病以及脑卒中等的发病有关,UFDP是UPS的重要组成成分,Han 等[10]认为UFDP对诊断中风病痰热证具有一定价值,可作为该证的生物学指标。王亚云等[11]研究发现中风病第14天时血清NDKA水平与气虚证评分具有高度相关性,对评价中风病气虚证的轻重程度具有一定意义。有研究显示MMP-9的异常表达可能是促使血肿周围形成水肿的重要因素[12]。钟学文等[13]收集42例中风急性期住院病人,检测发病72 h和14 d的MMP-9含量,并进行中医证候评分,结果表明痰证、火证成立组MMP-9数值较不成立组明显升高,提示MMP-9可作为脑出血急性期痰证、火证诊断的参考指标。另有研究表明,高血压性脑出血急性期肝阳化风证与恢复期阴虚风动证存在蛋白表达差异,其中肌动蛋白与纤维蛋白原a链前体可能与脑出血肝阳化风证、阴虚风证动的发展密切相关[14]。
2.2 炎性指标 脑出血后继发性的损害与炎症反应、自由基损伤密切相关[15-16]。可溶性细胞间黏附分子-1(ICAM-1)在炎症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17],其主要功能是介导白细胞与血管内皮细胞之间的黏附。有研究发现,急性脑出血白细胞黏附、机体氧化应激增强,病人血清ICAM-1、丙二醛(MDA)明显升高,以痰热腑实证最为明显[18]。C反应蛋白(CRP)是反映急性期炎症反应敏感性标志物,急性脑出血后CRP促进脑水肿形成,加重脑损伤[19]。仝淼等[20]将102例高血压性脑出血病人分为风火上扰、痰热腑实、风痰火亢、风痰瘀阻、阴虚风动5型,各证型间血清CRP水平和神经功能缺损积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CRP水平及神经功能缺损积分由高到低分别为:风火上扰证>风痰火亢证>痰热腑实证>阴虚风动证>风痰瘀阻证。故CRP可以作为脑出血辨证分型重要的参考依据。
2.3 免疫指标 Tarkowski等[21]研究发现,脑出血病人T淋巴细胞免疫功能下降的程度与脑出血的部位及病情严重程度具有相关性。脑出血病人体液免疫功能被激活,可能与应激导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改变有关。陈红芳等[22]观察了115例脑出血病人多项体液免疫指标的变化,结果显示不同脑出血量病人之间体液免疫功能有明显差异,大量脑出血病人CD19+-CD25+、CD19-- CD25-B淋巴细胞百分比及IgG、C3含量较中等量、少量脑出血病人明显增高,中等量脑出血病人IgG、C3较少量脑出血病人明显增高,脑出血恢复期CD19+-CD25+CD19-- CD25-B淋巴细胞百分比则较急性期明显下降,总淋巴细胞数IgA、IgG、IgM、C3也有所降低。提示脑出血后其体液免疫功能被激活,脑出血量越多,体液免疫功能被激活的程度就越明显,疾病越严重。故血浆免疫检测可以作为脑出血辨证的参考指标。
2.4 血液流变学变化 脑出血病人血液流变学呈浓、黏、聚、凝状态。有研究者对血液流变学与中医辨证分型做了相关研究,郭友林等[23]将脑出血分为肝阳上亢、气虚血瘀、痰热腑实、痰浊阻络4型,发现气虚血瘀型血浆血栓素B2(TXB2)高于正常对照组,痰热腑实型和痰浊阻络型血浆TXB2含量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气虚血瘀证型和肝阳上亢型血清纤维蛋白原降解物(FDP)均明显高于正常对照组。提示凝血可以作为脑出血辨证分型的参考指标。
3 小 结
一些分子生物学指标、炎性指标、免疫指标、凝血指标可以为脑出血辨证分型提供客观化依据,但是许多相关指标在辨证分型中并没有体现出显著的差异性,是否提示辨证分型过于复杂或有所重复,由此可见,脑出血的简化分型仍有必要,结合对古代著名医家分型的认识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多年研究及临床疗效结果,认为脑出血简化分为热证和非热证两型较为适宜,尤其是对西医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