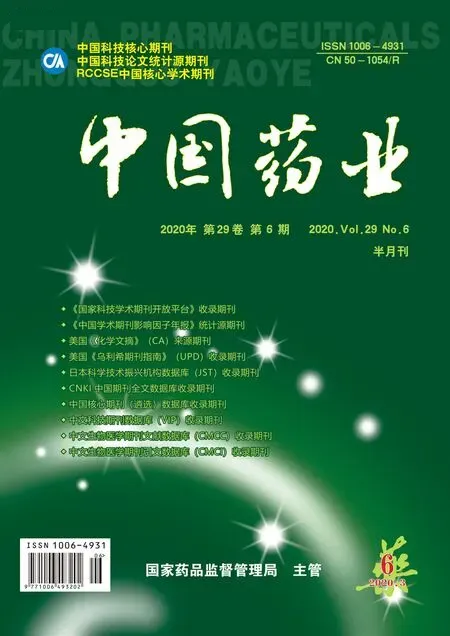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药物研发现状*
陈勇川
(陆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庆 400038)
2019 年年12 月以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中国大地。2020 年1 月30 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新冠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1]。随着疫情的进展,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国家卫健委)自2020 年1 月15 日首次发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版)以来,到2020 年3 月4 日发布了最新版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2],其密度之高,更新之快,史无前例,其中涉及的药物治疗相关内容也在不断更新。各医疗机构和有关企业也积极开展了针对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临床研究,根据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的登记数据显示[3],已有234 个有关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临床研究进行了登记注册,除去流行病学调研性质的非药物研究外,涉及药物治疗的研究高达126 个。在如此众多的临床研究项目中,除了“瑞德西韦”药物临床试验项目已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CDE)正式申请,并按2005 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特别审批程序》进行审批纳入国家应急通道外,其余项目均是按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科研项目形式进行的登记注册。这些研究在此次疫情暴发的特殊大背景下“争先恐后”地上马,希望能为战胜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希望。
1 新冠肺炎药物治疗的研究现状
1.1 临床治疗现状
根据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推荐的药物治疗方案,主要的药物治疗分为抗病毒治疗、抗菌(细菌和真菌)治疗和针对危重症患者的特殊治疗三大类。其中,明确给出的抗病毒药物包括α-干扰素、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利巴韦林、磷酸氯喹和阿比多尔;强调抗菌药物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尤其是广谱抗菌药物的联合使用,并未给出具体的药物品种;对于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可考虑使用糖皮质激素和血必净。同时,基于中医中药的特点,也给出了推荐方剂或中成药品种,包括近年来国家合理用药管控中因疗效不确切或不良反应被列入了重点管控的品种,在本次疫情暴发时却又进入了推荐治疗方案。
1.2 临床研究现状
针对本次新冠肺炎疫情,WHO 于2020 年1 月28 日也发布了《疑似2019 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严重急性呼吸道感染的临床管理》临时指导文件,其中针对抗SARS-CoV-2 的特效治疗和临床研究明确指出[4],对于SARS-CoV-2 感染疑似或确诊病例,目前尚无基于随机对照试验证据的特效抗病毒治疗方法,未获批的治疗方案只能在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的临床试验中或遵守《未注册干预措施在监控之下紧急使用的框架》的前提下应用,且需严格监控。可见,针对一个新病毒引起的疾病,在无任何试验数据和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对有效的药物治疗手段是持谨慎态度的。
1.3 特殊人群临床治疗
针对孕妇患者,应注意采取兼顾妊娠生理变化的治疗方案,使用无研究结果支持的试验性治疗方案时应基于母亲潜在获益和胎儿安全性,按个体权衡利弊。孕产妇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在各孕龄期均有可能发生,且妊娠期妇女对呼吸系统病毒性感染的炎性应激反应明显增高,病情进展迅速,尤其是妊娠中晚期,易发展为重症。2020 年2 月5 日,武汉也出现了1 例母亲感染SARSCoV-2 的新生儿,出生30 h 后咽拭子SARS-CoV-2核酸检测阳性,胸部X 线摄片检查提示有肺部感染。SARS-CoV-2 是否通过母婴垂直传播目前尚不明确,考虑有感染风险,产妇未痊愈前,不建议母乳喂养,以防止病毒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中也新增了对孕产妇患者的治疗考虑要点,特别强调:应考虑妊娠周数,尽可能选择对胎儿影响较小的药物,以及是否终止妊娠后再进行治疗等问题,并知情告知。
2 重点推荐治疗药物的研究情况
2.1 α-干扰素
α-干扰素可增强宿主的免疫应答,在体外和动物模型都可抑制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冠状病毒(SARS-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冠状病毒(MERS-CoV)的复制,而冠状病毒可抑制宿主体内天然的免疫反应,主要通过减弱干扰素的免疫应答和延迟诱导促炎性细胞因子的产生而实现[5-6]。但诊疗方案中指出,雾化吸入α-干扰素仅作为抗新冠病毒的试用治疗措施,用以提高呼吸道黏膜病毒的清除效果,起到预防病毒的作用。机体被病毒入侵时,在α-干扰素的刺激下,未被感染的细胞就会分泌一些抗病毒蛋白去杀死病毒或抑制病毒的复制。可理解为干扰素为广谱抗病毒药物,它不仅对SARS-CoV-2 有效,对很多其他病毒都有效,且其预防效果只针对未被感染的人群或轻症患者。有文献报道称,预防性使用干扰素或早期暴露后即用干扰素,可发挥最佳作用[7]。对于已被病毒感染且病毒已在体内大量复制的危重症患者,理论上干扰素不具有治疗价值,这也是仅推荐雾化吸入给药的另一个原因。
2.2 洛匹那韦/利托那韦
洛匹那韦(lopinavir)/利托那韦(ritonavir)为广谱抗病毒药物,于2001 年由欧盟首先批准上市,我国于2013 年批准进口,用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治疗,商品名为克力芝。洛匹那韦可阻止HIV 的Gag-Pol 聚蛋白分裂,利托那韦通过作用于病毒的天冬氨酰蛋白酶而抑制HIV 蛋白酶的活性,使其无法对Gag-Pol 多聚酶的前体蛋白进行剪切,两者的联合使用,导致病毒复制最终产生的是不具再生能力的非成熟形态的HIV 颗粒,从而达到抑制病毒复制的目的[8-9]。2016 年,沙特阿拉伯启动了一项临床试验(NCT02845843),研究了洛匹那韦/利托那韦联合干扰素-β1b 治疗MERS-CoV 感染,但至今仍无数据可供参考[10]。考虑到洛匹那韦/利托那韦与SARS-CoV 也有明确的结合位点,且SARS-CoV -2 与SARS-CoV和MERS-CoV 同属冠状病毒,序列同源性较高,故诊疗方案推荐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用于抗SARS-CoV -2的治疗。
但需特别注意,洛匹那韦/利托那韦是肝脏P450同工酶CYP3A 的抑制剂,与主要经CYP3A 代谢的药物联用时,可能导致联用药物的血药浓度升高,从而增加不良反应。重症患者大概率会使用抗菌药物,如使用伏立康唑预防或治疗真菌感染,由于利托那韦是CYP3A4的强抑制剂,与伏立康唑联用可降低伏立康唑的血药浓度。同时,由于伏立康唑本身也是CYP3A4 抑制剂,其又会影响经此酶代谢的抗病毒药物的血药浓度,增加不良反应。有部分患者在联用莫西沙星时出现了心动过缓,需特别关注并及时处理,必要时停药。
2.3 利巴韦林
利巴韦林(ribavirin)是一种合成的核苷类抗病毒药物,具有广谱抗病毒活性,对DNA 和RNA 病毒均具有抑制作用,于1972 年被研制出来后已在临床广泛使用多年,但仍缺乏令人信服的临床数据证实其治疗价值。
SARS 期间,有使用利巴韦林治疗效果较好的报道[11]。7 例SARS 患者予口服奥司他韦、广谱抗菌药物和利巴韦林静脉给药治疗,利巴韦林负荷剂量为2 g,随后每天给予1 g、每6 h1 次,第4 天开始给予500 mg、每8 h 1 次。结果5 例在5 d 内好转,1 例死亡,1 例在机械通气支持下症状改善;5 例好转的患者比另外2 例患者接受了更早、更积极的支持治疗。基于此,试行第五版诊疗方案中曾提出过利巴韦林4 g 日剂量的用药方案,但在一片争议声中又迅速修订,降低了推荐用量,调整为静脉使用每次500 mg,每日2 ~3 次。
继SARS 后,在MERS 的治疗中,利巴韦林再次进行了临床试验,结果无功而返,其对MERS 治疗的队列分析和回顾性分析均未获得数据支持[12-14]。同时,SARS 动物模型研究表明,单用利巴韦林效果并不好。在小鼠模型中,利巴韦林单用甚至可能延长或增强病毒在肺部的复制;在MERS 细胞模型中,利巴韦林只有在浓度很高时才会对病毒有抑制作用[15-16]。在新冠肺炎的治疗过程中,需专业医务人员严格把握其适应证,切不可“滥用”。
大剂量利巴韦林的使用,药源性损害较突出,特别是血液系统反应,包括急性贫血、溶血性贫血、再生障碍性贫血、粒细胞缺乏,甚至有因全身出血死亡的病例。同时,利巴韦林在特殊人群的使用也应注意禁忌证,如WHO 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均严格限制了儿童的应用,而我国儿童过度使用现象较普遍。利巴韦林妊娠期可透过胎盘,故妊娠期禁用。老年患者更易发生溶血性贫血,且因肾功能下降而易蓄积,故不推荐使用。
2.4 磷酸氯喹
2020 年2 月15 日,科技部生物中心张新民主任在新闻发布会上首次提到了磷酸氯喹。他表示,体外试验显示,磷酸氯喹对SARS-CoV -2 有良好的抑制作用,目前正在北京、广东等地的10 多家医院开展临床研究,累计入组患者超过100 例。2020 年2 月18 日召开的广东省抗疫情况新闻通气会上,钟南山院士也对该药潜在的治疗价值表示了谨慎乐观。
氯喹(chloroquine)是一种广泛应用于抗疟疾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药物,具有潜在的广谱抗病毒作用[17]。氯喹可通过上调病毒与细胞融合所需的体内pH 值及抑制细胞受体的糖基化来阻断病毒感染,对包括SARS-CoV 等在内的病毒复制有抑制作用。有研究发现,氯喹在细胞水平上具有抗SARS-CoV 活性,磷酸氯喹能抑制SARS-CoV 诱导的Vero E6 细胞系中病毒复制,50%抑制浓度[IC50=(8.8±1.2)μmol/L]接近急性疟疾治疗期间所达到的氯喹血浆浓度,明显低于50%细胞抑制浓度[CC50=(261.3±14.5)μmol/L],提示氯喹对该细胞系应用的安全性[18-20]。还有研究表明,氯喹对SARS-CoV -2 感染有效,除了有抗病毒活性外,还有免疫调节活性,可在体内协同增强其抗病毒作用[21]。
氯喹在临床已使用70 多年,究竟能否对SARSCoV -2 感染有效,拭目以待。但使用过程中需注意,该药成人致死剂量为2 ~4 g,而且是急性致死,因此治疗过程中应严密观察,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时及时处理。考虑到药物的潜在毒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将磷酸氯喹使用剂量由统一的每次500 mg、每日2 次、疗程7 d 修改为:18 ~65 岁成人,体质量大于50 kg 者,每次500 mg,每日2 次,疗程7 d;体质量小于50 kg 者,第1 ~2 天每次500 mg,每日2 次,第3 ~7 天每次500 mg,每日1 次。
2.5 阿比多尔
阿比多尔(arbidol,Umifenovir)是由前苏联药物化学研究中心研制开发的一种合成广谱抗病毒药物,我国批准的适应证为治疗由A 型和B 型流感病毒等引起的上呼吸道感染。阿比多尔通过抑制流感病毒脂膜与宿主细胞的融合而阻断病毒的复制,体外细胞培养试验显示,可直接抑制甲型、乙型流感病毒的复制,体内动物试验显示可降低流感病毒感染小鼠的死亡率,尚有干扰素诱导和免疫调节作用[22-23]。李兰娟团队的研究数据显示,与对照组比较,阿比多尔在10 ~30 μmol/L 浓度下能有效抑制SARS-CoV -2 达60 倍,且显著抑制病毒对细胞的病变效应。但从药物作用的分子机制上看,阿比多尔作用的病毒蛋白(hemagglutinin 和neuraminidase)在SARS-CoV -2 上并不存在,且报道中的有效浓度(10 ~30 μmol/L)换算成人体实际用药量有可能是个天文数字,副作用是否会远远超过其药效,还需要更多的数据证实。
2.6 抗菌药物
对于抗菌药物的使用,诊疗方案中仅有一句话:“避免盲目或不恰当使用抗菌药物。”可以预见,在临床实践中,抗菌药物的使用不可避免,特别是危重症患者,前期有可能使用激素治疗而存在免疫抑制情况。对于入住重症监护室(ICU)并行有创机械通气的患者,继发细菌或真菌感染的概率较大。
特别是重症患者,若存在合并其他病原体感染时,经验性治疗应以覆盖社区来源的常见病原体为主,入院后继发医院获得性肺炎(HAP)/呼吸机相关性肺炎(VAP)的抗菌药物选择应有区别。在抗菌药物临床应用指导原则大框架下,强调应用合理性,同时把握好以下原则:对于血流动力学不稳定者,建议强力降阶梯治疗,选择碳青霉烯类、万古霉素等;若存在医院获得性细菌性肺炎,应特别关注有无多重耐药菌感染,酌情选择抗多重耐药菌的药物;对于危重症患者,还需关注侵袭性肺真菌感染,酌情经验性或目标性抗真菌治疗,优先选择药物相互作用少的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力争在经验性用药前,尽早留取相应合格标本送病原学检测,以尽早明确病原菌和药物敏感性试验结果,并以此调整抗菌药物治疗方案。
2.7 糖皮质激素
糖皮质激素治疗重症感染的价值一直存在巨大争议。尽管《柳叶刀》2020 年2 月7 日在线发表了1 篇述评[24],指出“临床证据不支持糖皮质激素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但临床实践中医师倾向于对危重症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也是不争的事实。针对SARS 患者治疗效果的荟萃分析显示,大剂量激素冲击治疗对于患者生存并无益处[25]。WHO 关于MERS 患者的治疗指南也不主张对病毒性肺炎或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使用大剂量全身糖皮质激素[26]。同时,也有研究支持在冠状病毒感染的治疗中使用低、中等剂量的糖皮质激素[27]。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确实存在继发感染、远期并发症和排毒时间延长等风险,但对重症患者而言,大量炎性因子导致的肺损伤又可能会造成疾病快速进展。
鉴于证据的不确定性和临床需求的紧迫性,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的有关专家编写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糖皮质激素使用的建议》的专家共识[28],对新冠肺炎患者使用糖皮质激素提出了4 条基本原则:1)使用前需仔细权衡利弊;2)慎用,应主要用于重症患者;3)对于SARS-CoV -2 感染前因各种原因已存在低氧血症或慢性疾病已规律使用糖皮质激素的患者,使用应更加谨慎;4)剂量和疗程,中小剂量[≤0.5 ~1.0 mg/(kg·d)甲泼尼龙或同等剂量]和短程(≤7 d)。在本次疫情防控中,基于谨慎态度合理使用糖皮质激素,应该不会再出现当年SARS 治疗期间糖皮质激素带来的严重后遗症问题。
3 “争先恐后”的临床研究
3.1 登记注册项目
截至2020 年2 月23 日,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登记注册了234 个有关新冠病毒的临床研究,按研究性质进行简单分类可以发现,其中涉及药物治疗的研究有126 个,占到所有研究数量的一半以上[3],其中包括瑞德西韦、利托那韦、ASC09/利托那韦、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等本身针对SARS-CoV -2 设计开发的抗病毒药物;其他试验药物涉及中西药物结合治疗、中医药防治等辅助治疗,包括连花清瘟胶囊/颗粒、痰热清注射液、血必净注射液、糖皮质激素、利巴韦林+干扰素α-1b、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干扰素-α2b 等药物或组合药物。其中,不乏在近几年来国家临床合理用药管控中因疗效不确切或不良反应被列入了重点管控的品种,但本次疫情下却又“粉墨登场”进入临床研究。按临床研究注册信息显示,参与项目的具体医疗机构遍布全国,主要集中在四川、湖南、北京、石家庄、湖北、河南、河北、大连、武汉、广州、重庆等地。
3.2 项目研究内容
部分拟开展的临床研究主要是基于已相对成熟的广谱抗病毒药物进行的适应证扩大临床验证性试验,如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克力芝)+恩曲他滨(FTC)/丙酚替诺福韦(TAF)用于治疗新冠肺炎的临床研究,一项评价洛匹那韦/利托那韦和干扰素-α2b 联合治疗SARS-CoV -2 感染住院患者疗效和安全性的随机、开放、空白对照研究,其设计思路均借鉴了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期望通过联合用药从多靶点、多通道对病毒进行抑制,从而产生治疗效果。
3.3 瑞德西韦研究项目
作为本次疫情中唯一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而开展的临床试验品种,瑞德西韦(remdesivir)“万众瞩目”。瑞德西韦于2012 年正式进入吉利德公司的新药研发管线,体外试验显示出广谱抗病毒能力,包括丙型肝炎病毒、登革热病毒、甲型流感病毒、SARS-CoV、诺如病毒等。2018 年11 月,瑞德西韦却在为应对埃博拉疫情所发起的临床试验中却“铩羽而归”,吉利德公司仅发表了其可在体外抑制SARS 病毒和MERS 病毒的相关数据。2020 年1 月25 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抗SARS-CoV-2感染联合应急攻关团队筛选出了包括瑞德西韦在内的30 种具有治疗潜力的药物。1 月28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联合宣布,发现了包括瑞德西韦在内的3 种药物在细胞水平上对SARS-CoV-2 有较好的抑制作用。2 月4 日,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在《Cell Research》杂志在线发表了研究论文[29],发现瑞德西韦与核苷酸类似物的假定抗病毒机制一致,且在猴的肾细胞Vero E6 中针对SARS-CoV-2 的EC90 值为1.76 μmol/L,表明在非人灵长类有可能达到其治疗浓度。
但真正让瑞德西韦走向“神坛”的,还是2020 年1 月31 日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记录美国首例新冠肺炎患者治疗过程的1 篇论文[30]。该患者2020 年1 月15 日结束武汉探亲返回美国后的第2 天,就开始咳嗽和出现发热症状,第3 天症状未缓解,遂至医院就诊。基于患者的胸部X 线摄片结果显示出非典型性肺炎的特征,以及持续高烧,且多个部位样本出现SARSCoV-2 阳性结果,住院治疗第7 天使用了瑞德西韦静脉注射给药。用该药后的第2 天,病情得到了极大改善,体温从39.4 ℃降至37.3 ℃,血氧饱和度恢复至94% ~96%,而后病情持续好转,同时未观察到相关不良反应。但仔细阅读该病例的诊治细节,并不能确定疾病的最终好转与瑞德西韦直接相关。文中提到患者仅治疗1 d 病情就大幅度缓解,在瑞德西韦用药开始前病毒载量就已开始下降,这些现象都使得该药与病情缓解之间的关系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经我国药监部门批准,吉利德公司启动了瑞德西韦治疗SARS-CoV-2 感染患者的Ⅲ期临床研究。2020年2 月5 日下午,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王辰院士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宣布启动瑞德西韦治疗SARS-CoV-2 感染研究。研究分两项,第一项入组轻、中症患者308 例,评估瑞德西韦用于确诊感染病毒、已住院但未表现出显著临床症状的治疗效果;另一项入组血氧饱和度下降的重症患者453 例,评估瑞德西韦用于出现较严重临床症状的确诊病例的疗效。研究执行严格的随机双盲试验,并使用安慰剂对照。试验组患者在标准治疗方案基础上接受首剂瑞德西韦200 mg 静脉滴注,随后静脉滴注100 mg/d,连用9 d;对照组患者接受标准治疗方案和相同剂量安慰剂治疗。两组临床试验分别以临床恢复时间、临床缓解时间作为主要终点,其中临床恢复定义为体温、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恢复正常,咳嗽缓解,且维持超过72 h;临床改善定义为患者状态评分较入院时降低2 分。重症患者的临床终点治疗为病死率的改善。主要结果指标为从开始治疗到发热、呼吸频率、血氧饱和度转为正常和咳嗽缓解,持续至少72 h,即使用瑞德西韦后连续72 h 能证明临床症状都消失才有效。
3.4 其他临床科研项目
除了瑞德西韦外,其他临床试验几乎均为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科研项目。此类项目大多存在以下问题[31]:立题依据不充分,缺乏必要的研究背景;研究基础不充分,缺乏必要的临床前试验数据;研究条件不充分,缺乏必要的质量保证体系。
比如,对于一个抗病毒的药物,它究竟针对病毒的哪种特定蛋白、阻断病毒复制的哪个环节,其作用机理应该清楚,在此基础上再考虑临床的治疗价值才有研究意义。而大量的作用机制不明或从分子设计上已证明对SARS-CoV-2 无效的药物仍在登记注册、进行临床试验。还有一些项目仅基于粗糙的体外细胞试验观察到对SARS -CoV -2 有抑制作用,但其报道的有效浓度往往是几十甚至几百微摩尔,其在体内要达到此浓度几乎不可能。
对于几十个拟开展的中药临床试验,其中不乏国家药品监管部门连续多年发布的《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中反复提及的品种,如双黄连、热毒宁注射液等。
对于临床治疗使用价值本身就存在重大分歧的糖皮质激素类药物,也有不少登记注册项目、拟开展试验,这类研究究竟是基于患者受益的考虑,还是基于“利用”本次疫情难得的“海量受试者”机会进行的科学验证,值得深思。而利用“脐带血”等新概念来治疗SARSCoV-2 感染,其本身就不是治疗病毒感染的常规手段。
另外,从临床试验方案设计的科学性来讲,为了获得可评估的数据,不管是针对轻症患者还是重症患者,统计学上每个试验至少需要近1 000 例患者参与研究[32]。可以粗略估计,如此众多抗疫药物的临床试验,如果真要在当下疫情防控极其紧张的临床一线开展,那就要有更多的患者、更多的医护人员参与到临床试验的特殊流程中来,这在当下一线抗疫工作量极大的情况下,其操作性存在极大问题。可以预见,过多过滥的临床试验只会给临床一线人员增加巨大的负担,也会用掉宝贵的医疗资源和研究资源。可以大胆预测,随着本次疫情的结束,绝大部分登记注册的临床试验项目都将“无疾而终”,草草收场。
4 结语
综上所述,针对新冠肺炎,目前仍无特效抗病毒药物,所有的药物选择都是基于既往SARS 和MERS 或其他新型流感病毒的治疗经验,积极的对症支持治疗仍是救治的关键。国家卫健委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所面临的紧急状态,短时间内组织各方面专业人士制订的若干版本诊疗方案,对于治疗新冠肺炎仅是一个阶段性的临时方案,其中所涉及药物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仍有待在临床治疗和研究中进一步证实。
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我国的药物研发科研工作者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药物研发、疫苗研制工作,但基于药物作用靶点、作用机制的活性筛选仍是必须要认真做的基础工作,包括:使用标准的试验来测试现有广谱抗病毒药物的活性;在化学图书馆或数据库广泛筛选可能有活性的化合物;基于各个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和生物物理学特点,重新开发新的特异性药物。我们也应看到,随着疫情的发展,不少商业企业也“趁火打劫”夸大产品应用优势,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广大新药研发单位和研究者应该严格按照2020 年2 月25 日国务院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科研攻关组《关于规范医疗机构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药物治疗临床研究的通知》要求[33],在临床研究过程中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做好工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疫情阻击战中获得的研究信息必须服务疫情防控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