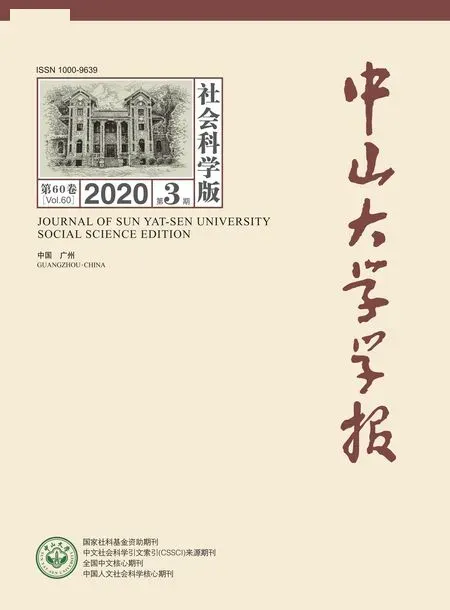心的两面:论孟子的心灵观念*
刘 伟
引言:心灵是如何成为一个问题的?
在中国思想史上,心灵问题成为一个显题进入思想话语,自孟子开始(1)牟宗三曾说:“孔子《论语》中未曾有‘心’字。‘心’的概念是首先由孟子创出的。”见氏著《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67页。。从逻辑上说,心灵成为一个问题,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人们意识到,心灵和除其之外的身体应予以区别对待,即意识到身心之区别;第二,人们意识到这一区分的深刻意义,相应地,赋予从身之整体中析出的心灵以基础地位,建构思想体系。第二点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将在后面几节中陆续展开;而身心之区别成为问题,则需要稍加说明。
孟子对于心灵的论说,从“身/心”的区分开始,这一点充分体现在他关于“小体”和“大体”的区分上。公都子曾疑惑,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人格高尚,值得景仰,而有的人则庸庸碌碌甚至人格卑琐呢?孟子的回答是:“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当公都子进一步追问“大体”“小体”时,孟子回答说: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告子上》(2)本文述及与引用《孟子》篇章均直接以篇名标示,特此说明。)
孟子区分了心灵和其他感官,心灵是“大体”,听从“大体”即为大人;心灵之外的其他感官——以“耳目之官”为代表,属于“小体”,听任“小体”屈服于物欲则为小人(3)朱子云:“耳司听,目司视,各有所职而不能思,是以蔽于外物。既不能思而蔽于外物,则亦一物而已。又以外物交于此物,其引之而去不难矣。心则能思,而以思为职。凡事物之来,心得其职,则得其理,而物不能蔽;失其职,则不得其理,而物来蔽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与我者,而心为大。若能有以立之,则事无不思,而耳目之欲不能夺之矣,此所以为大人也。”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42页。。
和区分“身/心”相应的则是划分身与心的功能:知属心,能属身。当然这不意味着,在孟子之前没有这种区分。孔子就说过,“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只不过作为日常语言,孔子并未赋予这种区分以特别的思想意谓。孟子则不然,他曾明确说: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思虑谋划,一般被认为是心灵的功能。而孟子则有意识地区分思和虑:前者是心灵本然的功能,后者则是经验中具体的谋划计算。在这一表述中,孟子强调的重点是良知——知爱亲和知敬兄都是良知,一种心灵本有的能力,不需要后天习得的计度和谋划。良能指什么,孟子没有明说,大概不是论说的重点而省略了。
“能”指什么?我们仍可以从孟子的其他表述中找到线索。在与齐宣王探讨“保民而王”的可能性时,孟子区分了“不为”和“不能”,并认为齐宣王恩及禽兽而“不能”保民,是“不为”而非“不能”。齐宣王问二者之别,孟子举例说:
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梁惠王上》)
同样指人的行为,在这一文本中,“为”强调主观意愿(心的功能),“能”侧重行为能力(身的功能)。同样,荀子也认为,人的行为包含两个条件:主观意图和行为能力,即所谓“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正名》)。
由上可知,“知”和“能”的区分,源于身和心的区分。这种区分,在早期经典中很常见,如《易传》所云“乾以易知,坤以简能”,其背后都预设了“身/心”二元的结构。只是区分身心何以必要,需要进一步探究。本文试图基于孟子思想言说回答这一问题,不过在这之前,需要交待孟子借以思考心灵的一个关键性区分——
一、庸与斯须:恒常的与情境性的
“庸”为恒常之义,此不烦多说,如“中庸”“为是不用而寓诸庸”(《庄子·齐物论》)皆此义。“斯须”则意为即时性的、片刻性的,如“礼乐不可斯须去身”(《礼记·乐记》),可引申为基于某一特定情境的即时的行为和表现。如“知”和“能”一样,二者之区分乃是早期日常语言中常见的用法,而孟子将这一习见的区分用于思考心灵功能,于后世影响至巨。
孟子有意识地区别“庸”和“斯须”,体现在《告子上》所记录的他和孟季子的“隔空对话”之中。面对孟子的弟子公都子,孟季子公开质疑孟子的“义内”说:如果“义内”体现为自觉地尊敬兄长,那么,如何理解在乡饮酒礼场合按齿序敬酒,即乡人长于兄长则“先酌乡人”。孟子的回答是:“庸敬在兄,斯须之敬在乡人。”作为类比,孟子还举了另外一个例子,用以说明“庸”与“斯须”之别:
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
寻常时候,卑幼敬尊长是常理,如子弟之于叔父。可当祭祀祖先时,为尸者代表祖先,“虽子弟为之,然敬之当如祖考也”(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334页。。不论乡饮酒礼还是祭礼,都是暂时的,属于寻常之外的特殊时刻。其特殊性表现在营造了特定的礼仪情境,进而规定了特殊的“位”,乡人和为尸者便处于特殊的“位”上。如果说,尊敬叔父和兄长是一种恒常的心灵取向和道德情感,那么敬“乡人”和“为尸者”则只是基于特定情境的情感表达。
区别“庸”和“斯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体现在孟子关于心灵的一系列思考之中。在另外一场孟子和墨者夷之的“隔空对话”中,孟子质疑夷之,作为墨者本应薄葬却厚葬其亲。夷之则答以“爱无差等,施由亲始”,回避“薄葬”而将问题引向儒墨争论的另外一个焦点:爱是否有差等?作为墨者,夷之当然信奉“爱无差等”(“兼爱”),并援引儒者所信奉的《尚书》中的话——“如保赤子”——为自己辩护。对此,孟子回答说:
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滕文公上》)
从字面上看,孟子并未使用“庸”和“斯须”这一组概念,但这一区分却隐含在道理言说之中。“赤子匍匐将入井”并非寻常事件,不论何人见此情此景,“斯须”之间必然激发内心不可遏抑的恻隐之情。而寻常时,对于“兄之子”的爱必然甚于“邻之赤子”的爱。
亲爱双亲和尊敬兄长指向的仁义,作为心灵“欲求”的对象,是心灵永恒的方向。孟子经常用“志”(心之所之)来表达心灵恒常的方向。所以,当有人问何为“尚志”,孟子回答“仁义而已”(《尽心上》)。志作为恒常的心灵所向,揭示了心灵的本然状态;本心之所向,表明本心及其所向之间是一种“欲求”关系。
与本心相对的是心之所发,而心之所发则源于具体情境的触动和激发。“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是今人置身于“见”孺子入井这一情境中而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齐宣王以羊易牛,是其置身于“见”牛之“觳觫”这一情境中而生“不忍”之心(《梁惠王上》)。这种在具体情境中的心之所发,后世称为“情”(5)朱子解释“恻隐之心”为“仁之端”时有云:“端,绪也。因其情之发,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见,犹有物在中而绪见于外也。”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39页。。而人心感物而有情这一关于心灵的基本共识,大概导源于此。
二、思:一种心灵的欲求
牟宗三以“仁义内在,性由心显”八字为孟学纲领(6)见刘述先《孟子心性论的再反思》一文,收录于[美]江文思、[美]安乐哲编,梁溪译:《孟子心性之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194页。,乃颠扑不破之言。对于孟子来说,心、性问题似乎难以彻底剥离开来,欲讨论心灵问题,人性论总是绕不过去的。后世论孟子思想宗旨,常以“性善论”概括之。而“性善”二字,在整部《孟子》中只出现两次:一次出现在《滕文公上》,一次出现在《告子上》。而后者所在的章节可谓讨论孟子心性问题最佳的文本。
该文本是一段孟子和公都子的对话。公都子依次列举了关于人性的三种不同看法:一是,告子的“性无善无不善”;二是,或人所云“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三是,或人所云“有性善,有性不善”。之后进一步问孟子:“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从这一诘问可知,孟子关于人性的说法被公都子总结为“性善”。孟子并未否认,且进一步解释说:
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
之所以说该文本是讨论孟子心性论最佳的文本,乃是因为这一段文字涉及了情、才、四端、仁、义、礼、智、思等对于心性论来说最重要的概念。反复推敲这些概念,仔细绎读这一文本,便可勾勒出心性论之基本轮廓。
其一,由“可以为善”“若夫为不善”这一类说法可知,孟子主要回应的是或人所云“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这一说法。其中“为”字,尤其值得注意。告子曾经以“杞柳为桮棬”喻“以人性为仁义”,遭到孟子的反驳。“为”乃人为,其基本意象是制作器具,告子就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加工一件器具,从器具的角度看,需要材质和人的目的;从人的角度看,需要源于心灵的目的(“知”),和源于身体能克服材质惯性的力量(“能”)。善的本义是合乎目的,所谓“可欲之谓善”是也。与塑造合乎目的的器具不同,人之“为善”是规范自身,这一过程同样包括源自心灵的目的或意愿(“知”)和源自身体的能力(“能”)。前者属“心”,后者属“身”,即文中的“才”(7)朱子注云:“才,犹材质,人之能也。”牟宗三认为:“才字即表示人之足够为善之能力,即孟子所谓‘良能’,由仁义之心而发者也,非是一般之才能。”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 334页。又见牟宗三:《圆善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第18页。。“为不善”非“不为善”,说到底就是不合乎目的,关键取决于心,和身所代表的能力无关,所以“非才之罪也”。同样在《告子上》中,孟子举例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为善的能力,正常的成年人都具备,区别只在于“存心”还是“陷溺其心”而已。
其二,“乃若其情”的“情”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好、恶、喜、怒、哀、乐(《荀子·正名》),当训为“实”,指内在本有、有待扩充的潜能。同样是在《告子上》中,孟子以“牛山之木”为喻:牛山之上树木曾经很茂盛(“美”),由于过度砍伐而变得荒芜;此过程中,树木非无萌蘖的能力,但屡遭放牧,最后变成了荒山秃岭。人同样如此:人心也能够萌蘖出善的根芽,但被平日行为不断地戕害,人最终变成了“禽兽”。孟子说,人见牛山光秃秃的,以为“未尝有材焉者,岂山之性也哉”;相应地,人见自甘于“禽兽”之人,以为“未尝有才焉者,岂人之情也哉”。“充实之为美”,所谓“美”,乃是指潜能充分实现的状态。牛山之木的“美”,根源于牛山的孳生能力,若未遭遇砍伐和放牧,树木生长的潜能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同样,自甘堕落的人并非没有为善的能力(“才”),而是戕害心灵的缘故,如果充分实现人心本有的潜能,必然能“长”出完美的“仁义之心”。
其三,仁义礼智之心是本心潜能的充分实现,而作为“四端”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则为有待扩充的潜能。在《公孙丑上》中,孟子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端是一个有动力的开端,只要获得合适的外在条件,即可实现自身的目的,好像种子一样。仁义礼智是“四端”的实现,而“四端”本身有实现其目的的动力,所以仁义礼智不是外力塑造的结果,而是人自身本有,此即“固有”之义。
其四,“四端”本有而未自然而然实现为仁义礼智之心,是因为没有发挥心灵“思”的能力。人一旦“思”,就能够获得,所以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由此可见,“思”本质上是一种欲求,只不过不是身体的欲求,而是心灵的欲求。其欲求的对象为人“固有”的仁义礼智,求之于自身,所以才能“求则得之”。孟子所说“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尽心上》),正可与此相印证。由此可得出孟子关于心灵官能的一个重要看法:心灵最本然的官能是“思”,思是一种欲求,欲求植根于自身的仁义礼智。唯其欲求之对象根于自身,才可能“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思”是一种心灵的欲求,这一理解显然是类比身体的欲求而来。在《告子上》篇中,孟子为了说明人的心灵有相同的欲求,举例说:
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
与之类似,孟子为了区分性、命,曾说过:“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尽心下》)欲求身外之物未必一定能够获得,就是“得之有命”。嘴巴欲求美味,耳朵欲求美声,眼睛欲求美色;或许还可加上鼻子欲求美好的气味,身体欲求安逸,这些感官欲求,统统“得之有命”,所以孟子说“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相比于身,心灵的欲求有什么不同呢?孟子断言:心灵欲求的是理义。理义和仁义礼智,大概是同一内容的不同表达。要言之,不论理义还是仁义礼智都在自身之中,不假外求。所以如上文所引,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
然而,何为“理义”?理,就是道。在《万章上》中,孟子说伊尹“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此处“其义也”“其道也”即“理义”。又《公孙丑上》中,孟子说自己的“浩然之气”和心中的“义与道”相配,否则就会气馁。不论是“理义”还是道义,其涵义都可以归结为“义”。理义的根基在心中,就是孟子一直坚持的“义内”说。
“义”的用法有很多,不过,这些用法大都基于一个基本意项——获得自己应得之物,引申而来。例如,当“非其义也,非其道也”时,伊尹“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万章上》);又孟子说过“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尽心上》),此类例证很多,乃先秦诸子共享的基本观念,不烦罗列(8)笔者《义利之辨发微》(未刊稿)一文,曾对“义”的这一意项有比较充分的说明。。这意味着,“义”的源初含义基于“欲求/获得”这一最基本的生活经验。义是合理地获得。如果像孟子一样,将“义”理解为一种本然的道德情感(“义内”),那么“义”便指合理的欲求(9)欲求,是孟子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却极容易被忽视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孟子所理解的人与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欲求—获得”关系,所以,孟子说眼睛是欲求美色的,而非辨别(认知)颜色;耳朵是欲求美声,而非辨别声音(声调),其他感官亦然。。身体欲求外物,心灵欲求的是合理的欲求。过分的欲望违悖心灵中的理义,进而伤害心灵,所以“养心莫善于寡欲”(《尽心上》)。
如果欲求体现的是人和物之间的根本性的关联,那么可以说,心中本有的“理义”就是一种秩序感。说到底,性善论的实质是秩序感在人心中,所以,基于人心可以推出整个世界秩序来。
三、一体与感通:论“恻隐之心”
有一次,齐宣王见到仆役牵一头待宰杀的牛走过,齐宣王感受到了牛的恐惧,心生不忍,便命令换一头羊来宰杀。国人嘲笑宣王吝啬,孟子则认为宣王此举乃是基于不忍之心,理由是:“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梁惠王上》)所谓“仁术”,是指“仁”的发生机制。孟子认定宣王并非吝啬,而是出于真切的“不忍”,因为宣王“见牛未见羊”。“见”“闻”意味着在场,因在场而切己相关,符合我们的日常经验。当在书本上看到一个悲伤的故事,又或者有人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个人的不幸,我们或许会“同情”不幸者,但这种“同情”与现场目睹产生的强烈的“不忍之心”似有不同。孟子所说“仁术”切中了这一区别:是否当下切己相关。
齐宣王不关心羊的死活却不忍牛的“觳觫”,说明想象某一情境和置身某一情境激起的心理感受有本质的不同。这一不同直接指向了自然身体和所处情境之间的相关性。只不过这种相关性的本质为何,需要进一步澄清。回到“恻隐之心”这一话题,按《公孙丑上》云:“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如朱子所说,恻隐之心是一种情,一种置身于“孺子将入于井”这一特殊情境中而自然生发出来的情。孟子试图用不容已的“恻隐之心”,说明每个人都有“不忍人之心”。所以,“恻隐之心”作为一种基于特殊情境的“斯须”之情,是心灵的另一种功能。
为什么要用“恻隐”来形容见孺子入井那一刹那的心理状态呢?“恻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需要特别认真对待的问题。
齐宣王见牛之“觳觫”而生不忍之心,孟子将这一心理解释为“隐其无罪而就死地”。此“隐”即“恻隐”的“隐”,赵岐和朱子都训为疼痛(10)东汉赵岐《孟子章句》注云:“隐,痛也。” 清人焦循引王念孙的说法解释为何隐可以训为痛:“《逸周书·谥法解》云‘隐哀之方也’,《檀弓》云‘拜稽颡,哀戚之至隐也’,隐与通,、哀一声之转,哀之转为,犹薆之转为隐矣。”(清)焦循:《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83页。另见(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08、239页。。此外,“恻隐”的恻字,《说文》也训为痛(11)(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22页。,说明“恻隐之心”表征的是“心痛”的感觉。需要指出的是,痛和心痛描述的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痛可以是头、脚、眼睛等任何一个身体部位的生理性疼痛;但恻隐之心表征的心痛不是心脏的疼痛,而是一种整体而非部分的、心理而非生理的感受。心痛和痛心是现代流行用语,很难说我们的心痛和古典语境中用恻隐表征的心痛是同一种经验,为了了解古典的心痛究竟是怎样一种痛,我们需要借助古典的用例。
在古典语境里,恻隐有时候也表达为“隐恻”或“恻怛”。依据古礼,亲人辞世后,孝子“恻怛之心,痛疾之意,伤肾乾肝焦肺”(《礼记·问丧》),这意味着至亲辞世带来的哀痛,是“恻隐”最真切、最极致的体现。相应地,服三年之丧,乃是称情立文,显示孝子“至痛极也”,因为“创钜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迟”(《礼记·三年问》)。“创钜”“痛甚”等说法透露出,在古典语境中,对“恻隐”的理解乃是基于身体疼痛这一经验。而生理痛感总是指心灵感受到身体某一部分的疼痛。以此类比,“恻隐之心”的发生,前提便是孺子是与我一体共在的一部分。我感受到孺子入井而产生“恻隐之心”,就和我的心灵感受到我身体某一部分受伤而产生痛感一样。由孺子而推至他人,由人而及物,即是后世论说“万物一体”的一般模式。事实上,孟子确实说过“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爱”是怜惜,对于物的“爱”,就像怜惜自己的身体一样。所以孟子说:“人之于身也,兼所爱。兼所爱,则兼所养也。无尺寸之肤不爱焉,则无尺寸之肤不养也。”(《告子上》)(12)阳明论证“万物一体”的思路和孟子一般无二,详见《大学问》。对物的感觉是心灵对于身体感觉的延伸,相应地,他者和物都是次一级的身体,本质上与我一体相关(13)陈立胜曾将“恻隐之心”理解为人在世生存的基本情调,这一基本情调揭示了万物一体共在。见氏著《恻隐之心:“同感”、“同情”与“在世基调”》,《哲学研究》2011年第12期。。
恻隐之心基于身体疼痛这一经验,而痛感揭示了“心—身”一体,感觉相通就是一体相关。这解释了“见孺子入井”的我和孺子何以相关,也解释了宣王以羊易牛的内在逻辑。一言以蔽之,相关性源于一体的感受。
顺着这一思路便可以理解,为什么“入井”的是孺子?诉诸日常经验,相比于一个成年人不慎坠井,孺子入井对我们心灵的冲击更为强烈。何以如此?和正常的成年人相比,孺子不具备成熟的理智,可能根本不知道“井”为何物,更遑论坠井的危险。孟子特别喜欢以小孩子为例,来说明他的思想主张。在与墨者夷之的论辩中,孟子表示,任何人都应该对“匍匐将入井”(《滕文公上》)的赤子施以援手,因为小孩子没有任何过错。不论是“赤子”的提法还是“匍匐”这一前行动作,都说明孟子设想的孺子年幼到根本意识不到坠井的危险。坠井这件事情与之无关,不是他/她自主选择的结果。在这个思想试验里,孟子强调将要坠井的不谙危险的小孩子,目的恰恰是要排除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与“孺子”相对,“今人”是一个拥有成熟理智的人,至少要能够理解坠井这件事情意味着什么。如此一来,“今人”和“孺子”才可以类比为心灵和身体的关系:心灵具备成熟的理智,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无理智可言。如果将孺子替换为一个拥有正常理智的成年人,恻隐之心便成了一个拥有成熟理智的自我对于另一个拥有成熟理智的他者的同情。
要言之,“万物一体”的“体”被设想为一个庞大的身躯,身躯的同一性基于身体中有一颗能够感通整体的心灵。
四、心的两面:基于心灵的秩序想象
至此,可以试着总结孟子心灵观念的两重意蕴:一是,本心欲求义理,说明秩序感根于心灵;二是,心灵感通外物,揭示万物一体相关。二者不可化约。更重要的是,区分心灵功能的两重性,在孟子那里似有明确的现实考量,而不只是完成其道德形上学的建构而已。
这要从孟子区分圣和王说起。在经学话语体系中,“圣王”是一个词,指称历史上为数不多德位合一的人。孟子则有意识地区分圣与王,在《滕文公下》中,出现了《孟子》文本中唯一一次圣、王连用: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这段话是孟子为自己“距杨墨”辩护的一段说辞。起因是公都子质疑孟子——“外人皆称夫子好辩”,孟子列举了大禹治水、周公兼夷狄、孔子作《春秋》,并认为自己“距杨墨”和三位圣人之事有同样的意义。文中“圣王不作”的提法,极容易让读者误解“圣王”是一个复合词,事实上应该在圣和王之间微顿:因圣不作,而“处士横议”(即“杨墨之言盈天下”),伦常崩解;因王不作,而“诸侯放恣”,政治失序。孟子以“圣人之徒”自任,认为自己继承三“圣”事业,即便“圣人”(非“圣王”亦非“王”)复生,也不会反对其“距杨墨”——“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距杨墨”与圣人事业一脉相承。在孟子看来,杨、墨之学是“无父无君”之学,目无伦常,悖弃圣人之道。如前文所言,“性善”是指心灵欲求自身本有的理义,欲求仁义礼智。而仁义礼智尤其是仁义,又分别对应着父子、君臣两种最根本的伦理关系。所以,“性善”所谓的秩序感内在于人心,更直接的表达是伦理内在于人心。心灵欲求伦理,而圣人是“人伦之至”。孟子“道性善”时“言必称尧舜”,乃是因为圣人充分实现了心中本有的理义。同时,人皆可为尧舜,用颜子的话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孟子以“圣人之徒”自任,要表达的无非是:他能充分实现欲求理义这一心灵功能。
以先圣之道自任的士人和孟子是同一类人,因为士人无条件地拥有“恒心”;与之不同,一般人的“恒心”是有条件的: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梁惠王上》)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
这两处表述和前文所引《告子上》“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相参看,别有意味。士人的“恒心”表现在不论身处何种境况,都能从其“大体”(心灵),此为“大人”;而一般民众只有在充盈的物质条件下才可能保有和充实本有的善端,养其身后才能养其心。一旦出现危及生存的物资匮乏,就可能从其“小体”(身体的欲望),欲求本不应有的事物,此为不义。一个英明的统治者,应该给民众足以满足身体欲求的“恒产”,“申之以孝悌之义”而后才能有“恒心”。由此可见,士人“有恒心”的“心”,指的便是心灵欲求理义的一面。如果将心灵欲求自身的理义视为一种秩序感,那么实现了心灵这一功能的士人,就是道义和现实秩序的担纲者。
以上是士人的职能,这一职能从心灵欲求理义这一面引申而来。下面则要审视一下心灵感通能力在现实政治秩序中的体现。
齐宣王曾问孟子,拥有什么样的德行就可以为王?孟子的回答是:“保民而王。”(《梁惠王上》)此外,孟子和墨者夷之的论辩中,曾涉及类似的表述——“若保赤子”,文本具体内容如下:
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谓也?之则以为爱无差等,施由亲始。”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为人之亲其兄之子为若亲其邻之赤子乎?彼有取尔也。赤子匍匐将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滕文公上》)
“若保赤子”一语出自《尚书·康诰》。夷之据此试图说明儒者所信奉的《尚书》也支持“爱无差等”这一原则。孟子则反驳道,只有在孺子将“入井”的关头,才能激发出他人无差别的恻隐之心;在寻常状态下,对兄之子与邻人之子的爱,肯定有别。又是一个孺子入井的案例。而需要注意的是:此处“若保赤子”是一个比喻,比喻君王对于百姓的怜惜(“爱”)。
按这一线索,不难发现孟子论“恻隐之心”的几章有着相同的论说目的。涉及“恻隐之心”的案例,除上文“若保赤子”外,还包括(甲)《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和(乙)《梁惠王上》“以羊易牛”,如上文所论,此处不再赘引原文。
关于(甲),学者谈论“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一章,往往陷于孟子设计的这一激发“恻隐之心”的案例,却忽视了谈“恻隐之心”的言说目的。按文本所示,孟子以“乍见孺子入井”必然激发人的“恻隐之心”来说明:第一,人都有“不忍人之心”,自然包括君王;第二,君王有“不忍人之心”就可以行“不忍人之政”。该章结尾处孟子强调说“有是四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道出了其言说的根本意图。
关于(乙),孟子主动提及齐宣王“以羊易牛”,目的是要说明有不忍牛觳觫之心,便“足以王矣”。
由此可见,孟子提出“恻隐之心”,最直接的目的是论证有此心即可为王。“恻隐之心”揭示一体感,扩充此一体感即可为王。这无异于说,王的职能乃是凝聚民众,形成共同体生活。这是对于王的品质和职能的全新理解,而不同于理想中的圣王,这大概也是孟子区分圣和王的原因。
基于这一前提——对于王的品质和职能的全新理解,才能更恰切地理解孟子和齐宣王关于音乐的对话。按《梁惠王下》记载,孟子得知齐王喜欢音乐,认为推此心即可为王。面对孟子直白的追问,齐王直言自己喜欢今乐而非古乐,可能会让孟子失望。孟子则进一步补充说,推好乐之心可以为王,无关乎古今雅俗,理由是:
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龠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
孟子剔除了音乐的内容,保留其“与民同乐”这一基本形式,只要能“与民同乐”就可以为王,哪怕喜好的是世俗之乐。问题是,什么是“与民同乐”呢?当孟子问“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时,宣王回答“不若与人”;孟子更进一步问“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宣王答以“不若与众”。这一问答,极容易让人误解“与民同乐”是共同处于一个可以带来欢乐的场景中,比如一起听音乐会。为什么说这是一种误解呢?孟子说,如果“与民同乐”会产生这一效果——百姓听到王的钟鼓之声,“欣欣然有喜色”,这不是因为共享了音乐,而是得知王健康无病。当王“与民同乐”时,民众则乐王之乐,即看到王“乐”时,其内心也处于“乐”的状态之中。此正《梁惠王下》中所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所以朱子注云:“与民同乐者,推好乐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14)(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214页。百姓“乐”的并不是王欣赏的音乐,而是王的内心因听音乐而产生的快乐。
在孟子之前的古典语境里,音乐与德性密切相关,只有圣王之乐“尽善尽美”,所以圣人才能“制礼作乐”。齐宣王因好世俗之乐而羞赧,大概是这个原因。孟子对于“王”的想象,似乎放弃了对“尽善尽美”的要求,只保留其塑造共同生活这一基本职能。这其中关键是“与民同乐”所体现的与民众“一体”相关的生存感受。这“一体”的想象,基于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相互感通。
和“与民同乐”相似,在孟子看来,文王的苑囿方七十里,与民共享,所以民众乐见其成(《梁惠王下》)。滕国蕞尔小邦,介于齐楚之间,危如累卵,孟子认为滕文公唯有与民同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梁惠王下》)。此外,齐王说自己像公刘、古公一样好货、好色,在孟子看来也无所谓,只要“与百姓同之”即可(《梁惠王上》)。这其中的逻辑,和上文不论世俗之乐还是古乐,只要“与民同乐”即可为王,如出一辙。
综上,在王与民众一体相关的想象之中,王被想象为心灵,而民众被想象为身体的各个部分。“心—身”一体,象征着共同生活。后来荀子所谓“君,群也”,更直白地表达了这个意思。因此,孟子心灵观念的双重意蕴最终指向了从心灵欲求理义而来的士人(圣人)作为道义和现实秩序的担纲者的职能,与心灵感通外物而来的王与民众“一体”从而塑造共同生活的职能,具有清晰明确的现实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