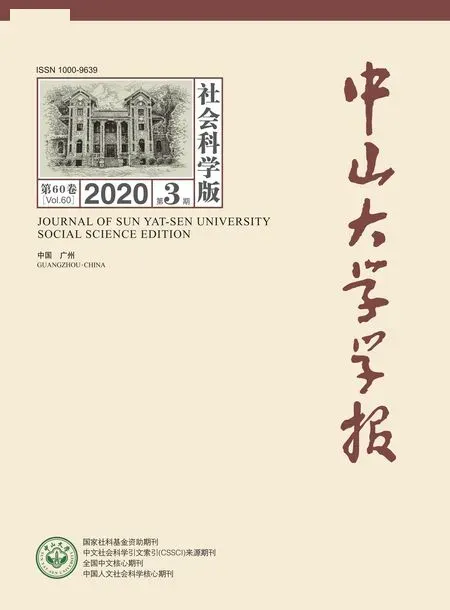召回被放逐的抒情*
——从1940年代穆旦的两篇诗论翻译谈起
王 岫 庐
一、作为翻译者的诗人穆旦
穆旦(1918—1977), 原名查良铮,祖籍浙江省海宁市,出生于天津,现代主义诗人、翻译家。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诗坛,诗人穆旦是一个令人瞩目的存在。袁可嘉在《诗的新方向》中曾将穆旦看作“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1)袁可嘉:《诗的新方向》,《论新诗现代化》,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221页。。1953年初穆旦从美国归国后,任教于南开大学外文系。从1953到1958年,他几乎全身心投入翻译,以本名“查良铮”翻译出版了普希金、雪莱、济慈、布莱克、拜伦等人的诗集及季靡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别林斯基论文学》等文学理论著作。
回溯中国新诗史,许多诗人都曾经从事过翻译,也从翻译中得到过重要的滋养,但这些诗人,如卞之琳、戴望舒、冯至等,大多在创作和翻译上同时推进。穆旦的特别之处在于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并且由于其诗歌署名穆旦,译著署名查良铮,学界长期以来将“穆旦”与“查良铮”分别对应“诗人”与“翻译家”这两个不同的身份。谈到1950年代查良铮的翻译,王佐良曾感叹“诗人穆旦终于成为翻译家查良铮,这当中是有曲折的,但也许不是一个坏的归宿”(2)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页。。王家新更直白地指出穆旦这一转型“甚至具有了‘幸存’的意义”,认为穆旦从诗人转变为翻译家,是“为了精神的存活,为了呼吸,为了寄托他对诗歌的爱,为了获得他作为一个诗人的曲折的自我实现”(3)王家新:《穆旦:翻译作为幸存》,《江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7页。。在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诗人放弃创作走向翻译,以间接转述的文学表达,获得隐晦曲折的自我实现,多少给人一些委屈的感觉。正如周珏良的感叹:“穆旦译诗的成就,使我们觉得可喜,但又有点觉得可悲。如果穆旦能把译诗的精力和才能都放在写诗上,那我们获得的又将是什么——如果? ”(4)周珏良:《穆旦的诗和译诗》,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29页。
诗人穆旦的翻译生涯并不是到了1950年代才突然以“查良铮”的身份开始的,他做翻译也并不完全出于时代造成的创作局限与无奈。穆旦在大学里就曾经翻译过诗歌(5)闻一多《致赵俪生(1940/05/26)》中提及穆旦在校期间曾尝试翻译诗歌,见《闻一多全集》第12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1—362页。,1940年代初也以“穆旦”的署名发表过若干翻译作品(6)除了本文讨论的穆旦诗论翻译以外,四十年代以“穆旦”的名字发表的翻译作品,还有一部分是诗人从缅甸战场回国以后,辗转于昆明、重庆等地,作为国际宣传处职员及重庆新闻学院学员期间翻译的一些新闻时论。。长期以来,学界对诗人穆旦早期的翻译活动关注不多,主要是因为穆旦早期翻译作品并未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穆旦译文集》(7)穆旦:《穆旦译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以及李方编写的《穆旦著译集目》(8)李方编:《穆旦著译集目》,北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等资料。易彬对穆旦研究的史料梳理颇有贡献,他注意到,穆旦1940年代曾在《大公报》发表过两篇诗论翻译,并翻译了台·路易士的长诗《对死的密语》和泰戈尔的诗歌《献诗》。易彬指出,1940年代穆旦已经“兼有诗人和翻译者两种身份”(9)易彬:《“穆旦”:作为翻译者的一面》,《现代中文学刊》2010年第2期,第58—59页。,他的翻译与其留校任教期间的社会身份、文化位置以及写作境遇有关。易彬着力解释了诗人穆旦翻译的背景和动机,但并未充分探讨其翻译活动的影响和意义。
2010年第2 辑《新诗评论》中“穆旦专辑”部分,收录了李怡整理的两篇穆旦诗论翻译佚文:《诗的晦涩》和《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其中,《诗的晦涩》(“Obscurity”)译自路易·麦克尼斯《近代诗》(Louis Macneice:ModernPoet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一书第九章。穆旦1940年11月在昆明译完,1941年2月开始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学生界”分11期连载。《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the Death of a Classicism” )译自麦可·罗勃兹《诗的批评》(Michael Roberts:CritiqueofPoetry. Jonathan Cape. 1934)一书第十六章。穆旦1941年4月8日译完, 1941年11月20日香港《大公报》“文艺”分3期连载。值得注意的是,穆旦1940年代初的这两篇诗论翻译,是诗人早年在全力投入创作的情形下主动发起的,与后来1950年代特定的政治历史语境中(10)在40年代与50年代之交的社会政治转折中,新中国文学在政治上的“一体化”局面逐步形成。详见洪子诚:《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96年第2期,第60—75页;谢冕:《文学的纪念(1949—1999)》,《文学评论》1999年第4期,第5—15页;张健:《新中国文学史》第一卷,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3页。,作为翻译家的查良铮对英美浪漫派、现代派诗歌的译介,不可同日而语。前者受到政治语境的影响和制约要小一些,更多反映穆旦本人作为一个诗人,对现代诗歌的理论反省,同时也是对自己诗歌观念的一次整理。李怡认为,穆旦的诗论翻译“是研究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文献,它们有助于我们深入把握这些中国诗人的‘现代化’追求背后的丰富的西方诗学资源”(11)李怡:《认识“新诗现代化”的重要文献——关于穆旦翻译的两篇西方现代诗论》,《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29—231页。。
事实上,翻译不只是一种对原文本的忠实“再现”(representation),也是一种意味深长的“改写”(rewriting)和“操纵”(manipulation)(12)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穆旦的诗论翻译不但让我们了解诗人的西学资源,在更重要的意义上,也体现了诗人本人的文化立场和诗学诉求。本文将对这两篇诗论翻译的选材、策略、传递的观念进行一次多维度的探究,并且结合当时的文学场域(literary field)分析这两篇诗论翻译背后的史学意义,希望在一定程度上还原穆旦翻译活动的历史背景,同时也为理解穆旦诗艺和诗学观的发展,尤其是“新的抒情”观的建构,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二、穆旦诗论的译本分析
(一)翻译选材
路易·麦克尼斯(1907—1963)、麦可·罗勃兹(1902—1948)以及穆旦翻译过其诗歌的台·路易士(1904—1972)都是“奥登一代”(the Auden Generation)或“三十年代诗人群”(the Thirties Generation)的成员。这个群体以奥登(1907—1973)为中心,批判地继承了从叶芝、庞德直到艾略特的诗歌传统。
关于穆旦诗歌的西方滋养,学界有相当深入的探究。袁可嘉曾谈到三四十年代,昆明西南联大校园里,穆旦等青年诗人受到“西方现代派诗人里尔克、艾略特和奥登等人的熏陶”(13)袁可嘉:《西方现代派诗与九叶诗人》,《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第37页。。穆旦的好友王佐良则更明确地表示,这些学子们“更喜欢奥登”,因为“他(奥登)在政治上不同于艾略特,是一个左派,曾在西班牙内战战场上开过救护车,还来过中国抗日战场,写下了若干首颇令我们心折的十四行诗”(14)王佐良:《穆旦:由来与归宿》,杜运燮、袁可嘉、周与良编:《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怀念诗人、翻译家穆旦》,第10页。。从诗歌表现技艺上看,奥登与艾略特是亲近的,但是两者在政治上有深刻的分歧。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艾略特提出两个最重要的主张:一是历史感,即“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集中后所发生的新东西”;二是非个性化,即“诗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15)Eliot, T. S,“Traditional and Individual Talent”,In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1932, p.10.。对应的诗学策略之一,是对现实材料持审慎的观照态度,将互相矛盾的材料并置,营造出“优雅而不安”(elegantly unsettling)的悖反张力,从而打开“多重不确定性”(several layers of uncertainty)(16)Gray, Piers,TS, Eliot’s Intellectual and Poetic Development 1909-1920, Brighton, Sussex: The Harvester Press,1982,p.56.。艾略特审视的现实,在时空上更为宏阔和延展,但这一全景式的现实却并非以整体方式呈现,而是以“碎片化”的手法,通过并置、拼接、叠加,相互交叉渗透又同时相互解构抵消,让个人情绪、现实片段、历史传统都化为支离破碎的残片。这种碎片化、客体化的描写,恰如其分地呈现了现代社会的各种衰落矛盾的败像,并随之产生沉默主义的、自我抑制的立场。奥登继承了艾略特的艺术表现手法,但其诗歌理想却主张积极的政治参与和道德选择。这一点,在奥登一代的诗歌及文论中均有体现。麦克尼斯的《诗的晦涩》批判了欧洲特别是法国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反思了英美诗歌中自叶芝、庞德、艾略特到奥登的写作传统。这篇文章把“晦涩”从诗歌技巧的层面,上升到主题和政治的意义上来讨论,对神秘、复杂的语言修辞和中立、疏离的写作态度提出批评。麦可·罗勃兹的《一个古典主义者死去》,表面在谈论奥古斯都时代的古典诗人,实际上18世纪所强调的“自我克制和平和的心境”(self-mastery and equipoise)、“憩静和智能的秩序”(the serenity and intellectual order)以及“隐居中静默的华彩”(the silent grandeur of retreat)(17)Roberts, Michael, Critique of Poetry, London:Jonathan Cape, 1934.与艾略特有精神上的互通。谈论奥古斯都时代的逝去,也是对艾略特式“古典”的一次隐秘告别。这两篇文论相互呼应,对疏离的、非个人化的现代主义诗学观进行历史关照,表达了奥登一代对艾略特诗学的扬弃。穆旦对这几篇文字的选择,有相似的诗学立场考虑。
毕竟,以沉默而言说,以逃避为参与,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书写策略(18)Sumner, Rosemary, A Route to Modernism: Hardy, Lawrence, Woolf,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0,p.166.,但若全盘照搬入中国的抗战背景,却显得过于冷静、克制,乃至于对社会现实无动于衷。穆旦选择翻译“奥登一代”的这两篇文章,体现了在一个战火蔓延的时代,诗人立足于自己的语境对诗歌理想的自我省察。
(二)文本对比
穆旦在1940—1941年留校任教期间完成这两篇诗论翻译。西南联大提供的正规英语训练、活跃的文学氛围,对穆旦翻译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与激励的作用;萧干、杨刚主编的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也为当时联大师生发表作品提供了便捷的途径。穆旦在大学末期与助教阶段开展的诗论翻译,的确有这一文化氛围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作为联大外文系高材生和助教的文化身份也是穆旦译文水平的一种保证。有新诗研究者引用《诗的晦涩》,称译文由“现代著名诗人穆旦所译,更平添了几分可信”(19)夏汉:《诗,及其本体的洞察》,《诗建设》2014年秋季号,总第15期,第223—236页。。大多数读者往往会根据译者的名望来判断译文的可信度,然而更科学更客观的做法,还是应该进行原文和译文的比对。
《诗的晦涩》和《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这两篇诗论翻译,总体上译笔流畅而富有诗意,但有可能因为当时翻译得匆忙,译文里也有不少明显的错误或笔误(20)穆旦的这两篇译文中出现不少英语人名拼写的错误,另外,还把consciously(有意识的)翻译成“有意义的”;把拉丁语ipso facto(事实上)翻译为“以弗若德讲来”;把an apparent statement of rejection(明显的否定陈述)翻译为“含蓄着否定的叙述”;把艾略特诗歌中烹饪散发出的smell(气味)翻译为“香水”;把诗歌的property(特征)翻译成“财产”;诗歌中的metric(韵律)翻译为“度量衡”。这些都是相当明显的误译。。另外,有可能因为原译文分成数段发表,某些地方重要用词的翻译出现了不连贯的缺点。例如,《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中谈到18世纪古典作家诗作的特点,作者文中两处引述了同样的表述:
…poetry was a pattern of‘good sense and elegant sobriety’imposed upon the unruly instincts.(21)Roberts, Michael, Critique of Poetry, Jonathan Cape, London, 1934, p.188,198.
而诗,它是“明达和雅慧”的模式以克制猖獗的本能的。(22)穆旦译:《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34,242页。
…to whom, in poverty and madness, that‘good sense and elegant sobriety’ meant nothing.(23)Roberts, Michael, Critique of Poetry, Jonathan Cape, London, 1934, p.188,198.
他们在贫穷和疯狂中,是不懂得什么“理性和雅静”的。(24)穆旦译:《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34,242页。
原文中的“good sense”是从洛克处借用的概念,更多强调理性,并非只是言辞上的明晓通达,所以译为“明达和雅慧”不如译为“理性和雅静”来得妥当。此外,文中不少关键词的翻译没有统一:“paradox”有时翻译为“似是而非”,有时翻译为“诡辩”;“antithesis”有时翻译为“对句”,有时翻译为“对词”。这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阅读不便。
考虑到当时翻译的情境与限制,我们无须过于苛责,也无意在此一一列举穆旦译文中的翻译错误。然而,通过文本比对,发现有一处翻译选词的偏差,显然不是由于翻译的仓促或译者的大意,而是译者非常自觉的、故意的误译。这一误译现象的背后,有更加值得深究的问题。翻译研究中,发现译者故意的、自觉的“误译”,往往是能够理解译者主体性的切入点。作为一个译者,查良铮翻译现代主义诗学关键词所选择的转译策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穆旦诗学观提供了一个重要路径。
(三)“impersonality”的翻译问题
《诗的晦涩》中,出现了艾略特诗学的一个核心用语“impersonality”。麦克尼斯以艾略特的诗歌为例,说明近代诗歌晦涩的来源之一,是破碎的现代经验及观念的剪裁与迅速切换。他引用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Tradition and the Individual talent”)中,关于诗人应当捕捉、收藏感情、词语、意象并将所有元素组合为新的整体的论说,然后给出了自己的一段评论:
Like a motor-car factory where the chassis slides past “impersonally” on its platform until all its body is fitted on to it. Eliot, remember, is an addict to “impersonality” .(25)MacNeice, Louis. 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162-163.
像在汽车制造厂里,车架“非自我地”滑过了平台,然后适合装在那上面。你必须知道,爱略特是惯于排除自我(impersonality)的。(26)穆旦译:《诗的晦涩》,《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49,254页。
麦克尼斯将艾略特和奥登相互比较,将前者归于impersonal,而后者看作personal的诗人:
When we leave Eliot or Pound or Yeats and come to Auden or Spender, we enter a more vulgar world. ...Where Eliot insists that the poet should be an observer,impersonal, looking at the stream from the bank, these younger poets do not cut off their poetic activity from their activity in generally. Being “personal” poets, then, their obscurity will be of a different kind from that of Eliot or from that of the modestly registering surrealists, also from that of the “personal” poet, Yeats, forpersonalityfor them does not imply such utter individualism.(27)MacNeice, Louis, 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p.168-169.
当我们从爱略特或庞德或叶慈看到奥登(W. H. Auden)和斯本德(Stephen Spender)时,我们就走进一个比较俗气的世界里……爱略特固执地要诗人当一个观察者,非自我的,从岸上看水流;但这些较年轻的诗人们并不把诗的活动和一般的活动分开。作为“有我的”(personal)诗人,他们的晦涩当然是不同于爱略特的,不同于谦虚地记录的超现实主义者的,也不同于“有我的”诗人叶慈的,因为对于他们,“我”并不是非常的个人主义。(28)穆旦译:《诗的晦涩》,《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49,254页。
穆旦将艾略特诗学关键词“impersonality”翻译为“排除自我”,认为艾略特要求诗人做置身事外的、非自我的(impersonal)冷静旁观者,而年轻的奥登一代则被命名为“有我的”(personal)诗人,他们的诗歌主张更为积极介入乃至融入俗世。
穆旦将“impersonal”译为“非自我的”,将“personal”译为“有我的”,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一般情况下,“impersonal”译为“非个性的”或“非个人的”应当更为恰切。穆旦不可能不知道“impersonality”应该怎么译。事实上,1941年穆旦翻译《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的时候,曾将古典主义者们的观点“art must be impersonal and detached”准确译为“艺术必须是非个人的,孤玄的”(29)穆旦译:《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34页。。
这就进一步说明,穆旦在《诗的晦涩》所使用的一系列与“我”相关的表述——非自我、排除自我、有我——是译者有意为之的选词操控。诗人穆旦匿身于翻译者穆旦之中,在异域他者的掩护下,立足于1940年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表达了特定的诗学理念和诉求。
三、作为抒情主体的“自我”
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原意在于纠正浪漫主义的个性放纵与情感矫饰,并没有要消除自我。穆旦将艾略特的“非个性化”诗学,置换为“排除自我”的诗学,是译者精心安排的一次误译,以便于借用奥登一代对艾略特的批评话语,表达穆旦本人的诗学观念。
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中对诗歌本质的著名论断,长期以来被看作“非个性化”诗学的宣言:“诗不是放纵感情, 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Poetry is not a turning loose of emotion, but an escape from emotion; it is not the expression of personality, but an escape from personality)(30)Eliot, T. S,“Traditional and Individual Talent”, In Selected Essays 1917-1932,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32.。可见,“非个性化”和“去抒情性”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两面。穆旦在西南联大受教于燕卜荪,对艾略特诗学的核心精神谙熟于心,对实现“非个性化”的艺术手法,例如客观对应物(objective correlative)、戏剧性场景(dramatic scene)、并置(juxtaposition)、反讽(irony)、悖论(paradox)、机智(wit)等,运用起来也颇有心得(31)刘燕:《穆旦诗歌中的“T.S.艾略特传统”》,《外国文学评论》2003年第2期,第134—142页。。穆旦对于“非个性化”的诗学观是认同的,他对艾略特的批评不在“非个性”,而在其“非抒情”的主张。以穆旦1939年4月创作的《防空洞里的抒情诗》(32)穆旦:《防空洞里的抒情诗》,《穆旦代表作》,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9年,第6页。为例。在这首诗中,穆旦将碎片化的战时日常经验杂糅、拼贴和并置,确立了他早期的抒情原则。表面看来,这首诗承继了艾略特风格,其内心独白和多重叙述视角的写作手法,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艾略特的 “反抒情诗”,然而最终穆旦为自己的写作命名却定格于“抒情诗”。虽然诗中的抒情主体看似含混,但“自我”的分裂、挣扎乃至发现,至始至终不曾缺席。在诗歌的结尾,“人们”和“他们”都退场了,“我是独自走上了被炸毁的楼,/而发见我自己死在那儿/ 僵硬的,满脸上是欢笑,眼泪,和叹息”。归根结底,这首诗“仍是一个关于自我的寓言”,并通过死亡“获得了抒情诗的历史针对性”(33)王璞:《抒情的和反讽的:从穆旦说到“浪漫派的反讽》,《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62—74,63页。。
同时,藉着对麦克尼斯的翻译,穆旦也明确了“我”(personality)和“非常的个人主义”(utter individualism)之间的区别。叶慈的诗歌同样充满了自我的指涉,用麦克尼斯文中的话来说,就是“私自的命意”(private meaning)和“刚强人的渴望”(aspiration of strong individual),但这种极端个人主义式的自我,也并非穆旦所追求的。穆旦充分理解了叶慈式和奥登式“有我的”(personal)写作方式之间的区别,在两者之间坚定选择了后者。仍以《防空洞里的抒情诗》为例,有学者认为,全诗中“我”和“你”“他”“她”“他们”等人称代词的并置,使得“抒情主体”的位置模糊了,动摇了(34)王璞:《抒情的和反讽的:从穆旦说到“浪漫派的反讽》,《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62—74,63页。。实际上,穆旦恰是用这一方式,打破了传统个人主义的抒情主体,把精神上的自我融入了历史和政治的反讽,从而建构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自我”,承担起更加富有伦理色彩的抒情话语。
王德威提出,抒情是革命和启蒙之外,“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35)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中国文哲研究汇刊》第33期,2008年, 第77—137页。。这样看来,穆旦在《诗的晦涩》译文中所使用的一系列与“我”相关的表述,与其说是翻译或误译了“叶慈—艾略特—奥登”这一诗学谱系的精神发展,毋宁说是诗人在热切呼唤“自我”在诗歌中现身,呼唤现代抒情主体的确立,为“新的抒情”观之建构埋下伏笔。
四、召唤抒情
单从翻译的角度考察穆旦的诗论翻译依然是不充分的。这两篇译稿的翻译时间与穆旦1940年两篇诗论的发表时间相当接近。1940年3月和4月,香港《大公报》文艺综合副刊分别于第 794 期、第 826 期登出穆旦两篇诗评:《他死在第二次》《〈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第一篇肯定艾青诗集《他死在第二次》的成功,欣喜断言“我们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的词藻当中, 看到了第三条路创试的成功, 而这是此后新诗唯一可以凭借的路子”(36)穆旦:《他死在第二次》,《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3页。。第二篇通过对卞之琳诗歌的评论,穆旦进一步阐明他心目中新诗诗艺发展的路径,并将之称为“新的抒情”。
这条“新的抒情”的道路,是在“枯涩呆板的标语口号”和“贫血的堆砌的词藻”中开辟出来的“第三条路”,几乎可以完全从穆旦曾翻译过的麦克尼斯那里找到出处。在《诗的晦涩》译文之前,穆旦附上了原作者和文章内容简介,并专门引用了麦克尼斯原书序言里的话:
Poetry today should steer a middle course between pure entertainment (‘escape poetry’) and propaganda. Propaganda, the extreme development of ‘critical poetry’, is also the defeat of criticism.(37)MacNeice, Louis,“Preface”, In Modern Poetry: A Personal Essa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今日之诗,应该在纯欣赏(逃避之诗)和宣传中取一中路。(38)穆旦译:《诗的晦涩》,《新诗评论》2010年第2辑,第243页。
宣传话语易于沦为标语口号,对自我和感情的逃避则可能让诗变成堆砌辞藻、玩弄形式的智力游戏。寻找一条不再逃避自我与感情、同时也不沦为口号与宣传的诗歌道路,就是“第三条路”的创试,也恰是穆旦1940年代初诗学思考之核心所在。穆旦诗评和诗论翻译之间,这一处无疑存在着明显的互文和呼应。
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穆旦指出除了口号和词藻之外,抒情还需要警惕的另一个面向:“在我们今日的诗坛上, 有过多的热情的诗行, 在理智深处没有任何基点, 似乎只出于作者一时的歇斯底里,因为不但不能够在读者中间引起共鸣来, 反而会使一般人觉得, 诗人对事物的反应毕竟是和他们相左的。”(39)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过于平静理智以至感情麻木,或者过于激动热烈以至情绪失控,都不是抒情应该走的路。在穆旦看来,“新的抒情”应该是“有理性地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的一种东西”(40)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在这个看似简单的表述中,“新的抒情”的意涵在多个维度上得以展开。抒情的方法是有理性的,目的是鼓舞人,格调是光明的,“抒情”不是一个既定的、封闭的概念,而是开放性的、实验性的、生成性的“一种东西”(41)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穆旦明确指出“我着重在‘有理性地’一词”(42)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对“理性”的强调,恰恰暗合了麦可·罗勃兹《一个古典主义者死去》中所描述的奥古斯都时代古典诗人“理性和雅静”的精神特质,亦可追溯到艾略特对“思想知觉化”的主张,体现为感性和知性的统一,以“客观对应物”的形式表现情感。穆旦同样赞成用意象来负载情感,使主观情绪通过艺术的想象表现为客观形象,然而他对这一做法的认同,主要在技法的向度,并没有推展到诗学观念或理想的层面。
在《〈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穆旦批评了20世纪英美诗坛浪漫主义抒情没落的风气:“脑神经的运用代替了血液的激荡,拜伦和雪莱的诗今日不但没有人模仿着写,而且没有人再肯以他们的诗为鉴赏的标准了”, 取而代之的,是艾略特影响下“用机智(wit)来作诗的风气”(43)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穆旦敏锐地看到,艾略特等西方现代派诗人面对的的精神危机,是死寂的、令人窒息的“荒原”,诗人要在上面垦殖出任何意义,不得不借助“锋利的机智”。而中国处在激越的抗战大时代,面对生死存亡的战斗,硝烟弥漫的战场呼唤着血性而并非机智。如果脱离中国现实,只以机智入诗,“也许有时是恰恰麻木了情绪的节奏的”,正如穆旦对卞之琳诗风委婉的批评:“这些诗行是太平静了。”(44)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164,164,164,163、165页。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平静诗行的背后,有一个更宏大的新诗抒情发展路线。新诗在草创期充满了与旧时代决裂的气概,对情感解放和心灵自由的呼唤是主调,抒情被上升到诗本体的高度。与此相伴相生的,是诗界对抒情手法及尺度的讨论。1920年代,梁实秋援引新古典主义的“理性”“节制”“秩序”“规范”等原则,提出抒情要有分寸,“须不悖于常态的人生,须不反乎理性的节制”(45)梁实秋:《文学的纪律》,《梁实秋文集》第1卷,厦门:鹭江出版社,2002年,第143页。。梁宗岱(46)梁宗岱:《论诗之应用》,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45期,1938年9月14日。、冯至(47)冯至:《里尔克——为十周年祭日作》,上海《新诗》第1卷第3期,1936年12月,第291—295页。在里尔克经验诗学的启发下,以经验整合、转化即物而生的日常情绪,尝试将感性体悟与理性沉思相结合。二三十年代,随着艾略特、瑞查兹等现代主义知性批评观的译介,中国诗坛对过度宣泄的浪漫抒情展开全面反思:从叶公超等人的诗论、金克木提出“新的智慧诗”(48)柯克:《论中国新诗的新途径》,上海《新诗》第2卷第4期,1937年1月,第456页。、抗战期间徐迟疾呼“放逐抒情”(49)徐迟:《抒情的放逐》,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278期,1939年5月13日。,再到1940年代袁可嘉对感伤主义的批评,整体的诗学风向趋于以理性、知性、智性的方法来处理、避免、制约甚至是对抗情绪的表现。究其背后的缘由,这种诗学趋向和1930年代后期的战争环境有莫大的关系。战火硝烟,的确容不得哀怨感伤的泛滥。在徐迟看来,“这次战争的范围与程度之广大而猛烈,再三再四地逼死了我们的抒情的兴致”(50)徐迟:《抒情的放逐》,香港《星岛日报》“星座”副刊第278期,1939年5月13日。。然而,更准确地说,只是过去那种风雅的、感伤的抒情方式再也行不通了,而绝不意味着“抒情”这一传统本身也因此走上绝路。痛苦的现实带来更为复杂而强烈的情绪,必须找到更为合适的方式来呈现。
在抗战的历史时局中,穆旦明确意识到诗歌的过度感伤和幽怨不可行,但以智性写作放逐情绪表达的做法,同样也不妥当。他提出的“新的抒情”所包含的诗学理想,指向实现“情绪和意象的健美的糅合”。“健美”二字带有蓬勃、光明的生命力,“糅合”则传递出一种持续的坚韧感。以“健美”的方式把情绪和意象相互“糅合”,就如同“一颗火热的心在消溶着牺牲和痛苦的经验”。惟其如此,抒情的主体“自我”才可能超越传统个人主义的狭隘视角,在读者中造成共鸣,充满“维系着诗人向上的力量”,表达出“一种博大深厚的感情”,并最终“鼓舞着人们去争取那个光明”(51)穆旦:《〈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3期,第164页。。
王佐良回顾穆旦写诗过程,富有洞见地指出穆旦的发展见于两个方面:“情绪上的深化,从愤怒、自我折磨到苦思、自我剖析,使他的诗显得沉重;诗歌语言上的逐渐纯化,从初期的复杂——‘丰富和丰富的痛苦’——进而能用言语‘照明世界’,使他成为中国新诗里最少成语、套话的新颖的风格家”(52)王佐良:《文学间的契合》,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年,第105页。。穆旦诗歌“情绪上的深化”表面看来是沉重的愤怒和苦思,实质却是 “自我折磨”和“自我剖析”,因为只有通过对“自我”的寻找和探求,抒情主体才能够得到真正的确立。穆旦诗歌“语言的纯化”,也可能并不仅仅事关风格,更指向一种为主观情感寻找客观表述的“理性”的诗学追求。这两方面关联起来看,恰恰是一个抒情的问题,一个“自我”如何“理性”抒发“感情”的问题,这也就是穆旦“新的抒情”试图回答的问题。穆旦同期的诗作,如《在旷野上》(1940年8月)、《我》(1940年11月)、《赞美》(1941年12月)(53)李方编:《穆旦诗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2—33、39、69—71页。等,也为“自我”之必要和“抒情”之理想,提供了实践的证词。
结 语
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情感元素及构成方式,也需要与之对应的载体或表达方式。20世纪三四十年代,压倒一切的民族解放战争对修辞方式造成了颠覆性影响,也直接催生了新诗抒情范式的变革。田园牧歌式的旧式抒情显然已不合时宜,“抒情”作为一种诗学成规也遭到质疑。穆旦1940年代初的两篇诗论翻译《诗的晦涩》和《一个古典主义者的死去》,与两篇诗评《他死在第二次》和《〈慰劳信集〉——从〈鱼目集〉说起》交织在一起,有破有立,既有对叶慈的个人主义以及艾略特逃避诗学的扬弃,也有对奥登一代融入时代的政治态度之认可,既有对中国诗人智性写作的批评,也有对中国时局和诗学情境的反思。在这一基础上,穆旦呼唤自我从隐匿中现身,要求诗歌的理性担当,渴望诗歌能够传达光明、博大、深厚感情,多维度构建了诗人“新的抒情”之诗学观。这一诗学构想将西方诗学资源和现代中国语境相结合,在“自我”之现身与“抒情”之理想两个方面,均提出相当有情怀、有见识的观点。重新召回被放逐的抒情,是新诗诗艺现代建构过程中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