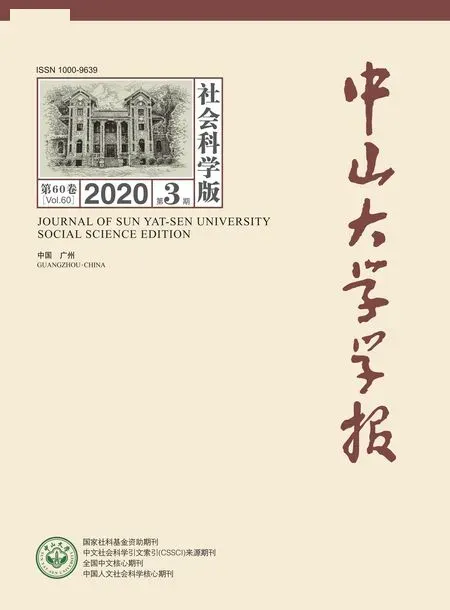生命的精神场景*
——再论《庄子》的言述方式①
陈 少 明
晋人嵇康说《庄子》:“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世说新语·文学》)一语道出许多好庄者的心声。训诂、注疏或校勘,只是专家的事情。而《庄子》一书,并非为专家所作。爱读书的人,即使不晓得“道”是“有”还是“无”,不知“道”从哪来和到哪去,都不妨碍其读《庄》获得的乐趣。《庄》书让读者快慰或沉迷的原因,在于其讲故事的魅力及其所呈现的生命的精神场景。
问题的奥秘,要从其独特的讲述方式说起。
一、从视觉到思想
《庄子》把自己的讲述方式称作“三言”,寓言、重言与卮言。一般认为,表达的主要方式是寓言,而所述的观念为卮言。什么是寓言?《寓言》篇的说法是:“亲父不为其子媒。亲父誉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意思是表达者的意图不能直陈,要借助某种中介来传达,以加强其说服力。这是比喻,也类一则微型寓言。综览全书,这种方式就是通过故事的陈述来传达对生命或生活的观点。故事不必复杂,无须史诗式的长篇,只要精致的情节或场景。所涉者无非是生活中的要素,人、事、物之类。其要义就是观点通过情景来呈现,而非通过概念去推论。即故事能让读者或听众能直接感受其意义。用《秋水》篇的话说,意义是“观”出来的。但它不是任何方式的“观”,“以物观物”所得者,只是庸常的观念;要做到“以道观物”,那才是道行之所在。因此,“观”是需要训练或者修养出来的能力。
汉语中,望、视、见、观等词与“看”有共同的意义,即指通过眼睛视觉功能的运用去掌握对象的行为。整个行为的完成,包括若干要素,如意愿、对象、位置、行动以及结果。这样看来,同是表达视觉行为的词,意义的侧重点可能就不太一样。例如,“望”字表达意愿与行动,但不一定望得出什么结果。故《庄子》说:“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天运》)荀子也言:“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劝学》)“视”也然,一般是近视远望。《秋水》中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的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同样也“视而不见”。“看”字起源较早,但其流行则时间上偏后。它也存在着“看见”与“看不见”的问题。如果什么都看不见,看了也白看。因此,“见”除了表达直接察看的意思,更重要的,还意味着看到一定的结果。前义如《论语》中的“子见南子”(《雍也》),“子路愠见曰”(《卫灵公》)以及《庄子》中的“孔子见老聃而语仁义”(《天运》)。后义如“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也”(《天道》),“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见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听之不闻其声,视之不见其形,充满天地,苞裹六极”(《天运》)等,往往表示“看”出了结果,有所收获,所以叫有所“见”。因此,“见”之古义也同“现”。但是,所见是否如所愿,则是另一个问题。因此,也存在浅见、偏见或洞见、远见之分,或者如佛学说的有正见、倒见之别。东施效颦就是见非所是或者同看不同见的例证:“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颦其里,其里之丑人见之而美之,归亦捧心而颦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颦美而不知颦之所以美。”(《天运》)
“观”则包含“看”(或视、望)与“见”两义而有所超越。先看“观”“看”之异。偶然的撞见或无心的一瞥,都是看。而且看是在特定的视角范围内才有效的。河伯未出崖涘时“东面而视,不见水端”。北海若告诉他:“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秋水》)观水较有普遍性,儒家也主张“君子见大水必观”(《荀子·宥坐》)。比较而言,“观”是更自觉的行为。同时视野更深远,甚至越出视觉的限制,不但“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易·系辞下》),还可以“观古今之异”,对象从空间扩展到时间。再看“观”与“见”。字型构造上,观字包含见字在内。“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逍遥游》)与“望之而不能见”义同,观与见都有看到结果的意思。但是,当其行为对象相同时,见、观之义便有别。“见人”指直接的会面,如“子见南子”或“孔子见老聃”。但“观人”则不是见人,如“今吾观子非圣人也”(《天道》),或“由天地之道观惠施之能”(《天下》),其重点不是看一眼或会一面,而是在于对人格及思想的考察、品鉴,观的过程包含有观念思考的成分。《齐物论》曰:“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淆乱,吾恶能知其辩!”同样是所“见”具体,所“观”抽象。重要的是,当下的视觉都是有限制的,有限的言行不能评价一个人,巨大的风景无法一眼望尽。因此,“观”不是视觉形象的一次性捕捉,而是一个过程。它需要不同视觉片断的连接。这些片断可以来自同一视角下对象的变化,也可以围绕着对象作不同角度的观察。过程一旦拉长,这种“观”就需要知识的辅助或补充。或者说,“观”把眼前的经验纳入到与过去经验相联结的思想活动中,是观察向思考的过渡。因此,同是看海,说观海与说见海就不一样。见海是指获得关于海洋的视觉形象,观海(或观水)则获得比视觉更多的内容,如胸怀、气度、境界等等。《秋水》中,北海若说河伯“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今尔出于崖涘,观于大海,乃知尔丑,尔将可与语大理矣”,也意味着“观”不是裸视,而是有准备的思想行为。所以,不但可以观天文地理,也可以观风土人情。同时,这种“观”还需要突破视觉表象,透过事物的外部形态去抓取其内在结构。如《易传》的“观物取象”,就不仅限于直观的行为,还有“取”的思想主动性(1)现代心理学家也重视视觉在诸感觉中的重要地位,强调注视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选择的行为,因而有“视觉思维”之说。参[美]鲁道夫·阿恩海姆著,滕守尧译:《视觉思维》,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
老子说:“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道德经》第一章)《庄子》借北海若之口接着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以功观之……以趣观之……”(《秋水》)所谓“以X观之”,不论是以“道”,还是以物,以俗,以差,以功,以趣,同老子的“无欲”“有欲”一样,表明这个“观”是需要立场或“先见”的。北海若所说的“以道观之”之“道”,就是庄子观天下人生的知识或思想依托。毫无疑问,庄子的“观”超越“见”,意义更宽广。日后,“观”便慢慢延伸出更抽象的含义,而且更突出观看的成果,如观点或观念。不但观心,而且可以观道。最终,道观、观道一体。今日所谓人生观、世界观、宇宙观之类,均由此延伸而来。
人是视觉的动物。这不是说只有人类才有视觉,而是指人类能把视觉的功能发挥到极致,把它从看得到或可以看的事物上运用到“看不到”或“不能看”的目标中。看不到者如宏观、微观对象,不能看者如思想现象。所谓“宏观世界”“微观世界”,或者“思想世界”“精神世界”,就是人类用思考模拟观看的表现。这不只是视觉需要思想,而是视觉如何进入及支配思想的问题。章太炎甚至主张,中国传统的道学,与其叫做哲学,不如称为“见”学:“九流皆言道。道者彼也,能道者此也。白萝门书谓之陀尔奢那,此则言见,自宋始言道学(理学、心学皆分别之名)。今又通言哲学矣。”他引荀子《天论》的说法,“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强调“予之名曰见者,是葱岭以南之典言也”(2)章太炎:《明见》,《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4,124页。。
有意思的是,章太炎把荀子同佛学联系起来,断言思想与视觉一样,其有效性可能通过验证来判断。“见无符验,知一而不通类,谓之蔽(释氏所谓倒见见取)。诚有所见,无所凝滞,谓之智(释氏所谓正见见谛)。”(3)章太炎:《明见》,《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4,124页。观察结果与对象不一致,或者看到事物特殊性而不知其普遍性,都是蔽的表现。见而无蔽称为智。然而,视觉上还存在“见”与“蔽”的另一种对立。对物体的任何一次观察,都只能见到其中的一个侧面,而看不见其位置相反的一面,故有所见便有所蔽。思想也是这样,囿于自己的立场,便会产生“有见于后,无见于先”或“有见于少,无见于多”这种局限。思想家的局限,也是观念史的问题。例如“道”,本意是走路,慢慢变成路,又变成到达目的地的途径,再变成达致抽象理想的措施,最后变成规则甚至形而上的本体。而每一新义的出现,都是对旧义的掩盖。有所见必有所蔽,遮蔽既久,根源就容易被忘记掉。正如考古场地一样,越原始的层次埋得越深。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到《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再到王弼“以无为本”的道,道便越来越离开其根基,同时也越来越玄虚。因此,那些有根源性追求的思想家就会出来揭蔽,或者叫做思想考古,因而从唐代开始,先后有韩愈、章学诚、章太炎等接二连三的《原道》。章太炎以为,智者的使命便是通过思想的解蔽,获得对道的洞见。太炎为何独尊“见”而不称“观”,我们不知道。但两者的思想逻辑是相容的,观道或见道,就是哲学的一个概念模型。
二、视角与场景
庄子就是通过视角的变动,实施思想揭蔽的观道或见道者。当然,思想的视觉不同于感官的视觉。眼晴对物体的整体把握,有两种方法。一是围绕着对象转动,从每个可能的角度对之加以观察,然后整合起来。这种方法可靠,但是费劲且不一定现实。因为不是所有的事物都让观察者有绕到背后或潜伏到下面察看的条件或机会。面对一座塔,不必绕圈也知道背面的大致面貌。看到动物如牛或马的头,自然知道后面连着一个有四条腿且带尾巴的身体。这是第二种方法,即借助经验或其他背景知识从事物暴露部分推测其被遮蔽的其他方面。这种思想的作用有时很直接,几乎是即时“看”出来的。当然,它也可能产生错觉,或者被误导,这是观看魔术表演时常见的情形。因此,思想也需要训练,尤其是思考观念问题的时候。思想与观看一样,都受视角或者立场的限制。荀子说的“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即指位置或角度决定视野的广度与深度。表面上,思想的变换比身体的移位容易。其实不然,特别是某种想法成为一种“观点”后,它既是持有者成功的手段,也可能是其思想的负担或者障碍。所谓世界观就是这样。《德充符》中无趾在老子面前嘲笑孔子说:“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彼且以蕲以諔诡幻怪之名闻,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在庄子笔下的得道者看来,孔子所祈求的名声,其实就是思想的桎梏,只是他自己不知道而已。当然,不只思想家才有桎梏,常人也同样。庄子的思想使命,就是破除这种无处不在的观念的桎梏。
常识中观察世界的基本观念,除了观有无就是辨大小。“无”不可见,从“有”出发,大小便是基本的视觉范畴。而且,我们都有崇大轻小的倾向。这种倾向甚至并非某些人的偏好,而是人类本性的表现。于是,庄子便来做“小大之辩”。注意,他的词序是小大,而非大小。《逍遥游》开篇所展示的“大”,看起来是横空出世的现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其实,生活中鲲鹏的原型,不管鱼还是鸟,体积都不大。把它放大后,再用常识中的小虫、小鸟作对比,效果就很奇特。这种大从小来,小大相对的观念,是通过强烈的视觉形象来表达的(4)参陈少明:《广“小大之辩” ”——从〈庄子·逍遥游〉说起》,彭国翔主编:《人文学衡》第一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庄子》不仅教人以大观小,还让人以小观大。《则阳》篇中,戴晋人劝魏王止战的说法,就是采取后一种策略:“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从更宏大的图景来看,魏王要发起的征战,看起来轰轰烈烈,其实无异于追逐蜗牛角上的利益。其执念系自以为是,不知道国中有国,天外有天的一孔之见。这两则故事,很有卡通感。一是小变大,一是大缩小,一推一拉,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镜头感。“自细视大者不尽,自大视细者不明。”(《秋水》)庄子深谙视觉的窍门,把视角的变动与观念的转换,搭配得十分巧妙。常规视角的调整需要借助观察者身体的位移,或者物理工具如望远镜或放大镜之类的运用,但思想视觉的转换则靠想象力。庄子的想象力,真可谓旷世无匹。今人能够想到高飞的鸟儿“背负青天朝下看,都是人间城郭”(5)毛泽东:《念奴娇·鸟儿问答》,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诗词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152页。,就很了不起,至少是高山之巅才可以体验的情景。而庄子想到的是,这山脉一样的巨无霸,其腾飞所需要的高度,决非人类的肉眼所能看见的。在那个高度,其感受只能是:“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即不仅前后无别,上下也难分。这也意味着,视角决定场景。世界的正见与倒见,只是角度或者参照系选择的问题。
调动视角,是庄子压制论敌、颠覆常识的策略。《胠箧》说,世俗的聪明人,为防止盗贼,总是把财物装好锁紧。殊不知这种自以为得计的想法,恰好方便了巨盗。因为他们把整个箱子一起抬走更省事。因此,“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楚王要拜庄子为相,庄子就以神龟藏之庙堂而死,不若曳尾于涂而生为由拒之(《列御寇》)。庄子病重,弟子以厚葬安慰他,理由是“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的回答是:“在上为乌鸢食,在下为蝼蚁食,夺彼与此,何其偏也!”(《列御寇》)弟子以为,敌对势力来自天空,庄子调整视角,提醒也要提防来自地下之祸害。“匠石运斤成风,听而镯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徐无鬼》)大家惊奇于匠石的神技,庄子则更重视这个惊险的表演需以郢人作为“质”的配合为条件,怀念思想对手的消逝。总之,剧情反转是庄子思想最富戏剧性的特征。这一点,孔子在《庄子》中的形象最具代表性。孔子明明是颜回的老师,可话没说几句,师徒关系就会颠倒过来。如《大宗师》论“坐忘”,《让王》谈自足之乐,均以孔子表达对颜回的心悦诚服而告终。
有见就有蔽,思想与视觉一样,都存在一定的死角。而每种思想最大的死角,往往需要相反立场才能发现,理论与常识也一样。庄子为何总与世俗作对,因为他要为人类去蔽。而人类根深蒂固的观念,几乎都是生命与生活赖以进行的基础,例如物理世界的有无、大小,精神世界的生死、梦觉等等,几乎都是颠扑不破的信念。一则庄周梦蝶,更是把这种颠倒视角的神技,运用了登峰造极的境地。“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齐物论》)这是一个神奇的问题。常人通常只会问,周为何会梦成蝶,只有庄子才会把问题反过来,想到是否是蝶梦为庄。而且,这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因为一旦梦之中套着梦,像俄罗斯套娃一样,做梦者的“醒”可能只是其中一个层次的“梦”的表现。道理上,你永远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处在终极觉醒的状态。这不能把它理解为否定常识意义上的梦觉之分,而是对什么是主体以及生命的意义的疑惑,其实质就是对人类生活状态的反省。如果“大小”是外观,那么“梦觉”便属内观。其绝妙在于,梦境也是视觉化的。在人生各式各样的蔽中,最大者莫过于庄子所揭示的梦之蔽。正是这个蝴蝶梦,不仅给人生提出一个永恒的哲学问题,同时为中国文化创造一个优美的象征(6)参陈少明:《想象的逻辑——来自中国哲学的经典例证》,《哲学动态》2012年第3期。。 它与今日美国式的“梦想成真”,精神意境迥异。
当然,有见必有蔽,对庄子也适用。荀子就说他是“蔽于天而不知人”(《荀子·解蔽》)。那么,什么是天?什么是人?庄子借北海若的口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秋水》)庄子把人放在天然,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背景下观察,以此削弱人类自我中心的观念。而荀子关于人的界定是:“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庄子想解构的,正是儒家认为使人更高贵的“义”。可是,如果人与草木鸟兽无别,人的意义又何在呢?事实上,人就是天人一体的存在物。人不仅通过“落马首,穿牛鼻”控制支配“天”,人也通过装扮、利用且最后束缚自身,使自己成为“人”。你只见天就会不见人,反过来,则只见人便不见天。因此,庄与荀可能各有所见,同时也各有所蔽。只是这种“见”不再是眼睛的观察,而是思想立场的运用。而且,庄、荀都把那种片面看待事物或夸大某种偏好的人叫做“曲士”。《天下》称:“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天下》)从字源上看,曲字在甲骨、金文中的写法,均类曲尺状,《说文》则像马蹄型,其释为“曲,象器曲受物之形。”《荀子·劝学》说:“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山道、河流拐弯处也称曲,故处于任何一曲中,均无法看见道路之整体。故荀子认为曲士不足以论道:“夫道者体常而尽变,一隅不足以举之。曲知之人,观于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识也。故以为足而饰之,内以自乱,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祸也。”(《解蔽》)荀子认为,只有圣人才真通道。
庄子也知道任何见解都是片面的,都是对其他方面的遮蔽,因此提出齐物论,也即齐是非的观点。齐是非不是与某一具体的观点争是非,而放弃任何是非的观念,要义就是放弃固定的立场。没有固定的立场不等于没有立场,其立足点叫做“环中”,也即圆心。《齐物论》说:“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从圆心看圆周,没有死角,也没有分别,故可“以应无穷”。推广到万物上,则“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寓言》)。无论是“道枢”,还是“天均”或“天倪”,其共同点就是以“环”即圆的视觉图式为思想模型。对于“卮言日出”,郭象注曰:“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7)郭庆藩撰,王孝鱼整理:《庄子集释》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47页。这个因满空的变化而倾仰的器具,其转动的形态正好也是一个圆。故章太炎说:“此以圆酒器状所言 ,是取圆义,犹云圆言耳。”(8)转引自崔大华:《庄子歧解》,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36页。因此,卮言就是圆融应对不断变化的各种物论。处于“环中”,面对旋转无尽的事物或物论,没有固定或者随时顺势调整自己的视角,不会胶着于对局部事物的彼是取舍,就不会产生一曲之见,自然就能够齐是非。均有均平或均匀之意,圆心与圆周的关系,还有圆周上任何点对点的关系,最能满足这一要求。而天均或天倪之“天”,大概是从日出月落,斗换星移的观察中,悟出的天道周行的道理。用“天”来形容它,意味着其普遍性与超验性。庄子克服视角局限的道理与方法,也是通过视觉的图式来呈现。
三、观之以道
庄子被汉人封为与老子并列的道家。今人对这个“道”的哲学意义,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把“道”理解成一个伟大的存在者,它本身不是某种具体的东西,但其作用遍及一切事物。这种观点类似于宋儒的“理”,是得于天而具于心的。故“道”同“理”一样,都可归于西式的形而上学。同时,这种论断也能从庄书,如《大宗师》中找到依据:“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样,道被视作“道体”,是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不过,本文倾向于另一种观点,即把“道”理解为看待事物的一种智慧的方式。《秋水》中,北海若“以X观之”的完整表达是:“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道与物、俗一样,代表观物的不同方式。其作用在于让人类摆脱“丧己于物,失性于俗”(《缮性》)的困境。这个“道”可称为“道观”,与“道体”相对。
《知北游》中对道的这一描述,通常是大家谈庄子道论时不可忽略的材料。“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甓。’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庄子曰:‘夫子之问也,固不及质。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汝唯莫必,无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这段话,当然可以成为“道”无所不在的证据,只是这个“道”究竟是决定事物价值的超经验的精神力量,还是理解万物包括人的处境的方式,则是有分别的。对前者而言,事物价值是秩序化,同时是先天的,问道就是去发现这一伟大对象如何存在。对后者来说,道是一种追寻生活意义的方式,意义不是概念的演绎系统,它不是待发现的存在,而是被激发的精神状态,因而是生动多样的。
“每下愈况”就是“道”无处不在。从“道观”的观点看,就是在生活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人生包含生命与生活两重含义,动物也有生命,但没有人所理解的生活。生命意味着死亡的限制,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生最大的恐惧。此外,生活不只是活着,要活得有意义,至少是要快乐的。而快乐不只是健康或感官的满足,还有精神的追求。物质的有限性与精神追求的多样性,导致快乐的追求是会冲突的。因此,意义不是单一的原则,更非抽象的概念。庄子领着大家见机赋意,随处指点。是非贵贱,有无大小,梦觉生死,观鱼解牛……等等,场景有大有小,角色或人或物,情节亦幻亦真。总之,所述观点充满画面感或者高度场景化。同时,其道理往往以颠覆世俗观念甚至常识为目标。庄子的“观”不是目光偶遇或随意的一瞥,而是经过深刻思考的构思与表达。很多感性的画面,不是照镜子的复现,而是通过文字描写调动起来的想象。观念一旦能够被直观,就有直指人心的力量。横空出世的鲲鹏,庄子不可能看见过。但他能够告诉你,当这个巨无霸飞达一定的高度以后,看上和看下没有分别,都只是其色苍苍而已。更绝的当然是被反复提及的梦蝶。其实,是否梦蝶既不特别,也不重要,问题在梦境之外。只有对庄子而言,这个梦才是绝妙的思想素材。把思想图像化,而非看图说话,才是庄子的思维特性。当然,先秦诸子借故事表达思想,也就是对寓言的运用,决非庄子一人。其他人如韩非也有卓越的表现,“自相矛盾”“刻舟求剑”以及“守株待兔”等等成语的形成便是证明。但庄子把它做绝,思想(卮言)与思想的表现(寓言)如盐溶于水,深刻与生动完美结合。虽然《齐物论》也存在丰富且深刻的概念分析,如“物我”“是非”甚至“有无”,但最打动人或者影响最深远的,还是这些思想深刻的故事。
庄子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道论,其论述方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现在,可以回到道与哲学的关系上来。哲学是个外来词,在其原产地西方,其含义或者说表现形态也是有变化的。福柯和阿多都认为,今天对哲学的理解,即依概念推导的方式,论证真理的存在,是以笛卡尔为转折点的(9)[法]皮埃尔·阿多著,张宪译:《古代哲学的智慧》,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85页。。 国人对西方哲学传统的理解,主要特征有两点:一是研究万物共有即“存在”的本质,二是用概念推导获致的理论。这种被称为“形而上学”的知识存在两个方面的弱点:一是其推论脱离经验可验证的范围,一是它外在于人的精神体验。经验主义者质疑前者,存在主义者则诟病后者。庄子不一样,其“齐物”论虽然持万物一体的观念,却是以人的生命形态的体验为基础的。他笔下用来与人对比的物,各式虫鱼鸟兽还有河海、大树甚至光影,都充满生命的动感。一方面是以人拟物,另一方面则借物训人。庄子的反人类中心主义,根本还是站在人的立场上。体验不是概念。体验是从活生生的处境中,感受生活的压力或刺激。它是意义原初的场域。庄子掌握其中的奥妙,把生命中的喜怒哀乐,通过各色人等的行为集结起来。把神仙圣贤、高人逸士、王公衙吏、书生盗寇乃至贩夫走卒,各种角色的表演场景,一个个推到读者面前。抽象不是生命的本质。一个灾难的数据,同一个灾难的情景相比,或者鬼的概念与见鬼的情节相比,哪一个更能激起情绪的反应,是不言而喻的。拟情景就是让人置身于模拟的环境中,去间接体验未必亲身扮演过的角色与遭遇,从而触发心灵中意义的阈门。因此,庄子观道不是形而上学的追问,不是寻找什么永恒的对象。即其目标既非没有方所的物,也非先天定在的理。庄子观道就是致力于揭开俗世积习的面纱,揭示从生命到生活的各种意义。
从近代西方开始,在科技发展刺激下的哲学,呈现出从存在论向认识论转向的大趋势。同时,以理解或宰制外物为目标的科学技术,其知识表现形式,逐渐成为哲学模仿、追逐的版本。哲学不止是“以向外找东西的态度来猜度”(10)这是熊十力对西方本体论哲学的批评,见氏著《新唯识论》,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0页。, 即以物的追逐为目标,而且其表达方式主要是制作成套的理论系统。庄子的道论,如果不能纳入这种存在论或认识论的框架来解释,它就没有在哲学史叙述中留下位置的机会。即便还留有痕迹,丰富的思想图景也会被榨成唯我论、怀疑论或相对论的枯枝。换句话说,科学时代的哲学屏蔽前科学时代的庄学。但是,我们时代面对的现实是,科学改善了生活的不少问题,但它不能解决人生的很多问题,甚至还给人类生活带来新的问题。庄子问题的意义,其实是跨时代甚至跨文化的。重读《庄子》,像庄子观道那样体味生活的意义,是刷新对生命或生活认识的重要途径。但是,没人拥有全能的视角,庄子的观点也非来自上帝的眼睛。别人看到机械的效率,庄子见到背后拥有者的“机心”;艰难时刻人们要“相濡以沫”,庄子以为“不如相忘于江湖”……我们欣赏庄子的睿智,但不必因此阻止技术的进步,也不应对水深火热中的同类熟视无睹,更不能劝说贫困线下的低端人群安贫乐道。明智的态度是,不要把庄子立场固化,而是把它变成平衡各种极端主张或惯性思维的思想利器。对权利意识高涨的人群,可以讲责任;而在集体至上的传统中,则要维护个人;或者对自由论者讲平等,对平等论者言自由。这不是道德相对主义,而是实践哲学。道不是言说,而是行动。生命是持续的行动,而持续的行动就需要选择调节。
借助庄子“环”形的思想图式看问题,如果“环”是作为转动的“轮”,轮圈上就得有均匀的质量或形状,不能突出某一“曲”,否则轮子的转动就有障碍甚至不安全。如果“环”变成圆桌,桌面的承重就须均衡,不能集中于某一“隅”,否则就失去平衡,桌子会打翻。庄子作为批判者,其实是思想的后发者,也是价值平衡的守护者。任何抽象理想主义或原教旨主义,都是庄子哲学的敌人。反之亦然,所以作为传统异端的庄子,在以启蒙标榜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也没能挤身庙堂(11)参陈少明:《启蒙视野中的庄子》,《中山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从“思想视角”考察庄子,不是我们做的比喻,而是从分析视觉经验的内在机制出发,对庄子讲述方式的一种刻画。庄子反常规的视角所展示的精神场景,与其致力于为人生揭蔽的思想立场密切相关。因此,庄子之道的哲学意义是警示性的:一方面,唤醒我们生命体验的热情;另一方面,提醒大家警惕任何极端思想对生活的摆布与控制。同样,庄子教会我们的思想态度,也是我们对待庄子哲学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