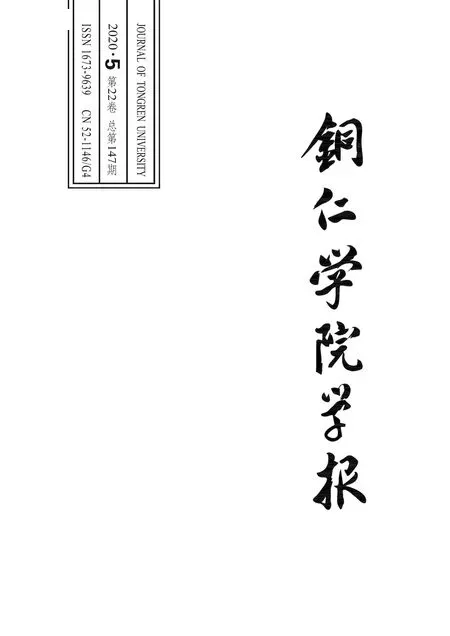论范成大题画诗的叙事艺术
范 悦
论范成大题画诗的叙事艺术
范 悦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宋诗表现出叙事性不断加强的明显趋势,范成大的题画诗也顺应了这一转变,表现出较强的叙事性特征。他以内聚焦的叙事视角表达观画感受,或寓己于画中,抒发自我之意,或自觉揣摩画作,传达画家之意;准确领会画中富有包孕的片刻,由此推想过去和未来,在诗中设想故事情节,更好地表现画家之意的同时,也使画中景物更加鲜活灵动;通过聚焦于“虚”的叙事方式,营造出一个虚空邈远的诗歌意境,扩大了诗歌容量,延伸了诗歌空间。
范成大; 题画诗; 叙事性; 虚实关系
宋代题画诗的创作达到了一个高峰阶段,与前代相比,不仅数量上空前,在题材与技巧上也有所突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相较于唐诗,宋诗亦表现出叙事性不断加强的趋势,正如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指出的:“宋人不仅将诗视为抒情或流露感情的场所,同时还将诗作为传达理智的地方。宋诗是具有叙述性的诗,是显耀才智的诗。”[1]有宋一代诗歌表现出来的这两个倾向值得我们重视,因此,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题画诗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一般说来,狭义的题画诗指的是题写在画面上的诗歌。而“凡以画为题的诗歌,或题写在画上,或题咏于画外;或称美画作,或寄托情怀,或阐明事理,或讽喻世情”[2]1均属于广义题画诗。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广义的题画诗。中国文学所谓的“叙事”也存在狭义与广义两种情况。狭义层面上与西方的“叙事”概念较为接近,强调故事的完整性,不太适用于解读以片断叙事为主的中国古典诗歌。对此,周剑之女士提出“泛事观”的概念。她解释:“泛事观对‘事’理解具有宽泛性,既包括相对完整的事件,也包括片断式的‘事’,并且以片断的‘事’为主流。”[3]在“泛事观”视角下来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较切合实际,广义的“叙事”概念体现出更大的包容性,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广阔的探讨空间。
范成大的题画诗数量较多,内容也较为丰富,但学界对其的关注度较弱。在探讨中国诗画的相关研究专著中虽多有提及范成大的题画诗,但多点到为止,并未设专章专节进行介绍。研究论文也仅见钟巧灵、陈天佑《范成大题画诗论》一篇,但所论不够深入。拓展不同的角度切入分析,有利于加深对范成大题画诗的理解。目前关于范成大诗歌叙事性的研究也较少,周剑之女士在其博士论文《宋诗叙事性研究》中,专列一节来谈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和使金七十二绝句的叙事性,但并不涉及范成大题画诗的叙事性研究。范成大诗歌表现出较强的叙事性,他的题画诗也不例外,因此本文试图从叙事视角出发,通过梳理和解读范成大题画诗,探讨其题画诗中的虚实关系。
范成大共有题画诗三十五题,所涉及的绘画题材以山水、花鸟、人物三类为主。在他的这三类题画诗中,虚实关系主要表现在情感意绪和画中景象事物的搭配调和上。从诗歌叙事性视角切入分析这种虚实关系,范成大的题画诗呈现出以下三个特点。
一、内聚焦叙事
阅读范成大题画诗,尤其是山水类和人物类,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诗人将自己置身于图画所描绘的情境中,仿佛他就是画中景象的真实见证者,是画中故事的亲历者,诗中所写的是他眼中所见之景,所抒发的是他在此情境下萌生的真切感受。若不指明其为题画诗,与诗人平日所写之诗相较,并无明显的分别。按理说诗人应为画外人,他自然会寓其观画感受于诗中,但他与画中情境的界限仍然是鲜明而无法逾越的,那么为什么范成大的题画诗能给读者如此的阅读感受呢?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在诗中选取了内聚焦的叙事视角。法国学者热拉尔﹒热奈特将聚焦方式分为“无聚焦”“内聚焦”“外聚焦”三类。其中,“内聚焦,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叙事,又可以分为叙述者内聚焦和人物内聚焦两种。”[4]27在叙述者内聚焦中,诗人即事件亲历者,他将自己置身于画境中,“述说自己的行踪和所见、所闻、所感”[4]27;在人物内聚焦中,诗人藉由故事中的人物观点进行叙述,此人物可以为画作中出现的主人公,也可以是隐藏在图画背后的画家。这两种内聚焦叙事方式在范成大的题画诗中均有表现。
叙述者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主要见于范成大的山水类题画诗中,如《题画卷五首》其三:
春阴十日溪头暗,夜半西风雨脚收。
但觉奔霆吼空谷,遥知万壑正争流。[5]113
诗歌的一、二句对应两个不同时空中的场景。从时间上看,首句中,“春”交代了时节,“阴”和“暗”两个形容词则表明此句所描绘的应是白天的景象。第二句中的场景则发生在“夜半”,描绘了一个西风忽起,暴雨将停的午夜。两句之间表现出明显的时间跨度,从白天到午夜,从阴云笼罩到风吹雨收。从空间上看,首句的焦点落在大雨将至前的昏暗的溪头;第二句虽无明显的聚焦对象,但我们可以感受到此时聚焦者所处的位置,或伫立窗前望着窗外雨收云散,或只是在屋内听到雨声渐行渐远,杂糅进越发嘈杂的枝叶摇晃时的簌簌的声音。
其实整首诗中出现了四个不同的空间,除了一、二句中的“溪头”、窗边或屋内,诗人在第三、四句还分别写到了“空谷”和“万壑”。虽然我们无法了解范成大所题的这幅画具体画了什么,但可以明确的是,一幅画中只可能表现一个时空场景,因此,这就涉及到了诗歌中虚实手法的运用。从虚实角度出发来考察整首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其实诗中所写的真实空间只有一个,即第二句中聚焦者所处的窗边或屋内。无论是白日昏暗的溪头,暴雷怒吼的空谷,还是沟壑中奔流的溪水,这三个场景应该都是聚焦者基于窗边或屋内所听、所见、所感之情境下思绪翻腾的想象,属于虚写。雨渐渐稀疏了,主人公(聚焦者)回忆起白日里依旧阴沉沉的天色,就料想今晚这雨还得下,春雨绵延少说也有十日,虽在屋内,主人公仿佛听到此刻的山谷还回荡着雷电的轰鸣,仿佛看到高涨的溪水正湍急地在沟壑之间奔流。范成大善于运用通感,在这首诗中诗人调动了听觉和视觉的体验来表现画面形象,紧扣聚焦者的心理活动,使整个情境更加逼真,使读者可以真切地感受到此时聚焦者的心理状态。如果把这首诗当作叙事者内聚焦来解读,即诗中出现的主人公(聚焦者)就是范成大本人,我们或许也不会产生怀疑,因为诗中所描绘的情境,所表现的主人公(聚焦者)的内心世界,读来是那么的真实可感。眼前这幅实在的画仅仅作为兴起诗人情绪的触媒,或许让他记起过去的某个春雨淅沥的夜晚,当时他的所思所想;抑或是诗人被画境吸引,不禁将自己置身于画中,成为画面故事的主人公,想象在此情境下的他的感受。
因此,从叙事者内聚焦的角度来品味这首诗是合乎情理的,诗人的叙述者身份与诗中的聚焦者重合,全诗仅有第二句为实写,其余三句均是基于第二句所展开的联想和想象,是虚笔——整首诗无论是实写还是虚写,都出自诗人的内聚焦叙事视角。这样的安排,扩充了一首绝句的容量,使诗歌呈现出更加丰富的意蕴,诗中情感并不明确点出,而是留给读者想象和回味的空间,读来更少板滞,更显真实灵动。
《题米元晖吴兴山水横卷》这首诗,也可以用叙事者内聚焦的叙事方式进行解读。
道场山麓接何山,影落苕溪浸碧澜。
只欠荷花三十里,橛头船上把渔竿。[5]393
道场山是湖州境内的一处名胜,苕溪为太湖的一条主要支流。有学者这样解读这首诗:“面对着水天一色的画面,诗人叹其美中不足,认为只可惜少了十里荷花,也少了些渔人打渔的生活情趣,画面空灵有余,然留白过多,生趣不足。”[6]112又“米友仁为南宋首屈一指的文人画家,然而诗人不盲从、不逢迎,敢于表达不同的意见,足见其艺术功力与胆魄,也足见其忠于艺术的精神。”[6]112根据于北山《范成大年谱》和这首诗在《范石湖集》中的具体位置,我们推算此诗写于淳熙十四年秋天,范成大六十二岁时,这年诗人已退居石湖别业。范成大少时就居住在石湖畔,晚年归隐的石湖别业也在此处。石湖属太湖的一条支流,可见,米友仁所画的应是范成大再熟悉不过的景象了。因此,若将“只欠荷花三十里,橛头船上把渔竿”这句,认为是范成大对画作提出的不同意见,也是符合情理的。依此观点,诗中仅一、二两句是关于图画的描写,整个画面意境在第二句戛然而止。自第三句起,诗人便站到了画外,以观画者的身份品评画作。
但如果用叙述者内聚焦的叙事方式来解读这首诗,诗歌的意境将会更加深长浑融。画家画技高超,诗人观之,不觉将自己置身于真境中,他仿佛就站在苕溪边,凝视着水面上浮现着的对岸道场山映射下的倒影,他望着出神,回想起今年夏天水中铺展开的片片荷花。现在已经是深秋,若此时荷花依旧,真想划着只橛头船到荷花中间幽闲垂钓。若按这样解读,“只欠荷花三十里,橛头船上把渔竿”此句便为诗人观画时所兴发的追忆和联想,是虚写;而“道场山麓接何山,影落苕溪浸碧澜”则为诗人对画中所画之景的真实描摹,为实写。其实我们很容易发现,诗歌后两句也是在变相地反映画中的真实信息。这样的解读方式,一实一虚,虚实结合,使得整首诗更富有纵深感,诗中幽微曲折的情感完全来自诗人主观的体验和感受,主人公(诗人)给读者一种已出画外又似在画中的朦胧恍惚之感。
用人物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也可以解读这首诗。与唐代重抒情、重写实的整体创作倾向不同,“‘尚意’是宋代诗歌与绘画的理论核心”[2]165。“题画诗作为诗人观照画图之后的创作,是诗画之间的桥梁,其尚意之精神尤为明显。”[2]165宋代画家注重通过所绘之景物表现自我之情性意兴;观照此类画作,诗人也更乐于去感受、去探索创作背后的主体精神。范成大一生与画家交往颇多,熟悉画艺,除诗歌外,他的两本著作——《菊谱》和《梅谱》也充分地表现出他的审美旨趣和审美成就。因此,范成大在创作题画诗时,也应会主动通过画中景象去洞悉、去表现画家的内心,以及画作中蕴藏的深意。如果用人物内聚焦的叙事方式来解读《题米元晖吴兴山水横卷》这首诗,米元晖是真实山水的聚焦者,画作中必然融入他在观赏山水时的想法和心情,可以说画家虽未出现在画中,但已然成为画中隐藏着的主人公。而对于诗人而言,他在观照画作时,就需要尽力去感受、去诠释画家在这一笔一划的勾勒描摹中,所寄寓的情感与深意,并通过诗歌的形式替画家表达出来。范成大揣摩,或许米元晖在观赏眼前山水时,会遗憾不见那十里荷花和渔人打渔的场景吧!因此,无论从叙述者内聚焦的角度,还是人物内聚焦的角度来解读这首诗,诗歌的一、二两句均系实写,而三、四句则为虚写。
人物内聚焦的叙事方式更多见于范成大的人物类题画诗中,如《题汤致远运使所藏隆师四图》其二《倦绣》:
猧儿弄暖缘阶走,花气熏人浓似酒。
困来如醉复如愁,不管低鬟钗燕溜。
无端心绪向天涯,想见墙竿旛脚斜。
槐荫忽到簾旌上,迟却寻常一线花。[5]123
诗人虽不点明,但读者很容易从字里行间感受到此诗的主人公应是个思妇,并把她当作诗中的聚焦者。整首诗便是思妇以第一人称“我”的身份进行的自述,无论是眼中所见、鼻中所闻,甚至于心中所想,都来自于人物自己的声音。除本诗第一句外,在其余的七句中,诗人通过细节描写紧扣思妇的内心世界,表现出人物忧愁沉郁的情感。梦醒后思妇感到力疲涣散,无心梳妆,却怨是花气熏得人迷离懒散。一种思绪莫名地涌现,飞向天涯,那是丈夫征战的地方。此时,思妇眼中仿佛望见远处长杆上的旛旗任风斜吹的场景。从这无边的愁绪中晃过神来,已是傍晚了,夕阳斜照,槐树的影子落上窗帘,思妇低头看看手中的绣花,还差一线才绣满。
读过此诗,想必读者多会惊喜于范成大对诗中主人公内心世界的刻画,竟如此细腻生动。叙事完全从思妇的单一视角出发,形象立体鲜活,如在目前。尤其是“槐荫忽到簾旌上,迟却寻常一线花”这句,初看之,只是对环境的描写,并不触及心理活动;但细品之,我们不仅可以透过字面看到此刻思妇抬头低头的动作,还能感受到她因心事重重而无心针线的忧郁不安的神情。此句曲折婉转却又有力地加深了整首诗的情感强度,使诗歌萦绕上一种思妇的无奈又遗憾的心情。“画面叙事功能的完成有待于接受者的想象和补充,题画诗则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补充的功能。”[7]的确,画中所呈现的或许只是一个妇人在窗前刺绣,这是画面上实有的场景,而具体的事件,人物此时的内心世界就要靠诗人的想象灌注进去,才能使平板的画像成为鲜活的事件中的人物,这便是虚笔。
二、表现图像中富有包孕的片刻
绘画是空间艺术,只能表现静态的画面,呈现动态事物的瞬间状态。诗歌则可超越时空,表现持续性的动作和情节。画家若想在画作中充分表露其意,让观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领会到画中深意,就需把所寄托之情志浓注在画面定格的这一瞬间里。德国美学家莱辛称这一瞬间为“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他在《拉奥孔》第十六章中说到:“绘画在它的同时并列的构图里。只能运用动作中的某一顷刻,所以就要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使得前前后后都可以在这一顷刻得到最清楚的理解。”[8]170诗人创作题画诗,则需准确捕捉画面中呈现出的“这一顷刻”,追溯过去、推想未来,利用诗歌自身的优势更好地补足画意,尽可能传达出画家之意。因此,“选择‘最富有孕育性的那一顷刻’来表现生活,便成为画家的艺术使命;同样,题画诗人便将画面上的‘那一顷刻’因诗句写出来,也就成为题画诗人的艺术使命。”[8]171范成大在书画艺术方面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高超的审美造诣,故多能把握画中所蕴藉之意。我们今天虽无法看到范成大所题画作的原貌,但通过诗歌内容,读者很容易能感受到诗中对于“这一顷刻”的精确捕捉,基于“这一顷刻”,诗人想象过去和未来,在诗中安排故事情节,生动地传达出画中之意,有些甚至极富有戏剧性。
如《题徐熙风牡丹二首》其一《紫花》:
蕊珠仙驭晓骖鸾,道服朝元露未干。
天半刚风如激箭,绿绡飘荡紫绡寒。[5]344
徐熙为五代画家,与黄筌及其子居寀均以善画花鸟著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云:“时谚云‘黄家富贵,徐熙野逸’,不惟各言其志,盖亦耳目所习,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也。……徐熙江南处士,志节高迈,放达不羁,多状江湖所有汀花野竹,水鸟渊鱼……”[9]258董逌《广川画跋》卷三《书徐熙画牡丹图》中称,徐熙的画品“神形俱完”,以“自然”取胜,“徐熙作花,则与常工异也,其谓可乱本失真,非也。若叶有向背,花有低昂,氤氲相成,发为余润,而花光艳逸,晔晔灼灼,使人目识眩耀,以此仅若生意可也。赵昌画花,妙于设色,比熙画更无生理,殆若女工绣屏障者。”[9]265从上述画论可知,徐熙为人高洁自适,淡泊名利,他的花鸟画,重在传达对象的“神”“意”和“气骨”,自然野逸,神韵灵动,表现出清雅高致形象背后的内在蕴意。
范成大所题的这幅徐熙的《牡丹图》,从诗题和诗歌内容可以推想画中景物应为在风中摇曳的紫色牡丹,诗人紧紧抓住画中牡丹这一不畏疾风、在风中洒脱强韧的姿态,结合画家高雅闲放的气质,为画面设想情节。诗中将紫花比喻成蕊珠仙人,《蕊珠经》又为道家的一部经籍。天刚晓时,蕊珠仙人驾着鸾鸟,身披道服准备去朝拜老子,露水点点沾湿她紫色的袍子。突然暴风袭来,就像激烈的飞箭直挺挺地迎面射来,一场猛烈的躲闪过后,只见蕊珠仙人的道服在风中飘荡。“天半刚风如激箭,绿绡飘荡紫绡寒”这一描写极具戏剧性,使整首诗的节奏在此处如坐过山车般,突然一下加速上升,但这紧张的时刻又如一阵风吹过般短暂,随后又急速下落,归于长时间的平静。像拍摄中的短镜头与长镜头,瞬间的激战过后,镜头久久聚焦于风中飘荡的道服。图画中紫色牡丹所呈现出的“这一顷刻”的状态是引发诗人想象的现实基础,故事情节的展开都依托于它,全诗围绕“这一顷刻”,形象地传达出画作之意,表现出风中牡丹的精神气质,同时也暗示了画家以及诗人的精神境界。
又如《题黄居宷雀竹图二首》其一:
群雀岁寒保聚,两鹑日晏忘归。
草间岂无余粒,刮地风号雪飞。[5]345
黄居寀,黄筌之子,以花鸟画最擅名。所画形象细笔勾勒,设色精细富丽。蜀郡范镇《东斋记事》卷四称:“黄荃、黄居寀,蜀之名画手也,尤善为翎毛。其家多养鹰鶻,观其神俊,故得其妙。”[9]262亲自体验观察,故黄居寀所画禽鸟动作灵动生趣,形态逼真传神。范成大所题的黄居寀的这幅《雀竹图》,诗歌一、二两句,运用拟人的手法描写了群雀归巢取暖,而两只鹌鹑仍辛苦觅食,日晚忘归的场景。诗人精准地抓住画中所呈现的这两种鸟的状态,短短十二个字简洁而又生动地将它们的神态、动作表现出来。“草间岂无余粒,刮地风号雪飞”这句描写出了生存环境寒冷恶劣,反问句式增强了情感力度,隐约让人觉得一股愤怒的情绪隐藏在其中。周汝昌《范成大诗选》云:“大约从淳熙十二年(乙巳﹒一一八五)起,他同情人民疾苦的诗显著增加,例如题《雀竹图》时,不忘记写出‘草间岂无余粒,刮地风号雪飞。’……而且表示出:‘汝不能诗替汝吟!’这种愿为喉舌的精神,何等令人感动!”[10]“草间岂无余粒,刮地风号雪飞”这句,带有诗人强烈的主观情感在其中,此情感虽并非为图画的原意,显然是诗人基于画面呈现出的“这一顷刻”展开的想象和延伸,但诗人通过这虚笔,借画中群鸟的形象,所表达出来的情感却是真实而可贵的,这也为画图中的“这一顷刻”增添了不少动人的力量。
再如《题易元吉獐猿两图二首》其二:
鸟逐山公噪,惊麋仰望疑。
春林无一事,獝狘自生悲。[5]351
易元吉以獐猿作为其作画的专攻方向,为了表现出猿猴、獐鹿之类的自然天性,“易元吉深入深山丛林,‘以觇猿狖獐鹿之属’,及穴窗窥伺水禽动物的‘动静游息之态’。……而这一行动所要付出的艰辛代价,有时甚至需要冒着生命的危险。”[9]278易元吉的这种精神着实难能可贵,也正因为如此,其流传下来的画作,所画对象栩栩如生,灵动传神。范成大所题的易元吉《獐猿图》,诗歌一、二两句形象地描绘了画图中所呈现的“那一顷刻”。“山公”为猿猴,鸟儿和猿猴在树上嬉戏,猿猴一手挂在树上,另一只手想去抓挠围绕着它嘈杂的鸟儿,烦躁气愤地发出叫喊声。低头悠闲吃草的麋鹿被猿猴的叫声惊扰,仰头望着鸟儿和猿猴打闹出神。画面所定格的“这一顷刻”被诗人捕捉,并表现在诗歌的一、二句中。尤其是句中的“噪”和“疑”二字,分别属于声音描写和心理描写,这都是图画中无法直接表现出来的。而诗人透过画中所呈现的这一静态顷刻,想象动态场景,化静为动,加入“噪”“疑”二字,使得所描绘的场景立刻鲜活灵动起来。“春林无一事,獝狘自生悲”,诗歌三、四句是诗人由一、二句自然生发出的想象。诗人借助以动衬静的手法,此处的喧闹躁动,更显出春天山林的静谧,而本是猿猴嬉戏打闹的叫喊声,却让山林中的飞禽走兽们听之心生悲戚。一、二句与三、四句之间,一动一静,一喜一悲,两相对比下,使得整首诗歌增添上了一层难以言说的深意。
三、聚焦于“虚”
范成大在题画诗的结尾部分,时常将读者的目光引向一个渺远的、虚空朦胧的意境中。此类题画诗的结构通常是,诗歌前几句,在如实地描述画面的同时,通过联想自然地将其中的叙事因素接续过来,呈现出一个有叙事性的场景;结尾几句,视角则从实在的场面转而聚焦于一种旷远虚无的景象中。这种结构方式,表现出一种诗歌中的虚实关系。
“诗与画的美学旨趣基本一致,都是力求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通过有限的形象来表现味外之旨,深远之致。”[11]值得注意的是,这有限的形象,还需以虚实关系来结构才能使作品中的所状之景与欲表之意得到更充分的表现。
就绘画而言,中国画是特别讲求虚实共构的,清方薰《山静居论画》说:“古人用笔,妙有虚实,所谓画法,即在虚实之间。虚实使笔,生动有机,机趣所之,生发不穷。”[8]339画面通常设近景和远景来表现层次感,近处一般聚焦于具体的、实在的景物,它们是整个画面意境得以生成的基础;远处则常不着点墨,唯留空白一片,“这种空白,在画家笔下,可以‘作天、作水、作烟断、作云断、作道路、作日光’,构成为整体画面的有机部分。”[12]它的存在能够点染和升华整个画境。在这远与近的结构安排上,画家之意往往就深蕴其中。中国古代诗歌也极为注重虚实相生,宋范晞文《对床夜话》引周伯弼“四虚序”云:“不以虚为虚,而以实为虚,化景物为情思,从首至尾,自然如行云流水,此其难也。”[8]339宋代题画诗侧重表“意”,诗人一方面要忠于画面,尽可能地表现画家之意;另一方面,诗人也乐于在诗中婉约含蓄地表达自己的观画感受。如何将画中之物与“意”自然结合于诗中,表现出韵外之致,营造出浑融的意境?这就要看诗人如何用一双妙手调和诗中“虚”与“实”的关系。
范成大的题画诗,运用聚焦于“虚”的叙事方式,寄所欲表达之意于虚无的场景中。诗歌由实而虚,虚实相生,情意就在这虚空中浑厚、绵长,此“虚”可谓是“有意味的虚”。
如《题画卷五首》其二:
欹倾栈路绕山明,隔栊人家犬吠声。
无限白云堆去路,不知谁识许宣平。[5]113
整首诗简练明了,二十八个字充分地传达了图画中的信息,读来极具画面感。诗人虽“不著一字”,但读者仍能感受到一位画中人的存在,他或真实出现在画面中,或只是画家、诗人在创作时寓己于画,将内心情志隐藏在画像背后。一、二两句,交代了时间、地点和事件,跟随着诗人的指引,读者仿佛看到崎岖的山路,耳边传来阵阵犬吠的声音。三、四两句,由实入虚,读者的视线继续跟随着诗人,聚焦到了山路尽头,那里堆积着大块大块的白云,白云那头可能是仙界,是诗人向往之地,不知这附近的人家可曾见过隐居修行的道士许宣平?眼前所见唯有一片虚空朦胧,以此场景收束全诗,将整首诗歌笼罩上一层虚幻飘渺的氛围。范成大在此诗中运用聚焦于“虚”的叙事方式,不仅有助于反映图画中的画家之意,为引出许宣平营造了相契的环境,同时也拓展了整首诗歌的空间,从山林中延伸至山路尽头,再进一步延伸到白云那头。诗中无一字论及情感,但读者仍能从眼前这片“虚”景中读出诗人寄寓其中的想法和心情。在这首诗中,诗人将解读和诠释的权力交予读者,尽量少地运用一些指实的字眼去干涉读者的判断,为我们提供自主思考和想象的广阔空间。
又如《题画卷五首》其五:
秋晚黄芦断岸,江南野水连天。
日色微明鱼网,雁行飞入苍烟。[5]23
全诗四句都是对画面的描写,诗人的视线循环往复,一、二句和三、四句均呈现出由近而远的视觉规律。诗句开端的“秋晚”一词交代了季节,然后诗人的视线从江岸边七倒八歪的枯黄的芦苇,延伸出去,越过广阔的“江南野水”,停留在更远处的水天相连的地方。第三句中的“日色微明”交代了具体的时间,深秋的清早,晨光微熙,诗人的目光先落在了岸边搭起的架子上铺晒着的鱼网,再过些时候,渔人就要纷纷来到岸边收起鱼网下海捕鱼了吧!那时整个渡口就该繁忙热闹起来。思绪回来,诗人抬头望见天边一只像是落单了的大雁,消失在苍茫的云烟中。诗歌对画面中的景物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但读来并不觉得局促,原因就在于诗人对物象的安排有疏有密,虚实相间,恰到好处。“黄芦”“断岸”“野水”“雁行”“鱼网”,在这些实在的具象中,诗人穿插进了“秋晚”“连天”“日色微明”“苍烟”这些模糊的、虚幻的、偏重于感觉的词语。虚实相济,使得整个画面富有节奏感,丰满灵动,眼中所见仿佛都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水雾,给全诗也笼罩上了一种晚秋迷蒙寂寥的气氛。“诗人、画家运用‘虚实相生’之法,贵在多变化,要做到实处有虚,虚处有实,密处要有疏,疏处要有密,实中有虚,虚中有实,虚实相生相济,整幅画面、整首诗歌变通而有灵气。”[8]342无论是一、二句,还是三、四句,读者的视线跟随着诗人移近就远,依次向更高远处流动,最后聚焦在朦胧一片的云雾中。
再如《李次山自画两图,其一泛舟湖山之下,小女奴坐船头吹笛》:
船头月午坐忘归,不管风鬟露满衣。
横玉三声湖起浪,前山应有鹊惊飞。[5]128
诗题已经简单地交代了图画中的场景,诗人在诗中又对画像做了更加细致的刻画。结合题目和诗歌一、二两句,我们眼前浮现出这样的一幅画面,寂寥的午夜,皎洁的月光映照出远处湖山下的一叶扁舟,孤舟在偌大的湖面上晃动,随着雾气升腾忽隐忽现。突然耳际传来动人的笛声,顺着声音寻去,才发现船头正坐着一位十二、三岁的吹笛的少女。和上一首诗歌的结构相同,此诗开头两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和事件,同时加深了画中小女奴的形象。在第三句中,诗人运用通感,化虚为实,将看不见的笛声诉诸眼中可见的湖面浪起。视角也从聚焦于船头吹笛的小女奴,转而跟随着浪花渐渐推去的方向,聚焦于更远的地方。读到这里,读者很容易感受到视界的突然扩大,眼前是一片澄澈的夜色,远处水和天交融在一起,空旷虚无仿佛没有尽头。如果诗人在第四句中,延续甚至追加这种虚无感,整首诗就会显得过于清冷虚空,生趣不足。而此诗之妙就在,诗人于此句中又添进了几个实在的物象,不仅有视觉上的山和鹊,还有听觉上的惊鹊扑腾翅膀的声音,整首诗歌的空间又被进一步扩大至山外山、水外水。“应有”二字虽表明其为想象之景,但也是基于前句所营造的意境,而生发出来的合理的联想,眼中聚焦是虚无,而心中却生出想象之花,也能算得上是无中生有,虚中见实了。
综上所述,范成大题画诗所呈现的这三大叙事性特点表明了,作为南宋“中兴”时期诗坛的代表性人物,范成大的诗歌创作顺应了同时期诗歌发展转变的总体趋势。阅读其题画诗,我们能够感受到,诗人对于内在情感体验的强调,对于物我之间感发兴会的重视,以及诗人深厚的审美功力。更可贵的是,在各类题材的诗歌创作中,范成大都能自觉借其作品为劳动人民发声、代言,表现出作为一名时代诗人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1] 吉川幸次郎.宋元明诗概说[M].李庆,骆玉明,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10.
[2] 钟巧灵.宋代题山水画诗研究[D].扬州:扬州大学,2006.
[3] 周剑之.泛事观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叙事传统[J].国学学刊,2013(1):140.
[4] 孙学堂,林宗正.“诗家夫子”的聚焦“魔镜”——王昌龄乐府七绝的叙事学观察[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1).
[5] 范成大.范石湖集[M].富寿荪,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 钟巧灵,陈天佑.范成大题画诗论[J].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6).
[7] 周剑之.宋诗叙事性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2013:197.
[8] 吴企明.诗画通融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8.
[9] 王朝闻,刘福星.中国美术史:6[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0] 周汝昌.范成大诗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6.
[11] 祝振玉.略论宋代题画诗兴盛的几个原因[J].文学遗产,1988(2):94.
[12] 朱靖华.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虚实论及其艺术表现技巧[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3):94.
The Narrative Art of Fan Chengda's Poems with Painting
FAN Yue
(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0, Fujian, China )
Song poetry shows a clear and increasing trend of narrative, and Fan Chengda's poems of paintings also conform to this change, showing strong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He uses the narrative perspective to express the feelings of viewing paintings, or embedding himself in the painting, expressing his meaning, consciously trying to figure out the paintings, conveying the meaning of the painter. He accurately comprehends the moments that are rich in the painting, and then infer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He envisages the plots in the poem, which better expresses the meaning of the painter and at the same time makes the scene in the painting more vivid and agile. Through the narrative method of focusing on the “emptiness”, it creates an artistic conception of poetry that is empty and far-reaching, and expands the poetry capacity and extends the poetry space.
Fan Chengda, poems with painting, the narrative, virtual reality
I222.7
A
1673-9639 (2020) 05-0037-07
2020-07-13
范 悦(1995-),女,福建永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诗词。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