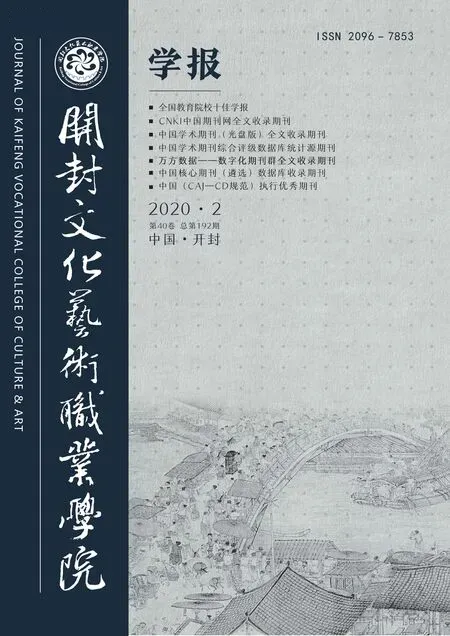胎儿的损害赔偿司法裁判实证分析
朱光辉
(青海民族大学 法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6 条明确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据此条规定可认定,胎儿享有的权利是附解除条件的权利。在此立法背景下,本文主要对胎儿的损害赔偿司法裁判进行实证分析,以两个典型案例展开,对胎儿利益的保护提出切实可行的立法建议和司法建议。
一、胎儿的损害赔偿研究现状
对于胎儿是否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在《民法总则》出台之后,学界达成了统一意见,即承认胎儿的民事主体地位。关于胎儿的民事权利,《民法总则》也只是明确胎儿在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两方面享有权利,其他权利只是用“等”字予以概括,并不明确。这个“等”字是否包含损害赔偿请求权,学界仍存在较大争议。杨立新[1]763教授认为,侵权损害赔偿是指当事人一方因侵权行为而对他方造成损害时应当承担的补偿对方损失的民事责任。对权利人来说,损害赔偿是一种重要的保护民事权利的手段;对义务人来说,它是一种重要的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梁慧星[2]教授认为:“胎儿在遭受侵害时可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李永军[3]教授认为,这种损害赔偿请求权仅仅是因果关系问题,而不是权利能力问题,胎儿因未出生前受到的损害发生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根本没有必要通过权利能力的方式解决,从保护胎儿的实际效果来看,采用因果关系的方式更为恰当。笔者认为,胎儿基于《民法总则》第16条的规定享有民事主体资格,且我国裁判实务中已经有了地方法院承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为了更好地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以及顺应国际上对胎儿保护持肯定态度的趋势,赋予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是合法的,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
二、典型案例简介
(一)李某、付某诉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①
李某与付某系夫妻关系,李某于2019 年3 月5日在山东省平原县第一人民医院(以下简称“县医院”)待产。当日行子宫下段剖宫产术与子宫次全切除术,术后产下一男婴,外观无畸形,新生儿无呼吸及心跳。山东金剑司法鉴定中心出具[2019]临鉴字第225 号法医临床司法鉴定意见为:李某待产期间,胎心变慢,医方没能及时予以剖宫产最终致胎儿死亡,由于胎盘早剥并发DIC 等,以致子宫次全切除,县医院的医疗行为具有过错,与李某的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本案(以下简称“案例一”)经过二审终审判决,法院最终认定县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过错,应当对李某的合理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胎儿娩出时为死体,该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县医院对李某、付某因胎儿死亡造成的精神损失承担一定赔偿责任。判决县医院赔偿李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鉴定费、交通费、精神抚慰金合计205 664.4 元;判决县医院赔偿付某精神抚慰金20 000 元。
(二)杨某、唐某诉临桂西城医院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②
杨某、唐某系夫妻关系,杨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临桂西城医院(以下简称“西城医院”)住院待产,于2018 年2 月6 日产下一新生儿毛毛,2 月7 日新生儿毛毛因抢救无效死亡。司法鉴定意见为:西城医院对杨某的诊疗行为未尽到告知义务,出现胎儿宫内窘迫未引起高度注意,处理及手术治疗欠及时,一定程度上延误了胎儿宫内窘迫的最佳治疗时间,毛毛出生后的复苏治疗不符合规范,医方的诊疗行为与毛毛重度窒息、呼吸衰竭及后期死亡等存在主要因果关系,参与度为70%。
本案(以下简称“案例二”)经过二审终审判决,法院认定新生儿毛毛出生后系活体,具有民事主体地位;司法鉴定意见具有科学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法院予以采纳。故判决西城医院赔偿杨某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尸检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498 547.95 元。
三、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实证分析
(一)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
依《民法总则》第16 条之规定,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是附条件的,胎儿娩出为死体时,胎儿权利自始不存在。在案例一中,新生儿娩出时是死体,法院认定该胎儿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在案例二中,新生儿毛毛娩出时是活体,哪怕出生后不久即死亡,也不能否认新生儿毛毛的民事主体地位,法院也要认定新生儿毛毛具有民事主体地位、享有民事权利,保护新生儿毛毛的健康权、生命权等合法权益,因此,关于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在立法与司法上高度一致。事实上,在《民法总则》颁行之前,司法实践中已经将胎儿权利限定为娩出时为活体这一条件③。《民法总则》第16 条只是将这一通行的司法实践上升到基本法的地位,强化了对胎儿权利的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胎儿民事主体地位的合法化将同我国刑事法律相冲突,因为堕胎行为在我国是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所禁止的,堕胎行为的再认定问题将会成为日后法律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堕胎行为的举证问题是核心所在、难点所在,但学界不会因此而回避。
(二)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民法总则》第16 条没有对胎儿的权利作出详尽的规定,学界对胎儿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仍存在争议,但主流观点是支持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在民事权利方面,基于侵权而享有的各种请求权是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权利。国内学者王利明④教授认为:“胎儿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在其出生后,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此,梁慧星教授也持肯定观点,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法总则》第16 条规定中的“等”字包含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案例二中,虽然新生儿毛毛在胎儿时期因医方的不当诊疗而出生后不久即死亡,但是法律认可他的民事主体地位。基于请求权基础,即侵权行为、因果关系、损害结果和主观过错,可以认定西城医院对毛毛的健康权构成了侵权,这种侵权可以溯及新生儿毛毛作为胎儿时期的生命体。法院最终的判决中也是支持毛毛的损害赔偿,即死亡赔偿金,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也是认可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还有一个问题,即当胎儿因侵权而导致其娩出时是死体的法律责任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基于权利主体举证困难,往往不认可此情况下胎儿的民事权利能力,而将其视为母亲身体的一部分,以对母亲的健康权侵害为由支持母亲的侵权损害赔偿。这是现行法对胎儿权益全面保护的漏洞,系当下司法鉴定技术不发达所致。笔者相信,随着科学技术和法学理论的发展,胎儿的权益将会得到全面、有效的保护。
(三)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
在案例二中,对于新生儿毛毛在胎儿时期所受的侵害,法院并没有支持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法院支持了毛毛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这也是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胎儿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那么也就享有基于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理论上是这样的,但理论同实践存在一定差异。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不会支持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将这种请求权在父母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中间接实现。这大致是因为胎儿出生后,作为新生儿,其心智极其不发达,不能感知和表达,导致精神的损害无法认定。笔者认为,胎儿也是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能因为其心智与感知而否认胎儿的精神损害,这是违背公平原则的。此外,基于平等原则,鉴于合乎法律规范的精神性利益对同等保护的相适应进而认可胎儿享有诉请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4]。考虑到胎儿权利的特殊性,需要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期限的起点作特殊规定。《民法总则》第191 条规定:“未成年遭受性侵害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笔者认为,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可以参照此条规定,将胎儿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在新生儿成年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精神受到损害之日时开始计算”。这样就可以很好地支持胎儿的精神损害赔偿的权利,在司法实践中也具有切实的可操作性,进而全面保护胎儿的损害赔偿 请求权。
结语
保护胎儿的合法利益是法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权的要求。胎儿作为人生命体的特殊阶段,应当同自然人予以区别对待,在立法上作出特殊的规定。立法的目的在于司法实践,而司法实践又能进一步弥补立法的不足,二者相辅相成。只有充分而全面地分析胎儿利益保护的司法实践,才能更好地在立法上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进而切实有效地保护胎儿的权益。
注释
①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山东省德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9)鲁14 民终1736 号。
②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桂03 民终3730 号。
③案例来源于中国裁判文书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8)湘民再225 号与广东省江门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5)江中法民一终字第854 号。
④王利明教授主持起草的《中国民法典人格权法编(草案)建议稿》第59 条规定“胎儿的身体健康受到损害的,在其出生后,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