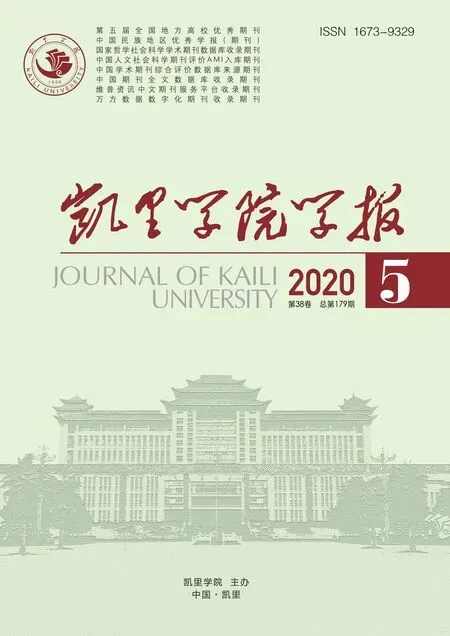“气韵生动”是影视艺术的生命
何天洋
(贵州广播电视台,贵州贵阳 550002)
本文之所以提出“‘气韵生动’是影视艺术的生命”这一观点,乃是基于这样几个原因:一、中国文艺向来重视“气韵”和“意境”的传统;二、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绘画中的“气韵生动”说;三、绘画艺术与影视作品在艺术本源上的相似性与共通性;四、从大量影视作品的创作和接受实践中感受和归纳出来的经验等等。
下面本文将分别对这一理论的渊源及其适用的可行性以及笔者对这一理论进行的若干改造和生发作一个粗疏的说明。
一
在中国古代文艺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对气韵、意境的强调可说是一脉相承、从未间断。从庄子的“得意忘言”、孟子的“养气”说开始,到刘勰“神与物游”“意翻空而易奇”的“神思”,皎然的“气象氤氲”“风韵朗畅”,司空图“超以象外,执其环中”的“味外之韵”“韵外之旨”,梅圣俞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苏轼“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的“高风”“远韵”,严羽“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兴趣”,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一起勾勒出一条中国文艺理论重视气韵和意境的粗大红线。
这种理论同样深深地影响到自魏晋时期才真正兴起的中国绘画,并在绘画创作实践中得到充分发展。关于“气韵生动”的说法,便最早见于南朝画家谢赫《古画品录》一书。谢赫当时是将它作为“绘事六法”之一提出来的。原文如下:
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1]213
按照叶朗先生的解读,谢赫所谓的“气”乃是指“画面的元气”,既是“宇宙元气和艺术家本身的元气化合的产物”,也是“艺术的生命”;而“韵”则来自魏晋人物品藻中的“风韵”一词,转到绘画上,就是“要求人物画表现一个人的风姿神貌”。至于“生动”则是对“气韵”结果的一种形容,或者说是“画面”具备“气韵”之后的一种必然结果。按叶朗先生的原话,即“有了‘气韵’,画面自然‘生动’”[1]219-222。
谢赫“气韵生动”说的最大意义便在于他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古代绘画重气韵和传神写意的美学标准。自此以后,中国画界关于“气韵生动”说的注解和在其基础上生发出来的理论一直层出不穷。比如,五代的荆浩就在《笔法记》中对“气韵”二字作如此解释:“气者,心随笔运,取象不惑。韵者,隐迹立形,备遗不俗。”[2]52显然,这里“气”主要指构思取材方面的谋划,“韵”则是画作表现出来的一种“不俗”的风格和韵味。清代的唐岱则明确提出“气韵者非云烟雾霭也,是天地间之真气”的观点。(唐岱《绘事发微·气韵》)而与之同时的著名画家邹一桂则在其《小山画谱》中说:“以万物为师,以生机为运,见一花一萼,谛视而熟察之,以得其所以然,则韵致风采,自然生动,而造物在我矣。”[3]可见,邹一桂的“气韵”指的是事物的“韵致风采”,其“生动”则指事物表现出来的“生机”。在他看来,这种“韵致”和“生动”是在画家潜心观察万物,了解和把握其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近人张大千也曾表述过类似观点,他在给其弟子王永年谈作画经验时说:“画山水时,应当观察山水在晴雨朝暮和烟云变幻中的种种奇妙变化,且要眼观手记,心领神会,方能得其灵秀之气。”[4]149还说:“作画,务求脱俗气,洗浮气,除匠气,去秽气!”[4]69由此观之,被誉为“五百年来第一人”的张大千所极力推崇的仍在于一个“气”字。
在邹一桂之后约半个世纪的安徽画家黄钺更是将“气韵”列为画品首格,其释词为:六法之难,气韵为最,意居笔先,妙在画外。如音栖弦,如烟成霭。天风冷冷,水波濊濊,体物周流,无大无小。读书万卷,庶几心会。(黄钺《二十四画品》)从中可见,黄钺所言之“气韵”其意义大致与五代荆浩所释相近,也主张在下笔之前先立意,并重视画外的“余味”,且认为这种“余味”是具备一定知识和鉴赏力的人才能心领神会的。
宗白华先生在分析谢赫的“六法”时则指出,“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并认为“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2]51而“生动”则是指灵动、有生气。要使画作“气韵生动”,艺术家必须发挥自己的艺术想象。他最终的结论是,“气韵生动”说是谢赫对于汉代以来的艺术实践的一个理论概况和总结,是他之于绘画而提出的一个美学要求。
从上述有限材料中可以看出,前人对于“气韵生动”解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对“气”“韵”的具体所指,以及如何具有“气韵”的不同阐释上。尽管对“气韵生动”说的解释殊多,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将“气韵生动”视为绘画艺术的生命和最高美学原则。这不仅可以从流传至今的诸多伟大画作上得到印证,而且还为今日画界创作者所遵循。
二
作为中国古代绘画理论的“气韵生动”说何以能应用于诞生于现代科技之上的影视艺术呢?这还得从绘画艺术与影视艺术的相似性和亲缘关系上说起。
根据电影理论大家安德烈·巴赞的观点,电影与绘画诞生的动力本源其实是相同的,都起因于人类妄图“复制外形以保持生命”的“木乃伊情结”。而从电影自身的发展历程来看,不管是中国早期的“皮影戏”还是西方的“幻盘”,电影的早期雏形实质上就是一种“活动的画面”。尽管电影(包括电视)发展到今天,早已成为一门相当成熟,并且享有独立地位和巨大社会影响的综合艺术,尽管它经历了无声到有声、黑白到彩色、胶片到数码这样几个巨大的转折和进化阶段,但一个基本的特性却是始终未变的,那就是它的视像性,即“以活动的画面形象作为基本表现手段,主要诉诸于观众视觉的性质。”[25]无论什么电影,也无论它发展到何种阶段,它都很难改变“画面是电影语言的基本元素”和“原材料”(马赛尔·马尔丹言)这一最根本的事实。
更让人感到惊异的是,中国古代画人在作画过程中已经掌握并运用到类似于今天的电影手段。宋人郭熙在其《林泉高致·山水训》中对当时“写真”之法就有如此记述:
学画竹者,取一枝竹,因月夜照其影于素壁之上,则竹之真形出矣。
以今日电影之“投影术”观之,其中的“真竹”便是底片,“素壁”无疑是银幕,月光则是投射光源,素壁之上得出的竹影则相当于电影画面了。
然而其间还有一个问题应予足够重视,那就是郭熙为何主张对影揣摩,而不是竹子本身?让·米特里曾经指出,“电影的主要魅力就是‘实在内容’成了电影自身的虚构元素。‘实在事物’变成‘非实在事物’,或者‘可能存在的事物’,或者‘只能如此存在的事物’,一个被改观的事物……我们看到的是目睹过的东西的一个影像,但在影像中,具有明显的美学效应的现实比其原貌更完美。”[6]对比之下,我们不难看出,那时的郭熙已在朦胧中具有了让·米特里的这种现代意识(也即费尔巴哈所指出的“符号胜于物体,副本胜于原本”的思想),而这种意识正是居依·德波这样的后现代影视理论家之核心观点的立论根基。在居依·德波的“奇观”理论中,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在现代生产条件蔓延的社会中,其整个的生活都表现为一种巨大的奇观积聚。曾经直接地存在着的所有一切,现在都变成了纯粹的表征。”[7]现代摄影技术对物质现实的高度还原能力及其可以无限复制的特性使得“表征”比存在的本来事物还要真实和易见、可感。就像今日大家所看见的影视作品一样,绝大多数都是经过对现实还原的作品进行再复制后所得的“表象”,而真正的“母本”却不知所往。而这一切,都不得不归功于本雅明所谓的“机械复制时代”的现代摄影术。
相对于中国绘画而言,西方绘画一直比较注重形似、写实,其开始注重表现精神、气韵要比中国晚得多,差不多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正如安德烈·巴赞所指出的那样,“到了15 世纪,西方绘画开始不再单纯注重用特有手段表现精神现实,而力求把对精神的表现和对于外部世界尽量逼真的描摹结合起来。”[8]3而在追求逼真、传神上,这一时期发明的“透视画法”无疑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制造出的三维空间幻象,已经能让物象同我们看到的实际物体相仿。除了不能表现运动这一缺陷,它已经使绘画十分接近电影给人们制造的“虚幻的真实”。
当然,摄影和绘画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在逼似事物本真、动态记录生活方面,摄影远远优越于绘画作品,这一点也早为人们所公认。对此,巴赞的论述比较充分。其最终得出的结论便是:“摄影的客观性赋予影像以令人信服的、任何绘画作品都无法具有的力量。”[8]7
尽管摄影在诸多方面要优越于绘画,但是,在以画面来表现生活、传达观点和审美意趣这一最终诉求上,二者却是相同的——它们都必须主要依赖于“画面”这样一种基本的物质材料来实现(尽管电影还有音响、音乐、灯光等等其他物质材料)。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许多有关绘画的理论和原则也同样适用于电影画面。
事实上,前人早已做过性质相近的工作。比如,蒙太奇理论之集大成者爱森斯坦就曾结合中国的“文人画”来谈电影镜头的造型性和概括性。[9]35-36
三
本文在将“气韵生动”说应用于现代影视艺术本体及其美学特征的分析时,既保留了它原先的“合理内核”,也对其内涵和外延做了新的拓展。具体而言,这里的“气韵生动”是指:影片必须具有丰富的思想、独特的韵味和风格,与现实生活具有本质上的联系,并反映人类的生存需求和生存状态,而且,这种反映还必须是动感的、富于生气的。总体上,它指向一部影视作品的思想内蕴和整体精神,在相对微观的层面上,也指向影片具体的结构、节奏和种种叙事技法以及在此基础上呈现出来的外在风格等。
(一)影视艺术“气韵生动”说的特殊含义
1.“气”——影视作品内在的灵魂和核心
它是影片整体呈现出的一种思想、精神和情感倾向。同时,也是影片创作的生机和动力。它在导演个人的气质和美学追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叙事和技术手法而生成,影片中所有的有机元素都可说是它的构成材料。不仅包括影片的结构和故事情节,也包括影片的主题思想。而其最直接、最可能被观众感知的便是其外化表现的“韵”。
在“气”的形成过程中,导演的个人气质和美学追求是最核心的内容。这种独特的气质和美学追求直接影响到影视作品的选材、结构和影像风格。比如吴贻弓醉心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电影的诗意追求而着意营造的那种抒情写意的散文诗式风格,张艺谋对浓墨重彩的偏爱及他对颜色别具匠心的影视运用,霍建起对江南水乡风情的热爱而表现出的那种独特的烟雨江南的氛围等等。这不仅是他们个人气质和美学追求给影片带来的独特“气韵”,也成为他们个人影像风格的象征性符号。
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中有所谓“意在笔先”“有感而发”,有所谓“胸中之竹”“眼中之竹”“手中之竹”的创作步骤,有所谓“立主脑、密针线”,其实,都无非说明了“气”为根本的重要性。
和传统理论相似的是,影视艺术同样“以气为主”,而且提倡“意在笔先”。通俗一点讲,任何影片的创作,导演都必须事前有所想法,有所盘算。也即夏衍老先生所说的“电影的目的性要明确”,[10]它不仅包括夏老提到的“为什么拍电影,为什么人拍电影,拍这部电影为了什么目的”这几个方面,甚至还包括诸如“怎样拍电影”这样的问题。《拿破仑》的导演阿倍尔·冈斯说,“构成影片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11]引言7笔者此处所言的“气”便近似于阿倍尔·冈斯所谓的“画面的灵魂”。本文以为,影视作品的画面只是构成影视作品的必需的物质材料,而使一部影视作品得以成立和流传的真正核心还在于它的“气”,一种带有明确目的性的精神和意志。
可能有人会将此观念等同于过去的“主题先行”而弃之不顾,但笔者以为,“主题先行”的创作方法本身并没有错,其错只不过因为某些人完全将所有的影视作品都拍成了一个模式、一种“样板”,从而导致影视界“气韵”全无、一片死寂。这无疑是忽视艺术自身创作规律和创作者的艺术个性所得到的深刻教训。
2.“韵”——影视作品整体营造并呈现出来的一种节奏、氛围和韵味
它以影视作品的“气”为本源,并与“气”紧密相连,形成一种水乳交融的独特意境,在特殊的“韵味”中让观影者自觉接受影视作品之“气”的灌注。从接受者的角度考察,也可将它视为影视之“气”与观众的观影心理和接受心境等共同作用而生成的一种氛围和韵味。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呈现于观众眼中的某一导演的独特风格。在物质层面上,它主要由布景、道具、灯光、音乐、音响、演员的表演以及镜头的运动和组接等多种元素构成。
对照西方的影视理论,本文所言的影视作品的“韵”既与麦茨所谓的“内涵的能指”(“就是电影的某种风格、类型、象征或诗意”)和“外延的所指”(强调通过特定灯光和特定摄影技巧等能指来表现的场景效果)近似,又部分类似于德吕克所谓的“电影性”(“由于电影的再现而增长了其精神价值的一切人、物或灵魂的风貌表现”)。总体而言,它也可看作“生”和“动”这两种能指的外延所指。比如在《城南旧事》这部影片中,这种独特的“韵”便是通过缓慢深情的回忆、抒情且带些感伤的音乐的重复、富于地域特色的建筑街道、零散而有机的生活片段、平稳而流畅的镜头、庄重而舒缓的节奏等等元素来营造的。
3.“生”——主要有三重意思
一是贴近性,指贴近生活,反映生活,富于生活气息,大致类似于我们一向强调的“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这个文艺创作原则;二是逼真性,指影视所表现的人物形象生动、栩栩如生,有生活基础和代表性;三是生命意识,指关注人的生存状况、生存需求,珍惜生命,对生命进行讴歌和反思,具有人道主义情怀。这种“生”的特性,主要靠画面、题材和拍摄手法来体现。如果把前两点看作内容和形式的话,第三点则显明是一种精神,而且是一种现实主义的人道精神。至于其重要性,爱森斯坦的这句话或可说明,他说:“离开了人,不是出自人和人性,那就任何一点真正生动的现实主义的形式、任何一点真正生动的作品形象都不可能产生、出现和发展。”[6]3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才在开篇就引用高尔基的“一切在于人——一切为了人”的名言。
当然,本文所谓的贴近性和逼真性并非指客观机械地复制生活,而是指影视作品的内容和精神必须与人们的生活相关或者直接来源于人们的生活,或者同人们实际的生活经验大致相适应,它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感悟和提炼,还是对生活的一种超越和反思,是影视作品整体呈现出来的“动感”“质感”和“鲜活感”。让·米特里曾经指出,影像虽然是一种揭示,但它揭示的是被强烈感知和集体表现的现实,而不是一个超验的现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尔丹才指出,“电影画面首先是现实主义的”,“电影画面同现实保持着联系,但它又将现实升华为幻术。”[11]1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生”的内涵也契合观众观影的特殊心理需求。对此,最早系统研究电影视觉表现手段之发生学元素的心理学家爱因汉姆指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满足于了解最重要的部分,这些部分代表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因此,只要再现这些最需要的部分,我们就满足了,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印象——一个高度集中的,因而也就是艺术性更强的印象。[12]
在他看来,借助人们惯常的“以部分代整体”的认知心理模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识”),电影只要对人们最关心的、最想了解的那一部分现实生活进行反映,观众就会得出一个关于其处身其间的社会的“局部幻象”并且满足于这一“幻象”。马尔丹也指出,“只要电影向观众提供了现实的主观形象,提供经过凝练,因而能生情的现实景象,观众的感觉就能逐渐被触动。”[11]5-6
正是相信这样的“局部幻象”,人们对影视作品逼真性的要求才越来越高。巴赞曾对此进行描述说:“今天,观众要求的是视觉形象的真实可信,而且,观众还会通过他们掌握的其他信息手段,如无线电、书籍和新闻报刊,来检验可信程度。”[8]29而这也是素来以逼真性闻名于世的好莱坞大片之所以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的不二法宝。今天电视界《超级女声》《非常6+1》等真人秀节目之所以迅速蹿红并大受欢迎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在以往的电影流派中,意大利新写实主义电影在“生”的体现上是最为明显的:首先,它取材于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其次,它多采取实景拍摄和非职业演员,使得故事环境(也是影片的构成画面)和人物表演十分接近生活原貌,富于生活气息;再次,它的长镜头拍摄和反情节的叙事,使得影片本身体现出一种在运动中记录生活的原生态特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它揭露生活中的黑暗,赞美人世中的温情,体现出一种对社会、对现实的反思精神,一种关注人们生活命运的人道主义情怀。这方面的杰作有《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偷自行车的人》《警察与小偷》《大路》,等等。
一句话,影视作品只有具备了“生”的这样一种特质,才能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并最终得到观众的认同。只要对影视创作史略加考察,人们便不难发现,举凡流传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奉为经典的影视作品,无不是关注人生,富于生活气息,并对人生进行反思和寄寓了人性关怀精神的作品。相反,如果影视文本完全脱离生活和过于虚假,观众心理上的“再度校正”机制就会自动处于不停息的工作和抵制状态,便很难与影视虚构的影像取得认同;那么,于观众而言,自然是享受不了“忘我”的审美体验,对影视作品的生产者而言,自然也无法取得理想的票房收入和对观众进行感化和“询唤”的目的。
4.“动”——主要指影视的运动性和运动感
“动”包括胶片(或磁带)的运动、摄像机机位的运动、镜头的运动、拍摄对象自身的运动等等,是构成影视作品“生动”这一特征的具体能指。这些运动主要通过镜头画面来体现。事实证明,在一部成熟的影视作品中,这几种运动方式都是不可或缺的。越是成熟的影视作品,所包含的运动方式就越丰富。
至于其重要性,自电影诞生之后不久即为人们所重视。从英国的布莱顿学派开始,导演们对电影运动性的认识逐渐加深并开始自觉的、丰富的运用。许多导演和电影理论家还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对于电影运动性的理论。比如爱森斯坦就明确表示“我创作的焦点始终是更突出地集中于运动”、“集中于动作和行为”[9]2,显然,他这里所说的运动绝不仅仅指“群众运动、社会运动、戏剧性的运动”,也包括镜头本身的运动。在其《蒙太奇论》中,就曾用大量篇幅论及画面的运动和运动感(其实,蒙太奇本身就是一种镜头的组接运动方式)。“悬念大师”希区柯克认为“追赶是电影手段的最高表现。”其实,早从格里菲斯的“最后一分钟营救”开始,追逐和奔跑就一直成为大多数导演“情有独钟”的表现内容,并且一直深受观众喜爱。这方面经典的镜头段落是很多的,比如《警察与小偷》中警察波多尼与美国富商几个追赶小偷爱斯波及托的片段,《罗生门》中强盗于林中奔跑的运动摄影段落,《黄土地》中憨憨逆着人流奔跑的镜头等等。
关于“动”的重要性,法国电影理论家马赛尔·马尔丹的两句话既堪称经典,也可作此节之小结:一句是“运动正是电影画面最独特和最重要的特征”[11]2;另一句是“电影作为艺术而出现是从导演们想到在同一场面中挪动摄影机那一天开始的”[11]6。
(二)“气韵生动”的辩证关系
本文所谓的“气韵生动”与传统的“气韵生动”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在注重整体意蕴和对“气”、“韵”关系的认识上,二者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区别,主要有两点:
第一,传统中之“气韵生动”作为一个整体考察的美学原则,只具有形而上的层面,而影视艺术之“气韵生动”不仅指整体上的一种美学精神,而且还包括具体的物质材料等形而下的内容;
第二,在“气韵”与“生动”之关系上,传统观点仅仅将之视为一个主谓结构,认为“生动”不过是对“气韵”的一种形容和阐释,或者说是“气韵”的必然结果。本文则赋予它们不同的实质内容,为每一个符号都界定其深层所指,并且认为各部分之间是一种相互关联、互为因果、层层递进、辩证统一的关系。
具体而言,“气”是一部影视作品的根本和立足点,是统摄整部作品的灵魂;“韵”是“气”的外在表现,它又必须借助“动”这种运动方式以及画面、音响、灯光等特殊物质材料来实现;“生”既是“气”“韵”诞生的土壤和试金石,其中又包含“气”“韵”的最高审美追求——鲜活感和生命意识;而“动”则是构成一部影视作品必不可少的条件,所谓“气韵”最终又有赖于“动”这样一种手段来实现。它们既分别对应着影视作品的每一个环节,也统摄着作品的灵魂。同时,每一个环节之间并非是孤立的静止的,而是一种相辅相成、错综交织的关系。对于一部具体影视作品来说,其“气韵生动”的最终实现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影视作品通过摄影机、摄影客体、摄影主体以及镜头画面的运动,通过对生活的反映、观察和反思,在银幕或荧屏上(最终是在观众的心里)制造出某种虚幻的关于现实的影像和某种特殊的氛围和韵味,最终达到传达影视作品编导(背后是强大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构思立论、传情达意(将个人询唤成主体)的目的。
当然,在“气韵生动”的生成和传递过程中,观众心理情感的主动参与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在此问题上,雨果·闵思特堡的“幻想投射”论,爱因汉姆的“局部幻象论”,麦茨所说的“再度校正”机制,博得里“电影机制是对主体某种欲念的想象性解决”的观点以及拉康关于婴儿镜像期的“误识认同”理论,都已从观影主体深层心理机制上作了详尽而深刻的研究,因篇幅所限,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优秀的影视作品往往都是“气韵生动”这几个特性兼具的作品,正是这些特性的有机综合才形成了影视作品的独特韵味和艺术生命。这四者中,无论少了哪一方面都会给作品造成根本性的损害。因此,在影视创作中,必须考虑这几个因素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