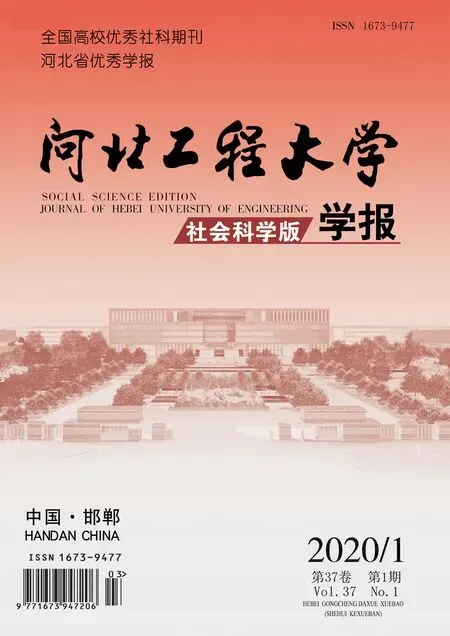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苏庆国,阎露方
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应对策略研究
苏庆国,阎露方
(河北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邯郸 056038)
乡村作为人类的基本聚落,其治理成效如何,直接攸关生产生活秩序能否有序、和谐、稳定。基于法治化框架来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与自治、德治有机对接,是确保农村社会长治久安的关键所在。由于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法治仍处于边缘化位置,“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因此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虽有明显推进,但乡村治理系统的运转仍然不够顺畅。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法治化;乡村治理;自治;德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法治作为现代社会最为突出的基本表征之一,在乡村治理体系场域之中,被赋予了框架、制度基石的重要意义,成为驱动自治、德治模式良性运转的关键所在。近年以来,在国家相关政策、制度的有力支持与引导下,乡村治理的法治化推进不断提速,综合治理效果大幅度提升,民众的法治意识也得到了相应提高。但与此同时,也需要看到,由于长期以来积存在乡村社会的“人治”观念难以在短期内彻底驱除,“知情祛魅”现象又普遍存在,加之法治管理与既有的“自治”“德治”模式又存在对接上的脱节,并未充分构建起彼此协同、相互助益的治理新体系。因此,乡村治理仍困难重重,乡村治理的法治化,仍面临重重阻力。为此,需在继续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其与“自治”“德治”两种治理范式之间的融合,由此驱动农村社会的稳定、协调、长效发展。
一、以法治视野审视乡村治理问题的依据
(一)以法治视野审视乡村治理问题的理论依据
近年以来,涌现出了数量客观的涉及乡村社会法治化转型、综合治理的学术观点,其普遍基于法治维度解析当下乡村治理的形态、困境,并提出了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为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具体而言,当前国内的乡村治理法治化理论主要涉及以下向度:
首先,推行“有限自治”模式。这一论点侧重于村党组织作为核心引导去指导村民,通过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道德规范等,实现本村事务的自治。而国家法律主要在于发挥其作为基本法律制度的框架作用,并不直接干预村民自治[1](P13)。而当法律显现出其滞后性之时,柔性治理方式则开始凸显其功能。对于并未触犯相关法律法规的纠纷,村党组织、村委会等机构即可依照既有的村规民约进行调解处理。这无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强村民参与法治治理的主动性与能动性。
其次,强调“法律介入村务治理”。这一论点认为村民自治权存在被滥用的可能性,所以应当借助司法、行政等法律手段进行审查,以充分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2](P48)。所以,法律应当在村民自治系统之中占据突出位置,发挥自身作为调解、规制力量的关键作用。
再次,“自治”与“法治”的交互推进。该论点主要采取辩证视角解析法治和自治的相互关系,主张构建一种相生、互动的运作形态,使二者能够尽可能地均衡共处[3](P107)。因为法律施行过程之中需要尊重村民的自治权,而当自治权难以解决村民纠纷之时,则需要将自治、法治进行充分结合,如此方能促成争端的妥善处理。
(二)以法治视野审视乡村治理问题的政策依据
近年来,乡村治理问题愈发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成为新时期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而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2005-2011年,我国农村贿选率达15.9%,贿选成功率有20.4%”。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工作报告第五篇也明确指出:“2016年全国共处分乡科级及以下干部39.4万人,其中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7.4万人,比上年增加12%。”这些资料显示,农村贿选、村官腐败、土地矛盾等乱象与问题长期未得到有效治理与解决。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转型。而随着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作为新时期农村工作的中心任务,以法治为保障、以村民自治为基础、以德治为支撑的新型治理模式,开始在国家制度的有力引导之下,成为解决以上积弊的有效手段。而在国家相关制度的不断完善的背景下,自治、法治以及德治相结合的新型治理体系,又不断强化了自律、群律以及法律三位一体的行为约束规范,使纠纷、村务得到了更为合理、高效的处理。尤其是随着村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体制、公共法律服务、监督考核机制、村级组织工作事务得到持续完善,村民议事协商形式趋于丰富,村级事务阳光工程进入全面推广阶段,自治、法治以及德治相结合的新型治理体系,又在整体部署、贯彻落实上,有了更加牢固的制度保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三治合一”的执行力,能够真正契合当前乡村社会所面临的各类现实困境[4](P226)。
(三)以法治视野审视乡村治理问题的现实依据
乡土性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文化内核,其投射出人们的思维模式、情感偏向、价值取向等,使血缘、亲缘、地缘、人情、伦理、宗族观念、权力秩序等,成为影响社会建构的重要因素。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区域中心城市,乡土性开始渐次被法治观念所取代,契约精神已经对所谓的讲求人情世故的思维产生着消解。而在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转型过程之中,乡土意识依旧显现出强有力的在场性与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对抗着这一现代观念。这种对抗性,又并非单一的对立,而可以视作是传统的社群文化、价值,尝试通过与现代文明之间形成一种相互制衡的关系,由此去维持现有的相对平稳的社会生态。不过随着城乡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口跨区域流动的趋势不可逆转,乡村中的大量人口,尤其是青壮劳力开始流入城镇地区,原有的以乡土性结构迅速被肢解。其中,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力量,也在近年来呈现着持续流失的趋势,这既导致乡村人力资本结构开始失衡,又严重弱化了乡村社会在政治、文化上的向心力,原有的“乡贤”体系难以正常、有序运转,其权威性也不断被削弱,由此使乡村社会秩序缺少了一定的自我约束力,一些原本依靠这一精英群体供给的公共物品,也面临着接续的困境。特别是在村民自治维度上,乡村政治精英层的持续断裂,也令这一治理范式实质上转为了由村委会少数人进行决策,无法真正体现自治的功能、价值。因此,在这一情境下,构建法治化治理体系、推动法治化进程、建立法治化社会,也就成为了凝聚乡村社会人心、体现农村人民意志、保障群众切身利益的必由之路[5](7P73)。
二、法治视野下目前乡村治理面临的困境
(一)法治制度与自治机制、德治传统有待进一步整合
党的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新时期任务与目标,清晰指明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即构建一种相互依存、彼此推动、交融共进的运作样态,借以科学、规范、高效地处理农村的各项事务。在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的场域之中,由于村民自治经过长期以来的以农民为主体进行的实践,已经具备了较为牢固的群众基础、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管理机制;德治则与乡村社会的历史文化紧密联结,呈现出鲜明的传统意味;法治无疑需要借助国家力量自上而下地完成推行。而如何使法治有效内嵌至自治、德治之中,使三者形成发展共同体,也就成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而现实情境则是,自治、德治既要基于党的路线政策、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又需立足乡村社会的发展实际[6](P49)。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不同地区在自治、德治的推行过程之中,仍普遍存在着诸如程序不规范、民主程度偏低、村规民约内容缺乏可操作性等一系列问题,难以与法治模式进行有效对接。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弱化了“三治合一”稳步推进的联动基础。
(二)法治仍处边缘化位置,形式意义大于实际效用
与近年来城乡一体化进程持续加快、乡村经济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同时出现的,是愈发频繁的各类乱象与管理弊病,诸如官民冲突、拉票贿选、小官巨贪等等,暴露了乡村社会在法治化上的巨大缺失。尽管随着国家不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施行了旨在推动乡村社会法治化转型的法律制度,然而在当前乡村治理的现实情境中,法治观念、法治模式仍未居于主流话语的中心位置。行政力量依旧占据着权力意志的主场,对乡村社会的各项事务产生着关键性的影响,“重问题解决”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样式,仍成为处理纠纷的首选。从处理的实效性来看,与法治所采用的程序模式相比,“重问题解决”这一模式的确具有突出优势,比如工作效率高、执行力度大。然而需要看到的是,这一模式其实已经对权力的规范行使产生了僭越,也难以切实有效地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力,导致矛盾继续积存,最终在某个临界点爆发,引发出更为严重的群体冲突[7](P131)。所以,严重依赖行政手段、淡化与忽视法治,只能让乡村治理的正向效果短期显现,而难以真正发挥对秩序稳定的持续性增益效应。
(三)“知情祛魅”现象渐次显现,导致法治方式“失语”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法宣传、基层法治建设成为国家战略意义上的重点工作,为法治意识在中国社会的流播、推动法治社会的形成,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农村社会,经过长期的法律意识传播、法治模式的导入,法治的权威性得以确立,也在不少民众之中产生了影响力,使乡土观念之中的“送礼”“走后门”“说情”等观念开始在纠纷处理之中失去实际意义。然而随着民众参与“法治”管理的渠道、方式的多样化,“知情祛魅”这一现象也开始集中显现:一方面,在当前的乡村社会场域之中,行政力量依旧具备某种“压倒性”的威权色彩,以权压法、人情执法、司法不公等失范行为并不能在短期内被完全禁止,一些秉公执法、拥护法律的基层干群,往往会遭遇行政力量的打压,导致其对法治产生质疑,难以建立真正的认同感;另一方面,虽然长期以来固化的乡土观念开始被现代意识所消解,不过在某些经济欠发达的偏远乡村,传统规则依旧可以在某一节点无视法治,甚至僭越法律,令基层干群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困境的成因
(一)缺乏规范、有效的法律制度供给,治理体系健全度偏低
较长一段时期以来,“重经济”“轻法治建设”的观念一直主导着乡村社会生态,使得乡村法治转型大大滞后于城市。而尽管近年以来,国家持续出台了多部法律法规,用于提升乡村治理的法治化程度,不过由于其法律制度基础较为薄弱,不少法律规定又缺乏具体的可操作,因此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乡村治理难以实现“有法可依”。需要指出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仍旧是当前乡村治理在国家法律意义上的主要依据。然而这部法规由于后续并未与乡村社会的发展形成同步性的修改、完善,因此在规定上普遍存在着指向的笼统性、模糊性,在具体的可操作性上,也缺乏依据。这也使涉及乡村治理的法律规定难以得到清晰、明确的指引,只能参照这些缺乏实际意义的法规,去尝试进行处理各类乡村纠纷。而随着乡村社会经济、文化的多元化演变,单纯依靠有限的法律法规,无法真正发挥法治治理有效引导、定纷止争的作用,进而很难去规范基层干部群众的行为,从而遮蔽了法治化的主体位置[8](P8)。
(二)治理主体法治素养亟待提升,相关人员依法治理能力不足
乡村治理主体是推动乡村社会法治化转型的核心所在,这一群体是否具备充分的法治意识与过硬的法治处理能力,也成为了个中关键。而虽然经历了长期的基层普法宣传、政治体制改革,当前乡村基层干部的整体的法治意识仍比较淡薄。从乡土社会的文化机理来看,不少基层干部仍倾向于采用“以权息事”的思维与解决方式,试图通过诸如胁迫、劝导、人情感化等途径,去以最小成本化解各类矛盾与问题,从而继续维持既有的社会秩序与既得利益生态。这也导致农村不少基层干部缺乏过硬的法治能力,难以通过法治方式去呼应、满足乡村民众的现实诉求。而同时也需要看到,在广大农村,基层群众的法治观念也颇为淡薄,其往往会将自身自觉定位为“法律的作用对象”“是被法律管的人”,因此也就缺乏抗辩意识。此外,当前乡村的基层法治队伍仍存在巨大的人才缺口,不少法务工作站之中,都没有足量的专业人员,大多由非专业人员为民众提供法律咨询,这当然无法真正凸显法治治理的公正、规范。
(三)治理机制的法治化程度不高,体系、规则需进一步完善
毋庸置疑,完整、高效的治理制度是推动乡村治理法治化的基础要素。而缺乏规范性、约束力的治理制度,不仅会严重制约公权力的有序运行,而且也难以保障主体的私权利。在当前乡村社会的治理生态之中,“乡政村冶”依据占据着主导位置。而由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其并未明晰划定基层政府、村委会各自对应的职权范畴,由此使基层政府责、权、利之间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这种对于治理主体权责划分的模糊性,无疑会导致权责不明、公权私用,进而引发各类潜在矛盾。而同时也需要指出,目前乡村治理机制也存在明显的弊端,其并未真正从程序意义上,以现代现代法治观念取代传统社会规则,与之对应的责任机制并未真正显现出约束力,导致诸如利益表达渠道、民主参与途径、纠纷解决方式等,普遍显得较为随意、浮动性偏大,弱化了其正常的功能。而参与、表达、维权载体的缺失与功能失调,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农村民众的负面情绪,导致其开始对法治治理产生质疑、抵触甚至排斥心理。
(四)法治推进缺乏充足保障,难以对接现有的自治、德治模式
法治氛围作为一种情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民众对于有别于传统治理方式的新生范式的自我区隔意识,诱导其通过主动接触、深入了解去建立认同,从而为乡村社会的法治化转型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而毋庸讳言,当前乡村社会的法治氛围仍显得比较淡薄,民众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究其原因,不难得见:一方面,法治思维并未真正介入乡村社会场域之中,而是被定位为带有破坏性的“他者”而存在。尽管在现代文明的持续冲洗之下,乡村社会的乡土基体开始被瓦解,然而对于中老年群体,其依旧坚守着传统思维,对外界事物采取观望事物,且普遍有着从众心理,使“私了”、闹访等闹剧与乱象普遍存在;另一方面,专业人才、专项经费的长期短缺,也导致乡村治理的法治化转型,一直缺少强有力的支持与推动。这其中自然不能回避农村经济条件较差、对于人才吸引力不足等现实。而在制度层面,基层政府不重视法治建设,不愿意投入经费,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公共法律服务供给不足、人员得不到专业培训,继而无法通过制度、人力,去加强法治与自治、德治之间的耦合度[9](P124)。
四、法治视野下乡村治理困境的应对策略
(一)加快专项立法、夯实法治基础,构建完整、规范的法律制度体系
一是应当加快对于乡村法治化治理的立法,尽快制定、出台具体的法律法规。厘清“村两委”和基层政府之间的交互关系,明确前者的自身定位,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去清晰划定其职权范围、运作程序,夯实乡村治理的制度基础;二是继续完善现有的村规民约,立足乡村社会的发展实际,尊重农村民众的传统心理、文化习俗以及生活习惯,基于法律法规框架,去科学审视法治管理与上述文化要素之间的作用关系,通过法律制度作为规范性参照,去有效引导基层组织、村民的行为,提高其法治意识与素养;三是打通法治化管理与村规民约之间的联结渠道,正视、发挥村规民约长期以来在乡村社会所负载的正向作用,借助其对于村民行为的规范与引导,将现代法治理念合理融入其中,促使农村民众真正准确、全面地认识法治化观念,并将之与自治、德治进行正确定位。进一步推动村规民约备案审查机制、民间规则体系以及国家法律法规之间的充分对接,不断提升整个乡村社会成员集体的法治意识,构建人人知法、人人懂法的法治化社会氛围,为构建法治、自治、德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奠定坚实基础。
(二)完善法治化治理组织模式、理顺管理机制,科学引导权力运作
要在切实巩固基层党委领导地位的基础上,不断提高其作为乡村治理核心的组织力,发挥其对于基层政府行政权、村民自治权之间的协调作用,使基层政府依据实际情势、适度减少行政干预,突出自身在空间规划、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监督保障等环节上的职能重点,合理扩大自治空间,促成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之间的高效互动。同时,也要大力培育基层社会组织,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划定其在法律地位、权利义务上的具体范畴,给予、确保其应有的合法性。此外,应持续完善乡村社会现有的依法决策机制,调整具体的相关规定,对决策的主体、范畴以及程序进行清晰划定,强调决策失误责任与追责要求,改进利益表达机制,落实利益补偿所要求的公平、公开以及公正等核心理念,完善矛盾纠纷的预警、排查以及调处,逐步使既有的村“两委”定期接访、村民信箱、智慧社区、网络维权平台以及意见反馈渠道能够得到充分整合,强化乡村治理在法治、自治、德治上的对接度[10](P138)。
(三)提升基层干部法治素养、打造高质人才队伍,推广公共法律服务
应当在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基层政府在选人、用人上的法治导向,借助群众访谈、专业考核、监督反馈等方式,真正了解、定位当前基层干部的法治能力。据此有针对性地完善现有的述职、述廉、述法“三位一体”的考核机制,将法治能力考察作为重点,真正实现法治能者上、法治平者让、法治庸者下。要继续加大对于法务工作站、法律服务机构等公共组织的支持与管理力度,依照当前乡村在法律纠纷上出现的各类新情势,合理设置诸如针对农民工、老年人、流动人口等相对弱势的社会群体的法律援助专项绿色通道,合理进行审批流程简化,真正去发挥法律定纷止争、维护权益的重要效用。考虑到专业性的法治人才的缺失这一短板,也要通过加强与相关院校的交流、合作,以定向、委培的形式共同培养专业人才,相应提高这一群体的待遇标准,吸引其在乡村本地长期生活、学习、从事法务工作,为乡村治理的法治、自治、德治相结合,提供充足的人才保障。
(四)创新法律纠纷化解手段,以德治与自治挖掘传统文化、保障人民权利
首先,要科学利用调解、司法以及仲裁等法治资源去处理各类乡村矛盾问题。逐步构建县、乡(镇)、村三级式的法律服务体系,重点在农村地区设置法律援助联络点、专业的法律顾问人员,推动多元化、全过程的纠纷解决机制的落地,使法律咨询、人民调解以及法律援助能够紧密结合、相互推动;其次,要明确村党支部在治理系统之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引导村委会依法执行职能,明确各自的权利、义务以及职责,形成分工合理、有机高效的新型“村两委”体系;再次,要大力发展乡村群众组织,将发展乡贤参事会、村落理事会等作为重点,积极推动乡村治理的民主化监督;最后,要构建新时代的乡贤文化、保障人民行使权利。基层政府、村民自治组织要积极引导乡村能人建立乡贤组织,营造民主协商的文化氛围。规范乡贤组织的内部管理机制,发挥乡贤群体与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对于构建法治、自治、德治“三位一体”式的新型治理体系的感召、带动效用。
[1]陈于后,张发平.新时代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体系研究[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9,(06):13-21.
[2]李营.乡村治理法治化转型困境及破解之策[J].领导科学,2019,(22):48-51.
[3]陈涛,李华胤.“箱式治理”:自治、法治与德治的作用边界与实践效应——以湖北省京山市乡村振兴探索为例[J].探索,2019,(05):107-115.
[4]黄君录,何云庵.新时代乡村治理体系建构的逻辑、模式与路径——基于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视角[J].江海学刊,2019,(04):226-232.
[5]陈成文,陈静.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J].山东社会科学,2019,(07):73-80.
[6]左停,李卓.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融合”:构建乡村有效治理的新格局[J].云南社会科学,2019,(03):49-54+186.
[7]覃晚萍,王世奇.新时代多元主体推进乡村治理法治化路径探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9,(03):97-101.
[8]宋才发,张术麟.新时代乡村治理的法治保障探讨[J].河北法学,2019,(04):2-13.
[9]王文彬.自觉、规则与文化:构建“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J].社会主义研究,2019,(01):118-125.
[10]汪鑫,李渡.反思法视角下乡村治理的自治与法治之维[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9,(01):132-139.
Research on the predica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it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le of law
SU Qing-guo, YAN Lu-fang
( School of Marxism,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
As the basic settle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rural area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order of production and life. The key to ensuring the long-term stability of rural society i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with autonomy and rule of virtue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rule by law. In the current rural social field, the rule of law is still marginalized, and the phenomenon of "disenchantment with knowledge" is widespread. Therefore, although the rule of law of rural governance has been significantly promoted, the ope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is still not smooth enough. Therefore, on the basis of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under the rule of law,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ith "autonomy" and "rule by virtue", so as to drive the stable, coordinated and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rural society.
rule of law; rural governance; autonomy; virtue
2020-01-03
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项目的研究成果(编号:20190303010110);河北省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编号:SD191003)
苏庆国(1970-),男,河北永年人,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法律。
10.3969/j.issn.1673-9477.2020.01.010
D63
A
1673-9477(2020)01-051-05
[责任编辑 王云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