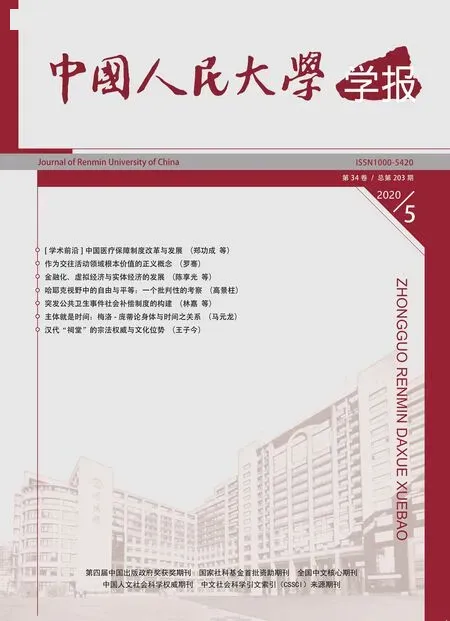汉代“祠堂”的宗法权威与文化位势*
王子今
秦人祀所包括“神祠”与“先祠”。汉并天下,继承了秦的信仰体系。两汉是中国文化开始走向成熟的历史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和社会交往的进步,两汉时期文化演进的几个重要特征,儒学教育的广泛普及,宗法秩序的初步稳定,道德建设的空前升格,都与一种社会文化存在有关,这就是“祠堂”。汉代宗族“祠堂”的作用超越了以往日月山川鬼神祀所,形成社会文化经纬的要络,其社会文化意义之重要,可以看作先祖祭祀的场地、孝道宣传的课堂、亲情凝聚的中心。“祠堂”在宗法体系中显示出权威,所占据文化地位大幅度升格,表现了“威重之权”与“位势之贵”。(1)司马迁:《史记》卷八三《鲁仲连邹阳列传》,2478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一情形,也体现社会观念格局中的人文因素的作用在与巫鬼的抗击中逐渐上升。皇族“宗庙”是国家礼祀正统,也是地位提升至最高等级的“祠堂”,其权威性尤其显著。汉家宗庙在政治权力接递程序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曾经决定最高执政权力的予夺。东汉时期,在浮华世风影响下,“祠堂”建设“崇侈”的趋向,受到开明士人的批判。两汉“祠堂”不仅是当时社会文化史观察的焦点,而且对后世也表现出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汉代“祠堂”研究,是涉及宗法史、礼俗史、信仰史、建筑史的复杂的学术主题。本文主要就“祠堂”地位上升这一现象做相关讨论。对于具体的礼祀程式、建筑形制等问题,限于条件,不做详尽论说。
一、“以孝治天下”与“祠堂”的兴起
在秦汉人的崇拜体系和信仰世界中,巫术传统有浓重的影响。秦旧有“祠”“庙”“雍”“百有余庙,西亦有数十祠”。祠祀对象,还有很多“小鬼之神”(2)。这只是“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3),民间祠祀体系更为纷杂。秦始皇东巡,对齐地原有的“八神”(天主,地主,兵主,阴主,阳主,月主,日主,四时主)也一一恭敬礼祠。(4)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1375、1371、1367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汉王朝对于这一体制基本继承,这就是《史记》卷二八《封禅书》所记载“悉召故秦祝官”“如其故仪礼”及刘邦诏令“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诸神当祠者,各以其时礼祠之如故”。(5)司马迁:《史记》,1378、29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不过,在两汉精神文明发展历程中,原始宗教的影响渐次削弱。与社会秩序、人文关怀和伦理规范关系更密切的宗族“祠”“庙”,受到更多的重视。
《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记述曾参事迹:“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作《孝经》。”(6)司马迁:《史记》,2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参见班固:《汉书》,17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载王莽上奏:“孔子著《孝经》曰:……”参见班固:《汉书》,408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史记》卷一一二《平津侯主父列传》载录“太皇太后诏”引述《孝经》。(7)司马迁:《史记》,1378、296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汉书》卷七《昭帝纪》和《汉书》卷八《宣帝纪》载帝诏,都自述对《孝经》的熟悉。(8)班固:《汉书》,223、2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王莽专政时的教育制度,“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9)班固:《汉书》卷一二《平帝纪》,3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基层学校都设置讲授《孝经》的专职教师。《四民月令》中有“命幼童读《孝经》”(10)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的内容,体现乡村学校的启蒙教育已经以《孝经》为基本教材。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指出:“《论语》、《孝经》者,汉中学之科目。”(11)王国维:《王国维遗书》,第四册,《观堂集林》(四),7页,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83。“孝”的道德导向,已经成为基础教育的主要内容。
虽然《孝经》有“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1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5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文句,但是应当看到,在汉武帝时代提升儒学地位之后,“孝”更明显地成为正统意识形态的主导。儒学学者将这一理念扩展、提升,进行了与政治相结合的普及性宣传,如高诱《吕氏春秋·孝行》注:“孝为行之本也。”“先王以孝治天下。”(13)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校释》,732-735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而社会的普遍相应,在东汉更为明朗。我们看到,“祠堂”设置与其他行为共同成为这一文化演进的表现。
汉代比较普遍的意识,以为在“家门”表现的“孝行”,可以自然上升至国家层面。“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国家政治和个人修养的结合,可以在“孝行”追求上找到结合点。孝亲者,可以移忠于君,因此“孝子”自然可以成为“忠臣”。这是执政者关心的人才选拔原则。而“孝”服务于政治的作用,也因此被看重。论者是在强调“垂恩选举,务得其人”(14)范晔:《后汉书》卷二六《韦彪传》,91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的主题时说这番话的。“夫孝行著于家门,岂不忠恪于在官乎?”(15)陈寿:《三国志》卷九《魏书·夏侯玄传》,2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孝行”著家,则“忠恪”在官。“孝”和“忠”的这种结合,被看作伦理文化与政治文化具有因果意义的必然。于是,东汉后期历史记述中反复出现的“以孝治天下”(16)《三国志》卷二《魏书·文帝纪》裴松之注引孙盛曰:“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内节天性,外施四海,存尽其敬,亡极其哀,思慕谅暗,寄政冢宰,故曰:‘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参见陈寿:《三国志》,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三国志》卷七《魏书·张邈传》载陈宫曰:“宫闻孝治天下者不绝人之亲,仁施四海者不乏人之祀。”裴松之注引鱼氏《典略》:“宫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参见陈寿:《三国志》,2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三国志》卷一二《魏书·鲍勋传》:“文帝将出游猎,勋停车上疏曰:‘臣闻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参见陈寿:《三国志》,3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成为一种理想的政治指向,一种确定的政治原则。而“孝行著于家门”的具体的物化表现,我们看到宗族“祠堂”之普及。关于两汉的历史文献中,有密集的关于家族“祠堂”的记录,而文物资料更丰富了我们对这一社会现象的认识。
“祠堂”是遵行孝行、孝道的基本条件。在特殊情况下,对“祠堂”的重视因此又显示出坚持“礼”的风节操守。《后汉书》卷三七《桓典传》说,桓典“举孝廉为郎”,不久,家乡沛国的长官“沛相”王吉因罪被诛杀,故人亲戚没有人敢为他办理丧事,桓典竟然弃去官职,为其“收敛归葬”,并且“服丧三年,负土成坟,为立祠堂,尽礼而去”(17)范晔:《后汉书》,1258、34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礼”的整体内容,是包括“立祠堂”的。
两汉“祠堂”形制,是社会史、宗族史以及建筑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学术主题。
司马迁《史记》正文中,没有出现和我们现在讨论的主题相关的“祠堂”,只是《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说,孔子葬后,“唯子赣庐于冢上,凡六年,然后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诸儒在“孔子冢”举行“讲礼乡饮大射”礼仪。据说鲁人“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刘邦经过鲁,“以太牢祠焉”。大概起初并没有“祠堂”建筑。据裴骃《集解》引《皇览》说“孔子冢”位置规模,称“本无祠堂”“冢前以瓴甓为祠坛,方六尺,与地平”(18)司马迁:《史记》,194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种“祠坛”设置,也是后来的事,《皇览》“孔子本无祠堂”的说法,又见于《续汉书·郡国志二》刘昭注补转引。(19)范晔:《后汉书》,1258、342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刘向批评丧葬“制度泰奢”(20),上疏谏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21)班固:《汉书》卷三六《刘向传》,1950、19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古之葬者”“不封不树”的说法也见于王符《潜夫论·浮侈》。(22)范晔《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李贤注:“《易·系辞》之言也。”参见范晔:《后汉书》,163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潜夫论·浮侈》:“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时,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参见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对于战国以前陵园墓区存在“祠堂”一类建筑形式的可能,多数学者持否定的意见。随着战国厚葬之风的兴起,大型墓葬开始出现用于祭祀或纪念的建筑。秦始皇陵附近出土铜锺有“丽山园”器铭。(23)丁耀祖:《临潼县附近出土秦代铜器》,载《文物》,1965(7)。陵园内发现许多建筑遗址,一般以为规模较大者是寝殿,也有学者认为其性质的确定,还需要开展更多田野考古工作。(24)刘庆柱、白云翔主编:《中国考古学·秦汉卷》,8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秦封泥有“泰上寖印”“天子寖监”“康泰后寖”“上寖”“孝寖”等体现诸庙寝园设置的实例,又有涉及“食官”制度的“甘泉食官”“丽山食官”“食官丞印”“右中食室”等文物实证。(25)刘瑞编著:《秦封泥集存》,35-39、44-4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所谓“食室”或许与后来的“祠堂”有一定关联。而《盐铁论·散不足》说:“古者,不封不树,反虞祭于寝,无坛宇之居,庙堂之位。”“今富者积土成山,列树成林,台榭连阁,集观增楼。中者祠堂屏阁,垣阙罘罳。”(26)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3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2。这是对当时民俗的批评。“古”“今”对比,说明了时代变化。其所谓“今”,已经是西汉中期。
《汉书》可明确看到西汉中期以后“祠堂”建设的记录。如《汉书》卷五九《张安世传》“将作穿复土,起冢祠堂”(27),《汉书》卷六八《霍光传》“发三河卒穿复土,起冢祠堂”(28),“祠堂”与冢墓同时营造。《汉书》卷八九《循吏传·文翁》也说:“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29)据《汉书》卷七二《龚胜传》记载,龚胜“称疾”拒绝王莽“安车驷马”征召,绝食十四日死。安排丧葬事宜:“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30)班固:《汉书》,2653、2948、3627、30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可见,“作祠堂”,已经是通常社会礼俗的表现。东汉初,“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的记载,见于《后汉书》卷一下《光武帝纪下》。(31)范晔:《后汉书》,12、314、684、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裴松之注引《陆氏祠堂像赞》(32)陈寿:《三国志》,134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说明汉魏之际,“祠堂”设置已经采用了艺术表现形式。
“祠堂”又有称“房”的。《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记载,(延熹)八年(165年)四月“丁巳,坏郡国诸房祀”。李贤注:“房谓祠堂也。”又引《王涣传》说,只保留了两处原有“庙”“祠”,即“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令王涣祠”(33)范晔:《后汉书》,12、314、684、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可见“祠”和“庙”的关系,名义虽不同,实质其实相近。
《后汉书》卷一八《吴汉传》李贤注引《东观记》:“夫人先死,薄墓小坟,不作祠堂。”(34)范晔:《后汉书》,12、314、684、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援夫人卒,乃更修封树,起祠堂。”(35)范晔:《后汉书》,12、314、684、85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说明东汉制度,夫妇同莹同穴,而且一同享受“祠堂”祭祀纪念。
司徒张酺去世,病危时指示其子丧事从俭:“其无起祠堂,可作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36)范晔:《后汉书》卷四五《张酺传》,15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他的遗言,告知我们当时“祠堂”可以采用的替代形式,是仅仅建构一个简易的棚顶,以遮护必须进行的“施祭”礼仪。
二、汉代“祠堂”的文物实证:“石室”和“食堂”
文翁的“祠堂”立于蜀地,可能和墓葬不在一处。类似的情形又有蔡邕《坟前石碑》所说:“封坟三板,不起栋宇,乃作祠堂于邑中南旧阳里,备器铸鼎,铭功载德。”(37)董治安主编:《两汉全书》,第24册,13752页,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9。“祠堂”在“邑中”,与“坟”有距离。但是一般的“祠堂”就在墓园。自宋代以来,对于汉代“祠堂”的发现和研究已经引起学界重视。当时著录的“祠堂”遗存,成为早期金石学研究的主题之一。现代考古学的进步,使得相关遗存得到了科学的考察收获。有学者根据汉代石刻资料指出:“祠堂是陵园中祭奠死者的地方,汉代陵园祠堂有多种称谓,如庙祠、食堂、斋祠、食斋祠、石室等。”(38)“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祠堂题记皆称祠堂为‘石室’,山东画像石习惯将祠堂称为‘食堂’。”(39)武利华:《徐州汉碑刻石通论》,121、146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以“石室”为类似纪念性建筑名号的情形,其实也见于正史。如《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记载:金城郡临羌(今青海湟源)“西北至塞外,有西王母石室、仙海、盐池”(40)班固:《汉书》,1611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仙海”,就是今天的青海湖。《史记》卷五《秦本纪》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据《十六国春秋》说:“酒泉南山即昆仑之丘也,周穆王见西王母,乐而忘归,即谓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玑镂饰,焕若神宫。”(41)司马迁:《史记》,17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又见《史记》卷一一七《司马相如列传》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据《十六国春秋》说,参见司马迁:《史记》,30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汉书》卷四〇《张良传》颜师古注:“赤松子,仙人号也,神农时为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雨上下。”参见班固:《汉书》,20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后汉书》卷二《明帝纪》:“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李贤注:“山有昆仑之体,故名之。周穆王见西王母于此山,有石室、王母台。”参见范晔:《后汉书》,1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后汉书》卷二八下《冯衍传下》李贤注引《列仙传》:“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能随风上下。”参见范晔:《后汉书》,98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又《后汉书》卷二九《郅恽传》李贤注引刘向《列仙传》曰:“赤松子,神农时雨师,至昆仑山,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上下。”参见范晔:《后汉书》,10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后汉书》卷五九《张衡传》李贤注引《列仙传》曰:“赤松子,神农时雨师,服水玉,教神农,能入火自烧。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随风上下。”参见范晔:《后汉书》,19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司马贞《索隐》引《浮屠经》说王舍国灵鹫山小孤石,“石上有石室者,佛坐其中,天帝释以四十二事问佛,佛一一以指画石,其迹尚存”(42)司马迁:《史记》,3165、2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里说的都是西北方向的神异“石室”。又有西南方向的“石室”。《后汉书》卷八六《南蛮传》:“槃瓠得女,负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43)李贤注引黄闵《武陵记》曰:“山高可万仞。山半有槃瓠石室,可容数万人。中有石床,槃瓠行迹。”参见范晔:《后汉书》,282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东方“石室”则有《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李贤注引《博物志》:“徐王妖异不常。武原县东十里,见有徐山石室祠处。”(44)这可以使我们联想到“徐州汉画像石中的祠堂题记皆称祠堂为‘石室’”的情形。而《续汉书·祭祀志上》“封禅”条关于泰山的内容,刘昭注补引应劭《汉官》马第伯《封禅仪记》也说“北有石室”。(45)“石室”传说常与神仙传说有关。《续汉书·郡国志四》“长沙”条刘昭注补引《荆州记》曰:“县东四十里有大山,山有三石室,室中有石床石臼。父老相传,昔有道士学仙此室,即合金沙之臼。”(46)有关“石室”作为“神仙”居所和“学仙”场地的故事,暗示汉代冢墓的“石室”遗存,有可能与当时人们的神仙崇拜与升仙追求有关。刘秀经营河北,受困于“呼沱河”,“有白衣老父在道旁”,勉励其“努力”,又指示求助方向。《后汉书》卷一上《光武帝纪上》的相关记载,李贤注:“老父盖神人也,今下博县西犹有祠堂”(47)范晔:《后汉书》,2808、3165、3484、12-1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也明确指出了“祠堂”与“神人”的关系。
《史记》卷六七《仲尼弟子列传》说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张守节《正义》引《随国集记》说汾州有“子夏石室”,又说“有卜商神祠”。(48)司马迁:《史记》,3165、220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这是学者拥有“石室”的实例。“食堂”名号,在正史中见于《汉书》卷九八《元后传》的记载。王莽取得最高权力后,“墮坏孝元庙,更为文母太后起庙,独置孝元庙故殿以为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长寿宫。以太后在,故未谓之庙”(49)班固:《汉书》,40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
汉代诸侯王陵地面建筑遗存,有的考古学者认为可能与“祠堂”有关。满城汉墓的发掘者指出:“汉因秦制,重视墓祀,皇陵皆立庙、寝、便殿,定时祭祀。”其他贵族官僚,也往往在冢茔附近修建供祭祀用的祠堂(或称“祠室”)。诸侯王的祠堂可能称为“祠庙”。满城汉墓依陵山开凿。“陵山顶上的汉代砖瓦,当即‘祠庙’一类建筑物的遗存。根据板瓦和筒瓦的纹饰较多样、时代有早晚等现象推测,在刘胜绝祀之前,‘祠庙’曾数经修葺。”(5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9页,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有学者注意到,虽然“传世文献没有明确记载西汉时期会在诸侯王陵附近修建与天子帝陵制度一样的陵庙,但在传世汉封泥中,有一些与诸侯王陵庙直接有关”,举列“齐哀庙长”“甾川顷庙”“中山穅庙”等,又指出,“此外在河北满城陵山窦绾墓中还出土有‘中山祠祀’封泥”,并进行了分析,以为“诸侯王国为每位诸侯王修建了以该诸侯王谥号为名的‘庙’”,“这些诸侯王庙”“修建在诸侯王陵的附近”。然而有学者认为:“但从现有考古资料看,我们还没有诸侯王陵陵庙建筑的其他具体考古学资料。”对于此前有的学者推定“可能是陵庙或祠庙的遗迹”,如刘胜墓相关遗存,论者认为,由于这些遗迹均未进行全面清理,故究竟是否为陵庙或祠庙的问题就需在考古资料增多后,才能进行一些新的分析。“就目前已知的这些考古学资料看,在诸侯王陵墓的墓顶和封土周围存在过的建筑遗迹的性质”,“应该不只陵庙或祠庙一种可能”。(51)刘瑞、刘涛:《西汉诸侯王陵墓制度研究》,419-42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也有学者关于祠祀遗存又举出“徐州狮子山汉墓出土有‘楚祠祀印’铜印章”“长沙出土‘长沙祝长’印章”等,对于墓上建筑遗存表示“这些修建在墓葬所在山顶的建筑还是有很大可能是作为诸侯王墓陵庙或祠庙存在的,这与丧葬习俗的延续、具体的地理环境及墓葬形制特征等有一定的关系”(52)刘尊志:《汉代诸侯王墓研究》,284-28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这些意见,都是我们考察陵墓祠堂设置时应当参考的。
一些列侯等级的墓园,考古调查和发掘都发现了祠堂遗存。陪葬茂陵的霍光墓,东北部有一高台,散存集中的建筑材料残件,考古工作者推测可能是祠堂遗迹。(53)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载《考古与文物》,2007(6)。陪葬杜陵的张安世家族墓园中,祠堂位于东兆沟北。其北侧有相连的小型房屋。(54)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西安凤栖原西汉墓地田野考古发掘收获》,载《考古与文物》,2009(5)。徐州荆山村一处以M4为主墓的西汉中晚期列侯家族墓园,包括祠堂。(55)徐州博物馆:《徐州荆山村西汉墓群发掘简报》,载南京博物院编著:《穿越长三角——京沪、沪宁高铁江苏段考古发掘报告》,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刘尊志:《江苏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性质浅探》,载《中原文物》,2016(6)。海昏侯刘贺墓园中有专门的祭祀性建筑“寝”,也有祠堂和相关的厢房。(56)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南昌市博物馆、南昌市新建区博物馆:《南昌市西汉海昏侯墓》,载《考古》,2016(7)。陕西西安石家街汉墓墓室东北相距30米处有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向的建筑,可能是祠堂,遗迹已被破坏。(57)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柴怡、张翔羽、孙武:《西安东郊石家街发现西汉列侯级别墓葬》,载《中国文物报》,2013-08-16。有学者分析了这一等级的墓葬多有祠堂的情形。“祭祀与相关设施”,据分析“以祠堂为多”,“确认的如南昌海昏侯墓地祠堂、西安石家街汉墓祠堂、徐州荆山村西汉墓地祠堂等。安陵东侧1号陪葬墓西北侧发现的大面积建筑遗址及霍光墓东北部残存的高台,原为祠堂的可能性较大”。研究者还注意到,“较多西汉列侯墓地还发现建筑材料残片,有的包含有一定数量的瓦当”,或与“祠堂”有关。“如聊城吴楼M1在地表发现较多文字瓦当,徐州拖龙山M3墓园内东侧大面积空地中板瓦、筒瓦、瓦当残片堆积较为集中”,推定这两处墓地“原应有祠堂类建筑”。对于墓园格局中“祠堂”的位置,研究者分析,“从《葬律》的记载看,西汉列侯墓园有垣墙、门、阙及罘罳等设施,而关于垣墙的记载中又穿插对祠堂的描述,推测祠堂的位置与垣墙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58)刘尊志:《西汉列侯墓葬墓园及相关问题》,载《考古》,2020(1)。。对于考古发掘所获具体资料,研究者也进行了考论。
三、“祠堂”“宗庙”:民间族权和国家政权的象征
邓晨与刘秀一同起兵反抗新莽。战有挫折,“汉兵退保棘阳,而新野宰乃汙晨宅,焚其冢墓”,这是在战争中破坏敌方宗族墓葬的通行手段。《后汉书》卷一五《邓晨传》写道:“宗族皆恚怒,曰:‘家自富足,何故随妇家人入汤镬中?’晨终无恨色。”(59)所谓“宗族皆恚怒”,说明“汙晨宅,焚其冢墓”的行为是可以产生一定的心理震慑效力的。所谓“随妇家人入汤镬中”,由于邓晨“初娶光武姊元”(60)范晔:《后汉书》,583、582、28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刘秀所以是邓晨的“妇家人”。《东观汉记》卷九《邓晨传》的记述是:“(邓晨)与上起兵,新野吏乃烧晨先祖祠堂,汙池室宅,焚其冢墓。”(61)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记校注》,28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对邓晨家族的惩罚,包括焚烧其“先祖祠堂”。“祠堂”,是“先祖”威望与“宗族”气运的象征。
“起祠堂”“立祠堂”,对于政治功业,也是一种重要的表彰嘉奖方式。两汉之际,益州太守文齐积极开发水利,发展垦田,稳定地方。刘秀即位,平蜀,“征为镇远将军,封成义侯”,然而途中去世。“诏为起祠堂,郡人立庙祀之。”《后汉书》卷八六《西南夷传》还记载,益州太守张翕“政化清平,得夷人和”。管理地方行政十七年,在任上去世,“夷人爱慕,如丧父母”,当地少数民族“二百余人,赍牛羊送丧”,直抵张翕家乡安汉,“起坟祭祀”。这一情形得到汉王朝执政集团的表扬,“诏书嘉美,为立祠堂”(62)范晔:《后汉书》,583、582、28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三国志》卷一五《魏书·贾逵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写道,曹髦东征,来到贾逵“祠下”,诏曰:“逵没有遗爱,历世见祠。追闻风烈,朕甚嘉之。昔先帝东征,亦幸于此,亲发德音,褒扬逵美,徘徊之心,益有慨然。夫礼贤之义,或扫其坟墓,或修其门闾,所以崇敬也。其扫除祠堂,有穿漏者补治之”(63)。以“礼贤”为目的的“祠堂”修缮,表现了“崇敬”之心。
《三国志》卷三八《蜀书·秦宓传》记载,刘璋控制蜀地时:“(王)商为严君平、李弘立祠”,秦宓致书表示赞许:“足下为严、李立祠,可谓厚党勤类者也”。又说扬雄的文化贡献显著,“邦有斯人,以耀四远,怪子替兹,不立祠堂”。而文翁促成“蜀学比于齐、鲁”“汉家得士,盛于其世”。也应当有所纪念,“宜立祠堂,速定其铭”(64)陈寿:《三国志》,484、9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可见“立祠堂”,是可以扩展文化功勋至于“四远”的适宜方式。
汉代国家“宗庙”,即刘邦家族的“宗庙”,是最高等级的“祠堂”。
汉王朝的“宗庙”在行政史中的作用,有非常重要的表现。刘贺政治生涯出现大起大落的情节。因“广陵王不可以承宗庙”(65),刘贺得以入长安。践帝位二十七日即被废,因霍光“具陈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庙状”。田延年等陈说废黜刘贺因由,言基于“汉之传谥常为孝者,令宗庙血食也”的考虑。(66)刘贺罪状,还包括“祖宗庙祠未举”“祠昌邑哀王园庙”,其最后政治结论的宣布,则与其帝位继承宗庙未曾认可有关,即所谓“未见命高庙,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庙,子万姓,当废”。废刘贺事,又“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庙”(67)班固:《汉书》卷六八《霍光传》,2937、2938、2944-2946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刘贺后得封海昏侯,却终生不能参与宗庙祠祀,“不宜得奉宗庙朝聘之礼”(68)班固:《汉书》卷六三《武五子传·昌邑哀王刘髆》,2769页,北京,中华书局,1962。。宗庙在刘贺政治浮沉经历中的作用,与秦汉帝国努力推崇的先祖崇拜有关。
是否“可以承宗庙”是帝位继承人选择的决定性要素。可以作为历史参照的,有秦二世胡亥自称即位得到“宗庙”认可的湖南益阳兔子山简牍文字“今宗庙吏及箸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69)孙家洲:《兔子山遗址出土〈秦二世元年文告〉与〈史记〉纪事抵牾释解》,载《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他在承接最高执政权之后的第一道政治公告中宣称,其执政合法性因“宗庙”的确定得以“明”“具”。
宗庙祭祀可能有非常严格的礼仪规范。据《史记》卷二〇《建元以来侯者年表》记载,有高昌侯董忠“坐祠宗庙乘小车,夺百户”,博阳侯邴翁孟“坐祠宗庙不乘大车而骑至庙门,有罪,夺爵”的案例。扶阳侯韦玄成“坐祠庙,夺爵”,时任太常,“祠庙”应当就是“祠宗庙”。(70)司马迁:《史记》,1067-1068、10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高平侯魏宾“坐祠庙失侯”。参见司马迁:《史记》,1065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其具体缘由不详,但是也反映了“祠庙”“祠宗庙”制度的严肃。董忠、邴梦翁两例,都是因为前往“祠宗庙”采用的交通方式不符合规定而受到削户、夺爵的严厉惩处。
汉代社会民间“祠堂”的营造规格、建筑形式和祠祀仪礼是否受到国家“宗庙”的影响,还需要获得更多资料才具备考论的条件。
“祠堂”作为纪念祖上、宣传孝道、寄托哀思、团结宗亲的方式,有很突出的文化意义。缅怀先祖的光荣,汇聚宗族的情感,在东汉豪族兴起的时代条件下,应该有益于宗亲这种社会关系的维系,有益于家族这种社会单元的凝聚。但是“祠堂”毕竟只是一种象征性的与物质层面存在距离的文化存在,对于实际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没有直接的作用。
前引张酺敕其子“其无起祠堂,可作槁盖庑,施祭其下而已”,体现出节俭风格。然而有人注意到,“祠堂”建设追求奢华富丽,已经形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后汉书》卷六三《李固传》“新营祠堂,费功亿计,非以昭明令德,崇示清俭”(71),就发表了否定性的意见。
《后汉书》卷四九《王符传》载录王符《潜夫论》文字,批判社会风习的“浮侈”。关于葬制,有这样的文句:“或至金缕玉匣,檽梓楩楠,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务崇华侈”(72)范晔:《后汉书》,2078、1637、24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其中“务崇华侈”,《潜夫论·浮侈》写作“崇侈上僣”(73)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1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三国志》卷五三《魏书·后妃传·文德郭皇后》记载:“……及孟武母卒,欲厚葬,起祠堂,太后止之曰:‘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皆由厚葬也。首阳陵可以为法。’”(74)陈寿:《三国志》,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制止“厚葬,起祠堂”的态度,表现出开明的意识。
两汉四百余年间,“祠堂”及相关文化表现,也有不同时期的变化,有时还会受到政治力量的异常冲击。上文说《后汉书》卷七《桓帝纪》记载“坏郡国诸房祀”事,李贤注引《王涣传》言保留“卓茂庙”“王涣祠”。《后汉书》卷七六《循吏传·王涣》的记载:“延熹中,桓帝事黄老道,悉毁诸房祀,唯特诏密县存故太傅卓茂庙,洛阳留王涣祠焉。”(75)范晔:《后汉书》,2078、1637、2470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帝王“事黄老道”,致使“诸房祀”普遍破坏。考察“祠堂”的历史变迁,这也是需要认识、理解并予以说明的现象。
到了魏文帝曹丕时代推行废寝殿、园邑的陵墓制度的改革,“祠堂”应当不再设于陵墓近旁。而曹操高陵曾经设置的“陵屋”(76)《三国志》卷一七《魏书·于禁传》记载:“权称藩,遣禁还……拜为安远将军。欲遣使吴,先令北诣邺谒高陵。帝使豫于陵屋画关羽战克﹑庞德愤怒﹑禁降服之状。禁见,惭恚发病薨。”参见陈寿:《三国志》,524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应当是与“祠堂”有关的建筑。魏晋及以后的“祠堂”,因曹丕对丧葬礼制的变革,社会文化意义已经完全不同于汉代。西晋时,“及宣帝,遗诏‘子弟群官皆不得谒陵’,于是景、文遵旨”(77)房玄龄:《晋书》卷二〇《礼志中》,6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晋书》卷四《孝惠帝纪》:“又诏子弟及群官并不得谒陵。”参见房玄龄:《晋书》,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民间“祠堂”建设的热情也有所衰减。行政之干预,有“为立祠堂”(78)《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其能兴云致雨,有益于百姓者,郡县更为立祠堂,殖嘉树,准岳渎已下为差等。”参见房玄龄:《晋书》,27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的做法,也有“禁州郡诸祠堂非正典者皆除之”(79)房玄龄:《晋书》卷一〇五《石勒载记下》,2748页,北京,中华书局,1974。的严厉措施。
汉代“祠堂”所体现的社会文化意义值得重视。汉代“祠堂”对后世表现出的长久的影响,也应当为丧葬史、宗族史、社会观念史研究者所关注。汉代“祠堂”的社会影响和文化作用,与儒学地位的上升、孝道宣传的盛起、宗法秩序的强化有密切的关系,其物质方面的条件,是社会经济的优裕和民间财力的富有。而魏晋以后“祠堂”的历史变化,同样既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生产与物质生活方面条件的限定。而北方非汉族人口构成的变化,也使得中原宗法传统受到一定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