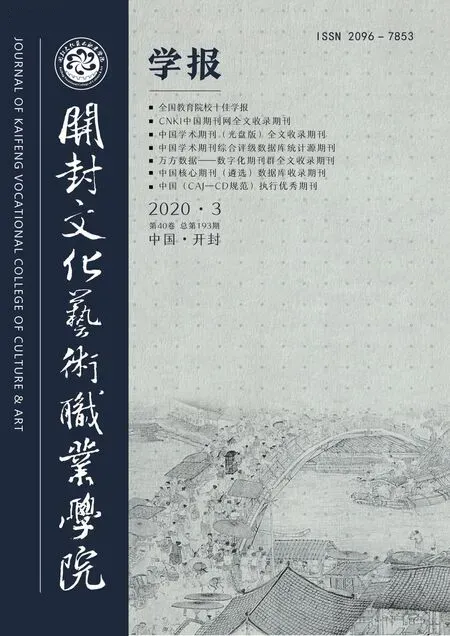论异域得宝故事所蕴含的文化观及其叙事艺术
张 阳
(聊城大学 文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唐代交通发达、政策开明、商业繁荣,吸引一大批胡商来华贸易。他们财力雄厚,所携之物往往珍贵且新奇,给大唐人民带来许多新鲜感。这极大地刺激了文人的感官,于是他们在小说中创作了大量胡商与宝物的故事。笔者梳理《太平广记》中的小说,观察宝物的来源,发现有不少珍奇异宝来自异域,于是将这样的故事归为“异域得宝”,下文将探索其蕴含的文化观及其叙事艺术。
一、异域得宝故事概述
胡商与宝物故事的基本情节就是得宝、持宝和鉴宝的过程。从得宝的角度看,可将胡商与宝物故事分为异域得宝和现实得宝两类。
异域是指那些迥异于人世间的非现实世界,那里有美不胜收的亭台楼阁、郁郁葱葱的花草树木、令人心醉的绕梁之音、含羞带笑的美貌仙女,这景致是人间所无法比拟的。唐人往往偶然进入其中,仙人会在分别时赠予其价值连城的宝物,最后胡人识宝[1]。笔者将这样的题材称为异域得宝故事。在《太平广记》中,异域得宝故事共10则,分别是《崔炜》《萧旷》《刘贯词》《华山客》《司命君》《韦弇》《崔书生》《赵旭》《张公洞》《任顼》。
二、异域得宝故事中唐人的社会文化观
虽然异域得宝故事具有奇幻、虚构的色彩,但任何文学作品都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加上创作主体的想象完成,因此,作品带有作者的主观意识和那个时代的特色。笔者将从三方面探讨异域得宝故事所蕴含的文化观。
第一,受道教影响,小说中道教色彩浓厚。从情节模式来看,这些小说中主人公的经历是典型的遇仙得道情节,有的虽没走上修道之路,但也得到仙人的所赐之宝。《萧旷》篇中的神女点化萧旷,“君有亲骨异相,当出世。但淡味薄俗,清襟养真,妾当为阴助”[2]2461,让其出世修仙,萧旷听后就拿着神女所赠之物开始修仙。从形象来看,塑造了一些仙人、道士的形象。《崔书生》中赐予书生宝物的女郎是西王母的三女儿玉卮娘子,西王母在道教神话中是女仙之首,她的女儿自然也属于道教的仙女;《任顼》中则塑造了一个贪婪、为了修道残害黄龙性命的邪恶道士形象。从宝物来看,唐人所得之宝属于道教。《韦弇》篇主人公所得宝物是玉清真人的,自然是道教之宝;《司命君》中的宝物则是天帝的宝爵。
第二,仙女与人的悲剧婚恋隐约透出严格的门第观。赐宝者的性别不同,故事的内容也大相径庭。在男性赐宝者的故事中,得宝者或是修仙者的朋友、同学、知己等。《司命君》中的二人即为同学,临别时司命君赠予元瑰宝爵。《任顼》中的黄龙感念任顼救命之恩,于是给了他一颗径寸大的珍珠。《张公洞》则是姓姚的人为了一探山洞究竟,偶然间进到神仙居住场所,道士见他饿得厉害,指着青泥让他吃。他把没吃完的青泥偷揣了回来,在市肆寻访时,胡人告诉他这是龙的食物。《刘贯词》中,刘贯词在苏州乞讨时遇到了龙子蔡霞,蔡霞让他帮忙给家里送信,信送到后,为了感谢贯词,蔡霞妹妹送了他一个价值十万钱的镇国碗。
当赐宝者变为女性时,故事的情节内容就变得相似,都经历了婚恋悲剧。如《崔书生》:
唐开元天宝中,有崔书生……忽有一女,自西乘马而来,青衣老少数人随后。女有殊色,所乘骏马极佳……崔生明日又先及,鞭马随之,到别墅之前,又下马,拜请良久。一老青衣谓女曰:“马大疲,暂歇无爽。”因自控马,至当寝下。老青衣谓崔生曰:“君既未婚,予为媒妁可乎?”崔生大悦,载拜跪请……其姊亦仪质极丽,送留女归于崔生。崔生母在故居,殊不知崔生纳室。崔生以不告而娶,但启以婢媵。母见新妇之姿甚美。经月余,忽有人送食于女,甘香殊异。后崔生觉母慈颜衰悴,因伏问几下。母曰:“有汝一子,冀得求全。今汝所纳新妇,妖媚无双,吾于土塑图画之中,未曾见此。必是狐魅之辈,伤害于汝,故致吾忧。”崔生入室,见女泪涕交下曰:“本侍箕帚,望以终天;不知尊夫人待以狐魅辈,明晨即别。”[2]393
女子一出场就骑着高头大马,身后随从百余人,可见其非富即贵。崔书生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他们虽十分恩爱,感情却经不起外界一丝丝的质疑。这样漂亮优秀的女子怎么会嫁给一个平凡书生?于是崔书生的母亲对其产生怀疑。一旦被人怀疑,女子便离开,他们的婚姻也随之破裂。出门声势浩荡、住“馆宇屋室,侈于王者”,可以说女子是典型的高门贵女。崔母的不信任其实是因为无法忽视二人身份、门第的差异。门第间的差异不仅存在于唐传奇名篇《霍小玉传》《李娃传》中,志怪小说中仙女与人的爱恋婚姻也受此影响,他们的悲剧结局正是严格的门第观念的必然结果。《赵旭》中,奴仆盗走琉璃珠,在与胡人买卖时起了争执,被官府抓了回去。在官府的审问下,奴仆将主人和仙女之事全部交代。青童仙女的身份暴露,而赵旭只是一个没有功名的书生,二人身份悬殊,注定了他们的恋爱只能以仙女离开悲剧收场。
第三,读书人对商业的矛盾态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观念和“士农工商”的阶级现实,使古人一直将学习孔孟之言、走仕途之路奉为圭臬,商贾之人则被视为末流。唐代发达的交通网、开明的贸易政策、强盛的国力吸引越来越多的胡商来华贸易,长安、扬州、洛阳这类大城市的市肆中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一些胡商还行走于各个村落贩卖货物。资本经过流转,越来越多胡商拥有了巨大的财富。虽然他们是商贾末流,可其雄厚的财力依然引起众多清贫士子的羡慕。读书人的尊严和现实的打击使得这些读书人对商业、对胡商呈现出矛盾的态度,反映在小说中就是创造出许多读书人偶然间或不费吹灰之力就在异域中得到仙人赐宝,而且拥有高超鉴宝能力的胡商往往主动上门购买宝物的故事。如果作为持宝者的读书人出价低,胡商不仅没有顺势买走,还会主动将宝物加价至对应的价格。《韦弇》篇中的韦弇考进士失败,游玩赏花时就误入了仙境。饮美酒、赏芳华、吃珍馐、品丝竹,尽享美妙,分别时还收到三件宝物,每一件都珍贵无比。第二年韦弇东游广陵,遇上前来求宝的胡商。胡商二话不说,用数十万金买下了玉清真人之宝。这种豪气看似比较虚假,其实正好说明贫困的读书人对金钱的渴求。在赚得巨款后,韦弇立刻置备家产,甚至辞官远游,“因筑室江都,竟不求闻达,亦不知所终”[2]210。虽然这篇小说中想象虚构的成分夸张,但这的确是士子希望能摆脱困顿的现实、拥有巨大财富的内心反映。
三、异域得宝故事的叙事艺术
到唐代,小说发展日趋成熟,无论是题材、内容还是想象、虚构,都较前代有长足进步,胡商与宝物题材的小说就是在这一时期兴起的。异域得宝故事是这类题材小说的一个小类,具有独特的叙事艺术。
从叙述方式来看,作为一种叙述文学,小说包括讲述式叙述和呈现式叙述。讲述式叙述是指小说以第三人称全知全能视角叙事,这个叙事者仿佛独立于故事之外,可以随时中断叙述,也可以对情节中的人和事加以诠释与点评,全文读来像在讲故事。敦煌通俗小说中有话说、单说等套语,是典型的讲述式叙述。呈现式叙述是指小说犹如一幅画卷,将故事展现在读者面前,《太平广记》中的十则异域得宝故事明显属于这种。《司命君》以时间为线索,从司命君和元瑰二人幼时开始叙述,一个天赋异禀走上修道之路,一个事业有成做了御史。宝应二年(763),二人偶然相遇,司命君邀请元瑰到家中游玩,于是有了之后元瑰异域得宝、胡商识宝买宝的故事。整篇小说自然而然展开,犹如一幅长长的画卷,将二人传奇的经历呈现在读者面前。
从叙事结构来看,唐人进入异域得宝,在现实社会碰到识宝胡商并将宝物卖掉换取巨大财富,这是典型的现实世界-非现实世界-现实世界的板块叙事结构[3]138。以《韦弇》为例,第一板块往往用史传实录原则,“韦弇字景照。开元中,举进士下第,游蜀。时将春暮,胜景尚多,与其友寻花访异,日为游宴”[2]209,交代事情发生的时间、缘由以及主人公;第二板块叙述凡人进入仙府、仙洞的奇遇,“忽一旦有请者曰:‘郡南十里许,有郑氏林亭,花卉方茂,有出尘之胜,愿偕游焉’”[2]209,用华丽的辞藻铺陈仙府、异域的美;第三板块篇幅较短,多是回归现实社会,“拜而谢之,即别去。行未及一里,回顾失向亭台,但荒榛而已”[2]210,使作品保持完整。三个板块间相互碰撞、转换,又相互衔接,将异域世界和现实世界完美连为一体,从而形成独特的叙事结构。这是唐五代时期佛道思想盛行在文学中的表现之一。
从叙事内容来看,异域得宝故事还有诗词出现。其实这些诗词是小说中人物和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刻画人物形象和推动情节发展起到了独特的艺术作用。《太学郑生》跟随着郑生的视角,见到了身世艳丽的女郎,她张口就能吟诵《楚辞》《九歌》《招魂》《九辩》之书,还能拟词赋诗,集才情和美貌于一身,刻画出一个识才智趣的美丽龙女形象。
结语
异域得宝故事发生在非现实世界,看似荒诞、虚假,但结局往往回归现实生活。它不是单纯地宣扬佛道、因果报应,其中蕴含着唐人当时的文化观,研究异域得宝故事有助于进一步整体把握唐代的社会文化。其独特的叙事艺术也为之后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