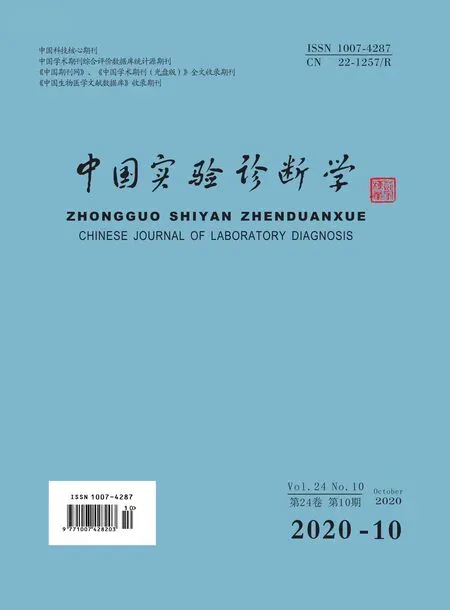唾液用于口腔扁平苔藓诊断的研究进展
郑 云,莫娟萍,张 炜,丁 典,王景云
(吉林大学口腔医学院 VIP综合科,吉林 长春130021)
口腔扁平苔藓(OLP)是一种慢性炎症性疾病,影响口腔黏膜,包括颊部、唇部、舌和牙龈组织。据估计,OLP影响了全球1.01%的人口,欧洲的发病率更高(1.43%)[1]。受OLP影响的患者会出现灼热感和瘙痒感,直至严重的糜烂性疼痛;由于日常活动(如进食或口腔卫生)的损害,这种疾病对生活质量有巨大的负面影响[2]。虽然对其病因尚未达成共识,但扁平苔藓的发生和发展被归因于一种免疫学机制,该机制与皮肤表现如红斑、白色条纹、丘疹或溃疡有关[3]。OLP的组织病理学很典型,上皮交界处有明显的淋巴细胞浸润,棘层和基底细胞层变性[4]。OLP被认为是一种潜在的恶性疾病,有1.14%的可能性发展为口腔癌[5]。因此,早期发现病变对患者预后、治疗干预、生存率和复发有重要影响。诊断和监测通常需要痛苦的侵入性程序,如活组织检查和重复的血液测试,这给患者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当今生物技术的飞速进步提供了独特的机会,可以通过利用唾液来评估健康和疾病个体的状况,从而避免有创措施。
唾液是一种由于技术进步而具有流行诊断潜力的生物流体,它为临床诊断提供了血液及组织样本的替代方案,特别是在儿童和青少年中,因为在儿童和青少年中,血液样本采集以及组织的切取往往会降低随访的依从性[6]。近年来唾液诊断口腔及全身疾病成为热点话题,本文就唾液用于口腔扁平苔藓诊断的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唾液及唾液诊断
1.1 唾液的定义、作用、组成成分
唾液是由龈沟液、黏膜渗出液、唾液腺腺泡超渗液等组成的混合液体。唾液来源于三对大唾液腺(腮腺、舌下腺和下颌下腺)和大量的小唾液腺。唾液能够提供润滑作用;促进咀嚼、消化;还具有抗菌特性;并可作为酸性食物的缓冲;还具有排泄作用;此外,唾液能抑制牙齿脱矿,防止龋齿[7]。唾液在生理分泌情况下每天产生0.75-1.5L,夜间减少[8]。唾液含有99%的水和剩余1%的蛋白质(黏蛋白、酶、免疫球蛋白)、电解质、脂质和无机物[9]。
唾液成分复杂,含有大量尿素、氨、尿酸、葡萄糖、胆固醇、脂肪酸、甘油二/三酯、中性脂质、糖脂、氨基酸、类固醇激素和黏蛋白、淀粉酶、凝集素、糖蛋白、溶菌酶、过氧化物酶、乳铁蛋白和分泌型IgA、溶菌酶、髓过氧化物酶、富组蛋白、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黏蛋白G1和G2、防御素等;唾液中含有大量来自于血浆的Na+、Cl-、Ca2+、K+、HCO3-、H2PO4-、F-、I-、Mg2+等离子成分;同时,唾液中含有大量与口腔及全身系统性疾病相关的700多种微生物[10]。
1.2 唾液诊断定义、发展及优势和不足
唾液诊断是通过检测唾液中与特定疾病相关的特异性物质来诊断疾病的方法。唾液诊断被认为是一种很有前途的方式,可以提供早期和准确的诊断,改善预后,并对治疗后进行良好的监测。唾液诊断学发展中的技术障碍之一是,与血液相比,唾液中的分析物浓度较低(以前的基质中分析物浓度低100-1000倍),在过去的二十年里,高通量技术的进步正在超越这些限制;如今,基因组、蛋白质组、转录组、代谢组和微生物组的方法已经被应用,以便全面分析唾液,发现区分生物标志物,并将它们结合起来,以获得附加和强大的诊断信息[11]。
作为一种诊断液,唾液比血清有几个优点:性价比高,具有实时诊断价值,有多个样本,容易获得,需要的操作较少。在诊断过程中,必须采用感染风险最小的非侵入性采集方法,并针对所有类型的患者,特别是那些抽血以及组织切取可能面临挑战的患者(儿童、焦虑或不合作的患者)[12]。
尽管有这些有利的属性,但唾液作为一种生物流体存在局限性,限制了其诊断潜力。唾液可能被认为是口腔和全身健康的一面镜子,但某些生物分子的水平并不总是与血清中这些标志物的水平一致[13]。唾液成分可能因采集方法和时间、使用的技术和唾液流刺激程度的不同而不同。这些变化,再加上唾液pH值的变化和同一个体一天中唾液流量的可变性,可能会对唾液标志物的浓度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唾液腺功能还会受到一些全身性疾病、大量药物和放射治疗的影响。此外,全唾液中来自宿主和口腔微生物的蛋白水解酶会干扰某些生物标志物的稳定性和浓度[14]。
2 唾液用于诊断OLP
根据2011年生物标志物定义工作组的规定,生物标志物是一种可以作为正常生物或致病性指标进行客观测量和评估的特征作为治疗干预的药理学反应的指标[15]。唾液用于OLP的诊断正是借助这些特异的生物标志物,它们的高或低表达往往预示着疾病的存在。
2.1 细胞因子
在OLP的生物标志物中,唾液细胞因子的测定可能成为诊断、预后、疾病应答和治疗靶点发现的潜在工具[16]。
Mozaffari等[17-20]研究发现,OLP患者唾液和血清中的白介素-4(IL-4),白介素-6(IL-6),白介素-8(IL-8)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均显著高于健康对照组,并且OLP患者唾液中上述细胞因子水平显著高于血清中水平,表明,唾液中这些细胞因子的检测可能比血清检测更有助于诊断OLP。Liu等[21]研究发现,OLP患者唾液和血清中IL-6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有显著差异,但与临床分型(糜烂型或非糜烂型)无关,表明,唾液及血液中IL-6水平与临床症状可能无明显差异。
有学者[22]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OLP患者血清和唾液中干扰素-γ(IFN-γ)水平的汇集MD分别为3.60 pg/mL(P=0.23)和±0.02 pg/mL(P=1.00);与非糜烂型相比,糜烂型患者血清和唾液IFN-γ水平的MD值分别为±2.52 pg/mL(P=0.03)和±2.01 pg/mL(P=0.20),表明OLP患者血清和唾液中IFN-γ水平与健康对照组,糜烂型与非糜烂型OLP之间在唾液水平上均无统计学差异,因此认为该细胞因子在OLP的发病机制和严重程度中不起重要作用。然而,Humberto等[23]研究发现,OLP患者唾液细胞因子(IL-4、IL-6、IL-8、IFN-γ和TNF-α)以及NO水平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表明它们可能对监测OLP的疾病活动性和治疗后反应具有重要的诊断和预后潜力。
Th1和Th2免疫反应均参与了OLP的发生发展,干扰素-γ(IFN-γ)和白细胞介素-4(IL-4)是Th1型和Th2型细胞因子中最具特征的两种细胞因子,在生理和病理免疫过程中分别调节T细胞分化和Th1型/Th2型平衡,干扰素-γ参与细胞毒性CD8T细胞的成熟和活化,维持主要Ⅱ型组织黏附分子的表达,从而参与角质形成细胞凋亡和慢性OLP;另一方面,IL-4促进Th2细胞分化,在调节抗体产生和体液免疫反应中起重要作用[24]。白细胞介素-6(IL-6)是一种参与免疫和炎症反应的多功能细胞因子。IL-6的产生来源于活化的T和B细胞、活化的单核细胞、巨噬细胞、内皮细胞、成纤维细胞和角质形成细胞,并通过核因子-κB来控制,据报道,核因子-κB在炎症过程的加剧中发挥重要作用[25]。
白细胞介素8被认为在OLP的异常增生改变中起作用,它可以激活中性粒细胞、嗜碱性粒细胞和T细胞,并且能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的表达,从而增加血管生成,促进淋巴细胞浸润和淋巴细胞的长期积累,导致OLP的异常增生改变[26]。TNF-α是一种促炎和免疫调节细胞因子,它能刺激炎症的急性期,导致其他促炎细胞因子(如IL-1和IL-6)的合成,并激活T和B细胞,被认为介导自身免疫和炎症过程[27]。以上表明唾液细胞因子中IL-4,IL-6,IL-8,TNF-α,IFN-γ以及参与氧化应激的NO这些生物标志物有助于临床诊断OLP。
2.2 皮质醇
皮质醇是调节过程和行为的主要糖皮质激素,包括免疫调节。高皮质醇水平归因于压力的存在,并可能引发免疫紊乱[28]。皮质醇被认为是压力和焦虑的生物标志,它的变化可以改变细胞因子分布[29]。OLP与压力有双重联系:焦虑和应激事件被认为是OLP发病的触发因素,但同时,OLP本身也是患者的压力源。鉴于有报道称应激可导致OLP的复发,皮质醇已被提议作为OLP的一个可能的诊断标志物[30]。
Jornet等[31]学者研究发现,OLP患者唾液皮质醇水平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其汇集MD为4.27 ng/mL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此外,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检测结果显示,OLP患者唾液皮质醇水平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然而Skrinjar等[32]研究表明,OLP患者和健康对照组的唾液皮质醇水平没有差异,需要对更多的OLP患者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确定OLP与应激之间的相关性。以上结果的不同可能归因于检测方法及实验设计的差异。
2.3 相关蛋白
Larsen等[33]研究发现,患者非刺激性(48.6±29.5 μg/min)和咀嚼刺激性(96.1 ± 51.7 μg/min)全唾液中SIgA水平均高于健康对照组(47.8±21.79,82.4±38.1 μg/min),但差异无显著性。Mozaffari等[34]研究表明,OLP患者唾液中Ig A、Ig G和Ig M水平均高于血清水平,其中Ig A显著高于血清水平。Fang等[35]研究发现,3种凝集素(AAL、PWM、PHA-E+L)识别的糖蛋白主要在OLP唾液中增多,同时,这些糖蛋白也表现出与年龄相关的显著变化,因此这有助于开发新的诊断OLP的潜在生物标志物。
有学者[36]发现,OLP患者唾液中NO(145.71 mol)和亚硝酸盐(141.01 mol)水平明显高于对照组(P<0.05),并且C反应蛋白(CRP)水平也明显高于对照组,表明,NO和C反应蛋白可能成为潜在的唾液生物标志物,用于疾病的早期诊断和监测。CRP经常被用来作为炎症的标志,OLP患者的唾液水平高于健康人,这表明在监测疾病进展方面有潜在的作用。
Talungchit等[37]通过ELISA和免疫印迹分析验证了唾液的蛋白质水平,结果发现纤维蛋白原片段D和补体成分C3c在OLP患者唾液中的表达增加,然而胱抑素SA的表达降低,表明,补体C3c、纤维蛋白原片段D和胱抑素SA可作为筛查和诊断OLP的唾液生物标志物。纤维蛋白原片段D和C3c在炎症中起核心作用,而胱抑素SA属于胱抑素超家族,是一组具有抗菌活性的半胱氨酸蛋白酶抑制剂。事实上,纤维蛋白原表达和C3沉积是使用IFD的OLP的典型表现[38]。
Souza等[38]研究表明,S100A8、S100A9、结合珠蛋白等蛋白可激活细胞因子,可能与OLP的病理功能和抗氧化活性有关。S100A8和S100A9(也称为MRP8和MRP14)是钙和锌结合蛋白,通过IL-17参与炎症和细胞因子的产生,S100A8还可以通过吸引CD8+T细胞和自然杀伤(NK)细胞来诱导细胞凋亡[39]。
2.4 氧化应激相关标志物
活性氧(ROS)参与了包括OLP在内的许多炎症性疾病的发病过程。因此,测定唾液氧化应激标志物是诊断口腔疾病的一种很好的替代方法。Darczuk等[40]测定了唾液氧化应激标志物,结果发现,OLP患者唾液中谷胱甘肽(GSH)和总抗氧化能力(TAC)水平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P<0.01),OLP两组(网状和糜烂型)唾液硫代巴比妥酸反应物质(TBARS)平均水平均高于对照组(P=0.01),监测唾液的氧化-抗氧化状态可能是确定OLP患者疾病发展阶段的一个有效且侵入性较小的指标。Bakhtiari等[41]发现OLP组唾液尿酸(UA)均值(2.10±0.19 mg/dL)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4.80±0.2 9 mg/dL),表明,UA可作为监测和指导OLP治疗策略的一个有用的抗氧化生物标志物。
2.5 微生物
还可以通过检测唾液中的一些特异性微生物来辅助诊断OLP。Wang等[42]研究发现,OLP组织与OLP唾液中微生物系统不同,与健康对照组比较,OLP患者唾液中二氧化碳噬纤维菌属和球菌属含量较高,OLP组织中大肠埃希氏菌和巨球菌含量较高,而肉杆菌科、黄杆菌科和柄杆菌科、韦荣氏菌科等7个菌科在OLP患者唾液和组织中均富集,表明,特异性细菌可能被认为是OLP的潜在的生物标志物。细菌群落组成的差异可能与环境因素和疾病易感性有关,唾液可能代表了整个口腔微生物系统的变化,易受口腔卫生和口腔疾病的影响,不同的微环境可能是细菌群落结构不同的驱动因素。
Hijazi等[43]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OLP患者唾液的细菌多样性显著降低(P=0.021),细菌多样性的降低与促炎细胞因子IFN-γ、IL-17A和IL-1β呈负相关,与TNF-α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的相关性,表明口腔微生物群多样性作为疾病活动性的标志物在控制免疫介导的口腔黏膜疾病方面具有潜在的价值。有学者[44]研究发现,口腔微生物系统与OLP相关,如直肠弯曲杆菌、核梭杆菌和黏膜奈瑟氏菌在OLP患者唾液中含量较高。
3 总结
唾液是一种有望可以替代血液及组织的良好的诊断物。唾液中的生物标志物在OLP的早期检测中可以提供很高的诊断信息,并具有很强的区分性。由于其简单、无痛、非侵入性的采集,能够避免重复采血以及组织的切取,从而减轻患者的不适并提高了依从性。
基于唾液的诊断技术可以潜在地以经济有效的方式对整个人群进行特定疾病标志物的筛查。基于其准确性、有效性、易用性和成本效益,唾液诊断测试目前被应用于临床和基础研究,它们可以为各种口腔和系统疾病的诊断铺平道路。然而,为了将基于唾液的诊断纳入日常临床实践,仍有研究要做。唾液采集方法和生物标志物需要标准化和进一步验证。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确定它们的准确性和有效性。预计敏感性和特异性的唾液诊断工具的出现和明确的临床指南建立将在不久的将来使唾液诊断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