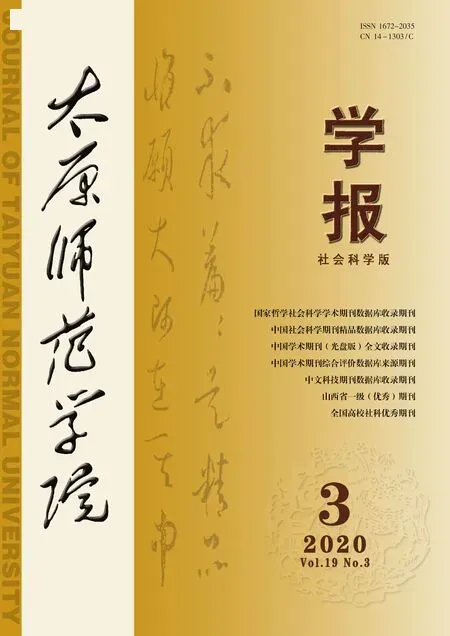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性论
韩 强
(南开大学 哲学院 , 天津 100073)
一、陆九渊的“宇宙心”和“自存本心”
陆九渊(1139—1193)提出了“心即理”和“自存本心”的心性本体论。他的心性一元论与程颐、朱熹的性两元论主要区别在于:程朱的性即理的本体论是客观精神的他律道德。由客观理性通过人生气禀具于心,转化为心性情的主观精神,再通过“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心性修养达到主客观合一。陆九渊的“心即理”是主观精神的自律道德。由自存本心的简易功夫使道德理性感情化。
(一)“宇宙即是吾心”的本体论
陆九渊说:“宇宙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圣人固言仁矣,天下之言仁者,每不类圣人之言仁。圣人固言义矣,天下之言义者,每不类圣人之言义。”[1]173陆九渊还认为:“理在宇宙间,未尝有所隐遁,天地之所以为天地者,顺此理而无私耳,人与天地并立,而为三极”[1]90,“在天曰阴阳,在地曰刚柔,在人曰仁义。故仁义者,人之本心也”[1]6。这些都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理”的内容。他又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东南西北海,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近世尚同之说甚非。理之所在,安有不同?”[1]173
这里,陆九渊发挥了程颢天人一本的思想,明确地把“理”规定为人的“本心”,强调“心即理”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永恒性。他还从心物关系上提出心为主、物为客的思想,认为“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1]3。这种主客关系,实质上是心体物用。
陆九渊在同朱熹辩论“无极而太极”时,反对以太极为形而上之理,他主张太极即阴阳,道器同体,这种观点进一步发展,就是道德感情的心性合一论。陆九渊充分发挥了孟子的心性合一论,把道德感情向上提升为宇宙本体的“天理”,主张“心即理”。这实际是把道德理性感情化。这正是朱陆心性论区别的关键问题。
(二)朱陆之辨——理在心外与理在心中
陆九渊明确提出“心即理”“心即性”的心性本体论。他与朱熹的分歧不仅在于“无极而太极”“尊德性道学问”,更重要的是心性论观点的分歧。
第一,朱熹的“性即理”是以理体气用或理在气先推出人的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论天命之性,则专指理言,论气质之性,则以理与气杂而言之”[2]67。理除了具有宇宙本体意义之外,是指仁义礼智之理。陆九渊的“心即理”把人的道德感情说成是理,是性善,而对于人生气禀则说得含糊不清。他说:“孟子当来,只是发出人有是四端,以明人性之善,不可自暴自弃,苟此心之存,则此理自明。当恻隐处自恻隐,当羞恶,当辞逊,是非在前,自能辨之。”[1]252这是发挥孟子思想把四端道德感情说成是本心善性。他还认为,人生天地间气有清浊,因此具体来说,人有智愚、贤和不肖的差别,但气禀与这种心理素质差别没有必然联系,“乃有大不然者”[1]52。因此,陆九渊的人性论主要是道德感情的心性合一论。
第二,朱熹“心统性情”之心,虽有体用动静意义,但心不是宇宙本体,理先于心而存在,先有知觉之理,理主宰气而有知觉之心,性即理,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情包括四端之情与喜怒哀乐,这是以《易传》《中庸》解释孟子,把孟子心之善端扩张为仁义礼智的自律道德,变成仁义“理智之理”发为四端道德感情的他律道德。陆九渊直接发挥了孟子的心性合一思想,认为“情、性、心、才都只是一般物事,言偶不同耳”[1]288。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爱、敬等道德感情就是良知、良能,“此吾之本心也”[1]3。这种思想与孟子的自律道德观点基本一致。不过,孟子所说的“心” 先天应有四端、良知的本性,不具有本体论意义,而陆九渊的“心即理”把四端、良知说成宇宙本体,“心之体甚至大,若能尽我之心,便与天同”[1]288。陆九渊强调心体自然发出道德感情和行为,而不像朱熹那样用心之未发、已发说明性静情动的体用关系。
第三,朱熹把知觉之心区别为“道心”和“人心”,认为“心只是这一个心,知觉从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觉从义理上去,便是道心”[2]68。陆九渊也认为人心只是一个心,但他认为天理、人欲的划分违背天人一本,性静情动的划分是把“动”排斥在性外,道心、人心的划分是把一心分为二心。他主张“道心”即是仁义,同时又认为知觉意念有正邪之分。
陆九渊按照孟子大体、小体的观点,把心之官能思的良知说成是“四端者,即此心也,天之所与我者,即此心也。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1]95,认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流浪展转,戕贼滔溺之端不可胜穷。最大害事……实乃物欲之大者”[1]43。由此他又进一步认为,心之灵受蒙蔽产生邪念,被声色货利引诱,产生了奸诈狡猾的邪念,本心之理不明,就是心之病。这样天理与物欲的对立就转化为人心念虑的正邪之分。思虑之正是公理、道心,为人心所固有。邪念是物欲,是耳目之官不思随物流转引起的,应该摈弃。因此陆九渊又说:“私意与公理,利欲与道义,从其大体与小体亦在人耳”[1]117。
第四,朱熹继承了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心性修养方法。他说:“未见端倪发见时,且得恭敬涵养,有个端倪发见,直是穷格去。亦不是凿空寻事物去格。”“涵养于未发见之先,穷格于已发见之后。”[1]403这种说法比程颐更明确。陆九渊也讲格物致知,但主张直觉顿悟。他不像朱熹那样主张“理一分殊”,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而是认为“天下事事物物只有一理,无有二理,须到其至一处”,“一是即皆是,一明一切明”[1]294,这是一种直接了悟整体的内心直觉顿悟。
陆九渊认为“格物”即是“减担”的说法:“到某这里,只是与他减担,只此便是格物。”[1]287这种减担的方法实际是减少向外认识,而发挥内心固有的良知。“当恻隐时即恻隐,当羞恶时即羞恶,当辞让时即辞让,是非至前,自能辨之。”[1]252这种道德感情的自然论带有知行合一的因素。在知行观上,陆九渊仍主张知先行后,认为只有先“心之明”“知之理”,再去践履,才不会犯“适越而北辕”的错误[1]5。
王阳明认为陆九渊沿袭了程朱“知之在先,行之在后”的旧说,其“致知格物”“未精一处”,未免于杂,终于以“知行合一”补陆九渊“知先行后之弊”[3]208。
(三)发明本心的心性修养方法
陆九渊提倡简易功夫,反对事事省察。他认为涵养省察没有分别,不必在存养之外再讲究省察,也不必于事事物物上求定理,他认为朱熹那套涵于未发之前,格物于已发见端倪的修养方法是“艰难其途,支离门户”,他认为功夫全在存养上,因此说:“古人教人,不过存心、养心、收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养,而反戕贼放失之耳”[1]41。他认为功夫全在存养上,存心、养心就是保持固有的良知,像灌溉一样,使之畅茂条达,“根本者立,保养不替。自然日新,所谓可大可久者,不出简易而已”。[1]41这种自我反省、自我认识、自我完善的过程,就是扩充本心,不断保养,自然日新。
首先是存心。陆九渊说:“孟子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其为人者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者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只存一字,自可使人明得此理。此理本天所以与我,非由外铄也。明得此理,即是主宰,真能为主,则外物不能移,邪说不能惑。”[1]3所以,必须保持住本心,才能做到养心。
其次是养心。陆九渊说:“能保敬谨养,学问思辨,而笃行之,谁得而御。”[1]116陆九渊的学生说:“先生之讲学,先欲复本心以为主宰,既得本心, 从此涵养,使日充日明。读书考古,不过欲明此理, 尽此心耳。”[1]336所以,养心就是涵养。
陆九渊还认为,“学能变化气质”,但只起辅助作用,“圣贤垂训,师友亲磋,但助鞭策耳”[1]43。最根本的方法仍然是自存本心,“不识一字,亦还我堂堂地做个人”[1]290。心学修养的目标是明理、立心、做人。一是做伦理道德的完人,二是要做超人。这种“完人”与“超人”, 可以达到“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1]299的最高境界,宣扬主观精神的无限扩张。
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心性论
王阳明(1472—1529)在陆学“泯然无闻”三百多年的明朝中叶,恢复其“圣贤之学”的地位,改变了明代“是朱非陆”之“论定”[3]806,建立了系统的心性一元论体系。他采取主观唯心主义的方法对朱熹的理体气用,性体情用,道心、人心和格物致知进行了改造,建立了心性一元的心体用论思想体系。
(一)心即理的真我精神
王阳明所说的“心”,也是知觉之心,他以“虚灵明觉”之体为良知。但是,王阳明的说法与陆九渊有所不同。陆九渊也说过:“人心至灵,此理至明,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他只从心物关系说明心为主物为客,对心体用意义说得不明确。王阳明则明确了良知为体、知觉为用,从心物关系上视良知为体,感物而动的事物为用。从理论思维方式上看,陆王都发挥了孟子的心性合一论,但陆九渊仍然沿袭了孟子心为大体、耳目为小体的思维方式,主张先立其大,排斥小体,因此没有提出明确的心体用论,只明确了心本体论。王阳明则把大体、小体的关系进一步概括为体用关系,以良知为体,以耳目闻见为用,因此进一步推出心体物用的观点。这是王阳明心学高于陆九渊之处。正因为如此,王阳明采取生理、心理、认识和伦理相结合的方法,提出了良知、真我的心体用论,把理气观、人性论、心性情论、道心与人心都包含在他的心一元论思想体系中。
1.真我良知为体,欲情知为用
王阳明发挥了程颢的“以觉识仁”和谢良佐的“真我”论,提出了良知本体的真我论,他认为言听视动的知觉之心是由天理主宰的,因此,他说:“汝心欲是那能视听言动的,这个便是性,便是天理。有这个性才能生这个性之生理,便谓之仁,这个性之生理发在目便会视,发在耳便会听,发在口便会言,发在四肢便会动,都只是那个天理发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谓之心,这个心之本体原只是个天理,原无非礼,这个便是汝之真己。这个真己是躯壳的主宰”[3]36。
王阳明认为心“不专是那一团血肉”的生理器官,而是包括耳目视听和知觉痛痒的知觉心。[3]36他在知觉的生理、心理和认识论成分上,又提出心为身之主宰,这个主宰就是天理、真己。因此,他认为心之全体是恻怛之仁,这种道德感情运用得宜就是义,其条理就是理。仁、义、理之心即是“良知”[3]43,良知是有生命的主体,能主宰视、听、言、动,这就是性,就是天理。心之本体是“无善无恶”[3]115的绝对本体,它是纯净的,这就是真己。
这里,我们可以把王阳明与西方的心理学家弗洛依德比较一下:弗洛依德提出了超我、自我、本我的观点。“超我”是指道德良心,“自我”是知觉的道德理性运用,“本我”是心理的冲动。王阳明“真己”的心体良知接近于弗洛依德的“超我”,无善无恶的良知本体具有绝对的超越性;“知行合一”的道德行为是知觉的运用,与弗洛依德知觉道德理性运用的“自我”意义相通;人欲与弗洛依德的生理冲动意义相通。
王阳明认为,心有知觉就产生意念,意念分为灵明的良知天理和人欲,诚意的功夫就是随着意念落实到具体事物。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格物致知。“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功夫所用之条理,虽亦皆是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功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故欲修其身者,心在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体则性也”[3]971。这样,王阳明就把良知本体通过耳目视听和道德行为的运用贯穿到了具体事物中。
2.性、情、欲、知统一于良知的性气一元论
王阳明发挥程颢“性即气,气即性”“性无内外”的观点,力求把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统一在心体用论的思维模式中。他说:“生之谓性,生字即是气字,犹言气即是性也。气即是性,人生而静以上不容说,才说气即是性,即已落在一边。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从本原上说,然性善之端须在气上始见得,若无气亦无可见矣。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即是性。……若此见得自性明白时,气即性,性即气,原无性气之可分也。”[3]61这里,王阳明把恻隐羞恶的道德感情说成是心性合一的天命之性,把气说成是性的运用,因此,强调“生字即是气字”。只有弄清本原时,才可以说气即性。离开了本然之性而说气即性就会偏执一边。从性善之端在气上见,可以说性气无分别。这实际是良知为本体、气为用的理气观在人性论中的具体运用。
王阳明还进一步把情、欲、知统一于道德理性。他说:“性一而已。仁义礼智性之性也。聪明睿智性之质也。喜怒哀乐性之情也。私欲客气性之蔽也。质有清浊,故情有过与不及而蔽有深浅也。私欲客气,一病两痛,非二物也。”[3]68这样,他就把性、知、情、欲分为四个层次。仁义礼智是良知本体之性,因此称为“性之性”;“知觉智力”是“性之质”,有清浊差别。
喜怒哀乐之情有过与不及。私欲客气影响良知的正常发挥,因此是性之蔽。王阳明的性情论看到了性发为情的过程中知觉的中介作用,这是他比程朱更精细之处。
3.心性体用动静一源,未发即在已发之中
王阳明以良知为体、情欲知为用的心体用论说明未发与已发的关系。一方面他吸取了程朱性体情用的观点,另一方面他又把道德感情的良知规定为性体,进一步说: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在人情里。其要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慎独。”[1]15。因此,他所说的“情”具有广泛的心理活动和人的行为意义。
未发、已发是程颐、朱熹讨论的大问题,对此程颐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是程颐最早的说法:“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心本善,发于思虑则有不善。若既发,则可谓之情,不可谓之心。”[4]204
第二种说法,是在与吕大临讨论“中和”时,开始程颐认为 “心”只能说已发,在情感发用的时候显现。而吕大临认为“未发”的时候,心也是存在的,“未发之前,心体昭昭具在,已发乃心之用也”[4]608。这时,程颐又说未发是“中”接近于性,心只能说是“已发”。
第三种说法,是程颐与吕大临讨论时说“凡言心者,皆指已发而言,此固未当,心一也,有指体言而言之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者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4]609。
对此朱熹有两种说法,也就是新旧中和说:
旧中和说认为:“盖天下只是一个天机活泼”,“流行发用无间容息,据其已发而指其未发者,则已发者人心,而凡未发者皆其性也”。这是从宇宙本体论和人的心体流行上说明体用关系。太极、诚体可以说是寂然不动的未发之性,而心体流行无息静止,只可说是已发为心。[5]1315-1318
朱熹“中和旧说”从知觉意义上说心体流行不容间断,这是程颐的说法。
朱熹在给张栻的信中谈了新的观点:“然一人之身,知觉运用,莫非心之所为,则心固所以主乎身,而无动静语默之间也。然方其静也,事物未至,思虑未萌,而一性浑然,……思虑萌焉,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谓和,是乃心之所以为用,感而遂通者也。”[5]1419
王阳明是从“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的知行合一论,说明“未发”与“已发”的关系。他说:“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是未尝无动静,而不可以言动静分者也。”[3]64
这样,王阳明就以体用一源、体用相即的心体用论观点破除了程朱心之体未发寂然不动,已发为情感而遂通的形而上和形而下观点。他从道德感情入手,以良知为体,知觉为用,把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言听视动和一切行为都说成是良知随遇而发之事,使人有生动活泼的感觉。同时他也取消了客观理性转化为主观精神活动的繁琐过程,以主观精神的心体用论直接说明人的感性活动,在理论思维的实际效果上起了道德感性化的作用。
(二)道德感情与践履合一的知行合一论
王阳明是从格物致知入手来破除朱熹心与理为二的客观唯心论思想的。他从21岁在北京居住父亲官邸,“格”园中竹子,领会“表里精粗”的道理开始,出入儒、释、道之学,到35岁于贵州龙场大悟格物之旨,终于否定了朱熹“求理于物”的思想,而“求理于吾心”,建立了“知行合一”思想,以后又发展为“致良知”。知行合一主要是针对朱熹知先行后的观点,强调道德与践履的合一,从广义上又包含着一切感觉、感情、认识与行为的直接合一,其宗旨是在“一念发动处克倒私欲”。因此知行合一包含心体用论的丰富内容。
王阳明把生理欲望、言听视动、学问思辨等一切行为都说成是“知行合一”。他说:“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仁民爱物,即仁民爱物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6“学、问、思、辨、笃行之功,虽其困勉至于人一己百,而扩充之极,至于尽性知天,亦不过致吾心之良知而已。”[3]46
王阳明这种内在的自我超越富于生动的感情色彩。
(三)道德判断的良知标准
王阳明说:“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不出此意,只是二字点不出,与学者言,费却不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3]1575因此,致良知是知行合一的继续和发展,它主要是以良知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做到“致吾心之良知天理于事事物物”。
王阳明说:“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便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3]111他认为,良知像规矩尺度一样能衡量无穷的方圆长短,应节目万变,随时随地指导人们意念发动向善,做到知行合一[3]50,人是天地万物的核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不知自身痛苦就无是非之心,是非之心就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的良知,无论是圣愚,还是从古到今,人们都有良知之心,因此致良知,就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视国犹家,“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求天下无不治”[3]79。王阳明实际是把程颢知痛痒“以觉识仁”和陆九渊的“千百万年前有圣人出,同此心同此理”融合为良知本体之心,提倡道德感情的自我判断。
王阳明还把“致知格物”的“格”解释为“正”:“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3]972此即是要人们依据良知判断是非的标准,诚意正心,“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是穷心与理为一者也”[3]45。这种格物致知的方法与程朱向外追求天理,达到心与理合一有所不同,是把心与理合一的良知落实到事事物物中。
王阳明还进一步把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推广到宇宙万物,认为草木瓦石、天地鬼神万物都是人的良知、灵明的产物。这种绝对精神自由的自我超越,带有庄子逍遥游的浪漫主义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