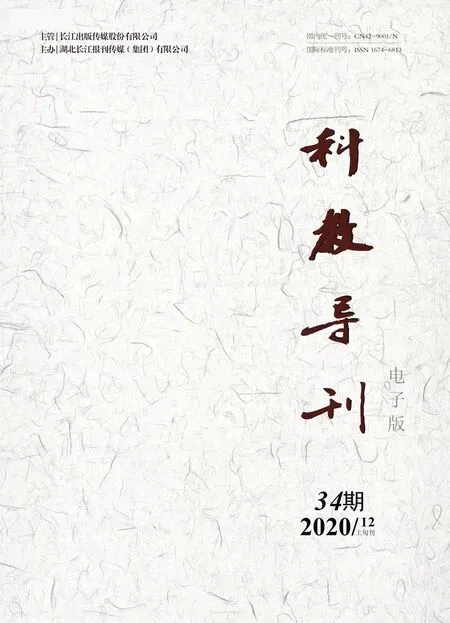弗里达自画像中的符号特征与情感表达
杨 宁
(东北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吉林·长春 130117)
弗里达是墨西哥著名的女性艺术家,其鲜明的艺术风格对艺术界、时尚界都产生深远的影响。她的绘画风格真实、自然、直接,运用强烈的视觉符号象征肉体的痛苦,从而传达情感与精神上的痛苦。弗里达敢于剖开自己的内心,坦诚地将身体内部器官暴露于画面中,细致地描绘破碎流血疼痛的状态,她开创了一种新的探讨女性身份的方式,不再是拘泥于华丽的服饰掩盖下的曼妙躯体,不再是精致妆容与温婉笑容覆盖下千篇一律的女性形象,弗里达画中的自己真实反映了每一个时期身为女性的不同的状态,优雅端坐的形象,跛足站立的形象、被伤害后血淋淋的形象,躺在病床上虚弱或丑陋的形象,弗里达的自画像是自我与自我表现不断冲突、对抗、谈判、和解之后的成果。
1 弗里达自画像符号的背景
艺术作品是画家现实生活经历的反映更是精神生活的产物,弗里达的作品三分之一是自画像,同时她也以自画像闻名于后世。与男性艺术家关注的角度不同,弗里达的作品很少关注历史、社会或政治生活,也并不像其他女性画家一样描绘田园风光或家庭生活中温馨的场面,她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可以说,弗里达的绘画作品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一种超脱于严谨造型的叙事与记录。她的画面充斥着家人、爱人、植物、动物、服饰等元素,这些符号是弗里达用来暗喻理想、生活、情感的一种表现方式。
弗里达于1907年生于墨西哥城,墨西哥独有的自然风光与热带动植物形象深深刻画在弗里达的脑中更反复出现在她的自画像中。这与印第安人的宗教信仰有关,他们认为自然与人是融为一体的,日月星辰、土地、动植物与人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画家总是被热带动植物包围,表达了她对生命的渴望与对祖国的热爱,同时墨西哥本土的动植物形象也成了她作品中的典型符号,构成了其独特的绘画语言。弗里达聪明美丽,拥有德国与墨西哥土著印第安人双重血统,她的相貌比欧洲女性多了一分野性与不羁,又比印第安女性体型更小巧而精致。她在自画像中并不刻意突出自己美貌,也不会用媚俗的笑容讨好观者,永远是冷静克制的表情,正面、五分之四侧面、四分之三侧面,用或冷漠或骄傲或睥睨或绝望的眼神与观众对视,她标志性的面部符号是连成一线的浓眉和嘴唇上的小胡子,这是她自画像中独创的形式感更是她区别于其他女性的标志性特征。1925年弗里达经历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导致全身多处骨折,丧失生育能力。婚后丈夫的不忠令她痛苦万分,她曾说过:“我的生命中经历过两次灾难,一次是车祸,另一个是迭戈”。在中后期的自画像中,在婚姻生活的不幸和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的双重折磨下,弗里达更多地用画笔书写疼痛,在符号的衬托下描绘千疮百孔的自己,抒发内心情感。
2 弗里达自画像中的符号特征
弗里达的自画像具有鲜明的符号特征,其最为显著的是女性符号、民族符号、地域性符号与宗教文化符号。在弗里达的早期(1926-1931)自画像作品中,女性符号特征突出,她喜欢画单人自画像,佩戴耳环项链等装饰物,服饰以现代简洁的裙装为主,绘制于1926年被公认为第一幅自画像的《穿天鹅绒的自画像》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品。弗里达显著的民族服饰符号特征常见于她与迭戈里维拉婚后作品中,此时的墨西哥正复兴民族主义思潮,她对传统服装的热衷体现了画家的民族性。
《两个弗里达》创作于1939年,是弗里达最著名的作品之一。这幅作品中颇具仪式感的坐姿、平稳对称的构图与各种象征性的符号元素反映了弗里达内心的矛盾性以及在她和迭戈里维拉离婚时所经历的痛苦。画面中两个弗里达以红色丝线相连,象征着两个自己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左边的弗里达身穿欧洲维多利亚式裙装,白色的衣裙上滴落的血迹尤为刺目。这个弗里达的心脏被剖开,裸露在外,预示着生命的流逝与内心的疼痛。右边的弗里达着墨西哥民族服饰,她的心脏完整,身形健硕,象征着更具生命活力的另一个自我,在这段身心备受折磨的阶段,两个弗里达反复拉扯,不断斗争和解。她的作品经常是自传式的,她说:“我总是独自一人,所以我最了解的是我自己”。
在作品《荆棘与带刺项链的自画像》中,以大面积绿色植物为背景,这种巨大的植物叶片在墨西哥随处可见,画中的猴子、豹、昆虫都是墨西哥地域性符号的典型代表。弗里达以往的自画像中佩戴的珍珠宝石项链,此时变为带刺的荆棘项链,暗示着自己的生活现状,甜蜜爱情转瞬即逝,随之代替的是背叛带来的伤害。荆棘的利刺嵌入到她的皮肤中,象征着与迭戈破碎的婚姻给她带来的锥心之痛。项链上挂着一只黑色蜂鸟,张开翅膀却毫无生机,在墨西哥文化中,蜂鸟象征着爱情,死去的蜂鸟是爱情破灭的符号。弗里达在画中穿着墨西哥瓦哈卡州传统的民族服饰,头发编成传统的民族风格样式,这是她个人形象特征中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她自画像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符号。
《宇宙之爱的拥抱》这幅自画像由众多符号元素构成,以墨西哥宗教文化衍生出的日与夜为背景,太阳和月亮一前一后,相互呼应;以女性形象出现的自然神环抱着弗里达和迭戈,周围生长着各式各样的灌木,这些灌木向下伸出细长又繁茂的根系,被日夜之神的大手紧紧包围。弗里达仍然穿着墨西哥民族长裙,表情安详肃穆,里维拉躺在弗里达的怀中,身体缩小,神情宛如婴孩,这种符号性的描绘,象征着潜意识里弗里达希望迭戈对她产生依赖,以及她对于丈夫深深的爱,这种爱从男女之爱上升到母亲与子女的爱,同时传达了另一层方面的信息,即弗里达无法怀孕生子的事实,这是她终生的遗憾更是心理上挥之不去的巨大创伤。
3 弗里达自画像中的情感因素
在女性视角,成为母亲是女性的权利,母亲与孩子的联系既是心理上的又是生理上的,想要成为母亲的冲动时刻支配着弗里达,而当无限接近一个母亲的体验时,命运给了弗里达致命一击。1932年,25岁的弗里达遭遇了人生中第一次流产,18岁时那场车祸留下的伤害,使得她的子宫无法承受一个胎儿的重量。弗里达在流产后的康复阶段,于病榻上画了这幅《亨利福特医院》。虽然以医院为题,整幅画却并没有出现我们所熟悉的医院内部结构,只有一张冰冷的黑色病床斜放在土地上,地平线消失的远方描绘了一些缩小却不容忽视的建筑,象征着美国城市与工业文明。与毫无感情的机器、工厂、大厦等现代符号相契合的生态环境注定荒芜而缺乏生机,就像她此时的身体状况,干涸而缺乏营养,难以孕育新生命。广袤的黄土地上没有一株植物,这与弗里达以往描绘的家乡墨西哥的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反映了弗里达厌倦美国的生活,思念与热爱故土的家园情结。画面中有六个不容忽视的图像符号:成型却未出生的胎儿、象征着女性生殖系统的模型、行动缓慢又湿滑的蜗牛暗喻流产后身体康复的遥遥无期,女性骨盆代表破碎的身体、迭戈送给她的紫色花朵和冰冷的医疗器械,这六个符号用象征脐带的红色丝带联系着,最终握在画面中的女性形象——弗里达自己的手中。在弗里达的身下,一滩斑驳的血迹在洁白的床单映衬下显得格外刺目。世俗和隐喻,身体和现实,通过艺术化的联系和延展,艺术家弗里达试图成为“母亲”,即使作为女性的弗里达在现实生活中不能有自己的孩子。弗里达的画作是她作为女性个体生命中与痛苦斗争的编年史,是她与丈夫爱恨纠缠的感情史,渗透着墨西哥多元包容的民族文化与宗教信仰,充满了诗意的魅力和神秘的色彩。
弗里达一生特立独行,她的自画像以鲜明的符号特征呈现强烈的自我表现意识,用暗喻的手法传达真实情感,她是最具有象征性的墨西哥文化符号之一,她的艺术影响深远,不仅影响着墨西哥本土文化艺术,也对20世纪女性主义绘画具有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