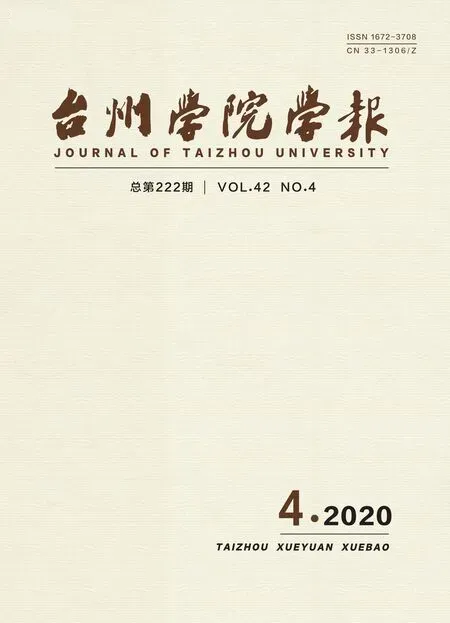隐喻中沉默的声音
——耿占春诗集《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读后记
苗 霞
(河南大学民生学院 人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在人们的惯常认知里,创作和理论分属不同的思维、想像、文字表达领域,大多数的书写者只占一端,但也偶见在两端游刃有余的摆渡者,如诗人帕斯之于《弓与琴》、诗人布罗茨基之于《少于一》、小说家残雪之于《灵魂的城堡:理解卡夫卡》,这些理论著述反映出他们对自己的文学行动有鲜明强烈的自觉意识。这时读者不得不赞叹其灵巧自如的智力转换和笔墨调转,并称之为写作上的“两栖”现象,乃至于对之充满深深的探究欲望。文学批评家、理论家耿占春诗集《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1]的最近出版也构成这样一个饶有意义的文学“两栖”(学人和诗人)现象。
在这本诗集之前,耿占春一直是以诗歌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的身份蜚声文坛的。其诗学理论专著《隐喻》(1993年)被徐敬亚断言,将会在中国引起一场语言、诗歌的革命。随后一本又一本的理论著作(共计十余本)逐步加重加深他的理论家、批评家身份。当前这本诗集的出版,耿占春又多了一重身份:诗人。该诗集的篇章写于1988—2018年,历跨30年的时间距离,从青年写到如今的晚年。从表面看来,诗集似乎并没有按照时间来编排,而是按“时间的土壤”“西域诗篇”“诗”“世界荒诞如诗”四个主题编排,无疑昭示出诗人的心理结构和精神图式。但据诗人自己讲,第一辑创作于1988—1993年;第二、三辑创作于2004—2007年;第四辑创作于晚近的2018年。所以这种主题编排也暗暗吻合着创作年代编排。
耿占春从其理论批评伊始,诗歌创作就伴随进行,甚至于他最初的创作意图不是成为一位理论家,而是一位诗人。但事实是,在这本诗集前,他一直是以学殖深厚的学者身份蜚声文坛的。我在读这本诗集的时候,一个饶有趣味的探询是:个体同时操作着理论话语和诗歌话语,其不同的语体特征是炸裂洞开还是相互融合?相较于他复杂深奥的理论体系,这些诗篇又想表达出什么样的观念?有些诗篇会不会是他理论观念的一次诗意转化?部分诗篇会不会是他思想情感的新披沥?对一个惯于操持理论文字的人来说,有什么是他不能用理性话语表述而非用诗性话语表达不可的?通过厘清这些问题,最终企图剖析出的是:写诗,作为一种创作行为,对于耿占春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对诗的本体性界定是什么?基于上述疑问,本文把探询的目光投射到诗集的四个主题上,四主题对上述问题的解答分别如何?
需要说明的是,四主题之间在编排上是分列的平行线,但在解读中,它们是缠绕的线团,内部有许多诗篇是相互支撑、互证意义的存在着。
一
第一辑《时间的土壤》。对诗人来说,时间的土壤是无限的厚土,不仅生产出一部广阔无比的我们的民族史,还有累累岩石蔓蔓葛藤的个人生命史。如一涓细流汇入宽阔的江海湖泊,个人生命史最终又融汇到民族史、文化史乃至宇宙史之中,是以盘古“垂死化生”的方式融汇的——
《时间的土壤》(第四章)
时间的土壤生长出什么?
曾经此时和现在。经过你流动的泪
曾经飘在一朵云上,悬在一叶草尖
在一个夏日存在了短暂的瞬间。你的泪
曾经是一个女子从清晨的河里提水回家
在更古老的世系里它曾经是另一个人
无人知晓的忧伤。现在飘落你发丝的
冷雨和尘埃,曾经是在情欲中战栗的骨肉
它为一个人而痛苦地燃烧
然后以灰烬告终
……
一切都在无限返回的万物之流
唯有你不再返回。永恒的生命
属于天地之间的水、火、气和土的运动
唯有死才是你自己的。……
那丛生的草就是我伸向风的舌尖
那些花仍在携带着我而开放
请你以礼物的形式把我收回你的怀抱[1]6
借助“化生”,人,从一种生命形态转向另一种生命形态,往而不返,去而不复的生命超越自然的生命终结而成为一种想象的自信与成就感,诗人借用古老的民间神话思维方式给一道无奈的生命之流营造着“永生”愿望的满足。这种“神话式的时间”或“神话学的时间”是一种最为古老的时间意识。它把线性时间置入圆形时间之中,即把个体生命的不可逆转的特性融入和消解到宇宙的永恒轮回之中。
一片砖瓦能历经几个朝代,被刈割的小草会重新长出头颅,我们人,为什么不能?对于生命的不可逆性和有限性,耿占春认为那是无声的宇宙强加于人的荒诞生存,“天地不仁,以万物为虚无”[1]143(《夏至清晨》)。他曾经用理论话语做过“天问”般的沉痛呼告:如果我们拒绝接受,又能挺身反抗谁?把无限的宇宙拉向人类的道德法庭作审判,这是想都不能想的荒谬的事情。但是我们这有血有肉的、有感情、有思想、有意志的存在者,难道必须像一只五月的蝇子,像垃圾上的虫豸一样死掉吗?并从此销声匿迹就像压根儿没有存在过一样,这公平吗?如果荒诞的境遇是不合理的,那么,谁来替生命作辩护?如果那判决我们的法官并不存在,那么又有谁来倾听我们的辩护?想来那种荒诞性的存在伤痛只能靠诗歌想象性地治愈了。
神话思维中的“死亡”不仅没有形骸融散,反而造就生命的丰富多彩、万千变幻。
时间还须在回忆中显现,
谁反对死亡,谁就是反对
时间和由时间产生的万千变幻。……
使物质有了意识,
因此
时间不是你的敌人,而是盟友
而永恒性,即没有时间
才是死亡的象征[1]11
诗人首先关注的是宇宙史、人类史、民族史宏大的时间,但其落脚点却在个人生命史的一己时间上。但个人如何才能构成一种命运、一种个体生命史?
在诗人看来,首先立足于现在,时间总是“现在”的“在场”,存在通过时间而被规定为在场状态。存在是作为一种“当下存在”而存在的。“当下存在”的时间是现在时的,空间是当下境遇的,“空间的现场性”和“时间的现场性”兼备。唯有立足于当下时间与在场诗学,个人才能活成自己。恰如诗人所言——
但一切都稍纵即逝。这是美的
本质。无视瞬间真实的人在时间中
将一无所获。但你将生活在你记住的
事物中,生存在你眷恋的时刻。
——《歌》(二)[1]24
生命是闪耀的此刻,不是过程,这样的现在就是一种“此在”,存在于世界之中,构成生命史组织原则的是在个性及个性的各个发展阶段中找寻生命的真实本质。
个人构成命运的第二个原因在于:时代的风雨必须落在个人语言的洞中,诗人所处的这个时代活在他的诗篇中。如《需要的,恰如所有》:
需要有痛苦喂养我的语言,需要有/愤怒喂养我的语言,需要有/死亡压迫平庸的密谋贪婪的剥夺恶棍的狂欢/民脂民膏敲骨吸髓喂养我的语言,需要/圣人慈悲绝望和哭泣衷情背叛喂养我的话语,需要/软弱崩溃沉默无言需要话语反面的一切喂养思想的灵兽,需要/廉价真理的灰烬喂养诗歌的谎言,轻盈的机智愚钝的力量左手的打击/意外的蹄子,以及无情的羞辱与反抗的徒劳信誓旦旦的冷漠/从灰烬到火焰冲上云霄,需要/泥坑里的自尊颠倒的责罚倒置过来的乌托邦需要/地狱高高在上糟糕的幻象岔道上错误方向的一望无际/喂养正确而强劲的语言。/……/因此所发生的一切/所给予的一切忍受的一切粗糙愚蠢傲慢卑劣都能够喂养/这只语言之鹰。/一个喂养者,我?一个饲鹰者/……[1]147
语言饕餮着世上的一切,爱这大地,爱一切腐朽光荣的东西,因为它以这些东西为养料,并把它们转变成炫目的光辉。
在个人生命史之中,诗人“对节日庆典活动的时间经验”有独特体认,在节日中,人们不再计算时间,不再想去支配时间,而是全身心投入其中,让生命去捕捉每一时刻、每一瞬间。节庆时间也即伽达默尔所谓的“属己的时间”。诗人欢快地歌颂着时间的节点——除夕
时间没有了
这里有你真正的欢乐:时间消失了
没有时间的时间,就只有此时和现在
那一直未曾发现的国土就显露出来
那未曾享有的欢乐就是
时间的完整形态:在时间之外
时间永远是现在
现在是处女的时间,童贞的时间
而等待,静处,使时间无比贞洁和空洞
新的时间将被诞生
节日这一天似乎是时间里头多出来的一天
这多出的一天出自上天的恩典
让凡人们也来到时间之外,过神祇的日子
时间停下来舞蹈,在众神面前,……[1]4
诗人的时间意识一头连着宇宙意识,另一头连着生命意识,但都是对时间哲学的诗性探索。生命意识觉醒的第一步是时间意识的产生,所以这部分早期诗作是诗人生命意识的发轫。只是如果用诗人自己的话“每一个判断都需要细节,需要叙事经验的支持”[2]116来判断,似乎这里个人的生命感受性还不太丰富,哲学概念还没有完全转化为充分的文学感觉化。相较而言,我更喜欢后来的《当我老了》《迟疑地》等。
第二辑是《西域诗篇》。据诗人讲,这些诗篇大多作于2004年左右。在那段时间里,他去了新疆、青海等地10余次,最长的一次待了一个多月。显然,西域对于他是一种特殊的情感向往。这源于诗人的童年生活经历。1957年夏,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展开。第二年,诗人的家庭也受到这一历史的冲击,举家从河南商丘迁移至青海一个叫莫河的地方上的骆驼厂上班。1963年举家又回迁河南商丘。去的时候诗人才一岁多,回来的时候五六岁,初谙人事。《茶卡记忆》《莫河》就是对这一原初生命的记忆,年近半百,他再次回到了过去,其中包含着无奈的思念以及读解和阐释的分析性倾向。诗人最早的活动足迹踩在莫河周围的地貌之中,戈壁滩、游牧生活、起伏的山脊、倾斜的山谷、洁白的雪山、大片大片的豌豆花……都是他生命发源的同伴,这一切构成他童年的生存经验,也构成个体最初的记忆。后来的世界对个体只是附加的虚幻。故乡和童年都是生命的开端,也是记忆的开端。西域对于他,首要的意义即在于回家,对精神家园的重建。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诗人回到西域,不仅仅是从遥远异乡的复归,回到自己生命的发源地、滋养所,更是回到世界的原初之地。这里的原初是历史的原初。《莎车:苏菲的城》《帕米尔》《其尼瓦格》《龟兹古渡》《密封的喀什噶尔》等诗篇一再为古老的西域史招魂,诗人甚至“更像向亡灵问卦的巫师,竖起耳朵想听听死者的声音”——“如果能够再来高昌/一定是在明月之夜,我将跻身/那群高贵的亡灵,从死亡中归来”(《高昌》)。对照历史,他想探究当代文明条件下另一种“族群”的存在方式和文化状态并对之进行深刻解读,在少数民族的风俗人情、宗教信仰,地理上的边缘位置和在文化上的陌异性中悉心地寻找文化的深度与思想的启示。
原初,更是自然的原初,诗人以一个自然的个体生命对自然原初的拥抱。当他游目骋怀或凝睇谛听于塞外漠北、古城残堞、高原山地、崇山峡谷的时候,这些既未受到人文污染又未受到现代污染的原始生态,总会感悟到大自然最原始的力量,人与自然的同体性,以一种敬畏之心去摹写其本身所具有的神性,来表达自己的虔诚和热爱。
《在阿勒泰》
阿勒泰群山怀抱,我在
云层移动着的最明亮的边际
一些次要的想法,风吹着
少量的流云漫过白桦
蓝色的山顶。一只鹰滑向
哈巴村万物终结时的本质
在早临的秋风中呈现
一种单纯而透明的真理
鲁瓦人在。阿勒泰
在一束夕照中闪烁
言不及义。所有的事物
仅靠其表象惠及梦想。在阿勒泰
不变的事物,为变化的世界
提供意义的起源
额尔齐斯河正穿越群山
而我,已接近于不在[1]86
在阿勒泰,万物终结时呈现一种单纯而透明的真理,生和死都是“意义发生的原初事件或存在之真的事件”[3]。“所有的事物/仅靠其表象惠及梦想。”“不变的事物,为变化的世界/提供意义的起源”,似乎是回复到了隐喻思维的时代,在这个世界的原初之地,“在之澄明”,“自然先行于一切现实事物,先行于一切作用,也先行于诸神。”[4]故,主体,“已接近于不在”。尽管诗篇无一处涉及“神”的字眼,但阿勒泰已处处呈现“神迹”,“神圣乃是自然之本质”,使人领承一种心灵受洗的恩宠。
世界的原初还具有神圣性的无限增值意义——
《重访塔什库尔干(二)》
如果我在塔县不属于日常之物
那就纯属一个偶遇,一场很小的意外
塔什库尔干的总体秩序预设了
偶然闯入的事物。没有偶然
塔什库尔干就不完整。它的总体性
由多余之物加以扩充,由偶遇完成
我不需要变成石头城上的一块石子
属于帕米尔高原。我属于它
非稳定性的一面。现在我试图
让这样的想法,给自己
一点安慰,摆脱走在帕米尔大街
如此多余的感受。我要跻身于
它的现实性之中。我观望。如今
是记忆,是无端的塔什库尔干[1]90
塔什库尔干是一个未完成的秩序,非确定性的可能性的开放事物,呈现出开放的语义场,开放在未来和宇宙之间,留待“我”一个个“天外飞客”似的偶然性来填补。“是你的仁慈,接纳了我的临时存在/且让我跻身于你明净的现实”(《重访塔什库尔干(一)》)。“我”是观察者,也是介入者,于是有了“我”对待地方事物的态度和方式,自我的观察带有某种个体特征的规约性,“我”以一定的方式和态度介入其中,使人与物、自然构成共同的有机体,从而激发出新的意义。其实在上帝眼里,这就是一种永恒,一种无时限,在未完成的事件中持续完成,永远保守着意义的生成力量。
第三辑是《诗》。该部分既然命名为“诗”,那么是不是更容易寻觅出诗人认知观念中的“诗”是什么?从内容上看,这部分更切己、细腻,应对着个人化的、境遇式的、偶然性的情感、经验与记忆。当诗人的朋友因不同的原因逝去时,诗人痛书悼诗,《重返海南》《对你说,余虹》《哀歌》《往世书》抒发了他在不同程度和不同场合与同样一种悲伤和哀悼之情的遭遇。当然,在这部分中,我们更能看到诗人心灵生活的细致和感受力的敏锐。外出归来,地板轻微的灰尘、旅行袋发霉的斑点、晾衣架上孤单的衬衣,在诗人敏感的心灵看来,仿若遗物冷冰冰的无情存在,构成一幕悲剧的现场。午后醒来的寂静……每一瞬间情态总能引发诗人不绝如缕的生命之思、存在之感。
这种具有感性特征的个体生命意识,在价值确认上面追问存在的秘密,体现出形而上的智慧。但同时它的发生带有个性存在的性质,理性思索中有细节经验的支撑,显得饱满、真诚。《迟疑地》《当一个人老了》是诗与思的激情碰撞的代表作,使读者感受到生命的微妙、声色和光泽。如《迟疑地》:
无疑常常我也会忘记:一个人只存在于瞬息/不知道哪一次呼吸诞生了中年//从自身的前一时刻脱离,无疑也是/一种死,可没人为之悲叹//应该增加隐喻使意识转向他物:秋天/豆荚的爆满,使豆粒在中午跌入干燥的土地//最终消失的是一个片刻的我。而他的一生/在活着时早已失去。去迟疑地/存在。迟疑地成为自我//一只黑色的鸟在黄昏低飞,迟疑地/有什么也在我的“灵魂”里/离开,迟疑地//不相信自我,不相信它是真的/对故事的结尾报以/一次呼吸之间的迟疑。”[1]102
这首诗让我想起蒙田的主体哲学。蒙田认为,人的主体性是不稳定的,人的行为总是受制于具体的情形、偶然的事件和突发的念头:“偶然之风将我们卷走。”[2]24这个不稳定的我不仅受制于自己的情绪和心境,也受制于向他扑面而来的外在之物。因为人不是一个整体,而是由许多片段和瞬间组成,这些片段和瞬间都是在同他的对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性:“我们都由片段组成,属于一个如此多变和不确定的组织结构,其中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片段都起作用。”[5]也许归结起来就是恩斯特·布洛赫的那句名言——“我在。但我没有我。所以我们生成着。”[6]我永远是我所不是的,而不是我所是的。
是的,诗思不妨作如是解,但该诗的魅力远不止此,它用诗的形式、话语给这些思之概念、断语以生命,能够用呼吸托起它们,给它们注入一种活力,致使种种抽象的内容获得栖身的躯壳。这首诗表述对人生的迟疑态度,这种迟疑态度难道不是从诗歌迟疑式的分行、断句中体现出来的吗?在读诗的时候,它会从读者口中发出迟疑的气息和颤音。
诗歌是命运之书,是对生活经验的提纯和抒情。“诗歌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事件,一种不断发生和持续发生的事件。借助感知和想象,借助语言和表现,通过表现世界,使生活的意义得以发生。”[2]25-26这也只是说“诗的意义何在”,只是诗歌在自我意识中的发生学根源,但还不是说“诗是什么”。“诗是什么”只能从诗歌的语言学根源上探求,在诗人看来,诗是语言的隐喻(比喻)性复活——
《论诗》
在小小的快乐之后
你甚感失望:写诗寻找的既非真理
也不是思想,而是意外的比喻
为什么一个事物必须不是它自己
而是别的东西,才让人愉悦
就像在恰当的比喻之后
才突然变得正确?人间的事务
如果与诗有关,是不是也要
穿过比喻而不是逻辑
才能令人心诚悦服?而如果
与诗无关,即使找到了解决方案
也无快乐可言?如此
看来,真理的信徒早就犯下了
一个致命的错误,虽然
他们谨记先知的话
却只把它当作武器一样的
真理,而不是
一个赐福的比喻[1]180
《碎陶片》
诗不再是发现真理的方法
它发现一颗隐喻的种子
让语言呼吸[1]131
这两首诗,都在传递着同一个诗之判断:诗是语言的隐喻(比喻)性复活。此处有两点须注意:一是他把诗落在了语言的基座上。语言是诗歌的基本伦理之一。诗歌是对经验的表达,但对复杂经验的提炼最后必然表现为语言上的复杂、语言上的张力,世界必须被包含在语言本身的展示中。二是诗语是隐喻(比喻)之言。说到隐喻,耿占春早在青春时期的著述《隐喻》一书就明确指出:建立在想象性心理机能之上的隐喻是语言的基本构成方式,最初的词的使用,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隐喻性的。但不幸的是,目前语言的隐喻性正在衰亡。“隐喻的衰亡,无可挽回的是语言这个文化母体的衰亡,是人类生存中原始文化综合体的解体。是天地人神四重世界的分裂,是人与自然的最无情的离异。隐喻的衰微,是人与宇宙的同一性和统一体的衰微,是神话精神的衰微。”[7]重启隐喻之兴的重责就落在了诗的肩头。当然,诗歌中的隐喻指的是远距、异质、产生智力性关系以表现真理的有魔力的隐喻,旨在发现事物间的隐秘联系。
第四辑是《世界荒诞如诗》。这部分诗作写于晚近一两年,距离上一集中阶段写诗的时间已有十年之隔,中断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但重新掂起诗笔的原因是“野夫怒见不平事,磨损胸中万古刀”,世界和人生的不义与荒诞所逼驱使:
《世界荒诞如诗》
许多年后,我又开始写诗
在无话可说的时候,在道路
像逻辑一样终结的时候
在可说的道理变成废话的时候
开始写诗,在废话变成
易燃易爆品的时候,在开始动手
开始动家法的时候,在沉默
在夜晚噩梦惊醒的时候
活下去不需寻找真理而诗歌
寻找的是隐喻。即使键盘上
跳出来的词语是阴郁
淫欲,隐语,或连绵阴雨
也不会错到哪儿去,因为写诗
不需要引语,也无需逻辑
在辩证法的学徒操练多年之后
强词夺理如世界,就是一首诗[1]163
熟悉耿占春理论专著的人都知道,其文学社会学理念建立在现代民主理念基础之上,他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关切成为他这部分诗歌的基调。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并不切入现实中的各种生存实况、生活现象,他聚焦的是现实中的理念、思想、意识形态的语言导向。那是因为在诗人看来:历史上很多时期,出自统治阶级的单一世界观压倒一切,政党掌握着彻底的“文化霸权”(葛兰西语)。所以诗人悲叹到:“如今所有真理到了我们手里/都已变成腐败之物”(《清晨的德性》),而且贻害无穷:
被毒化的意识比一切毒物更致命
每件事的事理都消失在
势利之中,让人心慢慢死去
残余的爱会在无泪时耗尽
而灵魂多半湮灭在肉身枯槁之前
每个人都将死于一场慢性谋杀
也将得到死者完美的配合
对此不会有人怀着下地狱的恐惧
死就像是一场怯懦的越狱
——《论死亡》[1]202
基于此认知,诗篇《论恶》《精神分析引论》《论消极自由》《论神秘》《论词与无》都直指这种思想上的蒙昧愚妄且流毒无穷。如《论词与无》——
在雪线之上,没有生物的地方
空气纯净,然而呼吸困难
唯有下降是获得拯救的途径
有些词语早已不再呼吸,有些知识
着实让人一无所知,犹如出生之际
就在意识中安装了没有痛感的假肢[1]201
诗人试图给众多的权力无远弗届的“镇治符号”和“假大空”的“宏大叙事”祛魅和解构,暴露其虚无作伪的真面目。由此一来,生存的困境也就转换为语言的困境,对现实的批判就延伸挺进到词语深处的批判,从而“再次避免了现实的提审”——
在虚拟的纸页上,我的一生
渐渐消失在错行的
诗句里,多么
遥远。说与沉默
同时留下我的
逃亡和返回的路,并且
再次避免了现实的提审
——《一个故事》[1]152
二
是的,在经过对诗歌文本的详细解读后,是该回答最初的提问了。诗歌创作和理论相比,主体可以更私人化,无法搁置在理论创作中的私人情感、经验和记忆可以放在诗中处理。因为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约性,而诗的语言则要尽可能地减弱公共语言的“通约性”。在这种不可通约性中,其诗歌话语直接指向的是被压抑着的、沉默着的、痛苦的、难言的甚至无言的内心皱褶里的郁积。
《今夜》
谁敢冒险有一个信仰?
在黑暗中,那重复不已、呼唤不已的声音,
渐渐沉入一本书的肺腑肝肠。谁,
是向人类说话的人,人类
在哪里?一只臂弯和一个世界
已脱离风中的芥菜和躯体,而独自
被你想起。伸出的手握不住风。
它们是否已生出了双翼,在那稀薄的
空气中?而这时候雨声淅沥,
谁敢向整个黑夜发出呼唤,而不致发疯?
寂静会盖过那重复不已、呼唤不已的
声音。谁,
敢让耳朵躲开谎言而去倾听,滴滴
沥沥在心的寂静?想吧,
想吧,只是不要怀有希望。
想吧,心啊,现在世界就靠它了。[1]37
在这个意义上,《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之于耿占春,就如《野草》之于鲁迅。鲁迅说,《野草》是为自己写作的,发表一些真正属于自己的极端黑暗、冷酷的内心体验,吐露灵魂的“真”与“深”。《我发现自己竟这样脆弱》同样凝视并剖析个体生命中最深层次的哀与乐、希望与绝望、疼痛与抚摸。
对诗人来说,诗歌更重要的还是一种隐语,真事隐去假语村言,是他精神游荡中黑暗的一部分,某种被压抑的欲望的象征。诗人在黑夜中写作,又出卖了黑暗,因为他从沉默中发出了声音。
一切美好之物都已染上时代的毒素:
音乐、爱恋、风景:已成为我们的禁果。
厄运会过去的,可生命消逝得。
更快。如果不能用内心的声音说话,
那就在内心的声音中沉默。
——《音乐与风景的毒素》[1]34
一首诗是从沉默开始说出的话,从消失的雪
这里的每一个字都想抓住那已消失的
此刻我写下的,仅仅是记忆阴面的
一片积雪,在久远的,在生活的一切灰烬之上
——《窗外的雪》[1]104
理论话语与诗歌话语的语体间有没有裂痕间隙?如果有,诗人如何缝合的?答案也许就在法国罗兰·巴尔特的一段话:“作家”不应以他所书写的文类为特征,而只应以某种“言语的自觉性”为特征,他体验到语言的深度,而不只是它的工具性或美感。[8]5是的,早在多年前耿占春就寻找这种“言语的自觉性”——将感官的直接性与思想的抽象能力融为一体的语言。从学术本位的观点来看,文学批评最终还是要体现为理论性的学术话语,分析、归纳、检验、证伪、辩驳、争论,诸如此类的论述策略是耿占春缜密的学术话语必不可少的。但他还在追求着:“我想写下一些使风或空气流通的句子,使耳朵或隐秘的皮肤在其中苏醒,呼吸。我渴望我写下的文字里充溢着宜于人呼吸的空气,使一种风在话语文字间吹拂,仿佛文词是一片丛林,或是湖波与水流,让风获得可见可闻可触的形式,轻轻地流动,在文字的空间里,甚至连文字也具有漂浮的特性,如风中的树,它的根坚实,深扎进血肉的泥土,屹立,而树冠早已与长风连为一体。”[8]127直至晚近他还在说:“文字的生命力不是来自纯意识活动,而是源于灌注身体的气的流动,否则写下的文字既不能流动也无法让人从中呼吸。”[2]130这些话转述为他的诗句就是这样的——
《深呼吸》
让书写的句子也——深呼吸
阅读转换为呼——吸——
享受词语的甘美
让深呼吸——进入语言
轻拂话语的边缘
和呼——吸——之间的沉默[1]215
耿占春的理论批评著作中既有以概念、范畴为形态的理性认知,又存在着灵感、顿悟等种种的审美形态。这种语体下的无论批评文字或是理论文字无不写得充满感性的描述,迸涌着激情,甚至是诗性的想象力。“言语的自觉性”缝合了其诗歌话语和理论话语的间隙,又最终铸成了他的“晚期风格”——
《论晚期风格》
然而,晚期风格
只存在于一个人最终锻造的话语中
这就是他的全部力量,在那里
他转化的身份被允许通过,如同一种音乐[1]178
耿占春认为,诗是语言的隐喻(比喻)性复活,诗之思“重建语言的隐喻世界”。那么,写诗,对于他来说,就是用隐喻发出沉默中的声音。这才是诗歌对于他最本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