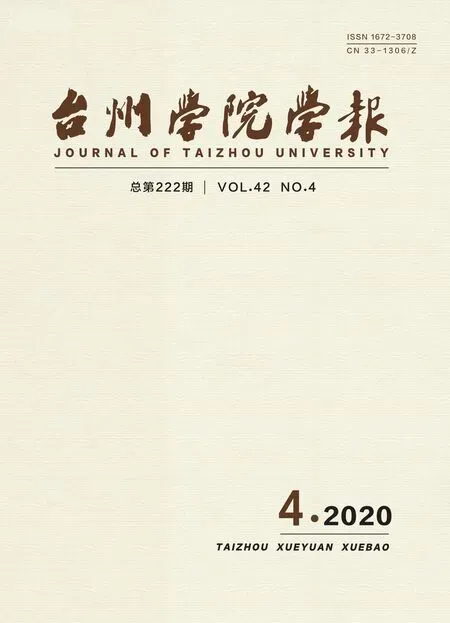风景就在身边
——简论江一郎诗的高识别度及其有机构成
洪 迪
(台州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江一郎,原名江健,1962年12月26日生于浙江温岭。中国作协会员,台州市作协副主席。1981年开始发表诗作,在《人民文学》《诗刊》《星星》《十月》《天涯》《青年文学》等发表大量诗歌,入选《中国新诗年鉴》《年度中国最佳诗歌》《中国诗歌精选》《中国诗选》《中国文学精品》等。著有诗集《风中的灯笼》、三人合集《白银书》中的《江一郎卷:加里·斯奈德摸到的水》《山地书》等。2000年参加《诗刊》社第16届青春诗会。2003年参加《人民文学》社第二届中国青年作家批评家论坛活动。2003年荣获《诗刊》社首届华文青年诗人奖首奖。2004年获“德意杯”《人民文学》首届青春中国诗歌大奖赛一等奖。2009年获“新世纪十佳青年诗人”称号。2015年获首届《人民文学》年度诗歌奖。自新世纪开门红以来,频频获奖,享誉日盛,渐趋日丽中天,痛惜天不假年。作为台州同乡,我心中郁着一泓情愫,“如捏着一团火”(鲁迅语)。在此必须讨论与申述:江一郎何以及如何是朦胧诗以来也是百年中国新诗的杰出诗人。
江一郎这棵天生地长的诗的野高橙,真幸运,大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和合。他学诗写诗的40年,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新时期相重合。在朦胧诗、后朦胧诗或曰先锋诗探索诗现代后现代诗歌喧哗与骚动及跨世纪新变中,他试水、畅游而一再跳跃龙门。没有前辈诗人的因袭重负。春风得意于好天时。台州温岭是新世纪第一缕阳光照临的地方。台州面朝溟溟东海,背靠四万八千丈的天台,与秀绝天下的雁荡南北对峙,怀抱大片温黄平原,历来为人所向往的神仙居所,鱼米花果之乡,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汉唐以来文化底蕴深厚,民风淳厚而灵秀。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到“台州式的硬气”和“颇有点迂”。这“迂”实则是有个性,自作主张,不怕头撞南墙;是“硬气”的必然,创造性的摇篮。这在台州人自被灭十族的方孝孺、龙华就义的柔石、“竹刀”似地挺身侵略者之前的陆蠡以来,早已成为民性的DNA。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右温州左宁波的台州,早已勇立改革开放大潮的壁立潮头。台州已从旧日的山海“关”迅变为山海“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的现代性先锋性已成日常生活的弥漫大气。于是,王自亮、伤水、杨邪、王彪、丁竹一批青葱新诗人蓬勃茁壮萌长;江健自是其间的佼佼者,自然获福的宁馨儿。
真诗人总会有零和的两种生活:日常生活与诗的生活。江一郎简直是为诗而生。他的日常生活道路从不自觉到自觉,尽做减法。高中毕业进了当地一所工厂。却早早从工厂出来,在街头摆香烟摊。待诗名足以支撑,便自行办起作文补习班来,“在家带一些学生,教他们如何写记叙文,每周工作二天,收取一定的酬金,像古代的私塾先生,难奔小康,但尚能温饱。”[1]154他终于自力更生成了在野的半专业诗人,将惜短的一生的聪明才智、生命能量倾铸于学诗写诗。他的平凡得出奇的生活道路便夯实了成为中国新诗杰出诗人的基础。
一个诗人之所以杰出,标志于其诗作的高识别度与极富于诗美含量,归根于其深解诗美本体与现代诗艺的诗观,与大气、纯美、特创的诗风。江一郎诗何以有如此高识别度,究其有机构成主要有三:
深度草根性。草根、民间、接地气是当今新诗界高频使用的热词,三者含义相近,但在不同的使用者的褒贬色彩各异。江一郎诗歌所特具的是一种深度草根性。他本身便一生生活在草根的底层。他在一篇访谈《一个独旅者的精神浪游》中说:“在体制外生存的诗人算是坚守民间立场吗?若是,那我就是民间中的民间,因为我最纯粹,纯粹到彻底沦为失业者。”[1]151“近些年,我是写下为数不少的与乡村有关的诗篇,但我却从未在乡村真实地生活过,我之所以愿写这类题材,可能与我的性格有关。”“尽管我一直居住在城乡结合部,但我努力拒绝城市的那份紧张和冷漠的侵入,我更向往的是农耕时代那种朴素的人文情怀以及清淡的田园风光。体现在写作上,我凭借自己的想象和阅读的经验。我可以没有乡村生活,就像叶延滨老师所言,‘一个伪农民’,但我从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出发,完全可以做得比那些终生都在田野劳作的诗人更出色。不知你是否注意到,我的那些所谓‘乡土诗’,其实与真实的乡村是拉开距离的。虽然谈不上超现实,但绝对存在明显的差异性。”[1]145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江一郎所特有的深度草根性的要妙所在。江一郎诗的深度草根性,当然同他“民间中的民间”的生活状态有关,他一生扎身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贫苦市民之中。居住在城乡结合部,摆烟摊于熙熙攘攘县级市的街头,沉浸而超越其中的却是一位真诗人。他有三只耳朵与长在额头的第三只眼睛,更有一颗异样搏动的诗人之心。诗人便是凌空的异人。江一郎将处于草根民间的农民、工人、贫苦市民的平常心熔铸在一起了,更由此深入,直捣人性深底之本真。诗人修炼达到如此境界,便没有诗的题材限制了。他喜欢多写“乡土诗”,他是透过“从一个乡下人的立场出发”,直抵人类的共同本性,直抵“人类情感的本质”[2]。而阅读是诗人更重要更深层的生活。阅读是诗人生活与沉思的望远镜、显微镜和高倍放大器。江一郎诗的深度草根性,正是借着几乎无所不览的勤奋阅读,高倍放大他的现实草根生活而透入人性本体的骨髓,从而使他获得将人类情感的本质清晰地呈现出来的形式。
还是一起来读江一郎的诗吧。写于早年的《灯》:
是你照亮我 还是我认识你内心/从现在开始/黑暗的水流去,我光明//天空看不到一颗星,你就是/大地看不到一朵花,你就是/你击穿岩石,和暗夜的女巫/你歌唱,像火中的鸟//没有一种力量可以将你扼杀/闪着寒光的刀子,斩不断光明的手指/我是爱你的呀,你的爱情/让我坚持下去,等待天明//最艰难的日子,一盏灯恰似闪电/划破沉沉的帷幕/赶路的人,风雪夜亮着的灯/就是一棵树/光芒的叶子,哗哗响[3]
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这个“赶路的人”,渴望“风雪夜亮着的灯”,“黑暗的水流去,我光明”。“灯”是我的渴望者,也是我渴望成为的“我”。这是一颗深度草根诗人光明的心。而将深度草根心态更坦白直陈的是《在低处,甚至更低……》:
在低处,甚至更低,我见到草/被日光照耀,或陷入什么也照不到的地方/一簇簇那么卑贱,而又/沉默地绿着//在低处,甚至更低,我见到泥巴/这些丑陋的阴冷的/被踩在脚底,永远被踩着,更糟的/与垃圾埋在一起//在低处,甚至更低,我见蚂蚁/如此弱小,如此不起眼/在大地最低处,活着无人理睬/死去,有谁痛惜//在低处,甚至更低,多少庸常的事物/被我看见,又常常被我漠然地/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4]119
“在低处,甚至更低”的“我”,见到草,泥巴,蚂蚁,等等“多少庸常的事物”,有同病的痛惜,也有因“常常被我漠然的/遗忘在生活的角落里”的歉疚,简直与长吟《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者诗心相近。而《运草车》则为所谓“乡土诗”的显例:
村前的大路上,一辆运草车过来了
那是谁家马车
远远地,只能见到一个高高草垛
踩着马蹄声
自己在走
路上空旷,吹过田野的风扬起沙粒
扬起青灰的草屑
和暗黄的草梗
风中野薄荷的呼吸
随木轮子一路
吱扭,吱扭
像带响的火柴,一辆运草车
运载着山里的秋色
闪进村口
冷月升起的时候
空空的场院里,草垛在走,月光下
如同不肯安睡的运草车[5]29—30
高超的现代诗艺凸显出来了。一组影视的长镜头活现出来了。眼耳鼻舌身的全感与通感交错并陈。马蹄声、木轮子吱扭声、田野扬沙的风声、冷月清冷的静音,奏起乡村秋收的交响乐。草屑的青灰、草梗的暗黄、高高草垛的丰收颜色、马与车的行动的杂色、收获来的“山里的秋色”,黄昏的夕照、秋夜月光的亮白,五彩斑斓并呈。种种音与色中暗暗透着“野薄荷的呼吸”,新干稻草的香气、“吹过田野的风扬起沙粒”微微呛鼻的干涩,月白下高高草垛与山里秋色所带来的丰收幸福的气息。好一幅色香味形中深蕴农人深情的动画,缓缓走动的会唱歌的秋收时节乡村绝妙风景风俗画。更妙的是全篇诗美时空建构独运的匠心。第一节2行,“谁家马车”一问,显露了说话人当是乡邻的目击者,却隐去了运草车的驾驭者。这位驭车的农人,直到进场院的最后,仍是胜过神龙,首尾皆不见。第二节3行,呈现目前的美妙,是“一个高高草垛/踩着马蹄声/自己在走”。随后3节是在路上,进村口,到场院。而“不肯安睡的”是草垛、月光、运草车。这位安享丰收的勤劳农人依然草深不知处。此诗明白如动画,却韵味隽永,俨然杰作。
圆融先锋性。在一次访谈中,江一郎说了自己关于先锋性的灼见:“先锋意味着前卫”。“这个词是处于时间状态之中的。”“新诗从草创时代开始就有其自身的先锋性,永远置身于不断的探索,也可以说,一直走在大众审美前面,这个词是孤独的,甚至是悲壮的。”“问题是诗歌中的先锋性到底表现在哪里?至少有一点我是坚信的,先锋不是体现在语言上或通过外在形式来呈现的,真正的先锋应该是精神上的,并非一个人写的东西别人看不懂就是先锋。”[1]150诗的先锋性意味着前卫、探索、实验、创新。本质上是一种高强度大跨度的诗美创造。与诗史上的各种流派、主义联系起来,多少是与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意象主义、抽象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深度意象主义等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现当代诗歌流派纠缠在一起。然而,时下有人断言“先锋写作的终结”。认为:“先锋写作基本上在世纪之交已经终结了,因为先锋写作是人文主义的一种写作,它是以思想上、精神上的叛逆性,艺术上的前卫性、实验性、探索性为标志的。”而且,“是时代的转换使先锋写作失去了存在的环境与条件,只是为了表明它形式上的依然存续,而衍变为了极端写作。”[6]这是对于新诗先锋性的误解与误导。百年新诗所以应运而生,与时俱进,其精神上的灵魂正是先锋性,正是诗美创造上的大含量与高识别度。宣告新诗“先锋写作的终结”,等于判处新诗死刑。江一郎诗的先锋性正在于它的大诗美含量与高识别度。江一郎诗的高识别度,是在于他既不排斥又不独钟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主义流派,他是现代诗艺鸡尾酒的高超调酒师。他善于临场以不同配比调和多种现成的,更加上几滴独家秘造的善酿。所以江一郎的酒杯杯是亲手自调的鸡尾酒,杯杯不同,杯杯烙着同一品牌。且举数例以明之。《冬日的田野》写景:
冬日的田野上
暮色像一地冷墨,浅浅流动
最浓的几滴,是乌鸦
乌鸦来了,冬日的田野愈加荒芜
那些散落的草垛闪进暗处
是谁家弃儿
乌鸦来了,冷飕飕地飞啊
但片刻间,乌鸦滑入夜的喉咙
——月光哑了
月光哑了,哑默的月光下
霜一粒粒叫了[7]45
呈现冬日田野的暮色、草垛、月光、霜,特出的是乌鸦。明白,简单,却隐动着感伤的浪漫主义情愫,而以不动声色的现代诗艺取胜。暮色像冷墨流动,“最浓的几滴,是乌鸦”。“乌鸦滑入夜的喉咙/——月光哑了”,“霜一粒粒叫了”!出神入化的高超现代主义手法。
《玻璃终于碎了……》[5]22—3320行诗,将一件任何人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写得如此揪心更引人深思寻味。劈头一句:“玻璃终于碎了”。“终于”一词,具有沉雷的力量。“有裂痕的玻璃,在起风的夜里/终于哗地一声碎了”,说明其必碎的原因。“天明起床,我见到碎片,那碎片/像残肢撒落一地”。进一步补叙。“残肢”一词,使玻璃人化,活了。“昨夜一声尖叫/如同闪电消逝/终于碎了,一块碎了的玻璃”。更进一步补叙。“终于碎了”是首句的复沓。至此,是一段落。后半是诗人我就此而设想沉思。“在破碎之前/有着怎样揪心的隐痛/又在巨大的忍耐中/坚守着什么”。是设想的一层。“现在碎了,它放弃了/或许痛苦太深/或许到了该放弃的时候”。是设想的进一层。“这样一块玻璃/我不知道该为它难过/还是为它庆幸”。是设想的更进一层。“它碎了,在起风的夜里/松开自己的生命。”对应着首句。它是他杀,更是自杀。不用说,这块终于碎了的玻璃是人间常见的或一种可悲的人生。
《树上的钉子》[4]79便不那么常见。所以开首便是:“天知道何时砸进去,砸得那么狠”,紧接着是观察者说话人感观:
如果不是裸露的一点痕迹
谁能看出,这棵苍老的大树
体内藏着长钉
寒光闪闪,进入的一瞬
该有多么迅猛
闪电的撕裂,也比不上
被它刺入的剧痛
更惨痛的是在可能是偷袭的刺钉之后:
在最深处,一枚钉子潜伏下来
并用白亮的牙齿
咬紧树的一生
时光流逝,钉子或许已经锈死
这样的钉子,如何除去
只能让它留在命中
痛到不能再痛
就是死了,僵硬的身体里
还扎着,锋利,尖冷
这种突袭中伤的惨痛,乃至死而不已。人世间的种种,乃有甚于超人间的恶毒惨剧。显然,江一郎诗的高识别度大得益于深度草根性基础上的圆融先锋性,骨子里的先锋性。
超强生成性。在江一郎诗中有三种生成性:诗美生成性,诗语言生成性,以及全部诗作呵成一气的生成性。一首诗的生成是诗美创造与诗语言创造融和一体一气前行的,而不是先有诗意的构思,然后予以语言表达,诗美与诗语言都是诗的本体。所以江一郎诗的超强生成性完整地表现在一首首诗的创作过程中。拙文的标题是从江一郎的一篇散文借来的。《风景就在身边》,也许正好凸显江一郎诗风的特色。文中记述了他陪同一批诗人作家游赏在家乡的长屿硐天。其间,大家在欣赏了硐群中最大的观夕硐的天然音乐殿堂中的不需要任何音响设备的大型交响乐演出。然后开展了作家现场题诗题词比赛。一郎虽因系主人不参加比赛,却激动到禁不住技痒,也在“不到三分钟,我真的完成了一首小诗《在岩洞听音乐》。这一刻,我突然体验到做诗人的那份成就感”[8]267:
我的耳朵要是这岩洞内一枝野花多好
远离浊世的喧嚣
只听美妙的音乐,仿佛来自天上
山风般吹过
山泉般淌过
做不了花朵,做一蓬野草也好啊
在摇曳中聆听,在聆听中
绿着,慢慢枯黄[8]267
“诗歌写得清新、朴素,说出了我的愿望。”[8]267此诗的超强生成性,一目了然。诗人的诗美创造主体早已养成有素,犹如一张琴。硐天中听音乐,又赛诗,激动着十指的弹奏,便有了诗之天籁。首句即显妙喻。第二、三行讲听音乐的环境与境界,第四、五行形容乐音。上节诗即已可见诗人的胸襟。下节3行更显出诗的高识别度,几乎只有江一郎才这么写,才对自己的一生有这种愿望。诗是不到三分钟中“流”出来的,看来是山泉般叮咚流下来的,是诗美创造与诗语言创造一体融合无间地一气呵成的。
但是,请注意,江一郎是非常重视诗艺技巧的。他在答问中说:“我在乎技巧。”“而诗歌写作最需要的,恰恰就是处理的能力。”“巴金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其实无技巧并不等于没有技巧,那是一种摘叶飞花的功夫,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很难相信诗歌写作可以抛弃技巧。技巧,不仅关系到形式、语言、诗中的乐感等诸多因素,更体现在情感的表达上。当然,掌握技巧不等于你就能写出好东西,诗歌的神秘性永远不能靠技巧去破解。但不懂技巧,你又如何写出好东西?在一个诗人身上,这份手艺应该是最基本的。”[1]152—153江一郎诗的“流”出来,最给力的有两条:深广开源;掌控流径。也就是源丰沛,流得妙。
且看《野花是风穿的舞鞋》:[7]28
如果我告诉你
风是快乐而美丽的少女
你信吗
如果我告诉你
野花是风穿的舞鞋
你信吗
向阳的山坡
我指给你看,那些会飞的花朵
风穿着它们
向远方去了
大地啊,多少追忆的事物
让我沉醉其中
——春天的风来了
可谁愿意
将我偷着穿走
显然,此诗的触发点与诗眼即是用作标题的这个警句。但第一节3行中先出“风是快乐而美丽的少女”来陪衬。第二节3行中才用这个警句,而且2节都以“你信吗”作结。第三节4行,说花说风说飞向远方,是推开。第四节5行一折,说花是“我”,祈愿“将我偷着穿走”,这个结末更显出江一郎诗高识别度的症结所在。
真诗人的诗,一生不管写多少首,合起来就是一首;所写的不论万事万物,光怪陆离,说到底或隐或显都是自传。江一郎尤其显得如此,这就是其诗超强生成性的总体呈现。因此,他的诗40年间先后是有所变化有所前进的。且看《穿墙术》:[7]73
而今,我不再相信世间,还有这门古老的/法术,也不再遍访天下,散尽盘缠/寻找一个会穿墙术的人/因为我根本不曾遇见/更别谈亲眼目睹/我见到的,不过是那些无知无畏者/走不出自己的迷宫/却渴望无师自通,穿墙而过/最终,被撞得头破血流/在冰冷的坚墙下/或昏死过去/或哀嚎不息
与上首《野花是风穿的舞鞋》相比,风味显然不同,与早年的《灯》相较,艺术上亦有所长进。大体上说,江一郎诗后期较前期有三个增长:叙述艺术,理性成分,超现实主义虚构。当然,他后期的诗也更显多样化。比如《山间遇雨》与《山中一夜》便显近同而实异,皆耐人寻味,但又显然出自一人之手。
深度草根性,圆融先锋性,超强生成性,三性的互为表里,相互渗透,遂有机构成了江一郎诗的高识别度与高诗美含量。他不到20岁便写诗,写了36年,出过3本诗集。产量不算太多,质量却臻上乘,甚不愧为现当代中国新诗的杰出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