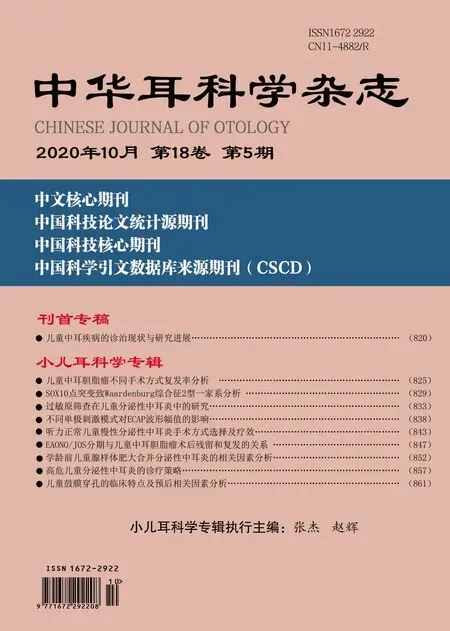耳鸣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关系的研究进展
李斐然 刘定 徐红 李俐华*
1南昌大学第二临床医学院(江西省南昌市330000)2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江西省南昌市330000)
耳鸣是指对没有外部来源的声音的感知。据统计,在美国曾有耳鸣经历的人群占25.3%,常常发生耳鸣的人群占7.9%,而这一比例可能有所低估,因为只有10%~15%的患者因持续性耳鸣寻求医学评估。同时耳鸣的发病率随年龄而增长,在60~69岁年龄段达到峰值,为31.4%[1]。我国局部地区耳鸣流行病学调查口结果显示,20~40岁年龄组现患率为2.08%,41~60岁年龄组现患率为9.89%,60岁以上年龄组现患率为14.37%;且女性耳鸣发生风险高于男性;市区人群耳鸣发生风险高于县城[2]。而耳鸣会降低生活质量,导致各种心理障碍,如抑郁、焦虑、睡眠障碍和注意力集中困难[3]。目前耳鸣的病因尚未完全了解,病因多种多样[4]。影像学和动物研究表明耳鸣的发育可能与中枢听觉系统和神经活动有关[5]。
1 耳鸣的中枢机制
为阐释耳鸣可能的发生机制,Jastrebofft曾于1996年提出耳鸣的神经生理学模型,将耳鸣与中枢的异常活动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耳鸣是由听觉系统中产生的信号的异常处理引起的,这种异常处理发生在信号集中感知之前并可能会导致“反馈循环”加剧这个异常的处理过程。而另一方面,耳鸣常造成个体的烦恼,这种烦恼导致其越来越关注噪音,这反过来又加剧了烦恼,从而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6]。
耳鸣的中枢机制基础研究发现,耳鸣的产生包括了外周和中枢听觉系统,其中中枢系统发挥着重要作用,耳蜗核中耳蜗背侧核和耳蜗腹侧核都存在神经可塑性的改变;下丘控制着整个听觉通路兴奋和抑制的平衡;听皮层的变化直接与耳鸣的感知和调节相关;边缘系统作为听觉外系统参与了耳鸣的发生发展[7]。
进一步的影像学研究更证实了耳鸣中枢神经异常活动的存在。耳鸣被视为是一种知觉过程,其引起的听觉系统的改变需要进入大脑的知觉系统进而发挥作用,因此,理解耳鸣声音的感知过程将有助于理解耳鸣的发生机制[8]。在对处于植物状态的患者影像学研究显示,仅仅有初级皮层的活动不足以产生有意识的声音感知,听觉的感知还需要顶叶下皮层、海马及扣带回前皮质的共同激活[9],同时某些接近于听觉阈值的声音,未被感知时往往仅有前岛叶的激活,而当其被感知时则需要扣带前皮质和前岛叶的共同激活[10],这些发现可能与耳鸣的发生有关。进一步地,PET显像显示,在耳鸣患者中,存在额叶和顶叶区与听觉皮质的共同激活[11]。因此,脑部上述区域的激活可能导致耳鸣时正常人不被感知的声音可被患者感知到。另一方面,耳鸣患者fMRI的异常信号不仅出现在了听觉皮层,还涉及了许多非听觉中枢,尤其是边缘系统、额叶和小脑,这就提示我们不仅是听觉中枢,非听觉中枢在耳鸣的中枢机制中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12]。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提出了“耳鸣中枢化”学说,认为当听觉中枢接受外周异常信号后,可能导致听觉中枢神经元的突触超微结构的改变并出现功能重组,产生可塑性改变从而使耳鸣持续存在[13]。
新进的研究则提示在耳鸣的发病过程中,与噪声引起周围神经传入阻滞相关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异常具有关键作用。听觉丘脑或内侧膝状体是介导声音刺激投射到大脑皮层的关键一环,而这些区域与耳鸣的发生密切相关[14]。在这里有两个相互矛盾的假说。一方面,在动物模型中,有人证实抑制性神经传递的下调导致了神经元过度激活进而导致耳鸣的发生[15]。而另一方面,有人提出内侧膝状体和听觉皮层之间的异常节律引起的丘脑神经元紧张性抑制的增强是耳鸣发生的原因[16]。
2 BDNF与神经可塑性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是第2个被发现的神经营养因子,是1982年Barde等首先在猪脑中发现的一种具有神经营养作用的蛋白质[17],是相对分子质量为12300的分泌蛋白,主要由119个氨基酸组成[6]。包括BDNF及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前体pro-BDNF(precursor for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pro-BDNF),而成熟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是由脑源性神经生长因子前体转化而来的。
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通过与相应受体结合发挥生物学作用,其中P75神经营养因子因子受体(P75 neurotrophin receptor,p75NTR)和酪氨酸激酶受体B(Tyrosine Kinase B,TrKB)分别为BDNF的受体,p75NTR、TrkB和sortilin为pro-BDNF受体[18]。当BDNF与TrkB结合,TrkB二聚体化,激活一种内在的激酶活性,进行自磷酸化,从而形成磷酸化-TrkB受体。而磷酸化TrkB能激活以下几种酶:磷脂酰肌醇3-激酶(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I3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s,MAPK)、磷脂酶 C-c(Phospholipases C-c,PLC-c)和鸟苷三磷酸酶(Guanosine triphosphatases,GTP-ases)[19]。而激活的上述几种酶可通过以下方式在突触可塑性中发挥作用。
首先,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Phosphatidylinositol 3-kinase/Protein Kinase B,PI3K/PKB)相关通路具有抗凋亡和促存活活性,调节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N-methyl-D-aspartic acid receptor,NMDAR)依赖的突触可塑性[20],磷脂酰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phosphoinosmde-3-kinase/Protein Kinase B/the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PI3K/AKT/mTOR)级联,通过调节蛋白质合成和细胞骨架发育,促进树突生长和分支,进而调节突触可塑性。
而MAPK相关的信号通路在突触可塑性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方面,MAPK/RAS信号级联调控神经元分化过程中的蛋白质合成,另一方面,MAPK相关信号也是激活细胞外信号调节激酶1/2(extracellular signal-regulated kinase1/2,ERK1/2)和cAMP反应元件结合蛋白(cyclic-AMP response bin ding prote in,CREB)所必需的[20]。这一途径不仅对早期应答基因的表达至关重要,对树突状细胞在海马神经元中的生长和分支也至关重要[21]。
BDNF/TrkB复合物还可激活GTP-ases,刺激肌动蛋白和微管合成,导致神经纤维的生长[22]。而Pro-BDNF结合p75NTR及Sortilin可引发神经元凋亡[23]。因此,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在调节脑内多种生理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是它的亚型与不同类型的受体相互作用的结果[20],并可以通过促进神经元的死亡或存活来决定神经元的命运。
由此可见,Pro-BDNF和BDNF通过利用不同的受体调节中枢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兴奋性、神经元重构、突触间通讯连接和突触可塑性。突触可塑性可分为短期突触可塑性与长期突触可塑性。短期突触可塑性主要包括易化、抑制、增强。BDNF具有提高神经元兴奋性和使突触增强的能力[24],而Pro-BDNF能降低神经元兴奋性,降低突触间传递的效率,促进突触抑制[25]。
综上所述,BDNF及其信号通路是神经可塑性的关键因素之一,对神经元的变态生长、存活起着关键作用[22],而“耳鸣中枢化”学说提示,耳鸣的发生与神经可塑性有关,因此,BDNF及其信号通路的改变可能是连接耳鸣与神经可塑性的桥梁。
3 BDNF rs 6265(Val66Met)基因多态性的影响
据报道,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基因在11号染色体(11p14.1)的短臂(P)上,长约70 kb。而编码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蛋白基因的单核苷酸多态性常见[22],导致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第66氨基酸由缬氨酸 (Valine,Val)突 变 为 蛋 氨 酸(DL-Methionine,Met),从而影响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胞内转运和活性依赖性分泌[26]。BDNF的Val66Met单核苷酸多态美国人口的携带率为30%左右[27];而欧洲约29%、亚洲国家达到72%[28]。
BDNF Val66Met基因多态性作用机制可能与BDNF前体与sortilin蛋白相互作用有关,BDNF空间构象,可能改变细胞内分泌与转运,以及减少神经营养因子向突触间隙释放[29]。也有报道称第66氨基酸为蛋氨酸的BDNF蛋白(DL-Methionin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Met BDNF)不能从高尔基体中分离形成分泌小泡[30];因此,Met BDNF倾向于聚集在胞体中,而含有缬氨酸的BDNF蛋白(Valine 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Val BDNF)则聚集在树突的点状小泡中,从而神经元分泌Val BDNF,而不分泌Met BDNF[31]。而这些效应可能引发神经元生长形态的改变,也可导致突触可塑性受损。
也有研究发现,在神经元中,具有Met66的Pro-BDNF在细胞内分布改变及运输异常。当pro-BDNF异二聚体携带一个BDNF(Val)和一个BDNF(Met)时;这些二聚体发生无效分泌,导致分泌的BDNF蛋白数量减少,从而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和情绪调节[32]。
由此可见,BDNF基因多态性将影响BDNF分泌水平,进一步影响某些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已有研究表明BDNF Val66Met可能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多种中枢神经系统疾病有关[32],也与间歇性认知和记忆障碍、抑郁风险增加和焦虑发展过程相关[33]。而基于耳鸣患者常伴有的焦虑、抑郁情绪,我们推测不同BDNF Val66Met基因型个体的BDNF水平不同可能是导致耳鸣发生的一个重要方面。
4 耳鸣与BDNF基因
根据“耳鸣中枢化学说”,耳鸣的发生与神经可塑性有关,而BDNF及其信号通路的改变将影响神经可塑性,因此,耳鸣的发生与BDNF基因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由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可以跨越血脑屏障[34],外周血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浓度水平可能被用来测量脑中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水平。因此,目前许多有关耳鸣与BDNF基因多态性关系的研究大多基于血清BDNF浓度的测定。
目前很多证据表明BDNF水平上升与耳鸣相关,如耳鸣诱导的听力损失患者其下丘脑的BDNF活化增多[35],再如水杨酸,作为耳鸣的诱导剂,不仅可以引起中枢和外周听觉神经元的异常神经兴奋,而且增加了耳蜗螺旋神经节神经元的BDNF表达[36],因此,血清的BDNF可能作为耳鸣的生物学标记。
而耳鸣患者中的BDNF水平升高的机制,有研究认为可能与听觉神经元可塑性不良和持续性耳鸣的发生有关[37]。而新近的动物实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研究表明长期使用水杨酸类药物会增加BDNF表达和CREB的活化,改变突触超微结构进而导致耳鸣的发生[38]。
另一方面,BDNF的表达水平将影响耳鸣的严重程度,有研究发现在轻度耳鸣患者中血清BDNF浓度较对照组高,重度耳鸣患者中血清BDNF浓度较对照组低,认为轻度耳鸣患者血浆BDNF水平升高可能反映了中枢听觉系统BDNF水平的升高;而在重度耳鸣患者中,血浆BDNF的相对减少认为是通过应激反应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BDNF的减少所致[39]。
由此看来,血清BDNF水平可以作为听觉系统活动性改变的一个标志,而同时,有研究表明BDNF可以作为耳鸣治疗的疗效评估手段。重度耳鸣患者经耳鸣TRT治疗,即用低水平,多频段的噪音配合有关耳鸣的患者医学教育咨询来达到患者对自身耳鸣状态的适应(此种方法尽管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却不能消除患者耳鸣声音的感知且其耳鸣的音量并未减少),其血清BDNF水平显著下降,因此,血清BDNF水平可作为耳鸣患者疗效评估的一个生物学标记。但耳鸣患者经TRT治疗后BDNF水平下降的机制尚未阐明,可能与与抑郁状态的改善有关[37]。
然而,在BDNF基因多态性的研究方面,尚未发现BDNF基因多态性与耳鸣致残量表(tinnitus handicap inventory,THI)评分、耳鸣的频率、严重程度、耳鸣视觉模拟量表(Visual Analogue Scale/Score,VAS)值有关[40]。因此,仍需进一步对 BDNF基因多态性进行研究,来阐释其与耳鸣的相关性。耳鸣往往合并焦虑、抑郁症状。而BDNF被认为是抑郁状态的一个可靠的标记,有研究表示大部分抑郁症患者血清BDNF浓度水平降低,经抗抑郁治疗治疗好转后BDNF增加[41],但也有研究发现严重抑郁症患者血清BDNF较高[42],因此抑郁症中的BDNF表达模式仍存在争议,仍需基于大样本的进一步研究对于揭示BDNF水平和抑郁状态的关系。但尽管如此,在耳鸣合并抑郁症的同时予以抗抑郁治疗往往能得到更好的疗效[43],同时,一项排除患有抑郁症状和在抗抑郁治疗过程中的耳鸣患者研究中发现,其BDNF水平反而较正常对照组更低[40],这就提示我们耳鸣患者的BDNF水平升高,可能与耳鸣患者存在的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有关。
BDNF及其信号通路已成为治疗的潜在靶点,有人提出可以通过刺激和调节神经递质受体的活性以及应用激活TrkB的小分子来诱导BDNF表达,或是利用小分子化合物如槲皮素、7,8-双氧氟沙星等来诱导BDNF的上调从而治疗某些脑退行性疾病,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亨廷顿舞蹈病[44]。尽管还没有研究证实通过改变BDNF水平可治疗耳鸣,但这不失为治疗耳鸣的一种新思路。
综上所述,耳鸣的发生机制尚未明确,但“耳鸣中枢化学说”提出耳鸣与神经可塑性可能相关基础上,随着对于BDNF基因的研究不断深入,探究耳鸣与BDNF基因及神经可塑性的关系将有望成为阐释耳鸣发生的有效途径,同时,以相关基因、蛋白为靶点进行治疗可能成为耳鸣患者解除疾病困扰的一种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