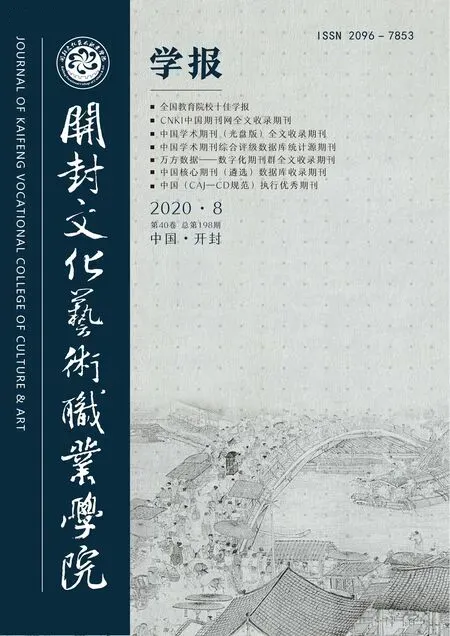滇藏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初探
李明建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省民族研究所,云南 昆明 650500)
茶马古道主要有南、北两条主线道,即滇藏茶马古道与川藏茶马古道。本文所论述的为滇藏道,其始于滇西部产茶区,经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市)、德钦、芒康、察雅、昌都,终达卫藏地区。云南藏区作为滇藏茶马古道重镇,千百年来汉、藏、纳西等民族共生发展于此。这条通道不仅是千百年来维系中国西南边疆稳定统一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促进沿线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纽带,对于当今建设和谐边疆民族社会,在理论和现实方面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滇藏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
7 世纪,吐蕃王朝向南扩张,且于公元680 年在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县塔城镇建立神川都督府,并修建了沟通吐蕃和南诏的铁桥。神川铁桥的修建,不仅拉开了滇藏各民族友好交往的序幕,而且标志着滇藏茶马古道的基本形成。《云南志》记载:“往往有吐蕃至赕货易,云此山有路,去赞普牙帐不远。”[1]266由此看来,吐蕃与南诏的商贸往来比较频繁。唐朝时,在神川铁桥附近已经形成了以茶叶与畜产品为主的贸易集市。唐人樊绰《蛮书》中记载:“大羊多从西羌,铁桥接吐蕃界三千二千口将来易。”[2]284随着这条通道商贸集市的不断增多,德钦、中甸成为滇藏两省(区)的交往要地。
明代,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贸易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木氏土司势力崛起后,滇西北至拉萨一线逐渐形成的经济带,进一步推动了滇藏贸易的发展,“滇商每年从丽江、中甸运来茶、糖、铜器、铁器、粮食等到康南及江卡、盐井地区销售,并从当地运出羊毛、皮革、药材等商品”[3]。明末清初时,“滇西北藏区格鲁派和噶玛巴派之间爆发了宗教战争和吴三桂叛乱,战火一度烧断了滇藏间传统的商贸链环”[4],局势稍稳,西藏地方政府为满足自身饮茶需求上书请求在北胜州(今永胜)互市茶马,清廷许之。康熙二十七年(公元1688 年),达赖喇嘛再次请求“互市于金沙江”,总督范承勋“以内地不便,请令在中甸立市,许之”[5]285。因此,滇藏茶马古道上的互市逐渐恢复。清雍正初年间,云南藏区得以改土归流,中甸逐渐发展成为滇藏茶马古道民间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清朝末年,德钦升平镇、维西保与中甸中心镇并称为迪庆藏区的三大镇。
民国时期,军阀乱战,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马交易逐渐淡出,但民间的商贸活动却始终活跃。抗日战争时期,滇藏茶马古道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大批军需物质从滇藏茶马古道运往抗日战争后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滇藏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样貌
从唐代开始,滇藏之间的民贸已经初具规模,沿线的各民族文化已相互交融,形成了经济、文化共生发展的结局。云南藏区作为茶马古道的重要中转站,南来北往的商人多汇聚于此,文化上实现了交流、交融;经济上互通有无,实现了西南民族经济上的互补。
(一)文化上的交流
自唐代起, 滇藏茶马古道就沟通了滇藏两省(区),联系着汉、藏、纳西等民族。明代以前,云南藏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宗教文化方面。公元680 年,吐蕃王朝在云南藏区设立神川都督府统治纳西族部落,藏族本教以此为中心开始在滇西北地区传播。纳西族的先民汲取部分本教的思想创立了东巴教与东巴文字,形成东巴文化。元朝时,忽必烈南下攻打南诏,带来了大量的回族人,伊斯兰教随之传入云南藏区。明至清中期,滇藏茶马古道上的民族贸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更多人汇聚到云南藏区,民族文化交流表现为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向其他民族渗透,木氏土司的崛起也加强了纳藏文化的交融,同时促进了与其他民族文化的交流。近代以来,国内局势动荡,大批传教士潜入滇西北地区,使得宗教文化更加多元,基督教以丽江为传教点开始向云南藏区渗透,在维西傈僳族地区创立了傈僳族文字。
云南藏区作为茶马贸易的重要中转站,各民族的交往自然始于茶。从唐代开始,云南的茶叶开始流入西藏,茶叶便出现在输往西藏的沿线地区,揭开了藏族人民饮茶的历史并逐渐形成不可一日无茶的习惯。《明史》中有“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6]1947的记载。在汉、纳西、白等民族茶文化的熏陶之下,藏族结合自身的身体需求,在茶的药用与食用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技艺与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茶文化,酥油茶便是藏族茶文化的集中代表。
(二)经济上的互通有无
自唐代茶叶输入藏区伊始,茶叶就成为藏族人民的生活必需品,于是滇茶大量进入藏区。清代中后期,“藏客” 这一特殊而又重要的从事远距离长途贩运的商人群体,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起到了极大的作用”[7]111,他们以成队的马帮往返滇藏间,从而与沿途的村户结成共生发展的关系。李旭在《藏客》一文中曾提到“马帮在路上肯定要采购一些东西,补充糌粑、酥油、马料等给养,于是,他们无一例外地要在沿途的一些村子选择一些家人做他们的‘主人家’,请他们为马帮提供各种便利服务”[8]188,这样就形成了“藏客” 与当地“主人家” 共生的“乃仓” 关系。“乃仓” 藏语的意思为“租借的住宅”,是“藏客” 们在长途商贸中与途经村寨农牧户结成的一对一互助共生关系。“藏客”称呼男主人为“乃布”,称呼女主人为“乃姆”。这样的“乃仓” 关系一般发生在规模较小的商贸交易中。据周智生总结:“乃仓关系一般是农区或牧区寻求交换者到对方某个村寨后,看上某一家,便会主动上门寻求借宿,在进一步交往中相互取得信任后提出交换要求,如交换关系得到双方认可便可结为乃仓关系,以后凡是需要交换物资过此地,都可投宿其家,并与之进行物资交换。如果这个主人家没有可交换的物资,也可代为居中与村中其他人家交换。”[9]正是“在无尽的交换历程中,手工业产品生产者都有了自己的传统伙伴,有的有亲缘关系,有的成了好友……由于建立了良好的伙伴关系,交易很容易实现”[10]。这种类似于“拟制亲属”的交换关系,在云南藏区特殊的自然与历史背景下形成了各民族经济上互通有无的保障。
据潭方之分析,民国滇茶入藏一年至少有一万担[11]107,且“云南于康藏一带的贸易,出口货以茶叶最大。康藏人民的茶叶消耗能力,可算是世界第一。他们每日三餐,一刻不能没有茶;所以云南的十万驮粗茶叶,三分之二以上都往康藏一带销售。思普沿边的产茶区域,常见康藏及中甸、阿墩子的商人往来如梭,每年贸易总额不下数百万之巨”[12]25。当地“主人” 就扮演了“经纪人” 的角色。他们为外来商人提供住宿且帮助其完成生意。在交易的过程中,当地“主人” 可以从交易金额中抽取一部分“牙用”,“客商不许和同房东客商店内的商人私货相卖,更不能越过客房房东的联系‘隐瞒牙钱’,如房东查出有上述隐瞒行为,将罚款,交给经堂即中心镇属卡地和会馆作‘香火’之资”[13]231。黄举安记载:“德钦人家都是店主,靠房子为生。各家客人上自康藏各属来此,下自丽江、鹤庆,乃至大理下关的商人均来此贸易。客人不论买货卖货或垫款,乃至担保归款时限,均全由主人出面负责。各个店主爱护他或她的客人,犹之家中手足弟兄或其侄辈。买卖绝对不允许客人吃外人的亏。”[14]365店主与商人之间形成了经济互助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云南藏区经济的发展。
三、滇藏茶马古道与云南藏区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驱动机制
(一)自然地理环境的作用
云南藏区位于滇、川、藏交界的大三角地区,其自然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其一,地势、地形、气候从青藏高原向云贵高原过渡,这一特点使云南藏区成为藏区与祖国内地联系的咽喉地带、桥梁地带与前沿地带;其二,处于高山峡谷相间形成的天然河谷孔道,这一特点使其自古以来就成为众多民族和族群商贸、迁徙流动的走廊。自唐宋起,西南各民族在这里南来北往,进行茶马互市。以藏族为主体,傈僳、汉、纳西等11 个民族共生发展于此。由于生态环境恶劣,云南藏区的物产相较于内地匮乏,且交通阻隔,物资的交换只能依赖于茶马互市的机会。各民族因为地理环境封闭性的原因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生计方式与生活习惯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差异。住在坝子地区的民族以耕作业为主,山区的民族则是半耕半牧,因而产生了不同的生活资源。生活资源的互补需求促使各民族之间产生了物资交换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
(二)民族文化渐进式的融合
明至清中期,藏传佛教在云南藏区的发展已经渐成规模。进寺院学习藏文经典、禅修,逐渐成为云南藏区民间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风尚。余庆远曾在《维西见闻录》中记载,“喇嘛之长至,则头目率下少长男女礼拜,视家所有布施,家贫,虽釜俎之属取奉之;西藏大喇嘛至,礼拜布施益甚”,且“头目二三子,必以子为喇嘛,归则踞坐中庭,父若母皆拜”[15]7,可见,以藏传佛教为主的藏文化对当地民族的影响已经蔚然成风。随着藏传佛教传播影响的不断扩大,以归化寺为主的寺院吸引了大量康藏地区的信众前来朝拜和做生意。这些商贸群体成为促进滇藏民间贸易的坚定力量。此外,奔走于茶马商贸的汉、纳、白等民族融入藏胞的生活方式中,如喝酥油茶、说藏话等。
(三)生计互补需求的牵引
云南藏区地处滇西北高原,自然环境脆弱,交通阻塞,由于各民族有限的自给,生计互补就成为必然,粮食、肉类、食用盐等生活用品成为各民族交流的物品。此外,“各民族商人以云南藏区为据点,从内地运来布匹、绸缎、茶叶、红糖、烟酒、沙盐等赴康藏销售,又采购回麝香、羊毛、沙金河药材等商品”[4]。不同民族还从不同地区为云南藏区带来优质的农作物品种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彝族从永宁、四川带来了洋芋和豆类的良种,汉族移民从昆明、安宁等地引进白菜,葱等蔬菜良种……木香和秦归的种子与人工栽培技术也由鹤庆汉族和白族商人传入维西”[16]。跨越族际与地域的界限,依托滇藏茶马古道这一路线,南来北往的商人汇聚云南藏区,生计互补需求的牵引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交往。
(四)国家力量的强化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国家力量总能推进社会演进的过程。无论是从唐宋至清初时期的滇藏茶马贸易,还是清中期至民国时期的边茶贸易,均反映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滇藏茶马古道的开辟与发展,始终没有离开国家治理边疆民族地区的政治功用与固边之需。元朝时,中央王朝在滇藏地区广设驿站。驿站体系的设立为两者之间的民贸交流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滇藏茶马古道的发展。明代时,屯田制度使部分中原地区的汉族输入云南藏区,使云南藏区的文化更加多元。此外,为了巩固西南边疆安全,中央王朝大力扶持木氏土司势力,木氏势力继而向云南藏区扩张,木氏统治云南藏区的一系列措施进而完善了滇藏茶马古道的发展,也使沿线地区的民间商贸越加密切,藏、纳、傈僳等民族的文化扩散范围越加广泛。清朝时,为了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统治,中央王朝对云南藏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减少了该地区的叛乱动荡,为汉、藏、纳西等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提供了安全的社会环境。民国时期,滇藏茶马古道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枢纽,云南藏区的商贸活动依旧频繁。
四、结语
滇藏茶马古道既是经济发展之路,也是民族文化的迁徙走廊。它直接沟通了滇、藏两省(区)的联系,实现了跨区域、跨民族的商品交换,既满足了沿线各民族日常的生活需要,又促进了沿线城镇的发展。云南藏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这条古道。云南藏区扼滇西北要地,为茶马古道重镇,南来北往的商客汇聚于此,汉、藏、彝等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文化上相互交流、交融,经济上互通有无,在生计互补需求的牵引及国家力量的强化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形成了多民族共生发展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