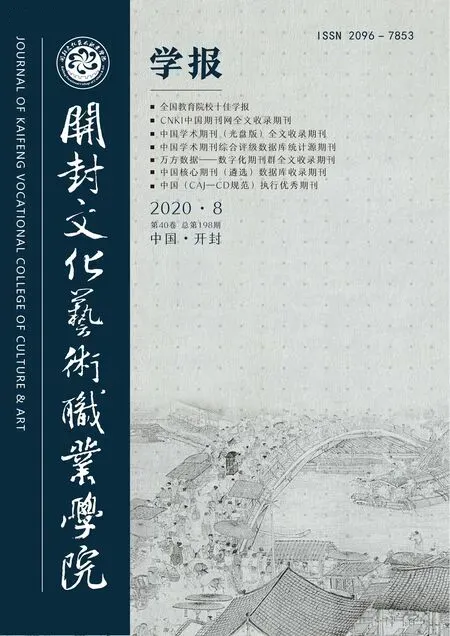论中国象棋“将” 功能转变的文化内涵
沈 旭
(安徽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现代中国象棋的“将” 在棋制上有特殊规定:“将”不可离开“九宫”,且走法和“兵”(“卒”)相似,每步只能向四周前进一格。相比国际象棋中的“王” 或者日本将棋中的“玉将”,中国象棋的“将”活动范围狭窄,杀伤力也明显不足。但在先前的中国象棋制度中,与“将”异名而同用的棋子皆有强大的攻击力。也就是说,现代中国象棋的“将”,其功能的“弱化”是历史发展的结果。鉴于此,笔者尝试梳理“将” 棋制的历史演变,揭橥定型后的中国象棋中“将”背后蕴含的人文精神,并尝试“以器见道”,探求象棋对当今人们生活与社会发展的启示。
一、历史演变的介绍
虽然中国象棋各个时期的游戏规则有所不同,但象棋游戏始终有一个决定战局胜负、至高无上的棋子。这类棋子与现在的“将” 在本质上没有差异。
古象棋有确据可考者,可溯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六博”。《楚辞·招魂》篇首次提及“象棋” 一词,其云:“菎蔽象棋,有六簙些。分曹並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 战国象棋由“箸”“棋”“局” 3种道具组成。棋子分为“一枭五散”,共有12 枚。伊文子谓:“博者贵枭,胜者必杀枭。”[1]12由此可知,“枭”如同现代象棋的“将”,其存亡关系着战局的胜负。《战国策》谓:“王独不见夫博者之用枭耶,欲食则食,欲握则握。”[2]331“食” 与“握” 皆含有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支配关系,透露出战国象棋中,“枭” 凌驾于其他诸子之上的姿态。这种行止随心的规则,赋予了“枭”强大的攻击力和掌控力。
发展到汉代,古象棋演化为“格五”[1]11,棋制有所不同,但“枭”子仍未变化。《汉书·吾丘寿王传》说:“吾丘寿王,字子赣,赵人也。以善格五,召待诏。”对于“格五”,苏林注曰:“博之类,不用箭(箸),但行枭散。”“格五” 较先前的塞戏相比,棋子中“但行枭散” 的“散” 子发生了变化,但“枭” 因其独一无二性,仍保持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唐代“宝应象棋”,已有“上将”“辎车”“天马”“六甲”等兵种,后由唐相牛僧孺增加棋子“炮”,与现代象棋在兵种上基本无异。《玄怪录》中描述“上将”有言:“上将横行係四方。”钱钟书《管锥篇》指出“係”字乃“擊” 之讹。可见,唐代“宝应象棋” 的“上将”亦拥有极大的攻击性,这正符合唐朝血气方刚、威震诸夷的盛大气象。
1997 年在洛阳北宋墓出土的一整套瓷质象棋,其棋制已于现代中国象棋无二[3]。由此,我们可以基本断定中国象棋的“将”,其功能从“对外征服” 到“困守九宫” 的转变发生在唐宋之间。
综上,中国象棋的“将”曾经也像国际象棋的“王”和日本将棋的“玉将” 一样,保留着极大的自主性和攻击性。然而,随着历史的演变,中国象棋凝聚出新的智慧,并逐渐改变了自身的规则。
二、深层规律的探究
自北宋以后,象棋“将” 的棋制不再发生变化。这说明象棋“将” 功能的最终定型符合超越时代因素的本质规律。象棋作为一种游戏艺术,处于游戏与艺术的中间地带,其同时受到游戏与艺术的双重规定。席勒曾说:“只有当人充分是人的时候,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的时候,他才是完整的人。”[4]405这正彰显游戏“无目的而合目的” 的趣味性。象棋是智力型游戏,其趣味性着重体现于“矛盾的建构与消释”。棋手的每一着子都是化解旧的势力格局并制造新的矛盾处境,在纷繁复杂的思维推理中完成与对手的矛盾斗争。而象棋“将” 棋制的变更,额外使“将” 与其自身构建了矛盾关系,即处于进攻方的势力同时也是防守方,反之亦然。若按照中国“阴阳” 的范畴来解释象棋的矛盾性,更可见象棋的中国智慧。举例来说,假设象棋中黑子处于主动进攻的优势,则黑子在整体上属“老阳”,已经打破势力的平衡并趋于胜利的完结;而黑子的“将” 却因其“自身的柔弱” 属“少阴”,随时可能有致命的危机。这时,红子处于被动防守的劣势,在整体上属“老阴”,呈现颓败下沉之象而存在失败的可能;但红子中的“帅”却因其“自身的存在”而属“少阳”,潜藏着反败为胜的希望。阳中藏阴,阴中孕阳,可见棋局便是一副立体展开的“阴阳鱼” 太极图。中国艺术理论信奉“艺进乎道”,而“将” 棋制的变更恰恰符合中国人心中阴阳交感、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宇宙图式。
棋制定型后的“将” 透露出“无为” 的思想,这符合官方与民间两个阶层的共同期盼。中唐以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5]141。人们思想的普遍指向由外而内,注重内心的修养与精神的高卓。这些都使国人对人世征服与进取的兴趣大打折扣,民族心理积淀的“无为而治” 思想重新焕发活力。另外,现代象棋中“将” 居于九宫而不可妄为是对权力的一种约束。体现在象棋中,便是“将” 作为最高统治者虽拥有莫大的武力,在一定的局势下可以同“車” 一样拥有最远的攻击范围,却不因此自矜自炫,深居“九宫”。这种规则虽以“将”为尊,但同时倒逼统治者“以民为本”。就社会整体而言,在上者“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 可以使处下者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并充分调动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现代象棋中,“将” 以其不矜不伐的阴柔之德凸显其他诸棋子的功用。无论是开局只可一步一步前行的“卒”,还是至始至终守护在“将”身边的“士”,皆以它们微小的举动影响着整个战局的变化。社会的发展也诚如此。只有掌权者善于分享权力,与民不争,充分保障民众的自由空间,才能够凝聚每一份细微的力量,从而推动社会的整体进步和发展。由此可见,象棋中“将” 功能转变的现象虽是历史演进中偶然的结果,但符合文化的进步趋势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三、文化内蕴的揭橥
《玄云棋经》云:“夫棋之制也,有天地方圆之象,有阴阳动静之理,有星辰分布之序,有风雷变化之机,有春秋生杀之权,有山河表里之势。”[6]74体悟象棋游戏的人文精神,有助于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今的启示。
其一,象棋“将” 的棋制蕴含内省静定的精神。象棋阴阳、强弱的互相转化使棋手不得不时刻处于自身的对立面进行反观。由于“将” 之柔弱而产生的危机意识使棋手在下棋时,不是一往无前地向外追逐最大利益,而是在内省中不断调整自己的思维与行动。这种三思而后行的行为模式会极大削弱内心的盲目冲动,有助于心灵复归静定。面对眼前的诱惑能够安然处之,这是一位优秀棋手需要具备的品质,也是我们为人处世必须遵循的法则。
其二,象棋“将” 的棋制有助于体悟“守中” 的智慧。“守中” 可以看作人在内省静定的基础上,对自我境界的进一步提升以及对“反者,道之动” 思想的体认。象棋与强调“益” 的围棋不同,它所蕴含的哲学智慧更多地以“损” 为着眼点。象棋的规则是“复归于无”,在矛盾对抗中一步步消磨最初的阵型。而“将” 的特殊属性更为象棋增添了以“损” 求得“保身”的色彩。这种思维虽然从消极的反面着眼,但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智慧。棋盘上,常常会有“弃子争先”“舍車保帅” 的现象出现。棋手通观全局后所不得不做出的这种判断,实与天地、圣人不仁之大心相通。因为象棋游戏的根本目的是守护无为之“将”,使自己立于不败,为完成守护任务,必须有负面意义上的“公正”。这种行为由象棋性质的先决条件决定,无可厚非。毕竟我们生存的世界,“益”“损”皆不可回避。“守中” 虽不是人生绝对要遵循的精神价值,却是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寻求安身立命的重要参照。
其三,象棋“将” 的棋制揭橥“尊体强用” 的思想。象棋游戏分为红黑两方,就某一方单看,“将” 是“体” 而其他诸子为“用”。虽然其他诸子各有其独特的走法与功能,但“将” 若亡则其他诸子皆无意义。如此,“将” 乃象棋游戏之根本,其余诸子的功能与意义都依附于“将” 的存在而存在。然而,游戏中,若诸子全无则“将” 亦无生机可言。现代中国象棋中,“尊体”与“强用”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若由棋局观社会,则会发现当下的中国是以“坚持党的正确领导” 为体,以“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领导,群众的积极性既不能提高,也不能持久。”[7]14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充分调动和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只有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够得到贯彻落实。对中国社会而言,只有体用不二、尊体强用,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
此外,中国象棋“将” 棋制的变化,额外增添了对游戏终结的反思精神及追求“和” 的深层内涵。国际象棋中的“王” 在残局中作用极大,而中国象棋的“将”不可脱离九宫,更不会跨过河界侵犯他国领域。中国象棋“将” 棋制的改变,使不得不“损” 的象棋游戏出现了更多“和棋” 的可能。放眼国际社会,在不得不进行的大国博弈中,中国也始终秉持谦逊、礼让的原则。中国如同现代象棋的“将”一般,不是没有强大的武力,只是我们一直不放弃在博弈中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能。总之,中国象棋游戏的精髓和中华民族的本性一样,不在于求胜,而在不败;不是克敌,而是无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