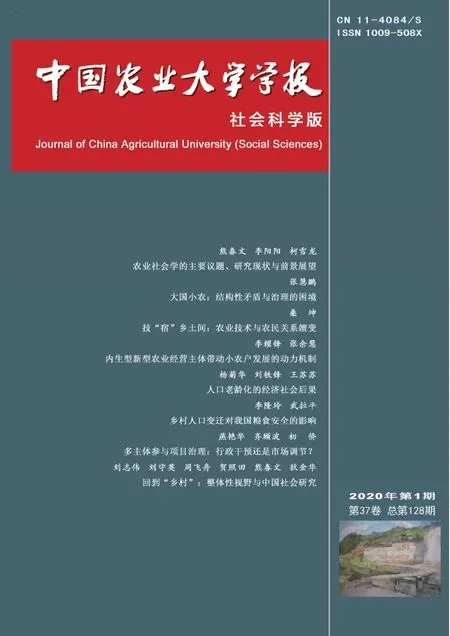作为方法和中国人精神根基的“田园”与“乡村”
贺照田
作为一个人文研究者,会非常有动力参加一个以社会科学家为主关于中国乡村的讨论,是因为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可以说也是把中国人从“土”里拔出来的过程,与这种状况相对,我近年开始关心我们能否再把自己种回“土”里。而我所以关心这个问题,是我担心如果中国人离开了“土”的帮助,中国人在精神、身心方面能否长久支持下去?
任何社会要长期支持下去,都要有一个精神、身心的基础。2018 年12 月在北大文研院参加活动,听心理治疗专家说中国人精神疾病患者的比例已经从1990 年代初的1%快速飙升到近年的17%。我想这是否可以理解为过去几十年中国的成就,在精神、身心方面是以消耗之前的积累为前提的,而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不能有所改善,不能给中国社会奠定出一个能让现代社会结构下的中国人精神、身心安顿的基础,那么,照现在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先前积累的精神、身心资源还能被消耗多久呢?而没有精神身心的支撑,中国社会又会如何呢?中国发展又会如何呢?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使我从两个方向上展开思考,一是以今天中国城市社会形态存在为前提,思考通过一些什么样的努力,能让人在生活和工作中获得更多的身心滋养、意义感支撑;另外一个方向则是,我们有没有可能找到一种把今天中国人、今天中国社会重新种到“土”里的方法,通过这种“种”,让“土”和“自然”重新成为能更积极支持、滋养中国人精神和身心的资源。当然,我知道宗教应该是回应中国人精神身心问题的重要思考方向,但因为我宗教方面积累不足,故我对中国人精神身心问题的关怀便集中在如上所说的两个方向上。
狄金华为这次讨论所写的宗旨非常能抓住我。首先是题目“回到‘乡村’:整体性视野与中国社会研究”,在这样的一种乡村关怀视野中,我对如何把今天社会形态中的中国人、中国社会,如何重新种回“土”里的关怀与思考,我对曾经对中国人、中国文化非常重要的“田园”“山水”经验的再思考,才能被当然纳入其中;其次我非常高兴他把乡村的问题与乡村发展是否仅仅就是乡村的问题,或者说它是否仅仅是一个局部性、区域性的议题这一重要问题,以如此尖锐的方式提出来,并且还明确指出,所以如此,不只是因为农业产值在整体产值及农村人口在全国人口中占比的全面下降等这些变化,还和中国当代知识思想本身出了问题有关。
下面我就呼应金华关于我们知识思想在和乡村有关的认识方面出了问题的判断,谈一谈乡村所以在今天沦为政策性问题、局部性问题,文学研究和艺术研究所负有的责任。
在文学方面,我以为最有责任也最该检讨的方面,就是文学研究在讨论在中国文学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田园”书写时的失败。比如,很多对中国田园诗开创者陶渊明推崇备至的文学史研究,都会说陶渊明崇尚自然,并举陶渊明作品为证。却不去细辨陶渊明的“自然”和魏晋南朝通常文人墨客所讲的“自然”关键性不同所在,和这一不同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首陶渊明经常被举证到的、也常常被众多选本青睐的诗:
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举证者会因此诗陶渊明自己肯定地谈到“自然”,认为最好地支持了他们关于陶渊明宗尚自然的观点,却没有细辨这时通常关于“自然”的使用意涵是和“人为”相对,在这一意义上,“山水”当然可以说是“自然”,但这首诗中陶渊明所返的“自然”并不是“山水”,而是“园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田园”。相比“自然”的“山水”,“田园”当然和人特别经营有关,属于陶渊明所说的“人境”。是以陶渊明此诗中的“自然”,并不是“山水”这样非人为的“自然”,而是和“尘网”“樊笼”相对。也就是,陶渊明并不认为“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这样的人为之所,及其在这样“人境”中的生活,是“尘网”“樊笼”,而恰恰是这样的“人境”,这样“人境”中的“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息交游闲业,卧起弄书琴”(《和郭主薄》其一)生活,最让他感到“自在”。
与陶渊明非自然的“田园”让他感到“自在”,我们不妨看与陶渊明同时代的山水诗人谢灵运的经验,谢灵运一方面依赖山水,一方面在“山水”虽有一时的饱满、畅发,可说“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却又不能从中获得持久的身心慰安,因此发出“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登池上楼》)的感慨。是以我们看到谢灵运痛下决心“持操岂独古,无闷征在今”,辞官归隐,他的隐居状态,我们通过他的《山居赋》等,可以了解他的归隐极有山水之乐。但他的传记资料告诉我们,他这种兼得山水、朋友之乐的归隐,仍没使他身心被有效安顿。由陶渊明和谢灵运的例子,我们可知“自然”和中国人精神、身心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仔细思考的问题。
比如,陶渊明也好自然,但他的“自然”并不需要像谢灵运那样倚赖奇山秀水,而可以是:
拟古·其三
仲春遘时雨,始雷发东隅。
众蛰各潜骇,草木纵横舒。
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
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
自从分别来,门庭日荒芜。
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就是陶和入住“我庐”可每天看见的燕子,经过推己、移情,使燕子由“自然”而入“人境”,成为“田园”和他个人情感、生活的更有机部分。就是陶渊明的“田园”“人境”,当然不是与“人为”相对意义上的“自然”,但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为”,和一般意义上从“自然”到“人为”的过渡地带,而是“自然”之物在最少被人改变物性、又经人的劳动和生活变成人生活和情感有机部分,从而实现的对“自然”和“人为”都有所超越的“自然”与“人为”的交融。同样,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因为他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等等,南山也已经既是“自然”,又是“人境”“田园”的延展、丰富。了解陶渊明是怎样以他超越“自然”与“人为”两分的“园田居”生活为媒介,转化周遭自然为“人境”“田园”的延展、丰富的,我们再读陶渊明最有名的这首诗《饮酒二十首·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就会想如下几个问题:如果此诗中的“真意”就是当时时代通常有的“返璞归真”“自然”之乐最高一类,他再怎么陶醉也不会“忘言”吧?事实上,不管是“菊”“东篱”“南山”“山气”“相与还”的“飞鸟”都是他“人境”生活所熟悉的,事实上也正因为熟悉,当多种熟悉要素不期而成惹他沉浸、遐思的图画与氛围时,他身心才能完全沉浸在当时、情味中,否则如南山等是他不熟悉的,他的“悠然”能这么持久、稳当,不受某种搅动吗?“飞鸟”“相与还”如不是他熟悉的,难道不会因这“相与还”的发现干扰他这要各方面因素凑合才可浑成的心景交融、物我两忘的状态吗?而因为他有上面所举“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那一类的熟悉经验,“飞鸟”“相与还”才会不仅不干扰反增加他“悠然”的丰厚与情味,而“悠然”的丰厚与情味又会深深反哺他的身心与日常生活。也就是,陶渊明周遭的“自然”当然比不上谢灵运的奇山秀水,但当这些“自然”经过陶渊明归园田居生活的中介,而相当程度上成为既构成陶渊明“人境”“田园”,又打开“人境”“田园”、扩展“人境”“田园”、活化“人境”“田园”的一部分之后,陶渊明周遭很有限的“自然”便因为他和陶渊明“田园”的相互支撑,相互滋养、加厚,反给陶渊明精神身心带来——比谢灵运的奇山秀水带给谢的精神、身心的慰安与支撑——更结实且持久的支持、滋养。
也就是,只有当文学研究认真研究陶渊明的“自在”“怀文抱质”“抱素守真”是如何、又为什么是在非自然的“人境”“田园”实现的,相比谢灵运倾心自然的、“以形媚道”的山水,虽也能在与“山水”的往复中有所得,却终究未能突破“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的瓶颈,才会思考,陶渊明的“人境”“田园”经验,和魏晋南朝以“自然”为中心的思考有关,也是对这一思考逻辑的拓展。如果像现在的文学研究这样,陶渊明被理解为崇尚“自然”,而“自然”又被理解为魏晋南朝通常理解的“自然”,陶渊明的独特经验便实际没有被面对,而这又意味着“田园”不同于“山水”对中国人精神身心的重要性没有被讲述出来,而“田园”作为安定中国人精神身心关键性场所的位置和文化意义,也就没有被讲出来。而文学研究中讲不对陶渊明的“田园”,“田园”所在乡村对中国人精神身心的重要性当然也就不容易讲深,不容易讲到关要处。这样,文学认识中的“乡村”,也便不再成为关乎中国人精神身心世界的根本。而如此也便意味着,中国文学研究讲不出田园对中国人精神身心世界、中国文化的关键性支撑、滋养,它实际上也就在以自己的方式参与着乡村在知识思想上的边缘化、局部化。
和中国文学史中一定会提到田园,但没找到足够适当的方式讲述田园同又不同,中国艺术史研究常常就不会提到田园。大家知道,中国绘画史通常把绘画分为“山水”“花鸟”“人物”三大类,这样的绘画史讲述“田园”“乡村”当然最多成为连带的问题,却不会成为需要正面面对的问题。但如果我们以上面提到的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为例,我们会发现诗里有“花(菊)”“鸟”,有“山水”中的“山”“南山”“山气”。而当我们把这首诗作为中国绘画史的一个参照,我们就会注意到如下两个问题:第一,这些景物陶渊明是站在他的“园田居”看的;第二,这些景物所以对陶渊明在那样一种时刻构成那样的意义,和他平时——已经以他的“田园”生活方式为中介转化了这些“自然”景物和他自我的理解、感觉关系——密切相关。
如果说,在中国传统社会,文人、士人都不缺乡居生活经验,故这部分和田园、乡村有关的经验,在传统中国的艺术讲述中不用特别提出来讲述,那在这一切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当代中国,在讲述中国绘画时再不特别正面展开处理——“山水”“花鸟”“人物”所以会对传统中国那么重要,所根基的下面这些基点性的存在,我们实际上不可能很好理解中国传统绘画和传统中国人的关系。就是中国传统士人、文人的日常生活、日常身心实际是通过“园田居”去安置的,“山水”“花鸟”和唐以后中国特别变形的“人物”画法,实际是在把田园乡居生活中人的精神身心进一步打开,并把田园所在的周遭“山水”“花鸟”转化为“田园”“人境”的有机部分,滋养和丰厚此“田园”“人境”与此“田园”“人境”中的“人”。现在讲中国传统绘画不讲这些(包括不足够正面突出讲传统绘画中不方便放置在“山水”“花鸟”“人物”分类,而跟田园很有关系的那些作品,该怎么进入、理解),而径直按“山水”“花鸟”“人物”分类去讲,其带来的知识、思想感觉当然也是去“田园”与“乡村”的。
相比乡村,中国现在关联“山水”但不关联“田园”与“乡村”的自然、环境、生态话语,不仅不弱势,而且相当强势,地方政府和资本的旅游开发,也近于谢灵运那样一种关于“自然”“山水”和人如何在此自然、山水中那样一种理解,这当中我们都看不到对“田园”、“田园”和中国人精神身心世界核心性关系的认识自觉。
现在流行的这些做法和理解,当年那么有条件的谢灵运就未能因之实现真正的“自在”,现在人实际在师法谢灵运,而非真师法被拔得很高的、并在不需要太多条件便极大程度实现了自在的陶渊明,实际上就是没有真正从精神身心角度思考——“田园”“乡村”曾经在中国人精神身心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以之为参照思考——“田园”“乡村”在未来中国人的精神身心生活中可以担当的核心性功能这些重要问题。而追溯这一切所以形成,文学研究、艺术史研究和文学教育、艺术教育存在的有关问题,不能不说有重要责任。
我当然怀疑这种“田园”实际缺位的“乡村”“自然”思考,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想如何把中国人种回“土”里,而不是种回“自然”的原因;也是我为什么觉得我们今天思考中国乡村未来,必需结合中国曾有的“田园”经验、“田园”视野,乡村才能对中国人精神身心生活构成更关键、有效的支撑。
但如上所说,并不等于当代就没有把今天的我们重新种回“土”里的思考,下面我分享台湾钟永丰所写、林生祥所唱《种树》的歌词:
种给离乡的人
种给太宽的路面
种给归不得的心情
种给留乡的人
种给落难的童年
种给出不去的心情
种给虫儿逃命
种给鸟儿歇夜
种给太阳长影子跳舞
种给河流乘凉
种给雨水歇脚
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
我第一次听《种树》时,前半部分我还好,但从“种给虫儿逃命”开始,我被震住了,因为它很自然就跳脱了人类中心,就带着我融于了乡野、自然,特别是最后一句“种给南风吹来唱山歌”,让我一下想起陶渊明和“南山”的关系。
沿着这样的感觉出发,衔接陶渊明当年如何获得自在的经验与思考,我相信我们可以在现代仍然把自己种回“土”里,并在这当中获得一种关键性滋养和支撑。
如此,乡村中国也就不会再是人们意识中“悯农”的场所和作为一般性城市生活补充的“农家乐”,而仍然是我们精神身心文化的根基与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