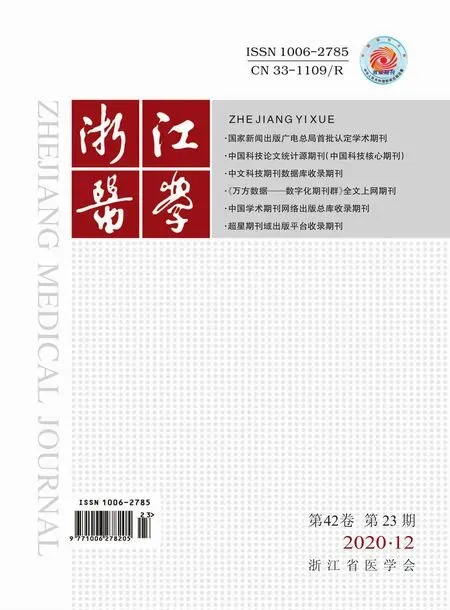慢性肾脏病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生物标志物研究进展
陈珂 聂振禹 包蓓艳
近年来慢性肾脏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患病率呈逐年升高趋势,国内CKD总患病率已达10.8%[1]。由CKD引起的各种并发症也受到重视。研究发现,心血管疾病是终末期肾脏疾病(end stage renal disease,ESRD)患者的首要并发症和死亡原因,发病率高达60%,是正常人的10~20倍[2-3]。动脉粥样硬化是导致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的重要危险因素。在CKD患者中,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病率是普通人群的数倍,其发病年龄也比普通人群提前[4]。CKD患者的尿毒症环境、氧化应激和促炎因子的失衡等共同作用促进了动脉粥样硬化[5]。动脉粥样硬化的生物标志物在CKD患者的心血管疾病早期阶段即可协助疾病诊断及预后预测,本文就此研究进展作一综述。
1 血管生成素 2(angiopoietin-2,Angpt-2)
Angpt-2是血管内皮细胞特异性生长因子家族Tie-2受体的配体。在稳定/静止状态下,内皮细胞具有抗凝、抗黏附和血管舒张表型,而活化的内皮细胞具有促凝、促黏附和血管收缩特性。Angpt-2仅在活跃的血管重建和新生血管部位表达[6],使静止的内皮细胞活化。除了血管生成外,Angpt-2可能在调节内皮细胞炎症反应中发挥有效作用,从而对促炎细胞因子的活性发挥激活作用[7-8]。内皮细胞的Weibel-Palade体(WPBs)是Angpt-2的主要来源,Angpt-2在内皮细胞活化过程中显著上调。CKD患者以及接受透析治疗的患者血液循环中Angpt-2水平升高,肾移植后3个月内个体Angpt-2水平明显下降。血清Angpt-2与动脉粥样硬化、炎症和营养不良密切相关,具有重要的独立预后预测价值,可用于慢性腹膜透析(peritoneal dialysis,PD)患者心血管事件分层[9]。在接受PD治疗的患者中,Angpt-2可能是心血管疾病风险增加的潜在介质。CKD患者血液循环中的Angpt-2水平与CRP水平相关,Angpt-2水平升高是这些患者远期死亡率的预测指标[10]。Angpt-2水平还与动脉粥样硬化及心肌损伤程度有关[11-14]。
2 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
MMPs是一类含锌内肽酶,具有重塑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和调节许多重要非细胞外基质分子包括黏附分子、细胞因子和生长因子等功能。根据其结构(或功能)和底物选择性,MMPs可分为6组,本文主要介绍明胶酶(MMP-2和MMP-9),其功能是裂解变性胶原、基底膜中的Ⅳ型胶原和某些趋化因子。MMPs的活性是由4种已知的酶调节的,这4种酶被称为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TIMPs可参与激活或抑制 MMPs活性,并与MMPs一样调节多种细胞功能,如细胞增殖、凋亡和血管生成[15]。MMPs可干预肾纤维化从单核细胞浸润到细胞增殖和瘢痕形成的所有阶段。所有这些过程均会导致CKD肾功能的进行性下降。MMP-2和MMP-9水平升高介导ECM在肾小球细胞中的沉积,同时导致细胞间连接的丢失,并在肾小管细胞中启动上皮-间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这些过程会导致肾小管萎缩和纤维化[16]。
ECM的重构和MMPs的促纤维化作用对肾脏以外其他器官也是有害的。Hansson等[17]研究发现,MMP-9和TIMP-1增加了社区群体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的风险。另有学者指出,MMP-2与颈动脉内膜-中膜厚度(carotid intima-media thickness,cIMT)和腹主动脉钙化呈正相关[18]。在CKD人群中,MMP-9与cIMT、动脉粥样硬化评分和颈动脉斑块数量呈正相关且关系密切[18]。研究发现,CKD患者血液循环中的MMP-2、MMP-9和MMP-10水平增加,并与血管损伤过程有关,且MMP-2和MMP-9能够降低CKD患者血管晚期斑块的稳定性,从而使斑块本身更容易破裂[19]。
3 可溶性肿瘤坏死因子样凋亡弱诱导因子(soluble TNF-like weak inducer of apoptosis,sTWEAK)
sTWEAK是肿瘤坏死因子超家族的一员,通过其唯一受体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诱导因子14(fibroblast growth factor-inducible 14,Fn14)诱导炎症,参与肾小管损伤、肾纤维化及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形成、增殖、血管生成、基质退化和血栓形成等多个过程[20]。研究表明,人类TWEAK蛋白分为膜结合性和可溶性两种形式,膜结合性TWEAK经弗林蛋白酶作用裂解并分泌到细胞外,成为156个氨基酸组成的sTWEAK分子,才能发挥各种生物学效应。
一项对257例非透析患者的横断面研究发现,sTWEAK水平与进展性肾衰竭内皮功能障碍相关,且与心血管疾病结局独立相关[21]。在CKD患者中,合并动脉粥样硬化患者与无动脉粥样硬化病史患者相比,其sTWEAK浓度降低;另外,在24个月的随访中,与早期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相比,严重动脉粥样硬化患者的sTWEAK水平更低[22]。同时,随着CKD患者sTWEAK浓度的持续下降,在24个月的随访后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数量增加[23]。这些数据表明,sTWEAK可能是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存在和严重程度的一个生物标志物。
4 生长分化因子15(growth differentiation factor-15,GDF-15)
GDF-15是转化生长因子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TGF-β)超家族中的一员,又称为巨噬细胞抑制因子 1(MΦ-inhibitory cytokine-1,MIC-1)。正常情况下,GDF-15在大多数组织中表达微弱,而在急性损伤、组织缺氧、炎症和氧化应激等疾病状态下,GDF-15表达明显上调[24]。GDF-15水平增高与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发展紧密相关[25]。在1型糖尿病肾病患者中,GDF-15水平升高与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与死亡率紧密相关[26]。一项为期24个月的前瞻性随访研究发现,与健康对照组相比,GDF-15水平在血液透析组患者中明显升高,GDF-15水平与cIMT、CRP水平呈正相关,提出GDF-15是一种亚临床动脉粥样硬化患者全因死亡率的强预测因子[27]。
5 成纤维细胞生长因子23(Fibroblast growth factor 23,FGF23)
FGF23是一种主要由骨细胞分泌的内分泌激素,通过作用于不同的关键分子,在调节矿物质代谢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28]。在CKD患者中,血清FGF23水平最早可以在CKD 2期观察到升高,在ESRD患者中可以显著升高[29]。虽然血清FGF23浓度被认为主要受血清磷酸盐和 1,25(OH)2D3的调节,但也有研究表明,缺铁、缺氧、炎症细胞因子或氧化应激均可刺激FGF23的产生[30]。
在CKD患者中,FGF23水平升高与心血管疾病和全因死亡风险升高之间存在关联[31]。一项针对CKD患者的研究中,FGF23的升高与非常高的死亡风险相关且独立于肾小球滤过率、血清磷酸盐、收缩压等重要协变量,这表明FGF23的作用超出了其作为CKD和磷酸盐稳态的生物标志物的作用[32]。另有研究报道,高血清FGF23浓度是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危险因素。有研究对1 512例CKD无卒中患者进行血FGF23和颈动脉超声检查发现,FGF23水平处于前五分位的参与者更有可能出现颈动脉斑块和较大的斑块,并且根据估计的肾功能、社会人口和血管危险因素等进行调整后发现FGF23水平升高与颈动脉斑块和更大的颈动脉总斑块面积相关[33]。此外,也有报道显示FGF23浓度与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之间不存在相关性[34]。因此,高FGF23是否引起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仍存在争议[35-36]。
综上所述,心血管并发症与CKD患者的死亡密切相关,动脉粥样硬化是心血管并发症的早期阶段。若能在早期评价动脉粥样硬化的生物标志物,对于可能发生动脉粥样硬化的患者及早进行干预,从而延缓病情的发生及进展,或可改善CKD患者的预后。上述5种生物标志物均可在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早期出现变化,其中MMP-2、sTWEAK及GDF-15作为其中最有前景的标志物,在临床应用前还需进一步的评估,而Angpt-2应用相对受限,FGF23则需更多的临床研究进一步证实与CKD患者动脉粥样硬化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