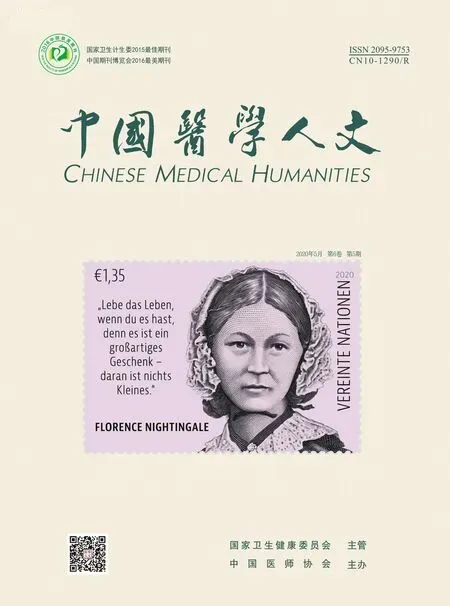鲁迅作品中的医学叙事与现代医学教育
文/王毅荻 卢 佳 夏媛媛 邵海亚
鲁迅,新文化运动的先驱,留下众多不朽佳作。以鲁迅作品中医学内容为引,概述医学叙事里鲁迅的角色,文学作品中的医患形象,强调叙事医学教育科学理论的必要性,对叙事医学中医生文学素养培养和医学伦理学的思考有现实意义。文学与医学都是创造美的科学,当代医学需要鲁迅文学作品中医学精神和人文主义。
鲁迅(1881年9月-1936年10月),新文化运动重要参与者,于1918年发表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一生写作1 000余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辑校和书信400万字,共66部书(含译著)。他的生命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文学作品上,生命的意义体现在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针砭时弊上。
纵观对鲁迅文学作品的研究,发现研究者对于鲁迅文学与医学话题的着眼点集中于鲁迅学医经历对鲁迅思想的影响:一是鲁迅作品中的疾病尤其是精神疾病如《狂人日记》的狂人形象,其隐喻是“科学”“民主”旗帜下国民愚昧的讽喻和民族顽疾的疗救。二是研究者们把描写真实病人的最终目的和落脚点集中于表达国民的精神沉疴和疗救的艰难,从对近现代文化痼瘴的思考转到对具体疗救措施的忧虑。本文另辟角度,分析鲁迅作品里的医学话语和医患形象,强调医学教学必须具有理论科学基础,通过探究文学与医学的关系,提高医生人文素养,思考医学伦理学问题。医学具有普世价值,教育受众不光是医学生,医务工作者,更是医患关系中的广大群众;教育不光是医务工作者被动接受,更谋求自我教育,自我发展。
医学叙事中的鲁迅
作为“患方”的鲁迅
鲁迅在其文学作品中不乏自己作为患者和家属的自我疾病叙事。
鲁迅年少时染上肺结核,体质孱弱的他终日咳得厉害,只能吃流食,遭受病情反复恶化以及精神上的压抑和痛苦,至最后,肺结核这隐形伴侣陪伴他走完了55个岁月。鲁迅一生经历了大大小小36种病,如牙病、气管支气管炎、肺炎、胃炎、痔、神经衰弱等1。无可置疑,每年超过20次患病记录使疾病成为鲁迅生命中最重要的体验。鲁迅的创作都是在与疾病的拼搏中产生,疾病与鲁迅的思想精神状态和心理结构有着密切联系2。
鲁迅亦是患者家属。在鲁迅八岁时,妹妹夭折让鲁迅直面惨痛的死亡体验;父亲生病卧床不起,《呐喊》的《序言》中提到“与药店的柜台一样高”的鲁迅四处典当求医问药,长达四年之久。在鲁迅的医学叙事中,中医名医的地位是极为崇高的,名医们对待鲁迅父亲的病情看得出是诚恳而尽力的,但和患者家属的沟通只是围绕病和治疗,一味地下药,医生眼里的救命良方,难得的药引药丸,都必须家属去寻找。但在家属眼里不像是治病良药,而是别生枝节。父亲在忍受庸医奇葩用药的煎熬中死亡。悲惨境遇带给鲁迅身体和精神的创伤,使他对中西医的疗效对比有了从患者角度的考量3。鲁迅作为家属,方子难以从现代医学进行科学性考证,对此产生巨大怀疑,甚至产生对整个中医体系的偏见。
作为“医方”的鲁迅
鲁迅没有成为一名挂牌从医的医生,是一名医学生。鲁迅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就是他学医经历和所学的医学知识。1904年鲁迅获得了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的机会。学医期间,藤野先生给予他不倦的教诲,讲义上的脱漏,解剖图结构错误和文法都有了红笔添改。正是藤野先生的教学指导让鲁迅在医学方面获得启蒙教育,扎实的医学知识丰富了鲁迅的知识结构,对文学作品中生病、诊断、治病等过程的刻画更加细腻准确,让鲁迅看待问题更具有科学严谨的医学家视角。
“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1906年,鲁迅因“幻灯片”事件弃医从文,从一名研究生理疾病的医学生转变成医治社会顽疾的“精神”医生。
鲁迅文学作品中“医”“患”形象
鲁迅一生所著的33篇小说中有20篇提到了疾病与死亡,有这样三段叙述印象尤为深刻。
《呐喊·明天》中的名医何小仙,被单四嫂子问及儿子宝儿病情时冷语回答,不顾家属焦急,断言实际得了肺病的宝儿病症为“中焦塞着”即消化不良,直接开方子“先去吃两贴”,医患之间缺乏沟通。
《彷徨·弟兄》中故弄玄虚,装高深的白问山,虽然态度不错,但基本的望、切之后,对于治病救人仍然含糊不清,把疾病发展与家运扯在一起,医术不精湛。
西医普悌思则是作为正面形象,观察、询问、诊脉、触诊,仔细观察病人的疾病表现,最后准确给出疾病的名称,又告诉病人相关禁忌和注意事项。细致的操作,耐心的解释,体现专业性和责任心。
小说暴露了庸医技术不过硬,还摆出高高在上、漫不经心的姿态,对患者的疾苦置若罔闻,缺乏共情,诊断、治病往往只有寥寥数语就结束了,医患之间失去了信任连结,医患缺乏共情纽带。若医学具有文学叙事的细腻和温度,即使看似不起眼的细节也可以满足真切的人的需求。
鲁迅文学中医学内容的辩证思考
从鲁迅个人经历和性格特点来看,鲁迅幼年青年时期遭遇中医庸医,承受失去亲人的打击以及他接受的西方医学,促成了他对中医的阴影和偏见,“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但不能笼统地归结为鲁迅具有反中医情节。他是反对中医中的害群之马,是在新文化运动下揭穿伪道士的真面目,来批判国人的麻木,挽救国人的精神落后。中西医的疾病系统分类和诊断方法截然不同,鲁迅作为一名西医学生,中医的外行人,没有考证中医手法的玄机和药引的药理作用,只能作为患者或者家属从疗效好坏这单一标准评价医生水平。从古至今中医确确实实具有疗效,用作者个人观点来全盘否定中医疗效和价值有失偏颇。
从现代社会的眼光来看,中医药和典籍对现代医学贡献巨大。中医强调认知和感知的平衡,是思维能力的锻炼。阅读《伤寒论》,学习中西医结合思维的人能从条文对应出病生生理,熟悉中医内科学的人能读出脏腑经络辨证的味道,这是中医中逻辑推演和认知的价值4。另外,近年很多人提出感性思维的方法,如学习脉诊就要去感受四季流动,中医不是针对局部用药遣方,而是注重从整体调节人体功能,恢复阴阳整体平衡。从动态平衡中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在环境与人的整体系统中探究人体的健康和疾病。虽然西医在认识疾病的病理生理和微观领域的考察上远比中医精准深入,但对人体生理的认识和对疾病治疗的整体思维方式上望尘莫及5。当然,过于强调合一而忽视了人的差异性会使得中医理论笼统模糊。
医学和文学思维关系的互补性。文学与医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文学和医学面临的对象都是生命。最基本不同的是医学面对生理、身体上的病人,研究人的自然属性,而文学面对心理、精神乃至整个社会的疾病,研究人的社会属性6。医学研究客观规律,通过医学知识的发现、传播、应用,提高人类健康和生活质量。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文学拥有充裕的力度和广阔的空间去表达生命这最高的存在,实质是对生命的观察和探讨。鲁迅文学作品中触目皆是医学术语,如痨病、癞疮症、痢疾、猩红热、红斑痧等疾病名称,《明天》《弟兄》《药》里的生理疾病,还有《狂人日记》《白光》《长明灯》的精神疾患,都应引起“医家”的疗救注意,它们的存在使读者初读就直观感受鲁迅对于“病态”的持续关注。“病”是鲁迅创作的源泉,“治病”是作品创作的目的。其文学作品中嬉笑怒骂,是文学中温暖的叙事力量和文学思维的人性之光,是冰冷的医学科学思维和技术所离不开的。但研究医学的普遍规律性科学问题不能过分强调文学气质。
对现代医学教育的启示
医学教育必须具有理论科学基础
科学理论是为医学基础。中西医的发展都需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西医把宏观的机体活动还原为低级的理化过程,注重人体的形态结构,把复杂人体分成八大系统,关注生理和解剖。但中医似乎没有合乎科学的理论。虽然古代解剖技术早已具备,但受社会伦理哲学束缚,技术条件不满足,古代医家不得不放弃解剖实践,解剖学出现不久就停滞不前7。由于解剖的粗疏,或基于腑脏结构、形态、位置,五脏对应阴阳五行,或基于血脉经络理论,再结合来源于《易经》的阴阳理论,调节身体的阴阳平衡,立足于哲学式空想8。曾任江苏省立医政学院(现南京医科大学)教务长胡定安提出“中医科学化”,与同僚特设“卫生特别训练班”,中医教育易改家学师承方式,中医可以报考入学,授以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等基本课程,使中医学生抛弃阴阳五行的陈腐观念;也坚持“医学国际化”,让青年深知医学作为科学一部分,如特效药发明,必须经过科学程序才走向世界医学界,为医学革命而努力,为国争光9。
中西医的文化基础可以存在差异,但其科学的部分不能有“双重标准”,最终还是疗效说话。疗效的观察一定要符合实证科学的标准,基于客观实证的数据。把发展中医单纯当作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是不可取的,建立在中国文化上的中医具有独特而系统的科学性,在其自身的境界里顺理成章,不是神学也不是骗术。别有洞天的生命观、健康观、疾病观的境界值得我们慎重对待、虚心学习。就像鲁迅《拿来主义》一文中的“鸦片”即文化遗产中集“精华”与“糟粕”为一体,中医发展必须取精用宏。
医生文学素养培养的必要性
很多文学家都用文学作品描写疾病和死亡,传达自己的生死观,反映个人置身于大社会的问题,他们都是用“诚”与“爱”对待文学,将医学内容上升到美的人性高度,他们也是医家,医的是全人类精神疾病。鲁迅写下《科学史教篇》,强调科学本质是一种人性之光,需要文学创造中的感性思维。作家与医学家思维方式的共性凝集、渗透在这种叙事特点和模式里,是潜在、内化、有温度的10。
近年提出的叙事医学不是以单纯疾病为中心,而是把医学和文学共同的对象——生命自由全面地发展作为核心主张,要求医生去倾听、理解、吸收患者的痛苦经历,及时回应并陪伴患者面对疾病、困境和死亡11。应将叙事医学理论加入正常教学内容,训练内容以关注、再现和归属为核心,关注和阅读患者的语言表达、停顿、表情、肢体动作,做好疾病叙事与书写的训练,撰写平行病历,激励医生书写自己的医疗故事,撰写科普文,让患者通过媒体、杂志、网络等平台关注医生动态,暖人心脾,拉近医患间的距离12。冲破医学复杂技术的冰冷,从根源化解医患矛盾,使双方拥有如亲人般的归属感,彰显出温度和价值。
对医学“生死观”乃至伦理教育的思考
“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这是《父亲的病》中一名西医对鲁迅说的话。《父亲的病》里鲁迅不断地描写奇特的中医药引,列出药引的名字,极尽笔墨其怪异,描写作者寻找药引的艰辛过程与方法。为了治疗父亲的病,作者从来没有放弃过一线希望,极尽所能。鲁迅一番折腾,父亲弥留之际的痛苦,是鲁迅多年之后自觉“我对于父亲的最大错处”,提出安乐死价值和生死问题是急需人们思考的尖锐问题13。它在社会观念上牵连着自然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与享用,在哲学上显现的是对生命神圣与尊严的理解。这只是伦理人文的一个命题。
作为医者或卫生事业管理者,应从伦理和人本视角开展有效的人文教育,做到关注病人生理和精神的疾痛。譬如临终关怀一块,孝悌之余,引导患者不避讳“死亡”二字,针对患者对死亡知识的不足进行补充,鼓励患者通过日记释放情绪,缓解患者的不安、紧张、恐惧情绪。平衡家属和病人的意愿,并教育家属尊重患者的意愿,保持人的尊严,理解疾病直至死亡的过程,提高最后生命阶段的质量。
结 语
鲁迅揭露伤痛,疗救病患,一生都未放弃自己的医生身份,从一名立志于治疗身体疾病的医学生转而医治国民精神疾病的文学家14。他虽已离开我们八十余年,却有历久弥新的影响力。有情怀的医生不光学习其作家身份在“新文化”运动中文学启蒙作用和批判性思维方式,还要以独到科学的眼光关注其作品中医学叙事故事和内容,感受鲁迅文学作品对医学教育中医学科学性、医生文学素养培养,医学伦理等诸多问题启示作用,认识到医学不只是冰冷冷的诊疗技术和仪器之外,医学和文学一样也是创造美的科学,在血泪与哀伤中重建人的尊严和温暖。总之,医学教育不光是医学科学知识的传授,人文素养成为医学生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鲁迅曾说“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医学人文素养的培养是长期精神内化的过程,如果医生在实际工作中应有理性和感性兼备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具有博大仁爱的人道主义精神,就一定能实现医患的和谐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