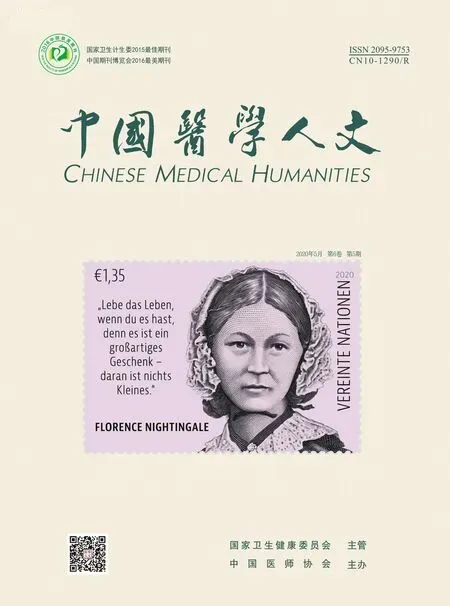古代医者地位
文/王 德
医生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医生自古社会地位就很低”,这样的论调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听到过。每当有医闹、辱医、伤医事件发生,这种想法有时也会成为医生内心无可奈何的自嘲。甚至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基因,难以改善。
那么,古代医生的地位是否真的很低?如果是,又低到什么程度、受哪些因素影响呢?这种现象真的会一直延续下去吗?
古代医官的地位
医官的地位与文臣武将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看待古代医官的地位,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根据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祖禹的历史军事地理著作《读史方舆纪要》统计,自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至明代的土木堡之变、倭寇入侵,古代大小战例共计6 192次:先秦时期661次(从周平王东迁算起),平均每年约1.2次;秦汉时期682次,平均每年1.6次;魏晋南北朝共有1 677次,平均每年4.6次;隋唐五代时期共1 411次,平均每年3.7次;宋辽金夏时期有620次,平均每年约2次;而元明时期,战争次数达1 141次,平均每年3次之多。
在这样动荡的社会背景之下,做好文治武功,保持军事的强大和维护政权的稳定,是统治者必然首先考虑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国家体制上,就是文臣武将会受到更多的重视。在元朝,蒙古主问西夏人智耀:“儒家何如巫、医?”对曰:“儒以纲常治天下,岂方技所得比?”(《资治通鉴·宋纪·宋纪一百七十三》)
最早根据《周礼·天官冢宰·叙官》的记载,古代医者是有机会入朝为医官的:医师,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食医,中士二人。疾医,中士八人。疡医,下士八人。
据其后历朝历代的史书记载,医官的人数和机构都趋于更加庞大和完善,但是其最高品阶通常只是四、五品(元朝例外达到过二品)。排在医官之前的,除了王侯,都是战功显赫的武将和有治世之才的文臣。而医者,如果被超授品级或官阶,往往会被认为是不当之举。
比如,唐朝有位尚医奉御(彭君庆)被超授三品,就有大臣进谏,认为“轻用名器,加非其人”(《新唐书·列传·卷三十七》)。
《宋史》中也有评论认为,国家应当对有功之臣多多赏赐,如果对太医、嫔御、伶官等赐予过厚,会过多地消耗国家财富,并且令边将愤叹。此外,对医官过多封爵,也出现过得宠者干扰政法的情况,担心出现类似唐监军滥政的危害。
在明朝,也有大臣对医人获取官职的情况表示担忧,这种担忧并不是仅针对医生群体,而是涉及所有“以画、弈、弹琴、医、卜技能而得官职者”“无功而晋侯、伯、都督者”以及“有无才德而位九列者”,因为这将导致“名爵日轻,廪禄日费,是玩天下之公器,弃国家之大柄也”(《明史·列传·卷六十八》)。
所以,在古代,治病活人与戍边护疆和治世理政相比,并不是举足轻重。从维护古代王朝统治的角度来看,统治者没有很强的动机将医官与这些文臣武将排在相同的位置。
术业有专攻的观点,影响医者的社会地位
文官武将在古代如此受重视,求之者也是人才济济,所以统治者应该没有必要考虑从医官中另行选拔行政官员。在他们眼里,医官做好治病的工作就好。例如,唐朝有个叫刘习的人,擅长医药,曾被委任为盐官,就被大臣反对:“医有本色官,若委钱谷,名分不正”,最终被皇帝遣还(《新唐书·列传·卷八十八》)。
不仅是医官,就算是文人,如果有偏才,也难以入仕。比如宋朝词人柳永,虽然闻名于市井,并且科举考试也榜上有名,却因为所擅长的填词过于世俗化,被宋仁宗一句轻描淡写的“且去填词”断了仕途。
史学家对于医者的态度
古代的史学家与统治者不完全是相同的立场,他们秉着客观的态度记录历史,对医者的列传往往有另一番视角。
司马迁认为扁鹊可称得上是医学的鼻祖:“扁鹊言医,为方者宗,守数精明;后世序,弗能易也”,《史记》将扁鹊与其它历史名人,如老子、孙子、管仲等并列作传。但是,对于普通的行医人,司马迁将他们统归为技术人员,认为他们竭精殚力,是为了获取更多的报酬:“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与渔人、猎夫、农、商等皆为“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并未对具体的人物作传。
《史记》之后的史书中,则是将各朝名医与相术、卜筮、音律、巧匠等统一编入“列传(艺术)”或“列传(方伎/技)”,不乏褒扬之辞:能以技自显地一世,亦悟之天,非积习致然(《新唐书·列传·卷一百二十九》);也认可其重要性:“虽方伎之事,亦必慎其所职掌(《金史·列传·卷六十九》)”。同时,他们也认为,这些行业中,能够“存夫贞一”的人并不是很多。小人携技,会出现种种乱象,比如“假托神怪、荧惑民心(《隋书·列传·卷四十三》)”“矜以夸众、神以诬人”,只有正直的士君子,才能“不迂、不泥、不矜、不神”“卓然有益于时”,他们的事迹应当被记录并流传后世。
华佗、孙思邈、钱乙等历代名医的事迹大多可在相应朝代的史籍中找到相关的记载,但是与华佗几乎同一时代、并且在后世非常有名的张仲景(隋、唐、宋的史书中均收录了他的著作),却未被当时的正史记载,而是通过他的著作以及同时期其他人物的交集为后世所知,如《脉经》中提到,当时的名医皇甫谧对他极为敬重。
由此可见,在古代的史学家看来,医者,无论出身如何,无论贫富贵贱,只要医术高超,就值得名留史册。但是,由于古代信息交流的局限性,正史的记载也难以尽善尽美,难免会有遗漏。
世人对于医者的态度
对于治病应验的医生,人们是敬重有加的。《贞观政要·卷五·论孝友》就记载,司空房玄龄对继母十分恭谨孝敬,继母生病时,他请医人来,一定要迎拜垂泣。《旧唐书·列传·卷一百三十八》也记载,有一位官员的母亲生病,所请的医生患有足疾,不能乘马,这位官员就亲自去把医生背到家中为母亲治病。
对于普通人而言,从医也是安身立命的一个不错的选择。古代的儿童启蒙读物《幼学琼林·卷四·技艺》就教导:医士业岐轩之术,称曰国手。《了凡四训·立命之学》写道:余童年丧父,老母命弃举业学医,谓可以养生,可以济人,且习一艺以成名,尔父夙心也。《梦溪笔谈·人事一》借杜五郎之口记录了当时的一种现象:乡人贫困时,会靠行医算卦来谋生。
古代医生地位低下的说法是从何而来?
与医官相比,民间普通医者的地位落差很大
古代医官的地位虽然与文臣武将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医官毕竟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比如宋高宗的一个妃子(潘贤妃)的父亲就是翰林医局官。
但是,古代官方的医疗制度不像现在这样完善和普及,能达到这个地位的医者终究是少数人,大部分医生还是在民间行医。古代民间的医者可以说是良莠不齐,《资治通鉴·唐纪·唐纪五十九》记载过一个游医,“巧谲倾谄,善揣人意”,得到徐州一位将领的举荐到军中任职,期间“浸预军政,妄作威福,军府患之”——这类事件势必会影响人们对民间医者的看法。
《旧五代史·后唐·列传一》记载,庄宗的刘皇后是幼时在战乱中被掳入皇宫的,她的父亲是在民间行医的医卜。当刘皇后还是宠妃的时候,她的父亲曾到皇宫来认亲,结果不但没有认成亲,还被自己的女儿下令鞭笞。刘皇后之所以坚决不与自己的父亲相认(其实当年掳她进宫的官吏是确认了刘父的身份的),也是因为民间医卜地位不高,她不希望父亲的身份影响自己在后宫的地位。
古代读书人以入仕为先,从医为次选
华佗最初是士人,因为入仕不顺才从医,虽然医术高超、闻名遐迩,仍然“意常自悔”(《三国志·魏书·方技传》)、“难得意,且耻以医见业”(《后汉书·列传·方术列传下》)。李时珍虽然出生于医学世家,却也是在科举不利之后才转而从医的。古代读书人以从医为次选、甚至下等,是因为从医之后,他们基本就与仕途无缘了,这是古代官员选拔制度的一个特点。
早至夏商周时期,古代的平民就有机会通过教育入仕为官:闻三代之道,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劝善也,显之朝廷(《史记·儒林列传》)。随着儒学逐渐成为社会的文化主流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儒家“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的观点也成为读书人的普遍认知。对于读书人而言,入仕为官,不仅可以安身立命,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
上文提到,入职医官的人是难以被任命为行政官员的。比如,《资治通鉴·唐纪·唐纪六十五》记载,医官梁新治好了唐宣宗的病,向唐宣宗求赏一个官位,没有得到准许,只是每月得赏钱三千缗。而民间的读书人,一旦以医为业,哪怕是熟读四书五经、才高八斗,也是没有机会再参加科举考试了。在古代的大多数朝代中,对此都有明文规定。
《旧唐书·本纪·卷十》:今后医卜入仕者,同明法例处分。《辽史·本纪·卷二十》:壬申,诏医卜屠贩、奴隶及倍父母或犯事逃亡者,不得举进士。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规定呢?
《管子》中提到,百姓应当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大类,并分别管理,“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书中认为,这样既便于各个行业内部的交流,还可以使各类人群的后代自小习染祖业,便于子承父业——“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文中还特别提到务农的人适合被选拔入仕:“农之子常为农,朴野而不慝,其秀才之能为士者,则足赖也,故以耕则多粟,以仕则多贤,是以圣王敬畏戚农”,但对于工、商业者,则没有类似的褒扬。而行医,通常被划分为工类,这也许是古代政权长期禁止医、商的从业人员入仕的原因之一。《礼记·王制》中也有类似的规定: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
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自古医、卜相关,不少医者对巫卜也有所接触。但巫卜在封建王朝主要用于祭祀,而不是统治手段。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是导致朝廷禁卜的重要原因。宋哲宗赵煦的女儿福庆公主因病危试验道家符水,也引发了一起宫廷巫卜大案(《宋史·列传·卷二》)。具备巫卜知识的医者难免会有意无意地使用巫卜之术。比如,唐朝的一位医官阎祐之就曾经与国子博士欧阳特谈论星相的征兆,结果二人皆被处死(《旧唐书·本纪·卷二十》)。如果这样的医者进入官员的编制,无疑会增加管理的难度。
医者参政
医官虽然没有行政官职,但有机会通过诊病面见皇帝,借此机会来进谏的大有人在。
《旧五代史·后晋·列传十一》中记载后唐武皇性情暴躁,一发怒就要杀人,大臣都不敢进言。给武皇治病的医生陈元深受器重,往往会揣情测意加以劝谏,救了不少人的性命。
金海陵王荒淫无道,太医祁宰极力劝诫而被诛杀。转年金世宗即位后,为祁宰平反,追封为资政大夫,给他的儿子授予官职,并破格给未及三品的祁宰颁赐谥号“忠毅”。支持该做法的尚书省官员认为:三品以上的官员有很多,但是没有一个人敢阻止海陵王,祁宰敢于为国谋事,为节操而死,虽然出身医卜,也没有什么可羞愧的。“非常之人,当以非常之礼待之”(《金史·列传·卷二十一》)。
在国家体制上明文规定医者可以入仕的,大概只有元朝。这与当时人才稀缺的状况有很大关系。在元朝初年,由于学习儒学的人太少,而以刀笔吏(执法人员)获官的人比较多,不少大臣建议重开科举,儒生、医、巫、阴阳、蒙古人,只要用心为学,都可参加(《资治通鉴·元纪·元纪四》)。
回溯历史,隔着历史的烟尘,过去的人和事仿佛就在眼前,却又遥不可及。通过了解古代医生的地位并分析其原因,我们可以得知,地位低下并非是医生这个职业的天然属性。看待医生的地位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同时也要辩证地分析。比如,曹操对华佗的轻视和迫害常常被引用为古代医生地位低下的例证,但这一观点经不起推敲:在曹操心中,有谁是不被轻视的吗?他不仅很随意地杀害了华佗,难道就没有很随意地杀害荀彧、杨修?至少在谋士荀彧眼里,华佗是“方术实工,人命所悬”,值得珍视。
在当代,医学发展日新月异,关系着民生,也关系着社会稳定。与古人相比,现代医生有更多的机会来施展才能、实现抱负,我们没有必要为医生地位的高低而纠结、哀叹。几千年来,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医生的使命始终不变。无论何时,坚守“济世活人”初心的医者,都会受到世人的敬重。在古代对医者有诸多限制的情况下尚且不乏坚守初心之人,在当今,我们更加应当能够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