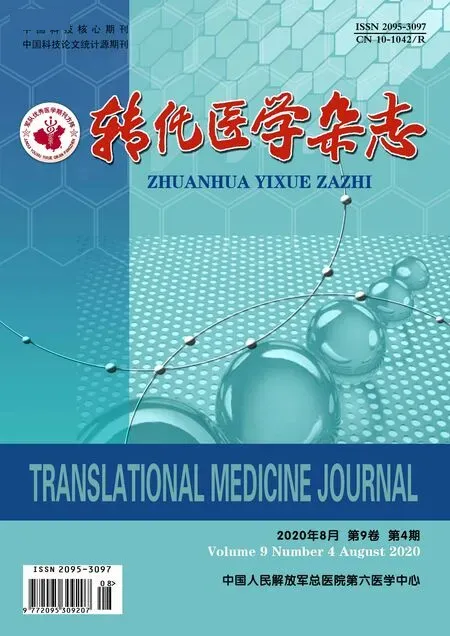乳腺癌中MDSCs的扩增和募集及相关临床应用
李嘉涛,陈佳能,刘 珣,刘 伟
在全球绝大多数国家中,乳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均居女性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首位。2018年,全球新增女性乳腺癌患者208.9万例,死亡62.7万例,分别占女性全部癌症发病和死亡的24.2%和15.0%。近年来,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率逐年上升,且年轻化趋势显著。乳腺癌转移是一个复杂的、多步骤的生物过程,涉及大量的基因和生物分子。在乳腺癌组织中,常聚集有大量的髓源性抑制细胞(myeloid-derived suppressor cells,MDSCs)。MDSCs被认为是肿瘤微环境中重要的免疫抑制因素之一,对乳腺癌的转移起到了重要作用,是许多肿瘤免疫治疗的障碍之一。作者对近年来发现的乳腺癌影响MDSCs扩增或募集的机制以及其相关临床应用作一综述。
1 MDSCs的来源和表型
在生理条件下,骨髓来源的未成熟髓细胞(immature myeloid cells,IMCs)分化为粒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在慢性炎症或肿瘤环境下,IMCs的分化过程受损,而外周血中成熟的髓细胞数量减少会诱导更强的骨髓增生,并在细胞完成分化过程之前增加细胞迁移。IMCs可以在骨髓中分化为MDSCs,也可以被分泌到血液循环中,在脾脏或外周炎症组织中被激活,导致具有强大免疫抑制功能的骨髓细胞的积累。由于它们的免疫抑制功能和骨髓来源,这种异质细胞群被称为MDSCs[1-2]。对人类MDSCs的定义较少,通常将表型为Lin-/LoCD33+CD11b+HLA-DR-的细胞定义为MDSCs。在小鼠肿瘤组织中,MDSCs可以被分成2类,一类是粒细胞性的MDSCs(G-MDSCs),其表型为CD11b+Ly6G+Ly6CLo;一类是单核细胞性的MDSCs(M-MDSCs),其表型为CD11b+Ly6G-Ly6Chi。同时,也有人将表型为CD11b+Gr1hi的细胞定义为G-MDSCs,将表型为CD11b+Gr1int的细胞定义为M-MDSCs[3]。
2 肿瘤微环境中MDSCs的产生和募集
2.1 MDSCs通过分解骨桥蛋白(osteopontin,OPN)促进自身生成 有研究[4]揭示了转录因子CCAAT增强子结合蛋白α(CCAAT/enhancer-binding protein α,C/EBPα)在MDSCs促进肿瘤血管生成和免疫抑制特性中的负面作用。肿瘤环境下的MDSCs表达C/EBPα减少,导致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MMP-9)表达升高,促进血管生成。因此,剔除骨髓细胞的C/EBPα会导致肿瘤表型恶化[4]。OPN作为一种细胞外基质蛋白,已被证明在调节对肿瘤的免疫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MMP-9可以将OPN分裂成片段,包括32 kDa片段。体外和体内功能实验证实,OPN 32 kDa片段在肺癌模型中促进MDSCs的生成,这可能有助于肿瘤逃避免疫反应[5]。
2.2 高迁移率族蛋白1(high mobility group box 1,HMGB1)促进MDSCs产生 有研究[6]证明,HMGB1普遍存在于体内的肿瘤微环境中,多种肿瘤微环境内细胞群(如肿瘤细胞、巨噬细胞、MDSCs等)能产生HMGB1。HMGB1从氨基端到羧基端的结构依次为A box,B box和受体结合模体,其中B box是发挥炎症的功能区域。HMGB1不仅能通过诱导白细胞分泌IL-1β,IL-6和TNF-α等因子促进MDSCs的积累,还能与IL-1β形成复合物,发挥更强的活性。另外,还有一种新发现的由肿瘤细胞分泌的HMGB1在Asn37位点被n-糖基化,而后它通过p38/NF-κB/Erk1/2途径促进骨髓祖细胞向M-MDSCs分化。用抗HMGB1 B box的单克隆抗体对HMGB1进行封锁,明显减少了MDSCs在肿瘤小鼠体内的积累,并延缓了肿瘤的生长和发育。HMGB1的作用机制已经在乳腺癌中得到证实[7]。
2.3 环氧化酶2(cyclooxygenase,COX-2)/前列腺素E2(prostaglandin E2,PGE2)正反馈环的建立利于MDSCs的扩增 COX-2是环氧化酶同工酶之一,可在多种细胞中对细胞因子、丝裂原和内毒素作出反应而被激活。COX-2是调节PGE2产生的关键因子,然而,在COX-2与PGE2之间存在正反馈回路,PGE2的积累会在一定条件下诱导COX-2的表达增多[8],从而使PGE2的水平进一步增高。COX-2/PGE2正反馈环的建立是CD1a+DCs重定向发育为CD14+、CD33+、CD34+M-MDSCs的充分必要因素,这种机制在肿瘤微环境中被用于促进MDSCs的局部扩增。PGE2直接靶向MDSCs表面的受体EP2/EP4,刺激MDSCs的扩增和募集,以上作用可以激活PKA信号,从而触发miR-10a的产生。Rong等[9]的研究发现miR-10a可以激活AMPK信号,促进MDSCs的扩增和活化。
2.4 集落刺激因子(colony stimulating factor,CSF)促进MDSCs的扩增 调节正常骨髓生成的因子也可以促进MDSCs的扩增,如GM-CSF、G-CSF和M-CSF。GM-CSF是Gr-1int/lowMDSCs的主要驱动因子,而G-CSF则优先诱导免疫抑制活性较差的Gr-1high细胞。G-CSF在乳腺癌内的生成可以依赖于3种途径;GM-CSF在乳腺癌内的生成可以依赖于糖酵解和SNAIL1蛋白等途径。
2.5 STAT3的激活对MDSCs扩增、分化的调控 STAT家族是一个DNA结合蛋白家族,调控大量的细胞过程。在人类乳腺癌细胞和包括MDSCs在内的许多肿瘤浸润的免疫细胞中均发生了STAT3的活化[10]。STAT3的激活可以调控MDSCs的增殖、分化及其免疫抑制作用,有利于肿瘤的免疫逃逸[3]。许多驱动MDSCs生成的肿瘤来源因子如IL-6、IL-1β、TNF-α、TGF-β和VEGF等能够激活STAT3信号通路,并且在肿瘤细胞条件培养基中培养的骨髓细胞能以STAT3依赖的方式触发MDSCs的扩增[10],从而可以认为STAT3参与了骨髓祖细胞向MDSCs的分化过程。
2.6 趋化因子在募集MDSCs中的作用 肿瘤微环境中募集MDSCs的趋化因子主要分为2类,一类是CXC趋化因子,一类是CC趋化因子。CXCL5/CXCR2和CXCL12/CXCR4信号通路参与了乳腺肿瘤小鼠模型中M-MDSCs的募集,而G-MDSCs的募集主要依赖于CXCL8/CXCR1和CXCL8/CXCR2信号通路[11]。在肿瘤微环境中CXC趋化因子浓度梯度的影响下,表达相应受体的MDSCs可以被募集到肿瘤中。
2.7 其他细胞因子对MDSCs的作用 许多肿瘤来源的其他细胞因子也可以对MDSCs的扩增、分化、募集或活性产生影响,主要包括IL-1β、IL-6、TNF-α和TGF-β:①IL-1β对MDSCs的募集有双向影响,过低或过高浓度的IL-1β均会减少MDSCs的募集[12]。适宜浓度的IL-1β可以通过调节COX-2合成前列腺素,促进MDSCs的募集[13]。②来源于乳腺癌细胞的IL-6可以通过活化MDSCs中的STAT3上调吲哚胺2,3-双加氧酶(indoleamine 2,3-dioxygenase,IDO)的表达。同时,乳腺癌本身也存在IDO的高水平表达。因此,肿瘤和MDSCs表达的IDO共同促进了CD11b+Gr1intM-MDSCs的扩增,且这一作用依赖于调节性T细胞(regulatory cells,Tregs)[14]。③跨膜肿瘤坏死因子α(transmembrane tumor necrosis factor-α,tmTNF-α)在乳腺癌等肿瘤中高水平表达。最近的研究发现[15],tmTNF-α与MDSCs表达的TNFR2受体结合后,通过NF-κB和p38 MAPK通路诱导CXCR4在MDSCs中表达,促进肿瘤组织中MDSCs的募集。同时,募集的MDSCs可在GM-CSF的诱导下自分泌TNF-α而促进其自身表达一氧化氮合酶2,增强它们抑制T细胞的能力。④研究发现[16],肿瘤细胞释放的外泌体富含TGF-β。在4T1BALB/c小鼠中TGF-β1可以通过诱导MDSCs中的miRNA-494的表达增加使PTEN的表达减小。
3 MDSCs有助于乳腺癌细胞的免疫逃逸
MDSCs具有强大的免疫抑制作用,能促进肿瘤细胞免疫逃逸。主要机制包括:①抑制T细胞功能。MDSCs消耗精氨酸、色氨酸[17]、半胱氨酸等氨基酸而阻碍T细胞的增殖。氨基酸耗竭产生的代谢产物会导致T细胞受体结构和功能受损[18]。②产生NO、活性氧(reactive oxygen species,ROS)。MDSCs分解精氨酸产生的NO能够损伤DNA并抑制蛋白质的合成。同时,MDSCs产生的ROS与NO相互作用,产生过氧亚硝酸盐而导致CD8+T细胞功能受损。③诱导其他免疫抑制细胞产生。MDSCs中色氨酸的消耗激活T细胞表面的蛋白激酶GCN2,从而诱导未成熟的CD4+T细胞分化成Tregs。另外,缺氧环境下MDSCs中STAT3的活性下调会促进M-MDSCs向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分化[19]。④抑制淋巴细胞归巢。HMGB1能促进MDSCs表达解聚素金属蛋白酶17,使T细胞L-选择素的表达下调,从而抑制CD8+T细胞归巢。
4 临床应用
4.1 CSF通路临床应用 乳腺癌可以分泌G-CSF,使自身长期暴露于高水平的G-CSF,提高自身转移率。基于此,药物BMP4可以通过抑制肿瘤细胞中NF-κB的活性使G-CSF分泌减少,导致MDSCs的数量和活性下降。因而,临床上可以通过使用BMP4或激活BMP4信号通路来治疗有转移性风险的乳腺癌患者[20]。然而,临床癌症治疗中也广泛应用G-CSF,因为适宜浓度的G-CSF可以大大降低化疗导致的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发生率。因此,在治疗的不同情形下合理地应用G-CSF和G-CSF通路抑制剂,可以提高乳腺癌的治愈成功率。
接种自体肿瘤细胞疫苗(autologous tumor cell vaccines,ATCVs)是一种安全的潜在治疗策略,可以以个性化和患者特异性的方式预防乳腺癌在肿瘤切除后的复发。然而,乳腺癌分泌的G-CSF有可能会降低乳腺癌ATCVs的疗效。Ravindranathan等[21]的研究发现应用G-CSF通路抑制剂或G-CSF基因消融可以增强乳腺癌细胞疫苗的免疫原性,可能有利于发挥ATCVs的全部潜力。
CSF1R抑制剂(如Ki20227、PLX3397、GW2580、BLZ945等)已显示出削弱肿瘤相关巨噬细胞的强大能力,然而,它们并没有在小鼠身上产生抗肿瘤作用,而且在几项临床试验中均未获成功。Kumar等[22]的研究发现肿瘤细胞产生的CSF1能抑制癌相关成纤维细胞产生粒细胞趋化因子(在小鼠肿瘤模型中为CXCL1,在人类肿瘤中为CXCL8),从而限制了粒细胞的募集。CSF1R抑制剂逆转了这一效应,并导致大量促肿瘤的M-MDSCs的积累。因此,CSF1R抑制剂(PLX3397等)与CXCR2抑制剂(SB225002等)联合使用可削弱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并抑制M-MDSCs募集,显著降低肿瘤生长。此外,如果加入PD-1抗体,可阻断肿瘤生长。
4.2 STAT3抑制剂相关药物 STAT3抑制剂对于乳腺癌治疗具有重大意义。除小分子药物和肽类、拟肽类之外,还有研究发现许多天然产物可以作为STAT3抑制剂并对乳腺癌的治疗有积极意义。姜黄素类[23],黄酮类的水飞蓟素[24],二萜类的丹参酮类[25],五味子素B[26]等均可以通过抑制STAT3磷酸化或阻断STAT3信号传导达到抑制肿瘤生长的目的。虽然目前临床上还没有使用STAT3抑制剂来治疗肿瘤,但许多STAT3抑制剂在体外已经被证明可以提高治疗药物的疗效,所以STAT3抑制剂可能是一种有前途的肿瘤化疗增敏剂[24]。
4.3 趋化因子通路临床应用 使用CXCR1/2拮抗剂reparixin可以干扰CXCL8-CXCR1/2通路,这提示了一种潜在的癌症免疫治疗方法。在具有免疫能力的荷瘤小鼠中,reparixin可以减少G-MDSCs的数量[27]。Dachshund 1 (DACH1)可以通过与CXCL8启动子的AP-1和NF-κB结合位点结合,抑制CXCL8诱导的乳腺癌细胞转移[28],显示出潜在的肿瘤抑制能力。缺乏CCL5刺激的骨髓细胞,细胞表型发生改变,MDSCs免疫抑制特性降低。因此,Ban等[29]提出以骨髓自分泌CCL5-CCR5轴为靶点,使用纳米颗粒使CCL5基因表达沉默,联合使用CCR5抑制剂Maraviroc,可减弱MDSCs免疫抑制功能,增强抗肿瘤免疫。芹黄素,作为一种抗炎物质,在最近的研究中[30]被证明能够抑制乳腺癌TNF-α介导的信号通路,控制释放CCL2,从而减少MDSCs在乳腺癌中的浸润,然而目前无相关的人类临床试验。至于芹黄素是否可以让癌症患者得到长期的缓解,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5 展望
乳腺癌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对MDSCs的扩增和募集产生促进作用。MDSCs具有强大的免疫抑制功能,因此,大量浸润的MDSCs常常与乳腺癌预后不良有关。除了CSF、趋化因子和COX-2/PGE2等经典途径外,OPN、HMGB1等新兴的通路最近接连被发现,但其机制尚未被完全揭示,未来可能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针对相关通路潜在的治疗方法已经被提出,但大多数并未应用于临床。随着各种机制被不断揭示和新药物的开发,未来采用多种通路靶向药物的联合应用来改善乳腺癌的预后,必定是一种有价值、有前景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