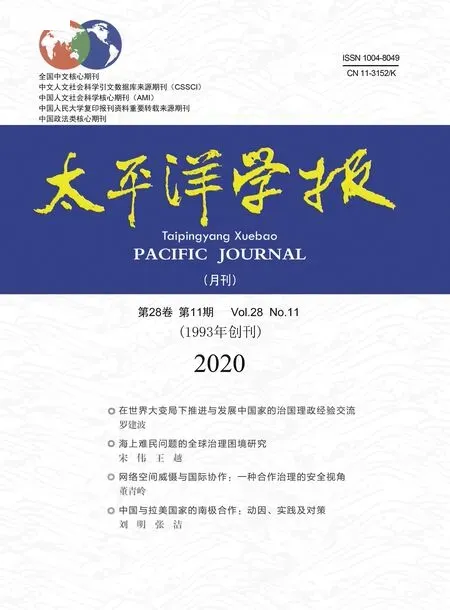论美国国际海底区域政策的演进逻辑、走向及启示
张梓太 程飞鸿
(1.复旦大学,上海200438)
国际海底区域是指“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海床和洋底及其底土”,《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将其称为“区域”。 “区域”约占全球海洋总面积的65%,地球表面积的49%,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海底资源。 据统计,仅其中蕴含的天然气水合物资源总量就约等于世界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总储量的两倍。 无论是在能源持续利用上,还是国家战略安全的部署上,“区域”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问题上,相关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动向非常重要。 所以,有必要分析美国的“区域”政策演变历程,预判其未来可能的走向。 以此为基础,为我国未来“区域”政策的制定提供启示。
一、美国国际海底区域政策的演进逻辑
1.1 《大陆架公约》与美国的支配地位
1945 年美国发布《美国关于大陆架的底土和海床的天然自然资源政策第2667 号总统公告》,此报告被视为全球进入“海底圈地运动”时期的重要标志。①Barry Buzan, Seabed Politics, Praeger Pulishers, 1976, pp. 7-8.其中的意义不仅在于,人类可以凭借技术手段对“区域”资源进行勘探开发,还在于人类开始对当时尚属无主物的“区域”资源进行先占式占有。 但是这种先占式占有激化了相关国家在瓜分国际海底区域过程中的矛盾。 于是1958 年联合国召开了第一次国际海洋法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即是解决当时的海底界限问题。 同年《大陆架公约》发布,以“200米等深线”作为划定各方边界的依据。 不过,在美国的主导和考虑到促进海底开发利用的双重影响下,《大陆架公约》又有例外规定,即拥有超过“200 米等深线”海底开发技术的国家可以不受此种限制的约束。
表面上看,《大陆架公约》确实构建了一种相较先占模式更显秩序性的开发制度,改变了以往无序的开发状态。 但问题在于,以当时实际的技术状况,美国作为海底开发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完全可以凭借先进的海底开发技术绕过“200 米等深线”的限制进行自由开发,甚至严重威胁一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安全。①郭渊:“海洋权益与海洋秩序的构建”,《厦门大学法律评论》,2005 年第2 期,第122-147 页。所谓“200 米等深线”,与其说是划定秩序的分野,毋宁说是圈住其他沿海国家的“牢笼”。 进言之,《大陆架公约》不过是由美国一手主导并使其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工具罢了。 因此在这一阶段,虽然美国积极参与“区域”事务,努力构建新秩序,但其本质仍是扩大其国家利益,拥有“区域”内绝对话语权,独享“区域”内的各项收益。 如何将美国在“区域”的收益最大化,是该阶段美国参与“区域”事务的主要议题。
1.2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及《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美国的挑战
随着不结盟运动在20 世纪60 年代的兴起,发展中国家逐渐渴望在国际舞台中获得更多话语权。②高志平:“不结盟运动与国际海洋新秩序的构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5 期,第90-97 页。在1967 年第22 届联合国大会上,由马耳他大使帕多(Arvid Pardo)提出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Principle of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即是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对“区域”资源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 作为对该原则的肯定,联合国以此为基础制定了《公约》,并成立了国际海底管理局(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这一专门机构。
“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和《公约》对美国的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原本《大陆架公约》的基础上,美国内政部和国防部的意见分歧严重:内政部主张“开发自由”和“利益至上”,希望对海底资源进行无限制的开发;国防部则主张“航行自由”和“飞越自由”,深感开发自由会影响美国舰队的军事部署,甚至威胁美国主权。 但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和《公约》使得原本意见分歧的内政部和国防部暂时握手言和:内政部认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突破了原有海底大陆架体系,对其“开发自由”原则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国防部认为国际海底管理局可能对“区域”上覆海域产生管辖效果,从而影响其舰队的“航行自由”。
与此同时,在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召开期间,美国发现此次会议的最终决议可能与其“一家独大”地支配国际海洋之愿景相去甚远。 为了维护其在“区域”的利益,美国以国内立法和多国条约联合的方式对抗“区域”的相关法律制度。 1980 年6 月,美国颁布了《深海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The Deep Seabed Hard Mineral Resource Act),并明确指出该法旨在建立一套符合美国价值观的制度体系,一旦美国不签署《公约》,便可借该法维护“区域”利益。③Lauren Finn, Superpower at Sea: U. S. Ocean Policy,Praeger, 1983, p. 117.在里根政府拒绝签署《公约》之后,美国旋即与英、法以及联邦德国签署了《关于深海底多金属结核矿暂时安排的协定》(Agreement Concerning Interim Arrangements Relating to Polymetallic Nodules of the Deep Seabed),试图构建一套以若干发达国家结盟的“区域”国际法律制度。 可以说,这种《公约》之外的国际协议实质上为美国提供了一种规避国际海底区域开发制度约束的选择。④王金强:“制度变革与政策选择——基于国际公共资源分配问题的理论分析”,《当代亚太》,2013 年第1 期,第33-50、157-158 页。
概言之,在这一阶段,由于其他国家权利意识的觉醒,以美国为主导的“区域”秩序已经被打破,美国的国家利益遭受严峻挑战。 面对这样的态势,美国采取了消极对抗的策略,并以国内法和国际法相结合的方式,试图继续维持自己在“区域”事务上的主导地位。
1.3 发展中国家的妥协与美国立场的转变
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意识形态、政治背景、国家结构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差异,两者对《公约》中的诸多条款意见不一,难成一致。 这种分歧直接表现在:从《公约》出台截至1990 年8 月底,批准《公约》的42 个国家中仅有冰岛一国属于发达国家。 问题在于,如果发达国家不加入《公约》,《公约》的普遍性原则就很难得到确认,其有效性也会大打折扣。 基于此,联合国又组织各方就争议内容进行了数轮磋商,并最终于1994 年7 月通过了《关于执行1982 年12 月10 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以下简称《执行协定》)。 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执行协定》可视作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妥协的产物。 具体原因有下四点:
第一,《执行协定》保证了发达国家的决策权。 美国认为在原本《公约》的决策机制项下,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其数量上的优势,影响决策的制定,从而有损美国的国家利益。 为此,《执行协定》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一般决策应由大会和理事会共同制定,决策应当采取协商一致的方式①《执行协定》附件二第3 节第1 条和第2 条。,而美国在理事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 同时,关于某些特定决议(譬如财政和预算),要先由理事会提出建议,再由大会协商表决。②《执行协定》附件二第3 节第4 条、第5 条和第6 条。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执行协定》在决策方式和决策机关上都做出不少的让步。
第二,《执行协定》取消了生产限额的限制。《公约》为了保护陆地资源生产国的利益,防止海上生产的同类商品冲击市场,对“区域”资源开发活动进行了限制。 这一主要维护陆地资源生产国的规定,显然不符合美国作为海洋大国的利益。 因此,在《执行协定》中原有的生产限额条款将不再适用。
第三,《执行协定》取消了强制性转让私有技术的义务。 原本的《公约》希望“促进和鼓励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这种技术和科学知识,使所有缔约国都从其中得到利益。”③《公约》第十一部分第144 条第1 款。这一规定与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和技术专利的诉求相悖。于是,《执行协定》规定应以市场交易或联合开办企业的形式实现技术流通。④《执行协定》附件二第5 节第1 条。此种举措既满足了发达国家对技术保护的需要,也允许以公平对价的方式实现技术的流通。
第四,《执行协定》减少了开发国在“区域”资源勘探开发上的财政支出。 美国认为,之前《公约》的海底开发条款对美国而言意味双重征税。⑤王金强:《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分配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119 页。为此,《执行协定》大幅削减了所谓“双重征税”的税额。 首先,将海底勘探与开发的申请费由50 万美元降至25 万美元。 其次,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缴纳的年费也不再设定固定数目。 最后,将原本需强制缴纳的对发展中国家援助的补偿基金变为非强制的经济援助基金。 多种措施并举以达到降低开发成本的目的。
正是由于上述改变,《执行协定》获得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认可。 在1993 年的第48 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投票支持通过《执行协定》,并于同年8 月正式签署该协定。 由此标志着美国对“区域”开发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消极对抗又重回积极合作的局面当中。
1.4 美国“区域”政策演进的总结
虽然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美国“区域”政策历经多次转变,但其中不变的主线是对国家利益的维护。 一言以蔽之,只要符合国家利益,美国就采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反之,则以消极的态度予以对抗。 有学者曾认为,美国“区域”政策的演进是受到国际公共资源分配制度演变的影响。 具体来说,市场型资源分配制度较之权威型资源分配制度更受美国青睐,其原因是前者侧重效率,而后者强调公平,前者符合美国对市场自由竞争制度的偏好。①王金强:《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分配与美国的政策选择》,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11 年,第117-118 页。但笔者不赞成此观点。 因为,只要往深层去分析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所谓“偏好”本就是虚无缥缈的物件,市场型资源分配制度之所以可以获得美国的青睐,归根结底是因为这一资源分配制度可以在竞争中凸显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技术的三重优势,合力打造美国的“区域”主导地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这才是美国作出政治选择的关键。
不仅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国家利益”一词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 具体来说,在20 世纪50 年代,由于各国深海开发技术的不发达,此时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策略无疑是尽可能地独占“区域”资源。 随着冷战的进行,以及随后苏联解体带来的“一超多强”局面,国家间综合实力的此消彼长使得各国在深海开发技术的发展上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新局面,美国独占“区域”资源的要求逐渐变得不现实起来。 实际上,从同意召开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到通过《执行协定》,不仅意味着美国对“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公开承认,同时也昭示美国对其拥护的市场型资源分配制度有松动之迹象。 此后,美国的“区域”政策转向了如何通过具体的资源开发机制维护其在“区域”资源分配上的主导权。 因此,改变以往较为过时的策略,在各方博弈中最大化美国的国家利益,并且尽可能维持以往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在当今世界中新的利益诉求。
二、美国在国际海底区域问题上的利益论争
在美国签署《执行协定》后,不少分析人士都认为美国加入《公约》或许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但事实截然相反。 自克林顿政府以来,美国国会多次举行批约听证会却屡遭碰壁。 美国国会的这一态度表明,在加入《公约》这一问题上,美国国内有着重大的利益分歧。 因此,分析此间的分歧究竟为何就有了必要。②相关分析主要有:讨论《公约》对主权的影响,See Horace B. Roberston,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Prospects for US Accession”, Reference Reviews, Vol.24, No.8, 2010;讨论《公约》对军事活动的影响,See Doug Bandow,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Inconsistent with American Interests”, Cato Institute, April 8, 2004, https:/ /www.cato.org/publications/congressional-testimony/law-sea-treaty-inconsistent-american-interests.当然需要明确的是,这种利益的分歧有多个维度,本文的旨趣仍围绕“区域”问题展开。
2.1 “区域”利益受损论
反对美国加入《公约》的论者势力非常强大,相关论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层面。
第一,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决策机制使得通过不利于美国的决策成为可能。 由于国际海底管理局大会的成员中包含不少发展中国家以及可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的国家,美国一旦加入《公约》势必成为少数群体。③Michael Tennant, “Will Our Freedoms be Lost at Sea?”,New American, Vol.28, No.13, 2012, p.10.这种少数群体的地位意味着,在《公约》的决策机制下,美国非但不能阻止,甚至还可能被迫通过不符合其“区域”利益的决定。 虽然《执行协定》弱化了大会的作用并增强了理事会在决策机制中的地位和权利,但诸如《执行协定》第三节第11 条等条款亦表明,如果理事会三分之二多数的成员反对某项工作计划,该工作计划同样存在付诸东流的可能。 受损论者认为,美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少数群体的地位仍未得到实质改善,与美国利益相悖的国家还是有可能运用现有机制损害美国的“区域”利益。
第二,加入《公约》后“区域”开发需要缴纳的费用甚巨。 《执行协定》虽然将原本《公约》中规定的50 万美元“区域”勘探申请费用降低至25 万美元,但是《公约》同样规定,“区域”勘探申请费用可能会变动。④《公约》附件三第13 条第2 款。与之相佐证的是,在2012 年7 月,国际海底管理局根据这一规定将25 万美元的勘探申请费调回至50 万美元。①Se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 Decision of the Assembly of the International Seabed Authority relating to the Budget of the Authority for the Financial Period 2013-2014” , ISA, July 27,2012, https:/ /www.isa.org.jm/documents/isba18a7.受损论者据此认为,这种趋势表明了“区域”勘探申请费费用在未来有着继续增长的可能。 更关键的是,仅仅是进行申请而非实际开发就需要支付如此高昂的费用,这显然是不能承受的。
第三,受损论者认为,美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国际国内“区域”开发法律体系,无加入《公约》之必要。 例如在国内法上,美国的《深海底固体矿产资源法》对申请勘探开发的企业从申请到审批都做出了细致和严格的规定。 在国际法上,《关于深海底多金属结核矿暂时安排的协定》等双边或多边条约赋予美国合理开发的互惠国地位,甚至美国与所有拥有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Clarion-Clipperton Zone)开采执照的国家都达成了有效的双边协议。②这些国家包括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和英国。而在具体开发层面,早在1984 年美国已经给四个跨国公司颁发了勘探开发的许可执照③这四个公司分别是:Ocean Minerals Company (OMCO);Ocean Management, Inc. (OMI); Ocean Mining Associates (OMA);and Kennecott Consortium (KCON)。,并且已经进行了较为成功的开发。 受损论者由此认为,这些情况证明了美国的开发制度具有“完备”的法理基础。 对比规则过分烦琐、成本昂贵并且效率低下的“区域”开发制度,美国并无加入的必要。
2.2 “区域”利益增进论
增进论的拥趸从反驳致损派的论点出发,提出了三点理由。
第一,《执行协定》已经改变了国际海底管理局原有的决策机制,赋予了美国在“区域”事务上必要的发言权和影响力。 《执行协定》规定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一般决定应当由大会会同理事会协商一致,共同制定。 如果在某一问题的协商事宜上,相关方面没有竭尽一切努力,那么理事会可以延迟决定。 美国恰恰可以通过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常设席位形成反对意见,以阻止不利决议的通过。④参见前文的论述及Scott G. Borgers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newable Resource Journal, Vol.25,No.3, 2009, p. 17.不仅如此,《执行协定》关于实质财政问题的决策机制更甚,其规定财政委员会应当采用协商一致的表决方式。⑤《执行协定》附件二第9 节第8 条。实际情况在于,美国是财政委员会最大的捐款国。 这就意味着没有美国的同意,任何实质财政决策都不可能通过。 这种改变无疑契合了美国对国际海底管理局内话语权主导地位的追求。
第二,《执行协定》降低了“区域”勘探开发财政支出,且所需缴纳的费用在可承受范围之内。 首先,国际海底管理局的所有机关及其附属机构的运作都必须虑及成本,甚至召开会议的次数、长短等因素概莫能外。 其次,《执行协定》在缴费费率、缴费制度以及年费等内容上都作出了减免或简化的规定。 最后,《执行协定》取消了原本《公约》规定的关于“区域”资源开发生产不得超过陆地同类资源开采产量60%的限额规定,这就打开了“区域”资源开发的窗口。开发“区域”所需缴纳的费用相比“区域”资源巨大的价值是可承受的。
第三,加入《公约》可以提升美国对“区域”事务的影响,树立美国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⑥Scott G. Borgerson, “The National Interest and the Law of the Sea”, Renewable Resource Journal, Vol.25, No.3, 2009, p. 17.由于美国没有加入《公约》,当今国际社会管理海洋事务的三大国际组织——国际海洋法法庭、大陆架界限委员会以及国际海底管理局(包括大会、理事会各委员会),均不包括美国公民。虽然受损论者主张,美国完全可以游离于现有的制度体系之外,但增进论者认为这对于美国想要维护其海洋权益以及主导海洋事务的决心是相悖的。 更令增进论者担忧的是,如果美国一直游离于《公约》体系之外,就等同于将“区域”各种规则的制定权和开发的优先权拱手让人。 如果等到“区域”制度规则和开发格局都已经成型时,美国再想介入其中谋求利益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2.3 受损论和增进论的实质及其分析
通过前文对受损论和增进论诸观点的罗列,我们可以发现双方争执的焦点主要围绕美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话语权、“区域”勘探开发费用以及美国是否有加入《公约》之必要上。笔者认为,这三点论争事由的实质仍在于美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话语权,而非其他。 首先,“区域”勘探开发所需缴纳的一系列费用并非美国不能承受之重,这笔费用相较于其前期投入巨大的技术研发资金以及“区域”资源的巨大价值,并不值得一提,以此为借口颇有欲盖弥彰之嫌。 其次,致损派认为的美国已经拥有较为完善的“区域”开发法律体系,实际情况也并非如此。 事实上,1982 年美英法德四国构建《关于深海底多金属结核矿暂时安排的协定》体系,如今仅剩美国尚未加入《公约》,这与其当初构想的发达国家“区域”勘探开发联盟相去甚远。最后,美国之所以构建国际国内的双重“区域”法律体系,其意图仍是主导这一体系。 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受损派的真实立场。
既然美国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话语权才是两派争执的实质,对这一问题的判断也就成为影响美国“区域”政策的重要因素。 一方面,如增进派所言,《执行协定》赋予了美国在“区域”事务上充分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美国并没有如愿以偿地取得国际海底管理局的主导地位。 在理事会实质性事项的表决中,理事会采用的是三分之二多数决和加权表决并用的方式。 具体来说,理事会将其三十六个成员国分为了五类四组,即四个消费国、四个最大投资国、四个主要净出口国(至少两个发展中国家)、六个代表特别利益的发展中国家以及十八个按地域分配的发展中国家。 其中四个消费国中必须包含“在《公约》生效之日起,以国内生产总值计最大的国家”,这等于是为美国量身定做的门槛。①《执行协定》附件二第3 节第15 条(a)款。但是该组中还包括“东欧经济实力以国内生产总值计最大的国家”,这一位置从1996 年起就属于俄罗斯。 另外两个位置,从2005 年起就是日本和中国。 换言之,按照现有实质性事项的表决机制,美国要想否决理事会的某项决议,就必须获得中日俄三者其二的支持。 考虑到日本与美国紧密的国家关系,可以说在实质问题上的表决上,最终又是中美俄三国的政治博弈。 但平心而论,这种决策机制已经是对美国做出的最大的妥协,当今的世界要求一家独大显然不大可能。
值得追问的是,既然美国无法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获得话语主导权,是否就意味美国的“区域”利益会因此受损? 笔者认为也不尽然。
第一,美国确实会因为没有话语主导权,而在“区域”勘探和开发的某些事宜中受到牵制或者作出让步,不过这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通过对美国不利的事项并非易事。 从决策机制上来说,理事会的确有可能通过对美国不利的事项。但反过来,要通过对美国不利的事项也需要在本组内没有过半数反对,也即必须在中俄同意的前提下再取得日本的同意,这基本等同于不可能。第三,如今的“区域”勘探开发法律体系中还有很多不明确和亟待完善之处,美国完全可以参与到“区域”勘探开发规则的制定过程中并施以影响,从而在即将开展的“区域”开发利用环节谋取最大化的利益。 实际上,如果在“区域”的开发阶段美国仍未介入其中,届时美国的“区域”利益将会真正受到严重损害,这也是最令利益增进派担忧的事情。 综合前述几点理由,可以认为加入《公约》对美国“区域”利益是利大于弊的。
三、未来美国国际海底区域政策的预判
3.1 对国家利益论一些干扰要素的厘清
以国家利益为分析对象,美国加入《公约》,并在随后参与到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各项事务中对其“区域”利益更为有利。 但问题是,美国却并未应循此论断的预判,至今仍游离在《公约》体系之外。 这是否代表着前文的结论存在偏差? 笔者认为并非如此,而是有其他因素左右了美国的决定。
2012 年5 月至6 月,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办了四次听证,分别就“安全与战略必要性”“军事”“商业与工业”以及整个《公约》举行听证。 美国政界三位代表,即时任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 Clinton)、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Leon Panetta)以及时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都做出了同意美国加入《公约》的意见。 美国军方的六位代表和美国商界的四位代表亦是如此。 美国智库的四位代表,有两位选择同意,两位选择反对。 虽然支持者和反对者两派力量对比悬殊(15 ∶2),但无疑分析反对派才更能找出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来自美国智库代表的两位反对者,一位是美国前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另一位是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的代表史蒂夫·格罗夫斯(Steven Groves)。 他们的观点与受损论并无二致,但他们所代表的政治力量却不得不让人注意。 拉姆斯菲尔德是一名典型的共和党新保守主义代表,他曾代表里根政府(反对加入《公约》)参与《公约》的谈判工作,而格罗夫斯所供职的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则以鲜明的保守主义立场,强调商业自由、美国传统价值和强大国防力量而被世人所熟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加入《公约》已经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选择的问题,其间还掺杂着政党博弈、政治思想等多重因素。 事实上,美国国内就有学者认为,如果当时不是里根而是卡特当选美国总统,美国早已成为《公约》的缔约国之一。①Doug Bandow, “The Law of the Sea Treaty Impeding America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estment ”, Competitive Enterprise Institute,2007, p. 5.各种因素相互交织,这是当下美国关于这一问题的真实写照。
但笔者认为,政党博弈也好,政治思想冲突也罢,这些无非是附着于其上的次要因素,影响美国加入《公约》的核心要素始终是国家利益。在一个短期的时间维度内,政治因素、思想因素或者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对美国“区域”政策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 但放在一个长期的时间维度下,美国的“区域”政策必然会转向更符合其国家利益的一方。
3.2 美国在“区域”开发问题上可能的关注重点
在宏观问题上,我们已经预判了美国有很大可能会重新回归到《公约》体系中,全面参与“区域”的各项事务。 但在具体问题上,我们仍需回答美国在“区域”问题上可能的关注重点是什么。 就当前“区域”各项事务而言,勘探阶段的制度和规则已经基本明确,而开发阶段还有很多具体细节的问题需要博弈,所以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各国讨论的议题都将围绕“区域”开发阶段的诸般事宜展开。 在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美国的关注重点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具体落实。 虽然美国支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但对这一原则在“区域”事务中的落实有不同看法。 尤其是“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求美国实现开发技术和开发收益的分享,这与美国的实际诉求不完全一致。 美国作为世界范围内“区域”勘探开发技术最先进的国家,也是为数不多有条件可以进行“区域”开发的国家,选择开发技术和开发收益的分享对其益处甚少。“区域”开发技术是一个国家的核心机密,关乎国家安全,即便支付合理对价美国也不会全盘托出。 除此之外,在开发利益分享的问题上,如何既保证开发者的利益又保证全人类的利益,是各方势力长期纷争的难点。
第二,“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已经明确“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是美国关切的重点。 直白地说,拥有话语权才可以谋求“区域”利益的最大化。 但在现有表决机制无法改变的前提下,美国想要提高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话语权无非三种途径:其一,以技术分享、利益分享或其他方式,提升己方话语权。 但需说明的是,其中的技术分享肯定不会涉及核心技术,利益分享也不会占开发收益的太多比重。 美国采取此种方式的目的,是以技术支持和物质援助的方式,来换取其他国家的支持。 其二,削弱其他国家在国际海底管理局中的话语权。 其三,将场外因素带入国际海底管理局事务当中。 例如,使用一些政治外交的手段,以期谋得相关国家的妥协或支持。
3.3 美国对《“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立场的预判
随着2015 年《多金属结核探矿和勘探规章》到期,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对“区域”开发事宜作出新的规定。 在这样的形势下,制定一个尽可能地符合绝大多数国家利益的“区域”开发规章尤为必要。 为此,国际海底管理局于2016 年制定了《“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并在2017 年和2018 年接连出台两个版本。①《“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历经三个版本,本文中的均是指2018 年版。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的内容主要聚焦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环境保护领域。 该草案全面细化了环境保护领域的规定,例如草案第27 条就对环境履约保证金做了极为细致的规定。②《“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27 条第2 款规定保证金要反映以下方面可能的所需费用: (a) 提前关闭开发活动,(b) 终止和最终关闭开发活动,以及(c)在关闭后监测和管理残留环境影响;第27 条第3 款规定了可以分期缴纳保证金;第27条第4 款规定了应审查和更新环境履约保证金数额的情形;第27条第5 款规定了审查和更新之后的重新计算并缴存保证金的期限;第27 条第8 款规定了承包者提供环境履约保证金不会限制开发合同为其规定的责任和赔付责任。除此之外,在环境监管执行计划③《“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50 条。和环境责任信托基金④《“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52 条和53 条。等方面亦是如此。 这些条款不仅表明各国深刻意识到开发环节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害,还希望能够通过制度手段维持环境保护工作的运行。 其次,承包者义务。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规定承包者义务主要包括,承包者对海洋环境的保护义务⑤《“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46 条至第56 条。,承包者确保安全、劳动和卫生标准的义务⑥《“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35 条。,承包者缴费的义务⑦《“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八部分。,承包者关闭计划(停止或暂停生产)与关闭后监测的义务等。⑧《“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58 条和59 条。需要指出的是,有关缴费义务的规定在草案的历次版本中由起先的混乱不堪到如今的简洁明确,说明各国在承包者义务上立场逐渐达成一致。⑨目前在承包者缴费义务上,仅有税率等细节问题还留有争议。 参见王勇:“国际海底区域开发规章草案的发展演变与中国的因应”,《当代法学》,2019 年第4 期,第79-93 页。最后,担保国责任。 担保国责任原本就存在于《公约》中。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把担保国的责任范围扩大到国际海底管理局规则和开发合同的条款,但在归责原则和责任范围上没有明确规定。⑩《“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103 条规定:“在不损害第6 条和第22 条规章,以及不损害《公约》第139 条第2款、第153 条第4 款和《公约》附件三第4 条第4 款为承包者规定的义务的普遍性的条件下,为承包者担保的国家应该尤其采取一切必要和适当的措施,以确保其担保的承包者依据《公约》第十一部分、关于执行《公约》第十一部分的协定、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则、规章和程序以及开发合同的条款和条件切实遵守规定。”造成这种现象,盖因各国对担保国在《公约》体系内所承担法律义务的具体标准,担保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方能免除赔偿责任等问题争议较大。⑪张辉:“国际海底区域制度发展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法学论坛》,2011 年第5 期,第91-96 页。具言之,不具备开发能力的国家希望担保国能够承担较重责任,而具备开发能力的国家则持相反观点。
因此,结合《“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主要内容,我们可以对美国未来参与到“区域”开发制度之后的决策做出以下预判。 第一,在环境保护和承包者义务方面,美国不会介入太多。 该部分内容各国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美国国内也多是持支持立场。 第二,在担保国责任上,美国会尽可能减轻担保国责任。 这符合美国作为开发国的基本诉求。 第三,美国在惠益分享的内容上会投入极大精力。 《“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并没有规定惠益分享的内容,但这部分内容却事关“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具体落实。 美国关注的焦点将在该草案应否加入惠益分享的内容,以及如何进行惠益分享等具体问题。
四、对我国的启示
通过前文的论述,我们可以合理预测:美国未来极有可能全面参与到“区域”开发制度当中,并且其关注的重点将主要围绕“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具体落实和“区域”事务中的话语权两项议题。 从对美国的“区域”政策演进和政策预判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4.1 坚持与落实“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虽然国家利益是“区域”政策中至关重要的一环,但如果一味以国家利益为导向,而忽视了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共赢,也只能将自己置于孤立境地,反而不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因此,实现国家利益与合作共赢的双重追求,成为我国未来“区域”政策前进的关键。
长期以来,我国始终主张并坚持“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这一原则契合了兼顾国家利益与合作共赢的目标。 当然,随着中国深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对合理勘探开发及先进技术的需求也会不断提升,这些因素都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一些冲突和担忧。 因此,我们必须结合中国当下的实际情况,消解这些矛盾,具体落实“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
(1)以制度设计打通利益分享与合理开发的隔阂
之所以《公约》要求对“区域”内活动获得的利益实现分享,是因为“区域”资源的所有权和勘探开发权相互分离,呈现出一种二元的结构关系。 换言之,“区域”资源的所有权归属于全人类,投资者的勘探开发权只是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授予合格主体的有限财产权。①Kemal Baslar, The Concept of 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 in International Law, Kluwer Law and Taxation Publishers and Martinus Nijihoff Publishers, 1998, p. 38.因此,出于对所有权对价的支付以及对资源消耗的补偿,“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要求在“区域”的勘探开发上实现利益分享。②吕琪、李志文:“国际海底区域资源开发的利益共享审思”,《学习与探索》,2018 年第8 期,第104-112 页。
但问题在于,利益分享的理论正当性并不能转变成承包者的履行自觉性。 承包者天然地要求资本的增长,而利益分享却是典型的利他行为。 那么,要求承包者自觉服从并支持利益分享本就成了“强人所难”。 所以必须通过制度设计打通两者的隔阂,构建一种既能保证利益分享又能激励承包者合理开发的机制。
而如前文所述,《“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第61 条专门对承包者的激励做了规定,却并未提及惠益分享机制。③法律和技术委员会编写:《“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国际海底管理局,2018 年7 月9 日,https:/ /ran-s3.s3.amazonaws. com/isa. org. jm/s3fs - public/files/documents/isba24 _ltcwp1rev1-ch_0.pdf。其中缘由,不得而知。 但正如中方代表所言:“开发规章制定过程中,单纯地强调深海采矿收益,包括承包者缴纳权益金和年费等,而不讨论其分享问题,在逻辑上是有欠缺的,在结构上也是不完整的,不利于‘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落实。”④“中国代表团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第24 届会上关于开发规章草案框架结构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处,2018 年8 月7 日,http:/ /china-isa.jm.china-embassy.org/chn/hdxx/t1583497.htm。不仅如此,《“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在激励措施上主要依靠财政鼓励,资金的来源又将牵涉多方利益,从而为具体落实平添不少阻碍。
因此在笔者看来,收益与分享是“区域”勘探开发的一体两面,两者都应出现在《“区域”内矿物资源开发规章草案》当中,不能有所偏废。在此基础上,我们首先应当确保国际海底管理局可以通过利益共享机制获得稳定收入,这是国际海底管理局正常运作的前提。 其次,以减免缴费而非财政鼓励的方式实现激励,这样牵扯的利益更少,或许更为妥当。 具体而言,在前端缴费环节上,可以进一步减免申请费和年费,例如申请费可以重新回到25 万美元或者更低;在开发过程中的缴费环节上,可以根据“区域”开发的具体情况调整权利金的缴金比例等等。
(2)以制度手段和开放态度实现技术转让
近年来,虽然我国在深海技术上已经取得了较大进展,但是相对于传统海洋强国仍有诸多不足。 尤其是随着我国“区域”获取能力与活动范围逐步提升,对尖端深海技术的需求愈发强烈,缩短与海洋强国之间的差距已迫在眉睫。因此,良性的技术转让对实现我国深海技术的发展有重要意义。①李志文:“国家管辖外海域遗传资源分配的国际法秩序——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视阈”,《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 年第6 期,第36-45 页。
当然,技术转让并非要求有技术优势的缔约国无偿转让技术,深海技术招标投标活动须遵循诚实信用原则,确保深海技术规范转让、公平合理②林家骏、李志文:“深海技术商业化机制初探”,《太平洋学报》,2018 年第7 期,第35-47 页。,在共同协商的基础之上实现技术转让的商业化。 问题在于,不少尖端技术实际上都掌握在小部分发达国家的手中。 以“区域”基因资源为例,欧盟、日本、挪威、瑞士和美国占据了全球有关“区域”基因资源开发专利申请的90%,而美日德三国更是占据其中的七成左右。③Marjo Vierros, Curtis A. Suttle, Harriet Harden-Davies,Geoff Burton, “Who Owns the Ocean? Policy Issues Surrounding Marine Genetic Resources” ,Limnology and Oceanography Bulletin,Vol.25, No.2, 2016, p.29.这些技术的持有人不仅可能滥用知识产权的保护,且可能据守其交易之优势地位进行交易垄断、独享深海技术等行为。 这就与《公约》力图构建海洋新秩序,避免海洋强国霸占海洋,实现“区域”利益惠益共享的目标截然相反。两者在“区域”内并存适用就必然会产生矛盾。因此,有必要以制度手段缓解这种矛盾局面。具体而言:
第一,提升技术转让的有效性。 技术转让的有效性取决于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条件的限度,也即技术转让的底线。 先进的“区域”技术通常涉及国家机密,所以明确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条件的限度,是进行长期技术转让的先决条件。 为了确保此种限度尽可能的公平公正,可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设立专门的工作组(包括承包者、担保国和利益第三方),对“区域”技术转让和许可的基本条件、技术转让的定价机制等内容进行商议。 不仅如此,鉴于“区域”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主要由各国国内法调整,所以可充分利用各国知识产权法或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制度。 由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世界贸易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国际组织,敦促缔约国在《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框架下完善国内法上强制许可实施的规范。 以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条件的限度为基础,以有差别的保护为区分,以强制许可为屏障。
第二,增强联合企业中技术转让的可操作性。 按照现有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制度安排,联合企业已呈替代保留区之势。④张丹:“关于国际海底区域法律制度的研究——以保留区及平行开发制为中心”,《太平洋学报》,2014 年第3 期,第11-18 页。因此,重新平衡联合企业中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将对后者参与“区域”活动有着重要影响。 其中的关键在于,在联合企业的制度安排中设置技术转让的义务。 需注意的是,这一义务应当是可商议而非强制的,即有意与企业部设立联合企业的国家和实体可以与企业部商议达成技术转让的具体条件。 相应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点:一是应当确保企业部和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联合企业的运作,此为实现技术转让的前提;二是应当明确技术优势方在联合企业中应承担的技术转让的最低责任和义务,这是实现技术转让的保障;三是在联合企业的协议中,可明确以适当的方式激励技术优势方开展技术合作、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等活动。
第三,促进“区域”研究中国际合作的可行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技术转让并非一劳永逸,最可行的方式始终是从根本上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海洋科学技术能力,提升海洋技术的研发水平。 这种“区域”整体研究能力的提升,需要以大规模的国际合作为根基。 但通常,涉及“区域”研究的国际合作宣示意义浓厚,实际的可行性并不充足。 因此,有必要改变这一局面。 具体来说:首先,“区域”研究中的国际合作应有更广阔的视野。 虽然“区域”研究中的国际合作仍是以“区域”为核心内容,但应当从“大海洋”的概念出发,围绕海洋科学、海洋工程、海洋经济和海洋考古等内容展开。 其中的原因在于“区域”的研究并非孤立,而是依托于整个大海洋学科之上。 提升大海洋学科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是“区域”研究的基础,将对“区域”研究起到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其次,充分发挥国际海底管理局、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以及国际海事组织等的效用,由其牵头,不仅从国家层面,更要从民间层面开展多层次的国际合作。 例如,在各国的民间层面展开“区域”知识的宣讲,促进大学间相关学者和学生的交流、访问。 最后,在具体的“区域”国际合作事务中,可以以探矿活动为重心展开具体的合作与援助工作。 探矿环节更加接近于海洋科学研究的性质,不易产生利益纠纷。 以此为切入点强化“区域”研究中的国际合作,相对于技术转让等敏感内容更具可行性。
需要注意的是,一方面,凭借制度的手段确实可以有效地预防技术垄断,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提高技术的转让效率。 另一方面,当我国实现技术升级之后,也需要同样秉持开放的态度,对其他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实现平等对价下的技术转让。 这也是我国坚持贯彻“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的应有之义。
4.2 构建“区域”制度中的引领国地位
不少学者都认为,在“区域”制度中我国应当构建引领国的地位。①参见杨泽伟:“国际海底区域‘开采法典’的制定与中国的应有立场”,《当代法学》,2018 年第2 期,第26-34 页;Michael W. Lodge,“The Common Heritage of Mankind”,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rine and Coastal Law, Vol.27, No.4, 2012, pp.738-740。笔者赞成这一观点。美国加入《公约》并参与到国际海底管理局的各项事务中,可以想见会对我国的引领国地位造成冲击。 这是美国追求“区域”话语权的必然结果。 如何维持我国在“区域”中的引领国地位,与各国合作共赢,成为重要议题。 此处的发力点可以聚焦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技术的引领。 技术的引领是指我国在“区域”勘探开发技术上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提供必要的便利和相应的指导。 我国在实现引领国的技术引领时,应当将技术指导和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努力促进其他相对落后国家的技术能力的提升,以实现其自主研发为核心要务。 我国也可以与其他技术优势国家合作,采取大学之间访学交流等灵活且相对非正式的形式提供技术的支撑。
第二,资金的引领。 资金的引领是指我国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进入“区域”进行勘探和开发活动提供物质上的支持。 多年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直持续向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自愿信托基金捐款。 中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田琦大使亦表示,“今后,中方将继续向国际海底管理局有关基金或项目捐款,支持国际海底事业稳步发展。”②“中国代表团团长、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田琦大使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第24 届会议大会‘秘书长报告’议题下的发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国际海底管理局代表处,2018 年8 月7 日,http:/ /china-isa.jm.china-embassy.org/chn/hdxx/t1583512.htm。
第三,规则的引领。 规则的引领是指我国应坚持并落实“人类共同继承财产”原则,积极参与“区域”规则的制定。 在美国尚未形成明确路线之前,我们需要加快对“区域”相关法律政策的研究,特别是对近年来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出台和即将出台的规章进行仔细研究。 积极主动地在相关问题上发声,在追求合作共赢的同时,也要把握住国家利益的底线,为将来的海洋大国在“区域”问题上的博弈,早做筹谋。
结 语
“区域”规则的制定由勘探事务全面转向开发事务,意味着新一轮规则体系的构建。 “区域”的开发不仅是获得“区域”利益的重中之重,更关乎我国长远的国家利益。 现阶段,我国既是开发阶段的规则推动者,也是深度参与者,并逐步发挥引领国的地位。 但在未来,美国会全面参与到“区域”事务中,势必会打破目前局面。“区域”因其特殊的地位和主要的战略意义,会成为大国交锋的主战场之一,我国必须早做筹谋,力求觅得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