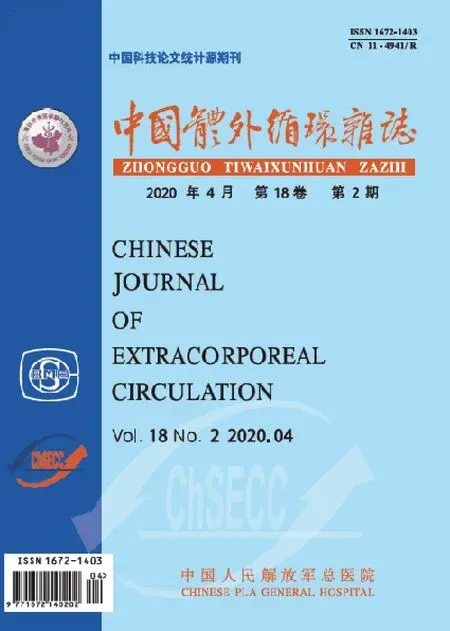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心血管系统表现
高思哲,张巧妮,吉冰洋
自2019年12月初以来,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V-2;也称2019-nCoV)在湖北武汉感染流行并迅速辐射至全国各地,目前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发现感染病例,2月28日起世界卫生组织将其风险级别调至“非常高”。截至2月28日24 时,全国累计确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病例79 251例,现存确诊37 414 例,现存重症病例7 664 例,占20.5%。《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提出临床救治的重点是挽救重症和危重症患者生命,降低死亡率[1]。根据临床资料,目前感染患者轻症偏多,重症患者多因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cute respiratory distress syndrome,ARDS)和感染性休克进展迅速,最终导致多器官功能衰竭,其中心血管系统受累尤其明显。本文总结COVID-19患者心血管系统相关的机制、病理损伤、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查、支持治疗等,探讨SARSCoV-2对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影响以及对COVID-19患者的心脏损害。
1 心血管相关机制
Zhou等人[2]在《自然》杂志中指出SARS-CoV-2 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冠状病毒相似度高达79.5%。与SARS冠状病毒相似,SARS-CoV-2也通过与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ACE2)受体和细胞丝氨酸蛋白酶TMPRSS2结合的刺突蛋白,进入靶细胞[3],因此ACE2可作为干预SARS-CoV-2 传播与致病的靶点。
ACE2是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RAS)重要的调节分子,组织RAS 会参与心、肺、脑、肾、血管等组织重构、炎症反应及组织损伤。ACE2 属于二肽基羧基二肽酶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家族,与人血管紧张素1转换酶具有相当大的同源性,可催化血管紧张素I(Ang I)分裂成血管紧张素1-9(Ang 1-9)和血管紧张素Ⅱ(Ang Ⅱ)分裂成血管舒张剂血管紧张素1-7(Ang 1-7)[4],具有舒张血管、抗炎、抗纤维化、抗细胞增殖等多种生物学活性[5]。
ACE2 在各器官和细胞的特异性表达提示其可能在调节心血管和肾脏功能以及生育方面发挥作用。目前已有报道证明SARS-CoV-2可结合ACE2,造成肝脏细胞、结肠腺细胞、肾脏和睾丸组织的损伤[6-8]。鉴于ACE2在心脏的血管内皮细胞和心肌细胞亦有表达,所以SARS-CoV-2所致心脏损伤也可能与ACE2的信号通路相关。
2 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特殊处理
COVID-19患者中合并既往疾病者比重较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最新发表的纳入44 672名COVID-19患者的横断面调查研究,最常见的前五位合并疾病为高血压(12.8%)、糖尿病(5.3%)、心血管疾病(4.2%)、呼吸道传染病(2.4%)和癌症(0.5%)[9]。
2.1 高血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发表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提示高血压为患者中最常见的基础性疾病,合并高血压的患者共2 683人,占总患患者数的12.8%,死亡患者中有39.7%患有高血压。钟南山团队研究纳入1 009名患者[10],其中165名患者有高血压病史,占15.0%。Wang 等人[11]的研究纳入138名患者,高血压患者占31.2%。合并高血压的COVID-19患者相对病情较重,转入ICU治疗比例较高。钟南山团队[10]的研究中,重症患者中,合并高血压的人数相对更多(23.7%vs.13.4%,P<0.001);Wang 等人[11]的研究中,合并高血压患者转入ICU治疗比例更高(58.3%vs.21.6%,P<0.001)。
目前,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inhibitors,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阻滞剂(angiotensin receptors blocker,ARB)是高血压的一线用药。自2000年发现ACE2以来,其作为一种潜在的降低血压的治疗手段引起了临床医生与研究者极大的兴趣,尤其是用于治疗过量的AngⅡ而导致的血压升高。鉴于ACE2可作为SARSCoV-2的靶点,目前临床上针对COVID-19合并高血压患者的治疗存在争议。在COVID-19患者中,SARS-CoV-2可能通过降低ACE2,激活RAS系统,导致肺损伤。高血压患者ACE2 蛋白表达量降低,应用ACEI/ARB反馈升高ACE2,一方面改善肺部炎症,另一方面导致病毒更易入侵细胞,目前并没有明确研究证明这两种作用哪一种占主导[12-13]。目前临床倾向不在病毒感染到恢复的短时间内应用ACEI/ARB,建议首选钙拮抗剂或直接肾素抑制剂阿利吉仑[14]。
2.2 心血管疾病2月13日,美国心脏病学会[15]就新冠病毒对心脏的影响发布公告,指出心血管病患者为感染新冠病毒的高风险人群。且重症患者中冠心病患者占比较大,死亡率更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病学特征分析》中,4.2%的患者及22.7%的死亡患者患有心血管疾病。Wang 等人的研究中,合并心血管疾病患者转入ICU治疗比例更高(25.0%vs.10.8%,P=0.04)。在最早公开报道的17例死亡患者中,有两名患者合并冠心病。其他早期研究中COVID-19患者患有基础心血管疾病者占2.5%~40%不等[10,16-17]。另外有研究提示,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发生心力衰竭的可能性较高[18],从而增加了死亡或其他终点事件发生率。
对于合并心血管疾病的COVID-19患者,建议继续使用他汀、β受体阻滞剂、阿司匹林等稳定斑块,提供心脏保护;在病毒感染到恢复的短时间内暂停ACEI的使用。
3 重症患者心肌损伤
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COVID-19患者中19%左右会出现呼吸窘迫,转为重症患者。而根据目前有限的临床证据可知,重症患者死亡率可达到50%以上[19]。在SARS和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中均有伴发心肌炎或急性心肌梗死的报道[20-21],也有研究报道SARS患者发生可逆性亚临床舒张性左心室损伤[22]。目前公布的COVID-19患者解剖结果提示其病理特征与SARS和MERS病理特征非常相似,尽管仅心肌间质中观察到少量单核细胞炎性浸润,并无实质损害[23],但这些结果仍然提示需要重视COVID-19患者中出现的心肌损伤。
3.1 临床表现COVID-19部分患者出现心肌损伤,症状无明显特异性,可伴有气短、呼吸困难、胸闷或胸痛等,应注意患者是否出现晕厥症状。而这类患者一般病情较重,转入ICU治疗比例增加。在纳入52名重症患者的研究中,共12名(23%)出现心脏损伤,而28%的死亡患者曾出现过心脏损伤[24]。Wang 等人报道的138名患者中,有10 名患者出现急性心肌损伤,出现心肌损伤的患者转入ICU治疗比例较高(22.2%vs.2.0%,P<0.001)[11]。在最早报道的COVID-19临床特征的研究中,纳入的41名患者中,有5名(12%)患者出现急性心肌损伤,出现心肌损伤患者转入ICU治疗比例较高,有统计学差异(31%vs.4%,P=0.017)[17]。
3.2 诊断COVID-19患者多出现心肌酶谱、肌钙蛋白、肌红蛋白的异常,提示心肌损伤。建议早期监测以上指标,辨别重症患者并早期干预治疗。根据《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相关心肌损伤的临床管理专家建议》[25],新冠肺炎相关心肌损伤的定义为:新型肺炎确诊或疑似患者中,出现心肌损伤标志物[肌钙蛋白(cTnI/cTnT)]升高和/或降低超过第99百分位上限(URL),且无心肌缺血的临床证据,以及可伴B型利钠肽(BNP)或N末端B型利钠肽原(NTproBNP)水平升高。该建议同时提示部分心肌损伤患者的体征往往不具有特异性,窦性心动过速特别是夜间心动过速、心率增快与体温升高不相称(>10次/℃),可作为诊断的重要线索。以下实验室检查可作为心肌损伤诊断的参考:
3.2.1 心肌酶谱COVID-19患者心肌酶普遍升高,以乳酸脱氢酶(lactate dehydrogenase,LDH)升高最为显著,肌酸激酶,肌酸激酶同工酶MB(creatine kinaseMB,CKMB),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aspartate aminotransferase,AST)等均有不同程度升高。Wang 等人的研究中,LDH升高,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为261(182,403)U/L;CKMB的中位数及及四分位间距为14(10,18)U/L,其中转入ICU治疗的患者高于未转入ICU治疗的患者[18(12,35)U/L vs.13(10,14)U/L,P<0.001]。现有研究中LDH升高的患者比例均超过70%,CK 升高的患者比例在13%~33%不等,37%的患者AST 升高[16-17]。因此建议对于COVID-19患者,早期监测心肌酶谱的异常升高,以确定重症病例。
3.2.2 肌钙蛋白COVID-19部分患者出现肌钙蛋白升高。很多中心应用高敏肌钙蛋白I(hs-cTnI)升高判断COVID-19患者是否出现心肌损伤。Wang 等人的研究中,hs-cTnI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为6.4(2.8,18.5)pg/ml,其中转入ICU治疗的患者高于未转入ICU治疗的患者[11.0 (5.6,26.4)pg/ml vs.5.1(2.1,9.8)pg/ml,P=0.004]。Huang 等人的研究中诊断为病毒性心肌损伤的5名患者hs-cTnI持续升高。
3.2.3 肌红蛋白COVID-19部分患者出现肌红蛋白升高。Chen 等人的研究中,肌红蛋白中位数及四分位间距为49.5(32.2,99.8)ng/ml,15例患者(15%)肌红蛋白升高。在一篇纳入28名1个月至17岁的儿童患者的文献中显示,儿科患者也在发病早期出现肌红蛋白升高[26]。
3.3 治疗
3.3.1 一般治疗所有重型患者均应严密监护,可及时给予有效氧疗措施,包括鼻导管、面罩给氧和经鼻高流量氧疗;可使用改善心肌能量代谢的药物改善心肌功能。在呼吸衰竭出现早期,应用呼吸机辅助通气改善肺功能。
3.3.2 体外生命支持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中提出:针对重型、危重型病例的治疗原则包括不同水平的呼吸支持及循环支持,并将体外膜氧合(extracorporeal membrane oxygenation,ECMO)列为严重ARDS患者的挽救治疗。Chen等也肯定了ECMO在儿科患者中的治疗[27]。ECMO是一项高级体外生命支持技术,维持机体循环灌注与氧供平衡,使心肺获得短暂休息的机会以等待其功能恢复。在现有报道中,ECMO均应用于重症患者,于ICU管理,应用率在0.5%~11.5%[10-11,16,24]。目前已有ECMO治疗COVID-19的成功报道[28]。
对于仅存在一般治疗难以纠正的呼吸衰竭的患者,建议使用提供呼吸支持的静脉-静脉(veno-venous,V-V)ECMO模式,推荐指征如下:氧合指数:动脉氧分压/吸入氧浓度(PaO2/FiO2)<50 mm Hg超过3 h;PaO2/FiO2<80 mm Hg 超过6 h;FiO2=1.0,PaO2/FiO2<100 mm Hg;动 脉pH值<7.25且PaCO2>60 mm Hg 超过6 h,且呼吸频率>35次/min;呼吸频率>35次/min时,pH值<7.2且平台压>30 cmH2O[29-30]。
对于以下情况应考虑应用同时提供呼吸循环支持的静脉-动脉(veno-arterial,V-A)ECMO 模式。合并心血管疾病的患者,病情进展期间出现药物治疗难以救治的心源性休克;病情进展迅速的患者,伴随感染性休克、循环衰竭;SARS-CoV-2 所致心肌炎,从而发生急性心衰[31]。
但值得注意的是,COVID-19患者多出现凝血激活现象,凝血检查中可见凝血酶原时间延长,D二聚体增高。因此,可根据凝血检查结果适当调整ECMO抗凝用药。
4 其他心血管系统表现
随着COVID-19确诊患者数量的增多,部分患者就诊时并无发烧、咳嗽等典型呼吸系统症状,仅以心悸、胸闷等心血管系统症状为首发表现[32],提示应重视发病早期的非呼吸系统症状。在一篇纳入137名患者的研究中,以心悸为起始症状的患者占7.3%[18]。
在COVID-19患者中,部分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发生心律失常的患者转入ICU治疗的比例较高。Wang 等人的研究中发现16.7%的患者出现心律失常,出现心律失常患者转入ICU治疗比例较高(44.4%vs.6.9%,P<0.001)。
此外,有研究建议[33]要注意维持患者心率,使其保持一个较高的水平,因为成功出院患者心率高于未出院患者[(98.6±8.8)次/min vs.(88.8±8.2)次/min,P=0.043]。
5 总结
自SARS-CoV-2感染迅速蔓延至全国各地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较大挑战,本文回顾了自疫情发展以来的心血管疾病相关报道,希望为COVID-19患者心血管疾病的管理提供部分信息,然而目前能获取的患者临床资料不足,若建立全国COVID-19危重症患者的治疗分享平台,一线临床工作者及研究人员可通过有效的经验分享,总结临床资料,提高整体救治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