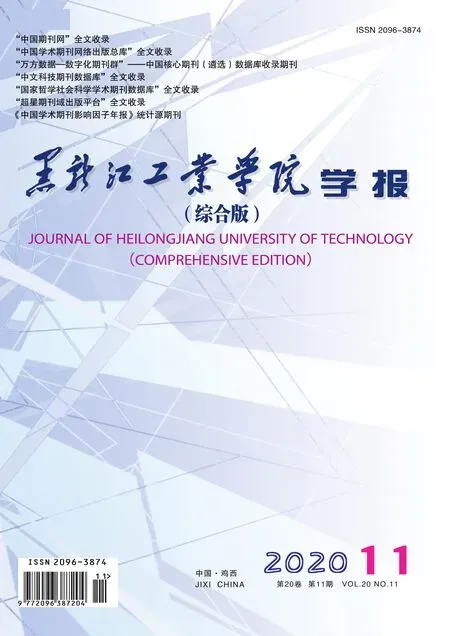命运的隐喻
——神话原型视阈下的《黑暗之心》解读
李梦茹,陈婷婷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000)
在英国作家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的代表作《黑暗之心》中,作者通过老年马洛的口吻,为读者讲述了马洛青年时在非洲的一次航行。在这次旅行中,马洛顺着河流逐渐驶入被殖民者肆意践踏的非洲腹地,亲眼目睹了殖民的罪恶,心境也随着航行的深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其时殖民主义盛行,对物欲的追求大行其道,人的精神世界因此而迷乱,这种迷乱随后带来了内心的疏离与癫狂,而康拉德通过典型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叙述手法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描绘。在文中,作者的叙事手法将他的意图深深地隐藏在其后,不易被发觉,但是同时,他也在文中多次隐秘地使用了宗教和神话原型,这为读者开拓了一条新的理解康拉德意图的道路,即神话原型理论批评。神话原型理论脱胎于文化人类学、分析心理学以及象征哲学。神话原型理论是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对荣格(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集体无意识”理论的发展,在弗莱的理论中,原型是一种典型或重复出现的意象,读者可以通过深入分析文章重复的原型来探索作者意图,而原型中最典型也是最常见的原型就是宗教神话原型。通过神话原型理论批评,对康拉德使用的宗教神话原型进行提取分析,或许从另一个角度探寻作者寄托在文中的意图。
一、隐喻与暗示的原型
康拉德所使用的宗教神话原型可以按照在文中的作用分为两类,第一类来自希腊与北欧神话,这类神话原型是最古老的“集体无意识”产物。自古希腊时期开始,欧洲人便通过文学和艺术作品不断地在意识中复现、加固这种“集体无意识”,康拉德也不能免俗。他在写作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使用了这类神话原型,通过这类神话原型来隐喻和暗示人物和时代的命运。
第二类则来自《圣经》,来自《圣经》的神话原型与来自希腊、北欧神话的神话原型不同,其中天然蕴含着浓厚的宗教色彩。值得注意的是,康拉德本人虽然是天主教徒却不信任何宗教,那么他在文中运用这类神话原型,必然不只是通过宗教隐喻来暗示人物命运、进行宗教隐喻。鉴于他自己对宗教的怀疑态度,康拉德很有可能试图通过这类神话原型来反叛当时不断膨胀的欧洲殖民主义社会,并且表达对非洲原住民的同情。
1.两个女人与命运三女神
在文中,马洛得到任命后便立刻去公司办事处准备相关事宜,他一进入办事处,便见到两个女人,她们“一个胖,一个瘦,坐在草垫子上结着黑绒线”[1]。马洛处理好文件后从候见室走出,再一次注意到了这两个女人,她们“还在一个劲儿地结着绒线”[1],他在这两个女人的注视下感觉浑身不自在,认为她们“一个在引路,不停地把人们引向那未知的世界;另一个则用一双漠不关心的老眼睛,明察秋毫地审视着一张张快活而愚蠢的面孔”[1]。这两个冷漠地编织绒线的女人形象,与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如出一辙。在希腊神话中,人们相信万物的命运由命运三女神莫伊拉(Moirai)掌管。莫伊拉是命运三女神的统称,但实际上她们三个人各自有名字,分别是:克罗索(Clotho)、拉克西斯(Lachésis)和阿特罗波斯(Atropos)。大姐克罗索负责决定万物的未来以及编织代表命运的丝线,她的两位妹妹便负责决定命运丝线的长短和切断丝线。另一种说法则是大姐克罗索负责编织和剪断丝线;二姐拉克西斯负责抽签决定万物的命运;小妹阿特罗波斯负责记录下二姐的签文,她写下的命运永远无法改动。
无独有偶,北欧神话中负责万物命运的神祗也是三位女神,甚至从形象上来说,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与文中的两个女人更加相似。北欧神话中的三位女神分别是乌尔德(Urd),薇尔丹蒂(Verdandi)和诗蔻蒂(Skuld),三位女神分别代表着过去、当下和未来,代表过去的乌尔德面容衰老,代表当下的薇尔丹蒂则正当盛年,代表未来的诗蔻蒂神秘不愿示人。她们负责用一种不断变色的丝线编织一张巨大的命运网,这种丝线的材质像羊毛,当这张网上出现一条自南向北的黑线,那就意味着死亡即将来临。
在马洛的描述中,这两个女人一个年老,一个年轻,年老的女人不断编织绒线,年轻的女人则来回走着给来人引路。她们冷漠而睿智,不断地审视着来往的面孔,似乎洞察一切,与她们只有一面之缘的马洛觉得她们“守卫着那黑暗世界的大门”[1]。显然,这两个女人的形象是糅合了希腊与北欧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的产物。这两个女人所编织的丝线,正如莫伊拉手中的丝线,两个女人一个年老一个年轻,又与乌尔德和薇尔丹蒂的形象类似。最重要的是,这两个女人手中的绒线是黑色的,希腊神话中的女神虽然编织的是丝线,但并没有指明命运之线的颜色,反而北欧神话中特意指出,一旦网中出现了一条黑色的丝线,就代表着死亡的来临。对于马洛来说,这两个女人好像看守着未来命运的大门,她们似乎知道一切到这里来的人的命运,但只是冷眼旁观着一切,也正如两种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冷漠而威严。
康拉德不断通过这两个女人暗示后文中所有人的命运。首先,她们手中的黑色丝线代表着这里所有人的死亡命运,但是这种死亡命运却不一定是肉体上的死亡,比如故事的主人公马洛,他的肉体并没有死亡,但是在亲眼目睹了殖民主义在非洲大陆上的行径后,尤其是在抱着对库尔茨的幻想见到库尔茨本人的所作所为之后,马洛内心的一种天真的理想主义死亡了,欧洲殖民主义在他心中种下的美好幻象也死亡了。其次,只有这两个女人出现也暗示了整片大陆被末日所笼罩。希腊神话中的三位女神往往是年龄相仿的,只有北欧神话中的命运女神有年龄差距,马洛见到的两个女人一个年老一个年轻,正如乌尔德与薇尔丹蒂一个年老一个年轻,但是代表未来的诗蔻蒂却没有出现在她们旁边,作者似乎在借此暗示,此时这片大陆没有未来可言。
2.黑人劳工与西西弗斯
西西弗斯的故事来自古希腊神话,西西弗斯目睹了宙斯掳走河神阿索波斯的女儿埃癸娜,失去女儿的父亲四处寻找线索,西西弗斯便以为科林斯城堡供水为条件向河神道明宙斯抓走了他的女儿。宙斯一怒之下宣判西西弗斯死刑,但是西西弗斯先绑架了死神,导致世间没有了死亡,随后又欺骗了冥王哈德斯。于是哈德斯被西西弗斯激怒,判处他每日去冥界那边的高山下推一块巨石,但是每当他即将把巨石推上山顶,石头又会自动滚落山脚,让西西弗斯永远重复这件无效又无望的劳动。
在文中,马洛在航行中经过了公司的贸易站,他看到好多黑人在那劳动。马洛说他们在修铁路,他看到“一群黑人在奔跑。一声重重的、沉闷的巨响把地面震动了一下,一股烟从峭壁上冒出来,如此而已,山崖的外表上没显出什么变化”[1]。虽然这群黑人如此兴师动众地大修土木,但是他们所炸的峭壁却并不挡路或是妨碍什么。他看到黑人排成一行往山上走,他们的眼睛木然无神,从他身边擦过,却望也没望他一眼。随后马洛又经过一个洞穴,他认为“它仅仅是一个洞穴而已……是要给那些犯人找点事干”[1]。从马洛的印象中可以看出来,殖民主义者迫使原住民成为劳工,又让他们在这片大陆上做似乎无用又无尽的工作,他们炸不碍事的峭壁,他们挖没有用的大洞,在日复一日的无用劳动和虐待中,黑人们失去了眼中的神采,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眼神木然的“黑色东西般的人形”[1]。
在荷马的观念里,西西弗斯是蒙冤的英雄。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在《西西弗神话》中提到“如果相信荷马的说法,西西弗斯就是最聪明、最谨慎的人”[2],但是最聪明最谨慎的西西弗斯也仅仅因为道出真相就被强权判处无尽无效的苦力。康拉德以西西弗斯和天神的关系来隐喻被奴役的黑人和殖民主义者,黑人没有逃过不公平的审判,被判处日复一日为审判者做无用的工作。在康拉德的隐喻中,黑人与白人的关系极其不平等,黑人恰如凡人西西弗斯,而白人却凭借着高度的社会化和高度的工业化带来的坚船利炮凌驾于黑人之上,正如拥有神力的天神对凡人的随意支配。在非洲这片大陆上,马洛所见到的黑人以及其他所有被奴役的黑人正如西西弗斯,即使再聪明、再谨慎,也只是任由“天神”鱼肉的凡人,抵挡不住来自白人“神权”的压迫,只能任由他们驱使,整日做无效无尽的苦力工作。同时,这一点也暗示着库尔茨在这片土地上的所作所为。
希腊神话是人的神话,讲述人的命运也赞扬人面对命运时不卑不亢的态度。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是命运的受害者,也是命运的承担者,但是同样的,西西弗斯也是生活的英雄,他的英雄特征在于看透了命运的荒诞本质仍然以积极的心态看待这种无意义的荒诞。康拉德笔下的非洲原住民在对待命运这一点上正如西西弗斯,也如希腊神话中的主人公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掳掠和奴役,他们面对命运,接受命运,承担命运,在痛苦而无意义的人生中仍然坚持面对生活,并且坚毅地坚持自我,用西西弗斯来隐喻黑人劳工隐含着对非洲原住民坚毅性格的肯定。
二、抵抗与反叛的原型
康拉德自己虽然从小是天主教徒,但却是坚定的无神论者,只相信自然的康拉德不相信任何宗教,也认为超自然现象是迷信。但是康拉德虽然不信宗教,却仍然在文中使用宗教神话原型来表达自己的意图,这本身就是康拉德想要表现的一种讽刺。
在小说的结尾,马洛午夜追寻库尔茨进入了一个黑人的仪式。在那里,他看到“一个黑色的身躯站起来,迈开两条黑长腿,甩着两只黑长胳膊,正打熊熊的火光前走过。他头上有一双角——是羚羊的角”[1]。第二天的中午,他又看到了那群人,他们“点着他们有角的头,摇晃着他们红色的身体”[1],“他们一阵阵有规律地齐声喊出一串串令人迷惑不解的话语,完全不像是人类语言的声音,而那突然被此喊声打断的这群人低沉的阵阵喃喃声,则好像是在应和着某种邪恶的祈祷。”[1]
羊角这一特征显示了康拉德在此处将撒旦作为这些人的神话原型。撒旦是《圣经》中的经典恶魔形象,他因想要与耶和华同等而反叛他,最后成为堕天使。在基督教世界中,撒旦是极度邪恶的恶魔,他对人和上帝做了最大的恶行,化身成古蛇引诱亚当和夏娃吃了禁果,才导致上帝对人类失望,将人类逐出伊甸园。在随后的复现和演绎中,撒旦也逐渐拥有了专属的标志和符号——羊角。
康拉德使这些参加仪式的黑人头上戴着羊角,在他们身上隐喻撒旦的形象,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康拉德认为这些黑人是邪恶的。
在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长诗《失乐园》中,对撒旦这个形象进行了重新审视。弥尔顿不再把撒旦看作刻板单薄的恶魔形象,而在诗中赋予了撒旦革命精神和英雄气质。在《失乐园》中,撒旦因不满上帝的专横狭隘而发起革命,他成为了追求自由和平等的英雄。康拉德在塑造仪式中的人物时显然也借鉴了这层意思。参与仪式的都是黑人,在白人殖民者眼中,他们是不开化、没有信仰的,他们头戴羊角举行仪式,似乎是康拉德特意设置的讽刺。不开化、没有信仰的黑人无意中选择以殖民者社会中最恐怖、最令人厌恶的撒旦形象举行狂欢仪式。这种形象和仪式反映了康拉德对宗教的怀疑与嘲讽,同时也体现了他对殖民主义者罪恶行径的反对。与此同时,康拉德对黑人作此隐喻就意味着他为白人殖民者设置的身份是站在撒旦对立面的上帝,上帝被撒旦挑战,这亦是对高高在上的白人在黑人面前自诩为神的嘲讽。
结语
康拉德在《黑暗之心》中多次隐秘地使用宗教神话原型,实际上就是将自己的隐含意图藏在其中。通过对文章进行神话原型理论解读,康拉德的态度与意图也就被完整地剥离出来了。康拉德对非洲这片土地的悲剧怀有怜悯之情,他认为此时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已经是一片死地,完全笼罩在末日的氛围下,所以他用命运三女神的原型来暗示其命运,同时,他也用西西弗斯的原型来表达对非洲原住民的同情和认同,他认为他们是直面命运的人。同时,他同情黑人,反对白人对黑人所作的一切高高在上的行径。他通过撒旦的隐喻表达自己的对白人殖民者的反对和嘲讽,同时希望黑人能够像撒旦一样反抗自诩为上帝的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