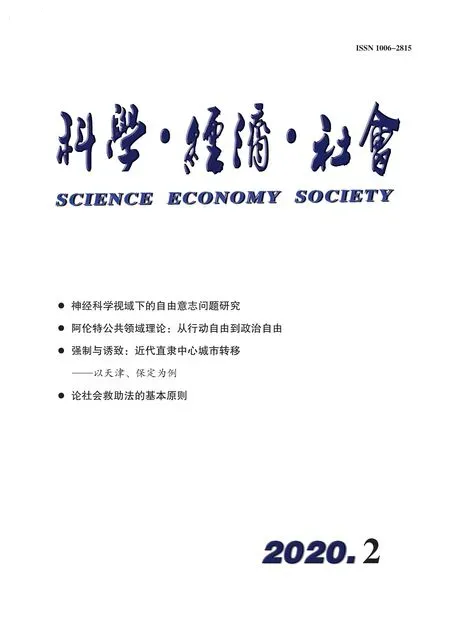文化古城时期北平都市变迁下的人文、世情与都市想象
王安乐
(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
一、“文化古城”与北平人文空间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将1928年6月北洋政府垮台到1937年7月“七七事变”后国民党部队撤出北平,这段时间定义为北京“文化古城”时期。
“文化古城”这个词语,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对北京的一种侧重称谓。其时间上限是1928年6月初,从盘踞在北京的北洋政府最后一位实权者张作霖及其国务总理潘复逃出北京开始;其时间下限是1937年7月“七七事变”之后,宋哲元率其部属撤离,北平沦陷为止。中间十年时间,中国政府南迁南京,北京改名“北平”。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等中心均已移到江南,北京只剩下明、清两代500多年的宫殿、陵墓和一大群教员、教授、文化人,以及一大群代表封建传统文化的老先生们,另外就是许多所大、中、小学,以及公园、图书馆、名胜古迹、琉璃厂的书肆、古玩铺等等,这些对中外人士、全国学子,还有强大的吸引力……凡此等等,这就是“文化古城”得名的特征。[1]
邓云乡先生所言的“文化古城”,是北京建城史中一段特殊的时期。它的特殊性首先体现为中心政治的抽离,北京自明永乐帝奠定的政治中心的格局被打破。政治因素的骤然抽离,对于北平而言是一大都市变迁,它迫使北平在经济上寻求城市发展的新起点,深刻改变了北平的经济面貌和居民生存境况。其次,体现为文化结构的重组。长期以来,北京一直以来是官的中心,不论是在帝国时期还是在民国初期,北京皆是一座大官场。基于此,北京发展出以统治贵族和上层精英为中心的官场文化和攀附性质的市井文化,这两种文化都是由政治因素驱动的,是一种有分明等级性质的文化结构。其文化结构的顶层,是一种以传统文化为基调的有闲阶级“雅”文化。其文化结构的底层则是一种在身份认同和等级制度下,以附雅为文化基调的平民阶级“俗”文化,这种俗文化因其侍奉于政治精英,却也沾染了官气和雅气。1928年,随着南方的北伐军队到来,“文化古城”北平得益于外来政治力量的冲击,将旧有的文化结构冲击破碎,这些旧有文化的碎片,却没有如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所言的“博物馆化”(1)参见(美)约瑟夫·列文森著. 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它们并没有因为旧有文化结构的瓦解,而完全成为历史遗迹,而是与新文化一道融进城市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也不像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提出的“发明传统”概念那样隐秘于仪式和风俗之后,转化成符合现代文化审美的要素。(2)参见(英)E.霍布斯鲍姆(E. J. Hobsbawn),(英)T.兰格(Terence Ranger)著;顾杭,庞冠群译. 传统的发明[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4.“文化古城”北平在重组自身文化结构之时,非但没有拒斥和隐藏旧文化的碎片,反而通过“传统回收”的方式,将旧有文化的碎片重新利用到城市现代文化的重组进程中,形成了以文人精英文化为雅,以平民市井文化为俗,以传统文化为审美情趣,以现代文化为进步诉求的雅俗共赏、新旧共存的文化格局,造就了专属于“文化古城”的独特的北平文化,这种文化被后世一再寻味,或被称为“老北京文化”“京派文化”“京味文化”…,都足以证明北平在文化结构自由整合期所孕育出的“文化古城”文化的独特韵味和鲜活生命力。对于当时的文人而言,北平独特的文化结构,构建了一种理想的城市人文空间。
这种理想的人文空间首先体现在传统文化氛围的保留上。得益于文化精英和底层市民对北平传统文化的自觉维护,北平虽然一度处于被革新的边缘,最终却没有彻底走出传统文化,在民国各大城市中,一直是传统文化的中心城市。董玥在《民国北京城:历史与怀旧》中曾详细考察了北平在城市发展中,是如何在交通、地名和空间规划中,新旧冲突并相互妥协的,即使小到一条胡同的命名,新文化的意图也不能顺利进行。(3)参见董玥著. 民国北京城 历史与怀旧[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这种在革新年代的保守城市文化,虽然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现代化进程,却也保存了北平文化的传统特色,成为“文化古城”时期北平强大吸引力的文化源泉。如果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大地上,找出最具特色和代表性的两座城市,那一定是上海和北平。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资本主义文明便扎根于此,并将其建造成中国独占鳌头的现代性大都会,它承载着国家现代文明的未来,是当之无愧的现代文明中心;北平,自从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它的名字更改后,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的北平,承载着传统文化的过去,成为寻根觅源的文化古城。许多人正是抱着一种文化寻根的心态,游历到北平,并扎根于北平。
“文化古城”北平的传统文化氛围混合着迟暮的历史感与安闲的现实感,给多数初来者留下的心理底色并非是鲜亮的,却能令人沉静下来。钱歌川第一次来到北平,他带着宫殿楼阁和北国风光的热烈想象走下火车,第一时间感受到的却是北平的“冷静”:“我从来没有到过一个车站有北平车站那样肃静……我们一到北平,火车进行中那种辘辘声一停,一切都静寂了。”他如梦中惊醒一样环顾四周,“全站都在半静止状态中,稀疏的旅客从容不迫地在前走,几肩行李跟在后面。没有一个小贩,没有一声叫唤”。当他出了车站,走在王府井大街,看到行人安闲的步调,又目睹中山公园里的人专心地打太极的场景,他不禁感叹:“北平有一点像伦敦,就在这些地方。这当然不仅车站为然,整个的北平,也都是这般沉静的。所以北平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沉静”。[2]姚克第一次来到北平,他之前对北平的想象建立在一套彩色风景片上:“一队黄得可爱的骆驼沿着雄伟的城墙走。”[3]姚克在脑海中构建出的北平是边塞与皇城的雄伟都城。当他同样沿着王府井大街走,遇到的却是六只满身煤灰的风尘仆仆的运煤驼队,这显然与他的北平边塞风光的想象截然不同。他沿长安街继续走,看到的宫墙楼宇也都是灰败的,连皇城紫禁城在他眼里都是一幅颓败景象:“从天安门口进去向北,就是所谓的紫禁城,若向南蹓跶去则可以一直到前门。但无论向北向南,在眼前展开的只是一种颓废的景象。所看见的东西——甚至脚下踏着的一块破石板——都能告诉你它从前的伟大;惟其知道它从前的伟大,所以更觉得它现在没落得可哀。不错,北平的一切都在没落!”[4]姚克感受到的正是北平独有的迟暮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带给文人的感受除了颓败,更是一种对过往历史的幽思。1930年秋,钱穆从南方来到北平任教,正是在北平富有历史幽思的文化氛围里,钱穆撰写成多部学术著作,直到晚年还对北平的文化氛围念念不忘:“其时余寓南池子汤锡予家,距太庙最近。庙侧有参天古柏两百株,散布一大草坪上,景色幽蒨。北部隔一御沟,即面对故宫之围墙。草坪上设有茶座,而游客甚稀。茶座侍者与余相稔,为余择一佳处,一藤椅,一小茶几,泡一壶茶。余去,或漫步,或偃卧,发思古幽情,一若惟此最相宜。余于午后去,必薄暮始归。先于开学前在此三五天,反复思索,通史全部课程纲要始获写定。”[5]北平特有的历史氛围利于学者潜心研究,大好局面一旦被破坏再也没能恢复,钱穆晚年无限感慨道:“诚使时局和平,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而惜乎抗战军兴,已迫不及待矣。良可慨也。”[6]除了学术环境的适宜,钱穆体会到他在南方未曾有过的安闲感:“余初来北方,入冬,寝室有火垆。垆上放一水壶, 桌上放一茶杯,水沸,则泡浓茶一杯饮之。又沸,则又泡。深夜弗思睡,安乐之味,初所未尝。”[7]钱穆初来北平所感受到的“安乐之味”,专属于知识阶层,北平的残败和贫困与他们无关,正如徐訏所言:“除非不是知识阶级,北平是一个离开了使人想念,居住着使人留恋的地方!”[8]
“文化古城”时期北平理想的人文空间也体现在对新文化的接纳上。对于文人而言,北平有毫不逊色于上海的新型言论空间,现代技术条件和经营模式下的出版业为文化古城注入了新文化的新鲜血液。北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新文化出版中心,就新文学而言,北平文艺出版物之多,与当时全国的出版中心上海比起来,也毫不逊色。
沈从文在1926年发表的《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中,曾对北京的文艺出版物做过详实的考察。这篇文章作于沈从文北京大学图书馆进修期间,在1925年的11月份到1926年的2月份沈从文在北大图书馆师从袁同礼学习图书馆专业知识。加之沈从文来京之后就一直潜心于京师图书馆,后工作于香山幼慈院图书馆,他对时下刊物具备相当的了解和专业考察。他在文章中指出“即以文艺刊物论,近数年来,略一纪之,亦不下五十余种。”[9]其中,文学副刊至少有五种,有《晨报副刊》《京报副刊》《国民新报副刊》《民报副刊》和《民国日报副刊》。这些大报往往还设有旬刊,如晨报就有《艺林旬刊》《文学旬刊》等,京报曾设有《文学周刊》《民众文艺》《莽原》等。影响力大且持续的文艺刊物如《语丝》《沉钟》《现代评论》,到了30年代更是涌现出诸如《文学季刊》《水星》《学文》等文学刊物。一些存在时间较短但影响深远的文艺刊物如开创京派文风的《骆驼草》;30年代出版两期,1943年又复刊的《文学评论》;朱光潜主编的,战前只出版了四期,发行量每期高达近两万册的《文学杂志》等。此外还有一大批以学院为依托的文艺刊物如《燕大周刊》《清华文艺季(旬)刊》《平大文学周刊》等,不胜枚举。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平),在众多文艺报刊的出现背后,实则是文艺繁荣的景象。这些文学报刊有几个特点,第一,以新闻业为依托的文学副刊影响最为持续和深广,当时几大报社如晨报、京报、大公报、益世报等为了吸引读者,增加报刊格调和趣味性,纷纷增设副刊,虽然多是一些不起眼的“报屁股”,却于文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第二,期刊是以书局为支持,同人或学生团体为基础办起来的。书局更多承担的是期刊经销商的职能,从校对到版式再到印务都是由同人组成的编委会负责,经销商也会根据期刊销量决定期刊是否存续或扩版。如《文学季刊》注明发行者是立达书局,发行人为张道一,这个立达书局就是当时位于北平王府井大街53号的一家经销书店,当时的许多书店也兼营出版图书,书店负责人往往会联系有影响力的文人,让他牵头组成编委会。由于《文学季刊》销路很好,书商们眼红,文华书局就联系《文学季刊》编委会另外出了一本期刊《水星》,所以文季和水星两者是同一个编委。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一份文学期刊的核心是编委,而资金来源是书局。这种文学和市场双重属性下的刊物,在当时很普遍。当然也有纯粹的同人刊物,比如《骆驼草》,这份杂志是完全由周作人、徐祖正等骆驼同人提供资金支持的,由废名负责编务,冯至负责印务和发行。类似这种完全依靠同人社团支撑的刊物,大部分都因为资金问题而寿命不长。第三,一份文学报刊背后必有一个文学编委,而这种团体性质的编委往往形成一个文学团体,可以说文学报刊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派别的一个重要依托实体。围绕这份报刊,形成一个文学场域,那么许多文学报刊,就构成了一个以城市文化为基调,各有特点又具有大致一致性的都市文学公共空间,文学史上著名的“京派”“语丝派”“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等皆诞生于此。可以说,报刊在传播功能上的空间属性,为中国现代文学提供了内部空间结构,孕育了不同风格和价值取向的文学流派,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文学流派所以诞生和繁荣的母体。
“文化古城”时期的北平既保留了传统文化氛围,又接纳了新文化的诸多要素,营造了一种传统与现代并行不悖的理想人文空间,正如邓云乡所言:“文化古城在环境和气氛上为人们提供了足够的条件,有各层次的最好的学校可供学习,有数不清的足以代表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可供师承,有上千年的古迹名胜,几百年的前朝宫苑文物可供凭吊、观摩、研究,有古木参天的著名公园可供休息、游览、思索,有大图书馆可供阅览,有数不清的书铺可供买书,有世界水平的大医院提供治疗,有极好的饭馆、烹饪可供饮馔,有极安静爽朗的四合院可供居住,有极方便的交通,有极低廉的生活,冬天有足够廉价的煤,夏天有极便宜的冰……这一切还不算,还有极和谐的人际关系,极敦厚的风俗人情,一声“您”、一声“劳驾”、一声“借光”……代表了无限的受文化熏陶过的人情味。”[10]
二、“文化古城”的政治变迁与都市想象
民国时期的北京,曾是全国的政治中心,但在国民政府成立,中央政权迁往南京后,北京因丧失了政治中心的地位,在全国的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
1928年的6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顺利开进北京城(4)部分著作将国民革命军入驻北京城的时间定为1928年6月8日,但根据《申报》1928年6月6日第四版《晋军即入北京城》:“晋军徐永昌、商震、谭庆林等部已及西直门等门附近,今夜明晨即入城(五日)”“昨尹扶一、孔繁蔚与奉方代表刑士廉同谒王士珍,因阎来电,奉军既和平退出,国军决以和平方法入京(五日下午三点)”又据《申报》6月10日第四版《晋军入北京之前后》:“鲍毓麟旅已准备由齐化门出京,七日晨一时鲍旅半部出城。(七日),七日子刻,谭庆林部抵西直门,秩序甚整。(七日下午九点)”《大公报》6月9日第二版,《第三集团部队入北京》:“已入北京城内之晋军、立赴各主要城门把手、此次晋军进城,系南京政府命令,其原驻城内之鲍毓麟旅,因与入城之晋军之间成立谅解,于七日夜中已撤退,徐永昌军八日早晨已陆续入城。市面迄今平稳,韩复渠军截止七日止到约三万,全驻南苑。”可见国民革命军本欲五日夜或六日清晨直接入城,经由王士珍主持的“北京治安维持会”中间协商,6月6日就任京津卫戍总司令的阎锡山决定和平入城,第三集团军谭庆林部于6月7日凌晨与北京保卫团实现换防,8日凌晨部队陆续进城。期间冯玉祥、韩复渠等部队都驻扎在京郊,严令不得入城。第三集团军进驻时间确切应为6月7日凌晨,接管北京防务算起。,南京国民政府入主北京,北伐基本上取得成功。在第二天, 6月8日的《大公报》上,头版发表了社评《五百零七年之北京》,这篇社评将北京的建都史设定在明永乐十九年,即公元1421年,在这往后的507年里,北京作为中华帝国的首都,帝都的历史从未间断过,但此时北京的地位发生了动摇。
“今者以南京为首都之国民革命军入京,北京首都之地位,事实上遂暂告废止。即单就历史眼光论,民国十七年六月七日党军之入京,诚可特记之一大事也。”[11]
这篇几乎是第一时间发表的社评,代表了社会间大多数人对北京城命运的判断:明成祖开启的帝都历史将随着南方政权的入主而宣告终结。虽然《大公报》的社论将尚未实行的迁都的预期,与日本之迁都东京、俄国迁都圣彼得堡、土耳其迁都安哥拉相对比,将迁都之举誉为国家大兴革时的举措,并解释中国之所以主张迁都,“原因于外交束缚,积习腐败,而思藉以解脱,以资刷新。”[12]但还是近乎无望地为北京国都地位进行辩护:“虽然,中国首都问题,是否因此简单理由,改迁南京,自尚有待于国民会议之解决。吾人之意,卜都建国,为义甚广。地理关系、历史关系,顾属当然。而于今后建设国家事业之大方针,亦须积极着想。若果国民会议,认为北京较为相宜,或南京北京之尚有适宜之地,均无不可。不可拘泥成见,为一都北京,外交束缚,便无法解脱;积习腐败,便无法刷新也。何以言之,吾人当认定今后之中国,为新中国。无论何地,外交束缚,皆应求解脱;积习腐败,皆应力予刷新。岂仅北京一城,则又何必小之乎专以北京为虑哉!”[13]
说理固然正确,却是无用。国民政府的政治根基在江浙,根本不会迁到北京,国都南迁是北京城的历史命运。似乎作为印证,就在国民革命军即将入驻北京城之际,国民政府常委会决议将南京城门改为更符合革命意志和首都愿景的名称:仪凤门改称兴中门、正阳门改称光华门、聚宝门改称中华门、神策门改称和平门、丰润门改称玄武门、朝阳门改称中山门、海陵门改称挹江门。[14]果然,在和平进入北京城20天后,南京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七十四次会议,会中通过了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局会议的决议,依照内政部所提交的“京兆直隶区域名称问题办法”,将北京改为北平,设立北平特别市。(5)1928年6月26日上午9时至下午2时,在南京本府举办的国民政府委员会第七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决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咨开,关于京兆、直隶区域名称问题,经本会议第一四五次会议决议:(一)直隶省改名河北省。(二)旧京兆区各县,并入河北省。(三)北京改名北平。(四)北平、天津为特别市,请查照办理。决议:照办。”会议同时还决定:“所有与北平相关联之各旧有名称,用京字者,一律改为平字”。参见洪喜美编《国民政府委员会会议记录汇编》卷二,国史馆, 1999年,320页、324页.北京至此丧失国都地位,易都之举成为既定事实。正如刘半农所感:“自从去年六月北伐完成,青天白日旗的光辉照耀到了此土以后,北京已变做了北平, ‘京’的资格已变做了 ‘旧京’了。”[15]北京变成北平,成了“旧京”。
在既成迁都事实面前,难言迁都之实的失落境况,大概占据了当时很多人的心境。一方面,国家基本上实现南北统一,北人心怀对南方政权救国图强的希冀,另一方面又隐含政权更迭、国都易址的黍离之悲。国都地位丧失,使得长期作为政治中心的北平,一时间丧失了城市赖以繁荣的政治基础。北平一度迷失了城市身份和发展定位,面临着城市空间转型的艰难困境,由此引发了忧时之士关于北平未来发展和都市空间面貌的群言献策。根据时人观察,北平“自国都南迁,市民生活遽失依据,凡百营业,莫不凋敝,市况日趋萧条,忧时之士,群思有以繁荣之,于是繁荣平市计划,报纸日有记载,惟见智见仁,各有不同,所拟计划,亦各不同……”[16]这些报刊所载的市政评议性文章,隐含着北平城在革新之际,人们对城市的都市想象,这些饶有兴味的都市想象,在现实语境下,折射着北京曾经拥有过的想象性和可能性。
1929年元旦,是北平作为故都的第一个元旦。这一天,北平的各大报纸在显要的位置,刊载了蒋介石元旦告国民书,蒋在第一次面向全国国民的元旦献词中,表达了对刚刚实现统一的国家,在未来内部建设、邦交正常化等方面的期望与劝勉,他以一种坚毅的领袖口吻,向全体国民宣告了全国业已统一,下一阶段国家将进入建设阶段,并以“救国之道,惟在吾人自强不息”,劝勉大家投身到国家的建设中。
就在当天,北平国民党的机关报《华北日报》创刊,在创刊号上刊载了《新年献词》,文章借一名关心北平社会状况的革命军人的名义,向民众解释了北平成为废都后,无法在短时间内建设繁荣的根本原因:“北平只有无其数坐而消费的阔人,从没有大规模的生产组织…号称百万的市民,除了商人,几乎不是官,就是差,”北平迁都后“颓废的现象,只是它本身的病态几百年宿疾的表现,社会组织自身的崩溃。”,报社呼吁北平的知识阶级“对于当今青年政府一切的措施,应以同情与诚意的态度,积极与建设的精神,作严重的批评,与适宜的赞助。”[17]国家领袖和北平的党报以一种开明的姿态,呼吁知识阶层积极为建设国家出谋划策,全国统一的第一个元旦正是在这种建设氛围中开启。
北平另一份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报纸《京报》,也于当天复刊。《京报》在复刊号上,转载了这篇献词,并在《华北日报》新年献词的感召下,连续刊载了北平市工务局局长华南圭的《北平市政之症候》(1929年1月1日增刊第四版)、北平市卫生部长薛笃弼的《薛笃弼谈卫生设施》(1929年1月9日第五版)、市民贞白的《新年后市府应该做的事》(1929年1月7日第八版)等系列文章,对北平现在的问题和未来城市发展建言献策。随后《华北日报》推出了专门针对评议北平市政和研究城市发展问题的副刊《市政问题周刊》,并在北平市政府的支持下,以此副刊为平台,成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市政问题研究会”,出版了专业刊物《市政评论》,发行区域遍及全国。在官方鼓励、大型报刊的舆论引导下,对北平的重建问题成为当时的热门话题,从众多的评议市政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政治变迁背景下,不同阶层的智识分子,根据自己对北平现状的观察,描绘出对北平这座故都的都市想象,这些都市想象,表达了人们对构建和谐都市空间的生活理想和一种尊重历史的人文情怀。
市政管理者和市政研究者将目光聚焦到北平都市物理空间的发展规划方面,他们的观察展现了一种基于对北平城市发展历史和现状问题的分析,进而提出合理的城市空间规划和城市发展定位的意见。
研究者着眼于北平的历史和现状,分析城市发展优劣势,以确定因地制宜的发展长策。在一篇有见地的分析文章中,作者指出,北平的地理位置不适合发展工商业,北平虽然有北宁、平津、平绥、平浦等多条铁路通过,但其交通枢纽在丰台,人流货物可不经北平城直接由丰台转输。北平的特殊性在于历史文化的关系,北平有国内最为发达的教育系统,有规模宏大的历史遗迹,更有令人羡慕的文化氛围。正是基于北平自身的发展条件,作者呼吁政府将北平的城市定位,定义为文化中心、教育中心和游览区,最终发展成“岌然立于世界为一有名之文化市。”[18]这种意见,将北平发展为文化区、教育区和游览区,而非继续作为华北政治中心或发展成工商业区,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在一些更具变革城市魄力的文章中,评议者提出了详实的意见,以图通过改造北平客观条件,达成人们对城市发展的主观意图。在一篇分析北平发展劣势并提出改造计划的文章中,作者针对北平城市发展的“先天不足”,提出改造地理位置限制、革新历史政区、维持社会经济设施三点意见。在著者的都市想象中,为了弥补北平地理位置的限制,著者构建了规模宏大的铁路系统:修筑“张库铁路”,使北平的城市辐射能到达边境贸易重镇库伦,并借此条铁路联通西伯利亚铁路,近一步与欧洲相连,以此连接欧洲和北亚;延长“平绥铁路”,连接伊犁,并借此与印度和中亚的欧亚铁路相连,以此连接欧洲与中亚、南亚,使得不走海路即可到达中国,[19]如此北平便成为欧亚交通枢纽。文章作者提出的设想,如今已成为现实,基本吻合于第一、第二欧亚大陆桥的路线,但在当时,确实是想象过于宏大的计划。更遑论作者还提出通过架桥通过白令海峡,连接美洲,使北平成为欧美亚三大洲的中心地,成为世界第一重镇的设想。基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在著者的想象中,北平应发挥传统文化中心城市的地位,改变原本由政治主导的政区划分,将北平划分为工业区、文化区和游览区。北平是文教中心和数百年的帝都,教育产业和旅游产业为北平市带来巨大收入,著者呼吁中央政府将北平市定位为全国考试中心,并呼吁市政修缮古迹,加强宣传,吸引中外游客。工业区则是藉由铁路的带动作用,辅以免税的政策,可以振兴北平传统的景泰蓝、雕刻、纱灯和地毯等手工业,同时也联通了西北羊毛产地,将北平传统工艺和现代机器结合,发展毛织产业。此外,半官方性质的市政研究组织“市政问题研究会”主席殷体扬在题为《田园都市理想与实施》的文章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田园都市的理论,在他的想象中,理想的北平应该“富于山野树林之胜景,四周之光景与风土求其适于劳动者之健康与卫生,更设置公会堂,俱乐部,美术馆等。奖励趣味高尚之娱乐,并使劳动者之子女,从年幼之时,得有机会与自然之美相接近,以养成田园生活之趣味。”[20]不唯如此,随着新任北平市长袁良的上任,政府将城市建设的重心转移到修复北平市名胜,吸引外国游览者的“观光北平”方向,晨报甚至刊出了《应使北平成为世界公园》的社论。(6)见《市政评论》1934年第2卷第10期转载。
这些市政评论的文章,与其说是为市政政策提供参考,倒不如说是一种美好的都市想象,构建这些想象的作者们,虽然对北平的历史和未来有清楚的了解和美好的期望,但在他们长远的眼光之下,缺乏对现实的短视,有些设想在如今看来,依旧是尚未实现的都市理想。在四郊多垒,民生凋敝的民国北平历史境况下,如此多的宏大而美好的都市想象,除了映证了学者董玥所提出的,“这些讨论反映出一种与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完全悖离的对待过往历史与帝制空间秩序的态度”[21],这种城市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性与现代性交融相织、界限模糊的学术论点,同时它也能反映,在北平选择城市现代化方向的历史节点,北平的知识阶层对优秀传统文化内核的自信和对现代化所能带给城市发展的外部动力的乐观心态,这种文化古城时期的文化上的自信与乐观的心态随着时局的变化,很快如烟散去,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政治中心的南迁虽然瓦解了北平以政治为主架的内部空间结构,却也重组了北平新的社会空间结构,给北平以重新平衡政治空间与文化结构关系的机遇。学者杨卫东在《城市季风:北京和上海的文化精神》中,将国都时代的北京视为一个“围绕政治权力轴心而组织运转的、官气弥漫的大官场”,他将在这个大官场中市民结构总结为“官、知、民”三层相互依附的递垒式结构。政治中心南迁,北平成了“王气黯然的古都”,“宽厚温柔、和平幽默的民气却在上升,弥漫着文化古城萧散悠远的韵致”[22],“知”这一阶层一时间摆脱了“官”一阶层的压制,满怀了对摆脱政治阴霾后的北平,在文化空间上的一种理想的想象。
政治势力的纷纷南迁,使得原本污浊的北京政治空气清爽了不少。即使是官场的旧习气依然如故,文人多有不满地调侃:“北京与北平就只差了一个屁(P)字”,[23]但不可否认的是,北平的文化空间越来越宽松了。
北洋政府末期被严厉打压的文人言说空间,因新政府的上台,发生了变化。北洋政府统治北京末期,是对文学界和新闻界言论空间打压相当严重的一段黑暗时期。1926年4月24日《京报》主笔,著名报人邵飘萍被捕,26日即被公开枪决。不久之后,另一位著名报人,《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也被军阀张宗昌公开枪杀。新闻界如此,文艺界情况也不乐观。上文提到的刘半农,曾在另一篇文章中,记述了在这一时期,他险些受到政治牵连的往事:“那时候的新闻记者,确不是容易做的:动不动就要请你上军警联合办事处去吃官司,丢脑袋的恐慌,随时可以有得。记得我办了世副一个多月,舍我就在极严重的情形之下被长脚将军捕去了。我因为恐怕遭到池鱼之殃,也偷偷摸摸的离了家到某校的 ‘高能榻’上去睡了几宵,直到舍我营救出来了,才敢露面。现在的情形已大不相同,军警当局时常招待新闻记者,饷之以茶点,甚至于饷之以饭;这回因为讨伐石友三而戒严,所有检查新闻事务,由官方与新闻记者会同办理,这种的幸福,是五年以前的新闻记者梦也不曾做到的。”[24]
这篇文章写于《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复刊前夕,即1931年8月31日。刘半农所记叙的事情,是1926年8月7日《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被奉系军阀张宗昌逮捕,并宣布枪决,当时刘半农担任《世界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因而避祸出逃的往事。虽然成舍我最终在北洋政府前总理孙宝琦的奔走下得以出狱,但当时北洋政府的政治高压几乎到了生杀予夺的恐怖境地。之后北新书局被查,《语丝》南迁,也是在此种迫害下不得已而为之。时人因政治的压迫倍感压抑:“《语丝》于1927年冬被迫迁沪,近来又听说业已停刊,北平的空气真时沉浊闷人。”[25]当时的文坛空气大致是沉闷的。政治中心南迁之后,北平因业已脱离政治漩涡中心,迎来了短暂的政治宽松的环境,像北洋时期停刊的《京报》《世界日报》副刊等都得以复刊。有些人也开始对时局抱有乌托邦式的幻想:“于是乎我们这班酸先生,就可以息心静气的读书,安安闲闲的度日,说不定过上数年之后,能把这地方改造得和日本的京都,英国的牛津剑桥一样。”[26]政治控制日渐宽松,文人乌托邦式的幻想在文化古城时期如昙花一现般,付诸到文学活动中。也正是在文化古城时期,“京派”文人以报刊为言说场域,通过同人期刊和“掌门”副刊,逐渐发展壮大,并受文化古城环境的影响,吸纳传统文化精髓,又接纳新文化的合理成分,阐释了中国现代文学史风景的独特风格。
三、“文化古城”的经济变迁与世情转变
北京在很多个世纪里,都享受着帝国都城带来的特权,它不仅是政治和权力的合法中心,更由政治和权力带来了经济上的繁荣,庞大的官僚和政客集团催生了种种消费型行业,北京及其城市子民也享受到优先调用国库之备的便利。也正是由此便利,北京几乎是一座供养之城,它的粮食需要由江南转运而来,煤炭需要驼队从城外输入,工业产品依赖进口,北京除了拥有一些手工艺产业,几乎没有发展出自给自足的经济,帝国时代留给北京的仿佛只有享受和荣誉。
从1928年到1937年,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北京沦为一座“边城”,成为日渐衰落的“废都”。期间很多人离开了这里,只有少部分人因为留恋它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氛围而重新返回,但整体上,这十年北平是处于城市史的低潮部分。
北平的衰落可以透过失业率来观察,根据一份客观的调查显示:1928—1929年间,北平的失业率高达32.69%,这还仅是统计的商会在册职员的情况。统计显示,在91476名商会职员中,有29902名员工处于失业状态,而根据上半年与下半年统计对比的趋势,失业人数和失业率还在不断增长。[27]这意味着北平经济状况的持续恶化。北平经济的萧条,使得久处在其中的人们都明显察觉到,将北京喻作“北旧”的刘半农,就观察到“北平的铺子,关门的真不少,尤其以节前节后为多。听说有许多有名的大铺子,要关是不准关,开着是每天所卖的钱,还不够支持一天的门面的开销,这才是要命。”[28]就连从前一向发达的饭庄酒楼,也清淡了不少。
政治中心的迁移,也改变着北平的消费人口结构,使得北平核心消费族群发生变化。从前占据北京核心消费人口的是处于消费金字塔顶端的官僚、政客、军阀和商人,他们人数有限,却是整个北京城经济的资金来源。围绕着这群政商权贵们,北京发展出的高度依赖政权的商业经济,在此时却面临着严重的“本土不服”。显著的人口结构变化是军政机构人员的迁离,中央机构的南迁,使得原机构人员要么奉命南迁,要么被裁撤赋闲,受此政权迁移影响的机构人员据报载达十万以上(7)数字来源:平市商业之萧条[N].北平:北京日报,1928-10-04(06).转引自许慧琦.故都新貌 : 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M].台北:学生书局, 2008.,政治中心的迁出也使得大批投机和谋求参政的财团巨贾、下野政客丧失对北京的兴趣,纷纷迁往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北平不仅丧失了它原本的核心消费人群,更丧失了财力支持,原本设立在北京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总部也都迁离至上海。一些没有随之而去的北洋遗老、京官因为没有了政治投机和人事通洽的需要,也逐渐隐去炫耀式消费,以玩鹰、养花、听戏等消闲型消费自娱。城市财力的枯竭,加速了贫困人口的规模,加之四郊赤贫乡民不断涌入城中谋生,富户减少而贫困人口不断增多,成为北平新的人口结构趋势。有学者将北平时代的消费人口结构进行分析,将其分纳为“三多一少”式结构,即穷户多、客民多、单身青壮年男性多和富户少。(8)参见《故都新貌 : 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第一章,第二节:消费条件的重组。这种贫者多富者少的消费人口结构,虽然严重制约了北平的经济发展,但也拉低了整座城市的消费水平,北平也因其低廉的生活成本与物美价廉的生活享受,成为一座物价水平极低的宜居城市。
故都时期北平的物价,常常使得从其他大城市来的人称羡。1935年,当时还是文艺青年的钱歌川出版了《北平夜话》,他从新都南京来到故都北平,最终在上海一个临街有阳台的房间里,每夜依着台灯,用游记小品文的形式,断断续续回味着北平游历的感受,也在城市间的对比中体味着北平的不同滋味。对比新都南京和商都上海,钱歌川认为北平是最宜定居的一座城市,除了北平特有静穆悠远的古都文化和平静悠闲的生活方式外,北平低廉的生活成本也给钱歌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他的文章里,处处流露着对北平生活的赞叹。在他初抵北平时,朋友请他到穆家寨广福馆吃了顿黄花鱼,“等到几个人大吃一顿之后,结出帐来,其数目之微,尤使我大吃一惊,这种对于代价的深刻的印象竟把对于菜蔬的浅浮的口味驱走了。”[29]这个久居上海的青年人,带着沪上生活消费的眼光,打量着北平城的消费状况。他写道:“北平十几块钱一月可以租一个四合院;一两块钱可以招待朋友吃饭,有一毛钱坐洋车,可以从城东拉到城西,天气冷了,买一件普通的羊皮统子也只花得十几块钱。衣食住行样样都贱,生活不能不算便宜了”[30]同时期上海和南京,生活成本远比北平要昂贵的多。单就“住”这一项,北平就可以为客居者省去一大笔日常开支。同时期的上海,房租水平为“一楼一底的房子,每月租金要三十元至六十元,自来水、巡铺捐、点灯费等,尚不在内。”[31],南京的房租水平一度比上海还要高,新的都城尚在建设之中,而政府人员和商业机构的入驻,使得原本只能容纳三十六万人的南京城,人口倍增,住房因此紧张。在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下,“房主人们便把房租提得异乎寻常的贵,一间普通的小房间要一二十元”,[32]逼得南京的租客们闹过好几次“减租运动”。其他方面更不用说,萧红就曾在寄往上海的信中,无不赞叹地对萧军说道:“我在东安市场吃饭,每顿不到两毛,味极佳。羊肉面一毛钱一碗。再加两个花卷,或者再来个炒素菜。一共才是两角。”[33]
此外,旧都留下的种种生活设施、消费服务和文化氛围,为生活在此的有产阶级提供了廉价又高品质的生活。他们只需要付出极廉价的价格,就可能享受到过去专为权贵阶层提供的生活服务。在一本介绍北平地理知识兼作旅游指南的读物中,散文作家倪锡英记述了北平消费生活的变迁:“北平生活的闲散舒适,还是近十余年内的事。当政府没有迁都南京以前,北平的生活是正和现在南京的生活那样,含着浓厚的政治意味,而兼以人口的拥挤,住所也不舒服了。各种物品供不应求,百物就昂贵了。虽然物质上的设备是要比现在的南京来得完备,可是因为生活程度很高,非一般普通人所能享受。所以在那时候,达官贵人的生活是比较舒适的,但是因为政事的烦扰,称不上安闲,而一般的市民,终天便在高昂的生活线上挣扎着,一刻也不容闲息。自从政府南迁以后,情形便大变了。往日的达官贵人们,有的随着政府南迁,有的便消声匿迹下来,不再过那奢靡纷扰的忙乱生活。甚至有些便成了灾官,不得不离开北平,回到家乡,或到别处去另谋生路。这么一来,北平因为政治的变革,生活程度便立刻低落下来了。往日各种物质设备是依然存在,可是因为市面上骤然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重心,一切的代价便全都低廉,于是一般人的生活,也随着由紧张而松缓了,不再像以前那样的挣扎了。”[34]
倪锡英例举了洋车价格,说明北平消费水平较之同等设施程度大城市的低廉状况。在同等条件下的洋车,上海或南京需要两三毛钱的路程,北平只需要四分或者五分。上文提到的刘半农也发现迁都后的北平一度出现了汽车平民化的现象,这是因为“阔人”们的迁离,带不走的汽车成为急于处理的商品,致使北平普通的“两轮阶级”(坐人力车)也可以享受到“四轮阶级”的阔绰享受了。[35]消费水平下降,生活质量却并未下降,甚至某些高端享受反而更加低廉。种种此类经济现象,使得北平在知识分子眼中,在与当时国内各大城市的对比中,不失为生活的天堂。
一方面,北平消费结构的变迁导致了消费水平的降低,另一方面,文人、学者的收入却因政局的稳定而得到了保障。
在北洋政府时期,财政危机一直制约和影响着底层官员和大学教员等国家机关人员的生活。当时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职员们的薪金拖欠问题,乃至于生存问题是相当严重的:“各衙门局所的经费都是积欠到二十个月左右,那些磕头虫铁饭碗的参事司长们车马衣服等等都不像从前那样炫赫,每日到衙门以 ‘谈天、看报、喝茶、画到’为生活的小官僚们,一日三餐狠都发生许多困难,看他们成群结队,上下衙门,破衣破鞋,好像化子一般,恐怕不久自然要各奔前程去了。你看那学界!前几年那些应运而生,好像雨后苍苔似的私立大学,一个一个的关了门…国立各校是国家培养人才的地方,到现在也是为穷所迫,许多教员们 ‘因故离京’,自谋生路去了。寒假以后,学是开了,课也上了,但实际上教员的缺额有三分之一,到校的学生也过不了三分之一,而实在到那寒冷空廓的教室之中去的人更是为数无几。什么 ‘最高学府’,‘弦诵辍响’,‘教育破产’等等话头,也都没人说了,完全是坐以待毙的神气。”[36]
刘半农也曾记述:“那是国立九校还没有合并,北平有九个国立大学校校长。私立大学也比现在多到一倍。却因为国立大学的经费拖欠至数年之多,私立大学本无固定经费,以致北平的大学教育,整个儿的陷于 ‘不景气’的状态之中:讲堂老是空着,即使有教员上课,听讲者也不过 ‘二三子’而已;牌示处的教员请假条,却没一天不挤的水泄不通。现在的北平各大学,虽然还没有整顿到理想的境界,比到从前,已经大不相同了。”[37]
国民党统治期间的北平市政,逐渐摆脱了北洋政府末期财政支出严重拖欠的窘境。等到钱穆来京时,正好赶上文化古城时期,情况果然大不相同。钱穆在《师友杂忆》中描述的是故都文化繁荣的景象:名教授汇集于各大名校,在各自课堂中表述各自的学术观点。自由之风盛行,可随时与一流学者商榷问题,可自由办刊以表述,又有无尽的书海资料可供检索收藏。忙时可闭门读书或于富有怀古之思的城阙御池边饮茗思索,闲时可访各大名胜古迹,乃至于遍游全国。致使钱氏数次感慨“北平人物荟萃,或可酝酿出一番新风气来,为此下开一新局面。”“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云云,之所以钱穆可以安和黾勉,趣味无倦,是他可以住在“凡三院四进,极宽极净”的大宅子,五年即坐拥藏书五万册、20万卷,上课有仆役温茶递巾,退家有保姆庖人端茶送饭。如此生活,自然是“比到从前”,“大不相同”了。
促成北平知识阶层经济状况改善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南北统一后,对全国财政实行了统一调度,又致力于裁兵解饷。以天津海关每月30万、中基会基金每月20万,加之教会、庚款等作为经费,北平教育界的资金来源有了保障,文人、学者特别是大学教授的经济状况得到大幅改善,不仅一扫之前讨薪兼职的种种困境,而且渐入佳境,成为北京城内新的富人阶层,且绝对属于有闲阶级。
时人邓云乡曾回忆一位留法归国的教授的生活:“鲍先生留学法国,回国后三十年代初在中法大学做教师,另外又在东华门孔德学校兼课,收入在300元左右。当时物价便宜,面粉只要三元左右一袋(二十二公斤),猪肉只要一角多钱一斤,二三百元收入就很可观了。当时鲍先生住家共有两个小院,八间北屋,两东,两西,有盥洗间、有浴缸、庖人、女佣,还有自己的包月车。有书房,有客厅,四壁书架上有法国带回来的上千种精美书籍,这在当时还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教授,至于老教授、名教授,其生活之优裕和安定更可想见。”甚至于“有些留学国外的教授还娶了外国夫人的,有的是法国夫人,有的是日本夫人,有的外国夫人自己也是教授,他们住的往往是有花园的房子。衣食住行都比她原来在法国、日本时还舒服,不但能维持住外国的水准,而且常常是有过之无不及的。”[38]部聘教授和文化名人的薪水更高,像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月薪都达到近500元,如果是教会大学的教授,平均薪金就更高了,文化古城时期,协和医学院的薪金水平是年俸4500银元,是普通工人收入的上百倍,即使是相比于资本家和地主也高出数倍,他们一年的薪水相当于中产商人全部的资产。[39]这段优越的生活,到抗战爆发后,随着故都的沦陷而告终,教授们的生活再也没有达到如此优渥境地。正是在这故都十年间,北平文人生活条件得以改善,他们终于有了闲暇去从事和消费文化活动,经济状况的持续好转,也令他们有余资支持文艺刊物的出版,有余暇从事文艺刊物的编写,这一切都从基础层面,支持了文化古城时期北平文艺出版物的繁荣。北平文人办报办刊、聚会沙龙,逐渐营造出文化古城的文化空间,同时以闲趣和纯正的文学性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具有独立色彩的一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