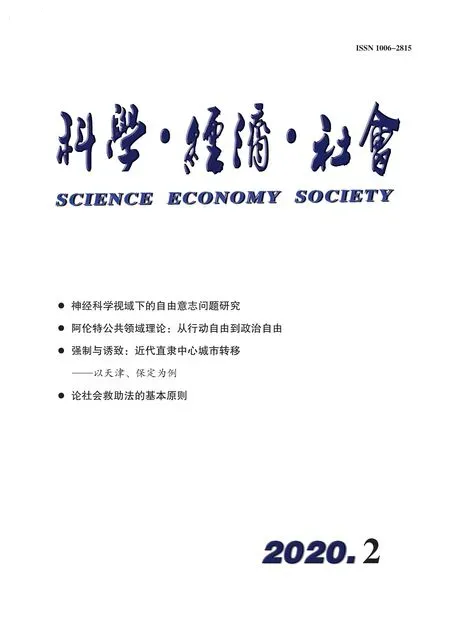意识可以上传和下载吗?
王 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一、想象的冒险与冒险的想象
如果说每个时代都有它特定的“时代精神”(Zeitgeist),那么在人工智能、纳米生物技术、脑神经科学和认知科学各个分支狂飙猛进的今天,设想和应对未来人类可能面临的人机一体化、去身体化和心灵的数字化,无疑是摆在哲学家面前的紧迫任务。哲学家们于是开始热衷于讨论诸如“后人类”(Posthuman)“赛博格”(Cyborg)“奇点”(Singularity)和“超级人工智能”(Super AI)这类新概念,并且忙不迭地以未来主义的眼光审视当下人类的生存论境况和社会文化的精神内核。这并不是说哲学家无权开展一场关于未来主义的想象的冒险,恰恰相反,我们担心的是,如果那样的想象到头来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它将反过来威胁哲学家对于当下社会、科技、文化、伦理、政治等问题判断的可靠性,想象的冒险容易成为冒险的想象。
在种种未来主义的想象情境当中,关于后人类和赛博格的终极样式,非“心灵上传”(mind uploading)莫属。有鉴于这只是模糊场景勾勒,我们在此无法对心灵上传给出严格的概念界定。大致而言,心灵上传指的是,在计算机和脑神经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未来,我们可以做到将人类个体大脑的神经元及其突触联结模式,以极其精确细致的方式,拷贝上传至计算机的硬件设备当中,从而让人类的心灵脱离大脑和肉身,在计算机和网络云端当中得以“永生”。关于心灵上传的实现方式、可能遇到的技术障碍,以及随之而来的种种后果,不少科幻作品提供了富有想象的启发。例如沃利·菲斯特(Wally Pfister)执导的《超验骇客》(Transcendence),讲述了男主角在生命弥留之际,通过非侵入的方式扫描自己的大脑,将心灵数据化上传到计算机,进而不仅成功实现了“活”在虚拟世界当中,更是做到了字面意义上的“呼风唤雨”,与世界万物“天人合一”。类似的场景也出现在吕克·贝松导演的《超体》(Lucy)那里,只不过这一次,女主角露西的心灵上传方式,是受某种能够激活大脑潜能的神秘化学物质的刺激,阴差阳错地最终实现心灵与万物的融合——当然包括各种计算机设备。不得不说,这两部科幻电影关于世界的本体论预设,无疑都是采纳了信息论立场——无论人类的心灵还是山川日月这样的物质实体,终极本质都是信息。也许这两部电影多少有点“超纲”,但是更多人所熟知的《星际迷航》(Star Trek)里的遥距传输技术,以及《阿凡达》描绘的把意识上传到克隆Na’vi人的“替身”当中,堪称心灵上传的典型方式。
大概受到科幻作品的启发,当代著名哲学家大卫·查默斯(David Chalmers)为我们梳理了心灵上传的三种“套餐”:A)毁灭式上传,B)渐进式上传,C)扫描式上传。[1] 102
B的实现方式略为复杂:S1.给大脑注入纳米机器人;S2.每个纳米机器人附着在一个神经元上,学习模拟神经元的微观行为及其联结方式;S3.学习完成后,替代原始的神经元进行工作,将信息无线传输到计算机上;S4.一个神经元的信息传送完毕之后,重新附着到下一个神经元上,重复S2和S3,最终完成大脑中全部神经元的信息上传。
C最简单省事:S1.装配类似于fMRI的扫描仪;S2.扫描仪精确记录大脑神经元的动态活动,并上传到计算机。[1] 102-103
查默斯并没有穷尽心灵上传的全部实现方式——例如《超体》所展示的“弄拙成巧”的心灵上传就不在讨论范围当中——但至少这是我们可驾驭(tractable)的实现方式。三者里面,A在技术上似乎最容易实现,但是毁灭原初的大脑却让它变得风险很高。B虽然比A安全,但是耗时漫长,也无法确保渐进上传的过程中不出现意外。C是科幻作品中最常见的上传方式,听起来最为安全,却也最难实现,而且保留原初大脑的完整性,将会面临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的困难。
不过,在我们继续这个话题之前,需要简单澄清“心灵”与“意识”这两个关键概念。不妨说,意识现象和意识特征,是心灵现象和心灵特征当中最有趣、最棘手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心灵上传仅仅只把心灵中的部分内容——例如我刚刚记住的一串电话号码——上传到计算机,这个问题就简单多了,同时也变得无趣多了。我们似乎可以谈论阿尔法狗(AlfaGo)是否拥有心灵,但除非有特定的语境,我们似乎不会争论阿尔法狗是不是已经有了意识。正因如此,当人们谈论心灵上传时,真正关心的其实是意识上传。这里所谓的意识,很大程度上是指生物意识(creature consciousness),也就是在人类和其它动物那里展现出来的、具有一系列特定属性的心灵能力。这些属性包括:拥有感知(Sentience)、是清醒的(Wakefulness)、有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有第一人称体验(What it is like)、是意识状态的主体(Subject of Conscious states),以及意识是关于某个对象的(Transitive consciousness)。[2]这些貌似学术行话的概念,倒是非常符合我们关于意识的直观理解——对于意识问题,难以言说的直观理解恰恰是最重要的。有了这些准备,现在我们来看以上三种方式,原则上能否实现意识上传。
二、意识上传的形而上学要求
事实上,我们无需对三种上传方式逐一考察,问题的关键在于,关于意识,它们都采纳了什么样的形而上学预设。正如我们在《超验骇客》和《超体》中所看到的,两部电影的主角都能做到连通宇宙万物(类似于某种版本的自然神论),背后预设了意识和物质的本质特征都是信息。在查默斯看来,上述无论哪种上传方式,对大脑信息的提取是必不可少的,这首先意味着意识与某种物理特征的属性有着必然关联,因此这样的形而上学立场首先排除了笛卡尔式的实体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认为意识与物质是截然不同、毫无交集的两种实体(substances)。进一步地,既然意识可以上传到计算机,意味着意识载体可以脱离原初的生物性大脑——例如《阿凡达》需要一个克隆生命的替身作为意识的载体,因此特定类型的意识状态就不必是等同于特定类型的脑神经生理状态,从而心脑类型同一论(type-type identity of mind)也被排除在外了。
熟悉心身问题的读者都知道,心脑同一论除了类型同一论之外,还有个例同一论(token-token identity of mind)。前者认为,疼痛这种类型的意识状态,必然等同于特定类型的(比方说,C-神经纤维激活)脑神经生理状态。不妨设想一下,章鱼也有疼痛体验,它们没有人类的大脑构造,从而也没有C-神经纤维。因此类型同一论在意识问题上,带有过强的人类沙文主义倾向。个例同一论在这一点就表现得更加宽容,它主张在生物个体那里,特定的意识状态个例,等同于它自身特定的脑神经生理状态。我的疼痛等同于我的C-神经纤维激活。一只章鱼的疼痛,则等同于那只章鱼自身的B-神经纤维激活。
如果坚持意识即大脑,并且类型同一论无法作为意识上传的本体论基础,似乎就得接受个例同一论。然而在意识上传问题上,个例同一论对大脑基质(substrate)的依赖性关联比类型同一论还要强。它不仅要求意识等同于某种特定类型的脑神经生理状态,还要求某个特定(the)的意识,等同于某个特定的(the)脑神经生理状态。把意识上传到阿凡达Na'vi克隆体上都行之无效,更别提上传到硅片基质的计算机存储空间了。
如此看来,在心—身问题上的逻辑空间里,关于意识上传的主要几个形而上学基础理论,似乎只剩下功能主义和泛心论(panpsychism)了。泛心论说的是,心性(mentality)是自然界中最基本和最普遍的存在。大到日月山川,小到夸克和光子,世界上任何物理事物多多少少都具有心灵属性。[3]尽管查默斯自己的立场倾向于泛心论,但泛心论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不是合格的形而上学配置。一方面,泛心论对于意识上传的处理没有显著的可驾驭性(tractable),另一方面,如果复杂程度不一的心性无处不在,我们似乎也没有很好的理由费尽周折,非要把意识上传到计算机上才可以保留意识——没准黄土一抔,亦可永生九泉。
关于方程的教学,在20世纪90年代末,陈重穆先生就提出了一个观点:“淡化形式,注重实质”。对于方程而言,要淡化的是“含有未知数的等式”这一定义。他指出,“不必在文字叙述上下功夫,更不要把这些叙述当成方程的正式定义,予以拔高”[1]。张奠宙先生也多次撰文强调这一点,2011年,他对小学数学中的一些科学性问题进行了分析,其中就指出这一定义“只谈了方程的表面,实在不重要”。同时,他还指出方程的本质是为了求未知数,在已知数和未知数之间建立的一种等式关系[2]。2014年,他再次撰文强调了这一点[3]。
因此,如果意识上传是可能的,最可靠的形而上学基础就是功能主义,而且还是一种强版本的计算主义(computationalism)。计算主义认为,心灵就是数字计算机,而思想和意识也都是某种类型的计算。既然如此,任何反对计算主义的理由,都可以将批评的火力引入到反对意识上传的可能性当中来。
对意识的功能主义批判,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布洛克(Ned Block)提出的“中国脑论证”(China Brain Argument)。请注意,这与我们熟知的塞尔(John Searle)反对强人工智能的“中文屋论证”不同。后者针对的是计算主义能否“消化”语义理解能力,前者则为我们设置这样一个思想实验场景:既然人脑的每一个神经元都可被视为信息输入输出装置,那么每个中国人都来扮演单个的神经元角色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假设我们每个中国人手里都有一部双向无线电通讯设备,按指令对特定的人接受或发送信号。如果全体中国人(假设有15亿人)通过统一命令,完全按照疼痛发生时,神经元集合的电信号状态在线联网,这样一来,整个中国脑作为整体,能否作为新冒出来的第15亿零1人?并且“它”还能感受到疼痛。[4]
布洛克认为,这样的结论是反直觉的。这个思想实验反对的是常识功能主义,尽管计算主义是一个后验(a posterior)论断,但对于意识上传而言,他的批评同样可以提醒我们,意识的现象特征(例如痛感体验),或许无法从功能同构的特定功能属性中先验推导出来。不过,关于计算主义的另一层担忧,对意识上传的可实现性的杀伤力更大。这种担忧将会导致计算主义沦落为泛计算主义,从而将其与泛心论联系在一起。既然计算主义试图摆脱意识之于生物性大脑的神经生理的依赖性,只要求在计算功能方面具有同构性即可,那么计算主义在落实(implementation)过程中,或将面临“落实的随意性问题”。根据程炼对塞尔的引述:
“按照对计算的标准的教科书定义,我们难以看到如何避免以下结论:1.对于任何对象,存在对该对象的某个描述,使得在该描述之下该对象是一台电子计算机;2.对于任何程序并且对于任何足够复杂的对象,存在着对该对象的某种描述,在该描述之下,该对象正在落实该程序。这样的话,例如我背后的这堵墙现在正在落实词星(Wordstar)程序,因为存在某种分子运动模式,它与词星的形式结构是同构的。但是, 如果这堵墙正在落实词星,那么如果它是一堵足够大的墙,它也正在落实任何程序,包括任何落实在大脑中的程序。”[5]14
诚如程炼所言,要回应落实的随意性问题,我们可以指出,“大量的物理系统落实了简单的、只有极少量内部状态的图灵机,这些图灵机只能刻画简单的算法。但是计算主义者不承认每一个物理对象落实了每一个计算,这是因为,极其复杂的计算所包含的计算状态数量,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知的宇宙体系的物理状态类型的数量。”[5]14-15但是这样的话,则会把意识上传的可落实性置于一个两难困境:如果意识上传在技术上容易落实,那么我们必须接受某种与计算主义可相融版本的泛灵论;如果要想避免落实的随意性问题,考虑到意识落实在计算机上的难度,“可能远远超出我们所致的宇宙体系的物理状态类型的数量”,它在技术层面上就几乎无法实现——更何况我们对未来的计算机算力的预期,只是建立在作为经验性总结的摩尔定律的不可靠的期许上。如此说来,即使关于意识上传的形而上学——计算主义——为真,意识上传要么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技术想象,要么因为泛心论亦可充当意识上传的形而上学选项而变得没有必要。
三、创造智能还是保留人格同一性?
尽管意识上传在“落实的随意性”维度有其两难困境的隐忧,但是到此为止我们还没有任何形而上学的理由反驳意识上传的可能性。现在的问题在于,哲学家和科幻作家所设想的意识上传,并不是简单地把心灵中的部分内容(例如可被计算编码的记忆)上传到计算机,而是要求对一个有感知、清醒的、现象性的、有第一人称体验、有自我觉知(self-aware)能力的意识主体进行上传。让人格(person)彻底脱离大脑和肉身而存在。并且,进一步地,这种离身性存在(disembodied being)的目标,是能够持续存在甚至永恒存在(只要计算机的运行不出现重大故障)。因此我们有必要去追问,查默斯所刻画的三种上传方式,真的能够让我们的意识连同特定的人格,存活在计算机设备或“云端”当中吗?
对于那些认为意识上传原则是不可能的脑神经科学家而言,他们大多认为,意识必须依赖于大脑。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得主坎德尔(Eric Kandel)指出:“心灵的新科学建立在这一原则上:我们的心灵和我们的大脑是不可分离的。大脑是复杂的生物器官,它拥有海量的计算能力:它构造我们的感知经验,管理我们的思想和情绪,控制我们的行为。它不仅对类似于吃饭和跑步这些相对简单的运动行为负责,也掌管了诸如思考、说话和艺术创作这些被视为人之根本的领域。从这一角度看,我们的心灵是由我们的大脑来执行的。”[6]1
不过我们可以退一步讲,假设此刻我们已将意识成功上传了,接下来会出现什么情况?作为心脑个例同一论的支持者,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在他著名的“沼泽人”(Swampman)思想实验中,邀请我们思考如下场景:
“设想一个闪电劈下来,击中了沼泽中一棵死去的树,而我就站在旁边。我的身体化为灰烬,纯属巧合的是,这棵树(虽然是不同的分子)竟然变成了我的物理复制品。我的复制品——沼泽人——与我的行为完全一样,它离开沼泽,遇见了我的朋友,也似乎认出了他们,而且它也用英语和我的朋友打招呼。它走向了我的住所,看似也在撰写一篇关于彻底解释的论文。没人察觉出有任何异样。”[7]19
在这一场景中,戴维森的身体因被闪电击中而瞬间消亡,但是闪电也按照戴维森的身体分子排列方式(包括大脑分子排列),彻底重构了沼泽中的那棵树。这使得新冒出来的沼泽人有着与戴维森一模一样的分子构成和行为模式。这场意外相当于“A套餐”所描绘的毁灭式上传,唯一的区别在于,这里省去了步骤S1和S2,无需对冷冻大脑进行切片处理,并且步骤S3和S4的是由闪电和沼泽中的物质瞬间实现的。但在沼泽人思想实验中,随之而来的问题包括:沼泽人就是戴维森吗?或者它算得上是“人”吗?它有思想吗?这些思想是戴维森的思想吗?根据戴维森自己的分析,他对这些疑问都持否定态度。
“但是(沼泽人和戴维森之间)有所不同。我的复制品无法认出我的朋友;它不能认出(recognize)认出事物,因为它一开始就从未认知过(cognized)任何事物……在我看来,我的复制品发出声音的时候,并不表达任何含义,它也没有任何思想。”[7]19在戴维森看来,沼泽人虽然在言语行为表现上跟思想实验中被毁灭的戴维森完全一样,然而它却没有思想、没有心灵、没有意识也没有戴维森的人格,理由是沼泽人不具有戴维森原始心灵的因果历史(casual history)。这意味着,我们所设想的意识上传,很可能仅仅只是创造或拷贝我们的心灵内容,却无从保留人格的同一性,而后者才是意识上传的要义。这类似于我拿到王希梦的《千里江山图》真迹,我用巧妙绝伦的复制技术,造出每个分子都完全一样的赝品,然而赝品仍然是赝品,即使它们的形式完全一样,由于它们的因果历史截然不同,它们的“客观意义”却无法等同。[8]191
支持意识上传的哲学家或许会指出,戴维森思想实验的结论无法获得辩护,因为那是他所主张的“无律则一元论”(Anomalous Monism)的产物。这种理论认为,心理学无法像物理学那样,在心理和物理之间并不存在无例外的自然定律。计算主义者会声称,就人格同一性问题而言,关于意识与大脑的关系,就好比是软件和硬件的关系。同样的软件,可以在不同的硬件上运行。意识上传后的人格同一性,也因此获得保障。豪斯科勒(Michael Hauskeller)改造了这个比喻,我们是否可以说,意识就好比一本书的内容,大脑好比呈现出该书内容的物质实体呢?如此一来,岂不是可以认为,当我的意识(书的内容)上传到计算机中,上传后的意识(书的内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等同于我的大脑(书的物质实体)的意识了吗?豪斯科勒指出,这个比喻遗忘了重要的一点:书的内容依赖于读者,如果没有读者,《红楼梦》并不存在。换一个说法,如果我在读一本《红楼梦》,你也在读同一个版本的《红楼梦》,假设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思想内容完全一样,然而我们仍然可以说,我在读我的书,你在读你的书,我们两人的心灵并不是同一个心灵。[8]192有鉴于此,我们很难相信,即使意识可以上传,我的人格也可以随之上传到了计算机上。我们最多只能说,通过所谓意识上传方式(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创造了一个虚拟智能。
四、不能上传,还不能下载吗?
如果说意识上传是后人类的终极梦想,当这个梦想变得不太可能(意识无法“计算可落实”)或者并无必要(泛心论的困境以及人格同一性不能得到确保)时,我们还能退而求其次,追求另一种可能性——意识下载吗?这里所说的意识下载,和上述“意识上传”的定义可以有所不同,它指的是把其它认知系统的心灵内容下载到人脑当中。这种类似于记忆移植的场景想象,倒是可以准确切中赛博格的要义。我们已经见识了现有的科技水平可以用机械替换人体的一部分,甚至将大脑与机械联为一体,例如人工视觉、人工触觉,以及用意念控制机械手臂等等,然而这还只是用义体替代原有的身体,它与我们这里所说的意识下载还差的远。心智健全的人倒是更渴望把一整套《四库全书》或者朗朗的钢琴技能直接“装进”自己的大脑。
很可惜这样的想象,从认知科学原理上看,恐怕也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这一次,意识下载遇到阻碍,与意识上传所面临的形而上学困难不同。一方面,意识下载很大程度上受到人脑神经生物学的限制;另一方面,根据认知科学哲学对心灵加工模式的设想,大脑无法任意接受不加分别的信息。
首先,意识下载受到人脑工作记忆(working memory)的限制。这个术语指的是我们在有限的一段时间内(通常是几秒钟)记住信息的能力。从控制注意力到言语工作,从逻辑推理到视觉听觉信息处理,大量复杂的任务都是以工作记忆作为最基础的工作平台。[9]26工作记忆类似于计算机的“内存”,它的“容量”或“带宽”范围,大致只能在短时间记住7个随机数字。因此,即使未来能够做到利用纳米生物科技将一部携带《四库全书》信息的微型存储设备直接植入大脑,要想调用提取这些信息,必须过了工作记忆这一关才行——除非另有神奇的办法对人脑的工作记忆进行技术扩容。
其次,人脑的神经元系统是高度可塑的,大脑的功能图谱将会随着存储记忆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例如钢琴家在听到钢琴音时,被激活的脑区面积比非音乐家要大25%,并且传导运动性神经冲动的通路也会有所不同。若这一事实无法改变,很难想象当一个人下载了朗朗的钢琴演奏技能并将之在自己的大脑中激活之后(如果可能的话),此人的其他认知功能仍然可以大致保留原样。
最后,根据霍伊(Jakob Hohwy)和克拉克(Andy Clark)等认知科学哲学家近年来提出的“大脑的预测加工模型”(Predictive Processing of Brain),生物性的大脑不仅仅只是一台被动接受外部信号的信息加工装置,大脑更类似于一台预测误差最小化的贝叶斯推理机。它一方面对即将接受到的外部刺激作出主动预测,另一方面在层级化的功能模型中,将这样的预测与实际采样到的信号进行误差比对和相互修正,从而以一种康德式的认知模型进行工作。如此说来,我们能够经验怎样的意识体验,以及拥有什么样的心理内容,并不完全取决于接收到怎样的信息刺激,更需要取决于每一个特定的生物性大脑的具体构造及其发育学习历史。强行植入的信息,在这个意义上也将成为无效的噪音。
五、小结
科幻场景的可设想性,并不顺理成章地等同于现实的可能性。关于意识上传和意识下载,既牵涉到意识的形而上学基础问题,又受到脑与认知科学相关的经验事实的约束。基于大卫·查默斯为心灵上传话题设置的讨论框架,本文已经论证指出了以下三点:第一,意识上传的形而上学基础是计算功能主义,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意识上传将会陷入一个两难困境;第二,心灵上传并不等同于意识上传,更不能保证人格同一性的维系;第三,不仅人类的意识无法上传,受制于我们生物性大脑的工作模式,意识下载也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