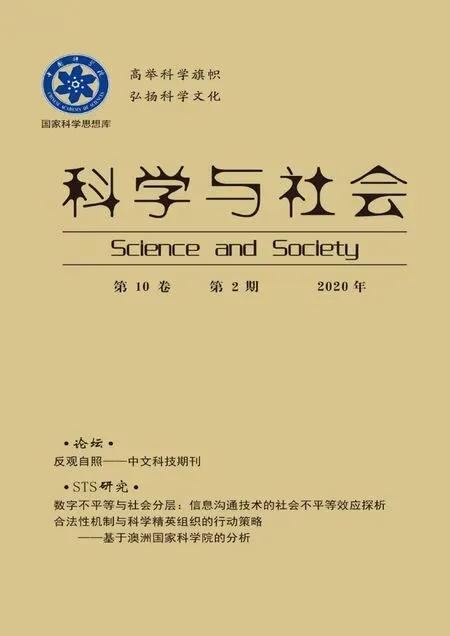对COVID-19疫苗人体挑战研究的伦理挑战
黄 雯 翟晓梅
(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
由SARS-CoV-2引发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公共卫生及社会构成极大威胁,给全球卫生保健系统带来极大压力。传染病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不断发出警告,COVID-19的流行将与人类长期共存,在缺乏疫苗的情况下,COVID-19在全球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巨大的。美国最近的一项模拟研究表明,即使采取保护老年人(减少60%社会接触)和放慢但不中断传播(减少40%广泛人群的社会接触)的缓解策略,今年仍可能发生2000万例死亡。如果没有针对COVID-19的经过验证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就无法以可持续的方式解决由于COVID-19大流行所导致的全球严重的健康、经济和社会危机。经过传统三期临床试验的有效疫苗研发上市所需的最短时间估计为12-18个月甚至更长。这种情况使得专家们开始考虑如何能加速对候选疫苗的测试,呼吁用人体挑战试验代替标准临床试验过程中最费时长,花费也最为昂贵的阶段—III期临床试验。用人体挑战试验代替常规试验中对疫苗有效性的测试,或在常规测试之前淘汰没有希望的候选疫苗,从而也部分替代了常规的有效性测试。
人体挑战试验与标准研究方法不同,标准研究方法是为大量处于感染疾病风险中的人接种试验疫苗(研究条件之一是需要大量新发病例存在),并将受试者的血清学转化结果与未接种疫苗的处在相似风险环境中的人群进行保护性免疫效果比较。人体挑战研究(Human Challenge Studies)也称受控人体感染研究(Controlled Human Infection),该研究涉及故意使健康的试验志愿者感染某种能够引起该疾病的毒株,以测试试验疫苗。近年来,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支持了一些人体挑战研究,开发了针对疟疾,霍乱和伤寒的疫苗。面对COVID-19的流行,对COVID-19疫苗进行人类挑战试验的压力也越来越大。2020年4月下旬,美国众议院的35名成员致信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认为挑战研究可以大大加快对有效疫苗的需求。
2020年5月6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一份文件,题为《COVID-19人体挑战研究伦理可接受性的关键标准》(以下简称《标准》)。《标准》认为,COVID-19的流行对全球公共卫生、社会经济构成极大的威胁,如果对此不采取有效遏制措施,COVID-19可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并给全球卫生保健系统带来极大压力,甚至导致医疗卫生系统崩溃。虽然疏离社交身体距离等公共卫生控制措施有助于减少COVID-19的传播,但这些措施也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成本,特别是贫困人群所承担的成本。目前全球公共卫生面对的主要挑战是缺乏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治疗药物,关于发病机制、免疫和疾病传播的科学知识的匮乏。人体挑战研究对于测试疫苗可能有特殊的价值:试验速度快得多,需要暴露于试验中的受试者人数少得多。这样的研究方法还可用于比较多种候选疫苗的有效性,从而为更大规模的研究选择最有希望的疫苗。因此认为,精心设计的挑战研究不仅可能加速COVID-19疫苗的研发,而且有可能使最终使用的疫苗更有效。挑战研究也可用于感染和免疫的过程研究,可用于验证对SARS免疫有效性;确定免疫保护的相关因素,以及研究受感染个体造成的传播风险。这些发现能够全面地显著改善公共卫生对大流行的应对。因此,在特定情形下,有意感染研究受试者的人体挑战研究在伦理学上是可以接受的。为此,《标准》提出对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八项伦理标准:(1)科学依据;(2)风险和潜在受益评估;(3)与公众、专家和决策者的磋商与共同参与;(4)研究的密切协作;(5)挑战研究的现场选择;(6)挑战研究的受试者选择;(7)专家评审;(8)知情同意。表示该文件“旨在通过概述此类研究能够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所必须满足的关键标准,为科学家、研究伦理委员会、资助者、政策制定者和监管机构就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进行讨论时提供指导”。
然而,故意使健康的试验志愿者感染SARS-CoV-2以测试试验疫苗的人体挑战研究,引起了国际社会巨大的伦理争论,虽然COVID-19的人体挑战研究有着眼于公共卫生的要求—挽救生命,以及降低成本和需要更少的研究受试者等其他益处,但考虑到生物医学研究必须把给受试者带来的潜在风险降至最低的伦理原则,以及伦理审查委员会将无法满足而应该必须满足的“确保”“最大程度地降低对受试者的风险”,并使用“不会不必要地使受试者承受风险的程序”的要求所致的伦理挑战,特别是在对受试者的风险评估问题方面,都使人体挑战试验面临种种伦理困境。
一、受益与风险评估问题
以人作为受试者的医学研究旨在获得可以被普遍化的医学知识、临床诊治方法和医学治疗手段,更好地满足公众的医疗健康需求,其社会使命是预防及减轻人类因疾病和损伤造成的痛苦。可见,以人作为受试者的临床研究是医学发展所必须的,不仅是伦理允许的也是伦理所要求的。作为改进人类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医学研究致力于产生和利用知识来促进全人类健康,这种奉献必须立足于这样的伦理承诺:开展研究是符合伦理的,并有望提高所有人的健康标准—通过获得可以被普遍化的知识实现其重要的社会价值。这里强调了关键的两点伦理学含义:(1)我们需要在促进发展医学知识与受试者保护之间达到最佳的平衡,只有当受试者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医学研究才能得到伦理学辩护,才能真正有利于医学和科学的健康发展。(2)研究必须具有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社会受益)。
研究的受益可分为两类:(1)只对社会有益处的研究;(2)对社会和受试者都有益处的研究。只对社会有益处的例子包括 I期药物临床试验,健康人作为受试者进行的非治疗性研究。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设计也同样应该视为并不着眼于受试者的个人受益的研究。大家都认为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重要科学意义和巨大的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从伦理学的视角看,某些人体挑战研究在原则上可能是允许的,但对在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风险/受益比的评估却面临很大困境。
《标准》一文提出:“根据标准的科研伦理要求,就受益风险比平衡而言,受益应大于风险”[1]。“预期受益应最大化以及风险应最小化”[1]。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2016年颁布的关于《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国家卫计委11号令)规定:“研究风险与受益比应当合理,力求使受试者尽可能避免伤害”[2]。在将社会价值纳入到受益风险评估框架中,那么不着眼于个人受益的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风险受益的权衡,需要将接受新冠病毒感染的受试者个人面临的风险与巨大的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加以权衡。美国学者以临床医疗中患者能够接受创新医疗情景下大的医疗风险,来对挑战研究中受试者可以接受大的风险进行合理性论证[3]。这样的论证实际上弄错了对象,在挑战研究中,个人的风险是与社会的获益相权衡,而非临床医疗中患者可能遭受的风险与患者本人的预期健康受益相权衡。认识到这一点对回答挑战研究的伦理学可辩护性是非常重要的。
当挑战研究有助于产生较大的甚至是极大社会益处时,是否意味着我们就可以接受使受试者个人承担更大风险的情况,即使这样仍然可以满足规定中对“比”的要求?
理性的生命伦理学家会坚持这样的伦理立场:我们不应该试图为了平衡期望的社会受益,而置受试者个人风险于不顾。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中关于“控制风险原则”规定,应“首先将受试者人身安全、健康权益放在优先地位,其次才是科学和社会利益的”考虑[4]。根据伦理原则,一旦研究在预期的社会受益达到一定的界限(阈值)后,就应当被批准,但同样,我们也应当对受试者个人可能遭受的的风险设立一个界限(阈值),超过这个阈值的研究就不应该被批准,而不是简单地对受试者个人可能遭受的风险与社会受益进行评估。
二、可接受的风险程度
为了避免伦理审查委员会对风险的评估由于受到委员各自的专业所限,仅仅依靠个人的直觉对风险加以判断,产生对风险程度判断高度不一致的结论,一直以来生命伦理学学者建议应将风险的种类客观化。《标准》一文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在可能的范围内,应对SAR 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潜在受益和风险进行量化(并在必要时模式化),并与其他相关研究设计进行比较。……风险的量化应包括预计:(1)暴露于风险的受试者人数;(2)受试者的绝对风险(根据最新数据);和(3)受试者的边际风险(即,与感染的环境风险相比,参与研究的额外风险)”。[1]
对风险的分析,可以从风险大小的程度以及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两个纬度进行评估。对于风险程度的分析,应该通过更多的科学的数据尽可能将风险的程度客观化并加以分级,结合风险发生的概率对风险的大小加以判断。对风险很低的研究或风险很高的研究,人们能够较为容易地对是否应该允许研究做出决定。但对于中等程度的风险呢?是否应该允许可能对研究受试者造成中等程度甚至略高于中等程度风险的研究进行?例如,为了研究某种抗病毒药物,可能使健康人暴露于所谓的人体挑战研究中,即在提供受检药物或安慰剂之前有意让受试者接触活的病毒。用已知引起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活病毒进行人体挑战研究,显然是不符合伦理的。国际医学科学组织理事会关于研究的伦理准则在关于人体挑战研究时指出:“即使这项研究具有重大的社会价值和科学价值,可以开发有效应对某种疾病的疫苗,而且具有知情同意能力的成人自愿地知情地同意参加研究,也会是由于得不到伦理辩护的风险而不可接受的”。例如炭疽和埃博拉病毒的人体挑战研究[5]。对于那些为了获得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社会价值,而让充分知情的志愿者接触一种至多可能引起轻微伤风感冒的病毒,则这样的挑战研究应该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挑战研究使受试者可能遭受的是中等程度,甚至是更高程度的风险,尚有科学认识上不确定性的、未知的潜在甚至可能会长期影响受试者健康风险时,这样的挑战研究是否能在伦理学上得到辩护? 《标准》一文提到,SARS-CoV-2人体挑战研究的“在道德上是敏感的,必须精心设计和实施,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志愿者的伤害,并保护公众对研究的信任,特别是,除研究者必须坚持标准的科研伦理要求以外,还应在特别高的标准下开展研究,这是因为:(1)该研究涉及使健康的参与者暴露于相对较高的风险中;(2)研究涉及第一次对人的干预(包括挑战)和高度不确定性的问题(例如,对于感染,疾病和后遗症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3)公众对研究的信任,在突发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这一点尤其至关重要”[1]。但这其中的问题是,对这种程度风险的人体挑战研究的受益风险应该如何评估?如何平衡?理由是什么?
三、有效治疗药物问题
许多伦理学家警示研究人员,使用人体挑战研究方法的前提,是对所研究疾病存在可接受的治疗。全球的科学家还在寻找治疗Covid-19的药物,对目前仍在使用的羟氯喹或氯喹和瑞德西韦的疗效问题,也一直存在争议。5月29日,医学学术期刊《柳叶刀》刊发临床试验数据论文对羟氯喹或氯喹治疗COVID-19的跨国试验进行了分析[6]。研究结果显示,羟氯喹/氯喹对新冠肺炎住院患者无益处,反而增加了院内死亡和室性心律失常的风险,其死亡较对照组高33%。这是对来自6大洲671家医院96 032名新冠住院患者的回顾性观察研究。研究团队是来自美国和瑞士的4名医学教授。此论文于5月22日首发,经同行审议后修改了相关数据并于5月29日正式刊发。这一结果无疑对公共卫生实践和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基于这篇首发论文,世界卫生组织于5月25日通报暂时叫停羟氯喹抗新冠病毒试验,暂时中止羟氯喹在全球团队试验中的使用,专家将审查迄今为止的试验数据,以评估羟氯喹的潜在益处和危害[7]。英国药监监管机构要求暂停所有羟氯喹使用的志愿者招募,以及针对治疗和预防的试验。法国也更改了羟氯喹在新冠肺炎治疗中的使用并终止了试验。中国药科大学教授李战表示:磷酸氯喹是治疗疟疾的一种老药,它具有明显加大心率失常的风险也是已知定论,欧洲治疗中患者有不少心率失常死亡的报道。美国FDA也承认,羟氯喹/氯喹与心脏风险相关。
但这一结果也引发业内专家的不同意见,全球上百名科学家对这个研究发出了质疑。5月28日,这些科学家联名发布了致研究者和《柳叶刀》的一封公开信“An open letter to Mehra et al and The Lancet”,对研究的统计分析和数据完整性等提出了10个质疑[8]。5月28日,单鸿、钟南山等中国学者在《国家科学评论》杂志在线发表了题为“Preliminary evidence from a multicenter prospective observational study of the safety and efficacy of chloroquine for the treatment of COVID-19 ”的研究论文,为羟氯喹/氯喹在新冠肺炎患者治疗中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提供了证据,并表明羟氯喹/氯喹可以作为对抗新冠肺炎大流行的经济有效疗法[9]。
在5月25日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暂时叫停羟氯喹抗新冠病毒试验后,安全性数据监控委员会一直在评估羟氯喹安全性数据,并基于已有患者病亡率数据,认为没有理由修改试验方案。6月3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鉴于目前使用羟氯喹治疗新冠肺炎尚存许多“未知”,只有通过临床试验尤其是规范的随机试验才能得到确切答案,因此世界卫生组织决定恢复羟氯喹抗新冠病毒试验。但同时将密切监控试验安全性数据,表示未来不排除再度对试验进行调整[7]。显然,面对实验数据以及药物本身作用机理,羟氯喹/氯喹的使用效果尚需继续进行科学评估。
瑞德西韦是美国吉利德科技公司研发的一款抗病毒药物,是一种尚未获批的用于治疗埃博拉出血热和中东呼吸综合征等疾病的在研药物。2020年5月1日美国FDA授予瑞德西韦紧急使用授权(EUA),允许瑞德西韦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重症的住院患者。关于瑞德西韦的临床数据十分有限。4月29日《柳叶刀》网站发布了由中日友好医院曹彬教授团队进行的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临床试验结果。研究结果显示,未观察到瑞德西韦联合标准疗法与标准疗法相比有统计学意义上显著的临床获益,“尽管瑞德西韦安全、耐受性好,但与安慰剂相比其益外并不显著”。6月1日,吉利德科学网站发表了关于瑞德西韦的总体临床数据的声明,称瑞德西韦现在有的三个随机对照临床试验,“显示瑞德西韦在多个不同的评估方式中可改善临床结果”。《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布的数据表明,瑞德西韦虽然缩短了患者经历严重症状的天数,但对降低患者的死亡率没有统计学差异,新冠患者死亡率还是很高,“未来的策略应该结合评估抗病毒药物和其他治疗方法,以改善治疗新冠患者的结果”[10]。
人体挑战研究的伦理要求包括,直到能够获得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才可能接受具有潜在致命的和尚无治疗方法的病原体的人体挑战试验。面对全球大流行,我们尚没有有效的治疗药物可用,世界卫生组织在其《标准》一文也明确指出:“当前的全球大流行使公共卫生面临着的挑战主要包括:(1)缺乏安全有效的疫苗和治疗方法;(2)关于发病机理、免疫力和疾病传播方面科学知识的匮乏”[1]。然而在世界卫生组织关于COVID-19研究可接受性的伦理标准清单中,并没有提出对该疾病的可接受治疗措施这一通常非常重要的伦理要求,而是认为“虽然治疗是降低风险的一种重要方法,但特异性疗法的存在并不是人体挑战研究在伦理上可被接受的必要条件”[1]。
这一立场也引起了伦理学上很大争论,有些生命伦理学家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例如美国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国际著名生命伦理学家Ruth Macklin①Ruth Macklin博士是艾伯特·爱因斯坦医学院教授。2014年黑斯廷斯中心(Hastings Center)的亨利·诺尔斯·比彻(Henry Knowles Beecher)奖的获得者,该奖项是对学者对伦理和生命科学终身贡献的认可。博士就认为,匆忙开始对一种缺乏有效治疗的严重疾病进行人体挑战研究,在伦理上是不合理的[4]。2020年5月7日,一个名为AIDS疫苗倡导联盟(AVAC)的非政府组织发表了一项关于COVID-19疫苗挑战研究的道德规范的声明。AVAC声明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阐明了评估挑战研究的重要标准,但却省略了最重要的一项,即“直到获得证明有效的治疗方法,才可能接受具有潜在致命和尚无治疗方法的病原体的人体挑战试验”。 一位疫苗研究专家也同样质疑这样的人体挑战研究是否合乎道德,并补充说其实常规标准的疫苗试验已经会很快进行。
四、讨 论
Covid-19疫苗的人体挑战研究提出了很多需要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科学知识(哪怕是极为重要的科学知识)的产生并不会使科学家(尤其是那些身处医疗卫生专业的科学家)免除其它义务,包括保护受试者不致遭受本来可避免的伤害,或得不到辩护的风险的义务。如果不是禁止所有可能对受试者健康造成危害的研究,包括有意使受试者感染某种病原体的人体挑战研究,那么就需要伦理学指导用以决定应该进行何种研究,不应该进行何种研究。《标准》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伦理学指导和要求,但是还有许多伦理问题尚待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无论各国疫情的流行情况如何,但来自政治、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以及对有效疫苗需求的紧迫性,都不应该影响我们对人体挑战试验可能使受试者遭受的风险进行科学、客观、理性的评估和伦理学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