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评黑格尔的“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 说
□朱 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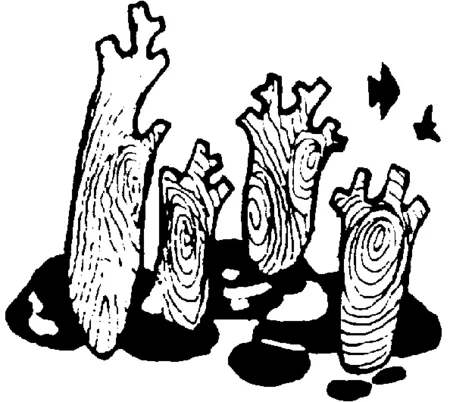
一、“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提出的背景
“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这句话出自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所著《哲学史讲演录》一书。当时,德国的哲学处于政权与教权冲突的漩涡之中,无法受到足够的关注。于是,黑格尔呼吁具有哲学研究传统的日耳曼民族发挥出自己的民族性,重新拾起对哲学的兴趣,以便在“世界精神”忙碌于现实,无法回复自身的时候,为其开辟道路使其回复自身,得到自觉。希望哲学重新受到人们的重视,是黑格尔所期待的。他认为,要想大众对哲学有所重视,必须以对哲学这个概念的界定为起点。而对哲学概念认识的首要条件就是厘清哲学所要研究的内容。宗教与哲学作为思想的产物,二者密切相关。研究哲学,必须同宗教、政治、科学、艺术有所区别。“由于宗教与哲学不分的看法流行,为了要使哲学史与宗教观念有一更明确的界限,对于足以区别宗教观念与哲学思想的形式略加确切考察,应该是很适合的。”(《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4页)于是,在这样的语境下,“东方哲学”被黑格尔用以区别宗教与哲学以及说明“哲学应是什么”这个命题。
对东方哲学的叙述被黑格尔安排在全书正文开始前的导言部分,而且他曾明确表达:“东方哲学本不属于我们现在所讲的题材和范围之内”(《哲学史讲演录》第115页),这表明在他看来东方哲学应该被排除在哲学史的范围之外。在《哲学史讲演录》中,他称:“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113页),甚至说:“我们所叫做东方哲学的,更适当地说,是一种一般东方人的宗教思想方式——一种宗教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可以把它认作哲学的。”(《哲学史讲演录》第115页)这里所称的东方哲学特指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且东方哲学之所以被称为宗教哲学,乃是因为“在古代东方,宗教与哲学是没有分开的,宗教的内容仍然保持着哲学的形式”(《哲学史讲演录》第64页)。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其实黑格尔在说这句话时并没有特地区分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根据他后文的叙述,“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中的东方哲学指的乃是印度哲学。因为在别处他曾提到:“在波斯和印度的宗教里有许多很深邃、崇高、思辨的思想被说出了。”(《哲学史讲演录》第64页)
二、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解
(一)印度哲学是宗教哲学
印度哲学被称作宗教哲学乃是因为在印度的宗教中包含着哲学的内容,但是它却不具有哲学的形式,宗教观念停留在普遍性中,没有发挥出主观性因素进入到个体的心灵,因此精神还停留在有限性中。具体来说,印度宗教的神灵与哲学中的最高理念一样具有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显示了哲学的观念与思想,但是印度宗教普遍化的形象在进入个体心灵时无法形成主观人格化的阶段,那么这种普遍化就是表面的,并未深入内在,因此是有限的、不彻底的。
乃至整个东方宗教的情形便是:“只有那唯一自在的本体才是真实的,个体若与自在自为者对立,则本身既不能有任何价值。也无法获得任何价值,只有与这个本体合而为一,它才有真正的价值。但与本体合而为一时,个体就停止其为主体,(主体就停止其为意识),而消逝于无意识之中了。”(《哲学史讲演录》第117页)这便是黑格尔所描述印度宗教的概况,至于印度宗教不能称作哲学而只能是宗教哲学乃是因为:印度宗教的神灵与哲学的最高理念都以普遍性的形式作为自己的起始,并且以追逐无限为各自的目标。宗教作为思想,指向人的内心和性灵,打开了主观性的范围,引导精神进入有限的表象方式的范围。永恒的东西作为精神的对象必然是进入有限的意识中被感觉到,因此在宗教中,“为这真的、永恒的事物所寄托的精神乃是有限的,精神之意识到它的方式也只包含在对有限的事物和关系的观念里和形式里”。但是精神作为普遍的、无限的、自己认识自己的存在,它不会拘泥在有限性中,只会在无限中自己认识自己。所以精神必然要超出个体性,进入它的对方(主观者的心灵),达到普遍者与特殊者的统一。印度的宗教,最高存在仅停留在外在的、客观形式的意识中,并未深入内在,进入个体的心灵。主体与个体是表面的统一,并未实现真正的合一,所以还未达到哲学的阶段。此外,宗教是理性自身启示的作品,是理性最高、最合理的作品。尽管宗教与哲学都以绝对本质、无限普遍的理念以及世界的本质、自然、精神的实体为认识对象。只不过最高理念呈现在宗教中以当下的直观与感觉的表象的形式,且宗教通过默祷、礼拜等仪式与它的对象——上帝统一。而哲学是通过思想、思辨的形式与最高理念合一,它是关于真理的科学,其目的在于认识真理之必然性,真理存在于知识中,真理既不能在直接的直觉中也不能在外在的感觉直观或理智的直观里被把握,只有在反思中才可以为我们所认识。
(二)中国古代没有哲学
黑格尔在谈中国哲学时,提到了孔子、《易经》以及道家的学说。他评价孔子的学问是“一种道德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第119页)。因为在他看来《论语》中所记载的孔子与弟子的谈话,仅是一些常识道德,并且这种道德每个民族都具有,所以毫无出色之处。孔子的学问被称为是“道德哲学”,是因为《论语》中的言论缺乏思辨性,“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这与黑格尔所理解的哲学标准不契合,因此称不上真正的哲学。《易经》显示了中国古代的思想不再停留在感性、具体的阶段,而是形成了抽象的、纯粹的范畴。但是这种纯粹的思想的范畴还不够深入,还没有达到概念化,仅仅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层面。而哲学作为概念的思维,是思想进一步规定的产物,它的发展是不断向内的深入,所以《易经》所表达的思想也称不上哲学。谈到道家的思想时,他认为“道”中包含了原始的理性,它产生宇宙、主宰宇宙。但是这种理性不同于哲学中思辨的理性,是一种超自然的理性,就像《道德经》中对“道”所描述的那样不可捉摸。并且道家将万物的起源规定为“无”,认为“无”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在黑格尔看来这乃是一种否认世界存在的做法。并且如果仅停留在否定的规定中,那万物的起源就无法解释,所以“有”应是作为万物存在的根本,然后才有“无”,“无”是对有的扬弃与超越。
三、东方哲学为什么不是哲学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宗教、哲学是精神这一范畴发展过程中所表现的不同形态,是精神在不同环节的显现。宗教、哲学都是思想的产物,作为绝对精神的意识形态,它们是精神自我认识过程的必要阶段。“哲学是这样一个形式:什么样的形式呢?它是最盛开的花朵。它是精神的整个形态的概念,它是整个客观环境的自觉和精神本质,它是时代的精神、作为自己正在思维的精神。”(《哲学史讲演录》第56页)精神对宗教外在的、有限的意识的扬弃便产生了哲学。逻辑上,哲学的起始在于:处于自在阶段的精神在宗教内感到自己是不自由的,随着精神的觉醒,它意识到自己是自由的,便开始冲破束缚,由自在向自为转变,将宗教作为自己的对象,并在这对象中认识自己,克服对方并将其作为自己发展的一个环节,最终到达哲学的阶段。这一过程在历史上则显示为:当一个民族有了自由意识,并且将“思想自己建立自己”的自由原则作为本民族存在的根本,便具有哲学产生的条件。从根本上讲,人是自由的,因为“所有的人都是有理性的,由于具有理性,所以就形式方面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性”(《哲学史讲演录》第26页)。一个民族当它以普遍性为思考的对象时,我们便称它开始有了自由。但是在东方,“意志的有限性是东方人的性格,因为他们的意志活动是被认作有限的,尚没有认识到意志的普遍性”(《哲学史讲演录》第95页)。意志的不自由导致思维的有限性,因此精神就无法思维普遍,意识到自己是独立自主的、自由的。历史上:“在东方只是一个人自由(专制君主),在希腊只有少数人自由,在日尔曼人的生活里,我们可以说,所有的人皆自由,这就是人作为人是自由的。”(《哲学史讲演录》第99页)其实,东方那唯一专制的人——皇帝也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是建立在别人也自由的基础上的。
哲学的发展是不断进步的,是世界精神不断冲破有限性而朝向对无限的追求。在东方,世界精神是停滞不前的:“它的文化、艺术、科学,简言之,它的整个理智活动是停滞不进的;譬如中国人也许就是这样,他们两千年以前在各方面就已达到和现在一样的水平。” (《哲学史讲演录》第8-9页)哲学概念只在表面上形成哲学的开始,但是真正的哲学需要思想不断的向内反省,对概念的证明才是哲学真正要做的事情,但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哲学是在发展中的系统,纯粹哲学表现其自身作为在时间中进展者的存在,它的目的在于认识那不变的、永恒的、自在自为的。它的目的是真理。哲学认识真理是通过一系列的理念实现的,即揭示出理念各种形态的推演和各种范畴在思想中被认识的必然性。哲学的发展亦依赖于理念的发展,理念是自身区别、自身发展的。理念发展的动力来自于内在的矛盾,矛盾的运动是由自在而自为的,所以理念必须要通过外化自己、认识自己、发展自己冲破自在达到自为。因此,理念的发展并非停滞不前,从它的本质来看,它就不是静止的,它的生命就是活动。哲学的运动乃是自由思想的活动,是思想世界、理智世界如何兴起,如何产生的历史。
四、结语
对黑格尔“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说的理解,应该分两个方面:印度哲学是宗教哲学;中国古代没有哲学。黑格尔对东方哲学的所有评判乃是基于精神哲学的立场,精神作为黑格尔哲学的最高范畴,是评判各民族是否存在哲学的标准。一直以来,东方宗教的特质便是将自然视为实体,西方宗教则是将精神作为实体,文化背景的差异是造成黑格尔对东方宗教、哲学评价有失偏颇的主要原因。再者,从黑格尔对中国哲学只言片语的评价中,明显可以看出他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仅仅用孔子的学问、《易经》、道家思想来举例证明中国没有哲学是非常片面的。而在黑格尔那里,对秦以后的中国思想发展状况只字未提。如此种种是造成他对中国哲学误会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