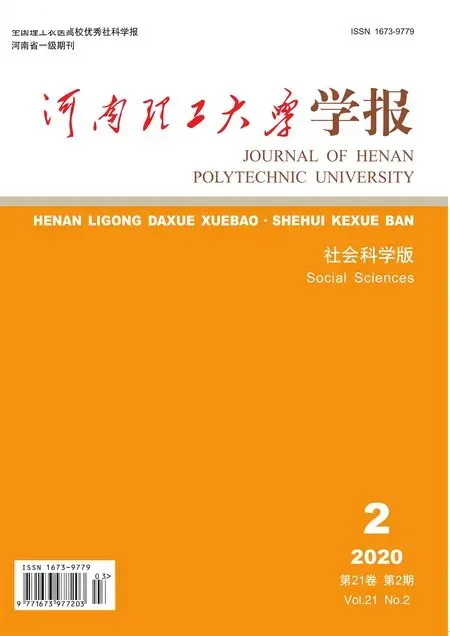从“真切”与“自然”双维度论王国维之意境说
——以《人间词话》为例
黄 健
(中央民族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1)
“境界”“意境”是中国传统文论核心范畴的一部分,历经数代学者的演绎与补充之后逐渐趋于成熟,并发展成为文学界、音乐界、绘画界、书法界等文艺领域甚至其他跨文化领域的极具东方色彩的学界术语。但其真正被定型并最终形成中国传统文论乃至文化界的一个关键词,却应归功于清末民初著名美学家王国维。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依托词论语境系统地阐释了核心概念“境界”,并赋予其特殊而丰富的美学底色和哲理意蕴。而一个尖锐而又有趣的问题亦伴随着王国维美学思想的研究一直萦绕不散,即王国维的境界说与后来更为广泛为人所知的意境说的关系问题。当前普遍为学界所接受的观点是,意境说以境界说为根基演变生成,前者脱胎于后者却比后者更为凝练生动。而具体体现于王国维的美学思想中,两者地位实则等同,但事实上此论断形成的原理在学界中并未达成共识,原因在于一直缺少某种切入王国维美学思想具体话语更为直观的途径。笔者研究发现,在境界说(实为意境说)大放光彩的著作《人间词话》中反复出现的“真切”与“自然”并非无的放矢,王国维境界说的众多重要观点都可以此二维为基点进行贯穿和概括,因而以此切入王国维的理论话语体系更能清晰地理清其中的学理瓜葛。本文试图从梳理境界说与意境说的渊源为起点,以“真切”与“自然”两个维度为剖析意境说的切入点,并具体阐释此双维度合力生成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即“有我之境”和“有我之境”,以期达到对王国维境界说的另一种解读,并在其看似完美的真与美的双维度理论构建中,指出其中的理论缺陷:对于善的维度的忽略而造成与社会历史现实严重脱节。
一、从境界说到意境说的嬗变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人间词话》第一则,以下引用均为此版本)王国维在《人间词话》开篇即引出境界范畴,认为词的胜景妙处在于有境界。其实,《人间词话》所提到的境界包含着几重含义,这是造成各家对境界的理解无法形成整体一致的根本原因之一。王国维境界说的含义大概分为以下几种:境界用于指人生境界,泛指一种哲学上抽象的界域,如“境界有二:有诗人之境界,有常人之境界”(《人间词话》第十六则);境界也用于指个人修养和精神层次,如“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境界……”(《人间词话》第二十六则);境界还能用于指作品中所描绘的景物和场面,如“‘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月’‘中天悬明月’……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人间词话》第五十一则)。
但在王国维《人间词话》中,境界最重要的内涵指向在于与传统审美范畴意境的高度相契合。王国维境界说体系的形成是在分析评点具体词作和词人、据此探讨文学本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认为构成文学的基本元素——“原质”:一是“景”,二是“情”。他在《文学小言》中说:“文学中有二原质焉:曰景,曰情。前者以描写自然及人生之事实为主,后者则吾人对此种事实之精神的态度也。故前者客观的,后者主观的也;前者知识的,后者感情的也。”[2]189-190王国维的立场承袭了传统文论中广泛为人共知的情景交融原则,此基调恰恰暗合了他对中国古代文学抒情特征和“天人合一”哲理追求的赞赏与继承。不仅如此,王国维在《人间词话》论及“造境”与“写境”、“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优美”与“宏壮”、“真景物”与“真感情”、“隔”与“不隔”等诗词审美范畴时,所指的境界与中国传统意义上强调的意境也是高度吻合的。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家、文论家一般认为“意境是我国古典文论独创的一个审美概念,是对抒情性作品内蕴的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形象系统及其所诱发和开拓的审美想象空间的一种界说”[3]216-217。据此而言,代表王国维境界说的重要作品《人间词话》的大致脉络和其所要表达的内涵与意境的理论思想是不谋而合的。意境的生发和更深层次的表现可以归结为虚实相交融、真境与神境的统一、寓有限见无穷的“天人合一”的瞬间领悟、超脱[4]14-21。中国传统的意境学说是王国维境界说的根源,二者对“天人合一”的追求是一致的。所以,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频繁使用的境界承袭了中国哲学和传统审美之余韵,与意境说在学理根基和理论沟通方面可谓一脉相承。
王国维的境界说是贯穿《人间词话》始终的主线,而与意境相容的有关思想理论才是境界说的真正核心。王国维后来写《宋元戏曲考》,在《元剧之文章》如此论及:“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谓之有意境?曰: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是也。古诗词之佳者,无不如是,元曲亦然。”[5]134开始用意境理论来评论一些文学现象和作品,此处提到的意境与王国维境界说所主张的“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人间词话》第五十六则)、“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则)等理论主张如出一辙。由此看出,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人间词话》中境界说内涵的高度概括,两者同源,意境说基于境界说而更加凝练,这也是王国维在其后的其他评论著作中很少使用他自创的境界说体系、反而改用意境这个术语的原因。王国维转而支持意境说并不是对境界说的否定,而是认为具有高度浓缩性的审美范畴意境更能够囊括他在境界说中所欲呈现的全部意图。
中国古典意境论是以儒为主、道佛相补的传统文化的诗学结晶,经钟嵘、皎然、司空图、严羽等人的立说与补充,再经王国维打磨始成体系[6]38-39。王国维的意境说与前人相比,显得更为完整、更加系统化、更有逻辑性,根本原因在于他将其理论建构在“真切”与“自然”这两个最基本的审美维度之上,具体呈现于词论名作《人间词话》。得益于“真切”和“自然”双维度的相互激荡交织、和谐共融,他的意境说具备更为丰富而独特的审美内涵,因此而使得境界、意境(下文统一概括为意境)逐渐成为现代中国文学、书画、音乐等领域的最重要的审美标准之一。
二、意境说的双维度:“真切”与“自然”
“真切”与“自然”是王国维意境说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两个概念,他们是两个最基本的审美范畴“真”与“美”的重要体现。通常而言,关于“真”,是指事物(或情感)本真的、本质的、原初的样貌状态,文学之“真”的要求是因为文学能促使人认识自己、认知世界,透过现象看到万物最本真的形态和面貌;而至于“美”,这是由文艺所具有的审美特征所决定的,美始终是文艺发展的起点和终点,文学之“美”在于人欣赏美的烛照所获得的审美理想,促使精神境界提升[3]151-152,170。在王国维的意境说美学思想体系中,此二者的演绎表现之一就对应着“真切”与“自然”。
(一)“真切”之“真”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人间词话》第六则),王国维认为境界的有无直接源于景物描绘是否逼真、感情抒发是否真诚。第一,景物之真。在景物描写中,要力求还原景物本真的面貌,王国维认为只有描绘出景物内在的“神理”才能寄托真切的感情。而神理,就是万物最本真的面貌,也就是真景物的表现。正如他在《人间词话》第三十六则所解释:“美成《青玉案》(当作《苏幕遮》)词:‘叶上初阳乾宿雨。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此真能得荷之神理者。觉白石《念奴娇》、《惜红衣》二词,犹有隔雾看花之恨。”王国维认为姜夔(字白石)咏物词不如周邦彦(字美成),原因在于不能得物之“神理”。第二,情感之真。作者情感的真诚是作品意境得以彰显的主基调。王国维最推崇李后主,他对李后主的评价是阅世浅而性情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俞浅则性情俞真,李后主是也”(《人间词话》第十七则),由于其性情极真,故能直抒情怀,不事雕琢伪装。恰若“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江山盛景消逝随流水落花,点点相思,化作天上人间两处离愁,也只有这样的真诚情感方能营造出如此真切感人的意境美。因而有人认为王国维将诗人性情之“真”与经历多少俗世、阅世深浅与否相对应,并据此得出王国维主观上存在某种避世的倾向,对封建礼教社会表现出内心的鄙夷,“王国维的这段话却包含了一种合理的理想,即是对封建社会的世道,特别是封建礼教扼杀了人的真诚,只有阅世浅才能发扬人的真诚。因而真感情也就是不受或少受封建礼教束缚的真诚”[7]84。类似的思想从王国维评说纳兰性德之“真”时说得更直白,在《人间词话》第五十二则中王国维说:“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由此出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他认为纳兰性德词之真切源于本性未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故其情真词亦真。王国维认为李后主和纳兰性德之所以能始终保持真性情、写纯真诗词,原因在于他们远离尘世、不与社会污浊风气同流。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社会保持“安全距离”的想法,一方面与他身处动荡年代而人心日下的社会风气相关;但另一方面,这种想法也促使他意图从真与美两个维度建构审美理想,并有意无意地将代表善维度的社会道德伦理排除在外,从而在他的意境说中呈现出脱离社会现实、浮于历史真实的乌托邦式色彩。这一观点沿袭了他早期在《文学小言》中所主张的“艺术无功利”纯文学思想,即“一切学问皆能以利禄劝,独哲学与文学不然”[8]27,从而在王国维的思想深处表现出两种自相矛盾的倾向,即倡导诗人真性情与逃离社会现实之间的张力,共同造成了他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现实伦理之“善”。
据此而言,在诗人真性情表达层面上,王国维标举性情之真并没错,具体体现于意境的营造离不开诗人真感情的代入,“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间词话》第十六则)。而真感情唯有当事人在摆脱个人意志、欲望、外界利害关系等的羁绊与奴役,短暂进入“自由”审美境界的时候最易出现[9]286。至此,景物之“真”与感情之“真”才能恰当地进行融合,相互渗透影响,二者缺一不可。在《〈人间词乙稿〉序》中王国维提到:“原夫文学之所以有意境者,以其能观也。出于观我者,意馀于境。而出于观物者,境多于意。然非物无以观我,而观我之时,又自有我在。故二者常互相错综,能有所偏重,而不能有所偏废也 。”[1]82这是对意境说中“意”与“境”关系的表述,也是对二者隐藏的内在联系之“真”的肯定。
如何写景才能真?如何写情才能真?王国维用“隔”与“不隔”来加以解释。所谓“隔”指的是所写景物不能畅快表达诗人的情感,如诗人用典、用代词、用砌字等片面追求字句格律,因此造成与诗人与诗、诗与读者、读者与诗人之间感情的隔阂,犹如雾里看花,显得情感不真切。而“不隔”则意在创造适合表达真感情的意境,没有“隔”的那些毛病。如王国维所举例欧阳修的《少年游》词“谢家池上,江淹浦畔”,认为其引出“谢家”的典故以写景显得景与情均不真切;“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人间词话》第三十九则),王国维评点姜夔词喜用典故,导致抒情不直接。王国维认为诗词用典故、代词等不能直觉地书写真感情,读者读来,终不能凭直觉感受到真情、深情。王国维关于“隔”与“不隔”的论述是建立在诗人与读者隔着时空互相交感的基础上,他认为诗人借景寄情应当“写情则沁人心脾,写景则在人耳目,述事则如其口出”[5]134,这样由读者直接观照到的审美意境才真实动人。因此,为了达到“不隔”之“真”的 目的,他反对用典故、代词、砌字等易造成感情不能自由表达的作诗手法。但他并不反对诗词中字句的反复锤炼,相反,他十分赞赏经过多重尝试而得出的新词语对意境产生的新鲜美感。如《人间词话》第七则:“‘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又如,“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方能见出草原之苍茫、天地之浩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方能见出南山夕阳的盛景、山间闲淡的雅意。在王国维的意境语境中,只有逼真的景物描绘与真挚的情感表达交织在一起,两者交融无间才能流露出真切的意境美。
(二)“自然”之“美”
“自然”之“美”是与“真切”之“真”完全不同的概念。在王国维的意境说中,由“真切”归纳出“真”或由“真”演绎出 “真切”这都不难理解,然而,由“自然”归纳出“美”或由“美”演绎出“自然”似乎不能成立。因此要理解“自然”与“美”的关系,必须先梳理王国维意境说标举的“自然”一说的来源,即“自然”一词在中国传统文论中的大概流变。
“自然”在本义上一般是指整个自然界,文论中引申为与主体意识相对应的外界事物,如整个景物。但在王国维意境说语境中,它还有契合中国古典文论“气之审美”的特征,“气之审美境层中形成的审美体悟要求在妙造自然中达到‘同自然之妙有’,这是由于意境理论的哲学根基是一种东方的大宇宙生命理论这一根本性质决定的。既然大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充满活色生香,气之审美作为对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生机活力与深层内涵的体认,就自然要体现把握万事万象万态千差万别的生机活力与生命内涵即把握其生命节奏与韵律的根本要求”[4]159。中国古典文论观里,“自然”是相当重要的审美评判标准。“自然”表征的是对“道”的契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即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终极体现和追求,讲究圆融透彻、和谐完满,它的表现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气”,如“气象”“气韵”“滋味”等虚无缥缈又隐有所指的概念都可以看作是气之审美的体现。“自然”是道的外在表征,它亦暗合一种和谐融洽、天然如此的境界。因而,作为审美范畴的“自然”早已脱离了“自然界”此类字面含义的范围,而成为在动静中、虚实间把握天人相合的节奏与韵律的一种审美标准。据此而言,此“自然”直指“道”的存在意义、“美”的直觉观照。至此,“自然”与“美”之间形成了互照——“美”是本质,“自然”是其最重要的表现,二者皆指向“道”——“天人合一”的彼岸。
王国维意境说中标举的“自然”即是对“美”的直觉观照的回归。在《人间词话》第五十二则中,他评价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便是肯定其天然不加修饰、直奔美之根源的做法;在《宋元戏曲考》之《元剧之文章》中,王国维曰:“元曲之佳处何在?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著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无不可也。”[5]133这些无不表明王国维所追求的那种意境美与上述之“自然”息息相关。
从写诗手法的“自然”上来说,首先,“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由分。然二者破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人间词话》第二则),在本句中姑且不论“理想与现实二派”是否来源于西方的论说,只从其“合乎自然”与“邻于理想”来考证,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诗人在造境、写境中都符合“自然”中的事物规律、道的规则。其次,“自然中之物相互关系,相互限制。然其写之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律。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人间词话》第五则),这段话说得更透彻,表明不仅是描绘的事物,就连事物之间的那种关系和诗人头脑中的意象,都应当遵循“自然之法律”。最后,“世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第六十则),诗人对宇宙人生的观察“入乎其内”才能发现“自然”的生气和韵律,“出乎其外”才能将之与诗的情思和谐交织、自然融合。
从诗的意境“自然”上来说,王国维意境说支持的是那些自然不做作且能得人生真味、天地至理的作品。“‘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月’、‘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此种境界,可谓千古壮观”(《人间词话》第五十一则),这些意境共有的特点是都暗合某种禅意,读之令人心生激荡,进而思索人生宇宙之奥妙。值得注意的是,“真切”与“自然”双维度在意境中并非独立发挥作用,而是互相交织、彼此成就。“真切”描绘真景物、抒发真感情,都离不开“自然”的平衡,“自然”是“真切”健康成长的“骨骼”;反之,“自然”的体现也不能建立在假景物、假感情的基础之上,因为他们不能承载和传达“自然”之美。王国维的意境,“真切”与“自然”双维度始终和谐地贯穿其间,他并没有偏颇某一方。“大家之作其言情也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人间词话》第五十六则),其情真故能感人肺腑,其景真故能使人六感愉悦,能引发如此效果是因为这样的“真”是符合人对“天人合一”的那种“自然”的欲求;“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只因其符合“自然”的道义,自能充分表现真景真情。至此,“真切”与“自然”在意境中达成统一、同化,共同支撑起意境这座审美大厦。
三、“真切”与“自然”的耦合:“有我”与“无我”
关于王国维意境说“真切”与“自然”二维“天作之合”的具体阐释,需从其理论本身的“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进行评述,此二者是王国维意境说中“真切”与“自然”之间合力的不同外化体现。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指出:“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万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对此,朱光潜在《诗的隐与显——关于王静安的〈人间词话〉的几点意见》[10]85-88中变用西方美学家立普斯的移情说,即以“移情作用”对王国维的相关理论进行诠释和解读,认为“有我”即是由于我的情趣移注于物使物有了“感情”,这种现象在注意力专注到物我两忘时才发生;而“无我”是我和物未得到分离,我的感情没有超脱出来,依然同物混合。朱光潜认为这是王国维不知诗的感情有隐、显之别,“有我”感情隐而深、“无我”感情显而浅。据此朱光潜用“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重新定义王国维的“有我”与“无我”,这样的解读有待商榷。下面试从“真切”与“自然”二维对两者进行分析。
王国维意境说中的“有我”,我作为主体,是不自由的主体,我还存有我在现实中的意志,因而与外界存在某种对立利害关系,这造成我与外物的主客二分,因此以我未得到的超脱感情观照外物,外物便带着我不自由的意志、未超脱的情感[11]201-201。“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少妇泪眼中的落花无不暗合她凄苦的命运,情真意切;“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感情真切,人处孤馆感到春天美好却寒冷无比,只缘于心中希望破灭后的百般迷茫。而“无我”,则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 ,何者为物”,我这个主体意志,已经摆脱了与现实间的利害关系,不再受现实束缚而进入物我两忘的超脱审美妙境,“审美愉悦也正是从这种‘物我无间’、自由无限的境界中产生”[12]159。我的主体意识还在,但它已潜入所观察事物的深处,自然而然地随意象动而动,抑或变成两个主体间的自然互动和交流。这样的“以物观物”思想暗合现代主体间性美学思想的某些原理。“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是前主体间性的主体间性,是主体尚未获得完全独立状态的主体间性。中国古典美学的主体间性植根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文化土壤中。‘天人合一’指的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都是浑然未分,天地万物与人的生命直接沟通,人与自然有机统一。”[13]21-25从此角度看,“以物观物”便成为我与物两个主体之间自由自在地交流、融合,这其中体现的是“天人合一”的和谐与“自然”。当然这样的“自然”之美必须建立真景物真感情的基础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物我淡然不分,悠悠闲情已融入南山体内和它交汇,我自获得“真意”;“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起”“下”之间,景物从容潇洒的姿态与我相拥相融,共赴“自然”之道。
再来比较“有我”与“无我”。“有我”的存在是由于有我之感情进行带动,而“无我”也有感情的渗透,它的存在却必须以我与物不分你我的交融为前提。朱光潜引入“移情作用”解释感情的进入方式是颇有见地的,因为无论是“有我”还是“无我”都是诗人创造出来的,就不免带有主观色彩。但他据此引入隐与显、超物与同物的概念来解释“有我”与“无我”的区别则稍显牵强,因为这是两对并不同质的概念。王国维的“有我”与“无我”强调的是我与物之间如何建立“真切”与“自然”之关系,而朱光潜的“超物”与“同物”强调的则是创作中主体感情代入的方式及其表现出来的程度隐显之别。
实际上,“有我”和“无我”是在有意境的前提上进行分化,这个前提就表明了对待“真切”与“自然”之时不可偏颇其一,因为只有当他们同时存在时才能蕴生“意境”,其中区别只是在于“真切”和“自然”在“有我”和“无我”之间所占据的比重不同。“有我”是指“真切”的成分比“自然”的成分稍重,这可从诗词中流露出明显的主体感情色彩窥见一二。这是与“诗言情”“兴观群怨”等传统文论相吻合的,也是大部分诗词所能达到的境界,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三则中所指出,“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有我”侧重的是“我之色彩”的充分表现,这与意境要求的写真景物、真感情并不矛盾,它反而使真景物与真感情的联系更加密切。相比于“有我”而言,“无我”对我与物之间“真切”与“自然”的融洽程度要求更高。欲达到“无我”,不仅“真切”与“自然”完美融合、不分彼此,而且更进一步流露出那种韵味无穷的“玄外之响”,此玄外之响的出现意味着意境走向了更高层次——“天人合一”。因此,“无我”可以看作是在“有我”的基础上进一步生发出来的,是对“有我”的超越,它要求超脱现实与自我,旨在全身心沉浸于“天人合一”的妙境,体悟其中“道”之真意。可见,“无我”比“有我”更加珍贵、更难达到、更为罕见。故王国维才有此一说:“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人间词话》第三则)他认为要达到无我之境,只有那些卓绝不群、才华出众的大文豪才有如此笔力。“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之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人间词话》第三十八则)
“无我”与“有我”获得的条件及其产生的美感也大为迥异。王国维云:“无我之境,人惟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第四则)“无我”是人的意志在摆脱与现实的利害关系之心境下静观得到,而“有我”是人在各种纷扰的现实中无法摆脱各式利害关系的束缚,偶尔在尘埃落定获得片刻安宁,在这种“由动之静时”的限制下获得[10]201-202,此二“静”字道出了其中深藏的含义——对真与美的回归。无论是“有我”还是“无我”,最终都要回归“真切”与“自然”这个大前提,只有在此意境中的“有我”与“无我”才拥有赖以生存的土壤。无论如何,“有我”与“无我”对真与美的不懈追求都是为了获得意境更深层的内蕴——玄外之响。诗词境界的大小不能成为评判优劣的标准,如“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并不比“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逊色丝毫,然而诗词的优劣却可以通过能否激发出“玄外之响”以及激发出的程度来进行直观的审美判断。因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四十二则评姜夔之词时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惜不于意境上用力,故觉无言外之味,玄外之响,终不能与于第一流之作者也。”他认为诗词的“言外之味,玄外之响”才是意境的最终追求,也是诗词能够始终永葆魅力的根本。可以看出,王国维意境说指出欲使诗词达到“言外之味,玄外之响”,就要在表现上做到含蓄有深味,在内容上做到情景交融,将“真切”与“自然”进行互通融合,以期激发读者再想象、再创造的空间诞生,进而获得共鸣、净化、升华等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达到“天人合一”的胜境。从另一角度而言,在“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都随之矣”(《人间词话》卷下,第十二则)中,可以看出王国维认可严羽论诗的妙悟、王士祯论诗的神韵都能触及“言外之味,玄外之响”的境界,但意境较之两者更触及根本。
至此,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在“真切”与“自然”(真与美)二维的合力支撑下寻找到了他们的共同归宿——“玄外之响”。只是,相较而言,“无我”更易达到这一境地。这一点也是与王国维意境说中并不反对“有我”的存在但更加推举“无我”的主张是相符的,即以“真切”与“自然”为基础的意境无大小之分,但有深浅之别。
四、结 语
王国维的意境说脱胎于其境界理论,在著名词论《人间词话》中,他从“真切”与“自然”两个彼此共融的维度出发,阐释了“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的意境生成在于寻求审美的最高理想——获得“玄外之响”。这相比于前人的意境说而言,无疑更显出王国维理论的自恰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从而为意境说在中国现代文论体系构建中做出强有力的开创和铺垫。但是,王国维意境说最危险的举动恰恰来源于他的“艺术无功利”纯文学主张,尽管存在清末政治与官场极度腐败、社会道德世风日下等客观因素,但极端推崇文学的纯粹自主性而完全与社会历史现实相脱离,这本身就体现了王国维思想的局限性以及对于“艺术源于生活”这一基本事实的认识不彻底性。因而,自王国维有意无意中将社会伦理道德层面之“善”审美维度排除在外之初,他依托于“真切”与“自然”双维度构造的意境理论就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与社会历史现实相脱节的虚幻性,这使得其精心营建的意境审美大厦犹如空中楼阁,脆弱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