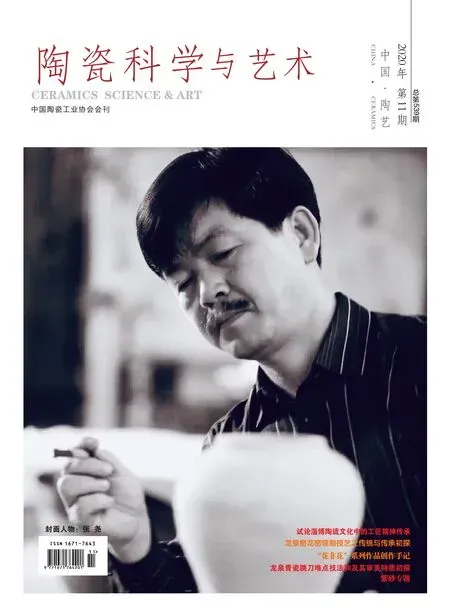论明清时期文人与紫砂匠人在紫砂领域合作的动因
周品鑫
清代,宜兴紫砂的发展和影响力到达了一个高峰。宜兴紫砂具有砂质与泥质相结合的特殊的肌理效果,有着优异的透气性,不闷茶汤,这一特性在明代已被时人发现熟知。紫砂器的的制作技艺在明晚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宜兴制壶匠人人才辈出,李养心、时大彬、徐士衡、陈仲美、陈子畦等一批制壶高手的出现,使紫砂器开始从普通日用陶器中脱颖而出。正是这些制壶高手巧夺天工,从当时的青铜器、金银器、编织器物等中汲取养分,丰富了紫砂器的制作技法和门类,为紫砂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明至清,紫砂器的制作技艺在明代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品种也愈来愈繁多,装饰手法和制壶工艺出现了新的创造与发明,在康乾时期一度成为贡品。王友兰、陈鸣远、惠逸公、许晋侯等一批制壶高手名家在这一时期涌现出来,使得紫砂器在制作工艺及水准上愈发专业化和艺术化。正是有这些大师巨匠在工艺上不断追求探索,使得紫砂从实用器迈入到艺术品的领域成为可能,才有机会以“雅玩”的形式摆上了上流社会、文人墨客的桌边案头。
文人士大夫的移情需求。由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兴起多起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及“科场案”,对文人阶层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使得广大的文人士子们感到不寒而栗,在朝的惶惶不安,在野的失望落魄。在这个时代背景下,无可避免的催生了“避世”的处世态度,这些孤傲的文人士子们又在努力追寻寄托内心情感,展示自我才华的途径。而这些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收到儒家“入世”文化的熏陶,内心依然有着入世的憧憬,然而残酷现实往往让他们陷入憧憬与现实的矛盾挣扎中,他们在生活的细微处寻找着安慰,在安慰中又感到失落。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的“出世”思想引导他们去追求田园风光闲云野鹤的生活,于是出现了一种及矛盾有统一的性格特征。他们有时行为偏执,乖张怪癖,孤傲;有时又寄情于山水,放纵恣肆,娱情享乐;有时自我哀怨,壮志难舒,徒增伤感;这种独特的个性在后世我们往往称之为“明清风流”,与“魏晋风骨”、“唐宋风尚”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把这个时期的美学发展称为中国美学发展史上的“伤感文学”时期,这种情感由《离骚》文化传承而来,在封建王朝末期发展成熟产生的一种情绪,也可以理解为对于生命自由的呐喊。庄禅的思想一方面引导着远离俗世的态度,同时庄子超越生死,超越功利,超越俗世一切的思想境界也在文人审美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庄禅思想对于文人审美情趣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对于“空灵”、“简素”、“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这种“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使得文人自身的艺术成就能够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度。所有的这一切情感与人生理想,在现实中找不到宣泄之口,这些文人士子便将他们完完全全地倾注在艺术创作与艺术实践里了。文人雅士们在自己的艺术生活中“聊发胸中意气”,宣泄满腔的情感,而借紫砂器的创造在当时也成为了一种“时髦”的方式。而这种寄托在具体紫砂器皿上的审美情趣,比起单一书法绘画挥洒笔墨,来的更为立体丰满,也更为耐人寻味。正是历史的诸多合力使得无数的文人雅士能与紫砂匠人合作创造,将自身的文化修养艺术审美融入一方壶中成为了可能。
紫砂匠人的主动迎合。清代时,紫砂匠人主动与文人雅士合作宜兴紫砂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风尚。据吴骞《阳羡名陶录·家溯》记载:“鸣远一技之能,间世特出,自百余年来,诸家传感器日少,故其名尤噪。 足迹所至,文人学士争相延揽,常至海盐馆张氏之涉园,桐乡则汪柯庭家,海宁则陈氏、曹氏、马氏,多有其手作,而与杨中允晚研交尤厚……制作精雅,真可与三代古器并列。 窃谓就使与大彬诸子周旋、恐未甘退就就被莒莒之列耳。” 虽然手工业者在社会上的地位卑微,不能进入大雅之堂,但如果受到文人的青睐,他们的社会地位还是可以提高的。再者,如果作品与文人合作,刻有名人题词,甚至著书立传,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效果,一方面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文人雅致。
文人与紫砂匠人的经济因素。梅调鼎、任伯年等文人生活清贫,梅调鼎家境贫寒,仅在钱庄当司帐谋生;任伯年曾一度流落街头卖画为生,后得胡公寿提携才有所好转。当时紫砂名手所制作的紫砂壶,重不过数两,价重每一、二十金,能使土与黄金争价,若有书画名家着以字画,更加价值不菲,这对于文人和紫砂匠人来说都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将赠送宜兴紫砂壶作为文人间礼尚往来的风尚。陈文述的《画林新咏》有以下的记述“山阴朱石梅仿古,以精锡制茗壶刻字其上,余在江都水陆通衢,嘉宾莅止例饋肴烝,因其虚掷受者未必属餍徒,损物命乃易制器,以订永好,茗壶其一也。易字而画花卉人物皆可奏刀。友人王善才、朱贞士、刘仁山并工此技,以比曼生砂壶曰云壶。余不欲与寒士竞名,故仍归之石梅旧制焉。”此段虽说锡壶,但亦勾勒出紫砂壶在乾嘉时期当做赠送纪念品的原因,不像食品容易腐败,不一定合受赠者口味,茶壶不腐坏,可在壶上刻字,如同碑文永久留传,当礼品送最合适。又鉴于砂壶容易打破,才有锡包砂壶的出现,希望永久留传,总比“秀才人情纸一张”,来得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