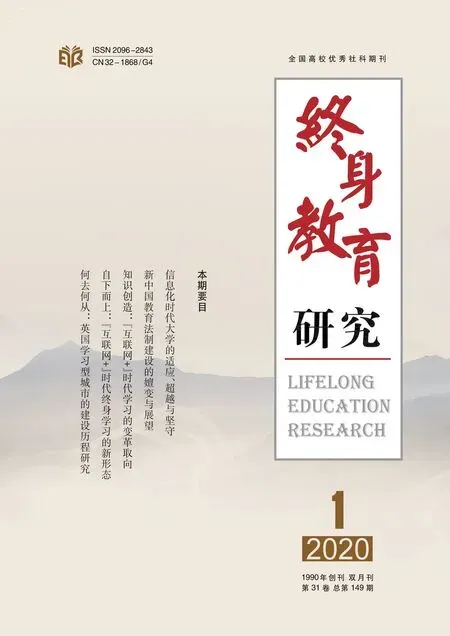何去何从:英国学习型城市的建设历程研究
□ 马丁·亚尼特
原文出处:Martin Yarnit. Whatever became of the learning city?JournalofAdultandContinuingEducation,2015(2):24-35.(中文版权归《终身教育研究》期刊所有)
译者简介:马鹏程,华东师范大学成人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比较成人教育和成人学习理论等
自18世纪英国开始工业化进程以来,教育和学习一直对城市的发展至关重要。20多年前,互联网时代尚未到来,唐纳德·赫希(Donald Hirsch[1])1992年就为经合组织(OECD)编写过《城市终身学习战略》(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该报告一经问世,便受到全世界教育界的欢迎,促使英国开始了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建设。“城市可以通过动员教育和终身学习资源来塑造城市自身的命运”, 赫希的观点得到了广泛共鸣——从1994年的少数几个城市发展到2001年的39个城市(包括澳大利亚的沃东加),这些城市中不仅包括了像利物浦、谢菲尔德、伯明翰和爱丁堡等这样的大型城市,还有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中型城市。部长们在议会上发表讲话,强调政府应给予财政支持。但到2003年,英国学习型城市网络(Learning Cities Network,LCN)开始走向衰落,到现在已不复存在。
尽管学习型城市在英国已不再普遍,但作为衡量城市发展的一个综合维度,这种理念的精髓仍然存在。在本文中,笔者将论证以下几个观点:
(1)虽然关于终身学习的言论很多,但学习型城市的概念未能获得城市管理者(政治家和高级官员或政府)的注意;
(2)在某些领域引发城市发展的新思考;
(3)重新评估教育本身作为经济的一部分的作用;
(4)采取措施以改进教育提供者之间和教育提供者与其他服务机构的关系;
(5)(在微观上)认识到学习之于城市发展的价值——贡献极具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必须强调的是,本文仅讨论英格兰学习型城市的发展。虽然在英国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趋势,但越来越多的政府下放权力已然成为事实,使这一讨论从英格兰推广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变得困难重重。
一、新的曙光
唐纳德·赫希于1992年在经合组织做了《城市终身学习战略》( City Strategies for Lifelong Learning)的报告,该报告的出版成为创立LCN 的契机。根据对欧洲、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地区约10个大型城市的研究,他认为,城市本身或许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为它(城市本身)可以有计划地尝试调动教育和培训资源,以促进城市复兴和社会正义。在赫希的研究成果发表时,学习型城市的概念就已经很明确了。第一次教育型城市建设大会于1989年在巴塞罗那举行。截至1995年底,100多个城市签订了《教育型城市宪章》(Charter of Educating Cities)。在赫希报告发表后的几年里,英国一些城市开始采用“学习”这个名称,随着采用的城市越来越多,1995年1月,学习型城市网络成立大会顺利召开。①
“来自教育、培训和商业领域的资深人士宣称要在诺威奇推广‘从摇篮到坟墓’的学习文化,这些事件标志着‘学习型城市’的诞生。”
“本周,轮到赫尔加入城市网络,其目标不仅是促进学习成为当地经济的基石,并且要使之具备应付社会拒斥的能力。为了促进发展和分享观点,赫尔去年成立了学习型城市网络。”
“负责人斯蒂芬·马丁(Stphen Maitin)认为,学习型城市将为地方政府、学校、继续与高等教育与培训及企业理事会提供有关终身学习的通用议程。他说:‘在缺乏国家指导的情况下,许多地方社区正在建立和发展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地方伙伴关系。’”
(泰晤士报教育副刊,1996年9月20日)
1996年,欧洲委员会将该年度命名为欧洲终身学习年,进一步推动了终身学习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政府也渐渐对“终身学习”“学习型城市”产生了兴趣。保守派国务卿兼教育部长吉莉安·谢夫德(Gillian Shepherd)筹得少量资金,以支持家乡诺福克郡的发展,并委托国家成人与继续教育协会(National Institute of Adult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NIACE)评估英国学习型城市运动的发展潜力。②1997年成功竞选的工党也给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带来了一次重大而短暂的政治助推。
1997年5月,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打着“教育、教育和教育(education, education and education)”的旗号上台执政,当时的教育部长大卫·布伦基特(David Blunkett)迅速发表了“学习时代”(The Learning Age)[2-3],这是一次对终身学习的呼吁,承诺会将NIACE争取了十多年所获得的政策付诸实践。布伦基特设立了“学习和技能委员会”(Learning and Skill Council),旨在资助16岁以上人群参与教育和培训(大学除外),其职责是提供资金、促进成人的学习和参与。NIACE还通过新设立的成人学习和社区学习基金,支持一些呼应终身学习整体系统的地方计划,这些计划通过综合服务,使失学者能够恢复学习并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组织。
1998年,大卫·布朗基特在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举行的学习型城市网络全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启动了绩效评估工具,评估工具由政府出资,NIACE资深人士苏·卡拉(时为市长)和伯明翰大学斯图亚特·兰森(Stuart Ranson)教授[4]负责编写。本研究以英国学习型城市的实践研究为基础,从参与、伙伴关系、绩效(Participation,Partnership,Performance,3P )三个方面进行总结。参与是指让人们参与学习并通过生活课程促进学习的技巧;伙伴关系主要关注义务教育后的学习,为终身学习建立全市性结构的合作规划(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学前教育和学校教育成为大多数学习型城市关注的问题)。如果参与和伙伴关系是学习型社区的基础,那么绩效就是保证该机体有效运作的工具。
LCN发展迅速,吸引了英国大部分城市加入,包括伯明翰、利物浦和爱丁堡,以及约克、南安普顿和诺维奇等为数不少的中型城市。几乎所有创建学习型城市的倡议都是由地方政府、学院、大学或诸如工人教育协会(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WEA)等志愿协会聘用成人学习专业人员发起和进行的,如“诺维奇倡议”就是由学习和技能委员会的经济发展部门发起的。LCN官方还在北爱尔兰、澳大利亚的会议上发言,并和设立在巴塞罗那的国际教育型城市协会建立了联系。目前,LCN是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城市网络。
二、全盛时期
有了工党的认可,NIACE和LCN得到了资金支持,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重要的是,LCN与英国教育和就业部、地方政府协会(该机构是所有英国地方政府的代表)联合发表了LCN对英国学习型城市的评估(包括哥德堡和鹿特丹在内的8个国内案例研究)[5]。
NIACE在政府制定基本技能政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LCN与教育部组织了一系列全国性活动,以推广“新生活技能(识字和算术)计划”。两个组织都对政府的国民社区振兴战略表示欢迎,认为这是将地方性终身学习计划纳入新城市运动框架的绝佳机会。LCN作为建立终身学习伙伴关系的“领头羊”,在一系列全国性活动的推广过程中,与当地教育和培训提供方共同讨论规划并分工协作。在英格兰,这种模式成为地方政府及其合作伙伴所构建的地方战略合作伙伴关系(Local Strategic Partnerships,LSPs)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得到了政府的资金支持。LSPs的主要目的是动员公共、私营和非营利组织围绕已商定的计划,缩小小型社区与其他社区之间的差距。几乎在每一个案例中,都设定改善健康、教育和培训效果、就业、住房、犯罪和环境的目标。政府还于2003年出版了儿童和青年新政《每个孩子都重要》(Every Child Matters),进一步推动英国的学前教育。[6]基础性立法《儿童法》(Children Act,2004年)旨在加强儿童服务,学校和儿童中心成为当地服务协调中心,这一战略与学习型城市相呼应,侧重于服务提供者之间的交流和协作。
三、衰落
2003年英国工党第二次选举获胜后,加强了有关缩小社会和教育差距的政策。新生活技能政策也聚焦于此,地方政府和财政部更愿意拨款支持更实用的技能和专业,结果使得更宏观更广泛的终身学习开始消弱。NIACE提醒这种狭隘的短视会把许多最需要识字和计算能力的人排除在外。一语成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系列举措的后果是参与学习的成人人数明显减少。2011年NIACE的调查显示,相比1996年的初测,男性的学习参与程度降到最低,其中基础技能组和失业组的比例比前一年下降了7%,65岁到74岁年龄组的比例也在下降。[7]另一方面,一些政治家仍然支持大卫·布伦基特早先的设想,因此,2003年国家教育部又宣布了一项新的倡议,即“试验田学习型社区”(Testbed Learning Communities,TLCs),由国家教育和文化研究所管理,强调利用新方法,促进最贫困地区更广泛地参与学习。当地一些组织筹集了一些小额赠款,创设了旨在鼓励学习参与的试验田方案。虽然试验田的规模和持续时间有限,无法产生可靠的结果,但很明显,还是得到了许多有推广意义的成果。一份关于试验田学习型社区的报告表明,他们“因其自下而上的服务意识和提供方、志愿者和社区组织良好合作关系而受到重视”[7]。同时,该报告还列出了在试验田方案中出现的一些新的服务模式——赋权模式,顾名思义,即赋予当地社区组织和当地居民权力的模式。
到2003年,LCN已现疲态。成员数量从2002年37个成员城市这一峰值开始下降,该组织开始就未来战略这一话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其实讨论往往就是影响力削弱的明确表象。这是否意味着学习型城市概念本身正在消亡?更有甚者传来这样的新闻报道——“如何说服政府和大学向LCN 交年费?”“学习型城市标志或已在这几个城市消失?”很明显,在大多数地方,这一概念没能在教育界获得一种超越地缘的广泛认同:对于关键的地方人物——地方政府的领导和大牌CEO、商业领袖来说,学习型城市和终身学习都未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些想法也未能给高级公务员或非教育部门的政客留下持久深远的印象。2012年,政府各部门各自规划地方倡议的状况与1992年如出一辙,这种情况促使议会呼吁合并部门预算以实现效率最大化。[9]另一方面,教育和培训机构之间的地方协作因其有助于制定城市战略和裁定优先支出项目,逐渐成为地方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人学习的传统主题,如自我导向学习、帮助弱势群体、志愿机构在解决社会拒斥问题中的关键作用,渐渐在当地政治家和专业人士中获得了更广泛的群众基础。学校在政府的鼓励下也开始扩大服务范围,热衷与当地社区有群众基础的成人学习组织进行多方合作。同样,在许多其他领域,政府的就业服务部门也与学习型社区建立起了联系。国家学习和技能委员会(National Learning and Skill Council)不断为学习型社区呼吁提供财政支持,让与传统教育和培训机构(如大学)合作不顺的社区最终也能够顺利地参与进来。
因此,尽管“学习型城市”这个名称的影响力有所下降,但“学习型社区”这一概念却在当地LSPs和英格兰各地街区的众多组织建设和倡导下,扩大了其在地方的影响力。由于政府将重点放在缩小教育、就业、医疗和住房方面的差距上,因此,规划弱势群体如何有效参与学习,已成为教育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共同责任。意识到这一点,同时考虑到非正式学习的特殊性,政府于2010年推出另一项小规模举措,以提升成人非正式学习的价值。与技术委员会一样,邀请当地的各个组织投资小额资金建设试验田,邀请人们参与学习并进行测试。然而,尽管该倡议受到欢迎,但投入非正规教育与学习的资金远不如正规教育和培训的资金雄厚。实际上,在经历了“学习时代”的繁忙之后,政府对终身学习政策的关注已经减少到只有技能和正规资格认定这两个方面。终身学习已经成为一种过时的想法,一种被政府、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区摒弃的观念。
四、教育一体化与城市发展
令人惊讶的是,20世纪90年代,“终身学习即教育和培训”这一狭隘的定义竟被纳入城市规划和管理体系中。查阅5年前的城市政策教科书,几乎没有提到学校、学院和成人学习[10],但最近几年的变化很明显。起初,LSPs 要求加大成人教育和培训的比例,乍看上去像是地方政客和高级理事会官员“脑袋一拍”的想法,但城市及周边地区对教育和培训需求的增长也的确有目共睹。像默西塞德郡、大曼彻斯特和伯明翰这样的城市正努力将就业、投资和教育联系起来,以此作为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时增强抵御能力的一种方式。
赫塞尔廷(Heseltine)勋爵2012年[11]在他关于联合政府区域发展报告《千方百计》(No Stone Unturned)中专门用了一整章的篇幅论述教育和培训问题,强调必须将教育和商业联系起来,以及社区的广泛加入才能克服根深蒂固的参与障碍问题。他的核心建议是将目前由中央政府各部门持有的主要预算有效地移交给地方,以新的方式建立LSPs,设定经济发展的优先顺序。但就在最近,一个议会委员会对地方企业进行审查后发现,该地方企业并未跟教育提供方接触。创新创业和技能特别委员会(The Business,Innovation & Skills Select Committee)[12]在其关于LSPs的报告(2012—2013年)中建议,“地方经济合作者必须阐明其参与地方教育的程度,特别是在学徒制中提供机构、继续教育学院和学校教育中的参与程度。” 鉴于伙伴关系对学习型城市和学习型社区至关重要,有必要问一问它是否确实产生了作用。事实上机构之间的合作比各自为政更有成效,这也是英国各地政府钟爱的做法,但要找到证据来支持这一论点却很棘手。一项由政府出资的重要评估结果显得苍白无力:“总的来说,虽然只有10%的LSPs进行过成本效益分析,但84%的受访者非常赞同LSPs所发挥的效益大于其在时间、能源和资源方面的收益。”[13]
该报告的支持者经常强调从这种具有共享特色的模式中所获得的收益。可以看出,通过合作,英国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组织得以从20年前基本被放弃的状态,后来居上为城市整体发展做出贡献,这一贡献也丰富了城市关于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五、绩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10月在北京召开国际会议,发布学习型城市倡议,并开发学习型城市进程评估指标框架。在这个“看事实制定政策”的时代,这一举措是大势所趋。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反思英国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经验。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了一种美好的愿景,但实际上,各个成员国对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视程度普遍较低,而且制定评价标准和体系也未能取得较大进展。主要原因有两方面:一方面,从业者不愿意从既有事务中抽出时间和资源来创建评估计划;另一方面,可用于评估学习型城市进展的现有数据通常是为其他项目设计的,很少有非常契合的数据,而采集新数据需要高昂的成本。加拿大和欧盟在资助城市网络后都发现,设计和使用评估体系完全是两码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全球成员在这方面能否做得更好,还有待观察。
圆明园是一座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殿堂金碧辉煌,亭台楼阁玲珑剔透。园内有民族建筑,有西洋景观;有山乡村野的田园风光,有驰名中外的风景名胜;珍藏着历代的名人书画,各种罕见的奇珍异宝,就是这样的伟大建筑,是怎样被外国侵略者毁灭的呢下面,我们就来学习第三段课文。
同时还有一些因素相互影响。根据笔者的经验,在收集数据和设计指标时,管理者倾向于易于收集、可靠的数据,和能够与其他城市进行比较的指标。但学习型城市的指标既要反映城市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发展,又要反映城市解决问题的能力(比如后者,“观测其在解决失业或无家可归等问题的处理效果”可以作为评价指标)。一方面,指标过多会加大数据分析的难度,对于非专业人员而言,做年份比较和不同城市比较分析难有成效;另一方面,过于简单的数据,可能会得到一些无关痛痒、浮于表面的分析结果,无法反映群体差异,例如社区学习的总体参与率往往会掩盖社会群体和性别之间的重要差异。经验表明,过分依赖质性意见的调查存在局限,有的调查者可能不愿意进行长期调查;不同城市的调查结果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类比分析。
六、成就
虽然“学习型城市”开创的方法在其他城市和领域尚不具备确切的推广性,但目前能够达成共识的是,LCN有助于促成决策者之间形成统一的舆论氛围,从而有利于某些想法和倡议的推广。即使只有邓迪、布里斯托、约克和埃克塞特等少数城市继续以“学习型城市”自居,直到2010年,仍然有数十个英国城镇在做扩大参与和建设伙伴关系的有益尝试。这里有几点做法值得探讨。
1.学习支持模式
在学习支持模式中,当地居民作为志愿者,鼓励朋友、邻居甚至陌生人参与学习。贝尔法斯特、诺丁汉和谢菲尔德在LCN的建设初期就尝试这种做法,到2011年,报告显示全英格兰使用此类学习模式的城市有44个之多。[14]研究显示,学习支持模式有四个不同的功能:(1)目标作用,为潜在的学习者提供合适的课程或活动方面的建议;(2)扩大原有的服务范围;(3)提供支持与指导;(4)将其他学习者转化为学习提供者。该报告同时表明,该模式的成功离不开两种人:(1)对“学习改变生活”有着深切体会的人;(2)好学的社区常住居民。
2009年,政府制定了关于学习支持模式的国家方案,作为促进成人非正式学习新战略的一部分,即“学习革命”(Learning Revolution)[15]。到2011年,有2 000人(其中大多来自弱势群体)加入并在培训后成为学习支持提供者,最终促成了10万多人参与学习的盛况。③
2.学习型社区
人们关于“教育也是经济部门”的意识日益提高,一部分原因是高等教育的迅速扩展(从1994—1995年至2009—2010年学生人数从150万增加到250万),刺激了许多城镇为创收建立学习型街区或学习型社区。哥德堡市开创了一种方法,目的是建立一个起协同作用的重要部门,以吸引学生和投资者。④当卡斯特曾是著名的交通枢纽城市,以其发达的矿业和工程建设闻名,受到去工业化的沉重打击后,选择在大型继续教育学院旁建立了一所大学校园,反而大获成功⑤;又如曾是纺织小城的奥尔德汉姆,在2001年种族冲突爆发后陷入混乱,城市管理者认识到如果要建设城市新未来,就必须排除白种人和亚洲人社区之间的各类障碍。该市第六学院的校长充满智慧且富有远见,主持成立了伙伴关系委员会并开展学习计划,提高了两个社区年轻人的参与度,并成功地开展了大学科学中心运动。⑥
3.高等教育和地方参与
英国许多大学认为,公民责任感的提升,主要得益于这些年的艰难时期里,城市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与当地社区和企业的交流,也反映出大学建构学习型城市的公共服务理念。利物浦是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它于1994年建立学习型城市伙伴关系,目前着力于强化其公民参与感,加强研究人员、市政委员会和企业三方之间的联系。[16]
林肯大学是高等教育积极构建学习型城市的又一范例。与利物浦、曼彻斯特和维多利亚城市大学一样,林肯大学通过公开募捐成立,2001年,市议会和企业联合发声,筹集逾3 000万美元建设了新林肯大学。大学也向公众承诺,会成为林肯郡城市战略发展的倡导者。后来林肯大学又与西门子工程公司合作,成立专门负责此类合作的工程学院,该学院已有20多年的历史。
林肯大学还与西门子共同开发了工程学习类课程,使学生学期伊始就与企业合作,从结构化项目学习,到工作经验的获得,最后到职位安排,体系非常完善。大学学者和西门子员工“同吃同住”,确保“多层次、多方面”的关系得以不断发展。工程学院吸引了市内外大量的投资,林肯市政策规划和经济复兴执行负责人尼尔·穆雷(Neil Murray)曾公开表示,正因这个学院的存在,意大利工程公司Bifrangi才决定投资4 000万英镑以扩大其在林肯郡的事业版图,从而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知道城市可以自己培养工程师从而改变发展现状,是吸引他们到林肯郡投资的关键。”事实证明,这所大学的确也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它不仅能吸引企业进行投资,还促使过于依赖重工业的林肯郡实现产业结构多样化。[17]
4.克服不利因素,促进公民积极性
作为学习型城市网络的创始成员之一,诺威奇极具前瞻性,将终身学习和社区发展结合起来,以此克服一些根深蒂固的不利因素,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发展路线。比如将教育预算与城市重建资金结合起来。在英格兰,单一再生预算( the Single Regeneration Budget,SRB)可以用于购置社区学习项目资源。为了加强公民的参与,诺威奇还建立了许多分论坛,并赋予它们自主设计社区学习计划的权力。诺威奇首创的“居民参与制定社区学习计划”模式,在桑德韦尔、谢菲尔德、伯明翰和伍尔夫汉普顿等地区都得到了广泛采用。但遗憾的是,诺威奇却不太重视对公民参与积极性的培养。
七、经验教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3年10月发布了学习型城市倡议,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反思总结英格兰学习型城市发展中的经验和教训。
第一,如果国家和地方政府官员不支持学习型城市的建设,那么很有可能只有教育家们会对之抱有热情。但话又说回来,只要官方支持相关倡议,用不着为名称是不是“学习型城市”而担心,毕竟重要的并不是叫什么,而是做什么。
第二,“学习型城市伙伴关系”应该积极为解决城市现存问题建言献策,比如寻求教育家们的专业知识援助。正如那句老话,“不要问国家能为我做什么,而要问我能为国家做什么。”
第三,要使学习型城市和终身学习的理念与公民健康、就业、环境和男女平等息息相关。做到真正关切民生,而非从考虑预算和提升服务质量出发。
第四,学习型城市评价指标能够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学习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但指标的设计和实施必须由实践者们亲力亲为,实事求是。
如果说学习型城市运动的目标是设计和实施地方终身学习政策,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相比20年前的英格兰,这一目标显然并未完成。政策制定者固守功利主义的教育观念,忽略了个体学习路径的多样性。一直以来,我们很少会听到政治家们关注受教育公民的个体价值,或者主张为了学习本身而投资学习。另一方面,唐纳德·赫希认为教育和培训有益于城市的未来发展,尤其在当今这个时代,将发展教育和培训及其所属的行业当作地方发展的核心规划早已屡见不鲜。“良好的学校、学院和大学是可持续和包容性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这一观点也得到了广泛认可。相比20年前,学习之于城市发展的价值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虽然目前关于“学习型城市”的提法已经非常少见了,但这并不重要。
注 释:
① “学习”和“教育”是有细微差别的。“学习”与“终身学习”的观念相吻合,而“教育”则反映了对以下观点的强调:城市是儿童的教育性资源。
② 塞特福德(Thetford)和其他城镇的发展记录在苏·卡拉(Sue Cara) 1998年的研究报告《学习型城镇,学习型城市》中,该研究报告由NIACE代表教育部出版。
③ 详见:http:∥www.CulyTysRealthCigs.Org.U。
④ 详见:王山帝(音译)的欧洲本地项目案例研究,http:∥eurolocal.info/sites/default/files/GothenburgLearning%20City.pdf (n.d.)。
⑤ 参见大纲计划(2012),http:∥www-BootoDistase.COM∥2012/09/CQQ-MestPrimultTCM27—5510PDF。
⑥ 对于奥尔德汉姆所取得的成就,请阅读奥尔德姆合作伙伴关系报告(2015),http:∥www.Pusith.Suthimut.UK/PA/CM200 304/CMSECT/CMODPM/45/4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