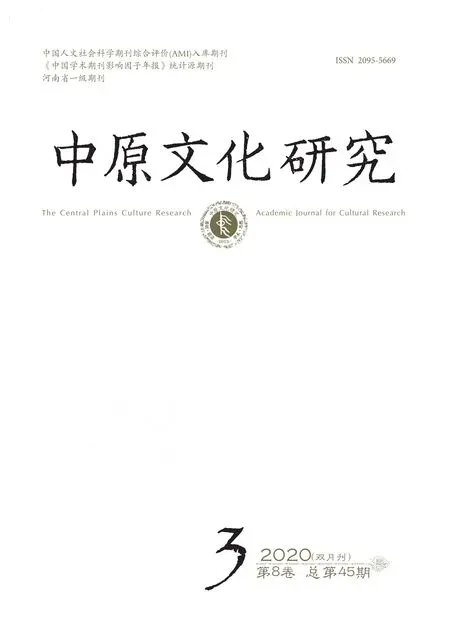“铜驼”象征与汉晋南迁的移民运动*
王子今
曾经有动物史学者指出骆驼的区域分布、生活习性和运输功能:“双峰驼……分布在中亚细亚和戈壁沙漠,现在中国的新疆和青海、内蒙西部还栖息着野生种。骆驼性情温顺,能耐饥渴及冷热,适于沙漠生活,负重致远,人称沙漠之舟。”[2]385有关历史时期中国野骆驼分布变迁的研究成果,有这样的意见发表:“据历代文献记载,从汉以前迄今,蒙古高原一带一直有骆驼广泛分布,同时也应有野骆驼存在,只是指明野骆驼及其具体地点的史料不多。”[3]258其实,居延汉简可见戍边军人追捕“野橐佗”的明确的简文记录[4]。
骆驼以善于行走沙漠地方的交通能力,增益了中原人的动物学知识。《艺文类聚》卷九四引《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国,济沙千余里中,无水。时有伏流处,人不能知。骆驼知水脉,过其处,辄停不行,以足踏地。人于所踏处掘之,辄得水。”[5]1630郭郛等《中国古代动物学史》写道:“中国学者认为双峰驼很可能是中国西部地区的人民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驯化的。”又说,“根据骆驼的古生物学、考古学、历史文献等证据,表明双峰驼是由生活在中亚、蒙古、新疆等一带游牧民族家化驯养成功。年代在公元前一二千年(殷商时代前后)。”[2]386《艺文类聚》卷九四引晋郭璞《橐驼赞》写道:“驼惟奇畜,肉鞍是被。迅骛流沙,显功绝地。潜识泉源,微乎其智。”[5]1630“奇畜”之说,更早见于《史记·匈奴列传》:“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骡、、、。”关于“橐驼”,司马贞《索隐》:“橐他。韦昭曰:‘背肉似橐,故云橐也。'”[6]2879
汉王朝控制河西,并进军西域之后不久,骆驼“入塞”,“衔尾”进入中土。但是中原人起初仍以为远方“奇畜”。200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和咸阳市考古所在对西汉平陵进行考古钻探和局部发掘时,获取了三个从葬坑的资料。其中2号坑南北长59 米,宽2—2.2 米,深4 米,北端为一斜坡,坑道两侧对称开凿了54 个洞室,每个洞室内有一具兽骨,均为大型动物,初步确认的有牛和骆驼。其中骆驼骨骼的发现尤为重要,“陕西乃至中原地区发现最早的大量骆驼骨架的出土,对汉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0]。这确实是汉地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的骆驼骨骼遗存。
东汉画像资料中骆驼形象更为多见。在陕西、河南、四川、江苏、山东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以商贩、行旅、乐舞为主题的画面中,多可看到以骆驼为交通动力的情形。
二、“铜驼”“在宫南四会道”
有关丝绸之路史的文献中可见铜质骆驼模型在西北方向的出现。《艺文类聚》卷二引崔鸿《北凉录》说到西北方向的“铜驼”:“先酒泉南有铜鉇出,言虏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万斤。”汪绍楹校注:鉇,“《初学记》二、《太平御览》二作駞。”[5]23《初学记》卷二引作:“先酒泉南有铜驼山,言虏犯者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11]27《初学记》“铜驼山”与《艺文类聚》“铜鉇出”不同。且《艺文类聚》“得铜万斤”,《初学记》作“得铜数万斤”。《太平御览》卷一二引作:“先酒泉南有铜駞,出,大雨雪。沮渠蒙逊遣工取之,得铜数万斤。”[12]58汪绍楹言“《太平御览》二”,误。“铜驼山”,“山”或是“出”字讹误。《太平御览》引文可能是正确的。然而崔鸿《十六国春秋》卷九四《北凉录一》:“永安九年,酒泉南有铜驼山,言犯之者,辄大雨雪。蒙逊遣工取之,得铜万斤。”[13]“铜鉇”“铜駞”,应当就是“铜驼”异写。如崔鸿《北凉录》记载可信,则“铜驼”“先”已在“酒泉南”形成了历史记忆。
《水经注》卷二《河水二》记述赫连勃勃都城统万城的宫殿区建设:“……又铸铜为大鼓,及蜚廉、翁仲、铜驼、龙虎,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则今夏州治也。”[14]84《晋书》卷一三〇《赫连勃勃载记》写道:“复铸铜为大鼓,飞廉、翁仲、铜驼、龙兽之属,皆以黄金饰之,列于宫殿之前。”[15]3206似乎“铜驼”是北方异族喜好的造型艺术铸作主题。
然而又有“铜驼”可能更早出现的信息。《艺文类聚》卷八四引《魏略》曰:“明帝徙长安诸钟簴骆驼铜人。承露盘折,铜人不可致,留住霸城。又列坐于司马门外。”[5]1444从“诸钟簴骆驼铜人”字句看,“骆驼”应与“钟簴”“铜人”一样,也是青铜铸作。按照这一记述,“铜驼”原先在长安,汉明帝时代迁往洛阳,“列坐于司马门外”。洛阳因有“铜驼街”。《汉书》卷七〇《陈汤传》言“槀街”,颜师古注:“稾街,街名,蛮夷邸在此街也。邸,若今鸿胪客馆也。崔浩以为稾当为橐,稾街即铜驼街也。此说失之。铜驼街在洛阳,西京无也。”[16]3015虽然“铜驼街在洛阳,西京无也”,然而“铜驼街”的“铜驼”却据说来自“西京”“长安”。《水经注》卷一六《谷水》:“渠水又枝分,夹路南出,迳太尉、司徒两坊间,谓之铜驼街。旧魏明帝置铜驼诸兽于阊阖南街。陆机云:驼高九尺,脊出太尉坊者也。”又写道:“《东京赋》曰:其西则有平乐都场,示远之观,龙雀蟠蜿,天马半汉。应劭曰:飞廉神禽,能致风气,古人以良金铸其象。明帝永平五年,长安迎取飞廉并铜马,置上西门外平乐观。”[14]400这样说来,汉明帝自长安“迎取”的,是“飞廉并铜马”,并没有“铜驼”。汉明帝“置铜驼”,又命名“铜驼街”,是“东京”新的城市规划内容、城市建设措施。
《艺文类聚》卷九四引《洛中记》曰:“有铜驼二枚,在宫之南四会道。头高九尺,头似羊,颈身似马,有肉鞍两个,相对。”[5]1630《太平御览》卷一五八引陆机《洛阳记》曰:“洛阳有铜驼街。汉铸铜驼二枚,在宫南四会道,相对。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12]770明确说“铜驼二枚”,所置空间位置,“在宫之南四会道”,提示了“铜驼街”在交通结构中的地位。《太平御览》卷一九五引华氏《洛阳记》曰:“两铜驼在官之南街,东西相对,高九尺。汉时所谓‘铜驼街'。”[12]943也说“在官之南街”。
“铜驼街”即所谓“在宫之南”“在官之南”者,其方位与走向,有两个要素值得关注,一是与“宫”或“官”的密切关系,二是朝向“南”的交通指向。
“铜驼”“在宫南四会道”,“在宫之南四会道”,于“四会道”“相对”形成显著坐标,其交通指示意义,也不宜忽视。
“铜驼街”,是东汉都城洛阳行政中枢即皇权决策中心的南向主干道路。西晋政治史若干迹象,可见“铜驼街”特殊作用的沿承。《晋书》卷四《惠帝纪》:“戊申,破陆机于建春门,石超走,斩其大将贾崇等十六人,悬首铜驼街。”[15]101《晋书》卷八九《忠义传·王豹》:“会长沙王乂至,于冏案上见豹笺,谓冏曰:‘小子离间骨肉,何不铜驼下打杀。'”[15]2305“铜驼”所在“铜驼街”,是政治权威与社会正义的象征。《晋书》卷五三《愍怀太子传附子臧传》:“到铜驼街,宫人哭,侍从者皆哽咽,路人抆泪焉。”[15]1464“铜驼街”因其地方之特殊,是宫廷生活与民间社会沟通的重要路径。
《晋书》卷六〇《索靖传》:“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15]1648所谓“铜驼”“在荆棘中”的著名预言,体现了在一般社会意识中“铜驼”被看作政治权力代号的情形。
洛阳“铜驼”,后来被迁徙到邺。《晋书》卷一〇六《石季龙载记》:“咸康二年,使牙门将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15]2764晋陆翙《邺中记》记述了“铜驼”形制:“二铜驼如马形,长一丈,高一丈,足如牛,尾长三尺,脊如马鞍。在中阳门外,夹道相向。”[17]前引“高九尺”说与此“高一丈”有异,或许与各历史时期尺度标准有所不同相关。
三、汉代两次大规模南下移民
西汉晚期社会危机严重。汉元帝时“关东困极,人民流离”[16]3047,“元元大困,流散道路”[16]288。汉成帝时,“水旱为灾,关东流冗 者众”[16]318,“灾异屡降,饥馑仍臻。流散冗食,餧死于道,以百万数”④。汉哀帝时,“岁比不登,天下空虚,百姓饥馑,父子分散,流离道路,以十万数”[16]3358,“民流亡,去城郭”[16]3087。汉平帝时,“郡国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16]353。王莽专政,“因遭大乱,百姓奔逃”[18]1300,“民弃城郭流亡”[16]4125,“多弃乡里流亡”[16]4157,“其死者则露尸不掩,生者则奔亡流散,幼孤妇女,流离系虏”[18]517。两汉之际,中原动荡,“百姓困乏,流离道路”[16]4175,“父子流亡,夫妇离散”[18]966。流移的方向,即史籍所谓“避乱江南”⑤。据说“荆、扬”地方有较好的生存条件[16]4151。东汉初期,“连年水旱灾异,郡国多被饥困”,“饥荒之余,人庶流迸,家户且尽”,其中往往有渡江而南者。永初初年实行“尤困乏者,徙置荆、扬孰郡,既省转运之费,且令百姓各安其所”[18]1128的政策,即说明民间自发流移的大致方向。通过所谓“令百姓各安其所”,可知流民向往的安身之地,本来正是“荆、扬孰郡”。
考察《汉书》卷二八《地理志》记录的元始二年(2年)户口数字和《续汉书·郡国志》记录的永和五年(140年)户口数字,前后数据两相比照,可以看到丹阳、吴郡、会稽、豫章、江夏、南郡、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国在138年的时间跨度内户口增长的幅度(见下表):
江夏郡与南郡辖地分跨大江南北,户口增长率亦最低。丹阳郡与会稽郡由于开发较早,故户口增长幅度亦不显著。然而另有史例说明,短期内绝对人口数的增长,也可能出现比较惊人的速率。如李忠建武六年(30年)任丹阳太守,“三岁间流民占著五万余口”[18]756,应当包括北来“流民”。汉顺帝永和五年全国户口数与汉平帝元始二年相比,呈负增长形势,分别为-20.7%与-17.5%。与此对照,江南地区户数增长140.50%,人口数增长112.13%,成为引人注目的历史现象。而豫章、长沙、桂阳及零陵等郡国的增长率尤为突出。户数增长一般均超过人口数增长,暗示移民是主要增长因素之一⑥。武陵郡户口增长幅度稍小,推想亦有山区民户未必尽为政府控制的因素。
江南地区户口元始二年占全国户口总数的比重,户数5.78%,人口数5.78%。而永和五年占全国户口总数的比重,则达到户数17.54%,人口数14.87%。正如葛剑雄等所指出:“这些单位的户口增长说明,它们的实际人口都有了大幅度的增长,肯定是人口的机械流动所致。从统计数字显示,吸收外来移民的主要地区是今湖南、江西,而今江苏、安徽南部移民较少。”[19]137黄今言也指出:“东汉时期江南地区人口增长绝对不是人口自然增长的结果,而是由外来人口机械迁入导致,江南中部是人口迁入最集中的地区……江南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是吸纳移民的主要地区,同时也为大规模吸收移民创造了基本条件。”[20]28除灾变和战乱之外,气候变迁是这一时期流民南迁的另一重要因素[21]。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也加剧了民众逃亡规模的扩大”[22]88。
有学者指出,“进入东汉以后”,“政府经营的重点明显地转移到了南方地区”,“史著中反映江南生产、赋税情况的记载也明显增加”,“《后汉书》所多次出现的余粮外调记录,更是一个明显例证”[23]150。这一见解,是从行政操作和经济管理的视角分析“江南”及“南方”因移民而发生变化所获得的认识。
东汉末年剧烈的社会动乱,再次导致人口向“南方”较大规模的流动。《三国志》卷六《魏书·董卓传》裴松之注引《先贤行状》有“黄巾起”“避难南方”[24]215。《三国志》卷六〇《吴书·全琮传》也有“是时中州士人避乱而南”的记载[24]1381。《三国志》卷一六《魏书·郑浑传》有“避难淮南”语[24]509。何夔亦“避难淮南”[24]378,刘繇“避乱淮浦”[24]1384,吕范“避乱寿春”[24]1109。司马芝“少为书生,避乱荆州”[24]386,毛玠曾有“避乱荆州”的计划[24]374,颍容“避乱荆州”[18]2584,杜袭、赵俨、裴潜均曾“避乱荆州”⑦。诸葛亮“避难荆州”事[24]930,尤为人熟知。王粲奉觞贺曹操,说道:“士之避乱荆州者,皆海内之俊杰也。”[24]598《三国志》卷二一《魏书·卫觊传》说:“关中膏腴之地,顷遭荒乱,人民流入荆州者十万余家。”[24]610史载刘馥“避乱扬州”[24]463,冯方女“避乱扬州”[18]2443。相当多的中原士人明确选择“江南”“江东”为迁徙方向。《三国志》卷五二《吴书·张昭传》记载:“汉末大乱,徐方士民多避难扬土”,中原“才士”“皆南渡江”[24]1219。吕岱“广陵海陵人也,为郡县吏,避乱南渡”[24]1383。赵达“谓东南有王者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24]1424。《三国志》卷一三《魏书·华歆传》注引华峤《谱叙》说:“是时四方贤大夫避地江南者甚众。”[24]401《三国志》卷二三《魏书·和洽传》裴松之注引《汝南先贤传》称“避乱江南”[24]658。《三国志》卷五二《吴书·步骘传》:“世乱,避难江东。”[24]1236《三国志》卷五三《吴书·张纮传》与《三国志》卷六二《吴书·胡综传》也都说到“避难江东”[24]1243,1431。《三国志》记录陈矫、徐宣、严畯、是依事迹,均言其“避乱江东”⑧。诸葛瑾、濮阳兴本传亦言“汉末避乱江东”[24]1451。鲁肃亦曾率“其属”至“江东”[24]1267。
黄河流域居民有南迁远至珠江流域者。《三国志》卷一一《魏书·袁涣传》:“遭天下乱,避难交州。”[24]336移居“交州”者,又有程秉“避乱交州”[24]1248。许靖,汝南平舆人,先至吴郡,“孙策东渡江”,与其“亲里”“皆走交州以避其难”[24]863-864。薛综以沛郡竹邑人“避地交州”[24]1250。甚至北方军阀刘备亦称欲往投苍梧太守吴巨[24]878。孙权也曾卑辞致书于魏,称“若罪在难除,必不见置,当奉还土地民人,乞寄命交州,以终余年”[24]1125。王郎亦曾“欲走交州”[24]407。据《三国志》卷三八《蜀书·许靖传》记述,许靖“至交阯”时,“寄寓交州”者,还有“陈国袁徽”[24]964。
《三国志》卷一四《魏书·蒋济传》记载,建安十四年(209年),曹操欲徙淮南民,“而江、淮间十余万众,皆惊走吴”[24]450。《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吴主传》记述建安十八年(213年)事,又写道:“初,曹公恐江滨郡县为(孙)权所略,征令内移。民转相惊,自庐江、九江、蕲春、广陵户十余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合肥以南唯有皖城。”[24]1118“江、淮间”或曰“江滨郡县”民众不得不迁徙时,宁江南而毋淮北,体现出对较适宜的生存环境的自发选择。其考虑的基点,可能是比较复杂的。我们注意到,江南地区气候条件的变迁,使得中原士民不再视之为“暑湿”“瘅热”之地而“见行,如往弃市”[16]2284。气候环境的改善,也使得中原先进农耕技术可以迅速移用推广。这些因素可能都有利于江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迅速提高[21]。正如葛剑雄等学者所指出的,“灾民的南迁本来是临时性的,在灾害过后应该返回故乡。但南方自然条件的优越在东汉以后已经很明显,加上地多人少因而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必定会有一部分灾民就此在南方定居”[19]511。汉武帝诏所谓“欲留,留处”,实际承认了这种“定居”的合法性。但是也许还应当注意到,农耕民族往往“安土重迁”,在不得不迁徙时,方向的选择,可能比较看重未开发地区的发展可能性(如所谓“地多人少因而比较容易获得土地”),尤其倾向于脱离政府的强力控制。从这一思路理解“亡人”往往由“中土”而“四裔”的流向,可能是适宜的。
所谓“民多弃乡里流亡”[16]4157,“关门牡开,失国守备,盗贼党辈”[16]3422,指出国家管理秩序被打破。然而“亡人”“流民”一旦脱离政府稳定的原有行政秩序的控制,可以激发惊人的生产积极性和文化创造力。在劳动热情蓬勃的大多是青壮生产力的人口涌入东南地方之后,自然可以显著改变当地的经济文化面貌。
四、永嘉南渡
经历“八王之乱”[25]后,永嘉元年(307年)晋怀帝司马炽将执政中心转移到建业(今江苏南京),引致中原大族纷纷南迁,史称“永嘉南渡”[26]984,或称“衣冠南渡”,前因即“洛阳”的残酷破坏。《史通·因习下》:“异哉!晋氏之有天下也。自洛阳荡覆,衣冠南渡,江左侨立州县,不存桑梓。”[27]183
据正史记述,“永嘉”年间的社会动荡导致政治秩序和文化传统的严重破坏。《晋书》卷五《孝愍帝纪》记载:“帝之继皇统也,属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5]132《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也说:“永嘉之际,氛厉弥昏,宸极失御,登遐丑裔,国家之危,有若缀旒。”[15]146一些大家名族都受到强烈冲击。《晋书》卷三三《何羡传》:“永嘉之末,何氏灭亡无遗焉。”[15]1000有的举族南迁,如傅氏“永嘉之乱,避地会稽”[15]1330,徐家“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15]2356,“永嘉之乱”,“祖逖拥众部于南土”[15]2843,一时“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者”[15]2574甚多。史家描述当时动荡之所谓“永嘉之乱,百姓流亡”[15]2628,体现了政治文化危局导致的全方位的社会残破。
“百姓流亡”,是原有社会格局被扰乱,传统社会关系被摧毁,较为恒定的社会秩序被粉碎所导致的现象。“永嘉之乱”后,出现了大量脱离政府控制,改变编户齐民身份的所谓“流人”[15]1714。人们被迫背乡离井,移居避乱,以所谓“没”[15]2289,“隐”[15]2451,“奔”[15]2311,“徙”[15]2959,“徙居”[28]2435,“避地”⑨等形式,离开了故乡,寻找新的生存空间。所谓“永嘉乱”,“民户流荒”[29]281,记录了移民大规模迁徙的形势。所谓“永嘉乱,渡江”[30],“晋永嘉乱后,幽、冀、青、并、兖五州流人过江……”[26]590,指示迁徙的主要方向是江南。
“永嘉南渡”的历史记忆,唐代已经非常深刻。前引独孤及《殿中监张公神道碑》“晋末以永嘉南渡,迁于江表”[31]4741外,《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序目上》:“晋武帝太康元年平吴……又增置郡国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县千一百有九,以为冠带之国,尽秦汉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狭,九州之地有其二焉。”[32]908前引《元和郡县图志》卷三九《陇右道·渭州》“彰县”条:“永嘉南渡,县遂废焉。”后世学人均认同“永嘉南渡”体现明显的历史转折的说法。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一《经籍会通一》:“云间陆子渊家多藏书,所著《别集》中有‘统论'一则云:自古典籍兴废,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33]顾炎武《日知录》卷七“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曰:“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五胡乱华”,或作“刘石乱华”[34]402,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永嘉南渡”。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七《文选·诗》“谢灵运《会吟行》条”:“灵运此诗,既序大禹及勾践旧迹,当举永嘉南渡名臣将相出于会稽,以征邦彦之盛。”[35]924
“永嘉南渡”历史记忆的文学表现,有杜甫《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见寄》诗:“边塞西蕃最先斥,衣冠南渡多崩奔。鼓瑟至今悲帝子,曳裾何处觅王门。”[36]269其中“崩奔”二字,形容社会动荡的烈度和民人流散的规模。唐人詹琲《永嘉乱衣冠南渡流落南泉作忆昔吟》:“忆昔永嘉际,中原板荡年。衣冠坠涂炭,舆辂染腥膻。国势多危厄,宗人苦播迁。南来频洒泪,渴骥每思泉。”[37]8643“板荡”“播迁”,动乱致使“国势”“危厄”,“衣冠”“涂炭”。“南来”“流落”的历史,“洒泪”回顾,有绵延数百年的伤心。
“永嘉之乱”导致的大规模“南渡”,在移民史的记录中较汉代两次大移民形成更深刻的记忆,因为这一事变标志着政治历史运行的重大转折,导致了民族分布格局的鲜明变化,引发了经济生活形态的显著转换,形成了主流知识阶层的深切怆痛。人们注意到这样的历史变局:一是政治秩序一时摧毁,即所谓“永嘉之乱,天下崩离”,“永嘉之乱,天下分崩”[38]33;二是文化传统受到冲击,即所谓“自永嘉之乱,庠序无闻”[15]2895,所谓“典籍兴废”,“永嘉南渡为一厄”;三是民族格局发生变化,即所谓“永嘉之乱,神州倾覆”[39]482,“戎羯之乱,兴于永嘉之年”[18]2969;四是中原大族遭遇败亡,即所谓“洛阳荡覆”,“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豪族富户或“灭亡无遗”,或“播流江表”。这正是所谓“衣冠坠涂炭”,“宗人苦播迁”。他们的历史感觉和文化情绪,更容易保留在以文献承载的记忆之中,长久地影响后世。后人从文献记忆认识历史,体悟情感。
五、全国经济重心和文化重心向东南方向的转移
“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中写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又说:“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6]3270看来,当地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较为落后,渔猎采集在经济生活中仍占相当大的比重。司马迁曾经亲身往“江南”地区进行游历考察⑩,他对于“江南”经济文化地位的分析,应当是基本可信的。
其实,司马迁这里所说的“江南”,与今人有关所谓“江南”的区域观念并不相同。司马迁写道:“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6]3268“江南”可以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并列,其区域范围或相当于郡。看来,司马迁语谓“江南”所指代的区域,并不如后世人空间定义所谓“江南”那样广阔⑪。《史记》卷五七《绛侯周勃世家》“(吴王濞)保于江南丹徒”[6]2076;《史记》卷九一《黥布列传》“与百余人走江南”,又为长沙王所绐,“诱走越”,“随之番阳”而被杀等[6]2606,似乎可以说明司马迁所处时代中原人地理观念中的“江南”,大致包括长江中下游南岸地区。这一地区,正是上文比较两汉户口数字时所指出的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即零陵、长沙、桂阳、豫章等地。
《史记》卷四二《郑世家》记述,襄公七年,郑降楚,襄公肉袒以迎楚王,有“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语[6]1768。又《史记》卷七〇《张仪列传》中郑袖言楚怀王:“妾请子母俱迁江南,毋为秦所鱼肉也。”[6]2289可见“江南”于楚,曾为罪迁之地。到了司马迁所处的时代,虽“江南”已经早期开发,在笼统称作“大江之南”⑫的区域中文明程度相对先进,然而与黄河中下游华夏文明中心区域相比,经济、文化均表现出明显的差距。《史记》卷三〇《平准书》记汉武帝诏“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强调“江南火耕水耨”[6]1437。可见,就当时作为社会主体经济形式的农业而言,“江南”尚处于相当落后的发展阶段。《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历数各地的“富给之资”,如“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等,却未及江南名产,看来当时江南确实具有“不待贾而足”的特征,民间“无积聚而多贫”[6]3272,3270。《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记载,天凤年间,费兴任为荆州牧,曾经分析当地形势:“荆、扬之民率依阻山泽,以渔采为业。”颜师古注:“渔谓捕鱼也。采谓采取蔬果之属。”[16]4151-4152这种以渔猎采集山伐作为基本经济生活方式的情形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风貌,到东汉时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
大致在东汉晚期,江南已经大致扭转了“地广人希”、“火耕而水耨”的落后局面[6]3270,成为“垦辟倍多,境内丰给”之地[18]2466。《抱朴子·吴失》记述了吴地大庄园经济的富足:“势利倾于邦君,储积富于公室。出饰翟黄之卫从,入游玉根之藻棁。僮仆成军,闭门为市。牛羊掩原隰,田池布千里。”[40]142,145,148这样的情形,与司马迁当年所谓“无千金之家”的记述[6]3270,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几乎完全体现出对王符《潜夫论·浮侈》中所描绘的东汉中期前后以“京师”“洛阳”为代表的黄河流域经济模式的复制⑬。
前引《史记》卷三〇《平准书》“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事,《汉书》卷六《武帝纪》系于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夏,大水,关东饿死者以千数。秋九月,诏曰:‘仁不异远,义不辞难。今京师虽未为丰年,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江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博士中等分循行,谕告所抵,无令重困。吏民有振救饥民免其厄者,具举以闻。'”[16]182《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是时山东被河灾,及岁不登数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怜之,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使者冠盖相属于道护之,下巴蜀粟以振焉。”关于“欲留,留处”,颜师古注:“流谓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留而处也。”[16]1172按照《食货志》的说法,“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者,是安置“山东”灾民。然而《武帝纪》明确说“今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惧其饥寒不活”,又言“江南之地,火耕水耨”,至少“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欲留,留处”者包括“江南”灾民,甚至因“今水潦移于江南”的灾情及“迫隆冬至”的季节因素,很可能主要的安置对象是“江南”灾民。汉武帝时代“江南”受灾民众如“恣其行移”的方向,即“欲住”可得“留而处”的地方可能是“江淮间”,也就是说,“若水之流”的自然的移民方向是由南而北。两汉之际及汉末时移民由北而南所形成的大规模潮流的方向,正与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东汉时期,史籍中已经多可看到有关江南地区的经济与文化取得突出进步的记载。《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卫飒传》记载东汉光武帝建武年间,卫飒任桂阳太守时事迹:“迁桂阳太守,郡与交州接境,颇染其俗,不知礼则。(卫)飒下车,修庠序之教,设婚姻之礼。期年间,邦俗从化。先是含洭、浈阳、曲江三县,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内属桂阳。民居深山,滨溪谷,习其风土,不出田租。去郡远者,或且千里。吏事往来,辄发民乘船,名曰‘传役'。每一吏出,傜及数家,百姓苦之。飒乃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于是役省劳息,奸吏杜绝。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又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飒理恤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于物宜。视事十年,郡内清理。”[18]2459
所谓卫飒“流民稍还,渐成聚邑,使输租赋,同之平民”,读来似有吸引外来“流民”的意味。而“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者,则明确是外来的“佗郡民庶”以及“亡命”者。桂阳郡户口较西汉增加了380.21%和220.41%,应当有循吏的功绩。而“流民”“亡命”们开发地方经济的贡献,也不可以否认。“亡人”“流民”“渐成聚邑”,自然也可以将文化先进地区的“庠序之教”和“婚姻之礼”带到原先“不知礼则”的地方。
《三国志》卷五四《吴书·鲁肃传》裴松之注引《吴书》说:“后雄杰并起,中州扰乱,(鲁)肃乃命其属曰:‘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吾闻江东沃野万里,民富兵强,可以避害,宁肯相随俱至乐土,以观时变乎?'其属皆从命。”[24]1267看来,秦及西汉时期所谓“卑湿贫国”⑭,到东汉末年前后,由于地理条件和人文条件的变化,已经演进成为“沃野万里,民富兵强”的“乐土”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超越“中州”的适宜居住的生存空间。
显然,自两汉之际以来,江南经济确实得到明显优胜于北方的加速发展。傅筑夫等学者曾经指出:“从这时起,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经济区的重要性亦即从这时开始以日益加快的步伐迅速增长起来,而关中和华北平原两个古老的经济区则在相反地日益走向衰退和没落。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巨大变化,尽管表面上看起来并不怎样显著。”[41]25
分析这种具有转折意义的历史“变化”的多种原因时,不可以忽视大批劳动力空间移动的作用。有学者提示我们注意,“向相对安定的南方流移”这种“大规模自发的人口迁移”,“使中国人口的地理分布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南增北减的变化”[42]147。正如黄今言所说:“秦汉人口南迁与江南社会进步是同步的。在地广人稀的前提下,人口的流入不仅促进了江南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江南的开发,而且因生产环境和通婚环境的改变而有利于江南人口素质的提高。同时移民也是文化的载体,移民流向江南也带着北方文化流向江南,所以,移民的过程也是中华文化交融和扩展的过程。”[20]32考察这种“移民”运动及其历史文化意义时,对于历代执政者视作危机表象的“亡人”“流民”们的积极作用,也应当肯定。分析相关现象,孙达人的意见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他正确地指出,中国古代“广大农民得以摆脱皇朝的束缚,去开发一个又一个新经济区,从而为创造辉煌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更广阔的基础”,是促进“历史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43]109-111。
“永嘉南渡”之后的移民运动,进一步把中原文化传统的精华向南方传布,给东南地方的文化发育增添了新的活力与动力,使东南文化出现了新的局面。东南文化于是继承了中原文化的正统。
六、南人的“铜驼”思念
两汉之际与东汉末年大规模的南下移民运动,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民户南迁的历史先声。“永嘉之乱,天下崩离,长安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15]132,“自永嘉丧乱,百姓流亡,中原萧条,千里无烟,饥寒流陨,相继沟壑”[15]2832。《晋书》卷六《中宗元帝纪》:“及永嘉中,岁、镇、荧惑、太白聚斗、牛之间,识者以为吴越之地当兴王者。”[15]157东南方向再次为世人瞩目。所谓“永嘉之乱,神州倾覆”[15]598,“中州尽弃,永嘉南度”[15]408,民族关系的变化,再次导致了中原移民南下。所谓“永嘉之乱,避地会稽”[15]1330,“永嘉末,以寇贼充斥,遂南渡江”[15]1593,“永嘉初……避难渡江”[15]1842,“永嘉中,避乱江东”[15]1989,“永嘉末……避乱渡江”[15]1974,“属永嘉之乱……南渡江”[15]2356,“自永嘉之乱,播流江表”[15]2574。所谓“百姓流亡”,“永嘉南度”,“播流江表”,密集的沉痛记录,保留了移民史空前严酷的一页。体会这样的历史,想象当时“避难渡江”“避乱江东”的北人回望“神州”“中原”,会是怎样的心境呢?
至于南北朝时代,“铜驼”长期依然是南朝皇家权贵及一般士人向往的中原文化的标志性象征。《陈书》卷六《后主纪》载录诏文:“……其有负能仗气,摈压当时,著《宾戏》以自怜,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诚难,亦宜去此幽谷,翔兹天路,趋铜驼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便当随彼方圆,饬之矩矱。”[38]107仍用汉世典故,“金马”“铜驼”对应前引陆机《洛阳记》“俗语曰:‘金马门外集众贤,铜驼陌上集少年'”,可以看作国家朝廷的代号。又《陈书》卷二六《徐陵传》:“岂卢龙之径于彼新开,铜驼之街于我长闭?”[38]327所谓“铜驼之街”,是象征着中原正统政治文化的。
南朝士人诗赋作品中,常常出现涉及“铜驼”“铜驼街”的辞句。《艺文类聚》卷七引梁任昉《奉和登影阳山》诗曰:“物色感神游,升高怅有阅。南望铜驼街,北走长楸埒。别涧苑沧溟,疏山驾瀛碣。奔鲸吐华浪,司南动轻枻。日下重门照,云关九华澈。观阁隆旧恩,奉图愧前哲。”[5]125其中洛阳的“铜驼街”,在对应有关“沧溟”“瀛碣”的宏大文化感觉中仍然具有神圣的意义。“日下重门照,云关九华澈”及下句“观阁”“奉图”等,说到“前哲”“旧恩”,怀思深远。又《艺文类聚》卷九引梁王台卿《山池》诗曰:“历览周仁智,登临欢豫多。穿渠引金谷,辟道出铜驼。长桥时跨水,曲阁乍临波。岩风生竹树,池香出芰荷。石幽衔细草,林末度横柯。”[5]172所谓“穿渠引金谷,辟道出铜驼”,依然寄托着对洛京繁盛时期文化风景的怀念。
南朝梁徐陵《洛阳道》诗写道:“绿柳三春暗,红尘百戏多。东门向金马,南陌接铜驼。乘轩翼葆吹,飞盖响鸣珂。潘郎车欲满,无奈掷如何。”[44]其中“东门向金马,南陌接铜驼”句,可以与前引“趋铜驼以观国,望金马而来庭”对照理解。又徐陵《与杨仆射书》:“岂卢龙之径于彼新开,铜驼之街于我长闭。何彼途甚易,非劳于五丁;我路为难,如登于九折。”[44]这里是把“铜驼之街”看作远途长路的。这应当颇为符合对洛阳的悠久怀思。而庾信《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八川风俗,五方名利。铁市铜街,风飞尘起。”清人倪璠注解释说:“铁市,即金市。铜街,铜驼街也。”[45]737,738南朝梁简文帝开文德省置学士,徐陵与庾信皆充其选。《北史》卷八三《文苑传·庾信》说:“陵及信并为抄撰学士。”“既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竟相模范,每有一文,都下莫不传诵。”[28]2793作为南朝梁享誉一时文学领袖,其作品关于“铜驼”“铜街”的咏叹,是引人注目的文字信号。其作品中表现的这种“铜驼”情结,或许代表了南朝“都下”共同的文化心理。
“铜驼”作为历史文化符号在典籍文献中频繁出现,体现了南下移民对故土原生文化的深切追思。“铜驼”代表着他们世代继承的传统,也可以理解为他们对于文化之根、文化之源的永远的历史纪念。
注释
①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中华书局1992年7月版,第28 页。有学者据此以为“骆驼从汉代(公元前81年)大量从西域传入中原”(郭郛、李约瑟、成庆泰著:《中国古代动物学史》,科学出版社1999年2月版,第383 页)。②1963年8月湖北鄂城出土的一件汉镜,有“主如山石,宜西北万里,富昌长乐”铭文(湖北省博物馆、鄂州市博物馆编:《鄂城汉三国六朝铜镜》,1986年3月版,图版46,图版说明第9 页)。参看周新:《鄂城汉镜铭文“宜西北万里”小议》,《南都学坛》2018年1 期。③或说“汉景帝阳陵陪葬坑中发现有陶制的写实骆驼俑”,南京博物院:《长毋相忘:读盱眙大云山江都王陵》,第151 页。此说恐不确。④《汉书》卷八五《谷永传》,第3462 页。《汉书》卷八三《薛宣传》:“岁比不登,仓廪空虚,百姓饥馑,流离道路。”第3393 页。⑤《后汉书》卷七六《循吏列传·任延》:“时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第2460-2461页。⑥黄今言指出:“人口流向江南使江南家庭规模变小。”“从各郡的每户平均人口来看,江南人口最集中的零陵、桂阳、长沙、豫章四郡均减少……”(《秦汉江南经济述略》,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30 页)⑦《三国志》卷二三《魏书·杜袭传》,第664 页;《三国志》卷二三《魏书·赵俨传》,第668 页;《三国志》卷二三《裴潜传》,第671 页。⑧《三国志》卷二二《魏书·陈矫传》,第642 页;《三国志》卷二二《魏书·徐宣传》,第645 页;《三国志》卷五三《吴书·严畯传》,第1247 页;《三国志》卷六二《吴书·是仪传》,第1411 页。⑨《晋书》卷四七《傅敷传》,第1330 页;《晋书》卷九五《艺术传·黄泓》,第2492页;《晋书》卷一一〇《韩恒载记》,第2842 页;《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第3127 页。⑩《史记》卷一二八《龟策列传》:“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第3225 页。⑪ 冯贤亮曾经讨论“古代‘江南'含义的变迁”。他认为:“秦汉时期,‘江南'的含义略显明确,主要指的是今长江中游以南的地区,即今湖北南部和湖南全部。”(《明清江南地区的环境变动和社会控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 页)⑫《史记》卷六〇《三王世家》:广陵王策:“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间,其人轻心。扬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政。'”第2113 页。⑬《潜夫论·浮侈》:“今举世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商邑翼翼,四方是极。今察洛阳,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今京师贵戚,衣服、饮食、车舆、文饰、庐舍,皆过王制,僭上甚矣。从奴仆妾,皆服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细致绮縠,冰纨锦绣。犀象珠玉,虎魄玳瑁,石山隐饰,金银错镂,獐麂履舄,文组彩绁,骄奢僭主,转相夸诧,箕子所唏,今在仆妾。富贵嫁娶,车軿各十,骑奴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王符著,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9月版,第120 页,第130页)⑭《史记》卷五九《五宗世家》:长沙王刘发“王卑湿贫国”。第2100 页。《史记》言南方“卑湿”文例,又有《史记》卷一〇一《袁盎晁错列传》:“南方卑湿。”第2741页。《史记》卷一一三《南越列传》亦言“南方卑湿”。第2970 页。《史记》卷一一八《淮南衡山列传》载汉景帝语“南方卑湿”。第3081 页。《史记》卷八四《屈原贾生列传》:“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第2492 页,第2496 页。《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第32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