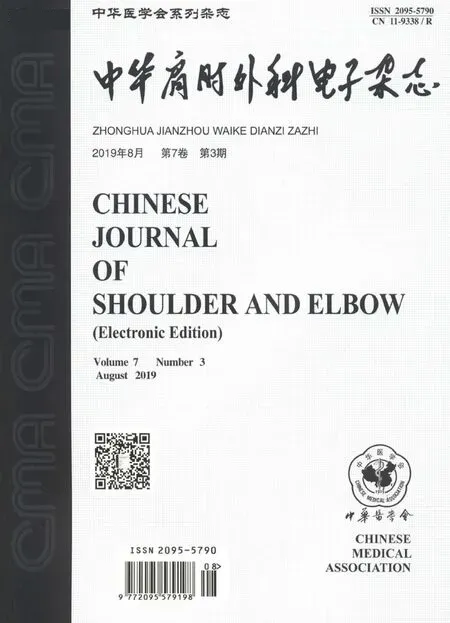临界肩角与肩关节疾病关系的研究进展
代飞 向明 黄勇
近年来,肩峰形态与肩关节疾病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肩峰形态与撞击综合征、肩峰下滑囊炎、肩袖损伤等的关系仍是争论焦点。目前研究测量肩峰解剖和形态学的方法很多,如肩峰形态、肩峰倾斜度、肩峰指数(acromion index,AI)以及临界肩角(critical shoulder angle,CSA)等。Moor等[1]提出CSA的概念,被认为是目前预测肩袖疾病和骨关节炎更具判别性的指标。近来随着对CSA的研究深入,其争议也越来越多。因此,回顾最新文献,讨论围绕CSA的一些争议,对于理解CSA,将其作为判断和预测肩关节疾病的工具是有指导意义的。
一、CSA的概念
CSA是指在肩关节真正的前后位X线片上,从肩盂的上缘到下缘(穿过肩盂平面)画一条线,再从肩盂的下缘画一条线到肩峰最外侧的最远端,二者所形成的夹角(图1)。文献表明,CSA正常值在30°~35°,<30°与肩关节骨关节炎的发生有关,> 35°被认为是肩袖撕裂的危险因素[1,2-5]。Moor等[1]将 94 例无症状、肩袖正常、无骨关节炎的肩关节作为对照组;肩袖撕裂组:102例MRI记录到全层肩袖撕裂,无骨关节炎的肩关节;骨关节炎组:102例原发性骨关节炎,无肩袖撕裂的肩关节。Moor等分别对三组患者进行CSA测量。作者发现对照组CSA平均为 33.1°(26.8°~38.6°);肩袖撕裂组为 38.0°(29.5°~43.5°),骨关节炎组为28.1°(18.6°~35.8°)。此外,在CSA>35°的患者中,84%为肩袖撕裂组;在CSA<30°的患者中,93%为骨关节炎组。而Mantell等[6]用ROC曲线显示,在骨关节炎患者中,>35°的CSA对全层肩袖撕裂的特异性为90%,对全层肩袖撕裂的敏感性为52%。与多数结果不同的是,Chalmers等[7]发现肩袖撕裂患者的平均CSA为34°±4°,而正常肩袖患者为32°±4°,作者认为该结果可能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
CSA需要在肩关节真正的前后位X线片上测量,尽量使肩盂的前后边缘重叠。CSA的测量方法影响测量值的准确性。Samy等[8]和Spiegl等[9]的研究表明,在X线片上和CT扫描中的CSA的测量结果呈高度相关性,模态间的差异可以忽略不计,X线片的准确性高于MRI。Moor等[1]发现,在X线片上,冠状面和/或矢状面20°的旋转不良对CSA测量变异性的影响<2°。然而,Suter等[10]发现CSA最易受前倾/后倾的影响,且不受人口学因素影响。当X线片上前倾角>5°或后倾>8°时,CSA与真正的前后位X线片比较有>2°的偏差;当屈曲>15°,伸展>26°时,CSA才发生>2°的变化。这项研究还纳入了一种新的放射学分类系统(Suter-Henninger系统),用于评估肩胛骨定向失调。作者发现,与真正的前后位X线片相比,在2°内准确评估真实CSA的概率为89%。因为要准确测量CSA是很困难的,所以使用该系统标准来测量前后位X线片以准确评估CSA在任何未来的研究中都是至关重要的。

图1 CSA的测量,在真正的肩关节前后位X线片上,从肩盂的上缘到下缘(穿过肩盂平面)画一条线,再从肩盂的下缘画一条线到肩峰最外侧的最远端,二者所形成的夹角
二、CSA在肩峰形态研究中的发展
肩峰形态与肩关节疾病关系密切,随着人们对肩峰解剖及形态研究的深入,逐渐提出了CSA的概念,因此回顾CSA在肩峰形态研究中的发展历史对理解CSA与肩关节疾病之间的关系有重要意义。
对肩峰形态的研究是为了更好地识别和指导肩关节相关疾病的治疗。Bigliani等[11]和 Neer[12]先前的分析表明,肩峰前外侧形态(包括喙肩韧带)是肩峰下疼痛的原因,也是引起囊侧肩袖撕裂的一个因素。目前,多项研究认为肩峰侧向延伸是肩袖疾病发生的危险因素[13]。这也为广泛采用肩峰前外侧肩峰成形术这一安全有效的方法治疗肩袖疾病及撞击综合征提供了理论依据[14-15]。但是,一项评估肩峰成形术对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效果影响的Meta分析[16]和一项随机试验[17]表明,行肩袖修复手术时,是否行前外侧肩峰成形术,其结果和失败率没有差异。
Armstrong[13]1949年提出肩部疼痛弧是由肩峰下滑囊的撞击形成,后来Neer[12]认为多达95%的肩袖损伤是由肩峰下的慢性撞击所致。此后许多学者集中研究了肩关节疾病与肩峰不同形态之间的关系。
Bigliani等[11]提出的肩峰分型是目前最流行的预测撞击和肩袖损伤的指标,他将肩峰形态分为三种类型:扁平(1型,17%);弯曲(2型,43%);钩状(3型,40%)。Banas等[18]所描述的侧向肩峰角主要考虑了冠状斜位核磁共振成像所测得的肩峰角和肩峰倾斜度。作者比较了不同严重程度的肩袖损伤患者的测量结果,发现全层肩袖撕裂与≤70°侧向肩峰角有显著相关性。
Torrens等[19]用一种不同的方法(肩峰覆盖指数)测量肩峰的侧向延伸,发现肩袖撕裂的患者与那些肩袖完整的患者之间的值有显著差异。Aoki等[20]将肩峰倾斜度降低描述为肩袖疾病发展的危险因素。作者进一步提出肩峰前外侧形态异常是肩袖疾病的原因,假设肩峰形态的改变会缩小冈上肌出口的面积,导致肩峰和大结节之间的狭窄,因此,在肩袖进入时会产生磨损,导致肩袖撕裂。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肩峰和喙肩韧带的适应性或获得性改变是肩袖功能紊乱的结果,而不是病因[19-24]。
Nyffeler等[25]进一步研究了肩峰侧向延伸与症状性肩袖撕裂之间的关系。他们提出了AI这一概念,并发现较大的AI与肩袖撕裂之间存在关联,较小的AI与肩关节炎相关联。与这一理论形成对比的是,在一项关于肩袖疾病的MRI研究中,Baechler和Kim[26]发现肱骨头未被前外侧肩峰覆盖的百分比可能是肩袖全层撕裂的致病因素之一。Baechler和Kim[26]将肱骨头的“未覆盖”定义为肱骨头未被前外侧肩峰覆盖的百分比。与无肩袖撕裂的男性相比,肩袖撕裂组显示出更大的未覆盖范围,与Nyffeler等[25]的结论截然相反。
在AI的基础上,Moor等[1]提出的CSA的概念,CSA的测量不受肱骨头的形状或方向的影响。此外,肩盂的倾斜,这也被认为是导致肩袖撕裂的一个危险因素[27-29]。肩盂的倾斜度和肩峰的侧向延伸度与CSA均有很大的相关性[30]。CSA的测量既考虑了肩盂的倾斜,又考虑了肩峰的侧向延伸度。
三、CSA与肩关节疾病的关系
(一)CSA与肩袖撕裂
非外伤性、退行性肩袖撕裂的病因一直是运动医学和肩关节外科争论的焦点。Moor等[1]的研究显示,肩袖撕裂组的平均CSA比对照组大(分别为38.0°和33.1°)。CSA的灵敏度为0.82,特异性为0.92,可能对预测肩袖撕裂有一定的价值,CSA的解剖差异可能是退行性肩袖撕裂发生的危险因素。
当与其他肩峰测量指标如肩峰形态、肩峰倾斜度、AI等进行比较时,CSA被发现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预测退行性全层肩袖撕裂的一个更具判别性的指标[4-5,31]。此外,Heuberer等[4]和 Moor等[5]的研究表明年龄和 CSA 的联合危险因素对退行性肩袖撕裂有很高的预测作用。随后的多项研究也证实了CSA>35°与创伤性肩袖撕裂的发生率之间的关系[3,31-35]。
虽然CSA与肩袖撕裂有关联,但CSA可能只有助于诊断全层撕裂,而不是部分撕裂。在随后的一项研究中,Moor等[36]发现,较大的CSA仅与全层撕裂的肩袖显著相关(P<0.0001)。Pandey等[37]进一步证实了这一关系,发现全层肩袖撕裂和部分肩袖撕裂的肩关节的平均CSA值,分别为41.01°和38.83°,高于对照组肩关节的平均CSA值(37.28°)。只有全层肩袖撕裂组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此外,Chalmers等[7]指出,1 552张X光片中只有21%的质量足以根据Suter-Henninger分级标准来测量真正的CSA,并认为:他们在研究小组之间发现的2°差异可能与临床无关,因为这可能仅仅是由于测量误差造成的。这些发现表明,虽然CSA可能与非退行性全层肩袖撕裂有关,但诊断不应仅基于这一测量,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先进成像技术,以确定是否存在肩袖撕裂。
关于CSA与退行性肩袖撕裂之间关系的研究,大多数为回顾性的观察研究,很少有生物力学研究。Gerber等[38]使用了一个肩关节模型来评估肩关节外展时CSA与冈上肌腱负荷之间的生物力学联系。他们发现,较小的CSA与更大的压缩联合力和较低的剪切力有关,特别是在外展早期。在另一项生物力学研究中,Moor等[39]用实验模拟器和尸体肩部研究了肩盂倾斜度相关的CSA的变异影响。两项研究均发现,随着CSA的增大,关节的不稳定性和剪切力都增加了,因此需要激活冈上肌来稳定CSA增大的肩关节。
虽然上述这些研究表明CSA与肩袖撕裂具有相关联系,但CSA在肩袖疾病中的临床应用仍有疑问。由于大多数评估这一关联的研究都是回顾性研究,所以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生物力学研究来支持CSA和肩袖撕裂之间的联系。
(二)CSA与肩关节骨关节炎
肩关节骨关节炎的病因与年龄、创伤等多种危险因素有关[40-41]。近年来,在肩关节骨关节炎相关的可靠预测指标中,肩峰形态受到关注。最近,为了更好地了解肩关节骨关节炎的病因,人们对CSA 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多项研究发现[1,4,31-32,34-35],肩关节骨关节炎与CSA具有显著相关性。
Moor等[1]发现,对照组与骨关节炎组在CSA方面存在5°的显著差异(平均 33.1°比28.1°,P<0.0001),并认为CSA<30°与骨关节炎有关,随后的几项研究表明,CSA<30°与骨关节炎有显著的相关性,且具有很强的观察者间和观察者内的可靠性[4,31-32,34-35]。Heuberer等[4]在对 1 000例肩关节炎患者进行回顾性配对队列研究时发现,骨关节炎组CSA明显小于对照组(P<0.001)。在这项研究中,CSA测量也显示了所有评估指标的最高灵敏度(82.0%)和特异性(76.1%)。最近,Bjarnison等[2]报道说,CSA与肩关节骨关节炎有关,但与肩袖撕裂无关。作者认为CSA<30°的患者骨关节炎发生的优势比为2.25(P=0.002),而CSA>35°的患者发生肩袖撕裂的优势比为1.12(P=0.63)。此外,一项评估CSA对解剖型全肩关节置换术后患者预后的影响的研究表明,CSA与晚期肩袖撕裂的后续发展无关系[42]。
尽管上述研究证实了CSA的减小与骨关节炎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但是没有任何前瞻性的研究表明其因果关系。一些研究表明[38-39,43],随着CSA的减小,三角肌的力发生改变,向水平方向移动,增加了肱骨头在肩盂上的压缩力,从而导致软骨的负荷增加,更容易引起骨关节炎。但是,这些生物力学研究的主要局限是在尸体模型中使用滑轮和钢丝来复制肩部肌肉,这样的模拟无法复制肩袖肌之间的动态关系。因此,他们无法评估轴向肩袖力偶的完整性。
虽然多项研究表明,肩关节骨关节炎与CSA具有联系,但至今还没有研究数据显示CSA与骨关节炎之间的因果关系,这很可能与大多数研究都是回顾性研究有关。需要进行具有标准化X线片测量的随机对照试验,以评估患者是否有患骨关节炎的风险,评估CSA与肩关节骨关节炎的因果关系。
(三)CSA与患者预后情况
目前已有研究评估了CSA对肩袖修复后患者预后和再撕裂率的影响。Garcia等[44]回顾性研究了76例接受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的患者,在平均随访时间为26.2个月后,作者发现CSA增大与术后6个月超声评估的全层再撕裂显著相关(P<0.01),CSA>38°的患者术后全层再撕裂的风险增加了15倍。此外,CSA的增大与术后ASES评分减少显著相关(P<0.03)。Kirsch等[45]报道了一项II级前瞻性研究的对比结果,其中53例(平均年龄61岁)非创伤性全层肩袖撕裂患者接受了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术后应用西安大略省肩袖评分、美国肩肘外科协会评分和视觉模拟评分评定,临床疗效明显改善(P<0.0001);在24个月的随访中,CSA与这些结果没有显著关联(P值分别为0.581、0.458和0.859)。同样,Lee等[46]研究了CSA和 AI对关节镜下肩袖修复术预后的影响。尽管CSA>35°的患者6个月时的Constant评分、牛津肩关节评分、美国加州大学肩关节评分明显差于CSA≤35°的患者的评分(P值分别为0.005、0.030和0.035),但24个月时临床疗效无显着性差异(P>0.05)。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CSA与肩袖修复后患者预后及再撕裂率的相关研究还很少,并且结论还存在较大争议,还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以明确CSA与肩袖修复后患者预后之间的关联,为手术的选择、术后康复以及术后预期结果等提供帮助和指导。
四、小结与展望
肩峰形态与肩关节疾病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肩峰形态的异常,可能会改变肩关节的力学环境,引起肩关节疾病的发生。CSA与肩袖撕裂和肩关节骨关节炎的发展有关。但目前的研究仍有一定的争议,其因果关系尚不明确,而这些相互矛盾的研究结果可能与CSA的测量方法和测量误差有关。为了明确CSA与肩关节疾病的真正关系,需要进一步的前瞻性研究,包括一种标准的、可重复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