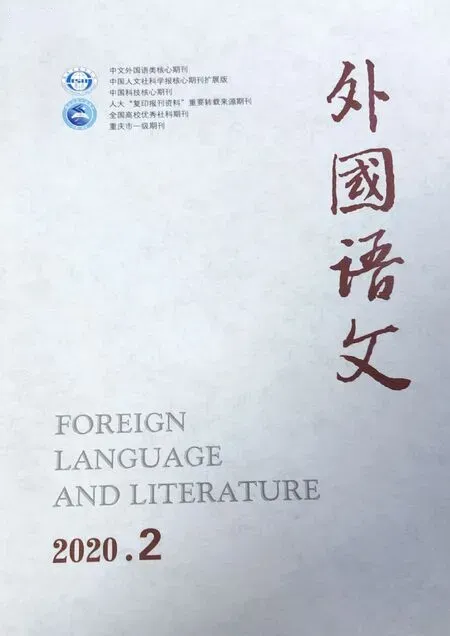苦痛与迷茫:《在女人中》的阈限性革命
朱新福 伊惠娟
(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6)
0 引言
约翰·麦加恩 (John McGahern, 1934—2006) 是20世纪下半叶爱尔兰文坛杰出的小说家,英国《卫报》称他是“自萨缪尔·贝克特以来最伟大的爱尔兰作家”(Price, 2010:27)。1990年出版的《在女人中》(AmongstWomen) 是他的代表作。该作品先后获得“爱尔兰时报文学奖”和“爱尔兰影视文学奖”等文学奖,并入围当年布克奖决选名单。早期的批评家们一般都认为爱尔兰现代文学奠基者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1941)对这位后起之秀的创作影响颇大,并指出其作品中的现实主义展现了更多乔伊斯时代无法书写的社会禁忌(Brown, 1991:159)。近年来,麦加恩作品中的爱尔兰乡村描写、对独立后爱尔兰天主教的批判性思考、对社会移民潮的书写以及独特的回旋式叙事方式备受国内外学者的关注。陈丽指出,《在女人中》“揭穿了文艺复兴作家关于爱尔兰西部农村的田园乌托邦神话,展示了巨变将要到来之前的真实乡村图景”(2017:91)。小说秉承了作家一贯的写作风格,将故事背景设定在爱尔兰岛北部的乡村牧场,讲述爱尔兰共和国老兵迈克尔·莫兰 (Michael Moran) 由中年逐渐走向死亡的战后生活故事。由小说题目可见,故事围绕莫兰的家庭生活展开,述说他对家庭成员尤其是女性(妻子和女儿)的暴力统治,批评家们不约而同地聚焦小说中体现的“父权社会的终结”。“莫兰对妻女的暴力统治并不是绝对的,在一步一步走向死亡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是子女的独立,权力的瓦解,永久的悲剧。”(Hanna, 2015:95)但这些观点只关注家中两性权力的抗衡,忽视了作品蕴含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小说开始,莫兰已是迟暮之年,老之将至,这位退役老兵的一生在不断的回忆倒叙中呈现出来,故事几乎跨越了整个20世纪中后期。此时的爱尔兰虽看似已脱离殖民统治,沐浴着胜利和平的喜悦,实则依旧暗潮涌动,纷争不断。1921年1月,《英爱条约》 (Anglo-Irish Treaty) 的签署宣告爱尔兰自由邦和北爱尔兰的成立,但也随之引发条约支持者和反对者之间的激烈冲突。条约反对者反对保留英国与爱尔兰之间的政宪联系,也反对北爱尔兰六郡归于英国,这成为内战导火索。内战伤亡远大于之前的独立战争,并在爱尔兰社会留下深刻裂痕,对今日爱尔兰政治的影响仍显而易见。经历血雨腥风洗礼的爱尔兰并未实现其民众期盼的国泰民安和欣欣向荣。战争的余威、党派纷争、精英政治崇拜以及经济停滞等现象依然笼罩着整个国家,爱尔兰面临着由战争走向和平、由殖民走向独立的艰难转变。显然,作者将故事置于这一背景下不仅仅是为了批判男权暴力统治。莫兰对家庭的暴力行为,其挥之不去的迷茫、苦痛与悲剧在本质上源于殖民与战争对战后爱尔兰的持续影响。
麦加恩在一次采访中谈到自己作品中的政治指向。他说:“一个国家最具有天赋异禀的人总是对其政治持批判态度。”(Maher et al., 2002:89)莫兰是爱尔兰共和军老兵,参加过辉煌的独立战争,经历过残酷的内战,虽然战后他买了一片农场并再婚,过着看似普通的日子,但每当他回忆起逝去的岁月,失落挫败感却涌上心头,话语中无不透露出对战争与战后政策的失望与无奈。通过描写莫兰对战争的追忆及其在新政权下的生活,小说展现了殖民与革命战争对独立后爱尔兰持续不断的影响,描写了由战争到和平、由殖民到独立转变过程中政治政策和党派纷争等给人们带来的迷茫与苦痛经历。
1 余波未平:和平下的纷争
武装暴力是阈限革命中争取政权独立的惯用手段,从小说中莫兰对战争经历的回忆看,在独立后的爱尔兰,阈限革命暴力余威仍挑战着老兵莫兰对于团结统一的认知。词源上,“阈限”来自拉丁语 “limen, limin” (英语threshold),意为“过渡的,跨越界限的”(张春明 等,2007:1229)。阈限性(liminality, liminal)由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尔德·范·热内普(Arnold van Gennep)在研究“通过仪式” (rites of passage)时提出,其含义是指“个体的生活不断从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通过仪式”共有三个阶段,阈限阶段(margin or limen)是处于“分离仪式”(separation)和“结合仪式”(aggregation)之间过渡的中间阶段(Turner, 1976:94)。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将热内普的人生礼仪三阶段改为阈限前(pre-liminal)、阈限(liminal)和阈限后(post liminal),并将研究重点放在仪式过程的核心阈限上(1976:94-95)。特纳认为阈限不是一种“状态”(state),而是处于结构的交界处,是一种在两个稳定“状态”之间的转换(1979:465)。现代研究进一步扩展了阈限性的概念。社会学家比恩·托马森指出,所谓阈限性,“即各种过渡期,其间施加于思想、自我认知以及言行的常规约束得以放松,由此,创新、想象、结构以及解构应运而生”(Thomassen, 2014:1)。阈限性理论跨越社会学研究范畴,进入政治和文学中的阈限空间研究视野。
莫兰曾是一名在独立战争中浴血奋战的英雄,本应享受用生命换来的独立自由,但事实上他却一直无法适应和平生活,忆起往昔的枪林弹雨,言语中交织着自豪与失落:“那是最痛苦的日子……打仗时天气湿冷,整个晚上隐蔽在下水道里,只有脖子露出水面……这就是战争。”回望过去,莫兰叹息:“我们又得到了什么?一个国家?如果你相信他们的话。这一切的意义又是什么,整场战争就是一场笑话。” (McGahern, 1990:5)为何曾为之献身的独立革命在获得胜利后却带给莫兰如此大的痛苦,是什么将这一光荣使命沉沦为参与者内心不愿面对的耻辱?这一切与革命战争这一“阈限”阶段的余威密不可分。
阈限性与现代社会发展关系密切。托马森指出,政治革命是典型的阈限过程,这一过程中现存的社会制度与阶级将被推翻,原有的社会结构与规约正土崩瓦解(Thomassen, 2014:119)。1921年《英爱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爱尔兰独立战争(也称“英爱战争”)的结束,南爱尔兰26郡成立爱尔兰自由邦,北爱尔兰6郡仍隶属英国。南爱尔兰看似将要实现自治,但条约规定爱尔兰的高级官员要宣誓效忠英国王权。战争时,英国有权在爱尔兰建立军事基地。条约在爱尔兰内部引起了政治分裂。曾经并肩作战的新芬党 (Sinn Fein Party)随之分裂为拥护和反对两派,长达一年的内战最终于1923年以拥护条约派的胜利告终。硝烟弥漫、炮火连天的革命时期似乎已远去,百年殖民制度被推翻,迎来的是独立新生的自由,但事实上革命的余威仍笼罩着刚刚被战火洗礼的国家,战争和革命似乎成为遥远而又清晰的记忆。
1923年,拥护条约派获得内战胜利,登上政治舞台,为了铲除政治对手,随之展开了对反对条约派的各种打压。“据估计,战后几乎所有的爱尔兰共和军(反对条约派),尤其是俘虏都被列入黑名单,无法享受任何权益,艰难困苦,备受歧视,许多共和军流亡海外。”(Foster, 2015:173)为了推翻原有的统治或制度,革命常常意味着战争等暴力手段,但更糟糕的是,这种“暴力获取权力的方法很难随着战争的结束而消失”(Thomassen, 2014:211)。1937年,瓦勒拉(Valera)当选总理,他领导的反对条约派重回政治舞台。虽然瓦勒拉一再保证“不会迫害或歧视拥护条约者”(Dwyer, 1998:101),但国民军依旧活在担忧、负罪和迷茫之中。前统一党(拥护条约派)的总理菲奥娜·林奇 (Fioana Lynch) 直言自己的迷茫与困惑:“我们觉得自己是国民军的叛徒,他们曾为了拥护条约献出生命,我们曾坚信条约的签署会带来和平安宁,如今我们却临阵倒戈。”(Dwyer, 1998:101)莫兰在和战友的相聚中不断地诘问:“国家确实是属于我们了,但看看现在的爱尔兰,一群头脑简单,自私自利的人掌控着一切,还不如独立战争根本没有发生。”(18)
战后两党之间为争夺爱尔兰自由邦统治权的纷争则是殖民战争和内战权力争夺的延续。在革命权力争锋余波中,党派之争愈演愈烈,无数像莫兰这样曾为了和平统一抛头颅洒热血的老兵陷入怀疑与迷茫的深渊。政治学家比尔·基森指出:“在内战之前,爱尔兰人民一直以团结对外的民族主义而自豪,这种民族自豪感超越了任何内部矛盾……然而这一论点却随着《英爱条约》引发的党派纷争不攻自破。”(Kissane, 2005:22-23)人们怀着美好的愿景,期盼战争结束并迎来和平与统一,但最终国家却走向分歧,在拥护或反对条约中失去了最初的目标。对于像莫兰这样的老兵,战争岁月虽然艰苦,但却赋予生命最明确、最具使命和自豪感的目标。跟自己战友一起津津有味地回忆起血腥战功,莫兰不禁感叹:“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战争是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时刻。一切都是如此简单清晰。”(6)
麦加恩在一次访谈中直言:“在一定程度上,莫兰是故事中虚构的人物,但他也代表着大多数人的状态,承受着梦想破碎的痛苦……[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辉煌自豪的时刻,因为他们为了共同的使命而努力。”(Maher, 2001:72)革命美好憧憬在党派纷争中沦为和平掩盖下的幻影。莫兰的生活看似平静,但却在不断的回忆中充满了无奈与迷茫,失望与痛苦。 “记忆是他[莫兰]最大的敌人,最具摧毁性的力量,不断提醒着他战争的失败,不安的局势,挑动着他躁动的心。”(Harte, 2014:58)
2 精英游戏:这不是我的家园
在小说中,阈限革命的余威还体现在权力等级的制度化上。《在女人中》的故事大致发生在1923年内战结束后至1990年爱尔兰第一位女总统当选期间。近半个世纪,无论是在拥护条约派的统一党还是反条约派的共和党执政期间,独立后的爱尔兰都是民生凋敝、经济萧条。由内战引发的党派斗争让莫兰质疑曾经浴血奋战的意义,而不顾大众疾苦只为议会大权的精英游戏更让莫兰失望至极。“革命时,革命参与者之间总会出现权力等级的划分,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者总是以代表人民利益的口吻说话。这种严格的等级制度会在革命结束后继续盛行,并且通常会导致最坏的结果,即阈限革命中权力等级的制度化。”(Thomassen, 2014:210)具有阈限性的革命结束后,领导者通常会将革命中的权力等级制度化,这一过程中位于权力金字塔的人为了保住阈限过渡阶段的地位,常常不顾大众的诉求与权益。战后的爱尔兰新政府政策难辞其咎。内战结束,统一党上台后,为了稳定民心保住统治地位,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得少数人成为经济中流砥柱,制造了经济繁荣假象。共和党的政策本质上就是“牺牲大众保障少数精英的利益,从未考虑小农利益”(Kissane, 2005:171)。众多小农因殖民而存在近一个世纪的经济劣势并未因独立战争的胜利而改变,爱尔兰“依旧依靠英国市场,大农场主依然是国家经济的支柱,决策者从未关注到乡村的贫穷落后”(Dunphy,2015:248)。
小说作者通过莫兰与昔日战友麦克奎德(McQuaid)相聚一幕深入剖析了精英政治下莫兰矛盾失望的心理状态。每年2月25日为爱尔兰天主教的传统节日蒙纳干日(Monaghan Day),这一天莫兰都会与麦克奎德相聚。交谈中莫兰总是表达出对当局者的不满:“现在拿着津贴,享受声名利禄的人连枪都分不清楚,而真正浴血奋战的人却一无所有,要么早早入土,要么背井离乡。看着自己曾为之拼命的国家,有时真的感到厌恶。”(15)战争已经结束,生活归于平静,无论是退役老兵还是普通大众都开始关心生计,“曾经年轻的起义军们也人过中年,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人势必开始为生计担忧”(Foster, 2015:172)。莫兰虽然买下一片小农场,却也无法摆脱对贫穷的担忧和恐惧,“他犹如畏惧疾病一般畏惧贫穷”(10)。为国家独立几乎付出性命,却依旧过着与殖民时期相似的生活,精英政治和经济劣势让这个新生的独立国度沦为另一种形式的“殖民”。政治学家汤姆·加文在《前景未卜:为什么爱尔兰一直如此贫穷》(PreventingtheFuture:WhyIrelandAreSoPoorForSoLong)一书中描述战后爱尔兰政治时写道:“战后爱尔兰政府代表了新生一代野心勃勃的天主教精英的利益……最初奋战的革命者逐渐从政治舞台消失,新的领导者没有任何革命情怀,他们只关心权力得失,从不在乎国家利益。无助和愤怒笼罩着大多数人的生活,人民的权益得不到保障。”(Garvin, 2014:26-27)精英政治的延续让莫兰对现有的生活只剩失望,他对当局者的厌恶甚至表现为迫使女儿莎莉(Sheila)放弃上大学的机会及成为医生的梦想,莎莉明白“站在这个国家金字塔顶端的人是牧师和医生,而不是曾经豁出性命的革命者”(88)。
经济发展在共和党瓦勒拉执政期间也是每况愈下。选举获胜后,瓦勒拉不计后果废除了统一党自由贸易政策,实施贸易保护,高额的关税在1932年引发了英爱之间的贸易战。长达六年的贸易战让爱尔兰经济形势跌入谷底。“贸易保护政策完全是以自给自足、完全脱离英国的独立意识为出发点而不是农民的利益……当整个欧洲经济全速发展时,爱尔兰经济却止步不前。”(Breen et al, 1990:30)政府对居高不下的失业率置之不理,导致移民数量激增。“十年间,大约40万人逃离爱尔兰,去海外谋求生路。1952年,大约五分之一战后出生的人移民他国,年轻人移民率甚至翻倍,移民人口一度和出生人口数量持平。”(Breen et al, 1990:35)被迫逃离给移民者和留守的人都造成了巨大的伤痛和苦难。莫兰的子女随着年龄的增长也纷纷离开父亲的牧场,在都柏林或者伦敦定居。他们虽然迎来了新的生活,但却无法在大城市找到身份归属感,于是回家探望亲人成了他们支撑流亡生活的力量。“对于莫兰家的女儿们来说,不时地回家让她们重新找回自我优越感。”(93)爱尔兰批评家迪克兰·凯伯德(Declan Kiberd)指出:“牧场给予莫兰女儿们生活的意义和概念。”(McWilliams, 2013:125)身份的追寻成了莫兰女儿这一代人必须面临的困境,他们一方面想要逃离不满的环境,希望在另一个国家享受富裕的生活;另一方面原生环境的影响又让他们无法完全融入另一个世界。“移民者们虽然在英国享有爱尔兰没有的资源,但却对自己的祖国有着深深的负罪感。这些移民者忠于自己的国家和信仰,认为自己不属于英国。但当她们回到爱尔兰,发现他们也不属于这里了。”(Wills, 2015:4)
移民不仅让离家的年轻一代陷入迷惘,也加剧了莫兰的痛苦。在莫兰眼里,英国就是敌人的代名词。妻子提议让大女儿马吉(Maggie)去英国做护士,莫兰反驳道:“多少人在英国走了歪路。”(49)麦加恩在采访中谈到移民与道德关系时指出:“去英国谋生的人常常被人看不起,好像他们犯了什么滔天大罪,留下来的人仿佛才是道德崇高的。”(Maher, 2001:75)上文提到的麦克奎德在独立战争时曾是莫兰的下属。战后他移民美国,靠买卖牲口发家致富。当初“麦克奎德刚开始做生意时莫兰还借给他一笔钱,但现在麦克奎德却财大气粗”(14)。不同的人生遭遇和价值观让这次相聚成为两位老兵友谊的终结。让莫兰更无法接受的是自己的儿女也一个个逃离牧场,迁居都柏林或者伦敦等城市,倒戈“敌方”。无奈之下,他不断诘问:“我的家人几乎都在为英国工作,曾经的反抗到底有何意义?”(5)阈限性革命虽已结束,但革命中的权力等级俨然已成为政客争权夺势的游戏的终极目标,以牺牲大众利益博取议会一席之地的精英政治让许多像莫兰子女一样的年轻一代逃离家园,使失望的莫兰痛苦不安地生活在封闭的牧场上,精英游戏下的爱尔兰已不能称之为心中的“家园”。
3 牧场共和国:爱尔兰的一面镜子
小说围绕莫兰一家的牧场生活展开,革命共同体思想在天主教的助威下对战后爱尔兰的影响也体现在日常家庭生活的描写中。莫兰作为一名退役的游击队领袖,对独立战争后的爱尔兰极度不满,但又无力改变外部世界。莫兰只能将理想寄托于家庭,他对家庭成员身体和精神的暴力统治使自己和家人都坠入痛苦的深渊。这种将家庭缔造成暴力统治的“共和国”的行为与当时爱尔兰社会大环境密不可分。
战争或者革命时期是处于两种社会结构之间的过渡阈限阶段,参与者“曾怀着满腔热忱,热血沸腾地朝着同一个目标而努力。处于阈限阶段的革命者们在这个过程中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同属于一个共同体(communitas)”(Thomassen, 2014:196)。虽然这种革命情结或共同体思想会随着阈限阶段的结束逐渐消失,但却很可能导致更危险的结果:共同体的无限化(exaggeration of communitas)。在宗教或政治运动结束后,存在于阈限阶段的共同体思想通常会恶变为“专制主义、官僚主义或者其他形式僵化制度”(Turner, 1977:129)。殖民时期,英国清教徒在爱尔兰享有绝对统治权,坐拥大片土地,在政治经济等社会领域占主导地位。“爱尔兰与英国的差异更多的是被英国所构建出来。因此,殖民的过程不仅是武力征服,更重要的是两种文化之间刻意地划分出高下。”(李元 等, 2016:32)战后共和党(反条约派)赢得议会多数席位后,瓦勒拉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重建天主教在爱尔兰的地位,以突显有别于英国清教的“爱尔兰性”,重塑独立战争时的“统一”的共同体思想。
在爱尔兰国庆日圣帕特里克日(St. Patrick's Day)的演说中,瓦勒拉公然表示了自己政教一体的执政理念:“爱尔兰从古至今都是天主教国家,这是我们永恒的命运,凌驾于其他一切教义和神祇。爱尔兰人民绝不允许我们的信仰遭到任何形式的抹杀玷污,只要我们秉持这种信念,其他任何形式的国家崇拜也将不复存在。” (Breen et al, 1990:28)1937年颁布的《爱尔兰宪法》(BunreachtnahEireann)标志着天主教正式成为爱尔兰社会的一大支柱。宪法第41章第一条规定,国家绝对认可“家庭是整个社会的根基,享有最高特权,是其他社会秩序的前提”(Wakefield,2018:92)。20世纪当其他欧洲国家正为政教分离而不懈努力时,爱尔兰却截然相反。麦加恩坦言“那是教堂统治着一切的时代……教堂如同军队,享有绝对权威,不可置疑”(Maher, 2001:72-76)。家庭作为战后爱尔兰的社会支柱,教会的绝对权威在这个小单位里展现得淋漓尽致。
根据爱尔兰天主教的传统,男性是一家之主,莫兰在牧场、家庭的权威如同教会在战后爱尔兰的地位一样不可侵犯。莫兰一直坚持全家一起唱诵《玫瑰经》(“Rosary”),多年来从未间断。其唱诵通常由莫兰引导,然后分别由妻子和孩子完成剩下的祈祷唱诵。这一看似平常的宗教仪式实则映射出男性在家庭中的权威与地位。“习以为常的宗教仪式中特定唱诵顺序本质上体现了莫兰对家庭成员的操控。”(Wakefield, 2018:257)在整个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莫兰将对战后爱尔兰的不满与失望自然而然转嫁于家庭,在自己可控制的地盘上试图建立理想中的“牧场共和国”。在莫兰眼中,家庭如同军队,家人则是自己的下属。小说开头描写长大成人的女儿们相约蒙纳干日这天回家看望老人。看到归家的女儿们,莫兰不知不觉说道:“怎么今天的军队人员都到齐了!”(3)纵然老之将至,虚弱不堪,莫兰依旧把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看作自己的下级。对经历过战争的莫兰来说,家庭是发泄情绪和体现自我价值的“王国”。
家庭成员是莫兰极端情绪的承受者。极端的挫败感让莫兰变得性情多变、暴躁不安。他常常无缘无故大发雷霆,即使在他与第二任妻子的婚礼当天也难掩内心的焦躁与暴力。“一整天他[莫兰]都感到愤懑不安,看似生活又向前一步但却又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45)似乎所有人都在担惊受怕地等待着莫兰情绪的爆发。与第二任妻子露丝(Rose)结婚前,露丝的母亲曾试探地问莫兰的女儿马吉:“听说你父亲经常打你。他打过你们吗?”胆小的马吉只是含糊地回答:“我们有时调皮,他会打我们,但很多家庭都这样啊。”(34)第二任妻子婚后不久就察觉到异样的气氛,发现孩子们似乎“被一种力量主宰控制”(46),“每次她跟莫兰女儿们谈话,只要莫兰出现,孩子们立刻鸦雀无声,房间陷入死一般的沉寂”(53)。 “莫兰代表的是参加过独立战争那一代人中的任何一员,无论是他对战争年代血腥战功津津有味的回忆,还是对家庭成员的暴力统治”(陈丽,2017:93),他将自己试图通过反殖民战争实现国家统一的所谓理想变相地强加给了妻子和儿女。
小说的题目“在女人中”出自天主教《玫瑰经》中的一句经文“在妇女中你最受赞颂”(陈丽,2017:93),是赞颂圣母玛利亚的一句话。莫兰在其家庭的位置是“被女人们环绕的中心,他替换了圣母。但一方面他是家庭绝对的男性家长,另一方面,他处于一种被包围的弱势状态”(陈丽,2017:93)。年轻时的莫兰是牧场独裁“国王”,掌控着子女的命运,但渐渐老去的莫兰无力阻止孩子成长独立的过程。随着儿女一个一个离开牧场,莫兰失去了生命的最后支撑,在妻女的注视中离开了这个世界。权力的瓦解、角色的置换带给以家庭为生命根基的莫兰莫大的苦痛和耻辱。面对死亡,莫兰更惧怕权力角色的互换,年迈的莫兰在妻儿的包围之中感到“人生第一次开始害怕他们”(178)。
战后,教会掌控着爱尔兰的方方面面,试图通过宗教实现国家统一,增强民族凝聚力,彰显爱尔兰作为独立国家的民族性。这种社会价值几乎渗透到20世纪爱尔兰的每个家庭,麦加恩在评论宗教政策对战后爱尔兰的影响时指出:“家庭是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似乎整个国家由数以万计个小的家庭共和国组成,秉着一个原则各自施行自己的统治。”(Gonzalaz, 1988:174)莫兰的“牧场共和国”只是当时特定社会背景下的缩影,折射出独立后的爱尔兰在经历百年殖民与战争后希望通过宗教重塑革命时期的凝聚力和民族性的理想。 “莫兰最大错误就是将自己社会理想的实现仅仅寄希望于宗教和家庭。”(Maher et al., 2002:95)20世纪后期爱尔兰教会因性侵女性和儿童等弱势群体逐渐失去民众信任和政治地位,莫兰的悲剧在一定程度上也暗示了不良教会势力的最终结局。
4 结语
殖民与战争并未真正随着一纸条约的签署退出爱尔兰人民的生活,相反,它们以各种形式波及这个新生国家的方方面面。革命延续下的权力纷争以及精英政治打破了人们革命时期的梦想,让无数像莫兰一样的老兵唏嘘无奈。和平表象下的暴力充斥着每个角落,造成了莫兰及其家庭成员的悲剧与迷茫。“一开始可能觉得书中记录了战后老兵的生活,但你会逐渐发现,它讲述的是一段缺失的历史,真正的国家民族并未随着战争的结束诞生,社会也没有进步。”(Maher, 2009:226)麦加恩在书中真实再现了20世纪独立后爱尔兰的乡村生活,揭示了生活在阈限革命阴影下一代人的失望和迷惘。麦加恩以家庭为背景的现实主义书写更加贴近生活,作品表现的个人悲剧透露出作者对战争和殖民的深刻思索以及对国家命运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