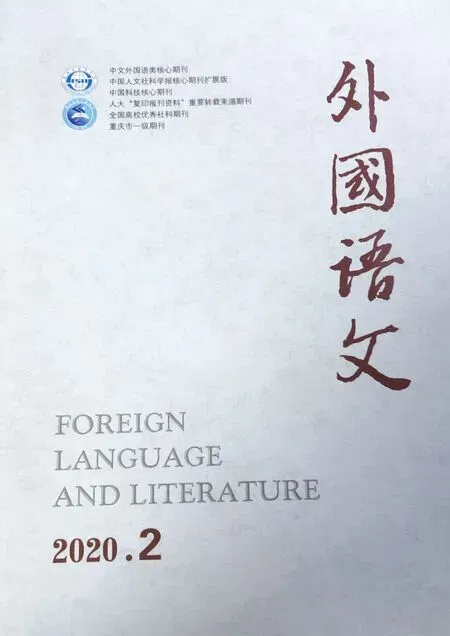传承与超越
——著名德语文学翻译家杨武能教授访谈录
李小青 杨武能
(1.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2.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5)
杨武能,著名德语翻译家,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全集》等经典译著60余种,并有《杨武能译文集》(11卷)行世。出版论著《歌德与中国》等5部,编著《歌德文集》(14卷)、《海涅文集》(5卷)等10余种。出版散文随笔集2部。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首席专家。因在德语文学译介和文化交流中的突出贡献,先后获得德国“国家勋章奖”“歌德金质奖”和中国译协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
1 文学翻译的传承者
李小青: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您是著名的德语文学翻译家,迄今为止一共翻译出版了60余部译著,译作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您的翻译成就也使您先后获得了德国“国家功勋奖章”“洪堡学术金奖”“歌德金质奖章”,尤其是在2018年您获得了中国翻译协会颁发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这是中国译协设立的表彰翻译家个人的最高荣誉奖项,主要授予在翻译与对外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杰出贡献、成就卓著、影响广泛、德高望重的翻译家。我注意到,您的翻译成果主要集中在德语文学翻译上,请问您为什么会选择文学翻译?
杨武能:对于这个问题,我把回答概括为一句话:“走投无路,因祸得福。”我中学时的理想,是做一名祖国建设急需的水电站工程师,但升学体检发现我色弱,达不到学习工科的视力要求,理想破灭备受打击。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高中语文老师的课精彩至极,极富启发性,渐渐地使我产生了对文学的爱好;另一位俄语老师上的课生动活泼,能让人学以致用,又让我深深地爱上了俄语。那时候学校图书馆里有不少俄罗斯和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的中译本,我把能找得到的都借来,如饥似渴地阅读,仿佛透过那些文字,足不出户的我看到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时间一长,看的书多了,自然也就会对比不同译本给人的感受,也慢慢悟出一个道理: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否好看、耐看,是否能让更多的读者喜爱并沉浸其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文的优劣。因此,文学翻译家的作用和贡献,是实在又卓著的。走投无路之下的我,忽然觉得,当一名文学翻译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
带着这个梦想,我考入了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前身西南俄文专科学校,成为一名俄语专业的学生。可很快因为中苏关系破裂,俄语人才过剩,我不能继续学俄语了。万幸的是,因为成绩优异我得以转学到南京大学学习德语。在这里遇到了我从事德语文学翻译的引路人。
1959年我的第一篇巴掌大的民间童话小译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给了我极大的鼓励。这时我遇到了才华横溢又循循善诱的叶逢植老师。叶老师虽然年轻,但已经在《世界文学》上发表了多篇译作。他不仅对我的语言和文学翻译给予极大的指点,还鼓励我挑战翻译文学精品,并将我的译作引荐给《世界文学》杂志,结果从1962年起,我的译作便陆续刊登在《世界文学》杂志上。开弓没有回头箭,我的德语文学翻译,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李小青:杨老师,从您翻译的60余部作品来看,涉及的文学类型很丰富,有小说、诗歌、戏剧、童话、寓言、访谈录等等,但几乎都是名家名作,如歌德、托马斯·曼、黑塞、施笃姆的小说,海涅、里尔克的诗歌,席勒的戏剧,格林兄弟的童话等等,基本上贯穿了德国文学全史。请问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因为名家名作更具影响力吗?
杨武能:一定程度上可以这么说。首先我们要弄清楚文学到底是什么。有人说文学也就是人学,文学关注人类社会中的人,讲述人的故事,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伤春悲秋,人们的恐惧与希望。从根本上讲,文学和哲学有共同的基点,都是在追问人的本质和价值,只是追问和呈现的方式不同,但殊途同归。哲学重在逻辑地沉思,文学强在审美地表述。我听到过一种说法,说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哲学的沉思是其骨架,文学的审美则是其血肉。我比较赞同这种说法,文学就是用引起人们情感愉悦、心灵震撼的方式,让人们领悟对人生的思考。而文学大家,就是那些思想深邃、表达技巧高超的人,他们通过作品呈现的东西,影响广泛,而且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认为我的翻译,首选这些文学精品,因为它们的营养价值更丰富,阅读这样的作品,才会让人在审美的同时,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我把对文坛巨匠作品的阅读和翻译视为一种传承。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的高度,除了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成就,更为重要的是能终身滋养我们心灵的精神财富,而文学就是最重要的传承精神财富的载体。我们阅读文学作品,就是在文学的虚构世界里探寻大师们留下的宝藏,阅读、接受和传播,就是对这些宝藏的运用和传承,于己于人,善莫大焉。
李小青: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教授曾把您比喻为“打开窗户的人”(陆建德,2012:31-32)。他认为,经典的外国文学作品,因为语言等因素的障碍,好似被紧闭的窗户挡住的美好异域风景,而“文学翻译家则是打开窗户的人,他让屋内的人足不出户就能看到窗外各种景色,功莫大焉”。您认可这个比喻吗?
杨武能:我认为这个比喻是比较客观的,不光是适用于我,也适用于所有的翻译家。翻译家掌握了语言的利器,率先跑去异域风景逛一圈,并且在那里流连忘返。风景美好,养眼、悦心、益智,但是这么好的风景,我怎么能一人独享呢,好东西要分享,它的价值才更大。这是我埋头德语文学苦译的根本动力。
我曾经说自己是一个“文化苦力”,并未言过其实。翻译的过程自然是很艰辛的,脑力劳动自不必说,那是需要绞尽脑汁地思考、推敲和选择。我绝大多数作品的翻译,是在电脑还没有成为普及的输入工具的年代完成的,全靠一笔一划在稿纸上写字、修改、誊抄。艰苦归艰苦,但我仍然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翻译的过程,会让你沉浸在文字的美妙中,沉浸在思想的深邃中,跟随文学世界中的人物,体验不同的人生,丰富人生的感悟。同时,我感觉我是在和这些作家们进行着跨越时空的交谈,我和他们隔着时空建立起了精神联系。我把这种辛苦看作是一种爱和享受,因为我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受益匪浅。而我翻译的书传递到读者那里,就是把这种文学世界的漫游、宝藏挖掘和文化传承的过程复制到更多的读者身上,就是让作家、我和千千万万的读者建立精神联系。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当你看到自己的心血,被更多的读者接受,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异域的文化、异域的思想,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知,你会觉得自己的辛苦是值得的,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
2 文学翻译的超越者
李小青:杨老师,您的译作中有不少重译的作品,尤其是您那本印刷了150多万册、影响巨大的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后简称《维特》),在您重译之前,该书已有几个译本,有的还出自名家之手,比如郭沫若。郭译的《维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青年读者中掀起了“维特热”,进而发展成为“歌德热”,极大地影响了我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郭译的珠玉在前,有他的名望和影响力在前,您为什么会选择重译呢?
杨武能:我在社科院读研时,有不少其他专业方向的同学向我抱怨说德国文学不好看,连郭老译的大名鼎鼎的《维特》也是徒有虚名,这就伤了我的自尊心。但我也承认,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郭译本的语言已经变得陈旧过时,不再为现代的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所接受。我那时在译界虽然还是初出茅庐,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斗胆对《维特》进行了重译。我敢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敢出版。一开始我还是有些惴惴不安的,但没想到出版后竟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能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这就是对我重译的认可。
李小青:在译界,专家们一致认为重译是一个历史文化现象,文学文本自身所具有的意义不确定性和开放性,再加上历史、文化、社会与时代等因素,使得重译成为一个世界性的现象(杨武能 等,2000)。但是,翻译从业者都清楚,重译的难度很大,甚至比首译还要大,译者不仅要完美地传递原文的意蕴,还要区别于已有的译文,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前人的超越。请问杨老师,您赞同这个看法吗?
杨武能:的确,重译有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能够广受欢迎的因素也是很多的。但对译者而言,重译的确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活儿,这对译者的能力和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就像俗话说的,没有金刚钻,揽不来瓷器活。对于文学翻译,我有过两句描述,一句是:翻译家就像个仆人,而且是“一仆二主”,另一句就是“翻译家是戴着枷锁献艺的舞蹈家”。第一句说明译者不仅是仆人,而且还要同时侍奉原著和译文读者这两个主人,如果你没有把原著吃透,没有把握住原著的精髓,甚至曲解、遗漏、错误理解了某些东西,那你就是没有把原著这个主人侍奉好;如果你的译文不受读者待见,或者让读者形成对原著的误读,那就是没有把读者这个主人侍奉好。这句话适用于所有的文学翻译。第二句话则特别适合用来描述重译,作为献艺的舞蹈家,姿态要舒展自如,表演要充满生气,但戴着枷锁就意味着受到了严格的约束和限制,且这个枷锁是双重的,一方面来自于异域文化的原著,另一方面则来自前人的译著,尤其是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译著。这对译者来说,是一个双重挑战。重译不光要经得起与原著的对照评估,还要避免让旧译牵着鼻子走,不仅不能对旧译亦步亦趋,还要做到推陈出新,更上层楼。要做到这一点,唯有绞尽脑汁,以求有新的创造,以期达到超越旧译的目的。
我对我自己的重译作品还是比较满意的,选择重译很大胆,所幸效果不错,受到了广大读者的赞赏和欢迎,也得到了译界的肯定和鼓励。能让德语文学名著在新的历史时期获得新的生命,一次次焕发青春,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超越。
李小青:就像您刚才说的,文学翻译要超越前人,这个过程需要“绞尽脑汁”和“新的创造”,这是让译作获得成功的关键。您能具体说一下如何才能做到吗?
杨武能:我曾经提出过,翻译家既是读者,又是作者;既是阐释者,又是接受者,理想的文学翻译家必须同时既是学者又是作家(杨武能,1987)。有人因此用“三位一体”来形容,我觉得很贴切,准确地定性了翻译家的身份,描绘了翻译家的境况。所谓学者,意味着他不仅很好地掌握了外语,还需要对所译作家、作品及其文化背景有深入的研究,才能把握作家的思想脉络,了解作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把握浸透在他们骨子里的文化价值传承,才能在原著的字里行间里看到文字背后作家的所思、所想、所感和所悟。我一直主张翻译什么,就研究什么。我在社科院读研时,跟随导师冯至先生研究德国大文豪歌德,从那以后,就没中断过对歌德的研究和翻译。只有深入地了解,你才能懂歌德,才能把他的思想在译文中准确地阐释出来、传递出去。正是这种深入的研究,对我翻译歌德的作品,最后形成14卷的《歌德文集》,起到了巨大的助力作用,同时,也形成了《歌德与中国》等研究成果,并作为首席专家,带了一帮年轻人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歌德及其作品汉译研究”。获得世界歌德研究领域的最高奖“歌德金质奖”也是鉴于我在研究、译介歌德方面所获得的成就和贡献。所以这也是个一举两得的方法。
至于说作家,这就要说到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了。不同于其他类型的文本,文学最首要的功能是审美,文学家的厉害之处就是能用大家都司空见惯的文字打动你,唤起你的情感,激发你的深思。现在的机器翻译很厉害,很有效率,但就是不能很好地进行文学翻译,因为这种机械的翻译,虽然效率高,却无法反映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思维。有译界的研究者认真仔细地对照了我的译文和原文,说我的译文虽然很好看、很吸引人,但也挑出了数处和原文字面上不对等的翻译,认为我是不是违背了翻译的“信”或者对等的原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美玉与蜡泥》,认为优秀的作家是有文学禀赋的,有丰富的想象力和敏锐的感知力、感悟力,以及一支生花的妙笔。而作为翻译家,你虽然达不到文豪的那个高度,但你至少要和他心灵相通,要有和他相似的文学禀赋,你才能把他写的文字翻译成“文学”。翻译文学作品如果完全拘泥于原文的字句、标点,翻译得毫不走样,那只是字面上的对等,如果缺少了文学的资质,译文便只是毫无生气、少有价值的一团蜡泥而已;但如果你有很好的文学禀赋,有丰富的人生体验和对艺术的敏感,加上你的文学修养和文字功力,你就能通过创造性的文字重组,呈现作者的匠心和巧思,这样的译文或许会有一些瑕疵,但总体上富有文学性,仍然是浑然天成、弥足珍贵的美玉。我长期坚持在翻译的闲暇进行练笔,散文、诗歌、随感都写,出版过一本散文集和一本随笔集,充其量算是个三流的作家,但是这对促成一个一流的翻译家,作用是巨大的。
李小青:其实翻译家这个“三位一体”的身份,结合到您谈的翻译的整个过程,说明翻译家并不只是一个语言的转换中介,不是一个机械的“搬运工”,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加入了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让文学翻译的结果成为真正的翻译文学。陆建德教授在评价您的翻译时,说您不仅为国内读者打开了窗户,“实际上还参与了窗外景色的创造”,让读者透过您的译笔“观赏了无数个您与作者共同描绘的德语世界的景观”(陆建德,2012:31-32)。
杨武能:我赞同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绝不只是在语言层面进行转换。追求文学翻译中的创新,对译者既有挑战,也有磨砺,更有助益。因为新对于旧,就是一种超越。不断地追求创新,才能使人不断地拓展眼界,增强洞察力,才能见人所未见,能言人所未言。翻译如此,研究也如此,做人更是如此。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文学翻译上不断地追求创新,努力走一条自己的路,也是一步一步对自我的超越。译得越多,就看得越多,想得越多,练得越多,手中的笔也越来越顺,译出的作品也越来越受欢迎。这样的超越我是很愿意一直继续下去的,而且我还慢慢悟出,超越别人其实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自我的超越,是自我的提升和完善,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就是要人一辈子不断地追求超越吧。
3 文化交流的践行者
李小青:有人说,文学翻译是一道沟通不同文化的桥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来说,就是促进中外文明互鉴。您的翻译很好地发挥了桥梁的作用,让无数人通过您的译作,了解到了德语文学和其中蕴含的异域文化,称您为文化交流的践行者,毫不为过。
杨武能:我认为,文学翻译是一种静态的文化交流方式,通过文学作品潜移默化的浸润,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虽然我的主业是采用翻译这种静默的文化交流方式,但也很重视现实生活中其他的文化交流方式。早在读研时,我对歌德的研究,就选择了文化交流与影响作为突破口,研究“歌德与中国”。当时的比较文学研究学者,多做“平行研究”,就文本论文本,而绝少做“影响研究”,因为后者难度显然要大得多。歌德虽然没有与中国有直接的接触,但是通过翻译文本,中国文化影响了歌德,而后歌德又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我最后的研究成果是一本专著《歌德与中国》,被学界认为是建国后第一部系统的歌德接受史。
因为做这个研究,我得以有机会去到德国,与德语文学界有了更直接的接触,就萌生了将静态交流变成动态交流的念头。在我的牵线搭桥之下,经教育部和国务院层层批准,于1985年在川外发起和举办了“席勒与中国·中国与席勒”研讨会,这是当时国内外语界举行的第一个大型的真正意义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不仅盛况空前,而且受到德国总理科尔的关注,得到了德国外交部和洪堡基金会的支持和赞助。CCTV采用川外电教馆自己拍摄的录像带,连续数天播放了长达20分钟的会议报道,文化交流方面的影响自不用说,这对川外的发展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远影响。
李小青:杨老师您的眼光和前瞻性值得赞赏,这在当年是一种开先河的举动。前段时间,您是数喜临门,先是获得了中国译协授予的“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同时重庆市成立了“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聘请您为中心主任。您已经功成名就,退休后也不打算好好休息吗?
杨武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奖人数寥寥,但我是里面最年轻的,我还有很多想法想把它们付诸实践。文化交流是双向的,不仅要引进来,还需要走出去。如果说我之前的翻译和研究,主要是引进来,那我现在侧重做的,就是要推动文化的双向交流。刚刚你提到的“重庆国际交流研究中心”,是一个为重庆市文化旅游和国际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和交流的平台,我就是想要利用翻译家、学者们的智力资源,既开展学术研究,也推动国际合作,通过对外翻译出版多语种译著、助推优秀演出剧目走向海外等等活动,来进行多层次、多形式的文化交流。刚刚不是说了嘛,活到老学到老,现在还要加一个,干到老。
李小青:杨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您如今在很多场合都称自己为“巴蜀译翁”,能谈谈为什么吗?
杨武能:我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从小就过惯了爬坡上坎的生活,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性,经得起人生的磨砺和摔打。我又长期在成渝两地工作和生活,巴蜀文化的博大和深邃滋养了我。我用“巴蜀译翁”这个大号或者笔名,意指一个出生在重庆,茁壮于天府之国丰厚肥美的文化沃土,毕生致力于文学翻译的老头子。我用这个名号,表达我对故乡无尽的感恩之情。
李小青:杨老师,您是著名的翻译家,也是川外的杰出校友,您在川外学习、工作、生活数年,对川外也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了解到当年就是在您的力主之下,将名不见经传的川外学报更名为《外国语文》,不只大大扩展了它的学科覆盖面,还从内容到形式都焕然一新,特色凸显,很快赢得了声誉和影响。您同时还为川外的科研发展做了一系列奠基性的工作。今年恰逢川外建校70周年,非常高兴杨老师能作为杰出校友接受我的访谈。
杨武能:我对川外有很深的感情,我的青春岁月有相当长一部分是在川外度过,也参与并见证过川外的建设和发展。虽然后来我调去了川大,但我仍然牵挂着川外的人和事。这些年来,我也为川外培养了好几个博士生,他们都在各自的领域有出类拔萃的表现,和他们的同事一起,为川外的发展做出贡献。我很惊喜地看到川外近年来的飞速发展,有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现在又有了博士后培养,外语学科水平在全国名列前茅,而且开始了多学科的协调发展。我视自己为川外人,为川外感到骄傲。在川外70华诞之际,祝母校的发展蒸蒸日上,也祝《外国语文》越办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