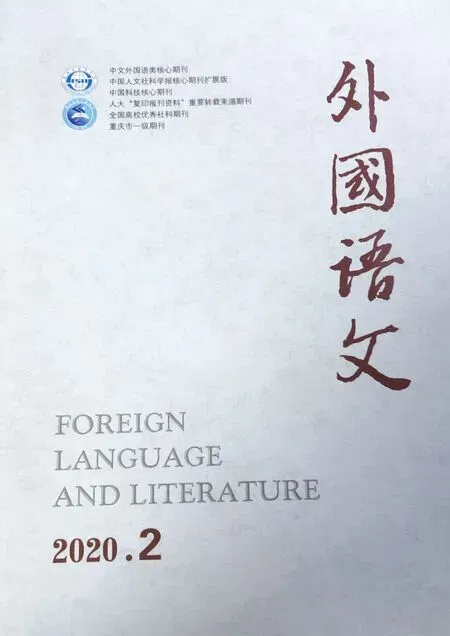钱锺书《谈艺录》中的中西诗学共同体意识
陶家俊
(北京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北京 100089)
陶家俊,1988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英语专业,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英国文学学会副会长,第六届、第七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外语学科评议组秘书长。学术代表作有:《文化身份的嬗变——E.M.福斯特小说和思想研究》、《思想认同的焦虑——旅行后殖民理论的对话和超越精神》(获北京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形象学研究的四种范式》等。
1 《谈艺录》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
钱锺书在《谈艺录》1948年初版序中有两段发人深省的文字。其一是:“《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纾愤,述往思来。……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其二是:“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两段话本质上设定了《谈艺录》的三重学术和思想前提。第一是其产生的现实语境。从他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日本侵略者占据下的上海到日本侵略下的整个中国,广而推及法西斯战争蹂躏下的欧洲和亚洲,其实是天崩地裂,避祸无地。第二是西方文明与远东华夏文明之间的分歧差异。第三是古今学术思想以及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断裂。从现实、历史、文明到学术思想整体上呈现出命脉弱弱、生机僵死、纷争不断、分歧差异的混乱状态。钱锺书的主观期许是文明劫难后的昌达盛世。他的学理预设是:华夏文明与西方文明在最高也是最精微的“心”和“理”上必然有着高度的内在同一性和通融性。他的学术理论命题是:作为人类共同体思想和精神生命彰显形态的“道”和“术”超越战争、历史、文明的藩篱和鸿沟,具有延续重生、生生不息的有机生命力。他就是在上述思想展望、学理预设和学术命题构成的精神境界中来具体关照阐发其诗学。借助对中西诗学的打通烛照,来揭示诗学及其背后的精神和思想最内核的“心”和“理”的趋同相通。
《谈艺录》中,中西诗学打通论述的部分总计24节,约占总体(91节)的四分之一。这24节包括:第1节,诗分唐宋:文学的历时规律;第2节,黄山谷诗补注:文学修辞;第3节,王静安诗:西学精髓与化合;第4节,诗乐离合:诗体演变存续之规律,诗与其他体裁;第6节,神韵:文学中的精神;第9节,长吉字法:诗中的意象物性;第11节,长吉用啼泣字:诗中的情与景的融合交互问题;第15节,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诗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第25节,张文昌诗:诗中的“烛”喻;第28节,妙悟与参禅:诗的悟性或性灵问题;第31节,说圆:诗艺的最高境界问题;第48节,文如其人:诗品与品人;第58节,文通:文辞的通顺与印象;第59节,随园诗话:语言文字的明白晓畅;第60节,随园非薄浪沧:中西光喻、灯喻;第61节,随园主性灵:诗歌创作中的性灵与辛劳“天机凑合”; 第69节,随园论诗中理语:诗中的理趣及诗学修辞;第72节,诗与时文:诗学对修辞学的借鉴必要;第75节,代字:诗中的借代修辞;第82节,摘陈尹句:诗意诗句的新旧;第84节,道术之别;第88节,白瑞蒙论诗与严浪沧诗话:“纯诗”的诗学原则;第89节,诗中用人地名;第91节,论难一概:散文、戏剧、乐、政论。
第3节讲王国维的诗,意旨是西学的精髓及其与中国学术的化合;第84节征引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摩斯(Marcel Mauss)有关宗教与科学的区别,旨在阐述道与术之别。第22节则从不同角度打通中西诗学,形成肌理细密、印证互鉴频繁、诗学论题和论点层层铺陈的诗学阐发和重构特色。需特别指出的是,这种统计完全是按照文本内容和主题自然归类的结果,而不是按照预设的论题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从结构形态讲,据此得出的论断与原文本有着自然、有机的思想生命契合,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出钱锺书本真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对上述24节的结构性重组和总体性阐发,如果以中国古典诗学为参照,学者们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即钱锺书选取中国传统笔记体文体和文言文,用短小的文字篇幅点评中国传统诗学,大量征引各种知识来源的材料,各篇之间没有主题、逻辑、思想上的内在连贯性和系统性。《谈艺录》无非是将各种独立诗艺解析散论串在一起。
《谈艺录》的问世,背景上有三类诗学著述。第一是比他更早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第二是他在清华读本科时的老师、英国剑桥文学批评派奠基人瑞查兹(I. A. Richards)的《实用批评:文学判断力研究》和《文学批评原理》;第三是美国批评家韦勒克(R. Wellek)的《文学理论》。王国维深受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的哲学影响,其《人间词话》将叔本华哲学思想隐入其中,从而立中国古典词学新论。其方法援西入中,以西学为理论指导。瑞查兹的《实用批评》的理论精华在第三部分,分析阐述意义的不同种类、形象语言、意义与感觉、诗的形式、无关联的联想与僵化的反映、感伤与禁忌、诗的原则、技巧预设与批评预想。韦勒克《文学理论》的精华是第三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探讨从外部视角研究文学的方法,如:作家传记研究、心理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观念研究、文艺类型研究。第四部分探究从内部视角研究文学的方法,如:文学艺术品的存在模式、和谐、节奏与格律、风格与文体学、意象、隐喻、象征和神话、叙事小说的本质和模式、文学类型、鉴赏、文学史。韦勒克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关注瑞查兹、利维斯(F. R. Leavis)、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等剑桥派批评家,在布拉格学派的刊物《文字与文学》上发表评论和研究文章,检讨剑桥学派。上述三种诗学理论的划时代之作各有千秋。王国维局限于古典词类,瑞查兹聚焦诗歌体裁。相比而言韦勒克的理论建构最为完备周到。更巧合的是,在英美新批评如日中天之际,韦勒克另辟蹊径、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于1942年出版问世。而此时的钱锺书则在上海与湖南蓝田之间颠沛流离,静夜灯下钩玄钓奥,探究中西诗学之规律法则。
如果我们以韦勒克的《文学理论》之谋局运思为镜子,我们发现上述24节整体上隐含着内在固有的棋路和脉络。沿着这些纵横交错的棋路和脉络,钱锺书重构了一种崭新的甚至比韦勒克更胜一筹、恢宏勃发、通照圆览、永恒高绝的中西跨文明诗学。其结构性脉络包括历时诗学和本体诗学。其精神面向是中西跨文明诗学昭示的诗学共同体意识。
2 历时诗学论
历时诗学探究动态的历史维度中文学的规律和规范,从时间之异中叩问诗学之同与异的规律。在《谈艺录》初版的1946年,德籍犹太语文学家和美国比较文学奠基人之一艾瑞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论模仿:欧洲文学中的现实观》问世。他从欧洲古典诗学的风格论入手探究欧洲两千年文学史,借以把握欧洲两千年的文明进程中文明精神传承更新的脉搏和脉络。钱锺书的《谈艺录》在1、4、82、91这四节中也以诗学风格和类型为经纬,以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为比较参照,钩织历时诗学。
第1节以诗学风格为经,提出“诗分唐宋”的风格论。所谓诗分唐宋,就是以文学自身的风格变化来建构文学史,而不是以政治政体的兴衰存亡为主线。唐诗与宋诗分别创造且代表了两类典型的诗学风格。“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钱锺书,1984:2)因此唐诗和宋诗被从具体的诗人、具体的文学时期中分离出来,成了两种极具代表性的诗学风格,以之既可分辨一个时期文学的演变发展,又可厘清文学史演变过程中重复出现的规律和现象,也可解释诗人作家个体早晚期的风格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他论述道:“诗自有初、盛、中、晚”“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也” (钱锺书,1984:2);“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钱锺书,1984:4)。
钱锺书在论述其历时风格诗学时充分征引了中西实例。英国18世纪文学在风格上接近古罗马奥古斯丁时期文学。18世纪文坛领袖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则被奉为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文学的先驱。西方诗学中与钱锺书持论一致的首推德国的席勒(J. C. F. Schiller)。席勒认为诗分两派——朴素的诗与抒情的诗。法国的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与席勒持相似的观点。在此基础上钱锺书引申出超越诗学范围的结构性比较。以唐诗和宋诗风格来厘定文学的历时演变,其认知结构模式与太极说的两仪论、卡尔·荣格(Carl Jung)的内向与外向心理结构论存在类通。他按照上述论点总结出中国诗史的普遍规律。“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唐以前之汉、魏、六朝,虽混而未划,蕴而不发,亦未尝不可以此例之。”(钱锺书,1984:3)
《谈艺录》第4节转向论述类型意义上的诗学历时规律。其立论辩驳、设定问题的出发点是以清代焦循为代表的诗乐差异论。焦循在《雕菰集》中的立论是:非乐不成诗,晚唐以后诗与文杂,诗失其本。“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钱锺书,1984:27)西方与焦循等的诗乐同体论相呼应的观点有三种。其一是里德(L. A. Reid)在《美学研究》中提出的诗乐利害冲突论;其二是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英国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的诗乐相互妨碍论;其三是诗乐同源论,以德国学者施马苏(A. Schmarsow)为代表。钱锺书认为焦循之流是“先事武断”(钱锺书,1984:29)。文体的历时规律应该是:“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钱锺书,1984:28)针对诗与文杂合的现象,他认为诗分诗情诗体,文、词、曲都极富诗情。“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钱锺书,1984:30)例如文又分为对、联、表、代。代就是揣拟古人圣贤之意作文,即八股文。而八股文源出骈体,在明清之际又与南曲相通,因此与诗、乐通杂而非截然分离。以文入诗的另一例体是文人之诗,“杜虽诗翁,散语可见,惟韩苏倾竭变化,如雷霆河汉,可惊可快,必无复可憾者,盖以其文人之诗也。诗犹文也,尽如口语,岂不更胜。”(钱锺书,1984:34)
西方诗学中对诗学类型的理论同样分别涉及诗与乐、诗与文、诗与史的关系。诗与乐的西方论述前面已谈到,不赘言。就诗与文的关系,钱锺书历数西方诗学中的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雨果(Victor Hugo)、施莱格尔(K. W. F. Schlegel)和什克洛夫斯基(Viktor Shklovsky)。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序言中力戒辞藻,提倡“以不入诗之字句,运用入诗也”(钱锺书,1984:35)。雨果认为一切都可作为题材。施莱格尔认为“诗集诸学之大成”(钱锺书,1984:35)。什公为俄国形式主义诗学先锋,他认为文学类型品相中的新品大都出身卑微,只是一时蟒袍加身,荣登时流上端。就诗与史的关系,西方如维科(Giambattista Vico)、克罗齐、杜威(John Dewey)等皆有论述。诗与史发端之初,混而难分,皆因“先民草昧,词章未有专门”(钱锺书,1984:38)。同时先民的历史意识处于粗粝状态。“不知存疑传信,显真别幻。号曰实录,事多虚构;想当然耳,莫须有也。述古而强以就今,传人而借以寓己。”(钱锺书,1984:38)因此诗与史在历时发展之端虽然同体未分,但是两者却有本质上的差异。“史必征实,诗可戳空。”(钱锺书,1984:38)上述种种例端旨在指出,对诗学类型的历时演变在认知上需求总体周观圆照。“此所以原始不如要终,穷物之几,不如观物之全。” (钱锺书,1984:37)
第82节征引古罗马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英国浪漫派的济慈(John Keats)和古希腊的柏拉图(Plato)等,看似简短散论,其实取旨立意都在论述诗传情达意中的故声旧意,即新词章表达弥久的情愫和人性共通的感受。惟钱锺书对这一点的阐发不及艾略特的诗论。新词旧调的论说仍是在论述诗的历时相通。而作为《谈艺录》压轴宏论的91节则更进一步拓宽了历时诗学的内涵,即历时诗学不仅是异中见同,而且也须同中掘异。因此这一节的主旨是:“知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钱锺书,1984:304)就中国诗学而言,同一个诗人笔下的诗与文殊异,如初唐陈子昂、宋代穆修;同一时代同一地方孕育出不同派别,如南宋的江西诗派与理学中的象山学派皆出于江西。就西方历时诗学而言,同样受这一诗学规律左右。英国18世纪的作家亚伯拉罕·考利(Abraham Cowley)的散文影响后继者约瑟夫·艾迪森,而诗歌却取法17世纪的玄学派诗风;德国的莱辛既尊崇莎士比亚,又推崇亚里士多德诗学;19世纪英国文学上的浪漫主义与哲学中的经验主义相左并立于世。如此论述,钱锺书实际上已经不单单是在论述诗学问题,而是放大到文化、文明的全局。如果仅局限于诗学论诗学,必导致偏颇偏激;如果仅局限于语言文明的藩篱,局限于地域空间,必导致偏执无知、故步自封。如此则能全解钱氏此论:“学者每东面而望,不睹西墙,南向而视,不见北方,反三举一,执偏概全。”(钱锺书,1984:304)
3 本体诗学论
从诗歌和诗学本体意义上洞察梳理中西诗学,阐发两者共同的诗学思想和诗学规律。严格讲,钱锺书对中西诗学本体理论的提炼淬化分别包含了诗学本体精神的提炼与诗艺形式本体的修辞剖析这两个层面。此处着重阐述钱锺书对纯粹的诗学本体精神关照的四大论点:神韵论、境界论、圆通论、理趣论。
3.1神韵论
《谈艺录·六》的核心是中西诗学中的神韵论。中国诗学中神韵诗学观可探源至严羽。从严羽的《沧浪诗辨》、陆游的《与儿辈论文章偶成》、明末王士祯、陆时雍的《古诗镜》、《唐诗镜》的《绪论》、清代翁方纲的《复初斋文集》卷三中的《神韵论》、明代胡元瑞的《诗薮》内编卷五、清代姚薑坞的《援鹑堂笔记》卷44到清代姚鼎的《古文词类纂》,钱锺书勾勒了神韵观的谱系脉络。严羽提出诗学的五法、九品、二概和一极。所谓“一极”就是诗的极致,“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钱锺书,1984:40)。钱锺书的解释更透彻,“可见神韵非诗品中一品,而为各品之恰到好处,至善尽美”(钱锺书,1984:40-41)。钱锺书最终为神韵的诗学阐释是:
古之谈艺者,其所标举者皆是也;以为舍所标举外,诗无他事,遂取一端而概全体,则是者为非矣。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钱锺书,1984:42)
钱锺书借以为此说注解的诗学论点,一是刘勰《文心雕龙》中融形、声、情于一体的情采,二是西方意象派诗坛领袖庞德(Ezra Pound)包容诗形(Phanopoeia)、诗乐(Melopoeia)、诗意(Logopoeia)的天然佳品。因此钱锺书的神韵专指形、音、义三者皆达到完美契合的诗学效果或状态。
那么在概念认知和思辨层面“神韵”何指呢?英国19世纪末的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在《鉴赏》(Appreciation)中论风格时区分了mind与soul。法国的亨利·白瑞蒙(Henri Bremond)指出了Animus/spirit与Anima/soul之间的对应及区别。钱锺书辨析到:soul/anima对应于中国诗学中的“神”,spirit/animus则对应于中国诗学中的“意”——言外之意。更进一步,钱锺书通过征引普罗提诺(Plotinus)、古罗马诗人卢克莱修(Lucretius)等西方学者论点,分辨出soul与mind的区别。所谓mind就是宋代心学中的“心”。由此形成两个序列:神、soul、Anima;意、心、mind、spirit。后来西方哲人如东罗马的波伊提乌(A. M. S. Boethius)、柏格森(Henri Bergson)等所标举的intelligence、intuition都近神意。宋代心学的“心”仅仅是“神”的意思之一。通过辨析《文子·道德篇》《法藏碎金录》等,钱锺书觉悟到“神”的三层境界。一为身体感官获得的觉触;二为用“心”思辨获得的觉悟;三为用“神”悟彻的觉照,超越思虑见闻,证妙境,合圣谛。诗学中的“神韵”就是透彻、无阻无碍、流转自如的觉照。它在艺境上与圆通、理趣、神妙都指向诗学的最高境界。
3.2境界论
如果说神韵论剖析的是诗学形、音、义三者交融的完美状态,那么境界论则重在分辨诗学中内在的情与外在客体世界中的物或者说主观的我与客观的物之间的物我关联美学。物我关联的第一种境界是以物拟人。“象物宜以拟衷曲,虽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映发也。”(钱锺书,1984:53)第二种境界是物我性、情相通相契。“要须流连光景,即物见我,如我寓物,体异性通。物我之相未泯,而物我之情已契。相未泯,故物仍在我身外,可对而赏观;情已契,故物如同我衷怀,可与之融会。”(钱锺书,1984:53)
3.3圆通论
《谈艺录·三一》专论圆通。一反惯常地从诗或诗学问题入手引出论题论点,这一部分以参照梳理中西哲学中“圆”的观念切入问题。西方从古希腊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普罗提诺、贺拉斯、中世纪的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8世纪法国的帕斯卡尔(Plaise Pascal)至19世纪初德国的黑格尔(G. W. F. Hegel),都持续地认为,从形体、宇宙真宰、尽美人格、精神道体、心灵流动到哲学思辨最周备完美莫过于圆。西方此论与中国思想中的论述契合无间。从《易经》《论语》、唐代张志和的《空洞歌》《太极图》、明代刘念台的《喻道诗》到《淮南子》都一脉相承,秉持这样一种“圆”的观念。以圆喻德的周备圆转或鉴包六合。以透照性灵自然的明珠喻诗艺的通灵通达状态。
西方诗学中从英国诗人亨利·沃恩(Henry Vaughan)、小说家蒂克(Tieck)、批评家弗农·李(Vernon Lee)、诗人歌德(J. W. Goethe)、缪塞(Alfred de Musset)、丁尼生(Alfred Tennyson)至亚历山大·史密斯(Alexander Smith)都从不同角度揭示诗学中的圆通论。如亨利·沃恩的诗《六合》将道体无垠的天人合一状态喻为光明朗照的巨圆。弗农·李将艺术的至善、至美、至真状态形容为“无起无讫,如蛇自嘬其尾”,好文章的结构布局环环紧扣流转圆通。诗人丁尼生盛赞苏格兰诗人彭斯(Robert Burns)的诗“体完如樱桃,光灿如露珠”。彭斯的诗达到了体圆,故神韵勃然。与西方诗学并行相契,中国诗学中从谢朓、元稹、司空图、梅尧臣、苏辙、张建、何子贞、曾国藩、李廷机到袁枚也都论述诗学中的圆通境界。“作诗不论长篇短韵,须要词理具足,不欠不余。如荷上湿水,散为露珠。”(钱锺书,1984:113)这是在讲用字造句中的义韵表达。“所谓圆者,非专讲格调也。一在理,一在气。”(钱锺书,1984:113)这是在讲文以载道和意义表达的流畅顺达。“有水月镜花,浑融周匝,不露色相者,此规处也。”(钱锺书,1984:113)这是在讲诗学的不执于我、不碍于物的奇妙境界。因此诗学上的圆通囊括了形式、义理、性灵通合几层内涵。
3.4理趣论
《谈艺录·六九》论理趣,在方法上又别具一格。钱锺书分别从中西有关理趣的内在梳理、理趣与其他表现形式的外在比较、对理趣全新的阐发这三个方面来破论立论。中国古典诗学中袁枚指出诗中理语,清代沈德潜的《息影斋诗钞》序、《说诗晬语》《国朝诗别裁》,方回的《瀛奎律髓》对理趣进行了较详细的界定。更进一步理趣说可追溯到严羽的《沧浪诗辨》中“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之论。但钱锺书将沈德潜的论述参照点定到胡元瑞的《诗薮内编》。那么袁枚、沈德潜、胡元瑞的说法分别如何呢?袁枚的理语之论包括人伦规劝、见道悟境两层。沈德潜在《息影斋诗钞》中明确提出“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在《说诗晬语》中借评价杜甫的诗句“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等提出理趣观,在《国朝诗别裁》中有“诗不能离理,然贵有理趣”之语。胡元瑞在《诗薮内编》中说:“禅家戒事理二障,作诗亦然。”如此梳理之后,钱锺书认为古典诗学中只提出了理趣问题却缺乏精微阐发。在西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皆对理有阐发。柏拉图的理念和模仿论将理置于诗之上。亚里士多德则认为诗能见理证道。黑格尔认为理与事交互彰显,“黑格尔以为事托理成,理因事著,虚实相生,共殊交发,道理融贯迹象,色相流露义理”(钱锺书,1984:230)。按照黑格尔的理论,诗中理趣天然凑泊。
钱锺书对理趣的理解是:“理趣作用,亦不出举一反三。然所举者事物,所反者道理,寓意视言情写景不同。言情写景,欲说不尽者,如可言外隐涵;理趣则说易尽者,不使篇中显见。……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谓理趣者,此也。” (钱锺书,1984:227-228)而诗中的理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这实际讲的是诗性语言的意义和意味之分别。贵在含蓄圆显的理趣自然就不同于中国古诗中的比兴手法或西方诗学中的讽喻手法。与这两种诗通史、玄的手法相比,理趣才是极致。他认为例概和凝合是理趣表现的两种手法。“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因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Comparison),乃举例以概(Illustration)也。或则目击道存,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即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Embodiment)。”(钱锺书,1984:232)
本体诗学阐发的神韵、境界、圆通、理趣诸说其实都是在引向诗艺的神妙。在《谈艺录》第88节中他引用严羽的《沧浪诗话》来说明何谓诗的神妙:“不涉理路,不落言诠。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妙处莹澈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这种神妙几乎近神秘莫测之境界——一种中西诗学诗艺俱向往的纯净明澈、超越语言和意义表述边界的境地。法国的瓦雷里(Valery)称之为文外的“独绝之旨”“难传之妙”“空际之韵,甘回之味” (钱锺书,1984:268)。而诗艺本体通达道原的功夫是需要靠积淀积累的。这就是他在第28节解析妙悟时所阐述的“解悟”(“因悟而修”)与“证悟”(“因修而悟”)之别(钱锺书,1984:99),也是他在第61节通览性灵时所讲:“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肺肝所流出,人已古新之界,盖超越而忘之。故不仅发肤心性为‘我’,即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应我需、牵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有。”(钱锺书,1984:206)
4 钱锺书批评意识的精神面向
钱锺书的《谈艺录》秉持这样一种诗学的认识论公理,即:异类互补、异中证同。这种超越地域、语言、艺术、思想、文明等分歧差异的趋同不仅揭示了诗学的通玄化境,而且彰显了超越现实的人类精神共通境界。这个神异透彻的精神世界通过诗学而显露出永恒此在的存在样态。与这个借诗学的媒介而通达的永恒光明的精神圣境相比,仇恨、战争、分歧、个体的磨难、虚假的主义、日常生活的媚俗等等都显得肤浅、脆弱、短暂,只不过是历史中短暂的叹息或虚妄的幻景。这种容性灵、智慧和通灵于一体的精神状态不仅是诗艺的化境,也是崭新的文明精神航程的终极家园。恰如弗吉尼亚·伍尔芙在现代主义小说的杰作《到灯塔去》中借拉姆齐太太、灯塔和认识拉姆齐太太的过程、到灯塔去的航程所象征的那样,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人类精神自我的发现之旅,都将人类文明推上超越于现代物质文明和政治乱象的精神化航程。这反过来印证了英国20世纪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重要文明史观:人类文明最高的成就是彰显人和人性的文艺成就,因为只有这种渗透了人类心灵感悟和智慧的文明高峰才是永远屹立不倒的。
因此钱锺书沿着诗学的太阳普照的精神圣途,用性灵甘露滋养诗艺的神奇,将现代文明救赎意识熔炼锻造,提升到空灵清澈、晶莹无暇、哺化万类、渡厄苍生的崇高境界。学者们多关注钱锺书的“史蕴诗心”之说,以之考究陈寅恪的“以诗证史”法,却忽略了他在打通中西古今诗学之论中隐匿的思诗化合之论。他分别从人类群体的文明历时演化进程和人类个体攀缘飞升的心路和生命体悟中剖露出永恒此在、崇高卓绝、通透朗朗的精神实在。唯有人类群体和个体能达到这个精神此岸圣境才能化解文明的劫难、文明之间的藩篱、人类彼此之间的仇恨,才能超度生活负累中的生命个体。通览厚厚一本《谈艺录》,他在论述思与诗的化合之时多以佛家、道家思想来交互阐发,这个精神此岸圣境蕴含的圣谛是悟彻心,是慈悲心,是救赎心。
20世纪80、90年代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对这种以批评为职业(而不是狭义的职业)的人文学者的入世情怀和精神有非常通透的论述。这种入世情怀和精神,他称之为“批评意识”。从著作《开端》到最后的思想言说《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乃至他离世后出版的《论晚期风格》,萨义德都始终强调当代批评家应有的批评意识。他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年)中深刻剖析了现代和当代批评意识的结构性张力。以现代主义为文化表征,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及其关注的对象世界分化出两极。一极是基于“连理”(filiation)原则的纵向自然、生物式繁衍、传承关系。另一极是基于“连接”(affiliation)原则的横向文化共同体联合关系。西方现代文明劫难衍生出一系列批评主体无法回避的张力、距离、断裂甚至危机。
这一方面表征为批评个体的意识对外在世界的疏离感的体验和回应。“一方面个体记录下并清楚明白地映照出个体意识的集体意识、语境或情景。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种明白——一种世俗的自我情景化,对主导文化的敏锐反响——个体意识绝不是文化自然而然的顺产儿,而是文化中的历史和社会角色。”(Said,1993:15)另一方面表征为现代诗学两种模式之间的张力。一种模式以欧洲文学经典和人文传统为圭臬,“那种几乎是无意识地抱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即人文学科的欧洲中心模式对人文学者而言代表了一种自然、正当的主题……任何非人本主义、非文学、非欧洲的对象都被排斥在这个结构之外”(Said,1993:22)。这种模式天然割舍了批评意识。另一种模式对自然“连理”与文化“连接”之间的差异、距离极具张力感的认知,进而让社会、政治、文化的异质矛盾世界进入批评审视的范围。换言之,这两种模式实际上是两种诗学的文明的认知模式,即:有机诗学和有机文明认知模式与异质多元诗学和异质多元文明认知模式。
对中西跨文明诗学和文明交互影响的宏论见之于钱锺书的《谈艺录》序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从世界文明大棋局中提炼文明对话的理和道,是批评意识探索追寻的最高目标。现代性的二律背反困厄——文明崇高孤绝的精神化运动与物质技术和科学进步的反精神化运动的悖离,西方现代文明与反西方文明的悖离——决定了现当代批评家的批评意识中沉重的张力感、危机感甚至苦难和救赎感。批评家的批评意识和个体生命体悟表征的是现代文明多元汇聚景象中精神化运动的轨迹。而这种精神化实践本身必然折射出历史纵深纬度中精神化运动与文化物质实践,不同文明之间横向纬度中知识、观念、审美品位、文艺风格等的迁徙流动、传播变异与跨文化的文化物质实践之间的辩证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