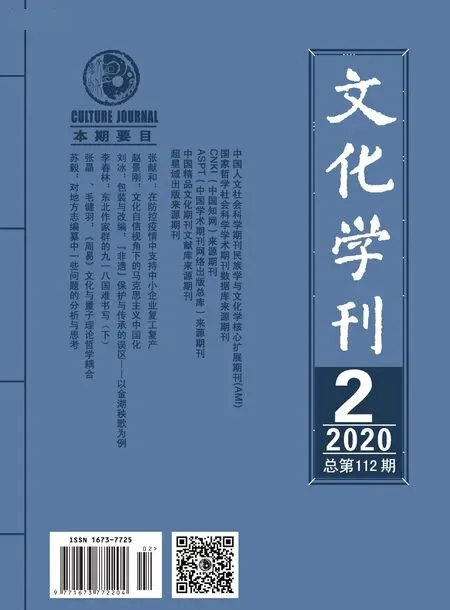包装与改编:“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误区
——以金湖秧歌为例
刘 冰
近年来,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将其视为展示文化成果、吸引外地游客、提升地域形象的重要手段。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截至2018年底,该市已拥有国家级“非遗”项目6个,省级“非遗”项目33个,市级“非遗”项目202个。此外,建成了3个省级传承示范基地,2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国家、省、市、县(区)四级“非遗”保护体系得到建立和完善,许多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发掘整理出来,并得到有效地保护和传承。
但是,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当前我国“非遗”保护与传承仍然面临诸多困境和误区。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使许多作为农业社会时代产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猛烈冲击,正面临着消亡的困境;封闭的乡村被打破,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以电视、电影、电脑为主的大众文化传媒的介入改变了农民的观念和娱乐方式,乡土文化被视为落后的象征而逐渐抛弃,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主体变成大众文化的消费者;加之绝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靠口传心授方式传递、延续和发展,年轻人的排斥与不解造成当前“非遗”传承处于青黄不接的境地,如果没找到合适的传承人,一门技艺将面临消亡的命运。
一、“非遗”保护与传承中的误区
如果说当前我国“非遗”保护面临诸多客观问题的话,那么对“非遗”保护与传承的内涵认识不清,在挖掘、整理、保护和传承等环节中不自觉加入了“包装”和改编,则是“非遗”保护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许多地方在开展“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的同时,过分注重对遗产的“包装”和改编,并将其视为“非遗”保护的成果推向社会。这种重改编轻传承、舍本逐末的行为在许多地方愈演愈烈,似乎只有这样才意味着发展和传承。殊不知,在传承缺位的情况下过分强调创新,只会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亡。如果不能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非遗”工作就有可能走向歧途。
金湖秧歌是苏北里下河地区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一种特有的民间艺术,有着浓郁的地域色彩,受到了国家、省市文化部门的高度重视并多次晋京展演,广受赞誉。2008年,金湖秧歌《格冬代》参加“长三角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民间音乐”展演;2010年,金湖秧歌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金湖秧歌从一项地方性民间艺术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但是,在金湖秧歌的热闹景象中,有一个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金湖秧歌在走出田野、走上舞台的同时,文化工作者为了使其更符合广大观众的欣赏口味,在原汁原味的金湖秧歌中加入了许多灯光、音响、舞蹈、美声唱法等“大众文化”的元素。这种“包装”和改编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了城市观众的审美预期,既有乡土的风情又不失现代的华丽,但这种“包装”和改编实际上使金湖秧歌失去了本来的特质,成为既非“原生态”民歌又非“学院派”音乐的“次生态”歌舞节目。进入专家视野的和台下观众所看到的金湖秧歌已不再是完整无缺、地地道道的金湖秧歌,而是一种歪曲的“文化镜像”。
原生态是生物科学领域的一个术语,借用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中,特指未经雕琢、原汁原味的表演形态。金湖秧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音乐,与生产劳动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的历史可追溯到明初洪武年间。洪武年间,大量江南移民被官方强制迁移到苏北里下河地区,带来的江南文化与当地歌谣相结合,逐渐形成了金湖秧歌的雏形。金湖秧歌中最具代表性的“锣鼓秧歌”,据说是清政府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时滞留本地的湘军带来的湖南习俗。金湖地区三面环湖的闭塞环境使金湖秧歌与外来的山歌、戏曲、宝卷、时调、唱本等其他艺术形式互鉴互学,历数百年交融与沉积,并逐步定型[1]。
二、包装与改编在金湖秧歌中的具体表现
目前,在群众文艺调演和重大演出场合,金湖秧歌的出场已经很难看出“原生态”的特点。经过专业文化工作者重新编排后的金湖秧歌改良了唱腔、增加了配乐和舞蹈,节目的观赏性和可听性大大增强,但对于不熟悉金湖秧歌的人来说,这种改编难免会把金湖秧歌与歌伴舞等表演形式混淆起来,产生一种金湖秧歌也是载歌载舞的错觉,它的出现已经破坏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具体表现有三点。
(一)不同艺术手段的横植
金湖秧歌不同于东北的“大秧歌”或陕西的“秧歌舞”,它没有舞蹈表演,而是集歌词、曲调和锣鼓伴奏为一体来表达情感的一种演唱形式,但组织者为了追求美轮美奂的舞台效果,对舞台灯光、服装、音响等进行大幅度改良,并增加了舞蹈的成分。演出时,最先出场的是舞蹈,歌手站在舞蹈演员中间,而不是立于台前。于是,演唱在整台演出中无形中处于次要位置,原本以唱腔为主的民间音乐顿时变成了民间舞蹈。2010年6月,为了适应上海世博会的演出需要,创作者在金湖秧歌中经典旋律的基础上重新进行作词、作曲,创作了一首新曲目《唱起秧歌喜洋洋》。为了追求观众认同,创作者依然采用了歌伴舞的形式,并且重新录音时采用交响乐伴奏,增加了号声等气势较强的配乐。殊不知,金湖秧歌之美美在它的唱腔,为了追求视听效果而加上交响乐,无异于舍本逐末。同样的例子还有同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南闸民歌。南闸民歌中的小调类旋律优美、水乡风味浓郁,但在某次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中,南闸民歌的组织者居然采用大合唱形式,数十人气势磅礴地列队整齐站在台上。更为夸张的是,演出过程中居然还采用了芭蕾这种西方舞蹈形式来对南闸民歌进行演绎。如果说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方式的话,那无疑是对“传承”的内涵进行了错误解读。
(二)专业音乐工作者的改良
民歌的原生态主要体现在唱腔的独特性。原生态民歌与特定生活场景、生产方式、审美理念等背景因素密不可分,某些独有的音乐表现语汇与当地的人口构成状况、语言表达方式、情感抒发形式和文化教育水平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金湖秧歌既有南方民歌的舒缓流畅,又有北方民歌的高亢豪放。有学者发现,金湖秧歌的单乐段中甚至存在复杂的调式运用手法,在我国的民歌演唱形式中可谓独树一帜。但不难发现,走向舞台的金湖秧歌歌手都经过专业发声训练。这类学院派歌手的介入无形中将专业唱法的发声技巧带入金湖秧歌,于是原生态金湖秧歌中某些“不规范”的地方都被视为“粗糙”而被专业歌手重新磨平。加之参演节目遴选时,评选专家也有意无意地用单一的学院派的科学唱法评价不同的民歌唱法,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打磨意见,于是,舞台上的金湖秧歌被逐渐磨去“粗砺”的乡土气息,逐渐走向“精致典雅”的大众审美。金湖秧歌在越来越符合专家和观众舞台审美,也意味着原生态的金湖秧歌离我们越来越远[2]。
(三)演唱主体的更换
秧歌,顾名思义,它的演唱主体是在田间插秧劳作的农民。但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业机械的普遍使用、插秧时间的缩短使锣鼓师傅失去了市场,金湖秧歌的演唱在田间劳动中已濒临消亡。随着许多老歌手和老师傅的相继辞世,现在农村能唱秧歌的年轻人日益稀少。而为了能让金湖秧歌顺利实现舞台再现,组织者不得不从文化馆、剧团等专业文化团体借调受过专门发声训练的演员来参与演出。2010年6月,金湖秧歌参加了在世博园内举办的“江苏文化周”活动。为了更好地将金湖秧歌的魅力展示给世人,组织者抽调了当地专业剧团、艺术院校、文化馆三个文化团体的精干力量进行集中排演。于是,经过专家审核、专业音乐工作者填词作曲、专业舞蹈演员排演的“次生态”金湖秧歌走进世博舞台与观众见面。这次演出虽然达到了预期演出效果,但对于那些从未有过务农体验的演员和歌手来说,他们的心态和为缓解农作辛苦、提高劳动效率、舒缓紧张心情而唱上两首秧歌的农民是否一致?任何文化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情境中发生的,对专业演员和歌手来说,舞台上的秧歌与流行歌舞并无二致。脱离了田间插秧的情境,金湖秧歌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将荡然无存。
三、结语
金湖秧歌走上舞台已经脱离了原来的文化情境,也意味着它不再是“原生态”。但是要扩大金湖秧歌的影响,唤起人们学习、保护和传承金湖秧歌的热情,又不得不通过舞台展示来进行。金湖秧歌走上舞台与原生态保护的悖论在全国已是一个普遍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有一条著名的“杨丽萍悖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歌舞不保护即意味着消亡,但将其搬上舞台后,质朴纯真的原生状态就被改变,仍然意味着死亡。因此,如何避免“杨丽萍悖论”在金湖秧歌这项优秀的民间艺术身上发生,将是当地文化部门深入思考和探索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