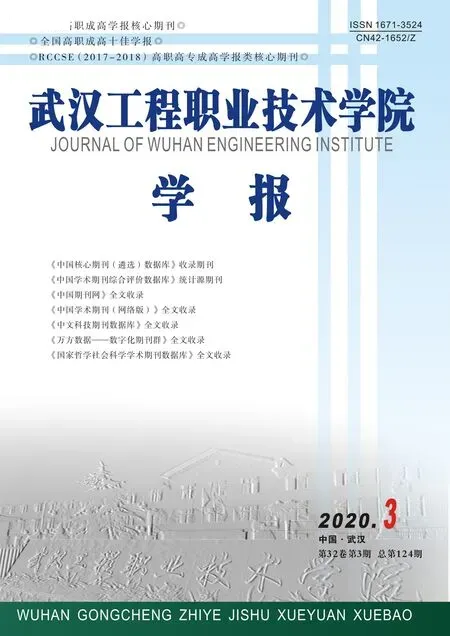基于消费伦理视角的小说《白鲸》分析
罗 玲
(内江师范学院 四川 内江:641100)
《白鲸》,被称为捕鲸行业的百科全书,是美国19世纪著名作家赫尔曼·麦尔维尔的经典巨著。小说以主人公以实玛利的视角讲述捕鲸船长亚哈因被白鲸莫比·迪克咬掉一条腿,继而展开疯狂复仇之旅。在亚哈专断的带领下,在深海中与白鲸展开激烈战斗,最终全船人员与白鲸同归于尽,只有以实玛利一人得救。小说既生动地描述了捕鲸者们惊心动魄的航海生活和丰富的鲸类百科知识,也蕴含了许多深刻的人生哲理。在评论界,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该小说进行了研究探索。首先,从生态角度分析小说。有学者认为小说体现出“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性之间的二元对立,亚哈与白鲸的博弈代表着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对抗”[1];还有学者分析主人公亚哈对待白鲸的态度,认为“亚哈与白鲸的对抗象征着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2],以此谴责与亚哈一样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其次,从善恶观和道德伦理意识角度分析作品。有学者认为人类对白鲸的伤害是人类从善美滑向丑恶的表现,小说体现出作者对人类道德沦丧的担忧[3];还有学者认为亚哈和白鲸具有不同的象征含义,都有善和恶的象征,以此探讨人类社会中善恶观。再者,从其它不同的角度分析小说。裴晓旭和向欣[4]则根据17世纪著名思想家约翰·洛克的财产观理论,深入分析了约翰·洛克财产权理论与《白鲸》中捕鲸业两条基本法条的对应关系,以此揭示作者麦尔维尔对于这两条基本法条的批判;和耀荣认为“小说中人物多元男性气质的刻画以及悲剧性的结尾体现了麦尔维尔双重矛盾心理:一方面,为美利坚民族的发展强大而感到自豪和骄傲;另一方面,反思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和殖民扩张的负面影响,表达了对资本主义时期人类无所敬畏的超理性和无所皈依的信仰缺失的焦虑和迷茫”[5]。
综上所述,现有研究大多从单一静态角度分析文本,本文以生态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以小说《白鲸》中捕杀鲸鱼、消费鲸鱼的描述为研究对象,批判分析了19世纪资本主义体制下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旨在警示现代人的消费观,提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符合的生态消费观。
1 异化的劳动
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正处于上升阶段,在生产劳动中,人们疯狂地向大自然掠夺一切资源,早已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需要,而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万物征服的欲望、对财富占有的欲望。正如小说所述,“捕鲸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它还兼有探险与开发的功能”[6]。捕鲸业被称为最伟大最光荣的事业,一方面,捕鲸业为资本主义发展带来巨大财富,另一方面,捕鲸水手可以开拓大自然,探索地球上最荒僻边远的地方,敲开许多闭关自守国家的大门,成为资本输出的先锋者。这种对万物和世界征服式的殖民行为使生产劳动异化。
首先,船长亚哈怀着报复心理捕杀白鲸,实际上就是劳动异化的体现。在亚哈看来,咬掉他大腿的白鲸是万恶之源,挑战了他的权威,因此,他势必与白鲸一决高下。显然,船长对白鲸的报复,不再是以理性和道德为原则,而是被本能欲望所控制,是为了重新树立自己的霸权,满足自己征服世界万物的欲望。为达到此目的,他违背船主的利益,威胁逼迫捕鲸水手服从于他,不顾全体船员的生命安全,孤注一掷追杀白鲸。可见,船长亚哈的劳动行为早已变质,既是扩张与征服的表现,也是对维持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任意糟踏。其次,捕鲸水手们对鲸鱼的捕杀行为也已变质异化。捕鲸者们被高额的利润蒙蔽了双眼,残忍地杀害无辜的生灵。鲸鱼对他们来说,不是应该被敬畏的生命,而是金光闪闪的金币。“裴廓德号”进入深海时,船员们一开始产生了畏惧心理,但当亚哈宣布将用金币奖励最先发现莫比·迪克的人时,全体船员又斗志昂扬,发誓找到白鲸并将其捕杀。可见,捕鲸水手们对鲸鱼的追逐捕杀是为了满足对财富的欲望。
“前资本主义时代,人们进行劳动、耕种土地、蓄养家畜是为了满足家庭的需要,只要够用就行。但是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市场经济)之后,人们的劳动受到经济理性的支配,只有遵循越多越好原则,才能实现利润的最大化”[7]16。人成了欲望的奴隶和生产的机器,生产领域的异化渗透到人类的日常生活。船长亚哈和捕鲸水手捕杀、猎杀、屠杀鲸鱼的目的和行为早已超出了人类基本生活的需求范畴,这是满足人类无限欲望的生产劳动行为。这种病态的欲望、扭曲的需要、异化的生产使人类屡次成功征服自然。无节制的生产活动造成资本主义社会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自身的霸权统治目的,宣扬消费主义价值观,以此弥补人们在生产劳动中遭受的挫折。因此,消费也必将走向异化。
2 异化的消费
《白鲸》详述了海上航行和纷繁的捕鲸生活,同时,作者对猎鲸、捕鲸、屠鲸过程也做了细致描述。例如,关于屠鲸,作者在“分割胜利品”章节写到:“‘裴廓德号’的每一个水手都成了屠夫,把鲸身上有用的东西,也就是鲸油割下来。……全船的人密切配合,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过程,就像剥橘子皮一样,从大鲸身上一大块又一大块地往下割着鲸脂。……被割下的鲸脂源源不断地送进炼油房”[6]323。关于消费鲸鱼,在“嗜鲸以生的人们”章节中,作者写到,早在几百年以前,鲸鱼被认为浑身是宝,精炼提取的鲸油比上好的葡萄酒还要珍贵,露脊鲸的舌头、小抹香鲸的脑髓被烹饪成宫廷菜,为贵族享用。食用鲸肉成为一种时尚,象征着荣耀和地位。在“鲸类学”章节中,作者提到,抹香鲸的鲸脑极其稀少和名贵,“只用来制做油膏和药剂,也只有在药房里见得到”[6]153;“独角鲸的角是一种上等解毒剂,昂贵之极,……它的角还应该是一种珍贵的工艺品,而且应该极具收藏价值”[6]157;“从乌拉鲸的嘴提炼出来的清纯的汁液尤为名贵,珠宝首饰和钟表制作商所必备”[6]199。从消费伦理视角解读这些描述,读者会发现远洋捕鲸的真实目的是金钱、利润和占有的欲望,这也是捕鲸的原初动机。正如作者所说,“人类之所以对动物如此的野蛮,来自于他们对这些动物的欲望”[6]319。有欲望就有需求,有需求就有消费,有消费就有生产(捕杀)。这种残暴捕鲸的背后映射出19世纪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消费观,这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而带来的消费主义,这种消费观主张“消费越多、浪费越多、地位越高”[8]76,其本质是一种反伦理、反生态的奢侈低俗消费方式。
倡导消费至上的消费主义,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人们以消费来宣泄不满,以此补偿在其他生活领域特别劳动领域内遭受的压力和挫折。长此以往,这种消费主义价值观激发起人们内心深处的欲望——贪婪、炫耀、虚伪等,催生出奢侈消费、过度消费等异化消费行为,以满足自身对物无限占有的欲望以及证明自己的身份。这种消费方式在统治阶层、贵族阶层,甚至普通大众阶层中日益盛行起来。显然,无节制的挥霍浪费和放纵无度的非生产性消费使最初的需求和消费变质。可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消费活动已然异化,消费者纷纷崇拜“商品拜物教”,消费需求已由真实变为虚假,这只会让人们过着物质优渥但精神空虚的生活。更严重的是,人类为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所谓的地位面子等,过度消耗自然资源,消费之后留下的废气、废物、废水破坏自然界的自洽性和生态平衡。异化消费必然使整个人类社会陷入物质困境、精神困境和生态困境,给大自然带来灾难性后果。
因此,消费的异化促使人类开始思考“消费是究竟什么”、“消费了是为什么”以及“要如何去消费”等问题。从生态学角度看,消费并非只是用光、摧毁、耗尽;从经济学角度看,人们不能把自然界当作推动人类生活、经济社会发展的原料库。伦敦皇家社会研究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科学学会从保护生态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消费:“消费是人类对自然物质和能量的改变,消费是实现使物质和能量尽可能达到可利用的限度,并使对生态系统产生的负面效应最小,从而不威胁人类的健康、福利和其他人类相关的方面”[7]13。
在现代社会中,消费的无限性与生态的有限性的矛盾关系愈加突出,使现代人再也无法忽视,人类需要从伦理学视域找到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方法,并寻求新的消费方式。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开始研究消费与生态之间的关系,可持续消费理念逐渐盛行起来。在近年的生态文明建设中,生态革命拉开序幕,消费主义时代即将落幕,异化消费、虚假消费即将结束,人们开始树立新的消费伦理观——从基于欲望的奢侈消费、过度消费转向生态消费、绿色消费,做到如生态学者所说:“手段俭朴,目的丰富”[8]68。总言之,消费更少、生活更好的生活方式终将成为主流。
3 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
劳动异化、消费异化最终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变为征服与被征服,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小说中,船长亚哈以及捕鲸水手与鲸鱼的关系代表了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下人与自然的关系。首先,船长亚哈与白鲸的关系。亚哈出海的唯一目的就是杀死白鲸,这表示亚哈与代表自然的白鲸完全是敌对的,亚哈充满仇恨,立誓要杀死伤害过自己的白鲸。根据生态伦理学,亚哈是“自我”的体现,是人类“自我实现”的最初阶段,象征着是人类内心最原始的欲望和野心。在自然面前,亚哈是主宰者、征服者,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以自我欲望为借口,企图操控自然,绝不允许来自被征服者的反抗和伤害,在疯狂的复仇之旅中,亚哈最终变成了在大自然面前不负任何责任、毫无敬畏和忏悔之心的冷酷残忍形象。这样的生态价值观助长了人类历史发展中对于大自然无所顾忌的主宰行为。其次,捕鲸水手与鲸鱼的关系。他们以获取钱财为目的跟随亚哈出海捕鲸,这类人还映射出19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下的另一类人,即享用珍稀物品的消费群体。从生态伦理学角度解读,他们都代表着“自我实现”中的“社会自我”阶段,对于自然,他们是掠夺者和消费者,主张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主体,自然是客体,肆无忌惮地夺取自然资源,从中获取暴利和享乐。这样的生态价值观致使人类肆意地掠取自然资源以满足人类的异化消费需求。
“马克思主义在对人与自然本质关系的历史考量中,对资本主义社会方式进行了批判,认为资本主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这种人类异化的生存状态,将导致人与自然的多重矛盾”[9]18。可见,对物的无限占有欲望致使人们肆意践踏生态环境,而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当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自然无法承受之时,生态平衡将被打破,进而引发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已然代替了现代社会中的经济危机,成为阻碍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从生态失衡、环境恶化、资源浪费、能源枯竭等严酷现实揭示出一个真相:如果人类不减少对物质的欲望,人类社会就不会得到更良好、更健康的发展,自然生态也无法得以改善。要解决生态危机,首先要解决好生态与消费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纵观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人类社会和时代的变化发展而改变着。“从原始文明的崇拜、敬畏自然,到农业文明的模仿、学习自然,再到工业文明的改造、征服自然,人们认识到,当人类合理利用、友好保护自然时,自然的回报常常是慷慨的”[9]10。因此,在现代生态文明社会中,人类应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新型伦理关系——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互相依存、共生共赢。
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指出要“加快建立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和政策导向,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9]36,“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反对奢侈浪费和不合理消费,开展创建节约型机关、绿色家庭、绿色学校、绿色社区和绿色出行等行动”[7]2。所有这些都为树立经济、生态、伦理三者相统一的生态消费伦理观指明了方向。
4 结语
综上所述,人类因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而日趋物质化,消费观也发生变化。消费不再是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而是满足人们的各种欲望,这种基于欲望的需要导致了异化的劳动和异化的消费,进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造成严重的生态危机。本文从消费伦理视角分析《白鲸》,探究19世纪资本主义发展上升期的消费观,以此启示21世纪现代人的消费观:消费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也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文化现象,现代人要树立经济、生态、伦理三者相统一的生态消费伦理观,从消费伦理角度调整自身的消费行为,形成符合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型消费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