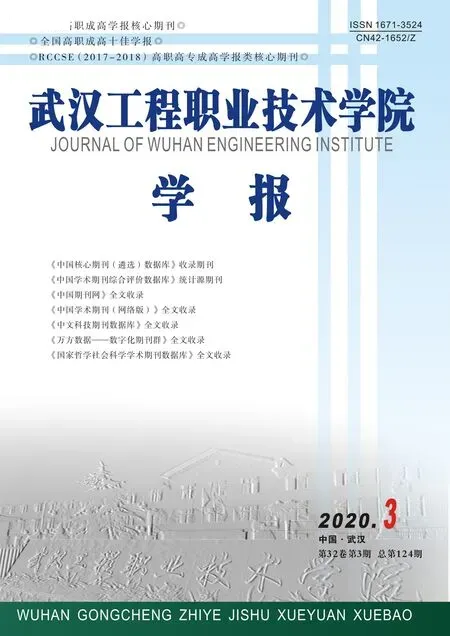“西学东渐”的主观愿望与发展走向
郭燕华 凃明星
(1.江汉大学 湖北 武汉:430056;2.国家开放大学(武汉) 湖北 武汉:430033)
汉学家费正清直言:近代中西关系的实质,“是扩张的、进行国际贸易和战争的西方同坚持农业经济和官僚政治的中国文明之间的文化对抗”[1]251。近代中西文化冲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其时间跨度大致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间。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得中国国家主权开始被破坏,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渐变。西方文化随着坚船利炮进入中国,与中国文化开始剧烈的碰撞和博弈,在随后80多年的时间里,渐次形成了“西学东渐”的高潮。西方输出的初衷,是有目的、有条件的;中国的引进是被迫的,不情愿的,其过程是极其艰难的。回望这段历程,双方主体的原始初衷与文化博弈的发展走向,悬殊甚远,出乎双方意料,成为世界近现代文化交流史中一大趣事。
1 中西文化对比出现强烈的反差
在欧美,伴随封建经济的解体、新航路的开辟、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西方文化与呈上升趋势的资本主义经济相适应,一些思想家和改革者,高举人文主义的大旗,抨击封建专制压制人民、残害人民、奴化人民、法律废弛、官场腐败等罪恶现象,他们的思想主张直接渗进了政治改革运动,成为资产阶级的“立国思想”,用来变革政治体制和社会生活。以伏尔泰、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用理性战胜了迷信,创立了以天赋人权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提出自己的主张,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许多欧美国家着手国内制度的改革,消除社会积弊,掀起一股强大的改革浪潮,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英国、西班牙、荷兰等国,建立了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联合专政的国家,着手经济制度改革。如:英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第二类是通过民族独立战争或国家统一扫清资本主义道路上的障碍,如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美国独立战争推翻了英国殖民统治,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铲除了殖民时期封建残余。法国推翻了封建专制的君主制度,推动了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德国通过王朝统一战争,结束了德意志长期的分裂状态,成为新兴的强国,改变了欧洲的国际格局;第三类是由封建主义制度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改革,如:俄国实行了自上而下的具有资本主义性质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度。从改革目的上看,这些国家都在调整上层建筑以适应社会经济的演进,调整生产关系以满足生产力的发展,并获得不同程度的成功。通过这场革命或改革,资产阶级掌管了国家政权,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
中国古代的文化与科技,长期居于世界遥遥领先的地位。明朝中后期,在江南一些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封建体制禁锢着民众的思想,束缚着科学和生产技术的进步。满清政府固守封建专制制度,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未能得到充分的发育,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缺乏必要的经济前提,未能出现欧洲近代史上的产业革命或科技革命。西方列强仰仗战船大炮,接连发动侵略战争,貌似强大的清王朝不堪一击,他们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一系列卖国求和的不平等条约,肆意割占中国领土,划分势力范围,勒索赔款,设立租界。进而得寸进尺,在政治上操纵满清政府,操纵中国外交,把中国当权者培植成他们的代理人和驯服中国民众的工具,在经济上实施商品倾销和资本输出,致使中国逐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
2 中国救亡图存的多样探索
19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文化呈大规模、多领域的态势渗透到中国。在早期,双方主体的主观愿望,各自盘算。西方列强除了军事进攻、经济掠夺外,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文化渗透活动,并着手在中国培植一批有影响的人物,“使他们成为中国未来的领袖和指挥者,给未来的中国施加最有力的影响。”还有一批人打着“文化传播”的旗号,在中国非法从事间谍侦察活动,刺探搜集大量军事情报,扰乱中国经济、法律秩序,甚至公开干涉中国内政。
面对西方军事侵略和文化参透的双重挑战,封建统治阶级存有盲目排斥、盲目引进两种极端。盲目排斥者视先进科技为“奇技淫巧”,盲目引进者则希望抓住挽救封建统治的稻草。一批有识之士,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认识到闭关锁国不能制夷,林则徐“开眼看世界”,寻找御敌之策;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郑观应反对“泥古不化”,认为甘守愚陋必“受制于人”,主张与西方开展“商战”,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制度;严复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疾呼“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并较为系统地将西方人文社会学和自然科学引入中国;梁启超主张提高全民素质;孙中山在海外创立革命团体,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他们探索国家出路,由技术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思想文化层面,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先后掀起五次大动作[2]181。
第一次是洋务运动。洋务派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法则,开办了新式学堂,开启了近代教育,客观上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维持封建体制的目标下发展一些近代工业,以及引进的宗旨和手段上存在严重的缺陷,更有甚者,幼稚地认为西方列强会帮助中国实现“自强”、“求富”。然而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真正富强起来,同时利用洋务活动的依赖性,加紧对华侵略控制。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失败,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第二次是戊戌维新运动,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主张改革君主专制制度,开启移风易俗的社会新风,由于康有为只主张变法,反对革命,加上守旧势力过于强大,维新派脱离群众,甚至幼稚地幻想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持,变法最终失败;第三次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洪秀全试图用西方思想与中国本土文化结合的方式来改革国家命运,但最终失败了。这表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四次是新文化运动。陈独秀、蔡元培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以“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为先导,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封建旧礼教、旧道德,开始文学革命,启发了国人的觉悟,起到了启蒙作用;第五次是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大批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在众多的社会思潮中拨开层层迷雾,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探索社会改革和民族解放的出路。
3 中国最终成为赢家
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背景下,清王朝封建专制文化衍生出明显的封闭性、自大性和保守性。当强势的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传入时,中国仍然固守着日趋衰落的封建专制文化,与西方文化形成强烈反差。西学渗入经历了中国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选择的过程,并从多方面促进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蜕变[3]353。
第一,西学促进了中国近代新学的产生,变更了封建文化的内核。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由此逐渐发展起来,初步奠定了近代学术分科发展的基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由汲取西学到融会中西,成为中国文化走向近代的起点。
第二,西学催生了中国近代具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技术的知识分子群体。洋务企业生产培养了一批应用技术人员,清政府和地方官员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后来还出现一批自费出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中国近代社会出现了具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群,他们成为近代社会思想最活跃的一个群体。
第三,西学改变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结构,动摇了中国封建文化的一统地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改革运动。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思想开始撞击封建专制的藩篱;越来越多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西方民主与科学的思想,相信近代自然科学,崇尚致用、重视科技的风气日臻浓厚。
第四,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是从西学中寻求思想武器,特别是孙中山,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构建了民主革命理论,促成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创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但这些革命斗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幼稚病,要么将斗争目标主要集中于反对封建势力,对帝国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缺少明确的反帝目标和坚决的反帝决心;要么对于帝国主义本质认识不清,缺少必要的反帝斗争的策略,出现盲目排外。这些革命的领导集团未能制定彻底的反帝反封的革命纲领,最终未能领导中国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但他们的探索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第五,五四运动将先进青年追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他们清晰地看到: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了农民阶级领导的革命不能救中国;百日维新和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不推翻旧制的改良运动不能救中国;辛亥革命的失败证明了资产阶级不能救中国,资产阶级共和国不是中国的出路。五四运动以后,各种社会思潮纷至沓来,错综复杂。他们先后展开“问题与主义论争”、“东西文化论争”等问题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处理好本土传统文化和西方舶来文化的关系,如何改造和汲取传统文化中优质的部分。通过激烈的论战,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西文化的的特质,选择哪一个思想主张能够救国救民的指向进一步明朗化,并且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顿悟”,还得益于两件影响世界格局的大事,即第一次世界战争后世界局势的变化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随着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等相继取得独立,亚洲爆发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十月革命提供了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胜利的“俄国样本”,殖民地的人民看到了希望。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和援助下,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并建立了以国民党合作为基础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着手领导工人农民运动。中共二大提出了民主革命要分两步走的战略,并制定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毅然决然地肩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任。
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主要在技术层面借鉴西方;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主要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希望从文化层面学习西方,并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在“改造中国与社会”的呼声中,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率先把马克思主义逐步中国化。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了自己的军队,开创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政权的新道路,团结劳苦大众,推翻了封建帝制,消除了军阀割据,打败了国民党政权,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帝国主义列强侵犯中国、欺凌奴役中国人民的苦难历史。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在国际上,取得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国际声望与影响力日臻提升。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巨大成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华民族从任人宰割到自强自立,从战乱动荡开始走向长治久安的起点,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走向强盛的起点。
综上所述,文化交互视域下,西方有条件的输出与中国谨慎的引进,还是归结为“文化交流”的范畴。早期“交流”,显然是不平等的。因为从主观愿望来看,西方是主动的,列强试图使西方文化成为殖民侵略、殖民统治的工具,而中国方面,以满清贵族为中心的封建统治阶级是被动的,他们只是希望引进一些形式的东西来适应旧的生产关系,并非借助西方先进的文化来变革中国社会;从文化交流的过程与影响来看,西方文化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随着渗透的广度与深度变化,越来越深入和复杂;从文化交流的发展走向来看,出现了不以双方初期意志为转移的变化,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经过权衡对比、实践探索,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完成了民族民主革命。中国由此迈步走上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康庄大道,可以说这是“西学东渐”最为瞩目、最为欣慰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