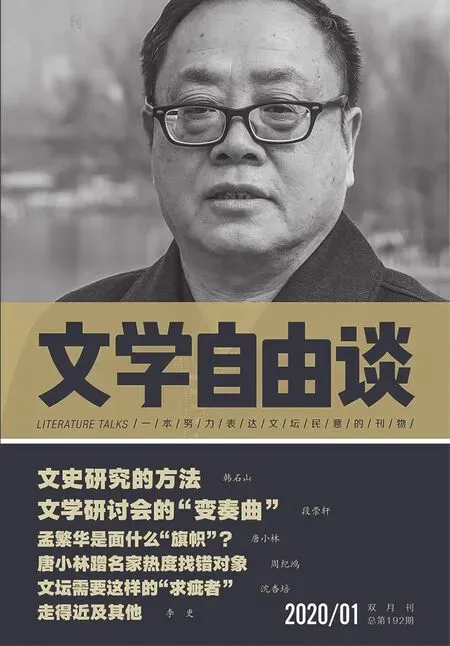文坛需要这样的“求疵者”
□沈杏培
一
近几年,总能在一些期刊、微信等不同平台看到唐小林的文章,而他的文章辨识度是那么高,看过一两篇便再也忘不掉,闭起眼睛都能把他的学术面孔从高度趋同化的学林里勾勒出来。如果根据学术特性对学界众生进行合并同类项的话,一定有一个脸模是唐小林专属的。唐小林如同挥舞着犀利的剑,朝着文化病象砍伐的文坛堂·吉诃德,又像喜欢对着那些“参天”或“茂盛”的名贵巨木叮咚捕虫的啄木鸟。他身在体制外,却把利剑和铁嘴指向体制化的学术江湖,穷追深查各种文坛“病症”。
从2006 年至今,他在各类学术刊物上发表“求疵”文章数十篇,狠批各种文坛乱象,怒“怼”那些名作家和名批评家的各种谬误。唐小林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常常直指作家的写作、评论家的研究,以及文坛内外的种种“问题”和“病象”。他的文风朴实,没有理论气和学究腔,立足于文本细读,通过考据实证和“历史化”的研究路径,指陈硬伤,拆解名家和名作的假面。这种吃力不讨好、每写一篇文章都在树敌的学术实践,唐小林坚持了多年。这个游走在文坛边缘的“独行侠”,以其学术上的谔谔之声和高调学术态势,已然成为文坛的一道独特风景。
法国文艺理论家蒂博代专门论述过“寻美批评”和“求疵批评”,他引用法盖的话这样介绍“求疵的批评家”:“他的职能是根据每位作者的气质了解他应该有的但只要稍加小心就可以避免的缺陷;对于那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至少可以掩盖或减轻其严重程度。”而关于“寻美者”和“求疵者”对于文艺活动的作用大小问题,法盖指出,求疵的批评家更有用,因为他是“真诚的合作者”。唐小林的文学批评是一种诚而真的学术实践,“诚”是说他对待文学的那份诚挚态度,他热烈而诚恳地守护着理想的文学和批评,固执地痛击着各种病象;“真”是指他的学术较少虚言,靶标精准,论证严密,总能击中要害。在文坛看似花团锦簇的当下,唐小林的可贵在于,敢于以求疵的胆识和冒犯的姿态,向假言虚言笼罩、病象乱象丛生的学术江湖发出真的声音。
总体来看,他念兹在兹不断追问的问题包括:作家应该何为,什么是不好的文学,批评家的职责何在,文学知识分子的底线在哪里。他选择的大多是业已扬名经年的大家名流,实非要借名人之“势”攀高枝搭顺风车,而是因为名人的社会影响,病象经过他们更易传播,影响更大。对于他所批评的对象,唐小林“死缠烂打”的并非艰深的理论之类,而是更为“形而下”的文史常识、语法词句的“硬伤”,以及讲真话、不阿谀的文人底线。对于作家,他怒批由于态度草率或学养不够形成的种种“硬伤”:贾平凹对时态助词“着”“了”“过”的混用,误把明代归有光和张岱视为先秦作家,错把李贺“秦王骑虎游八极”的诗句当做李白所做;莫言把《诗经》“七月流火”中指称星宿的“流火”望文生义地理解为炎炎烈日;穆涛错将《易经》中的“大亨以正”一律写成了“大享以正”,把县令和县长混为一谈;王安忆《长恨歌》中人物年龄的混乱令人咋舌……可以说,“的”“地”“得”混同,“着”“了”“过”不分,语病迭出,以及误用典故、古典诗词和古代文化知识,显示的既是写作者捉襟见肘的学养,更是写作态度上的轻慢。除了这类硬伤,唐小林对于作家审美、精神上的偏狭保持着警惕。比如对于贾平凹、莫言、余华等作家“嗜脏成癖”“嗜痂成瘾”“性噱头如牛毛”的恶趣味和病态审美,唐小林给予了尖锐的批评。对于那些光环加身的“名人”和被奉若经典的“名作”,唐小林并不迷信,在全面阅读和细致分析的基础上,常常能看见那些易被忽略的精神偏狭和人格暗面。
对于批评家毫无节操的“谀评”和“飙捧”,唐小林深恶痛绝。当下文学语境下,无论是声名显赫的大家,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只要有新作出来,常常是由出版宣传、媒体批评和学术批评共同“抬轿”。出版商照例会先声夺人地以“某某推荐”和“民族史诗”“重要收获”之类的“腰封体”赞语展开宣传攻势,媒体推介和学界研究紧随其后,通过采访、研讨会的方式,进一步追加各种夸赞之词。对于这些动辄用“奇迹”“巅峰”“里程碑”“新高度”“百科全书”等词飙捧作家的“抬轿”行为,唐小林毫不留情地给予批判。他将栾梅健称为“头脑发热的学界粉丝”,将张学昕看成“在文坛大炼钢铁”,将陈晓明称作“放卫星”和“既卖矛又卖盾”的人。之所以如此“围剿”批评家,主要基于批评家写作上的种种问题。比如,刘再复对卢梭《忏悔录》的评价,由于缺少对卢梭人格的全面了解而使立论偏颇,他对顾彬的“仇视”由于建立在媒体不负责任的报道上,而显得偏激和主观;谢冕的出彩之作稀少,但这位“编书大王”,却在主编“经典散文”时,大量塞进本人那些质量低下甚至有文法错误的“私货”;程光炜《艾青评传》中,字词语法错误比比皆是,对西方美术知识和历史掌故的误用也是随处可见……可以看出,唐小林对批评家的批评,并非空洞无物和情绪宣泄式的胡搅蛮缠,而是基于批评家的语法硬伤、文史知识错误、缠绕式文风和浮夸立场所进行的真诚商榷。他的这种真诚也赢得了不少批评家的理解。
唐小林的批评文字读来生动有趣,常常令人击节称快。他的研究路数是朴实的、笨拙的。这种“笨劲儿”体现在他的阅读上,各种谬误和硬伤的发现,都是建立在查阅原籍和细致的校勘基础之上。为了评价的客观,他采用的是“知全人”和“知人论世”的方法;为了立论的公正,他几乎要读遍作家、批评家甚至批评对象的所有材料。这种诚实的阅读态度和巨大的阅读体量,正是唐小林文学批评具有坚实力量和及物特性的重要保证。
二
唐小林有本名为《孤独的呐喊》的集子,书名有明志的意味。在为博眼球常常夸大其词的媒体批评,以及各种吹捧、颂赞大行其道的当下,唐小林认为,文学批评往往充当着作家的“亲友团和义务宣传队”。他不愿加入合唱,宁愿守着这一民间立场,给中国文坛“剜烂苹果”。实际上,放眼近些年的文坛内外可以发现,唐小林并不孤独,和他一起从事着这种“剜烂苹果”事业的还有不少人,他们构成了当代的“求疵派”。这派文学批评,不以赞美和寻美为指归,而是致力于发现、批评文坛的病象、假象和乱象,对那些已成经典的,或正在被热捧的、流行的作家与作品,保持必要的警惕和理性的质疑,正视名作家的“局限”和“消极写作”,批判批评家的逢迎套词和种种堕落行径,拆穿市场、权力和其他因素合力造成的文坛谎言和虚假风景。当代文学批评的这种求疵传统,一方面体现在一些学术刊物的自觉倡导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众多真诚、正直批评家的学术实践中。
这些具有知识分子风骨的批评家,用他们的学术实践诠释着“真的批评”的含义。正是这些秉持着“必要的反对”、敢于向文坛流弊说“不”的学者,彰显了“求疵批评”的尊严和正义。相对极为庞大的当代学人,这些学者是学界的“少数派”:李建军、王彬彬、肖鹰、韩石山、陈冲、李美皆、杨光祖、刘川鄂、翟业军……这些学者有一些共性,喜欢“找茬儿”,因而,他们的学术实践中,有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为文坛“剜烂苹果”上。这些人被一些学者称为“怀疑者和提问者,文学病象的观察者和诊断者”,他们的文字特征表现为:“你从他们的文字中看不到上下其手的捣鬼,看不到险恶刻毒的侮蔑,看不到世故圆滑的投机,看不到互相吹捧的交换,看不到骑墙居中的两可之论,看不到不关痛痒的温吞之谈,看不到毫无定见的执中之说,看不到四平八稳的公允之言。”比如李建军,被称为文坛“清道夫”,他崇尚俄罗斯文学直面苦难、抵抗邪恶、追求真理的精神传统,反对作家被市场绑架、被欲望劫持、被时尚裹挟,反对各种消极、空心的写作。
李建军理想的批评家是别林斯基,那是一种热爱真理,具有论战家性格,以“为敌”的姿态从事文学批评的人格形象。以赛亚·柏林将别林斯基概括为“一个痛苦但满怀希望、努力分辨是非真伪的道德主义者”。李建军非常欣赏别林斯基身上的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和求真进击的知识分子气质,认为他的文学批评具有“完美的典范意义”。他痛心疾首于当下批评家与作家的“腐败性合谋”,哀叹半个多世纪以来,“低眉顺眼、屏声敛气的跪在地上的批评”,因而提出“敢于为敌”的文学批评:“真正的批评,就是它的时代和文学的敌人。它与自己的时代及其文学迎面站立,以对抗者的姿态,做它们的敌人——一种怀着善念说真话,以促其向善推其进步的特殊的敌人。”带着这种批评立场,面对当代诸多名家的各种写作病象,李建军直率陈言、激烈论辩,由于他扎实的知识体系和自觉的精神立场,因而尖锐的求疵、争论,总体上显得缜密而理性。
再如王彬彬,也是一位正直坦荡的文坛“吼狮”。在他的文学观里,文学应该有精神深度和终极关怀,应该表现人性的丰富与深邃。在他看来,当代中国作家普遍缺少灵魂和精神,表现为精神的侏儒化、灵魂的庸人化和思想的贫困化。他不满中国作家过于聪明和过于世故的生存哲学,看不起“太过无聊”的文学批评。他的学术文章从来不摆弄花哨的理论,朴实无华,青睐文史互证。尤其他的那些“求疵”类文章,常有一针见血或一剑封喉的杀伤力,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对于批评家,他更是不能容忍学术硬伤、错误、学风问题,每每遇到都要发出无畏怒吼。这让王彬彬树敌无数,但他似乎无意放弃这种文坛“求疵者”的角色,批评的锋芒丝毫不减,仍然无所顾忌地批评文坛的种种堕落与恶习。
由于篇幅所限,“求疵派”其他学人的学术特点不及一一细述,但关心当代文学的人一定对他们不陌生。毫无疑问,唐小林与这些文坛“啄木鸟”们所代表的批评共识,显然有别于擅长造势的媒体批评和冬烘气十足的学院派批评,虽常被冠之以“酷评”,但这一派所具有的精炼晓畅的文风和敢于为敌、尖锐辩驳的精神立场,恰恰是一种稀缺品质。别林斯基说,说出真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模棱两可的,不愿违背公众意见的暗示,是谦虚型批评,另一种是率直而尖锐、忘了自己的批评。别林斯基欣赏的是后种。唐小林所代表的正是这种面向真理忘了自我的批评家肖像。“求疵派”并不是完美的批评范式。他们刺伤人情,让人难堪,他们体现的是“片面的深刻”。但是,这又何妨?当作家、批评家和市场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相互吹捧、谀词纷飞时,面对作家和学者由于能力和修养的孱弱而出现种种“硬伤”“病象”时,批评家如果装聋作哑,在立场上模棱两可,那么文学批评的尊严何在,知识分子的底线何存?当精致的学术垃圾漫天飞舞,不负责任的摇旗呐喊不绝于耳,我们不应该更加珍惜求疵派的这种“不合作”,和“只带显微镜和手术刀,而不带鲜花”式的学术耕作吗?
三
以赛亚·柏林的《俄国思想家》一书中有篇很有趣的文章,题为《刺猬和狐狸》。他将作家或思想家分为刺猬和狐狸两类,这一分类源于古希腊诗人阿奇洛克思存世的断简残篇中的一句:“狐狸多机巧,刺猬仅一招。”在柏林看来,狐狸型人格追逐许多目的,而诸目的往往互无关联,甚至经常相互矛盾,他们的行为与观念是离心的;这类人有莎士比亚、亚里士多德、巴尔扎克。而刺猬型人格则凡事归系于某个单一的中心识见,他们的言论、思想和判断,必定要归纳在某个单一、普遍、具有统摄组织作用下的原则中;但丁、柏拉图、黑格尔、尼采属于这一类。而他用巨大篇幅阐述的列夫·托尔斯泰则“是一只狐狸,他想成为一只刺猬”。柏林所持的这种“狐狸与刺猬”的分类方法,本质上是在探讨不同人格中的“一元论”和“多元论”,以此辨别思想家的内在面向以及作家的风格类型。这种分类方法同样适合于我们对当代中国批评家、学者、知识分子进行风格、立场上的归类。在当下学林,大多数的批评家属于狐狸型的,他们各种荣誉加身,以饱学之态穿梭在学术江湖之上,老练地游走在人情、权力和市场之间。他们出言谨慎,下笔平和,在学术文章、学术会议、新书分享会、新人推介时,常常受制于人情、嘱托与“好处”,又或者受制于门派师承,便藏起不满和锋芒,求疵退后,朱唇轻启,说尽“拜年话”,武断地贴上“丰碑”“杰出”“伟大”等桂冠和赞词。很多人的学术活动已经成了取消价值判断、没有是非立场的谄媚行为。
唐小林似乎不愿做那只机巧圆滑的“狐狸”,而宁愿做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柏林说,刺猬总是力图依照他们所热衷的某个模式去联结和表现事物,常常运用某个统一的原则来观察事物和考虑它们的意义。在唐小林这儿,这个观察事物的“统一的原则”,便是对所有作为“标杆”的名人和名作,保持高度的警惕。他不信任那些人们趋之若鹜的“经典”,和文坛名流们业已盖棺论定的文学“秘方”。在旗帜飘扬和众人顶礼膜拜的地方,他看到假象和黑暗。在唱和成风一团和气的文坛,唐小林远远地凝视着,固执地坚守着与作家、学者的“不合作”姿态,盯着文坛、名作家和大教授们的局限、硬伤不放,立场鲜明笃定,论述绵密扎实。这个文坛独行侠的所作所为,不得不令人注目。
刘再复有一本名为《人论二十五种》的书,论述了中国古今的二十五种不同人格类型,其中一种叫“点头人”。这种人事事都称是,都要歌功颂德一番。古人李康将“点头人”的特点概括为“意无是非”“赞之如流”“应之如响”,形象地写出了缺少是非立场,凡事说好,遇事急于表态、高亢响应的情态。当下学界充斥着太多这种“点头人”式的批评家。在这样一个“假大空”学术流布于市,文人普遍缺骨少血的时代,有唐小林们这样的学界“独异”战士,是一种幸事。他们是对文人底线的坚守,是对求疵传统的传承。
可以说,“寻美”和“求疵”是文学批评这一体上的两翼。两翼茁壮,方能并力齐飞。但在现实语境里,由于人情、面子和利益等因素,求疵者往往面临着得罪人、被孤立的风险,求疵批评因而常常是一种更有难度的行为。总体上来说,求疵作为一种学统,既是立场,也是方法,既是态度,也是能力。作为精神立场的求疵,它不是非此即彼的唱反调,或由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翻烧饼”式立场。它是一种胆识,体现了治学者始终如一的怀疑精神以及对于流俗的“不合作”态度。另一方面,作为学术能力的求疵,它不是纠缠于细枝末节里挑刺儿,或用一己偏见去武断地否定一切,它需要学术主体具有基本的文学修养,熟悉创作规律,具有较好的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熟练驾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方法。
唐小林作为当下文坛的“求疵者”,始终执守着柏林所说的那个“单一的原则”——不合作地“求疵”。看得出,他对自己所研究的对象是认真通读过的,从他征引的大量书籍,可知他的知识谱系是丰满的。在具体论证时,他能够通过文本细读、版本校勘、实证考据等方法演绎自己的观点。他的文学批评里没有花里胡哨的理论或概念,所依据和标举的无非是语法、审美、写作上的常识和基本的普世性价值,聚焦各种“病症”和“问题”,以分析问题和批评病象这种“症候批评”作为主导性的研究范式。我们应该为学林有唐小林这样的“啄木鸟”而庆幸,他那不绝于耳的叮叮咚咚的声音,也许会让很多人心烦意乱,但啄破林木叼出虫豸终究有益于健康。
当然,需要警惕的是,任何一种方法成为一种“主义”时,都会蕴含着某种危险。比如唐小林以求疵视野去看待学人和文坛时,目之所及几乎都有病症,似乎文坛是一个带菌大工厂,文人都是精神贫血的病人,比如评价陈思和的学术功过,以及评议陈晓明的系列论文,笔力过狠,立论稍显偏颇和苛刻。当求疵成为一种唯一尺度和目标,以此视角来审视文坛和学界群体,打捞出的永远是疾患、猥琐和无趣,而作家、批评家的那些精彩、有趣和意义,则可能会被遮蔽。对研究对象“表一种之同情”,在“求疵”时存一份“寻美”之心,怒批时怀一份商榷之平和,并非研究上的中庸、骑墙和狡猾之态,而是为了避免激昂的情绪、单一的评价尺度可能会造成的评判上的矫枉过正。
求疵,是一种观察事物的视角,意在彰明作家写作中被人有意或无意忽视的短板和暗角,还原被放大的现象本源,从而试图还原文学的真相,重新定义文学的价值秩序。
可以说,唐小林经年如一的求疵诊病式学术实践,彰显了求疵的学术效用,亮化了文学批评中略显孤寂的求疵传统,让当下文坛乱象和文人之病无处躲逃。如何求疵,求疵的尺度和限度是什么,求疵批评与“酷评”有何不同,这些正是文坛“求疵者”引发的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