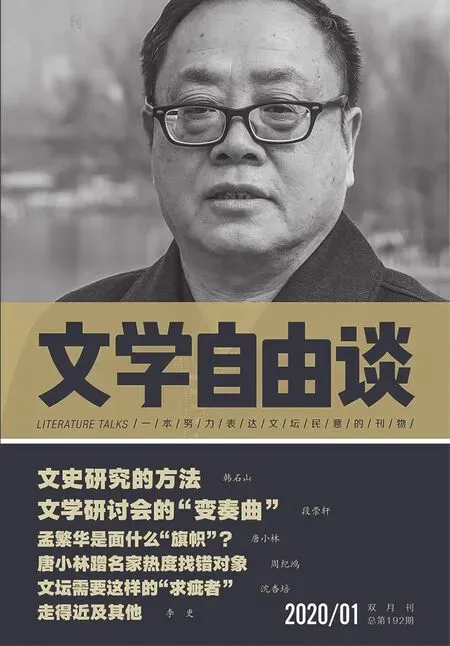孟繁华是面什么“旗帜”?
□唐小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文学批评家”常常和“浮夸”“肉麻”“溜须拍马”“抬轿”“颠倒黑白”“集体起哄”这样一些贬义词牢牢地捆绑在一起,而评论家群体也因此变得毫无尊严,其中的一些人甚至被称为“最不脸红的人”——文坛的“浮夸风”,几乎就是由他们从各种书商的新书发布会、当红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上刮起的。他们看似在冠冕堂皇地谈论文学,实际上却是在以文学的名义糟蹋文学。
2018 年出版的《孟繁华研究论集》,堪称这种风气的典型标本。该书编者之一,也是孟繁华在社科院的“关门硕士”张欢在《有参与性地写在前面的话》(此文似可视为这本书的“序言”)中说:
作为当代文学领域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孟繁华的名字每被提起时总会激起一种可见的鲜明和振奋,而在他洋洋数百万的文字面前,再麻木的人都无法忽略其强劲的内在气韵:深厚的学识、非凡的敏锐、持久的耐心、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与批判立场、对人的精神困境的思考和反抗,同时还会收到的是他文如其人不可复制的力量、温度、感染力。这个时代拥有这样的批评家是值得庆幸的,而更难得的是他本身就是一部作品。
在这位“弟子”崇拜的目光里,孟繁华似乎不但能够通过自己的文字让麻木的人苏醒,而且还能够让台下的人当场接收到其“带功”信息。类似的浮夸和赞美,充斥全书,有人甚至宣称,孟繁华是一面竖立在文学批评界的“旗帜”,他“就像一棵幸运树,任是花草、行人、雨雪、鸟虫,在树的周围都会变成风景,于是风景的美成了我们的生活”。
在我看来,如果说孟繁华是什么“旗帜”的话,那最多也是一面见风使舵的“白旗”。当年讨伐《废都》的孟繁华,后来不但向贾平凹“举手投降”,而且还猛然调转枪口,向曾经与自己同一个“战壕”的“战友”——那些一起批评《废都》的批评家们——反戈一击。此事有蹊跷、够反常,值得学界研究、探讨。不过,值得研究、探讨的远不止“反水”这一件事,而是或可称为“现象级”的“孟繁华文学批评的病象”。
那么多错讹,也叫“修订版”?
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洪子诚先生以其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著称。他精心撰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受到学界的交口称赞。为了精益求精,洪子诚一再对该书做修订,其踏踏实实的学风,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学术声誉。与此“相映成趣”的,是孟繁华和程光炜编写的另一种文学史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
同样是为当代文学治史,洪子诚对《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真可谓苦心孤诣、锦上添花,而孟繁华和程光炜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再版时,作者似乎连认真检查一遍的耐心都没有,却在书名后堂而皇之地标注“修订版”三个字。这难道不是在欺骗读者、玷污学术吗?我们不妨随便举几个例子,来看看两位作者是如何“修订”的:
仁宝追上去,捏紧他的后颈批.(皮。引文括号内文字均为笔者所加)让他给自己磕几个响头。
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的美丽的图画:光滑的铁钻.(砧)子。……老铁匠的歌唱被推出去很远很远,像一个小绳.(蝇)子的嗡嗡声。
现在老师已经做.(作)古,上次老师来看病,也没能给他找个医院,到家里也没让他洗个脸……
1985年,《透明的红萝卜》声名大噪后,作者又相继发表了《金发男.(婴)儿》、《红高粱》等力作。……莫言自己坦言,“红高梁.(粱)”系列受福克纳、马尔克斯小说很大启发……
一个“贼”字使他们的面部全部.(都)颤动起来,一个“贼”字使他们的眼睛里全都蒙上了一层畏惧。
在宿舍里.(“里”为衍文)他可以什么都忘掉,忘掉功能的走向,忘掉作品分析时的错误,忘掉(漏掉“乐器”二字)配置法、忘掉九度三重对位引起的神经错乱。什么都忘掉了,可就是忘不了马力。
孟繁华应该认真读过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也就知道小说中的小铁匠,他不该把打铁的铁砧子写成“铁钻子”啊。书稿完成后,他如果仔仔细细地检查一遍,也不至于把“颈皮”写成“颈批”,把“小蝇子”写成“小绳子”——“小绳子的嗡嗡声”,这画面太美,我不敢看。
这里列举的,仅仅是《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中错讹的九牛一毛,类似的错字、脱字、衍文现象,比比皆是。可以说,书中只要涉及到引文,就几乎无一幸免。
你很难相信,如此多的低级错误,居然出自经过孟繁华和程光炜“精心”修订,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 世纪课程教材”——我真不知道,有哪些大学敢用这样的教材?如果用了,那些讲授当代文学的教师,又是怎样手捧这教材给学生上课的?是奉若圭臬,还是弃若敝屣?——也许是前者,因为,就是这样一部错误百出的书,竟然还能受到一干学者的吹捧:“新的视角新的问题意识”,“寻求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的结合点”,“在书写‘整体当代文学史’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有“‘成一家之言’的雄心和勇气”,是“当代文学学科的一次丰厚的收获”……
这类低级错误,并非仅仅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一书中,在孟繁华其他的学术专著里,同样是恒河沙数:
而此时,他(指陈晓明)的大著——《德里达的地.(底)线》刚刚送到我们的手上不久……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现代文明诞生之后,陶渊明想象的“桃花园.(源)”就不再存在了。
——《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
叶弥也写到男女床第.(笫)之事,但那些点到为止隔靴搔痒的描写并不是张扬男女之间的性事,而是为了凸现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和.(的)变化。
——《文化批评与知识左翼》
在这部煌煌(皇皇)40万言的著作中,作者试图将“表意”镶嵌于历史的总体性中,从而揭示出历史的总体性意愿或历史的精神意愿。
——《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
笔者曾经批评过陈晓明不懂什么是“暴得大名”,其实孟繁华也一样,也是连这个常用成语究竟是褒义还是贬义,甚至究竟该怎样写,大概都没有弄懂:
青年作家王跃文因《国画》而暴得大名,《国画》一时洛阳纸贵。
——《游牧的文学时代》
主人公忆摩,不仅命名与毕业于康桥的徐志摩同学有关,而且硕士论文研究的内容也与这位因写了《再别康桥》而暴得大名的诗人有关。
——《坚韧的叙事——新世纪文学真相》
80年代哪怕是中学生作文似的小说,只要它切中了社会时弊,就可以一夜爆(暴)得大名。
——《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
孟繁华从事学术研究数十年,严谨认真的态度自不必说,语言文字的功底更应该十分了得、不容置疑,那怎么会出这些错讹呢?难道是出版社编辑跟他过不去,故意把原稿中正确的字词改成错的了?——这怎么看都是一种有点“烧脑”的“神推理”,至于可信度嘛……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互捧够哥们,盛赞无底线
与文坛哥们结成联盟,互相吹捧,你抓住我的头发,我抓住你的头发,彼此“提升”,这是孟繁华多年行走文坛的秘笈。孟繁华、程光炜,以及陈晓明这些“当红学者”,经常聚结在文学的江湖里,甚至一起合作著书。他们的学问基础也许并非浅薄,但做学问的严谨性、严肃性,实在是令人大摇其头。特别是他们彼此之间互相点赞时的表现,直让人怀疑他们的那些话是否出自真心。
孟繁华与陈晓明之间的往来,即是一例。二人相互捧场、相互提携,每有新书出版,常常是你为我作序,我为你作序。而这些序的主旨,一言以蔽之,不外乎八个字:当下文坛,数你最牛!
在为孟繁华的《中国当代文学通论》所作的序中,陈晓明说:
(孟繁华)始终关注当代中国文学最新的发展动向,始终站在当代文学批评最前沿的位置,参与到那些对最新文学现象和事件的阐释中去。他的精力旺盛,又十分勤奋,好像永远有忙不完的事,但却著述不断,评论满天飞……它比之一般的文学史显得更为自由灵活,无须文学史面面俱到,事无巨细都要兼顾。它只抓主要矛盾,只抓文学史中的要害问题。就此而言,可以看到孟繁华处理当代文学史的独到手法,那就是他的开阔眼界和洒脱的叙述。现今的文学史大多拘谨刻板,难得孟繁华以他的洒脱来叙述当代文学史历经的道路。当代文学史研究最大的难题,在于当代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这是一般写作文学史的人都试图要回避的问题,或绕道或淡化,但孟繁华却采取了正面强攻的手法。这让我有些吃惊。
在将别的学者贬得一钱不值之后,陈晓明开始曲终奏雅了:
孟繁华的文学评论写得越来越洒脱,做“通论”就自然显出他的洒脱自由。
面对陈晓明的友情点赞,孟繁华自然是心领神会的。不久,他就投桃报李,对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一书,使用了同样的“模板”:
多年来,陈晓明一直站在中国当代文学的最前沿,引领着当代文学批评的风潮,发动了一次次标新立异的批评活动,对改变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型构、方法乃至修辞方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是近年来这一领域的重要收获:从1999年至今,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写作几近处于停滞状态,而陈晓明的文学史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观念、视觉和范式。
这种为了抬高一个人,而不顾事实地贬低同行学术研究成果的路数,可说是一种毫无底线的吹捧。据笔者所知,至少早陈晓明的《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十年,洪子诚就出版了《中国当代文学史》,由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比《中国当代文学主潮》早出版十年。孟繁华怎么能够如此不诚实地把别人的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称为“停滞状态”呢?难道偌大一个中国,那么多中文系教授都碌碌无为,只有陈晓明一个人才戛戛独造?
孟繁华的“文坛哥们”不少。摩罗说过,他第一次来北京的时候,就听说孟繁华热心邀朋友谈论文学,并主动管饭。在日后的交往中,摩罗也果真常常被老孟“主动管饭”。摩罗本就是个著名的“吹鼓手”,曾说刘震云是“大作家”,说张炜最大的光荣在于其所达到的个人成就的峰巅和目前文坛多元格局中某一元的峰巅,说余杰让他在中国文坛第一次看到了青年文体……好话不白说,比如,余杰就曾反过来表扬摩罗“有成为巨人的天赋”,是“中国的别林斯基”,他的出现,“是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幸运,更是中国思想界的幸运”。
那么,问题来了:孟繁华何以要对摩罗“主动管饭”?笔者不想去推测背后的动机,但我们从二人在“互捧模式”的表现中,或许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摩罗宣称:“孟繁华乃是80年代送给文坛的一件礼物。”孟繁华则故伎重演,以贬低其他作家的方式来抬高摩罗:“那些号称受过俄罗斯文学哺育和影响的作家,甚至连皮毛都没有学到。他们以为呻吟就是苦难,自怜就是文学。摩罗对此显然不以为然,他甚至无言地嘲笑和讽刺了这些自诩为文化英雄的真正弱者。”他说,摩罗的《六道悲伤》是一部“不用启蒙话语书写的具有启蒙意义的小说,……他是一个知识者有着切肤之痛吁求反省乃至忏悔的小说。对摩罗而言,他实现了一次对自己的超越,对我们而言,则是一次灵魂震撼后的惊呆或木然。目睹这样的文字,犹如利刃划过皮肉。”“我们惊异的不止是摩罗的文体转变,当然还有摩罗驾驭文学形式的能力。”
对孟繁华们的捧赞能力,我们也表示十分“惊异”。
见风使舵,见缝插针——哪里有热闹哪有我
在我看来,孟繁华大概不是一个有正确是非观的人,因为,在他的学术生涯中,“蹭热度”的事时有发生。
从一开始,孟繁华就在跟风。1993年6月,贾平凹的《废都》在经过新闻媒体的轮番炒作后,迅速占领了各地的图书市场,一时大热,但很快遭到了学界和文坛的批判;孟繁华和陈晓明就是批判“阵营”的骁将,比如,孟繁华就曾挖苦《废都》是“对明清文学的皮毛仿制”“《花花公子》的中国兄弟”。当其时也,孟繁华虽已42岁,但刚刚“出道”,还寂寂无名。通过这次批判,他终于在文坛掘到了“第一桶金”。
随着时间的推移,贾平凹在一帮文坛兄弟一波又一波“造神”攻势的推动下,走向神坛,再一次成为众多媒体追捧的“偶像”。这时的孟繁华和陈晓明发现风向不对了,开始频频向贾平凹“抛媚眼”,痛心疾首地表示真诚反悔,承认当年对《废都》的批判是误入歧途。就像祥林嫂一提起阿毛的惨死就会说“我真傻,真的”一样,孟繁华也是逢人就说自己当初是如何的愚蠢,做了不该做的事:
我当年也参加过对《废都》的“讨伐”,后来我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当年的批评是有问题的,那种道德化的激愤与文学并没多少关系……今天重读《废都》及它的后记,确有百感交集的感慨。在其他场合,包括在文学会议或文学讲座上,我都曾表达过:《废都》一定会重新评价。
对于孟、陈的组团“投诚”,贾平凹表示了深切的理解。“知错就改”的这二位,将会对自己大有好处——所谓“善莫大焉”的“善”,或可“歪解”为“好处”。2009 年,贾平凹的散文集《大翮扶风》出版时,邀请孟繁华为新书作序。对孟繁华来说,这不啻是一个绝妙的机会!在序中,他再一次表示忏悔,并大赞《废都》和《秦腔》是贾平凹至今最重要的两部小说,也是奠定他在中国当代文坛地位的作品;至于自己曾经“误批”《废都》的往事,自然会堂而皇之地成为这篇序言的精彩“桥段”。
从此,孟繁华是“逢贾必夸”,就连贾平凹的长篇小说《高兴》,也受到了孟繁华的狂捧:
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最精彩之处往往在细节的书写或描摹上。《高兴》在这一点上所取得的成就,应该说在近年来的长篇小说中是最为突出的。《废都》之后我们再没见到这样的文字,但在长篇小说进退维谷之际,贾平凹坚定地向传统文学寻找和挖掘资源,不仅为自己的小说创作找到了新的路径,同时也显示了他“为往圣继绝学”的勃勃雄心和文学抱负。
对当红作家的吹捧,可说是孟繁华的“常态”。比如,评论徐则臣的《耶路撒冷》:“对‘70后’作家来说,它标志性地改写了这个代际作家不擅长长篇创作的历史;对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来说,它敢于直面这个时代的精神难题,处理了虽然是‘70后’一代——也是我们普遍遭遇的精神难题。”这样的评论,实在是太不靠谱了。70后这一代作家,还有漫长的几十年,谁能因此断定他们不擅长长篇小说,而只有徐则臣才能“挽狂澜之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说徐则臣通过一篇小说就解决了70后和我们普遍遭遇的精神难题,这不仅是在神话作家,同时也是在过分夸大小说的功能。
孟繁华夸人时善用极限用词,把人往天上吹,丝毫都不考虑被吹者会不会摔下来。他说刘震云是这个时代最具时代感和现实感的作家,是一位最坚定的现实主义作家,其虚构能力和讲述能力,当下几乎无出其右者;他把张炜封为“书写大地的圣手”和“这个时代最后的理想主义作家”;他称阎连科“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为我们提供的还要多”——这段评论,可说就是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那段话的翻版:“我从这里(指《人间喜剧》——引注)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
多年来,孟繁华把他的批评文章,写得越来越像“应用文”——它可以“应用”于一切出版商的大肆炒作。《狼图腾》被炒得火热的时候,孟繁华主动加入到出版商们的“推广大合唱”中,拼命吹捧这部赞美狼吃羊的血腥小说;《大秦帝国》成为出版商和影视宠儿的时候,孟繁华居然对这部篡改历史、美化暴君的小说进行热情的讴歌,盛赞它是“一部结构宏大、情节复杂、人物众多的史诗性作品”,并声称,这部作品“以严肃的笔触、丰沛的想象力和有训练的、简约又富于文学性的语言,为我们重现了秦帝国前后丰富而复杂的历史场景,为我们重塑了那个遥远而又心向往之的大时代”。
“孟氏批评”高产有模板
虽说孟繁华已经出版了数百万字的文章,但这样庞大的数字,多是重复写作的文字堆积。其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的《文学革命终结之后——新世纪文学论稿》中的许多文章,都是在炒旧作的冷饭,哪里有多少新意?如果将这些文字进行水分挤压,你很难得到什么像样的“干货”。
作为一名从事文学理论与评论专业的学者,孟繁华似乎有自己的一系列“写作模板”或曰“套路”。谓予不信,兹举一组例子——
之一,评论姜戎的《狼图腾》:
如果将它作为小说来读,它充满了历史和传说;如果将它当作一部文化人类学著作来读,它又充满了虚构和想象。作者将他的学识和文学能力奇妙地结合在一起具体描述和人类学知识又相互渗透得如此出人意料、不可思议。显然,这是一部情理交织、力透纸背的大书。
之二,评论孙皓晖的《大秦帝国》:
这是一部用小说的形式书写的历史。这一特殊的小说体式,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在评价《伊利亚特》时所说,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它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它充满了历史。这也正是《大秦帝国》作为历史小说的魅力。
之三,评论阎连科的《受活》:
这虽然是个荒诞不经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却会让人联想到汤因比对《伊利亚特》的评价: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故事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那里却充满了历史。在汤因比看来,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也一定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阎连科是一个文学家,但他却用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反映或表现了那段荒诞历史的某个方面。
之四,评论贾平凹的《山本》:
如果把这部作品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来读,里面也充满了历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都应该像伊利亚特一样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之五,评论梁鸿的《出梁庄记》:
任何事物一旦进入讲述就进入虚构,历史也一样。我们读书看到历史,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而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到《伊利亚特》:“如果当作历史,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当作虚构,里面充满了历史。”“梁庄”系列本身也是虚构作品,说它是非虚构是因为它更注重客观性,但一个作家书写的文本怎么可能是非虚构的呢?
历史,文学,虚构,汤因比,伊利亚特……同样的“关键词”乃至语句,在孟氏的多篇评论中反复出现,连对《左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的评论,也“依样画葫芦”:
《左传》这是一部酷似于《伊利亚特》式的著作:如果你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又充满了历史。
陈寿的《三国志》是罗贯中创作《三国演义》最基本的材料,这是毫无疑问的。但虚构是存在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里说,以《伊利亚特》为例,如果把它当作历史来读,里面充满了虚构;如果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里面充满了历史。
稍一对比,我们就不难看出,孟繁华早已将文学评论当作习惯性“填充”,鲜有思想、创见。只要看一看他的《小说现场——新世纪长篇小说编年》,我们就可以知道,“孟氏批评”大都是一个固定的模式:文坛现状+作家评价+故事概述+心得体会。这种“套路”,只能称为机械、僵化的工业化生产,它与有深刻思想和独到见解的专业小说评论,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
“写作模板”大大地提高了孟繁华的写作效率,只是有投机取巧的嫌疑。以如此“套路”从事文学批评的孟繁华,又怎么能称得上是什么文学批评的“旗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