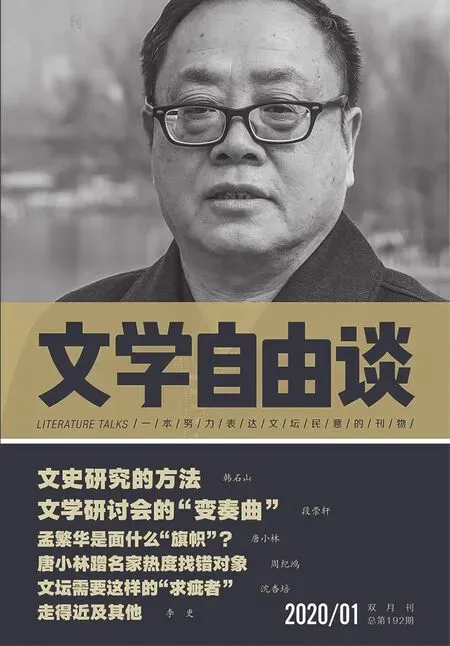文史研究的方法
□韩石山
感谢大同大学宣传部的安排。刚才介绍来宾,其中一位是河南文艺出版社的郑雄先生,他是该社副总编辑,与他同来的还有两位编辑。此番来山西,是为了给他们的一本新书造势,第一站是太原,第二站是大同。这本书不是别人的,是我的,叫《边将》,去年12月出版,这才5月,已是第二次印刷了。春天的时候,有朋友联系我,说是大同大学想叫我做个讲座。我答应了,但老没有合适的时间。这次是两好凑成了一好。按说今天该多讲这本书,想想,时间宝贵,机会难得。在座的不光有中文系的学生,还有历史系的学生。我想根据自己的体会,谈谈文史研究的方法,顺便也会说到《边将》。
这个讲题,来的路上就想过。在太原,去两个地方讲过,一个是省文史馆,主要讲了《边将》的写作过程;一个是山西大学,主要讲了明史研究的重要性,讲题为《山西大学应当成为明史研究的重镇》。说是山西大学,具体是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再具体些是历史系。到大同讲什么呢?很费踌躇。
这就要说到我对大同的看法。山西的几个城市里,从历史上说,最有都市景象的,不是太原,也不是平阳(临汾),而是大同。这是一个真正做过一个朝代都城的地方,遗留的古建筑之多,规模之大,全国少有;若以密度而论,恐怕都超过了北京。我曾跟朋友开玩笑说,如果大同当了山西省的省会,山西的文化品位,都会提升一个档次。
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来过一次大同。父亲在大同当兵,爷爷带上我母亲和我,还有我哥哥,来大同探亲。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骆驼驮着一大堆干草过城门洞子,看着草堆那么高,以为肯定过不去,可它走着走着就过去了。当时觉得很奇怪:明明高出一截子,怎么走着走着就过去了?长大就明白了,小孩子个头低,视线从草垛子顶部掠过去,视点落在了城门洞最高处的上头,就觉着过不去;走着走着,视点低了,自然就过去了。御河边的铁牛,父亲也领上我和哥哥到跟前看过。那会儿没有栏杆,说不定还上去骑过。有了这个亲切感,就觉得到了大同,要多讲些切实的东西。我不是纯粹的学者,谈文史研究的方法,主要是谈自己切身的体会。
大学,我上的是历史系,山西大学历史系。正赶上文化大革命,我们没怎么上课,是混出来的。对历史的兴趣,跟许多不良嗜好一样,不能沾上,沾上很难戒掉。这么多年,虽一直应着专业作家的名分,实际上最喜欢的还是历史。买书买得最多的是历史书,看书看得最多的是历史书,其他书也买也看,就少多了。有些场合,人家介绍说韩某人是个作家,我听了没有一点荣耀感,反而觉得是“时运不济,沦落至此”;要是吹牛,还会说句“家门不幸,出此孽子”。因此上,一有机会,总愿意“显话”一下自己史学上的底子、做学问上的功夫。“显话”是晋南土话,跟北京话“显摆”是一个意思。
北京有个鲁迅文学院,是专门培养作家的,可说是个作家速成学校。我跟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关系。这个鲁院,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办起的,起初叫“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五期”——所以叫成“第五期”,是跟五十年代的中央文学讲习所接续上的——没两年就改名叫成了鲁迅文学院。我是讲习所第五期的学员,也可说是鲁院第一期的学员。大致是一个省一个学员,山西的,就是我去了。学习方法,主要是请外面的专家学者讲课,然后看几天书,再开个讨论会交流心得。一个课题,前后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史记》请的是北大的季镇淮先生讲的,《红楼梦》是请北大的吴组缃先生讲的。讲《红》的还有一个学者,没记错的话,是社科院的陈毓罴先生。《红》重要,学了两个星期。全班三十二个人,讨论时先是分组,再是全班。全班讨论时,一个组出一个人发言,再自由发言。我们组的发言人,几乎每次都是我。我这个人很浅薄,爱出风头,每次轮到我发言,都要精心准备显一显自己。小组讨论在前一天,全班发言在后一天,都是上午,中间只隔一个下午。按说这么短的时间琢磨不出什么,我们是学了一两个星期,才全班讨论的,有的是时间从容应付。
有次学习苏联小说《活着,可要记住》,主人公是个女的,叫纳斯焦娜。书的版权页上有俄文的版权信息,标着重音。我学过俄语,一看就知道该怎么读,重音在“焦”上,同学们听了很是惊奇。发言中我说,少妇较少女,具有更多的女性魅力,也就具有更多的文学性。世界级的大作家,多是描写少妇的高手,世界文学史的长廊,站满了一个又一个裸体的少妇塑像。我的这番话,可谓之“少妇论”。到了8月,放了一个月创作假,各自回去写东西。班上有个同学叫古华,回来跟我说,他回到株州写了个《芙蓉镇》,是按我的“少妇论”写的,过去从未听人这么说过。我的《边将》里,也是按我的“少妇论”,写慕青这个女人的。
接着说学习《红楼梦》的事。这本书,上高中时看过,工作后又看过,很熟。不光对书里的情节熟,对成书过程、历来的评论也都熟。比如成书的原委,有“反清复明说”,有“自传说”,当年最占上风的是“四大家族说”。作者呢,学界几乎已认定是曹雪芹写的,没写完,高鹗续写了后四十回。对这些,我都有看法。写书的动机上,绝不认同什么“四大家族说”。明明只写了贾家,林王薛三家是亲戚,很少正面着墨,怎么说是写了四大家族呢?还有人说写了阶级斗争,更是牵强附会。那个时代的文人,怎么会有阶级斗争的观念?
全书的命意是什么呢?我认为是“正邪二气说”,即是说,全书体现的思想理念,是正邪二气的生成与斗争。对此,书中有明确的提示。第二回的回目叫《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主要内容是:冷子兴说荣国府的人事,祖上是谁,父辈是谁,荣宁二府又有谁,末后说到宝玉的出生与异秉。冷子兴说了,贾雨村有番议论,是这么说的:
天地生人,除大仁大恶两种,余者皆无大异。若大仁者,则应运而生,大恶者,则应劫而生。运生世治,劫生世危。尧、舜、禹、汤、文、武、周、召、孔、孟、董、韩、周、程、张、朱,皆应运而生者。蚩尤,共工,桀,纣,始皇,王莽,曹操,桓温,安禄山,秦桧等,皆应劫而生者。大仁者,修治天下;大恶者,挠乱天下。清明灵秀,天地之正气,仁者之所秉也;残忍乖僻,天地之邪气,恶者之所秉也。今当运隆祚永之朝,太平无为之世,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上至朝廷,下及草野,比比皆是。所馀之秀气,漫无所归,遂为甘露,为和风,洽然溉及四海。彼残忍乖僻之邪气,不能荡溢于光天化日之中,遂凝结充塞于深沟大壑之内,偶因风荡,或被云催,略有摇动感发之意,一丝半缕误而泄出者,偶值灵秀之气适过,正不容邪,邪复妒正,两不相下,亦如风水雷电,地中既遇,既不能消,又不能让,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故其气亦必赋人,发泄一尽始散。使男女偶秉此气而生者,在上则不能成仁人君子,下亦不能为大凶大恶。置之于万万人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万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万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纵再偶生于薄祚寒门,断不能为走卒健仆,甘遭庸人驱制驾驭,必为奇优名倡……
好了,不念了,下面是一大串人名,除了陈后主、唐明皇、宋徽宗三个风流皇上外,全是卓异的诗人、画家、书法家,最后两个是崔莺莺、朝云。崔莺莺是《西厢记》的女主角,朝云是苏东坡的爱妾。
念了这么多,你们未必理得清头绪。简单点说,是说天地之间有正邪二气,大仁大德之人,乃正气之所秉者,大凶大恶之人,乃邪气之所秉者。正气与邪气相遇,如同雷电相碰撞,风水相激荡,有一丝半缕误泄而出,若有男女偶秉此气而生,必为才情卓越之异人。这当然说的是贾宝玉。不要忘了,作者为贾宝玉设置的这个生存环境,恰是一个正邪二气相碰撞、相激荡的大家族。也就是说,《红楼梦》的故事设置、人物安排,正是体现了作者的这一社会理念与人生理念。
看看荣国、宁国二府的人名吧。宁国府那边是老大,叫贾赦,下面是贾琏,“爬灰的爬灰,养小的养小”,没个正经坯子。荣国府这边是老二,叫贾政,贾母在这边坐阵;管事的王熙凤,是宁府那边的媳妇调到这边管家;儿子是贾宝玉,女儿们也都俊俏可爱,知书达理。贾政,政者,正也。贾赦,这个赦,就是赦免的那个赦,该赦的能是好东西吗?可以说,赦者,邪也。一个正,一个邪,雷电相激荡,水火不相容,便生出许许多多悲戚哀婉的故事来。“正邪二气说”,这才是《红楼梦》成书的理念与宗旨。
再说对书名和作者的看法。
作者,现在都说是曹雪芹。这个人名,并非像现在,出了书写在书页上,而是胡适、周汝昌一班学者考证出来的。连生卒年、出生地、人生经历,都是一笔糊涂账。不信你们百度下,曹雪芹条下,生卒年是约1715年至约1763年,年下还有月日。年都不准,月又从何而来?依据这个时限,曹雪芹成年后,主要生活在乾隆年间,是清朝的太平盛世。我认为,在太平盛世,一个没有功名又平庸穷困的书生,写不出《红楼梦》这样的大作品。
会是什么人写的呢?一下子我也说不清,但我可以做个大致的推测。此人极有可能是一个生在明末,有相当社会地位与声望的名士,遭受家国巨变之痛,发下大愿,才能写下这么一部警世劝人的大著作。为什么说有家国之痛呢?看看书名三字——红楼梦,颠倒过来就是“梦红楼”。中国人在做梦上,要么是强烈的追求,要么是深深的怀念,都能做出好梦来。《红》书里人物的穿戴,是明朝人的衣冠。全书就是一场大梦,梦的是往昔的繁华与荣耀。这个书名,作者在第一回里,做了好些掩饰,一会儿《石头记》,一会儿《情僧录》,一会儿又《风月宝鉴》;还说是《金陵十二钗》,更是没来由。有一个地方泄漏了天机,说是在悼红轩里增删多次才成书的。梦红楼,悼红轩,作者的用情在“悼”字上,要彰现的是那个“红”字。清朝初年,士人都有亡国之痛,不能呼天抢地,大放悲声,最常用的隐语是“恶紫夺朱”。古诗《咏紫牡丹》里有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有个文人引用一下,也叫杀了头。“朱”不能说了,红为正色,不能让人不说,于是有才华的文士,便以之名其处所,写下这样一部名中带“红”字的大书。我认为,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将作者定为曹雪芹这么一个落魄书生,实际上是降低了此书的品格。不如干脆署上“无名氏”,作者生存年代,可写作明末清初。好几次看到有人说是吴梅村写的,年代合,身份也合,但是证据不过硬,还是不要妄作定论。
这是我早年在学问上的一些思考。也曾跟人说过,不多。《红楼梦》的“正邪二气说”,记得是1981 年吧,在一个什么会上,跟山西大学一位研究红学的教授说过。他鼓励我写成文章发表,我笑了笑没有答应。他说他是红学会的理事,可以推荐到《红楼梦学刊》,说不定会登的。学问上的事,要慎重,一得之见,千万不敢自以为是。一时冲动,白纸黑字,丢人可就没个深浅了。就是现在,正式场合我也不会说这个。今天在这里说,是要引导同学们学会思考,怎么个想,往哪儿想。
前多少年,写《李健吾传》,写《徐志摩传》,考证个什么归拢个什么,也有做学问的意思,但主要是理顺材料,显现人物的品质。只有这次写《边将》,让我过了一次做学问的瘾。有人说,小说嘛,编吧。或许有人能这么写,写下还叫好,我不行。我是上过历史系的,知道写下的东西,糊弄今人只是一时,胡编乱造后人会笑话的。因此上,动笔之前,对大同一带边防的布局,军堡的设置,将领的调配,都做过也还不算粗略的研究。比如杜如桢做了大同镇总兵之后,为了解决闲散兵士滋事这一社会问题,与巡抚方逢时商议,拟用“转输”的资金,雇用休假兵士修筑边墙,既增加了兵士的收入,又维护了当地的社会秩序。这办法,就是看《山右丛书二编》第五卷收录的《杨襄毅公本兵疏议》得来的。不看这样的书,你就不知道“转输”是什么,也就编不出这样的故事情节。杨襄毅公就是杨博,《边将》里写了这个人物;“本兵”是对兵部尚书的尊称,杨博当过兵部尚书。
《边将》出版后,按说可以不看明代的史书了。怪得很,我是反而上了瘾,丢不开了。没事了,爱看这方面的书,见了有兴趣的,还是个买,买了还是个看。来大同的路上,带了一本闲书叫《典故纪闻》,预备晚上一个人睡不着了看的。是在右玉吧,刮大风,有半天没出去,闲翻书,一翻就翻到一则史料。心里直后悔,如果写《边将》期间看到这则史料,我的书里,说不定会增加一个人物,或者是让主人公有这么个经历。
《边将》最早的本子上,写嘉靖二十九年,杜如桢陪新婚的嫂嫂,从右卫城出来,去马营河堡给二嫂的父亲上寿,就是过生日。一出城,路边不远处一个新坟头,一伙人披麻戴孝在坟前祭奠。车夫老张给杜如桢说,这是在祭奠前些日子,蒙古人进犯大同,中埋伏战死的大同总兵张达,同时死了的还有副总兵林椿。这是真事。嘉靖二十九年是明史上一个重要年头,俺答,蒙古人一个部落的首领,率兵突破边墙,先围大同,总兵张达和副总兵林椿战死;俺答又挥师东进,铁骑直抵北京东直门城外。城外的火光,皇上在紫金城里都能看见。这年是农历的庚戌年,史称“庚戌之变”。后来为了写隆庆和议,让杜如桢参与其事,将他的年龄提高五岁,看见上坟祭奠这个情节就舍弃了。但是后来写到边关马市时,仍说杀胡口堡守备官林某,是林椿的儿子。可见对张达、林椿战败殉国这件事,还是心有所念的。
在《典故纪闻》书里,看到一则什么材料呢?
有一则记载说,张达原先驻守宁夏还是什么地方,贻误军机,论罪当斩。某大员求情赦免,以其勇猛善战,为可用之材。庚戌年调任大同总兵,俺答来犯,张达果然奋战身亡。若写《边将》前见了这则史料,我会在杜如桢的副将中写这么一个将领,犯了错,本当重处,赦免之后,以死报效朝廷。这样就增强了战争的惨烈,丰富了边将的阵容。也可以让杜如桢犯了什么重罪,赦免后更加忠勇——当然不能让他死了。
说这些,意思是要看闲书,丰富知识,扩大视野。有没有学术兴趣,端在爱不爱看闲书。爱看闲书的,才是真正有做学问的兴趣。现在的学生,读上四年本科,都不知道自己的学术兴趣在哪儿。快毕业了要做论文,老师出个题,自己从网上找些参考文章,东凑西拼,就是一篇论文。就是看书,也只看与写论文有关的书,关系不大的,根本顾不上看。这样的学生,上了几年大学,跟没上是一样的。学问之事,一定是有兴趣才能做好,没兴趣,那叫混饭吃,不能叫做学问。多看闲书,在闲书中得到线索,得到启发,再在正史中找材料来进一步论证,绝对是做学问的正经路子。胡适说的“大胆的假没,小心的求证”,我想着就是这么来的。一点苗头也没有,怎么个假设?做学问,底子要厚实,思维要活跃。底子怎么个厚实?多看闲书才会厚实。怎么个活跃?看得多了才会活跃。
做学问上,一些几何学上的原理,同样适用。两点定一条直线,三点定一平面,给一个点再给个半径,就能确定一个圆。用在做学问上,两个证据延伸,说不定就发现一个规律;三个证据,说不定就能破解一个历史公案;一个确定的点与一个确定的时段,就能确定一个历史现象的范畴。你说你做了,可是得出的结论是错的,那只能说,你的两个点选得不对,不能说两点定一线的几何学原理是错的。
古人说,做学问讲究的是才、学、识。有人以为这是平行的三个条件,其实不是,是递进的。“才”是说你得有那个灵性,“学”是说你得有那个积累,经过那么个步骤,“识”是“才”加上“学”之后的升华,也可以说是“才”与“学”糅合起来的一个结果,一个飞跃。光这三条,总觉得不全,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里加了一条:德,连起来就是才、学、识、德。梁启超很是赞同,且将“德”冠在四条之首。我不这么看。我认为,“识”里就包括了“德”。在为人上,说某人“识不及此”,多半说的是德行不好。一个人在学问上弄虚作假,能说他在器识上够用吗?品质不好的人,学问上也不会有大出息。为啥?他的心眼,不能全放在学问上。全力以赴犹不及,心有旁骛怎能行?
有人会说,你这是道德至上主义。我不这么看。德的问题,在智的层面上就应当解决,拿到“识”的层面上,已经是高抬了。说做学问,就是说德上已不存在疑惑。叫我说,要加上一个字,该加的是“为”字。有才有学有识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为,就是做出成果,表现出来。这上头,我们有许多惨痛的教训。某个学者死了,追悼会上说他还有什么书稿没有写出来,常用的词是“赍志而没”,听起来怪吓人的,好像死的时候,肚子跟孕妇似的,里面是一摞子书稿。有的是真的,有的就那么一说。要是这个人只活了三四十岁,还可信,要是活了六七十岁,他的儿女可以信,旁人是不信的。一辈子能有多忙,连部书稿都写不出来?我说加个“为”字,就是说,要做出来,要将你的才、学、识展示给世人看,别在追悼会上落下遗憾。孕妇是能把孩子生下来,你那个“赍志而没”,谁也看不见。
对同学们来说,眼下是学的阶段,主要是读书,打底子。这个时候,读书要乱,要杂,有兴趣的,都可以看看。史学研究,过去多注意政事,变法啦,战争啦,再就是典章制度。近世以来,加大了对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的关注。在大同,更应当关注边疆沿革、边防经济。我写《边将》时,因为当时主持隆庆和议的宣大及山西总督王崇古,是蒲州人,我的老乡。运城的盐池,明代属蒲州管。当时边防粮秣的解决办法,有一条是用盐引解决,就是你给边防上输送了多少粮食,给你多少盐引,你就可以做盐的生意赚大钱。聪明的商人并不真的赶上马车往边防送粮食,而是雇上人在边防一带开荒种地打粮食。这儿交了粮食,领下盐引去那边进盐,一本万利,没有不发财的。可是我当时看书少,找不下盐引换粮食的具体史料,也就没写。这些日子看《典故纪闻》,对盐引沿革、兑换数据,都有清楚的记载。只能说我当年看书,还是不杂,还是不多。
刚才说做学问要的是才、学、识,还可以更简略地说,做学问凭的是两力,一是记忆力,一是联想力。看得再多,记不住跟没看是一样的;记住了,却都是一个一个的点,连不成线,撑不起面,也不行。要连成线撑起面,靠什么?靠的是联想的能力。这个联想力凭的是什么?叫我说,凭的是活跃的思维。这上头,一下子想不起个好例子。这次讲学,本来就有推荐《边将》的意思,我就举这本书里的一件事吧。
右卫围城期间,杜如桢和二嫂去偏院书房,看望爷爷杜俊德。闲得无聊,爷爷就出了个谜语让叔嫂二人猜。谜面是“象喜亦喜,象忧亦忧”,谜底是“镜”。猜的过程中,叔嫂二人相互打趣,很是亲近。过后爷爷说了这个典故的出处。舜的父亲是个瞎子,母亲很坏,一心要害死舜。舜上房苫草,他们就掀掉梯子放了把火,舜拽着斗笠跳下来逃走。家里有井,水不旺了,舜下去淘。下去没多久,父母就从上面倒土,要将井填实闷死舜。幸亏舜一下去挖了个偏窑,相当于地道,上面土倒下来,舜就顺着地道逃走了。纵然如此,舜与那个叫象的弟弟,仍然相亲相爱,所谓“象喜亦喜,象忧亦忧”,从不嫌弃。
杜如桢兄弟三人,都是卫所的青年军官,每天早上值守前,都要去正房向父母请安,古人的礼节,叫晨昏定省。母亲这个人,有点偏心眼儿,喜欢老二老三,对老大一个眼角都看不上。每天见了面,心情不好了,就训斥一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气不打一处来。问安时,杜如桢住正院,常是先去,出来往往会遇上大哥正要进去。若母亲心情好,他就给大哥做个笑脸,若母亲心情不好,就做个苦脸,这样大哥就知道要小心伺候,别招母亲斥骂。爷爷说了谜语的第二天,请安时母亲心情好,如桢在门洞见了大哥,就做了个笑脸。他骑上马去城门值守时,路上想起了爷爷说的“象喜亦喜,象忧亦忧”,如桢就想,上房苫草,下面点火,拽着斗笠跳下,还有情可原——天热戴个斗签避暑,天阴戴个斗签防备下雨;淘井下去,先挖个偏窑作地道,不就等于知道父母要加害于他吗?以狠毒之心猜测父母,先就是大不孝,是要受天谴的。会是什么原因呢?如桢一想就想到了他与大哥的关系。对,一定是那个叫象的弟弟,给哥哥传递了什么信息。说父母要害人,也是大不孝,于是便用表情暗示哥哥,没事还是有危险,哥哥就会及早做出防备。谜语、请安、脸色,这三点连在一起,就颠覆了两千年来,世世代代对“象喜亦喜,象忧亦忧”的定论。我是用在小说里,化成了故事情节。就是写篇文章发表,也有地方登的。
最后还想说说表达的能力,就是要有文字上的功夫。你们还年轻,谈这个话题有些早,不过这种事,早点知道比晚点知道好。我有个建议,就是在你们这个年龄,一定要喜欢文学写作,小说、散文、诗歌,喜欢什么写什么,能发表就发表,不能发表也要不停地写。图个什么呢?什么都不图,就图个笔下通畅,拿起笔不生涩。要么坚持写日记——这个办法最灵,生活中遇到的事,很是芜杂,你能用笔清晰地写下来,这是大本事。我是写小说出身,后来做起学问,也还有点成绩。我有个三弟,说起来跟大同还有点缘分,是大同师范学校中文科毕业的,现在也是个作家。好多年前,弟兄俩谈起写作,他说,二哥呀,你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能取得成功吗?我以为他要夸我如何勤奋,如何爱买书;说我聪明是不指望的,因为他常说我们老韩家的孩子都不是多么聪明,只能说还都本分。结果他说什么呢?他说你的成功在于,作家没有你这么好的学问,学者又没有你这么好的文笔。我让你们写文学作品,就是为了让你们早早就练下一手好文笔,将来写什么都不吃力。
我是老二,那个是老三。还有个老四,南开大学毕业,如今在法国一所高校教书。前不久弟兄们在“老韩家群”里交流,不记得我说了个什么,老四说老二这个人呀——我们相互之间,都叫老几老几,不叫哥呀弟呀——他说老二这个人呀,有中国古代文人的特质,以良心顶天,以学问立地。我老伴回复说,只有老四这样夸二哥。这话说我,我是担当不起的,但是我今天在这里,把它送给同学们。是的,往后的岁月里,希望同学们能做到,以良心顶天,以学问立地。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儿。总结一下,前面说的就三句话:读书要杂乱,思维要活跃,文笔要通畅。再加上这两句,以良心顶天,以学问立地。愿以这几句话,与同学们共勉。
2019年12月14日,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