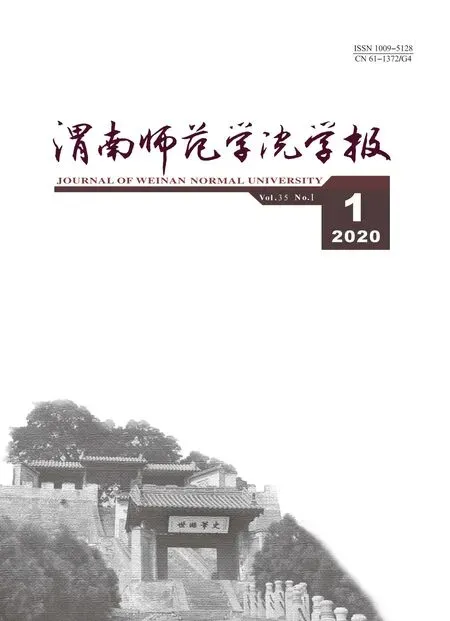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本《太史公书知意》标点商榷
徐 兴 海
(江南大学,江苏 无锡 214122)
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由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标点,2009年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刘咸炘《史记》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许多创见,是对古来《史记》研究的一次清理,成为《史记》研究者的必备书。刘咸炘《太史公书知意》是其巨著《推十书·论世》的首篇,也是“四书知意”之一,1919—1929年间完成。刘咸炘发明主旨谓:“吾既撰《汉书知意》,复究《太史公书》,亦作《知意》六卷,体与《汉书知意》同,偶涉考证、论事、论文,必与义例有关。是书前人议论甚多,故辨驳加详。”并针对传统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探史义是史学研究的核心,明史法是探史义的关键、是史学研究的基础,挈史旨是史学研究的归宿等一系列观点。此书乃《史记》研究之必备书。此书作为《推十书》之一种,1926—1937年间刊行过,然流布不广,且未加标点,难为广众所利用。
此整理本本为《史记》研究提供读本,然而因为此整理本标点、校对中存在一些问题,或因不知姓名,或因不明文献,或因不具常识,或因不明文意,或因失校而致误多有所在,反而给读者造成许多误解,现就50多处问题分为11类提出商榷以就教于方家。
一、不知姓名而误断
(一)上海本第10页第13行“一、辨真伪”
《史通·古今史篇》:续《史记》诸儒有刘向、歆、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
商榷:“梁审肆、仁晋、冯段肃”,四人误作三人,名字相混致断句误,当作“梁审、肆仁、晋冯、段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王煦华标点本浦起龙《史通通释》于此段标点为:“《史记》所书,年至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浦起龙于“段肃”下有注:“《班固集》作‘段肃’,《固本传》作‘殷肃’。”[1]338可证“段肃”为一人,而不是“冯段肃”。又浦起龙释文:“刘向等十五人:此十五人并在班史未作之前。……晋冯、段肃见《后汉·班固传》。”[1]339浦起龙认定此句所举为十五人,若依上海本断句则为十四人,明显少一人,则可推断标点致误。又浦起龙此处明示“晋冯、段肃”为二人。 “冯”字当上属,作“晋冯”。查中华书局本《后汉书》:“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东阁,延英雄。时固始弱冠,奏记说苍曰……京兆祭酒晋冯,结发修身,白首无违……”[2]1331是为“晋冯”。班固又推荐:“弘农功曹史殷肃,达学洽闻,才能绝伦,诵《诗》三百,奉使专对。”[2]1332是“段肃”作“殷肃”。
(二)上海本第26页第7行《五帝本纪》“按语”
黄帝、顼、喾及虞、舜,何可与后稷、武王同例?
商榷:“虞舜”乃一人,不可断开为二人。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五帝本纪》称虞舜为一人,“虞舜者,名曰重华”[3]31,“四岳咸荐虞舜”[3]33,何以称舜为虞舜?“虞舜者,名曰重华”下《索隐》:“虞,国名,在河东大阳县。舜,谥也。”是说“虞”是国名,“舜”是谥号。即舜,帝舜、大舜、虞帝舜、舜帝皆虞舜之帝王号,故后世以“舜”简称之。
(三)上海本第93页第7行《伯夷列传》“而说者曰”至“盖有许由冢云”
盖许由、巢父,卞随、务光、石户之农及越王子,搜诸事皆道家寓言,所谓厉怜王之论也。
商榷:“越王子搜”即越王错枝,一作孚错枝,《庄子》称王子搜,是战国时期越国的君主。《庄子·让王》:“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国无君,求王子搜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熏之以艾。乘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4]253“子搜”是为一人,“子”“搜”之间不当断开。
(四)上海本103页第15行《仲尼弟子列传》“梁曰”
设曰弟子籍以受业先后为序,则颜路、曾晳之受业,岂后于其子邪?
商榷:“颜路”指颜渊、子路,为二人,“颜路”应当断开。查阅上海本上下文,颜渊。子路(季路)均断为二人。
(五)上海本128页第15行,《魏其武安列传》
高祖之侯泽释之也,以为将有功。而台、产之并侯者,以父泽死事。
商榷:查中华书局本《史记·吕太后本纪》,“泽”为吕泽,“释之”为吕释之,乃二人,吕释之为吕文次子,吕泽之弟,故此处当分标为“泽、释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亦分列为二人,周吕侯,吕泽;建成侯,吕释之。[3]888-889又《太史公书知意》下文之“父泽”似已提示泽为另一人。此处将吕泽、吕释之之封,与吕台、吕产之封相排比;吕台、吕产为二人,则吕泽、吕释之亦当推断是二人。
(六)上海本128页第19行,《魏其武安列传》
是故长君少君至长安,而绛、灌以为我辈他日命且悬两人手,则文帝示私外戚之祸,可胜言哉。
商榷:“长君少君”当断开为长君、少君。查《吕太后本纪》长君、少君为二人,又《外戚世家》将长君、少君分别介绍:“窦皇后兄窦长君,弟曰窦广国,字少君。”[3]1973又下文 “窦长君、少君由此为退让君子,不敢以尊贵骄人”[3]1974,亦指此二人,当可自证。
(七)上海本128页第20行《魏其武安列传》
是故窦太后趣侯王信,政君敕让下传之嚆矢也。
商榷:“下传”其意不明。查《太史公书知意》辛未本,“下传”当为“丁傅”,恐字误而上海本未校出。“丁傅”当为二人。刘咸炘此处所引为包世臣《艺舟双楫》,查包书得知正是“丁、傅”。据中华书局标点本《汉书·哀帝记》“丁”为丁姬家族,“傅”为傅太后家族:“立皇后傅氏。……丁姬曰恭皇后。……追尊傅父为崇祖侯、丁父为褒德侯。”[5]335乃是二人。又中华书局标点本《资治通鉴·汉纪》:“丁、傅弟子闻之,使人上书告。”[6]1078“丁、傅宗族骄奢,皆嫉傅喜之恭俭”[5]1082,亦可证“丁傅”为二人。
(八)上海本130页第26行《李将军列传》
《论》之称许,亦张、季、冯公之等耳,未尝有用广已足御匈奴之意也。
商榷:“张季”是一人,不当断为二人。《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张廷尉释之者,堵阳人也,字季。”[3]2751“张季”即张释之,“冯公”即冯唐。
(九) 上海本第160页第22行《太史公自序》传“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索隐》曰:史以黄帝为首,而云述陶、唐者,以《尚书》雅正,故称起于陶、唐。按:此说是也。崔适谓自黄帝始,乃旁记入正文,下文已言维昔黄帝,此何待言?此言乃可笑。然则陶、唐以来,亦何待言邪?
商榷:“陶唐”指尧一人,尧之号为陶唐,故不当断为二人。尧十三岁封于陶(山东菏泽市定陶区)。十五岁辅佐兄长帝挚,改封于唐地,号为陶唐氏。《五帝本纪·正义》“帝尧”引徐广曰:“号陶唐。”[3]15
“史”指《史记》,似当标作《史》。
(十)上海本第164页第1行《太史公自序》传“欲详知秦楚”之事条
此《序》独举周緤,与《刺客》独举曹豫,《平津主父》独举平津同,皆以撮要,故略。
商榷:据《史记·刺客列传》曹沫、豫让为二人,事迹分列,故“曹豫”当断开。此处误标恐受“独举”一词影响而误判;又“周緤”为一人,“平津”为一人,故而推论“曹豫”亦为一人。
二、因不明文献而致误者
(一)上海本第40页第12行《吕后本纪》
《文心雕龙·索隐》谓当立《孝惠纪》,而以吕后两少帝附之。
商榷:查无《文心雕龙·索隐》一书,当是《文心雕龙》与《史记索隐》并列,二书皆有此主张。查刘勰《文心雕龙·史传》是有此意:“及孝惠委机,吕后摄政,史班立纪,违经失实,何则?庖牺以来,未闻女帝者也。汉运所值,难为后法。牝鸡无晨,武王首誓;妇无与国,齐桓著盟;宣后乱秦,吕氏危汉:岂唯政事难假,亦名号宜慎矣。张衡司史,而惑同迁固,元平二后,欲为立纪,谬亦甚矣。寻子弘虽伪,要当孝惠之嗣,孺子诚微,实继平帝之体;二子可纪,何有于二后哉!”[7]65-66又《吕太后本纪》标题下之《索隐》亦有同样主张:“吕太后以女主临朝,自孝惠崩后立少帝而始称制,正合附《惠纪》而论之,不然,或别为《吕后本纪》,岂得全没孝惠而独称《吕后本纪》?合依班氏,分为二纪焉。”(1)中华书局2013年版《史记》于《吕太后本纪》卷后有《校勘记》:“此条《索隐》原无,据耿本、黄本、彭本、《索隐》本、柯本、凌本、殿本、《会注》本补。”可以证明《文心雕龙》《史记索隐》皆“谓当立《孝惠纪》,而以吕后两少帝附之”。
“吕后两少帝”指吕后与刘恭、刘弘两位少帝,当断开为“吕后、两少帝”为是。
(二)上海本43页第11行《三代世表》,以《五帝系牒》《尚书》集《世纪》
崔据《索隐》谓本作《五帝德帝系姓》,今脱三字,是也。
商榷:《五帝德》《帝系姓》为二书,中华书局标点本《五帝本纪》“太史公曰: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3]46其中两处均将其作为两种书,又中华书局标点本上文所引之《索隐》文也如此标点,是上海本合二书为一,误。
(三)上海本第55页第6行《礼书》
然改正朔、封禅,已详《封禅》与《历书》,而《封禅书》之《论》,又曰有司存是,其意又不欲因书而见也。
商榷:查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封禅书》作“有司存”, “是”属下句,充当主语。《封禅书》“太史公曰”:“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3]1404“是”字当下属,乃承接转折之词,引出结论。此处乃因未检《史记》而致误。
(四)上海本第94页第6行《伯夷列传》“而说者曰”至“盖有许由冢云”
近儒宋翔凤则谓由与夷与阳一声之转,许由即《书》之伯夷,《尚书大传》之阳伯伯夷封许。
商榷:“由与夷与阳”当断开为“由与夷、与阳”,指“由与夷”“由与阳”都是一声之转。又,“之伯夷”与“之阳伯”是排比句,宋翔凤认为许由即《尚书》之许由,亦即是《尚书大传》之阳伯,“之阳伯”当句断。而“伯夷封许”乃是另一句。查梁运华点校本宋翔凤《过庭录》卷四《尚书略说》上,“四岳”条,“由与夷、夷与阳”以顿号断开,另外,“《大传》之阳伯”,与“伯夷封许”,文字本非连接,亦可知不当标为“《尚书大传》之阳伯伯夷封许”:
云八伯者。尚书大传称阳伯、仪伯、夏伯、羲伯、秋伯、和伯、冬伯。其一阙焉。郑注以阳伯为伯夷掌之……春秋左氏隐十一年。夫许。太岳之胤也。申、吕、齐、许同祖。故吕侯训刑称伯夷、禹、稷为三后。知太岳定是伯夷也。墨子所染篇。吕氏春秋当染篇。并云舜染于许由、伯阳。由与夷、夷与阳并声之转。大传之阳伯。墨、吕之许由、伯阳。与书之伯夷正是一人。伯夷封许。故曰许由。史记尧让天下于许由。本庄子。正附会咨四岳、巽朕位之语。百家之言。自有所出。[8]69-71
(五)上海本97页第20行《伯夷列传》“君子疾没世”至“后世哉”
其人见六艺,即为考信,而特表之以其传,曰:此变例也。
商榷:《伯夷列传》中伯夷事迹全自轶《诗》之“传曰”,与《史记》中其他人物不同,故而谓之“特表之”,于是成为《史记》之变例。《伯夷列传》:“其传曰: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3]2123上海本将“传曰”二字断裂,分属上下句,则与《伯夷列传》文不合。此不明《史记》文献来源而致误。
(六)上海本第114页《吕不韦列传》“孔子之所闻者”
梁曰:不韦乱民也,而以闻许之,岂因其著书乎?《黄氏日钞》《经史问答》并言其误。按:乱民何待言。《索隐》已明引《论》语为证,何必致疑。
商榷:查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吕不韦列传》“太史公曰:……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3]2514此处当为《集解》引证《论语》之《颜渊篇》第十二子张问,而非《索隐》。刘咸炘误,而上海本未校出,沿误。
“论”指《论语》,不当独此一字加书名号,乃此处误将《论语》作《史记》之“论赞”语。
(七)上海本162页第1行《太史公自序》传“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韩世家语》不详,或简脱,或别有据,己所不知,何可以疑古人?
商榷:《史记》有《韩世家》,无《韩世家语》,误标。“韩世家语”,谓《韩世家》所言所记也。
三、不明篇名而误断者
上海本第11页第25行《序论》“一、辨真伪”
褚生之时已亡,而褚据《自序》,传补之者凡二篇,曰《三王世家》《日者列传》,而今本前半又不出褚生。
商榷:《自序》当为《自序传》,且“传”字入下句遂致文意不通。此句主语为“褚”,褚依据司马迁《自序传》“补之”两篇,而非“传”补之两篇。司马迁之《自序》,刘咸炘称之为《自序传》,于本书列传末专门列“太史公自序传”一条,反复说明司马迁《自序》当为《自序传》,为七十列传之一。
四、不明刘咸炘所云而致误者
(一)上海本第50页第17行《秦楚之际月表》“岂在无土不王”至“岂非天哉”
要之,史表所以明事势,非以褒贬一切。推测争论,皆无谓徒劳耳。
商榷:当断句于“褒贬”。“一切”上属,则下句无主语,而刘咸炘关于史表功用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一切推测争论,皆无谓徒劳耳”。刘咸炘论点是:“表之用,所以齐不齐”,而非寓含褒贬。名‘秦楚’者,正以上接六国,下接汉兴耳。此乃事之自然,非有抑秦尊汉之意。钱氏所说,皆是支词。上海本标点为“非以褒贬一切”,似上句通而实全句不通。
“史”指《史记》,似当加书名号《史》。
(二)上海本第60页第14行《律书》
言疏略者王若虚。曰:多叙兵事,何关于律。若果《兵书》,安用许多律吕事?梁曰:律为兵家所重,故史公序律先言兵。昔贤谓《律书》即《兵书》,是已。然言用兵之事几七百言,未免于律意太远。且止述历代用兵之事,而不详其制,又不及汉景、武,毋乃疏乎?
商榷:“言(律书)疏略者”,除王若虚外,尚有梁玉绳,谓“毋乃疏乎?”故而断为“言疏略者王若虚”有误。“言疏略者”为总领,而下分列王若虚与梁玉绳之观点,故当标为“王若虚曰”与“梁曰”并列。
(三)上海本第63页第11行《封禅书》“盖有无其应”至“是以即事用希”
杨慎曰:此一篇之纲要也。曰无其应而用事,后所论秦始皇曰:岂所谓无其德用其事者邪?应此曰:虽受命而功不至。谓未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所谓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应此曰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至梁父,谓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所谓武王克殷,天下未宁而崩,周德之洽,惟成王亦应。此以汉高比武王,则德犹未洽也。
商榷:杨慎指出封禅有几种情况,有“无其应而用事者”,有“虽受命而功不至”,有“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杨慎指出封禅与效果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某某应此,某某应彼。行文句式则以“应此”为排比词。“应此”者,与此相对应也。据此,则应以“应此”为结句;与“亦应此”排比。而上海本以“应此”为起句,则将应该对应者错移,将所应对应者误为上一事例。又,《封禅书》开端司马迁就提出封禅有回应的问题:“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给,是以即事用希。”[3]1355杨慎之分别排列与司马迁所列正好一一对应。此一段似应标点为:
杨慎曰:“此一篇之纲要也。曰‘无其应而用事’,后所论秦始皇,曰‘岂所谓无其德用其事者邪?’应此。曰‘虽受命而功不至’,谓未有天下而政不及泰山。所谓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应此。曰‘至梁父矣而德不洽’,至梁父,谓已有天下而政及泰山,所谓武王克殷,天下未宁而崩,‘周德之洽,惟成王’亦应此。以汉高比成王,则德犹未洽也。”
(四)上海本第66页第11行《平准书》“林駉曰”
统观全篇,史公未尝非卜式自输财,固其忠武帝,苦费而牟利。宏羊、孔仅等之搜括于民,非式启之也。天下不乐输县官,乃教之不善,如式者少也,而括取之,则病民矣。史公既引式言以著盐铁租船之害,又引式言以著宏羊之罪,未有非之之意,后儒争詈之何哉?
商榷:按此标点,则“史公”为主语,“未尝非”一层,“固其忠武帝”一层,“苦费而牟利”一层,三层均是“史公”之作为,岂不谬哉?刘咸炘论证主旨,乃司马迁未尝否定卜式通过自输财以达到强固其忠君的行为,此一点于段末再申述之。刘咸炘同时指出,汉武帝苦费而牟利,一层;桑弘羊、孔仅等搜刮于民,二层,均非卜式开启之。“苦费而牟利”者非卜式,而是汉武帝。而依上海本 “史公未尝非卜式自输财,固其忠武帝,苦费而牟利”之主语为“史公”,则“史公”“固其忠武帝”,史公“苦费而牟利”,岂不是意思颠倒?
(五)上海本第73页第12行《管蔡世家》
王曰:按《曹世家》只僖负羁、公孙疆两事耳,相映成文,国有与立,于斯可见。观于《论赞》,史公之意亦显然矣。按:此说亦非本有此事,岂故为相映乎?桐城家议论,往往以事之自然为文之妙。
商榷:“此说亦非”当断开,此为刘咸炘按语之结论。刘咸炘指出《曹世家》僖负羁、公孙疆两事为本有之事,并不如王说,王说乃桐城派议论,认为司马迁如此写乃为了相映成文,故为相映。刘咸炘进一步批评桐城家议论,往往以事之自然为文之妙。而刘之“此说亦非”, “亦”承接上文,上文批评恽敬《大云山房文集》“此说甚曲,求之过深耳”。此处若不断开,则所云不知其意。
(六)上海本第82页第20行《外戚世家》“黄淳耀曰”
王氏谓薄、窦、王、卫各为篇,皆史公原文。亦谬。诸段中错出,诸后妃本一篇,书后世提行,取易明耳。方氏从而圈断之,竟以为各自为篇,则窦太后后叙慎夫人、尹姬,卫后后叙王、李夫人,皆有不整齐之讥矣。
商榷:刘咸炘批评王氏“亦谬”、方氏“竟以为(《外戚世家》各后妃)各自为篇”。刘认为《外戚世家》中各后妃交错出现,本为一篇,可是后来印行的格式有变,逢后妃则提行。后人不明,乃以为各自成篇,误解则由此出。上海本标点未明“诸后妃本一篇书,后世提行”,此为关键。似当标点为:
王氏谓薄、窦、王、卫各为篇,皆史公原文,亦谬。诸段中错出诸后妃,本一篇书。后世提行,取易明耳。方氏从而圈断之,竟以为各自为篇,则窦太后后叙慎夫人、尹姬,卫后后叙王、李夫人,皆有不整齐之讥矣。
(七)上海本第91页第6行《伯夷列传》
史体每篇一义,先以一时代之事,罗于胸中,而分篇说之。举一事为一篇,或数事为一篇,旁见侧出数十篇,书如一篇,非拘拘为一人立一传,非拘拘为一人备始末,此之谓圆而神。
商榷:“旁见侧出”一句,“数十篇书如一篇”一句。刘咸炘此处解读为何说《史记》“圆而神”。关键在理解“旁见侧出”之意,此处指司马迁所创作的一种述史方法,又叫“互见法”,用此法,则可使“数十篇书如一篇”成为一个整体。上海本标点为“旁见侧出数十篇”,意则不同,乃是谓旁见侧出了数十篇。
(八)上海本第99页第15行《伯夷列传》“君子疾没世”至“后世哉”
彼无异故,凡于中权余甚惑焉一语,铸成错耳。不知自是邪非邪以上,皆太史公设为或人难端,所谓余者,代或人自余焉耳,其下则史公之折之也。
商榷:“所谓余者,代或人自余焉耳”,文意不通。“或人”,指不定人,所谓之“余”,即代“或人”。当断于此。“余焉耳”即“余甚惑焉”,刘咸炘谓自“自余焉耳其下”之下皆司马迁折断之语。明此,则“自余焉耳”与“其下”不可断开。
(九)上海本126页第3行《扁鹊仓公列传》
学术生计,本史所当书。
商榷:“学术”与“生计”当断为二,因刘咸炘将“学术”与“生计”各执一概念,分而论之。如其论“学术”:“此节略说古今世变、文籍原流、学术异同”,如“条辨学术同异”,如“夫史备学术,岂论文之高不高。”再如其论“生计”:《货殖列传》:“生计者,史之大事,本不容不书,非必特有用意。”
(十)上海本144页末行《酷吏列传》
按:王谓深贬郅都,是也。至说侯封不数之意则迂曲,不明封,殆事少无传耳。其论子长节次,用意则甚简明,反过于方评。
商榷:刘咸炘谓王之评说,节次、用意二者皆简明。王即王鸣盛。查刘咸炘所引王鸣盛其论曰:“次叙宁成、周阳由……末又结之曰……见酷吏多,而政治坏在武帝世也。又次赵禹,而言禹‘晚节,吏愈严,而禹治反名为平’,其用意如此。”“次”“末”“次”皆是节次;“见”如何,“其用意”皆是用意。
(十一)上海本161页倒3行《太史公自序》传“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传中意指隐微,往往繁迂其词乃能达,必责此数语中以发明,又愚而不当,义浅词庸,毋乃易言。过以奇求古人,遇不奇则以为庸,岂百三十篇篇篇皆奇邪?
商榷:“毋乃易言过”当断开。“义浅词庸”,刘咸炘引用王拯语:(褚少孙)“于诸纪、表、志所言,大都义浅词庸”。既如此,则容易言其过失,故当断于“过”字。上海本断于“言”,则无宾语,言何?刘咸炘接着批评“以奇求古人”,如此方与“遇不奇则以为庸”相接。
“陶唐”为一人,不当断开为二人,本文前已说明理由。
五、断句破坏文气者
(一)上海本第34页第10行《秦始皇本纪》“太史公曰”以下
今取原书寻绎上篇,是专赞始皇,而以陈涉六国相形,以见其不施仁义,亡国亦易。中篇亦数始皇罪恶,而下半欲归罪二世。下篇则兼责子婴。其次第甚明。
商榷:此处所标三句实为一句,排比句。“寻绎”是全句主语,当断开;“上篇”“中篇”“下篇”是并列谓语。全句文脉清晰,是排比句式。如上海本标点,则隔断文气,意义不明。
(二)上海本第47页第7行《六国年表》传曰“法后王”段
上治民,莫善于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
商榷:当断句于“何有”。 “何有”,有什么?此处为排比句,“能以礼让为国”如何,“不能以礼让为国”如何。此句上文为:孔子曰“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此处申说老子主张,强调以礼治国,设若能够以礼治国拥有什么呢,不能以礼治国则将如何对待礼呢?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上海本标点文意则含糊不清。
(三)上海本第55页第10行《礼书》
《评林》引杨慎曰: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论》之文;自治辨之极也,至刑措不用一段,《议兵》文。自天地者至生之本也至终,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马讥其率略芜陋,其为褚少孙补明矣。
商榷:“《礼论》之文”当断开。乃杨慎之论,发明《礼书》之自,谓某至某引自某文,某至某引自某文,是排比列出,“《荀子·礼论》之文”“《议兵》文”“《礼论》之文”皆是排比,故“皆《礼论》之文”当断开,以与上相应。而“太史公曰”一段,正是从“至矣哉”开始。《索隐》说明其源自曰:“以下亦是太史公取荀卿《礼论》之意,极言礼之损益,以结《礼书》之论也。” 杨慎的批判正是针对太史公曰一段,谓同是荀卿《礼论》,不当将“至矣哉”一段断出,而加“太史公曰”,认为这正好印证了小司马对《史记》“率略芜陋”的批评,也正说明了这是褚少孙的补充。
从以上分析可知,杨慎的观点谓同是出自荀卿《礼论》,不当将“至矣哉”一段另外断出,而加“太史公曰”。如此一来,“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便当断为“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乃断”不当属上句。
(四)上海本第82页第11行《外戚世家》
黄淳耀曰:首论归之于命,今以其所载考之,信矣。其为命也,宠辱推迁,祸福倚伏。当其贱也,尘埃不足以喻其微;及其贵也,天霄不足以喻其远。虽万乘之君,爱憎予夺,且莫能自主也,而况下之者哉。信矣,其为命也。
商榷:“信矣,其为命也”于此段两次出现,上海本则将第一处割裂,“信矣”归上句,“其为命也”归下句。然上海本于下文有“信矣,其为命也”,不意此处乃呼应上文,致使语气不畅。
(五)上海本第94页第16行《伯夷列传》“孔子序列”至“何哉”
此书之意,不专在表让。自黄帝迄于汉武,所褒贬发明多矣,岂专重一让字。若云规切,当时汉武又无不让之失。且果表让,何不以尧、舜冠本纪邪?
商榷:此处刘咸炘猜度司马迁写此传的意图,非为规劝当时,况且汉武帝又没有不让的过失。“当时”上属为妥。
(六)上海本158页第2行《货殖列传》“由此观之贤人深谋”至“归于富厚也”
方曰:岂真能守信死节,特深谋议论时云然耳,盖谓赵绾、王臧之属。隐居岩穴,设为名高,谓公孙宏之属。以士大夫而阴怀欲富之心,则与攻剽椎埋,赵女郑姬无以别耳。
商榷:“王臧之属”句断,则使全段文意不通。方之论,“谓……谓”排比,“谓公孙宏之属”是主谓结构,当有如何如何的表述语作补语。如断于“之属”,上句似可通,而下句补语“以士大夫而阴怀欲富之心”则无所承接。而且,“设为名高”后置分号为妥。
“赵女郑姬”指赵国之女,郑国之姬,当断开,标为“赵女、郑姬”。
六、因不明文意,标点误置
(一)上海本第8页第13行《序论》“辨真伪”引吕祖谦《大事记》文
以张晏所列亡篇之目校之,或其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无书也。其一曰《景纪》篇,具在者也。
商榷:《大事记》将所列亡篇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篇具在”,一是“草具而未成”。当断句在《景纪》,“篇”字属下,“《景纪》”即是上文所说“篇具在者也”。初看上句无误,然下句与“篇具在者也”无对应。
(二)上海本第23页第7行《序论》“较班范”刘咸炘按语
事变之自然,如衡之左右倚,相矫者,所以救偏弊也。
商榷:“倚”字上属,似为可通,谓车衡左右相倚,然下句失去“倚”字,则意义不明。全句是说:事变之自然,如同车衡之一左一右,相互倚仗而互相矫正,其所以这样是为了纠正偏颇的弊病啊。故而当为“倚相矫者”,指相互矛盾对立,正是承接上句“衡之左右”,解释为何设有左右的道理。
(三)上海本第25页第9行《太史公书》
《史通·六家篇》谓迁作百三十篇,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自是汉世史官所续,皆以《史记》为名。迄乎东京,著犹称《汉记》。按此则本名之义,知几已不知其谓。迁自目《史记》,固非事实。续者之名《史记》,盖以已非太史公,故不袭其号而用通名,是亦理之所有。
商榷:“知几已不知”,当断句,“迁自目《史记》”为“其谓”之谓语。此句回应上句“《史通·六家篇》谓迁作百三十篇,因鲁史旧名,目之曰《史记》”。刘咸炘指出刘知几已经不知道司马迁之作原名《太史公书》,而谓司马迁自己命名所著为《史记》。刘知几是错的。“其谓”当指刘知几所言。
(四)上海本第28页《夏本纪》之第7行“相崩,少康立”
此不书羿、浞事,而见于《吴世家·索隐》以为疏略之甚。
商榷:羿、浞事非见于《吴太伯世家·索隐》,而是载于《吴太伯世家》,认为《夏本纪》“疏略”的不是《吴太伯世家·索隐》,而是《夏本纪·索隐》。如此断句使人误解而又含糊不清。查羿、浞之事见于《吴太伯世家》:“伍子胥谏曰:‘昔有过氏杀斟灌以伐斟寻,灭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缗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为有仍牧正。有过又欲杀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于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于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后遂收夏众,抚其官职。使人诱之,遂灭有过氏,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3]1496《夏本纪·索隐》认为羿、浞事当记于《夏本纪》。《夏本纪》“子弟少康立”句《索隐》云:“然则帝相自被篡杀,中间经羿浞二氏,盖三数十年。而此纪总不言之,直云帝相崩,子少康立,疏略之甚。”[3]86徐文靖《竹书统笺》进一步解释说:“盖史公之意不与羿浞以代夏,故详于彼而略于此也。”如果检索《吴太伯世家·索隐》,则不会如此误断。
(五)上海本第37页第24行《项羽本纪》“汉之元年”刘咸炘按语
登本纪本非与元号,亦不可削古史,亦不以削元为贬,此皆后儒妄凿之论,史家不计是也。
商榷:此处讨论记述项羽之事为何用汉之纪元,用汉之纪元是否说明司马迁“不与楚而与汉也”。“与”者,赞同,称许。刘咸炘认为项羽列入“本纪”,本非称许之意,其元号自然不当削去,古代史文并不以削去元号作为贬损人物的手段。似当标点为:“登本纪本非与,元号亦不可削,古史亦不以削元为贬,后儒妄凿之论,史家不计是也。”上海本断裂文意,意谓项羽列入本纪本非称许元号,也不可削去古史,也并不以削去元号为贬损。则不词,不知所云。
(六)上海本第45页第4行《十二诸侯年表》
《春秋》本编年,鲁事已不待表,此特以《春秋》为纲而表六国,故不数鲁也。
商榷:当断于“鲁事”,即《春秋》为编年鲁事,《春秋》为鲁国编年史,何以“鲁事已不待表”?何以“不数鲁”?甚谬。故如此方通。此处刘咸炘赞同王拯所见,王拯曰:“史公殆以齐至吴为十二诸侯,而周、鲁不与焉。盖此表本《春秋》,以周、鲁为纲纪。《序》曰‘齐、晋、秦、楚微甚’。而不言鲁。又曰‘自共和迄孔子’,是以周、鲁为起讫也。”王拯关键语乃《春秋》以周、鲁为纲纪。亦即是以鲁事为编年,所以鲁国可以不出现,故当标点为“《春秋》本编年鲁事”。如上海本标点只说明《春秋》是编年体,而没有说明鲁国为什么可以不出现。
(七)上海本第48页第26行《事》传曰“法后王”段
是天意欲变古今之局。故史公发愤而作全书,言废书而叹者三:一厉王好利,恶闻已过;一孟子言王何必曰利;一公孙广厉学官之路,其义类可见矣。
商榷:“古今之局”,逗号,“发愤而作”当断开。当是“全书言‘废书而叹’者三”。“作”,创始之作。史公知天意欲变古今之局,故而发愤作《史记》。若标点为“作全书”意不通,且致使 “三”之举例句无主语。实则是全书总计“废书而叹”者三,若无此主语,则下无所承接。《史记》三处“废书而叹”分别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牒》,至周厉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3]509《孟子荀卿列传序》:“太史公曰: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3]2343《儒林列传序》:“太史公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3]3115
(八)上海本第81页第27行《外戚世家》
方曰:外戚专纪汉代,不宜称秦以前。《孝惠后传》后不宜及迎代王事,盖汉兴至居北宫,史记之。旧秦以前,尚略矣二句,末迎立代王语,则褚少孙补也。
商榷:“史记之旧”被断裂,则意思不明。方苞辨析《外戚世家》何处为《史记》之旧,何处为褚少孙补。方认为“盖‘汉兴’至‘居北宫’,《史记》之旧”;“秦以前尚略矣”二句,以及末尾“迎立代王”语,则为褚少孙所补。“汉兴”,《外戚世家》文字;“居北宫”,《外戚世家》文字。上海本未明此旨,将二者相混,且未查《外戚世家》无“旧秦以前尚略矣”之句,是:“太史公曰:秦以前尚略矣。”[3]1969故知上海本断句有误。“旧秦”,不词。又,此处加上引号所指方明晰。
(九)上海本第95页第10行《伯夷列传》“其传曰”至“怨邪非邪”
疏曰:传乃轶诗之传古者,承上,文辞甚明白。
商榷:“传乃轶诗之传古者”文意不通。意此句解释“其传曰”之“传”何谓?《疏》解答:乃是轶《诗》之传。《伯夷列传》“其传曰”之上原文:“余悲伯夷之意,睹轶诗可异焉。其传曰……”[3]2122其下则《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所载伯夷、叔齐故事。据此可知,“古者承上文”意指“其”乃指代上文之轶诗,承接上文。若谓“传”是“轶诗之传古者”,则意义不明。
(十)上海本第96页第18行《伯夷列传》“君子疾没世”至“后世哉”
《正义》谓引同明相照云云,乃明已著书,而万物睹此。皆不顾文义而横生支凿者也。
商榷:“万物睹此”文意不通。查中华书局本《伯夷列传》引贾谊文,“圣人作而万物睹”[3]2127,句读止于“睹”。又中华书局本此句《正义》谓:“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周易·乾·象辞》也。太史公引此等得感者,欲见述作之意,令万物有睹也。孔子殁后五百岁而己当之,故作《史记》,使万物见睹之也。”[3]2128同样断句于“睹”:“万物有睹”“万物见睹”。可知“此”字当下属。
(十一)上海本123页第5行《刘敬叔孙通列传》“方曰”
首载秦二世之善,其对以为面谀之征也。
商榷:断句当在“善其对”,秦二世称善叔孙通之对言也。而不是记载秦二世之善。查《叔孙通传》开篇未曾记载秦二世之善,仅有对叔孙通对各地农民起义的表态:“叔孙通前曰:‘诸生言非也……何足忧。’二世喜曰:‘善。’……乃赐叔孙通帛二十匹,衣一袭,拜为博士。”[3]2720-2721此即为“秦二世善其对”,此即为当面阿谀的证明。
(十二)上海本123页第9行《刘敬叔孙通列传》
此《传》中,如知上益厌之,与秦仪杂就之,不知时变。吾能为此,诚圣人也。诸语皆讥刺甚显。
商榷:“诸语”乃指:“知上益厌之”,“与秦仪杂就之”,“不知时变”,“吾能为此”,“诚圣人也”,共五句。排比而下,“不知时变”, “诚圣人也”,皆不当句断。 “诸语”承上而来,“诸语”不当另为一句。
(十三)上海本142页14行《汲郑列传》
然前郡守之治,后九卿之治也,其体各异,故分言之,且与张汤文深小苛武帝分别文法反对。
商榷:传中所述张汤“文深小苛”,与武帝“分别文法”为两事,为明晰,当以引号标识;因是两事,“张汤文深小苛”与“武帝分别文法”当以顿号分开。
七、因不明词义而误断者
(一)上海本第48页第21行《事》传曰“法后王”段
孟坚读之,乃不得其旨,归猥以为陷刑之后,贬损当世,是非颇谬于圣人。
商榷:“归猥”不词。“旨归”意为主旨,要旨,不当断开。此处批评班固不得司马迁之旨意,猥(苟且)以为司马迁受刑之后,是非颇谬于圣人。
(二)上海本第52页倒5行《建元以来侯者年表》
《殿本考证》齐召南曰:《汉表》列长平、冠军于外戚恩泽,甚失。平卫、霍之功,岂可以吕、窦、王、田例?《史记》叙功,不曰皇后弟姊子,可谓公论。
商榷:“平卫、霍之功”一句当断于“平”字,上属,即“甚失平”,谓很不公平。原标点“平卫、霍之功”,平定卫青、霍去病则不知所指,《史记》未载。“卫、霍”当为主语,属另一事。“平”者,公允、公平。此段讨论是否公允,是否公平。齐召南认为:“《汉表》列长平、冠军于《外戚恩泽》”,甚失公平。为什么这样说?“卫、霍之功,岂可以吕、窦、王、田例”。那么,他认为怎样才公平呢?“《史记》叙功,不曰皇后弟、姊子,可谓公论。”显然,“平”是公平。谓卫青、霍去病的功劳显然不能与吕、窦、王、田一例看待。“外戚恩泽”指《汉书·外戚恩泽侯表》,当加书名号。
(三)上海本第53页倒3行《汉兴以来将相大臣年表》
王曰:大事记遂为后人所宗,将相御史则百官表所由昉也。按:纪既题纲本,不须有大事表,此不过为大臣对照耳。
商榷:“题纲本”不词,“题纲” 当断句,“本”字下属。刘咸炘评价王拯之说,谓本纪既已为大纲,本来不须再有大事表,此种表不过是作为大臣行迹的对照而已。且 “题纲”即已是“本”,不须重复成“题纲本”,且断裂文意。
八、不明官职执掌而致误
上海本第62页倒3行《历书》“民是以能有信”
引《国语》者,太史公职在天官,历算与神仕相联,故著神事之古谊。王氏曰:“天官,史公家学,文与《禹贡》《周官》伯仲。”
商榷:太史公之职责既有天官,又有历算。故“天官”“历算”之间当用顿号,“历算”之后用逗号。天官、历算之事都与神仕,即神的祭祀有关。神仕者,以祭神事务为职事者。《周礼·春官·神仕》:“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犹鬼、神、示之居,辨其名物。以冬日至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致地示、物鬽,以禬国之凶荒、民之礼丧。”[9]48《太史公自序》追述祖职时谓历算乃其祖先所掌:“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后,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1]3285而《历书》谓:“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其后三苗服九黎之德,故二官咸废所职,而闰余乖次,孟陬殄灭,摄提无纪,历数失序。尧复遂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而立羲和之官。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1]1258故而太史公所执掌既有天官,亦有历算。如谓“历算与神仕相联”,则天官何不与神仕相联?
九、失校而致两段合为一段者
上海本第65页第7行《封禅书》自“齐威、宣之时”至“不可胜数也”
此明方士起于燕齐,非古所有。与巫咸之巫,孔子所言之禘,《尚书》《周官》之巡狩郊祀异。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方曰:大书之,与孔甲好神,三代而亡,武丁慢神,二世而亡相应。
商榷:“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乃《封禅书》文字,刘咸炘引方苞评语对此评论。故而“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是标题,上海本误置入上一段,乃失校而将两段合为一段。清人方苞认为司马迁也是“大书始皇封禅后十二岁秦亡,示无德而渎于神,为亡征也”。应该的段落划分是:
自齐威宣之时至不可胜数也
此明方士起于燕齐,非古所有。与巫咸之巫,孔子所言之禘,《尚书》《周官》之巡狩、郊祀异。
始皇封禅之后十二岁秦亡
方曰:大书之,与孔甲好神,三代而亡;武丁慢神,二世而亡相应。
十、有衍文,致文意不通
上海本第82页第6行《外戚世家》
篇目所以历叙古事用《国语》者,正通史所宜。此即正文,非《正叙论》也。
商榷:查辛未本《太史公书知意》为“非叙论也”,无“正”字,“叙论”无所谓正负之说。“正”字疑衍。
十一、不解文辞而致误
上海本104页第7行《仲尼弟子列传》“太史公曰”段
史公志在整齐而力不克,副于此篇尤显。
商榷:“副于此篇尤显”,不通。当断于“克副”。克副,相符、承受。克,承受;副,相称,符合。
上海本,全书150千字,依照原版格式排印,而加以标点,但对长的段落未加分段,且不用引号,不可谓不是遗憾。
该书说明不用引号的原因,谓“本次整理不使用引号,以免产生新的错误”。此说使人一头雾水,不知使用了引号,何以就会产生新的错误?那么,人们会问:加上标点之后,是不是也会产生新的错误呢?为什么单只是加了引号就会产生新的错误呢?该说明并没有解释。古籍整理中引号的作用是区别引用文字的起讫点,如何点断文字是一难,如何断定所引文字的起讫点更加难,尤其是引号的后端当置何处往往需要查对原始作者的原话,是一件十分麻烦的事。反过来说,有了引号,所引文字的起讫清楚,十分有利于理解原意。比如本文所引五之3,上海本第55页,第10行,礼书一段,不加引号致使文字不严密,从何而起,至何而止不明。若加引号,则当作:
《评林》引杨慎曰:“自‘礼由人起’,至‘儒、墨之分’一段,《荀子·礼论》之文;自‘治辨之极也’,至‘刑措不用’一段,《议兵》文;自‘天地者’,至‘生之本也’至终,皆《礼论》之文。乃断‘至矣哉’之上,加‘太史公曰’,此小司马讥其率略芜陋,其为褚少孙补明矣。”
古籍整理看似打打标点而已,实则非知识里手不敢妄下雌黄。今日在下不揣浅陋,班门弄斧,诚有惶恐,然意学问之道在于切磋,故而献丑,尚待方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