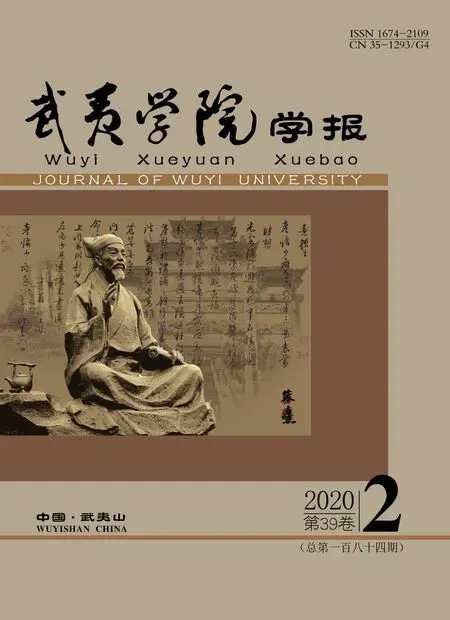论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的适用
(福建警察学院 刑罚执行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我国罪数理论借鉴于德国与日本,德、日刑法对罪数问题皆有明文规定,其学理研究往往依循立法。”[1]德日的罪数论规定在刑法条文里,罪数体系有法律依据,而我国的罪数理论并无刑法规定,罪数判断的适用遭到体系建构的障碍,罪数论的规范适用在司法实践层面的展开依靠着法官的智慧与法律适用能力。罪数理论是一个在解释论范畴里研究的问题,它不仅影响了我国刑法理论体系的构建,也影响了我国司法实践活动的开展。罪数论要解决的问题是当行为人触犯数个罪名时,法院是如何确定罪名的,刑罚是怎么作出来的。
一、问题的提出
罪数论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成为难题,一是因为“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从罗马法时代到今天,它依然是学理上无奈的痛,亦成为实务上深怕触碰的伤痕,这是一个无解的难题”[2];二是“因为关于罪数问题的学说或者实务,大皆直接遽下判断,鲜少说明其法理所在。”[3]在我国刑法未明文规定罪数问题且刑事裁判文书多数未对罪数问题进行说理的情况下,罪数理论在裁判文书中的适用就会变得混乱和棘手。有些刑事裁判文书虽有法理的释明,但只是寥寥数语,说理极其简单,甚至变成简单嵌套内容的文书。有的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过程中运用了刑法理论知识,出现了“竞合”和“牵连”,但只是简单的论述,如陈百泉、郁树良等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一案,“被告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虽系为了骗取国家税款,但法律明确规定,此行为应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且此罪的法定刑重于偷税罪;被告人的行为即使与该两罪发生牵连关系或竞合关系,亦应按择一重罪处断的原则处理。”[4]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中应有规范性的缺乏导致刑事裁判文书功能的发挥受到限制,不仅影响到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功能的展开还导致刑事裁判文书陷入模板化的泥沼中。
罪数论的释法说理是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刑事裁判文书法律规范适用的罪数需要被阐释清楚,却由于罪数论的体系发展问题遇到了困难。首先,由于我国刑法受苏联刑法影响深远,罪数问题的立法例有别于德日等国家,刑法条文中并未具体规定罪数形态,我国的罪数理论体系尚未构建且构建过程存有太多障碍与困难,这是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时理论上的第一重障碍,这导致在刑事裁判文书出现说理与否的尴尬,也会出现适用的混乱。其次,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如何说理是另一重障碍。从我国刑事裁判文书的发展过程看,刑事裁判文书一直跳不出往文书里堆砌证据与审理过程的窠臼。再加上罪数理论之争由来已久,既复杂又混乱,不是一时之间就能得到解决的,刑事裁判文书中的罪数说理问题的解决就难上加难。本文相关问题的研究是放在我国传统罪数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探讨的是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适用的原因及如何适用的问题。
二、罪数理论在刑事裁判文书中适用的原因剖析
罪数是指行为人犯的罪的个数,罪数论是指确定行为人所犯罪的个数及如何适用刑罚的理论概括。罪数的判断是法官量刑的基础,罪数理论的不规范适用将会影响到法定刑的确定,进而影响到刑事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我国刑法中虽没有关于罪数形态的具体规定,但在刑法的一些条文中可以找到有关罪数形态的规定,如刑法第89条第1款、刑法中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本文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等规定。罪数理论认为罪数形态包括想象竞合犯、法条竞合、牵连犯、吸收犯、连续犯等形态,其中最难区分的当属想象竞合与法条竞合的区分,罪数论的厘清功能是存在数规范的情况下,检讨究竟如何从该数规范中,对于评价对象的行为做完整之评价。[2]因此,刑事裁判文书中必须对罪数的规范与评价过程作出说明。
(一)刑事裁判文书厘清功能实现的要求
随着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改革的深入,刑事裁判文书对于大众而言的厘清功能越显重要,裁判文书的公开,就是在发挥裁判文书对外的沟通与厘清功能。犯罪人及其家属、每一位公众都是司法公正的感受者,要实现感受得到有温度的司法正义,光有文书的公开还不够,还需要法官履行好释法说法的职责。如果刑事裁判文书的说理是过于简单的、模糊的,不仅无法实现刑事裁判文书的功能,还会带来另一层误解。许多公众还停留在杀人偿命的同态复仇观念上,对于刑法条文及蕴含的法理一无所知,对于说理简单的刑事判决的结果更是带有偏见。如此,刑事裁判文书公开的意义就大打折扣。刑事裁判文书承载的厘清功能里还包含着法治教育的要求,法治教育要求让社会大众直接了解什么样的行为会得到刑罚的苛责,罪与非罪的界限通过案例可以感受得一清二楚。如,河南大学生“掏鸟案”,在新闻媒体报道之初,引起了网民的热议,许多网民并不清楚为什么抓了十几鸟获得如此重的刑罚,认为这又是司法不公的结果。当河南大学生“掏鸟案”的刑事判决书被放上网时,网民们才了解被告人闫某猎捕的12只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被告人闫某还加入“河南猎鹰兴趣交流群”,在网上兜售凤头鹰的时候还特意标明“阿穆尔隼”等信息。也就是说,掏鸟的大学生并非只是偶然的无意的捕鸟行为,被告人主观上是有故意的。[5]尽管这个案件还是存在其他争议,但最初社会大众对于司法不公的误解因为判决书的上传而得到澄清。这个案例说明,在复杂的、对社会影响较大的案件上,刑事裁判文书适时的法理阐明有助于社会大众加深对法律的了解,这也是刑法一般预防的实现方式之一。刑事裁判文书承担着释明的责任,罪数的说明是刑法苛以刑责的判断前提,把罪数说理加入刑事裁判文书中是文书厘清功能的必然要求。
(二)全面评价原则的遵循
全面评价原则系指对于刑法规定的各种罪行必须毫无遗漏地加以评价,以促规范与事实之间相互对应。全面评价原则与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是相依相靠的两个原则,是罪刑均衡在罪数形态下的具体适用原则。全面评价原则要求刑事裁判文书体现出全面评价的过程,事实层面与规范层面对应的体现不应只存在于法官内心中。全面评价原则的体现,有如卿太苏一案①,法官在犯罪事实的逻辑评价过程中首先体现了全面评价原则,被告人的行为同时触犯了徇私枉法罪与受贿罪,这是犯罪成立的初步判断;然后在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框架下,行为人的一行为只能得到一个评价,超出的评价则是被禁止的,行为人只能得到一罪的刑法评价,因刑法第399条对于罪数形态的规定是特殊的,根据刑法第399条第4款规定,对这种行为系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结合被告人的犯罪情节,判决书最后给予被告人卿太苏徇私枉法罪的一罪评价。全面评价原则要求刑事裁判文书说理时应注意定罪与量刑两个方面的全面评价,评价过程的逻辑顺序让刑事裁判文书的读者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法院裁判评价的过程,感知司法过程的严谨与威严所在。
三、我国台湾地区刑事裁判文书罪数说理的考察
我国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具有可读性,刑事判决书语言表达生动、贴近现实生活。台湾地区向来把竞合的问题视为罪数论问题,认为罪数论要解决的问题包括“行为人触犯数罪时,法院是否要罗列所有罪名,宣告一个罪名还是多个罪名,最后又该如何定出应执行的刑罚”。[6]台湾地区“刑事诉讼法”第309条规定,“有罪之判决书,应于主文内载明所犯之罪。对于想象竞合犯,不论轻重,都应该把所触犯罪名罗列出来”,“借由这种论罪方式,也可以让人从主文中就清楚知悉行为人所成立的各罪名。”[7]
早期台湾地区刑事判决书关于数罪的要件与范围表达较为笼统,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1942年度台非字第11号判例”指出:“被告人等因图脱逃,继续两夜将监舍地基挖掘,系属一行为之继续活动。”[8]在判决书中,法官仅简单把被告人的行为评价为一罪,法官把行为人两夜挖掘监舍地基的行为认定为一行为,并未对被告人是否属于接续犯作出判断和说理,便直接得出结论,作出结论的过程未曾得知,刑事判决书的厘清功能发挥不足。囿于当时刑事实务对于接续犯的要件与范围的认定不明朗,在早期的刑事判决书中关于罪数的说理较为笼统与罪数理论发展有关,特别是实务中罪数理论的发展。通过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公布的判例解释争议、阐释实务和学说观点,实务界关于罪数理论的发展和说理就是在一个个鲜活的判例说理中发展的。特别是2005年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原刑法第56条连续犯的规定被删除后,接续犯成为实务中罪数论重要的探讨对象,接续犯的认定在刑事判决书中的说理显得更加重要,特别是与集合犯的区分,关系到定罪和数罪并罚。台湾地区刑法的修正对罪数理论在刑事判决书中的说理提出了要求,判决书的说理不仅承担了罪数厘清的责任,还需根据罪数理论相关定义结合案情说理,有时还会对法条的立法原意作出法官的理解,罪数理论逐渐在刑事判决书中得到厘清和区分。
2006年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年度台上字第307号判决”对于接续犯的说理如下:“意图营利使‘同一女子’与他人为性交易,或图利容留性交、猥亵犯行,系以经营‘应召站’之目的为之,在主观上乃基于单一之犯意,以多数举动接续进行,而侵害同一法益,在时间、空间上有密切关系,依一般社会健全观念,难以强行分开,在刑法评价上,以视为数个举动之接续实行,合为包括之一行为予以评价,是色情经营者先后多次使‘同一女子’与他人为性交易等行为,具时间、空间上之密切关系,且系各基于单一犯意接续为之,应各仅论接续犯一罪。”②该刑事判决书在接续犯的理论基础上结合案例,认为意图让同一个女子与他人性交易的行为是因为单一的犯意接续而为的,认定为接续犯,应以一罪论处,成立共同意图营利而容留未满十八岁之人为性交易罪。
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关于罪数的说理经历笼统、不明确到说理详细,通过观察可以看出,这与罪数理论的发展有关,如连续犯的规定被删除后,法官通过刑事判决书的说理厘清接续犯的概念。台湾地区的刑事判决书关于罪数论的说明更加详细,关于罪数的认定更加清晰,行为人通过刑事判决书主文可以得知法官定罪的具体评价过程。由于台湾地区刑法实务深受罪数论的影响,对于刑事判决来说罪数论是定罪科刑的理论基础。然而罪数说理存在着类似案件说理不同的问题,罪数论的发展与刑法实务的自我探索犹如一股麻绳上的丝线缠绕一起,一起向前延伸。
四、罪数理论如何体现于刑事裁判文书
2018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的通知,该指导意见对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的释法说理工作提出了要求,基于提高司法公信力与司法权威的目的,裁判文书的裁判结论的形成过程和正当性理由是裁判文书的两大重点。可以说,裁判文书说理的合理演绎是未来裁判文书写作的发展趋势。
(一)刑事裁判文书说理基础的建立
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的前提是营造良好的司法氛围,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在这个基础上,刑事裁判文书中简单证据、说理不足的问题才有可能得到解决。
1.营造良好的刑事裁判文书改革氛围
法官承担的各种指标考核带来的压力和司法责任制的实施带来的责任,诸多的限制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在刑事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上。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强和规范裁判文书释法说理的指导意见》要求裁判文书释法说理要阐明事理、合理说理,但关于罪数理论如何体现在刑事判决书的说理中并未具体规定,这意味着,罪数形态的说理依赖于法官的合理发挥。在现有制度的框架下,许多法官不敢“大展拳脚”,影响了刑事裁判文书罪数形态说理的发展,罪数理论与实践形成两张皮。罪数理论适用于刑事裁判文书需要营造良好的改革氛围,需要在更大的空间里进行,只有这样良好的氛围,罪数理论才能与具体案例结合,才能找到理论与实践的契合点。因此,在刑事裁判文书改革中应把罪数形态说理的主动权交由法官,保障法官能真正发挥主观能动性,真正做到阐明事理。
2.提高我国司法人员的法律适用能力
拘束司法氛围下的司法人员,法律适用能力令人担忧,在办案过程中越来越依赖司法解释,以致不敢有自己的判断或对自己的判断失去信心。他们法律适用能力的不足表现在刑事裁判文书的书写中,出现如刑事裁判文书的书写模板化、说理的简单化与案件材料的简单堆砌,刑事裁判文书中突兀、直接的定罪量刑。我国罪数理论极具复杂性与争议性,现有的罪数理论要在刑事裁判文书中体现势必要求法官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与法律适用能力。制度构建得再美好,如适用的人无法发挥主观能动性,制度的推行就有可能产生异化,增加我国司法改革的难度与不必要的成本。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探索与建立也对司法人员的裁判文书书写能力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司法人员在制度设计与推行中是重要因素,这些司法适用人员应具有灵活的法律适用能力,努力挣脱制度障碍与枷锁,真正从人的角度去进行制度建构。
(二)刑事裁判文书说理要求的梳理
采罪数论或竞合论,争论不休,张明楷教授指出,“罪数论与竞合论所讨论的具体现象相同、目的相同,只是研究方法略有不同(但不矛盾),部分用语与归类有所不同,因而导致对部分问题(现象)的处理不同。”[9]无论罪数论或竞合论如何争论,罪数的判断是定罪量刑的基础,更是刑事裁判文书厘清功能实现的基础,罪数的判断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应得以具体体现。刑事裁判文书中的说理应把握下列基本要求。
1.合理释明罪数形态
当行为人触犯数个罪名时,刑事裁判文书是否要把所有罪名罗列进来,罪名的宣告是如何作出的,最终的刑罚又是如何确定的,这个过程与理由是刑事裁判文书的重点内容,理应结合具体案情进行分析。但多数的刑事裁判文书系直接给出结论,行为人涉及的其他罪名未加以评价,法律评价过程模糊,如果再碰到类似案件判决结果差异过大的情况,社会大众根本无法知悉差异评价的原因,刑法一般预防作用的实现更是平添困难。刑法理论的发展与司法实务的发展是一体的,如果刑事裁判文书无法合理释明罪数形态,只会导致罪数理论与司法实务进一步割裂,罪数理论未知实务的具体评价过程,罪数理论发展混乱无法为司法实务服务,实务亦是迷茫。罪数形态的合适释明限度应当是结合具体案情,对行为人所触犯的所有罪名进行评价,亦包括罪名的宣告。
2.罪数形态释明符合逻辑性
罪数形态如何释明要以具有逻辑性为边界,评价时应遵循刑法理论的逻辑性。刑事裁判文书在释明罪数形态过程中应遵循两层逻辑,遵循行为人的行为属于一罪或数罪的判断逻辑,此为第一层逻辑;在罪数判断的基础上,遵循罪数并罚与否的判断逻辑,此为第二层逻辑。第一层逻辑就行为成立一罪或数罪进行评价。一罪或是数罪的判断标准存在多种学说③,通说认为将犯罪构成标准作为一罪或数罪的区分标准,犯罪事实侵害一个法益,符合一个犯罪构成,即为一罪。“罪数的判断必须先依赖于一罪的判断,而一罪的判断实质上是犯罪成立的判断。”[10]
因此,罪数判断采取犯罪构成标准说与我国犯罪成立的判断标准是一致的。我们还需要注意到,罪数形态在刑法分则中的规定是混乱的,这些特殊的刑法分则规定并不一定按照罪数理论的判断标准定罪,在进行一罪或数罪的判断时需注意这些特殊规定。采用犯罪构成标准要求对犯罪的法益保护有所认识。犯罪构成标准解决了罪数的问题,罪数处断的问题交由第二层逻辑解决。第二层逻辑的任务是对数罪实行并罚与否进行说理,这正是罪数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该理论的实务意义。“司法实践中,正是因为缺乏罪数形态的说理,直接得出的结论要么把它忽略了,要么由于认定错误,该并罚的没有并罚,不该并罚的实行了并罚。”[11]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闽刑终337号④于上诉人辩诉理由不采纳的说理为:“经查,无论我国刑法规定或者立法原意还是司法实践,对于独立的数起故意伤害的罪数形态,都是吸收并处,即以其中最为严重后果基准,综合考虑全案情节的原则量刑。”根据我国刑法第69条⑤,刑法关于数罪并罚采取的是混合原则,当行为人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的,与有期徒刑、拘役并罚的,采吸收原则;当数罪判处均为有期徒刑、拘役,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假设,行为人的两个故意伤害罪中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一个被判处有期徒刑,这种情况下采吸收原则,只执行一个无期徒刑;假设行为人的两个故意伤害罪中被判处有期徒刑,采取限制加重原则,受总和刑期和数罪中法定最高刑期的双重限制。但,此份判决书并未对行为人涉及的两个故意伤害罪进行分别评价,便直接得出结论:“独立的数起故意伤害的罪数形态是采吸收并处的结论。”此案一审判处无期徒刑,二审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二审判处的十五年有期徒刑的刑罚符合人民法院的量刑规则,但法官说理却与刑法第69条数罪并罚的原则相左,且罪数形态说理不足。因此,此份刑事裁判文书不仅无法发挥裁判文书的厘清功能,反而还为数罪并罚理论增添迷雾。在罪数形态说理的第二层逻辑上,如果并罚与否不进行说理,被告人、上诉人、辩护律师乃至法律学习者、社会大众都无从得知该案量刑的过程,刑事裁判文书像是不可登顶的高塔。罪数说理第二层逻辑的展开首先应该是在数罪分别评价的基础上,对并罚与否进行说理与确定,“量刑的过程体现为法定刑—基准刑—调整刑—宣告刑。”[12]
罪数理论说理逻辑的严密性与说理的透彻性是刑事裁判文书的两大特性,不仅记载着案件的裁判过程,也是对刑事裁判文书改革的另一种有力推进。刑事裁判文书的改革与刑法理论的发展息息相关,绝不是形式上的改革。刑事裁判文书是为罪数理论的体系构建提供司法实践经验与样本,罪数理论的发展又为刑事裁判提供理论依据。刑事裁判文书的厘清功能体现在每一份刑事裁判文书中,厘清功能的实现也是个案公平正义的实现基础。
注释:
① 海南省海南中级人民法刑事裁定书,(2004)海南刑终字第184号。
② 台湾地区最高法院2017年度台上字第307号判决。
③ 罪数区分的学说包括法益说、构成要件说、行为说等。
④ 主要案情:2012年5月24日被告人在饶某2家门口,向被害人饶某3讨要其哥哥的工钱时,双方打架,被告人持刀刺中饶某3的背部、腹部和大腿等,经鉴定饶某3的伤情为重伤乙级;2015年8月30日,被告人在漳州金山湘菜馆门口,与被害人熊某2言语不和发生打架,从车上取了一把工具刀返回与熊某2打架,刺中被害人胸部,经抢救无效死亡。被告人的损伤程度鉴定为轻微伤。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9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