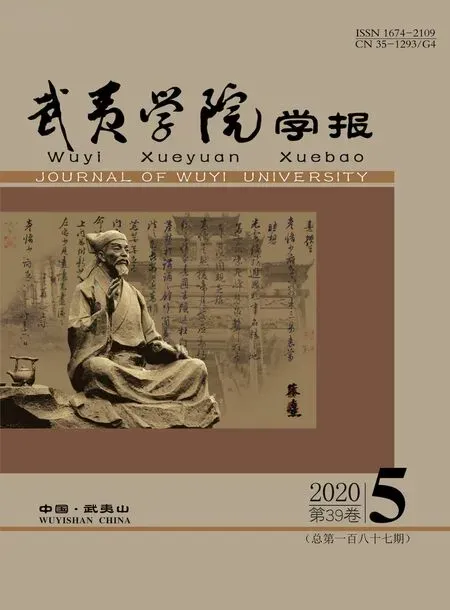评朱熹对佛教心说的批判
黎晓铃
(武夷学院 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不同于张载与二程对佛教“心迹”是否一致的纠结,朱熹更加重视的是作为主观能动性之主体的心如何恰当应对客观现实之“迹”的问题。为此,朱熹将张载具有因物顺应性质的“太虚”本体之虚,用在了心之本体的性质之上。朱熹说:“虚灵自是心之本体,非我所能虚也。耳目之视听,所以视听者即其心也,岂有形象?然有耳目以视听之,则犹有形象也。若心之虚灵,何尝有物”?[1]所以,正是因为有“虚”的性质,心之本体还有明、灵、觉的特性。如此看来,朱熹十分强调心之综合分析与判断的功能,从而超越了二程只强调心对理之绝对服从的直线性模式。为此,朱熹又将自己所强调的心与佛教重视的心进行了辨析。
一、用虚心批判佛教的空心
朱熹十分重视将自己强调的心“虚”与佛教强调的心“空”区别开来。朱熹说:“吾儒心虽虚而理则实,若释氏则一向归空寂去了。吾以心与理为一,彼以心与理为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见处不同。彼见得心空而无理,此见得心虽空而万理咸备也。”[2]在朱熹看来,佛教将心和实理分为二,心所思考的不是理而是空,而理学家的心万理兼备,包含和思考实实在在的现实事理。所以,理学的心虚与佛教的心空不是一回事。然而,其实还是有很多人比较欣赏佛教唤醒此心而觉悟的修养论的。朱熹说:“其唤醒此心则同,而其为道则异。吾儒唤醒此心,欲他照管许多道理;佛氏则空唤醒在此,无所作为,其异处在此。”[1]朱熹依然是以佛教没有照管现实中的道理而否定了佛教的唤醒此心。
同样,“释氏所谓敬以直内,只是空豁豁地,更无一物,却不会方外。圣人所谓敬以直内,则湛然虚明,万理具定,方能义以方外。”[2]佛教和理学也都强调心之敬,但朱熹认为,佛教没有就外界客观之理作为敬的对象,敬的也是空。如何判断佛教并没有敬重和思考现实之理呢?朱熹说:“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阙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何在乎?”[1]朱熹认为,父子、君臣、三纲五常就是作为人最重要的也是首先要遵循的客观之理,佛教僧人断舍了与家庭的关系而出家,就是逃避了这种关系,从而肯定佛教实际上并不敬重客观之理,并推断其所强调的敬以直内也就是空理。“圣人之道,弥满充塞,无少空阙处。若与此有一毫之差,便于道体有亏欠也。若佛则只说道无不在,无适而非道,政使于礼仪有差错处亦不妨,故他与此都理会不得。”在朱熹看来,外在之理是不能有一丝一毫差错的,佛教不重视礼仪就是道体上有亏欠,从而佛教心中所敬的并不是客观之理。然而,礼仪是否就完全等同于客观之理呢?显然,礼仪和理并不能完全划上等号,不能因为佛教不重视礼仪的形式从而等同于佛教不重视客观之理。
朱熹其实也知道,佛教所强调的空,并不是指否定一切的断灭空。“(释氏)说‘玄空’,又说‘真空’。玄空便是空无物,真空却是有物,与吾儒说略同。”[1]佛教理论中的空是包含有的,对于这点,朱熹表示了肯定,并认为儒家也是有同样的道理。但是,朱熹并不认同佛教的“空不真空”:“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无了,所谓‘终日吃饭,不曾咬破一粒米’;终日着衣,不曾挂着一条丝’。若老氏犹骨是有,只是清静无为,一向恁地深藏故守,自为玄妙,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无做两截看了。”[1],朱熹认为,佛教没有践行客观之理(儒家纲常伦理),那么其所强调的“空不真空”其实是将有也变成了空,与儒家的空包含有还是不同的。然而,佛教的“空不真空”是否真的是将有也变成了空呢,这依然还是值得商榷的。
依此逻辑,朱熹更严厉批评了佛教的“作用是性”。朱熹说:“如某国王问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见性为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为性。’曰:‘如何是作用?’曰云云。”[1]然而,这其实是佛教传说中的波罗提尊者与印度异见王的谈话,强调的是当下现实之心不起妄念的一种状态。但是朱熹的理解却不是这样:“‘作用是性:在目曰见,在耳曰闻,在鼻齅香,在口谈论,在手执捉,在足运奔’,即告子‘生之谓性’之说也。且如手执捉,若执刀胡乱杀人,亦可为性乎?龟山举庞居士云‘神通妙用,运水搬柴’,以比‘徐行后长’,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后长’乃谓之弟,‘疾行先长’则为不弟。如曰运水般柴即是妙用,则徐行、疾行皆可谓之弟耶?”[1]朱熹认为,佛教的“作用是性”就是缺乏本体的把持,而只在用处的末端的为所欲为。朱熹举儒家中的“徐行后长”与佛教中的“运水搬柴皆是妙用”进行对比。“徐行后长”其实出自孟子对告子的批评中,原话是“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意思是,慢慢地跟在长者后面走,叫作悌,快步抢在长者前面走,叫作不悌,强调的是对兄长要敬重且顺从。然而,若走路时走到兄长前面就意味着不敬,这依然是将礼仪等同于理的逻辑。
其实,朱熹之所以特别强调批判佛教的“作用是性”,与这种禅法在朱熹的生活地特别流行有关。“作用是性”的禅法真正在中国被明确化而产生深远的影响,是从洪州禅的创始人马祖道一那里开始。慧能注重的“直指心源、顿悟见性”至马祖道一之后为之一变,开始出现了一种向随缘任运、无证无修方向发展的倾向。[3]而马祖道一在建阳佛迹岭传法之后,其禅法在福建迅速传播开来。百丈怀海、沩山灵祐、黄檗希运等作为其禅门开宗立派之祖师都来自福建。朱熹长期生活在此,对于这种禅法因传播不当而带来的负面影响了解较为深刻,从而举起理学理论以对治之就不难理解了。在朱熹的理解中,“作用是性”就等同于其心性论中很容易被欲望牵走的“人心”:“释氏弃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遗其精者,取其粗者以为道。如仁义礼智为非性,而以眼前作用为性是也。此只是源头处错了。”[1]因此,朱熹提出,人心必须听命于道心,并以此继续批判佛教的观心说。
二、用人心听命于道心批判佛教的观心
在朱熹看来,心是兼体用而存在的,而佛教的“作用是性”则是忽略了体而仅在用处的任意妄为。为此,朱熹吸收了张载的“心统性情”来解释其理学中心的含义。其中,性为未发为体,情为已发为用。朱熹说:“盖孟子所谓性善者,以其本体言之,仁义礼智之未发者是也。所谓可以为善者,以其用处言之,四端之情发而中节者是也。”[4]未发之性是静,已发之情是动,而心则是兼体用未发已发之性情的主宰者:“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6]情的发用是否得当中节,就由心来决定。如此看来,心确实非常重要。
有人问朱熹如何看待佛教的观心说。朱熹却说:“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为主而不为客者也,故以心观物,则物之理得。”[5]朱熹强调心就是主宰者。每个人的心只有一个,这个心主宰着人的一切。而这个主宰一切的心却不需要反观。因为朱熹认为,反观其心则意味着有另一个心可以观察着这个心,在朱熹看来是不符合逻辑的。朱熹说:“释氏之学,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吃口,如目视目,其机危而迫,其途险而塞,其理虚而其势逆。”[4]那么,又如何保证这个主宰一切的心发用得当呢?所以有人问:“若子之言,则圣贤所谓精一,所谓操存,所谓尽心知性、存心养性,所谓‘见其参于前而依于衡’者,皆何谓哉?”[4]可见,此心必须得到管理才能发用得当中节,而管理此心的心又被称为道心:“夫谓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奥也。心则一也,以正不正而异其名耳。”朱熹认为其哲学中,虽有道心和人心两个概念,但是实指一个心,只是因人欲之萌和天理之奥而有不同的名字而已。然而,只有一个心,名字可以不同,但是却又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朱熹解释说:“‘惟精惟一’,则居其正而审其差者也,绌其异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则信执其中,而无过不及之偏矣,非以道为一心,人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朱熹否认有道心和人心两个心,然而何者居其正审何者之差?何者纠正何者之差?朱熹继续解释:“夫谓‘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则亡者存;舍而不操,则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昼之所为得以梏亡其仁义之良心云尔,非块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觉而谓之操存也”[4]。朱熹再次强调,心只有一个,重要的是良心的自主性是否能够得到呈现而已。
为了更好地表达道心与人心的关系,朱熹做了一个比喻:“人心如船,道心如舵。任船之所在,无所向,若执定舵,则去住在我。”[5]人心听命于道心,就象舵控制船一样。但是舵并不是船,它只是船的一部分。船驶向哪里由舵控制,如果舵不控制,船就会无目的地乱飘。那么,舵又应当如何控制船呢?目标是必不可少的。由此,朱熹批判佛教之心是无定向之心:“释氏虽自谓惟明一心,然实不识心体;虽云心生万法,而实心外有法;故无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备。然其为说者,犹知左右迷藏,曲为隐讳,终不肯言一心之外别有大本也。若圣门所谓心,则天秩、天序、天命、天讨、恻隐、羞恶、是非、辞让,莫不该备,而无心外之法,故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其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是则天人性命其有二理哉?”[4]
三、问题之所在
朱熹指出,虽然儒佛都强调唤醒此心,然而儒佛唤醒此心的目的却不同。在儒家,唤醒此心的目的在于认识外在的作为本体的理,也就是舵手知道自己的方向。在朱熹看来,佛教始终不肯承认外在之理才是天下之大本,心就没有需要认识的外在对象,于是便会迷失自我。这其实也是对契嵩去除天命而论心的批判。在契嵩处,没有客观必然的天命,只有一心向道,而道究竟是什么,没有确定的说法,所以在朱熹看来,佛教的心就是迷失的小船。而朱熹理学强调外在的客观道理就是认识的对象,船有了目标,心的主宰也就能得以实现。“盖穷理之学,只是要识如何为是,如何为非,事物之来,无所疑惑耳。非以此心又识一个心,然后得为穷理也。”[4]因此,在朱熹理学中,心虽然很重要,但是心本身却不是需要认识的对象。因为由于心体“自明”的机制,心体是什么的问题在逻辑上已经解决。[6]关键在于道心(良心)的主宰能不能实现。朱熹认为,将理作为认识对象,心就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良心的主宰才有实现的可能。
所以,朱熹认为,儒佛的根本差别其实与自私与否无关,而是有没有以现实中的理作为思考对象。朱熹说:“陆子静从初亦学佛,尝言:‘儒佛差处在义利之间。’某应曰:‘此犹是第二者,只它根本处便不是。当初释迦为太子时,出游,见生老病死苦,遂厌恶之,入雪山修行。从上一念,便一切作空看,惟恐割弃之不猛,屏除之不尽。吾儒却不然。盖见得无一物不见此理,无一理可违于物。佛说万理具空,吾儒说万理具实。从此一差,方有公私、义利之不同。’”[1]朱熹认为,正是因为没有见理,才会产生公私、义利的差别。
然而,问题在于,客观之理其实非常复杂,并非只有一个。朱熹也说,“物物皆有理”“花瓶便有花瓶底道理,书灯便有书灯底道理。水之润下,火之炎上,金之从革,木之曲直,土之稼穑,一一都有性,都有理。”[5]如何处理这些复杂的道理才是问题的关键。所谓“发而中节”其实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如何实现这一理想才是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学生问朱熹:“于学者如何皆得中节?”,朱熹的回答是:“学者安得一一恁地!也须且逐件使之中节,方得。此所以贵于‘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无一事之不学,无一时而不学,无一处而不学,各求其中节,此所以为难也。”[5]对于复杂的客观道理,朱熹认为需要把眼前现实每一件事物的道理都一一搞清楚,“各求其中节”,这其实是一个求真和扩大见识的过程。“朱熹之心体以‘湛然’为特质,以物来能照得其真为目的”。[7]而知识是无止境的,求真其实是没有终点的。如此,朱熹譬喻中的小船的舵手(道心)依然会因无法分辨现实中的复杂的道理而迷失方向。所以,如果仅以客观之理为认识对象,其实并不能完全保证道心(良心)的主宰得以实现。因此当有人问朱熹:“‘满腔子是恻隐之心’,如何?”时,朱熹的回答是:“腔子是人之躯壳。上蔡见明道,举经史不错一字,颇以自矜。明道曰:‘贤却记得许多,可谓玩物丧志矣?’上蔡见明道说,遂满面发赤,汗流浃背。明道曰:‘只此便是恻隐之心。’公要见满腔子之说,但以是观之。”[1]朱熹以谢良佐为例,指出若把求真等于圆善就不是正确的方向。而当其听完程颢的话而汗流浃背、满面发赤之时,才是由性体而直接导至四端七情的发用,这才是发而中节的状态。由此,发而中节的情才是人需要达到的目标所在,也是朱熹譬喻中小船之舵(道心)把控方向的关键。然而,道心究竟如何主宰人心这艘小船依然是没能解决的问题。
朱熹理学中的本体是天理,然而这个本体并不能直接去把握,而是需要通过对分殊之理的一一了解之后豁然贯通得知天理。朱熹认为“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8]。然而,由于本体的非实体性,常规的认识方法,比如分析、推理、综合、归纳等,其实很难准确、完整对其进行认识和把握。[9]其实,虽然朱熹一再强调“知性知天,则能尽其心矣。不知性不能尽其心”[5],知性似乎必须在尽心之前,然而他自己其实也说:“心梏于见闻,反不弘于性耳。”[5]可见,如何使心不梏于见闻也是见性的关键,反观其心使其见性其实也是必要的过程。佛教的观心说当依然有其不可否定的价值和可资借鉴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