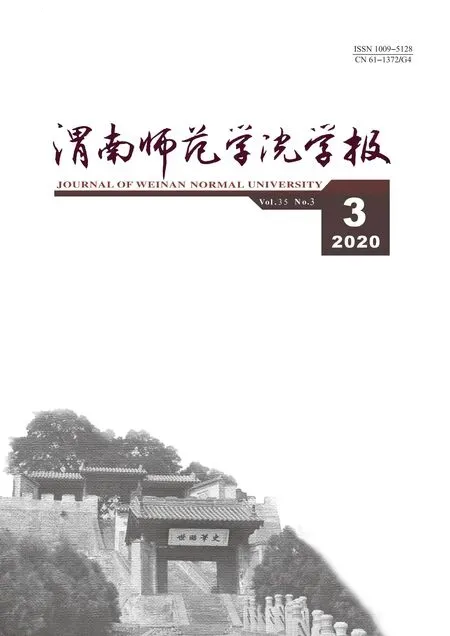唐宋诗词中的司马迁形象
梁 中 效
﹙陕西理工大学 两汉三国文化研究中心,陕西 汉中 723000)
司马迁的人生悲剧与《史记》的文化经典地位,使司马迁成为千百年来文人墨客崇拜的偶像、学习的楷模和同情的对象、惋惜的同类,唐宋诗词中留下了许多歌咏司马迁及《史记》的诗词,展示了司马迁的人格魅力与《史记》的崇高地位,值得我们研究和珍视。
一、“司马迁文亚圣人,三头九陌碾香尘”
司马迁的悲剧人生和《史记》的不朽著作,使得百世同情,千载敬仰,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永恒的话题。《史记》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被列为“前四史”之首,因此司马迁被后世尊称为“史迁”“史圣”,与司马相如合称“文章西汉两司马”。唐代追求大一统的盛世,需要借助司马迁的《史记》大一统精神;宋代文人高举批判大旗,重建儒家道统,也需要司马迁的独立人格榜样。“文以载道”“文以明道”,司马迁的雄文与《史记》的文化精神,自然成为唐宋文人学习的楷模。
唐代开疆拓土,文治武功超过汉朝,尤其是科举取士,《史记》与《汉书》《后汉书》一起,被列为“三史”科进行考试,以《史记》为代表的“前四史”地位空前提高。《唐会要》卷七十六记载:长庆二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奏:“历代史书,皆记当时善恶,系以褒贬,垂裕劝戒。其司马迁《史记》,班固、范晔两《汉书》,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伏惟国朝故事,国子学有文史直者,宏文馆宏文生,并试以《史记》《两汉书》《三国志》,又有一史科。近日以来,史学都废,至于有身处班列,朝廷旧章,昧而莫知,况乎前代之载,焉能知之。伏请置前件史科。”“能通一史者,请同五经、三传例处分。”“其三史皆通者,请录奏闻,特加奖擢。仍请颁下两都国子监,任生徒习读。”“敕旨。宜依。仍付所司。”[1]1398唐穆宗批准了殷侑的建议,“史科”得以延续。值得注意的是,唐人认为“三史”仅次于“六经”,地位崇高,其“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正是在此大背景之下,司马迁受到唐人的崇敬。唐代诗人贯休在《上卢使君二首》中说:“司马迁文亚圣人,三头九陌碾香尘。”唐代诗人同情司马迁的不幸,白居易《杂感》诗云:“君子防悔尤,贤人戒行藏。嫌疑远瓜李,言动慎毫芒。都尉身降虏,宫刑加子长。吕安兄不道,都市杀嵇康。斯人死已久,其事甚昭彰。是非不由己,祸患安可防。使我千载后,涕泗满衣裳。”千载之后,仍为司马迁受刑而感伤。他的《咏怀》诗云:“冉牛与颜渊,卞和与马迁。或罹天六极,或被人刑残。顾我信为幸,百骸且完全。五十不为夭,吾今欠数年。”有感于司马迁“被人刑残”,珍惜自己的生存现状。他的《读诗五首》诗云:“马迁下蚕室,嵇康就囹圄。 抱冤志气屈,忍耻形神沮。当彼戮辱时,奋飞无翅羽。 商山有黄绮,颍川有巢许。何不从之游,超然离网罟。”面对司马迁遭受酷刑,他想借道家的退避来免祸。但司马迁没有选择逃避,因此是时代英雄。唐人牟融的《司马迁墓》诗:“落落长才负不羁,中原回首益堪悲。英雄此日谁能荐,声价当时众所推。一代高风留异国,百年遗迹剩残碑。经过词客空惆怅,落日寒烟赋黍离。”诗人在为司马迁悲伤时,更敬仰他的英雄气概。唐人常将司马迁与班固放在一起,称为“班马”,赞美他们是文章高手、文学大家。杜牧《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我家公相家,剑佩尝丁当。旧第开朱门,长安城中央。第中无一物,万卷书满堂。家集二百编,上下驰皇王。多是抚州写,今来五纪强。尚可与尔读,助尔为贤良。经书括根本,史书阅兴亡。高摘屈宋艳,浓薰班马香。李杜泛浩浩,韩柳摩苍苍。近者四君子,与古争强梁。愿尔一祝后,读书日日忙。一日读十纸,一月读一箱。”[2]5941-5942杜牧喜爱侄子,精心培养,教导他读经史子集。希望侄子学习屈原、宋玉与司马迁、班固,成为文学大家。白居易在《谈氏小外孙玉童》诗中说:“中郎余庆钟羊祜,子幼能文似马迁。”用司马迁之文,东汉蔡邕、西晋羊祜来形容谈氏父、女、外孙的文学才华。皎然《讲古文联句》诗云:“屈宋接武,班马继作。”也将“屈宋”与“班马”相提并论,称为文学大家。唐人黄滔的《遇罗员外衮》诗云:“绮园难贮林栖意,班马须持笔削权。”赞美“班马”的史学成就。唐代也有人赞成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司空图的《狂题十八首》诗云:“交疏自古戒言深,肝胆徒倾致铄金。不是史迁书与说,谁知孤负李陵心。”肯定了司马迁为李陵辩护。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以司马迁《史记》为榜样。韩愈认为,汉朝人莫不能文,独司马相如、太史公、刘向、扬雄之为最。认为司马迁作品的风格是“雄深雅健”,《史记》成为韩愈作文的样本。柳宗元认为《史记》文章写得朴素凝练、简洁利落,无枝蔓之疾;浑然天成、滴水不漏,增一字不容;遣词造句,煞费苦心,减一字不能。因此,司马迁对唐代古文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朝守内虚外,重文轻武,经济繁荣,文人地位高,敢于议论时政,但国力不强,更加同情司马迁为李陵辩护。宋代诗人林同《司马迁》诗云:“悲哉执手泣,论著谨毋忘。岂识迁它日,能紬石室藏。”同情司马迁的遭遇,赞美《史记》的不朽。王安石的《司马迁》诗云:“孔鸾负文章,不忍留枳棘。嗟子刀锯间,悠然止而食。成书与后世,愤悱聊自释。领略非一家,高辞殆天得。虽微樊父明,不失孟子直。彼欺以自私,岂啻相十百。”[3]38赞许司马迁忍辱负重,完成名著。秦观的《司马迁》诗云:“子长少不羁,发轫遍丘壑。晚遭李陵祸,愤悱思远托。高辞振幽光,直笔诛隐恶。驰骋数千载,贯穿百家作。至今青简上,文采炳金雘。高才忽小疵,难用常情度。譬彼海运鹏,岂复顾缯缴。区区班叔皮,未易议疏略。”秦观认为司马迁的人生挫折,导致他发愤图强,完成巨著。这两首诗都将司马迁的“愤悱”与“高辞”相联系,其人生的巨大灾难,变成了其文章的奔放不羁。秦观的《无题二首》诗云:“君子有常度,所遭能自如。不与死生变,岂为忧患渝。西伯囚演易,马迁罪成书。性刚趣和乐,浅浅非丈夫。”因获罪的悲愤,才有了《史记》的巨著。赵希逢《和寄苕溪故人》诗云:“蚕室史迁非有罪,从来文士例多穷。”刘克庄《夜读传灯杂书六言八首》诗云:“麟经之笔既绝,蚕室之书遂行。聃非二子同传,齐鲁两生失名。”这里的“麟经”指的是孔子《春秋》,“蚕室之书”应该是《史记》。宋人在同情司马迁的同时,更赞美司马迁是文学巨匠。宇文虚中的《题平辽碑》诗云:“百年功业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将司马迁的文章与秦始皇统一天下相提并论。宋代文人大都推崇司马迁的史传文学,称他为文章高手。黄庭坚《写真自赞五首》诗云:“吏能不如赵张三王,文章不如司马班扬。”他的《东坡先生真赞三首》诗云:“子瞻堂堂,出于峨眉,司马班扬。”将苏轼与司马迁、班固、扬雄相提并论。辛弃疾《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词云:“我觉其间,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称赞司马迁文章“雄深雅健”。陆游在《感兴》中云:“文章天所秘,赋予均功名。吾尝考在昔,颇见造物情。离堆太史公,青莲老先生,悲鸣伏枥骥,蹭蹬失水鲸;饱以五车读,劳以万里行,险艰外傋尝,愤郁中不平。”[4]1433陆游的《夜观严光祠碑有感》诗云:“生陋范晔,琐琐何足录!安得太史公,妙语写高躅。”陆游认为司马迁的雄文,既与他游历天下得江山之助有关,更与他“愤郁中不平”的生命历程相联系。方回《赠朱师裕》诗云:“故因高韵如袁粲,岂但雄文似史迁。”文同的《奉送少讷还青神》诗云:“词章直如子长健,辩论不比仲连黠。”两位诗人都赞许司马迁是文章高手。读书是做文章的前提和基础,宋代文章学把读《史记》作为学习文章的主要范本。朱熹《朱子语类·论文》:“司马迁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战国文气象。”[5]3299宋人认为,司马迁胸中有侠气,作传则“分外精神”。楼昉《过庭录·史公有侠义》云:“太史公作苏秦、张仪、范雎、荆轲传分外精神,盖子长胸中有许多侠气,所谓爬着他痒处,若使之作董仲舒等传,则必不逮,以其非当行也。”说明作者胸中之“气”,影响文章风格。李流谦的《峡中赋百韵》云:“杜陵半九州,诗史入嘉话。马迁多经践,有文资博雅。”诗人将司马迁博雅宏放的文章与杜甫忧患天下的诗史相媲美,反映了宋人对司马迁文学地位的认同与推崇。
二、“马迁信史炳丹青,黄老搀先六籍名”
唐朝建立后,贞观君臣以史为鉴,总结隋亡唐兴的经验教训,设馆修史,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榜样,《史记》的正史地位得以确立。唐代科举有“三史”之目,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列为科举考试科目,鼓励士人研习“三史”,并通过科举选拔治史人才,对于《史记》在社会上的普及起到了推动作用,在文人士子中掀起了研究《史记》的热潮。羊士谔《郡中即事三首》:“青门远忆中人产,白首闲看太史书”,衰老之身,仍读《史记》。因此,在唐代诗人笔下,普遍肯定和推崇《史记》的史学地位。唐太宗李世民《咏司马彪续汉志》:“二仪初创象,三才乃分位。非惟树司牧,固亦垂文字。绵代更膺期,芳图无辍记。炎汉承君道,英谟纂神器。潜龙既可跃,逵兔奚难致。前史殚妙词,后昆沉雅思。”这里的“前史”,即司马迁的《史记》,证明李世民熟读《史记》。唐代诗人黄滔在《遇罗员外衮》中说:“绮园难贮林栖意,班马须持笔削权。”强调了司马迁的秉笔直书的“史德”。崔湜的《春日赴襄阳途中言志》:“一朝趋金门,十载奉瑶墀。入掌迁固笔,出参枚马词。”也同样赞许司马迁的秉笔直书。皎然的《讲古文联句》:“屈宋接武,班马继作。”将班固与司马迁相提并论,强调了他们并驾齐驱的史学与文学地位。沈佺期《三日独坐驩州思忆旧游》:“禊堂通汉苑,解席绕秦楼。束皙言谈妙,张华史汉遒。”在赞许张华史才的同时,将《史记》与《汉书》相提并论。高适的《过卢明府有赠》:“我行挹高风,羡尔兼少年。胸怀豁清夜,史汉如流泉。”赞美卢明府精通《史记》与《汉书》。宋之问的《游禹穴回出若邪》:“著书闻太史,炼药有仙翁。”太史公即司马迁。王维的《和尹谏议史馆山池》:“洞有仙人箓,山藏太史书。”赵嘏的《江亭晚望》:“无愁自得仙翁术,多病能忘太史书?”戴叔伦的《曾游》:“碑留太史书,词刻长公调。”这三首诗中的“太史书”即《史记》。王起的“滞周惭太史,入洛继先贤”,罗隐的《封禅寺居》的“周南太史泪,蛮徼长卿书”,指的是司马迁与司马相如。从唐人的诗可以看出,由于唐太宗等唐朝皇帝的率先垂范,由于科举考试中的“三史”考试,在唐代社会盛行读《史记》、学《史记》、用《史记》,所以唐人大都赞美司马迁的《史记》。
宋朝虽然文化发达,文人士大夫待遇优厚,但软弱无能屈辱外交和屡战屡败的对外战争,迫使文人士大夫学习汉唐盛世开拓进取的龙马精神;知识分子主体地位的提高,也使得他们主动学习司马迁浩然独行的人格。这二者使得宋代诗人对《史记》与司马迁的研究远远超过唐代。
首先,宋代文人敬仰司马迁的人格,赞美他著史的品德。宋代诗人常将苏武、李陵、司马迁这三位重然诺、有气节、敢担当的英才放在一起,彰显了文弱书生司马迁的人格与品德。赵希逢的《和读苏武李陵司马迁传》:“不爱其身过易于,尽判一死外无余。麒麟阁上没公议,却把芳名最后书。”刘过的《怀古四首为知己魏倅元长赋兼呈王永叔宗承载》:“煌煌太史公,逸气横八方。”黄然的《题涪翁亭》:“清音妙绝东坡老,方响名高太史公。”这两位诗人都将司马迁视为名满宇宙的文化巨匠,将他与文豪苏东坡相比。司马迁不惜为真相、为朋友一死,这不仅是做人的品德,更是良史的美德。华岳的《读苏武李陵司马迁传》:“河梁一别子卿归,删后无诗始有诗。若把李陵从反汉,马迁膏鼎亦何辞。”也为司马迁鸣不平。吴龙翰的《读十七全史岁久而彻》:“灯火青编结兴长,可能历历记兴亡。董狐笔底风霜重,班马书边兰蕙香。往事输赢棋几局,浮名今古纸千张。重重公案休拈起,中有灵台定否臧。”将《史记》与《汉书》视为十七史的楷模,但诗人更崇敬司马迁的人格。宋人常将司马迁的通史与杜甫的诗史相提并论。徐瑞的《元日题仲退漫游四后》:“奇探马迁作史意,老气杜陵出峡年。何当囊笔挪杖屡,与君题篇名山川。”李处权的《亨仲家兄擢居谏省诗以贺之》:“诗似少陵多教化,文从太史有波澜。”周端臣的《送翁宾旸荆湖》:“莫如子长子美但能事文章,蚤归来献平戎策。”这三位诗人不约而同地将司马迁与杜甫相并肩,实际上司马迁与杜甫虽然异代,但忧国忧民的情怀与人生坎坷的经历大体一致。他们是德操与才学俱佳的汉唐文学与文化的标志。
其次,宋代诗人认为司马迁是超越左丘明的史学巨匠,《史记》是名垂千古的信史。欧阳修是北宋文坛领袖,也是史学大家,他学习司马迁。他的《新营小斋凿地炉辄成五言三十七韵》:“兴亡阅今古,图籍罗甲乙。鲁册谨会盟,周公彖凶吉。详明左丘辩,驰骋马迁笔。金石互铿鍧,风云生倏忽。”他的《绿竹堂独饮》:“予生本是少年气,瑳磨牙角争雄豪。马迁班固自歆向,下笔点窜皆嘲嘈。客来共坐说今古,纷纷落尽玉麈毛。”有时也不免轻狂。柴元彪的《送侄一斋游武林》:“长安草木成焦枯,暗暗落日栖平芜。凄凉往事增欷嘘,子长一部太史书。寄在名山大泽区,之子安肯侣樵渔。”诗人鼓励他的侄子向司马迁学习,写出像《史记》那样藏之名山的巨著。王安石的《王子直挽辞》:“多才自合至公卿,岂料青衫困一生。太史有书能叙事,子云于世不徼名。”政治家的王安石还是希望以司马迁、扬雄为榜样显达于世,有用于时。曾丰《寄题双清亭》:“马迁史里万古具,张说诗中四时俱。诗编史帙一关目,姑掇余甭清冰肉。床头拈出周易读,更悟太清清蜕骨。”在诗人的阅读中,将司马迁《史记》放在首位。陈起的《史记送后村刘秘监兼致欲见之悰》:“嘱以马迁史,文贵细字雕。名言犹在耳,堤柳凡几凋。兹焉得蜀刻,持赠践久要。会晤知何时,霁色审来朝。”陈起将自己得到的蜀刻《史记》送给朋友,因为司马迁的史书文史俱佳。胡寅的《和范元作五绝》:“马迁法左氏,实录系日月。孰传经世学,傥可论绝笔。”认为司马迁《史记》可与日月共辉。张明中的《延昌观道纪堂》:“马迁信史炳丹青,黄老搀先六籍名。清净元非人纪有,虚无幻出道家声。”认为司马迁《史记》可以彪炳千古。李觏的《读史》:“子长汉良史,笔锋颇雄刚。”赞美司马迁是大史学家,而且文史优长。张镃的《次韵王耘之秋兴二首》:“派自王摩诘,才分马子长。”赞许司马迁才气纵横。大文豪辛弃疾以读司马迁《史记》为精神享受。他的《汉宫春·会稽秋风亭观雨》说:“千古茂陵词在,甚风流章句,解拟相如。只今木落江冷,眇眇愁余。故人书报,莫因循、忘却莼鲈。谁念我,新凉灯火,一编太史公书。”伴词人度过寒冷长夜的是温馨的《史记》。
最后,唐宋文人推崇司马迁与班固,常将二人称为“马班”或“班马”,将《史记》与《汉书》并称为“史汉”。陈鉴之《陪守斋至玉湖书院作》:“读易发妙蕴,不惟评马班。著述五百卷,星芒照人寰。”赞美司马迁《史记》与班固《汉书》,文化之光照人寰。曾巩《之南丰道上寄介甫》:“方投定鉴照,即使征马班。相期林兰楫,荡漾穷川湾。”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以司马迁为楷模。方岳《次韵张录携书见过》:“君家自有神奇在,底用浓熏到马班。黄石一编灯火外,紫芒双剑斗牛间。”将司马迁与班固视为文史群星中最耀眼的星座。蒲寿宬《纯阳洞读书和中山陈礼郎韵》:“羞羡鹤俯仰,空悲马班醒。终南在何许,得去何须还。”为司马迁的遭遇而悲伤。唐宋诗人也常用“班马”指代司马迁与班固。唐人皎然的《讲古文联句》:“屈宋接武,班马继作。”与杜牧一样,也将“屈宋”与“班马”并提。温庭筠的《病中书怀呈友人》:“班马方齐骛,陈雷亦并驱。”宋人程公许的《送别魏校书借参预李先生韵》:“词华班马富,道术鲁邹醇。”推许“班马”是文章高手。喻良能的《送洪右史赴召三首》:“上追班马真辈行,下视燕许如儿嬉。”将汉代司马迁、班固与唐朝“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相提并论。方逢辰的《题卢文峰十二知丞文集》:“骈花俪叶妙天下,文赋直追古班马。”赞扬班马的文章妙天下。彭龟年的《和临江庚子鹿鸣宴诗韵》:“笔下雄深过班马,马中洒落似张程。”也是赞许班马的雄文宏深。唐宋诗人常将《史记》与《汉书》并称为“史汉”。梅尧臣的《依韵答宋中道》:“史汉抉精深,文字光粲粲。”《史记》《汉书》是精深的史学巨著。陆游的《散怀》:“遗文诵史汉,奇思探庄骚。”他的《书志示子聿》:“载笔敢言宗史汉,闭门犹得读庄骚。”可见陆游不仅自己读《庄子》《楚辞》与《史记》《汉书》,而且也让儿子阅读。方回的《后秋思五言五首》:“诗与风骚迫,文兼史汉长。”也将“风骚”与“史汉”相提并论。晏殊的《癸酉岁元日中书致斋感事》:“却展旧编探史汉,更惭高步接夔龙。”大词人也常常研读《史记》《汉书》。总之,司马迁《史记》是唐宋文人案头必备的文史著作,特别是唐代科举有“三史”科目,促进了唐宋文人对《史记》《汉书》的阅读与研究。
三、“何异周南太史家,西上九疑东访禹”
唐宋时期文化的繁荣,主要体现在思想领域的三教争衡与兼容并包,更得益于科举制之下文人向司马迁学习,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览山川之胜,得江山之助,写锦绣华章,抒凌云壮志。
首先,唐宋文人学习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书写祖国山川的豪情壮志。王安石的《拟寒山拾得二十首》:“我读万卷书,识尽天下理。”方回的《送康彦博文夫吉州教长句二十韵》:“子曾精读万卷书,子又远游万里路。”陆游的《闻鼓角感怀》:“平生空读万卷书,白首不识承明庐。时多通材臣腐儒,妄怀孤忠策则疏。”宋代的超级大文豪,都有像司马迁那样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生历练。宋人裘万顷的《送范光伯北行》:“有客当此时,中流驾风樯。欲学太史公,穷汶泗沅湘。”希望像司马迁那样探索湘江流域。楼钥的《次韵翁处度同游北山》:“伊余历聘佳山水,爱奇切慕太史迁。”他的《游龙瑞宫》:“子长直爱奇,万里探禹穴。”诗人欲学司马迁对山水有好奇心,以此游天下。赵蕃的《登岳阳楼》:“太史南游上会稽,爱奇端欲助文辞。萧骚白发离骚国,不到巴陵终欠诗。”诗人也将司马迁的南游会稽视为“爱奇”,诗情得江山之助。曾丰的《广东黄漕改除广西帅过郡送行》:“包笼天地孟轲篇,收管山川马迁记。仰观俯察易象真,更勘画前精入神。”也认为司马迁遨游山川之间增添了《史记》的魅力。文天祥的《长溪道中和张自山韵》:“夜静吴歌咽,春深蜀血流。向来苏武节,今日子长游。”他的《有感》:“故旧相思空万里,妻孥不见满三秋。绝怜诸葛隆中意,羸得子长天下游。”文天祥的游历既有忧患,更有苦痛,所以他最能理解司马迁游历天下时的内心世界。马元演的《游洞霄纪实》:“虽慕子长游,未学子真逸。”诗人仰慕司马迁游历生涯,但希望能超凡脱俗。周端臣的《送翁宾旸荆湖》:“君不见司马子长志横秋,少年足迹不肯休。胸中盘屈奇伟气,笔力直与造化侔。又不见杜陵子美夸壮游,一身几走半九州。吟怀吐纳天地秀,作为篇章光斗牛。”作者认为《史记》与“杜诗”之所以能“篇章光斗牛”,与司马迁、杜甫在游历时“胸中盘屈奇伟气”有密切关系,可谓抓住了司马迁、杜甫游历天下的奥秘,这正是他们与常人游历山川的最大不同。丘葵的《呈张尚友》:“吏部文章悬日月,子长史记在山川。”也是将司马迁、杜甫游历天下相提并论。陈著的《次韵梅山弟醉吟七首》:“隐处是甪里先生,放游是司马子长。试问梅山老居士,判断两家谁最香。”可能司马迁的放游比“商山四皓”对于国家民族更馨香。王奕的《呈申屠御史忍斋二首》:“壮游久负子长才,斥鷃几成困草莱。”诗人认为司马迁以博大的胸怀壮游天下。喻良能的《次韵马叔度再用前韵见寄》:“善弈从来数弈秋,胜游今作子长游。”向往司马迁的胜游。陈长方的《赠画者徐琛》:“我行江南江北山,真赏会心那可数。独爱黄陵古庙前,四水粘天迷浦溆。胸中历历着山川,有句如枝不容吐。欲将写作无声诗,笔底愧非韦与许。”“何异周南太史家,西上九疑东访禹。君能点染出江山,造物炉锤困掀侮。李成不作郭熙死,谁谓今人不如古。”诗人认为绘画的“点染出江山”与诗文的“得江山之助”有异曲同工之妙。总之,宋代文人生活优越但精神苦闷,在忧国忧民之时寄情山水,学习司马迁壮游天下,但很少能体会到司马迁、杜甫放游天下时的奇伟之气。
其次,唐宋文人效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滞留周南要求司马迁继承遗志完成《史记》的精神,用“周南太史”来激励自己。《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岁(元丰元年,前110)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指司马谈)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后因以“周南留滞”为壮志未酬。杜甫《寄韩谏议注》诗:“周南留滞古所惜,南极老人应寿昌。”[6]1510罗隐的《封禅寺居》:“周南太史泪,蛮徼长卿书。”陆游的《闻虏政衰乱扫荡有期喜成口号》:“博士已成封禅草,单于将就会朝班。孤臣老抱周南恨,壮观空存梦想间。”宋祁的《感怀》:“俯首周南泪未干,惊开鱼素得双盘。”刘克庄的《用厚后弟强甫韵》:“岁晚归休老学庵,敢嗟白首滞周南。”这些唐宋诗人的诗作,都有壮志未酬之意,从而借司马谈的“周南留滞”来赞美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文史巨著《史记》。唐宋诗人也借“周南留滞”来表达司马迁行游天下或羁旅他乡,借以抒发诗人的感情。唐代诗人岑参的《送史司马赴崔相公幕》:“珍禽在罗网,微命若游丝。愿托周南羽,相衔溪水湄。”杜甫的《敬简王明府》:“叶县郎官宰,周南太史公。神仙才有数,流落意无穷。”白居易的《咏身》:“周南留滞称遗老,汉上羸残号半人。”唐诗中的这些诗句,表达了司马迁行游天下对后世的影响。宋人也有许多类似的诗作。宋人张耒的《出京寄无咎二首》:“长安城里谁相识,只有周南太史公。”他的《遣兴次韵和晁应之四首》:“露下风悲萤火流,周南羁客意悠悠。山川老去三年泪,关塞秋来万里愁。”他的《官舍岁暮感怀书事》:“北风吹雁去翩翩,流滞周南又一年。”这些诗都表达了行游或羁客之意,既不失原典意义,又表达了新的寓意。刘克庄的《送陈叔方侍郎二首》:“君归定访耆英社,问讯周南太史公。”他的《再和四首》:“留落周南众,萧条冀北空。”李若水的《次颜博士游紫罗洞》:“逸兴未忘河朔饮,羁踪已分周南留。”陈棣的《送郑舜举赴阙》:“酒病诗愁应有梦,鸟啼花发正争妍。君空冀北今行矣,我滞周南岂偶然。”廖行之的《和松坡刘迂诗四首》:“平生湖海敝貂裘,一笑周南底滞留。豪放不妨诗李白,峥嵘何意吏朱游。”这些宋代文人的诗作,虽然创作的时间不同,心境各异,但都表达了“滞周南”的意境,从而抒发了对“周南太史公”司马迁父子的敬意。
四、结语
诗人们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赞美、歌咏应该是唐宋“史记学”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以往学术界对此关注不够。
唐宋是“史记学”繁荣发展的时期,对司马迁《史记》的研读与普及,为唐宋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唐代科举考试的“三史”之一即《史记》,《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云:“凡弘文、崇文生,试一大经、一小经,或二中经,或《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各一,或时务策五道。经史皆试策十道。经通六,史及时务策通三,皆帖《孝经》《论语》共十条通六,为第。”[7]128宋代科举继承唐代的“三史”考试,《玉海》卷四十九引《两朝志》:“国初承唐旧制,以《史记》、两《汉书》为三史,列于科举。有患传写多误,雍熙中,始诏三馆校定摹印。”[8]卷49正是科举考试这个神圣的“指挥棒”,使得唐宋文人将《史记》的研读变成了“童子功”,进而促进了唐宋诗词中对司马迁和《史记》的赞许,也出现了以《史记》为题材的许多诗词佳作。“唐代掀起的古文运动,举起了向《史记》文章学习的旗帜,使《史记》所蕴藏的丰富的文学宝藏才得到空前未有的认识和开发。”[9]4而唐诗与宋词深受《史记》的影响。“唐诗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闪烁着夺目的光辉,而其中就有《史记》的功劳。”[10]115
唐宋是中华原典创新的第二个高潮,诗人们在学习《史记》的基础之上固本拓新,在以《史记》为诗词创作题材的同时,还将司马迁的心路历程、人格德行、行游天下、秉笔直书等方面作为学习榜样,尤其敬仰太史公“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会遭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以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这种献身精神和“三不朽”的追求,让唐宋诗人敬佩不已,因而在他们的笔下司马迁的形象高大而神圣、真实而崇高、多才而悲壮!主要表现为:
其一,“司马迁文亚圣人”。唐宋是中国文章学的巅峰时期,司马迁则是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文学家们学习的榜样。唐人认为“三史”仅次于“六经”,地位崇高,其“音义详明,惩恶劝善,亚于六经,堪为世教”。在大唐三教争鸣和宋朝儒家重整的时代,司马迁特立独行的人格与百科全书的《史记》,给文人树立了“三不朽”的榜样和“内圣外王”的楷模。宋代宇文虚中的《题平辽碑》:“百年功业秦皇帝,一代文章太史公。”
其二,“马迁信史炳丹青”。唐宋是中华历史学的繁荣时代。唐宋诗人们都认为司马迁是一代“良史”,宋人刘克庄在《题杂书卷六言三首》中说:“论笃惟昌黎伯,史法止太史公。”他希望像司马迁那样遨游天下写信史。他的《谒南岳》说:“茫茫鬼神事,荒幻难穷悉。吾师太史公,江淮遍浪迹。”邓有公在《送曾子华游赣》中也说:“昔年子长游,落笔妙信史。”诗人们希望像司马迁那样漫游名山大川,成一代信史,写锦绣文章。
其三,“子长史记在山川”。唐宋是文人遨游天下,将诗文写在山川的时代。司马迁写《史记》得江山之助,为唐宋文人树立了榜样。[11]唐宋文人效法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写千首诗。裘万顷云:“欲学太史公,穷汶泗沅湘。”正是这种寄情山水的文化之旅,才使得唐宋文人“得江山之助”,胸中历历着山川,笔下滚滚抒情志,诗词华章传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