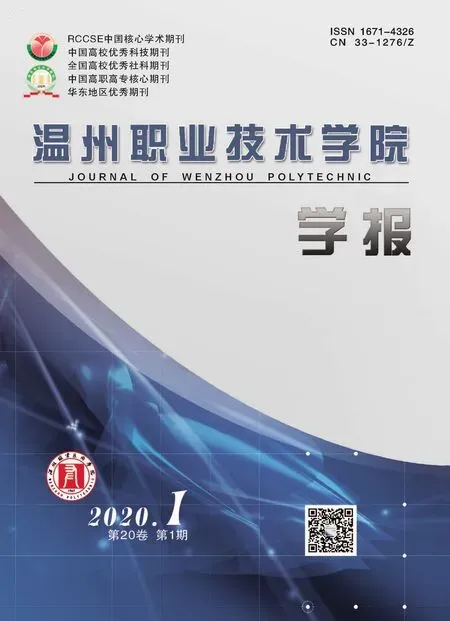近现代温州的疫灾与民间信仰
潘阳力
(温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浙江温州 325000)
受特殊的地理和气候原因影响,温州自古就是一片饱受疫灾折磨的土地。历代温州地方志均有霍乱、天花等传染病肆虐的记录。为应对这些传染病造成的疫灾,除使用医疗卫生手段科学防治,信仰也被人们视为抗御疫灾的一种力量。作为民间信仰资源较为丰富的地区,凡有疫情出现,温州的民间信仰往往表现得比其他地方更为突出。在应对疫情时,温州的民间信仰不仅有司职祛除对应疫病种类的神祇系列可供信众选择,更有完整的仪式和相应的解释,来为信众群体或个人提供心理干预。近现代温州,一方面由于历史,民间信仰依然被大众视为医疗卫生科技外应对疫情的主要手段,另一方面由于科技发展和社会变革,以新视角看待民间信仰在疫情中的作用也成为可能。因此,这一时期的温州不仅保持了自身丰富的民间信仰资源,还保留下许多客观记载疫灾与民间信仰关系的历史文献。梳理这些文献,考察疫情中的民间信仰仪式当代遗存,对正确认识民间信仰在疫灾中扮演的角色,探寻疫灾影响下民间信仰的变化、发展规律,甚至在当代抗疫语境下引导、发挥民间信仰的积极影响,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疫灾袭扰下的温州与民间信仰
温州位于浙江东南部,东部濒海,其余三面多山,属地多丘陵、水道。四季分明,降水丰沛,为较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尽管温州地区气候温和,环境宜人,但大规模自然灾害频仍。尤其在近现代,文献有记载的天灾人祸几乎每隔一两年就会发生,城市地区如此,农村区域更甚。此外,频繁发生的大规模灾害,让中央政府不得不以外来移民补籍的方式来稳定人口。不稳定的生活环境和多文化背景的移民群体,使得温州人无论身处城乡,都拥有强烈的信仰需求,并以此来求得心理上的宽慰。
早在南宋时期,温州因宋室南迁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科学技术与医疗卫生条件与中原发达城市相比并无太大差距。到清中后期,温州城区的整体卫生状况优良,建有高效完善的下水系统,城区空间开阔,环境整洁,绿化率高,被时任瓯海关的外籍医员玛高温(Dr.D.J.MacGowan)称之为“帝国最干净的城市”[1]38。但尽管如此,近代以来,有文献记载的带有传染性的瘟疫灾害却仍然在温州地区多次爆发。根据当时瓯海关《医报》的记载,温州的疫灾大多是在因季风气候变化导致的过量降雨和干旱,以及频繁的自然灾害诸如台风、泥石流或是饥荒之后,以次生灾害形式出现的[1]。温州近代以来出现较多且影响较大的有霍乱、天花、鼠疫、疟疾等烈性传染病,此外,伤寒、痢疾、脑炎、登革热等传染病也曾见诸史料之记录。在清末记录温州口岸医疗卫生情况的瓯海关《医报》中,经常能看见外籍医疗人员对温州爆发的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的记载[1]。甚至在英国驻沪领事馆办《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中,更有不少有关温州的报道直接以“霍乱”作为标题[2]。传染病导致的疫灾对温州的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正是由于疫灾横行,本已“好事鬼,多淫祀”的温州民众,更有理由选择以其长期仰赖的民间信仰来为饱受疫灾苦难折磨的现实生活带来精神安慰。由于温州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性,民间信仰已成为当地民众生产生活中重要的部分。在科学观念和科技手段尚不发达的时代,发生重大的灾害,如瘟疫横行时,民间信仰会成为民众极度仰赖的对象。比如,自近代以来,温州历史上曾多次发生俗称“大㱦年”的霍乱疫灾,民间认为是瘟神作祟,因此每次疫灾之后,都要举行“搜耗”“送耗”等民间信仰仪式,将瘟神送走;除了送瘟神的仪式,民众还要向司职驱瘟除疫的民间神祇祈祷、献祭,期望以其法力祛除病邪疫灾,护佑人畜健康平安。尽管这些朴素甚至显得“迷信”的信仰行为在时代的前进和科技的发展面前已经被证实似乎缺乏应有的驱疫禳灾效果,但由于这一传统已经在民众心中烙下了记忆,成为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所以每到疫病流行时期,民间神祇在当地社会文化中常常会重新被提及。同时,疫灾也成了塑造温州地区民间信仰文化特性的重要因素,许多民间信仰的仪式、传说、戏曲,神祇司职的功能,甚至庙宇宫观中的用品、象征性实物,也都因为疫灾进行了重构。
二、与疫灾相关的温州地方神信仰
1.温琼信仰
1902 年全国霍乱大流行,温州府及周边地区为重灾区。在《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1902 年9 月24 日有关温州的报道中,“仅仅这一个城市,估计在过去两个月中已经出售了5 000—6 000口棺材,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那些因为霍乱去世的儿童……有两万多人在这场可怕的瘟疫中丧命”[2]112“这个灾害(霍乱)的破坏性甚至比佩雷火山或者维苏威火山爆发更加严重”[2]112。尽管现在认为当年的霍乱大流行是因为晚清时期人口剧增、交通发展、气候异常与战争匪乱等多重原因导致的,但是在公共卫生观念落后和卫生防疫体系缺失的大背景下,民众只能求助于民间信仰来获得精神慰藉。因此,在如此惨烈的疫情期间,除了清理水渠和处理污水坑等传统的常规卫生防疫举措外,温州的“东岳庙中汇聚了所有有影响的神灵,人们在这个城市里的每条街道游行了很多天,很多人在祈祷和吟诵”[2]112。
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疫灾,当时的温州民众在求医无门的恐惧中聚集于东岳庙,祈求庙中诸神灵驱疫禳灾。而在这些神灵中,最受民众崇拜的便是温琼。温琼又称温元帅、温太保、忠靖王等,是温州地区历史上最早的专司驱疫禳灾的神祇之一,由于历朝历代都获敕封,为官方承认的驱疫神,其在祛除疫灾方面的影响力和影响范围也较其他神祇为大。温琼的神像造型多为一青色皮肤的武将形象,青色皮肤因其吞瘟丸中毒导致,武将形象则是由于其为道教中的元帅。温琼的原型说法较多。宋时称温琼为平阳人,曾为唐名将郭子仪麾下猛将,为人公正中直,后化为东岳太保,因北帝欲命其降疫人间,温琼不忍,仰天尽吞瘟药舍身救民,顷刻浑身中毒肤色变青,玄帝念其心善,赦免其渎职之罪。至元代,温琼原型由武将转为书生。至正十五年(1355)宋濂在为温州华盖山下新建的忠靖王庙所作碑记中,称温琼“七岁习禹步为罡,十四通五经,百氏及老、释家言。二十六举进士不第,乃拊几叹曰:‘吾生不能致君泽民,死当为泰山神以除天下恶厉耳!’复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上神鬼。’言已,忽幻药异象,屹立而亡”[3],为一个际遇不顺而立志为天下人除危解恶的书生,但并无吞瘟丸救民的戏剧性义举。至明清,民间流传的关于温琼的传说,大多结合了宋元两个版本,虽有出入,但差别不大。多是平阳书生因夜读听得室外有恶鬼私语,欲投瘟丸于井中散播瘟疫,书生大惊,起身警告邻人却被嘲笑,便投身井中,亲身试毒以证清明,众人将其打捞上来时,书生已全身中毒青肿,暴毙而亡,众人感其大义,便将其祀为神明,专司驱疫禳灾,称“瘟元帅”,后又因温琼来自温州,有谐音“温元帅”,又以其在道家任东岳太保之首,因此又被称为“温太保”“东岳爷”。因其舍身救民的大义,历朝历代敕封温琼无数;又因其专司驱除瘟疫,在卫生条件落后的时代广受民众崇拜,不仅在温州地区深受敬崇,其影响力更“直达闽广、巴蜀而遥”[4]。在温州地区,只要有疫灾流行,民众都会自发前往拜祭温琼,以求其驱灾退疫。因此,在1902 年遭受重大霍乱疫灾期间,温州民众蜂拥至东岳庙祈求平安健康,尽管现在看来有聚集感染的危险,但其心理在当时实属正常。
2.陈靖姑等女神信仰
自清代晚期开始至中华民国一段时间,温州地区因台风海难、干旱洪水、兵匪祸乱等天灾人祸多发,加之人口暴增,交通发展导致人员交流繁杂,过度开发周边自然资源等原因,传染病大流行的概率不断增大。此时,民众虽对现代医学的接受程度逐步增长,许多代表了“封建迷信”的道教、佛教等主流宗教的宫观庙宇在“德”“赛”二先生的冲击下逐步走向衰落,但作为面对疫灾时的重要心理依赖对象,民间信仰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尤其在“庙产兴学”事件层出不穷背景下,民众的强烈信仰需求向着更加草根的层面倾斜。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时代,面对时有发生的疫灾,具有驱邪除疫功能的女神也受到了民众狂热的追崇。
温州民间信仰中的女神众多,扮演的多是护产送子,或是贞烈孝女等角色。其中,来自福建的女神陈靖姑,因其善于驱邪收妖、为民除害而被福建移民迁籍温州时一同带来。陈靖姑,又称陈十四夫人、临水夫人、顺天圣母、顺懿夫人等,其原型相传为唐代福建女子陈靖姑(或进姑、静姑)。陈靖姑学法斩蛇的收恶驱邪、斩妖除魔的传说,在进入温州地区后大受欢迎,并形成了地方上广为流传的独特曲艺形式——鼓词中的“娘娘词”(又称大词,即《南游传》)。作为移民的守护神,有着斩妖除魔传说的陈靖姑信仰不仅为移民在新家园开荒拓土提供了精神支持,同时也随着他们在实际生产生活需求以及温州本土信仰需求的变化,而产生功能上的变化。首先,移民开荒需要人力,人丁兴旺就成了新移民的首要需求,因而信众就开始将陈靖姑斩妖驱魔的女武神功能抛到一边,为其增添了求子保嗣这一重要功能。其次,围绕这一功能,信众又为其塑造了端庄美丽的女性形象,重构了陈靖姑在温州的信仰形象[5]。然而,温州地区天灾人祸频繁,其后次生的疫灾更是让民众受苦不堪,在民众们朴素的传统观念中,无论是灾害还是祸患,都是邪魔作祟妖孽作恶的结果,疫灾也不例外。因此,信众们在面对灾祸时,又会将原有的陈靖姑斩妖驱邪的功能强化,重新赋予其除疫驱邪的能力,并以其女性特有的慈悲济世的温柔形象,为信众带来心理慰藉,从而以表象化的象征意义强化其驱邪驱疫的能力。直到今天,每有疫灾发生,温州各地都会依据本地实际情况,请出陈靖姑来举办“唱大词”的仪式,举行“搜耗”“送耗”等仪式,以此来驱疫禳灾。
同样以慈悲济世的驱疫女神形象在温州出现的,还有观音。观音是佛教中的神,其名最早出自鸠摩罗什梵语译名观世音,女身形象则可以追溯至11 世纪的河南观音信仰[6]5。至16、17世纪,在“口语文学的发展和通俗书籍的出版”双重作用下,妙善传说留下了“流传最广及最久的形态”[6]61,成为了具有慈悲济世形象的女身菩萨,因其大慈大悲救民于困厄,加上传说戏曲的传播,使观音成为疫灾来临时灾民众最可依赖的信仰对象。由于民间信仰具有随意的特性,许多在民间有施药行医善举的佛道弟子往往会被视为其所信奉的具体某个神祇的化身,进而间接为某一神祇增添了除疫的信仰功能。如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被认为是源于宋代的观音种痘传说,就体现了这一现象:一位来自江苏的影响力巨大的年轻尼姑漫游到峨眉山,令“那个地区所有的女星都成为其信徒,随她斋戒、诵读经文和做善事”[1]85,同时,她告诉追随者,自己被指示要去传授天花接种的指示,并为附近的民众做了接种,从而避免了天花在此地的传播。在其名声传扬至京城后,宰相也邀请其为自己的儿子成功接种,事后宰相欲答谢她,却被其拒绝,并请求宰相为民造福。在返回圣山多年之后,这位尼姑告诉追随者自己其实是慈悲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其使命就是通过种痘来拯救性命,随即坐化而去[1]85-86。从这个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观音慈悲的信仰形象在这一传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并拥有了治病除疫的能力。这个观音化身为尼姑种痘除天花的故事被玛高温医生载入1883—1884 年度的瓯海关《医报》。虽然传说的起源不在温州,但仍可以看出其在温州地区也有所流传。事实上,温州民众对观音的崇拜自古以来一直非常兴盛,温州多地有观音寺、观音阁、观音洞,而各种民间信仰宫庙中,也大都有从祀观音。因此,在面对疫灾时,温州民众自然更有崇拜观音的理由和条件。
除了陈靖姑、观音外,在疫灾来临时,妈祖也是为温州民众所崇拜的女神之一。同陈靖姑相同,妈祖也是来自福建的女神,有天后、天妃等称。妈祖信仰在温州更多是为洞头、平阳、苍南等沿海地区福建移民族裔所崇拜。妈祖起初是一位海神,保佑出海平安,然而在疫灾来临时,受其困扰的民众也会向护佑平安的妈祖祭拜以求度过难关。赵钧《谭后录》就有记载:“甲申岁,温郡痘症大发。邑有吴士俊者,家仅一子,痘出如蛇皮,医者束手。其妻披发泣救于天后娘娘,一步一拜,至庙哀求。分香火,亦一步一拜,归供于家。”[7]
在温州,民间信仰的随意性体现得较为突出,各位女神虽然基本司职不尽相同,但在疫灾来临后,都会为信众提供除疫禳灾的庇佑。如永嘉卢氏孝女信仰,其历史原型为唐代孝女卢氏,因代母投虎口而死,被宋理宗敕封“孝佑”。乡民初以其孝悌称道而立祠祭祀卢氏女。因永嘉地区深入山地,男性劳动力需求较大,且山区缺医少药,医疗卫生条件恶劣,产妇难产、儿童夭折或死于天花、麻疹等疾病的十分常见。因此,来孝佑宫求子保育和驱疫保健成了信众对卢氏孝女的主要信仰需求。
同样司职孩童驱疫保健的女神还有花粉娘娘,民间传说这位花粉娘娘姓柳,又称柳氏圣母。柳氏幼时父母双亡,为徐姓人家收养。后为避元明兵乱迁至福建,以采药行医为生。朱元璋兵下赣闽时,麾下士兵染上瘴疫,被柳氏所救。朱元璋称帝后深念柳氏解困之恩,欲加以赏赐,却获悉柳氏因攀岩采药坠崖身亡的消息,由于其所采花粉救治幼童无数,遂封柳氏为花粉娘娘,专司保育护童、医药“收宝”(种痘、麻疹等)。每到儿童多发麻疹、天花时,信众都会前来祭拜。
3.其他驱疫神祇信仰
除了上文提到的观音、卢氏、柳氏等女神外,在温州地区还有一位被称为张三令公的专司放花种痘的男性痘神。张三令公信仰在温州地区极为普遍,几乎大小宫庙都有从祀,民间有染天花者,均会前来祭拜张三令公。温州民间普遍认为张三令公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据传是他带入西域的天花病毒,但因其为人正派,民间依旧尊其为神,求其驱瘟避疫保平安。然而张骞卒于前114年,中国最早关于天花的记载为晋人葛洪《肘后备急方》中的东汉建武年间(25—56)病例,因此张骞一说当是民间附会的结果。在乐清,张三令公的起源有另一说,其原型为陈十四麾下张三。民间流行的《陈十四传奇》中,有两则关于张三和天花的故事:一为扬州马容得罪张三染天花暴毙;一为洪江渡林九与张三发生冲突染天花而死。可见张三令公原为散播天花者张三,被陈十四收复后,专司种痘,治愈天花患者。
温州各地几乎都设有祭拜关帝之处。关帝即关公,三国蜀将关羽,因其忠义无双,朝廷、民间都有崇祀。因关帝又被称为“武圣”,英武忠勇,故在温州乡村,一般会将关帝庙或祭祀关帝的位置设在水口处,以其英勇之姿抵御疫病与邪秽于村外。在疫灾来临时,乡民则会祈求关帝驱邪除疫。
明万历年,闽籍进士林应翔任永嘉知县,亲历“瓯数十年来苦疫,每春夏之间盛行,气能传染”[8],立志根除疫病造福一方,遂以施药请医,巫祝傩逐双管齐下,仍收效甚微,于是认为应祭祀瘟鬼,便募捐集资,在海坛山一侧天宁寺旁建五灵庙。所谓五灵,即对应《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中的“五瘟使者”,又名“五瘟神”,分别代表了五种瘟疫。林应翔称“瘟有五,是五行之沴气也”[8],这是根据五方五土和五行思想产生的鬼灵概念,民间常与五通、五猖混用。严格意义上讲,五瘟、五通一类位格低下,不属于神祇级别,但“当瘟疫发生时,无论官府还是民间,五瘟神都受到普遍信仰”[1]37,因而建庙祀之,祈求其不要散布疫灾,从而在另一个角度起到消灾除疫的效果。
三、应对疫灾的民间信仰仪式
1.搜耗与送耗
温州地区因自然环境及季候影响,易成疫病流行之地。在疫灾频仍的背景下,温州的民间信仰仪式也处处体现着消灾除疫的内涵。这其中,针对疫灾的最典型信仰仪式,就是搜耗与送耗。所谓搜耗,即请司职驱疫的神祇出位,由信众抬着四处巡游,借以“神力”将祸害一方的瘟疫邪魔尽数收服;送耗,则是通过仪式将神搜来的瘟疫邪魔送走。1902 年霍乱大流行期间,深受疫灾之苦的温州民众涌入东岳庙祈求温元帅护佑,并筹集资金举行驱瘟禳灾的仪式。《北华捷报及最高法庭与领事馆杂志》1902年9月24 日的报道中,就对此次仪式中的搜耗和送耗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人们希望这些神灵(温元帅及其配祀神)能够在夜里护送来访的瘟神去河里。……一起护送陪伴的人群高达5 000—10 000 人,每个人都提着一个挂在长长竹竿的尽头的灯笼,或者是一个燃烧的火把。游行者都是男人……每个人都在声嘶力竭地大喊。”[2]113“到达河岸后,船被快速送出,一个船夫猛地一拉,同时其他人已经做好准备将这只纸船送到水里,这些瘟神很快就会被送到烈火笼罩的地方。这个纸糊的大船被送入水中后,在所有的灯笼熄灭之前,所有人都快速溜走,从另一个城门回到市里,那些邪灵就不会随着他们回家。”[2]113
这种搜耗和送耗仪式,体现了温州民众对疫灾的认识。他们认为疫灾的发生是因为邪灵恶鬼在作祟,或是象征瘟疫的瘟神在散布疫病,所以只能通过请司职驱疫等神祇如温琼以神力收服邪鬼瘟神。然而收服来邪鬼瘟神,又怕其报复民众或是留恋当地不肯离去,便又以神戏娱之,置备纸扎的大船,装满纸制的金银财宝和经卷,待神戏结束将邪鬼瘟神们接上纸船送进水中,让其离开当地前往更富庶的纸醉金迷之地别再回来。有意思的是,在温州举行送耗仪式时,信众相信载着瘟疫邪祟的船将驶往扬州,因为扬州是一个更为富裕、更华丽的好地方;而在温州旁边的处州(今丽水)一带,同样存在的送耗仪式则是将载着瘟疫邪祟的大船送往下游更加富裕美好的温州。
当代温州仍然延续着这种传统的送耗仪式,且与一百多年前相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更多时候,民众们会请词师演唱陈靖姑收妖附魔、驱瘟除疫的“大词”,歌颂其功绩的同时,将搜来的邪鬼瘟神送上纸扎小船,寻一处僻静之地以火化之。
2.赎罪
面对疫灾,集体层面以送耗仪式来消疾避祸,个人层面则可以选择“赎罪”来消除恶疾。温州民间的“赎罪”之俗,又称“扮犯人”“扮罪人”,多见于春节、三月三、七月半等日的地方神巡游队伍中。“犯人”或“罪人”们,或戴枷锁,或坐囚车,往往处在队伍中间醒目的位置,由狱卒“押解”着绕境一周。犯人或罪人的扮演者,多是饱受疾病之苦(或是家中有亲属患病已久)的信众。温州民间认为如有人染疫病久而不愈,多是身有罪孽冤结所致,必须在神前游街赎罪,方能痊愈。这类罪人、犯人,通过扮演犯人套枷锁坐囚车,或是以模拟刑罚等仪式,以求赎清前世罪过,来治愈现世感染的疫病。同时,赎罪也是通过模拟的形式宣传信仰中的“诸恶莫作,诸善奉行”“善恶有报”等思想的特殊手段。直至今日,依然能在龙湾宁村七月十五汤和巡游、瓯海茶山元宵巡游等活动中看到赎罪这一仪式。
除了扮演犯人、罪人赎罪外,还有一种看起来近乎自虐式的赎罪活动,其历史也非常悠久。1881年瓯海关《医报》中就记载了这一被称为“挂肉灯”的赎罪仪式:“在温州城,当地百姓为了除疫,甘愿忍受巨大痛苦,以证明他们的赤诚。他们会手持高温的花瓶,……用钩子挂在自己手臂的肉上。”[1]38与前文中扮演犯人和罪人的信众相似,以挂肉灯赎罪的信众认为只要忍受此种疼痛,就能达到驱除病疫的效果。为了更彻底地忏悔、赎清罪过,挂肉灯的“罪人”,甚至还会在灯下挂上石盘等重物,以增加重量。直到现在,这种挂肉灯赎罪驱疫的仪式在温州地区依然存在。
四、结语
面对温州地区史上频发的疫灾,温州的民间信仰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不可思议的丰富内涵。受疫灾之苦的民众通过民间信仰能在精神上得到慰藉,部分掌握治疗疫病技术的医僧、医道、医巫通过民间信仰增强治疗效果,组织抗击疫情的政府能通过民间信仰安抚、疏导和积极干预受灾群体心理,体现其在民俗活动中的“国家在场”等, 这些都体现了民间信仰在抗御疫灾时展现出的积极作用。直至今日,仍然能在现代医疗卫生技术作为抗疫主力的战线上看到民间信仰的身影。在2020 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重疫区武汉市,为抗击肺炎建设了“火神山”医院,或许是巧合,“火神山”正应对了传统民间信仰中五行对应五脏,以火神山之“火”克肺炎之“金”的五行理念。而在这之后,将抗疫专家钟南山和李兰娟两位院士画成抗御疫灾于门外的门神美术形象也于网络上迅速传播,这是否并非仅仅是善意且带着敬意的网络“游戏”,也可以被认为是与史上因疫情影响敕封神祇相似的“造神运动”?无论是火神山医院的命名,还是两位院士的门神形象,都可理解为疫灾影响下民间信仰文化的现代遗存,也说明民间信仰在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断演变、延续和传承,继续为抗疫除疫发挥积极的影响。
当然,在面对疫灾时,民间信仰产生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参与者众多的民间信仰活动,往往会产生人员聚集的行为,这在传染病流行期间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此外,因民间信仰中存在迷信落后的一面而引起的骚乱、恐慌,诈骗、劫掠,谣言传播等,都可能会为疫灾影响下的社会雪上加霜,带来恶劣的消极影响。这些消极影响即使在今天,也同样须在抗击疫情中引起重视。